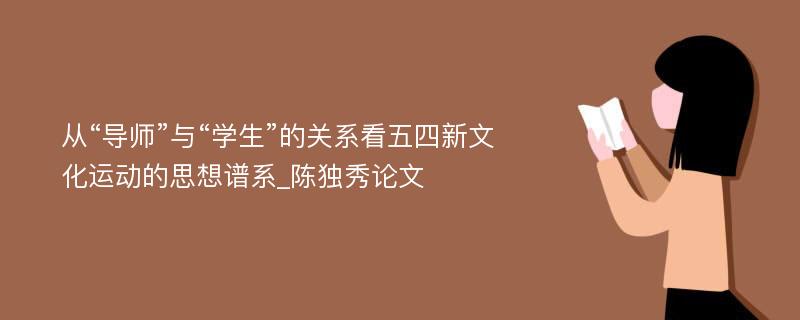
从“导师”与“学生”的关系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谱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谱系论文,导师论文,思想论文,关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2)01-0067-04
这里的“青年”即是“五四”先驱当年立意“辅导”、“铸造”的富有个性自由、民主理想之“新青年”。[1]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都曾以不同的思想方式赢得了青年学生的信任,因此成为“五四青年”当之无愧的导师。“五四”高潮过后,当鲁迅应邀为“青年必读书”的“导师”时,他内在思想理路的演绎以及对与自己不同类型导师的微词已足以说明本文“歧导”命题的确凿性:“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2](p56)我们这里关心的是:五四青年如何在导师“个性自由”的笼统意念下走向了不同的归途。
一、共识:朦胧启蒙理念下的“人”意
从“戊戌”开始,尤其是经过辛亥革命惨痛的一幕,寻求真理的先觉就已经切实体验到了“国民性”问题的严肃性与当前性。历史的车轮驰急“五四”,思想界同人共执一个逻辑平台:由“立人”而立国。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平台,所以留美归国的胡适在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击掌”达成一个“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君子协定时,就有了不同的思想潜流。恰恰是由于“五四”同仁保持了各自的个性,才共鸣出了和谐的时代强音。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所说:“对立造成和谐,正如弓与六弦琴。”[3]
启蒙的核心内蕴无非就是我们上面所述的个性自由、思想解放。而这一切又必须从启蒙运动的个人主义思潮说起。就西方启蒙运动的发生、发展源流来看,18世纪的思想狂飙首先在法国突起,后在欧洲蔓延开来,英国、德国等都是其精神传统的受益者。然而,必须看到,由于以卢梭为首的“启蒙”对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引渡和点燃,“瘟疫般流行”的负面效应使个人主义在法国自19世纪以来成为最不受欢迎的思潮。与法国理性自负个人主义对应的还有德国的完全反理智的个人主义。欧陆个人主义就在一味夸大理性、感情、意志的关怀中走向了否定个人权利的唯理主义建构。这也即是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批评的失真的个人主义。相形之下,英美传统意义上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则发展出了以宪章、自由为前提的纯正个人主义。[4]陈独秀在认定了“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端在“个人本位”与“家族本位”时就如此表述道:“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英、美如此,法、德亦何独不然?”[5]这样,西方个人主义形成的历史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别差异就“一笔勾销”了。不是有意模糊,也不是择一而从,只是在思想意念上的朦胧向往。这从具有浓重崇法情结的陈独秀对英国思想传统代表洛克(John Locke)人权学说的大力“启蒙”以及对自由颂歌美国国歌《亚美利加》的译介就可以读出大义。在其节选的《现代文明史》译稿中有言曰:“陆克(洛克——引者)以为……人权者,个人之自由也,家主权也,财产权也。”[6]著名政治哲学学者高一涵在英法思想传统之间的左右摇摆已经将“五四”先哲意念的模糊直观地再现了出来。他在《新青年》上撰写译介的文章诸如《民约与邦本》、《自治与自由》、《读弥尔的〈自由论〉》的意义也多是让人了解了中国老庄以外还有很多精彩纷呈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著作。与陈独秀精神气质极其相似的李大钊在大谈革命及其流传的同时对英伦传统里崇尚调和、宽容、妥协思想的汲取,又与胡适浓浓地胶合在了一起。在他那里,世界之进化,全为激进与保守二种思想所“调和”并驰以行,“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二者缺一,进步必以废止。”[7]胡适,一位英美气息十足的学者,《新青年》最初几卷的英美传统思想可以说尽是他的主意。除却他那“健全的个人主义”的公然申明,他对英人莫烈(Morley)的笃信也是掷地有声:“友人以英人莫烈之《调和论》相假,读之不忍释手,至晨时二时半始毕,手抄数节。”[8]
二、歧义:启蒙导师的“意念之差”
胡适的“巧夺天地”在《新青年》前两卷隐形潜行。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在24篇介绍西方启蒙主题的文章中,有18篇是以英美个性自由思想的舆论,其中有关法国启蒙思想的文章只占6篇。即使是陈独秀、李大钊那些法国情结浓重的激进分子也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新文化运动在前期的方向应该说是胡适的方向,而不是陈、李的“天地”。
不过,陈独秀的感觉是敏锐的。面对西洋“各国之教育方针”,[9]陈独秀对法兰西民族文化传统情有独钟:“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之“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在这一点上,他和自己推崇的人物尼采的观点不谋而合,对“法兰西人历世创造之天才”的判断坚信不疑[10]。表现在“文学革命”方阵里,陈氏有着同样的“恋法爱德”情结:在一篇推介欧洲文化以及文学大师的文论里,12位思想先驱竟有8位是法德籍的。饶有趣味的是,文化哲人每个国家平均是4人,单单文学界的6人中也是平均分配为2人。为文学新生而设计的“革命”、“推倒”、“宣战”的套路以及“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的激情,[11]都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一个相同的内涵:与法德个人主义传统密切相连的欧陆自由主义理路已经成为陈独秀们不二的激情归途。[12]
在这一归途中,以寻求“新”字号为理想的浮躁情绪弥漫了思想的天空。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以导师自居的陈氏更是毫不懈怠。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居高临下地说道:“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13]接踵而来的是,“民国六年”“不谈政治”的“理想”承诺很快变成一纸空文。为此,胡适曾进行了自觉地抗衡。陈独秀一贯的“国内大事记”和“国外大事记”在胡适入盟后的改变就已经说明了问题。此后以重视经验、“研究问题”、“输入学理”为方针的编辑思路使《新青年》的学术色彩很快强化。随着法俄革命色彩在杂志上的染浓,为了缓和同人内部的冲突不致使团体分裂,1918年出台的《每周评论》就暗示着“问题”与“主义”的紧张。李大钊为息事宁人还写信给胡适道:“在这团体中,固然有许多主张不尽相同,可是要再想找一个团结像这样颜色相同的,恐怕不大容易了。”[14](p936)
如果说办刊宗旨的龃龉是“纸上谈兵”,那么具体到他们对理想中“新青年”的“铸造”、“辅导”、“教育之方针”就有点“真刀真枪”的火药味了。《敬告青年》里“新青年”资格认定标准就是以无畏“牺牲的精神”为人格道德、以“直接行动”为标准的[15](p74-78)。而胡适们则以书生式的“消极”见长。《文学改良刍议》中的谦逊、温和之绅士风度与陈氏的“文学革命”性情有天壤之别。[16]对“最爱专制”的社会“怎么办”这类关键问题的回答也难免使学生失望。[17]他给青年指引的方向完全是内倾、退缩、自御的消极路径:“其余的事都算不得什么……最要紧的是救出自己。”[18](p15)“健全的个人主义”演绎出了“独善其身”的修身逻辑。
1919年春,杜威来华演讲。他将西方的两种政治自由传统作了较为完整的转存:“洛克的学说,主张三权分立;立法司法行政并立,不能偏重,偏了就是专制。这是英国人相传的见解。卢梭既立法为最重要,故不信代表制度,以为人人应该参与立法。……这是极端的民主政体。”“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的理路泾渭分明。[19]学生很快盗了老师的版:“民治主义在法国偏重平等;在英国便偏重自由,不认平等;在美国并重自由与平等,但美国所谓自由,又不是英国的消极自由,所谓平等,也不是法国的天然平等。”[20]这两种民主与自由的干系也就是今天的民主理论家概括的“一种是理性主义的、乌托邦的和理想主义的民主概念,另一种是经验的、描述的、制度的和程序的民主概念。”[21](p5)
三、走向:“十字路口”的历史选择
自“五四运动”游行示威的高潮过后,《新青年》思想内讧就一刻就也没有消停过。从编辑方针的“冷战”、文学理论的龃龉到“新青年”两种导向的歧异,中经“问题与主义之争”,达到了高潮。1920年秋,《新青年》南下,由于胡适对其“色彩鲜明”的分歧愈来愈大,而这时的陈独秀已经从“统一战线”的角度变成旗帜鲜明的“依照多数意见进行”、“不愿多说话”,[22](p133-p134)他们的矛盾便公开化了。1921年,胡适曾寻求同盟“联合抵制”,但这时的另一同盟却统统“不以为然”,时至《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导师们就分道扬镳、各自为政了。
导师之间的你追我赶咄咄逼人。运动降下帷幕后,陈胡的把舵意识猛长巨增。7卷1号上,胡适面对刚刚出狱、名声鹊起的陈独秀[23]之捷足先登就暴露出很强的抢滩意识。《新思潮的意义》对几年来文化运动的目的、手段、态度、意义作了周全总结。其中醉翁之意还是对文化运动走向的根本性部署。他在正标题下排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十六个大字,将态度、手段、意义都压缩进了字里行间。[18](p151)与此同时,陈独秀也以主将身份紧锣密鼓地赶制了《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战略性篇目。他以高屋建瓴的语气强调新文化运动要特别“注重团体的活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15](p515-p516)1920年11月,胡适挑头的“提高”与“普及”之争的帷幕拉开。带病出席的胡适针对“新文化的两方面”以《普及和提高》为题尽情发挥:普及“这种事业,外面干的人很多”,“不希望我们北大同学加入”。而具体到“提高”就不然了:“提高就是——我们没有文化,要创造文化;没有学术,要创造学术;没有思想,要创造思想。要‘无中生有’地创造一切。这一方面,我希望大家一齐加入,只有提高才能真普及。”最后他一再教导学生说:“我不希望北大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齐用全力‘提高’这方面做工夫。”[24](p418)就在胡适热衷“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普及性新名词之际,陈独秀以他人驳论胡适的话不到位为由发表《提高与普及》的两种感想说:“(一)大学程度要提高,同时也要普及。……(二)我觉得眼前不必急于提高……劝适之先生别高谈什么提高不提高。”最后,他质诸胡适曰:“我这两种感想适之先生以为如何?”不必讳言,“整理国故”只能是将自己关闭起来在“象牙之塔”里“提高”;“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也只能走向“十字街头”去“普及”。
1918年10月20日,以“学生救国会”为基础的国民社在北大成立,同年11月19日,以文化再造为主旨的新潮社也应运而生。随着青年学生的纷纷加盟,1919年初两个社团分别发起并创办了《国民》与《新潮》杂志。《新潮》最直接的指导者当是胡适、周作人、鲁迅。其成员傅斯年、俞平伯、杨振声、罗家伦、康白情,他们多注重思想、文艺的创造与传播,所办的刊物也充满“研究问题”之风,是较为完全意义上的个性自由、思想解放式的文化启蒙路子。相比较而言,国民社成员与陈独秀、李大钊更为亲近些。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人也激情满怀,属于关注时事、热血报国的那类男儿气质。他们将主要精力都投到了政论和社会活动上。
“五四”学潮渐渐落定之后,新潮社成员的一贯宗旨不但没有半点改变,而且对青年学生和群众运动的风起云涌产生了抵抗情绪。就连那些一度在“象牙之塔”与“十字街头”徘徊的学生也在顾问胡适的引导下纷纷向内转,退回书斋访古问史。为了“输入学理”,胡适在为杜威实验主义摇唇鼓舌的同时还力劝新潮社青年奔赴自由主义的乐园英美留学。正是这些学生在导师的谆谆教导下的文化选择才有了一批佼好学术种子的栽培与保留。傅斯年、杨振声、何思源、徐彦之等新潮社成员的远离社会,致使原有四十人的社团失去了中坚。
应该看到,胡适教诲学生的“提高”连先前思想启蒙的那点添加剂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有那点淡而又淡的学术余晖。傅斯年出国前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与同学共勉道:“(1)切实的求学;(2)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3)非到三十不在社会服务。中国越混乱,我们就越要有为学的耐心。”[26](p150)顺便指出的是,利用庚子赔款选派的留学生多留学英美,比那些热衷社会运动的浮躁而自费留学学生享受的待遇优裕得多。一边是在镀金,一边则是在打工。留学英美的新潮社成员在优裕的读书条件下减失朝气。1920年8月1日,出国不及半载的傅斯年之心迹流露颇能说明问题:“近来很不想做文章:一来读书之兴浓,作文之兴便暴减;二来科学上有些兴味,望空而谈的文章便觉得自惭了;三来途中心境思想觉得比以前复杂,研究的态度稍多些,便不能说冒失话;四来近中更觉得心里力extroversion(外向)的趋向锐减而introversion(内向)之趋向大增,以此不免有些懒的地方。”[27](p105)与新潮社截然对立的另一个走向便是陈李大纛下的“国民社”。他们一行对社会改造问题的注重使该社青年在谈论劳工、介绍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迅速走向了十字街头。
1919年10月12日,陈独秀出狱后的首次公开活动就是参加《国民》创刊周年纪念大会。他充满自信和热望:“希望贵社以后对于国民觉悟之程度务使其增高,一方面使具此觉悟者人数增加。”对该社成员一意侧重“国民运动”的举措他大为赞赏。不过,这里他的国民觉悟已不是原装的既定目标——“伦理的觉悟”[15](p108),而是带有民族伤痕、阶级怨恨、政治意识的觉悟。他将国民觉悟之程度的观测点进行了位移:一是爱国心之觉悟;二是政治不良之觉悟;三是社会组织不良之觉悟。陈独秀的避重就轻是显而易见的。
出席这次纪念大会的还有李大钊。他虽属沉默寡言,但“人类解放”之观测点却是登峰造极:“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诸根本此进行,将来对于世界造福不浅,勉旃!”[14](p101)正是在陈李的指引下,国民社开辟了“与劳动阶级打成一气”之路。“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出现也是他们栽培、灌溉的花果。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传播,1920年4月,平民教育社讲演团里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下工厂、进农村,走上了入场下乡的道路。当然,这种普及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隔膜、冷遇的尴尬总是难以避免。因此“偃旗息鼓”、“宣告闭幕”、“免开尊口”也是司空见惯的情形。确实,“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打成一气”决不是随便说说的口惠,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深入生活”、六十年代的“上山下乡”、“九十年代”初的一年体验是知识者一个时隐时现的永恒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