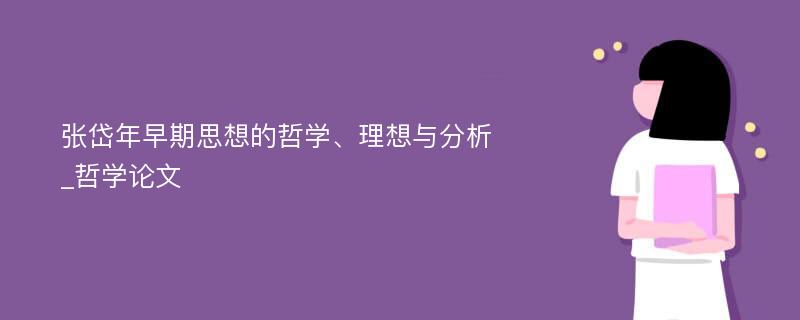
张岱年早期思想中的哲学、理想与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理想论文,思想论文,张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岱年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发表于1935年4月8日的《国闻周报》。该文对当时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系列问题,如应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应有什么样的应对社会危机的态度、需要什么样的生活理想等,都作出了深入分析。这篇文章连同这一时期发表的《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西化与创造》、《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生活理想之四原则》等一系列文章,奠定了张先生一生哲学思想的基础,是他后来许多重要观点的滥觞,甚至决定了其晚年哲学、文化研究的基调。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对哲学、理想以及逻辑解析的看法。
一、哲学与理想
张先生基于对上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精神状况的深刻剖析,认为当时最需要的是一种昂扬的志气、坚韧的精神,以及对民族文化的充分自信。他说:
中国现在需要新的人生理想。新的理想能给人以新的力量。无理想的人,必不会感到生活之意义。无理想的人,必没有与环境搏斗之勇气。唯理想能鼓舞人的精神,能坚定人的意志,能使人面对逆境而无所惧。(《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80页)
张先生明确指出,提出生活理想这个问题,是为了使处于文化存亡之际的中国人树立昂扬向上的人生态度,破除科技不如人便万事不如人的萎靡心态,振奋民族文化自信心。(同上,第328页)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危机的主要表现是知识界文化自信心的丧失和崇洋心态的弥漫,“许多学者、教授,一头埋在研究中,却忘了祖国。他们不想为祖国争光,为国家在世界学术界争地位,而只想替个人在世界学术界谋声闻。因而,他们的论文总想用外国文发表,而不思给国人读看;即或有所创发,他们宁向外人报告,而不肯令国人周知。这实是亡国现象之一”。(同上,第235页)他指出,学者、教授应负有文化创新、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任务,而在文化建设中,首要的是建立一种信仰、一种精神:“在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中,应有坚定的信仰,不挫的勇气,精进不息的精神。应坚信中国民族是能再度建设起光明伟大的灿烂的文化的,应能战胜无数的障碍困难而不为所阻,应能不断地努力而不以小成自足。中国民族应再度发挥其创造力。”(同上)
张先生还提出,在当时文化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势下,亟需一种哲学思想为中国传统文化争取地盘,对低迷的文化心态做出抗争,为未来文化的走向指明方向。他说:
现在中国需要一种哲学,本不始于今日,然而今日实乃尤急。不过却也有人不能认识这种需要。一般的识见总以为现在中国只需要科学工艺,当然科学工艺是现在中国所需要的,然而中国所需要的却非止于科学工艺。且如没有哲学,没有统一的思想系统,纵即学会了人家的科学工艺,恐也未足以建立一个独立的文化;而科学工艺或且被枉用以达到不正当的目的,有益的工具成了戕贼人群的利器。(《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37页)
张先生在多篇文章中都指出,当时中国的文化危机主要是国人对自己的传统失去了自信,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自惭形秽。不仅当时第一流的学者、思想家言必称希腊,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看得一钱不值,就是一般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也对自己的文化是否还有生命力发生怀疑。(同上)因此他认为,当时知识界的首要任务是提出一种哲学,一种能给国人指出光明前途的哲学,一种鼓舞国人信心、提振国人士气的哲学,这一点至关重要。他大声疾呼:
亡国有亡国的哲学,兴国亦须有兴国的哲学。颓废的思想可以促进民族之衰萎,有力的哲学可以激发民族的潜能。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乃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能给中华民族以勇气的哲学。须能从绝望中看出生路,从危险中看出光明,从死中看出生,从否定中看出更进的肯定。须能鼓舞人的勇气,培养人的斗争意志,激励人的坚韧精神。惟其如此,才能把中国从危亡中拯救出,才能有助于民族的再兴。在一时代能有积极作用的哲学,必是能助其民族应付新环境的哲学,有变革现实之力量的哲学。(同上,第239页)
张先生之所以反复呼吁、召唤新哲学的诞生,是因为在他看来,当时国人没有看到哲学的力量和哲学的用处,常常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只有科学才是手中的利器,才是应付时代危机的最好工具,才是使中国走向强盛的根本,这正是国人短视、狭隘、自卑诸病症之所在,他们不知道西方诸强国的哲学在其强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指出,意识虽然受生活的决定,但理论却可以做实践的前导。没有理论做指针的实践,常会是妄作无功的。(同上,第237页)他还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是适合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形态。古代思想虽已是陈迹,但它里面包含有真理的因素和永恒的价值,可以为当代人提供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智慧。西方思想是生活在西方的人的知识结晶,未必能给当时的中国人提供直接的精神养分,未必能直接满足国人的精神需要。中国人必须创造出适合当下中国人需要的哲学。(同上,第238页)
张先生提出,中国当时需要的哲学有四个条件:其一,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和西方哲学的长处组成一个大的系统;其二,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以力量;其三,能创造出一个新的一贯的原则,能建立新的哲学方法;其四,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结合。(同上)
对于第一个条件,即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综合,他作了如下解说:要想综合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古老而延续不断的这两大哲学系统,先要对之进行抉择。对中国古代哲学,要择取其精粹,然后将其发扬光大;对其中不适合现代生活的部分,必须革正、改造。对西方哲学,则要批判吸收。这两项任务是中国哲学界的责任,不能推给外国人。特别重要的是后者。要吸收西方哲学的长处,首先是要迎头赶上。所谓迎头赶上,就是以现代西方哲学所达到的水平为基础,作更进一步的发展,不重演西方哲学所经过的阶段。这方面德国哲学对英法哲学的赶超是最好的例子。西方哲学的某些偏向,特别是它的西方中心论及因此而有的对东方哲学的轻视,是一定要破除的。(同上,第239页)他强调,综合不是混合或调和,而必然是一个创新,必然有一个新的一贯的原则作此新哲学的根本,为此新系统的中心。这个原则必不是从别的哲学中取来的,必是新创的。有了这个大原则,才能成立伟大的哲学。没有新方法、新工具是创造不出新哲学的。(同上)这些观点是他晚年倡导的“综合创新论”的基础。
张先生还提出,满足以上四项条件的哲学应当具备四个特征:(1)从某种意义上说应是唯物的;(2)是辩证的;(3)应具有理想性;(4)是批评的。(同上,第240页)其中第一点唯物论和第二点辩证法,是张先生一贯坚持终生不渝的。他对“唯物”和“辩证”有清楚的说明。关于“唯物”,他说道:
心不能离物而有,物总是心之所待,这是稍有客观态度的人所必承认的。理想须根据现实中的可能:理想固是要对现实加以改造,然而却亦为现实的条件所决定;离开物的基础而只谈理想,不过是空想而已。把宇宙、人生理想化,讲先于自然统乎一切的大心,也不过是自欺而已。(《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40页)
这是从常识的角度,从一般人所无数次经验而居之不疑处立论。它是张先生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张先生曾说:“凡一理论,在感觉经验上及生活实践上有充分征验者,亦即能最简捷又最圆满地解释感觉经验并生活实践者,方是可以信持之理论。感觉经验与实践两不足征之问题,便应在讨论之外。”(同上,第352页)对于这一点,他在多处文字中反复论证。张先生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对立论根据的实在性要求很高,不喜神秘的、玄想的东西。虽自谓如扬雄“默而好深湛之思”,但此“深湛”建筑在“无征不信”,即对经验性的东西作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离开经验,纯靠纵思绪、骋想象、逞臆见的东西,他皆斥而不言。(同上)
关于“辩证”二字,张先生后来所言甚多。在《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中,对辩证法只大略提到,未作详细论证,但已提出了它的一般法则,尤其重视对立双方的斗争与和谐。张先生说:
新哲学欲能综合各哲学之长,欲了解宇宙人生之实相而无所蔽,则更必须是对理(dialectical)的。必能见两之一、对之合、相反之相成、矛盾之融结,以及一之两、合之乖、统一中之互违、谐和中之矛盾。如此方能兼综众善,方能融会异见,方能免于顾此失彼,方能不至以偏赅全。对理是解蔽之术,是综合之方。而且,欲能挽救危亡,转弱为强,其哲学尤须是对理的。对理原是对待厄运应付险夷的法门……善用对理,乃能死以求生,死中得生。(同上,第241页)
此中之“对理”法,即“辩证法”。辩证法一词在当时十分流行;辩证法的内容也多一致,无论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还是贺麟新心学的“矛盾法”。(《〈黑格尔学述〉译序》,见贺麟,第653页)张先生此处所谓“对理”法,皆对立面的统一。而通观其辩证法,则多讲“两一”。如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中,他谈到唯物论的人生论应注重的五个方面:天与人之两一、群与己之两一、生与理之两一、义与命之两一、战斗与谐和之两一,皆用“两一”而不用“辩证”。(《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76-277页)这里明确表示出张先生对张载思想的偏爱。张先生在中国哲学研究上的一大贡献,是他在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两大派之外,提出了以张载、王廷相、王夫之为代表的气学派。(同上,第8卷,第590页)他对张载的“两一”学说十分赞赏,认为是辩证法的集中表达。(同上,第2卷,第152页)他还对张载的“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正蒙·太和》)以及“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此天之所以参也”(《正蒙·参两》)诸说深为服膺,认为是唯物辩证法的集中体现,故此处宁用“两一”而不用“辩证”。(同上,第272页)
对于中国当时需要的哲学,张先生提出“理想的”来做第三个特征。“理想”二字在张先生的体系中用法不同,要稍微费些周折来分析。张先生一生持守唯物论甚力,不接受唯心论。而“唯心”二字的英文idea,许多人译成“理想”。张先生的“理想”却不是哲学上的“唯心”,而是一般所谓“理想”,即对未来的想往、筹划,它同时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以力量。张先生对“理想”二字解释说:
然而承认物质实在为根本,却并非甘受物质现实的限制,更须敢于变革现实,克服现实。一个伟大的有力的哲学,必能悬定伟大的理想,不敢悬理想与不敢看实际,是一样的病态。人群是必有一个伟大的理想作其努力的目标,以一卓越的当然原则作其努力的目标,以一卓越的当然原则裁制其生活,然后才能有所成。一个民族,必须有值得为之牺牲的理想,人民更必须有为理想而牺牲的精神,然后这个民族才能强盛。有这种大理想,才能促起人们的努力,才能鼓舞起人们的勇气。有了这种大理想,人们才会觉得人生有意义,才会觉得人生有价值;没有这种大理想,人们会感到空虚、无谓,因而萎靡、堕退。这种大理想,是一个健全的民族所必须有,而宣示这种大理想者,当是哲学。(《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41页)
此处之“理想”,不是“理想主义”(idealism)的理想;理想主义的“理想”可歧作“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是张先生深恶痛绝而必欲去之的。此处的“理想”是对未来的美好设想,是鼓舞人们突破限制使之达于更高标准的内在动力,是克服萎靡、堕退、消极诸精神障碍的良方。这样的“理想”是张先生的综合哲学必不可少的要素。所以,张先生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中提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同上,第262页)
但张先生又有“理想主义”的提法。所谓理想主义,一是指“唯心主义”,二是指唯心主义中重视心的能动作用这一点。前者如他在写于1936年的《人与世界》中提到的,“反哲学”的哲学除神秘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外,还有“理想主义之一部分”。张先生说:“理想主义中,证世界之美好,证上帝之存在,证心之不朽等理论,应划出哲学自成一科,乃哲学宗教之混合,其目的非在求真,乃在证明预存之信念。以前将此参入哲学中,哲学实深受其大害。哲学最须解蔽,此则自始即存一种目的。理想主义之大部分理论本属虚谬,而此部分理论更非哲学。”(同上,第351页)此处之“理想主义”,指“唯心主义”;“理想主义之一部分”,指宗教哲学。唯心主义中的宗教哲学部分,固为张先生所反对,想将之驱出哲学领域,而“理想主义之大部分”,也认为其虚妄。理想主义为张先生所认可的,只有其中张扬人变革社会的力量、征服自然的勇气、鼓舞人之士气、增进人之信念这一部分,即他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中所谓“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那个“理想”。后者如张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这个综合的哲学,在性质上则是唯物论、理想主义、解析哲学之一种综合。”(同上,第278页)此处之“理想主义”,实则取唯心主义之基本原则,即重视人变革世界、变革社会的决定作用,重视悬一理想于前作为努力奋斗的目标、旗帜之鼓舞人心的作用,而不以理想主义之基本原则为宇宙观之出发点。所以须知,张先生不喜“唯心主义”这个词,宁可用“理想主义”代之;而关于理想主义,又不是对其全部,而只是对其中的一部分感兴趣。他欲取来作为他的综合哲学的一部分的,只是其中他认可的合理部分:“理想”。张先生的哲学出发点是唯物论,这是他的新的综合哲学的基础。
此外,对“理想主义”,张先生也讲到其补充唯物论的作用。如他一再提到,在他的新唯物论中,宇宙是一个历程,这个历程中的存在是有等级的;这个等级最基础的是物,为其出发点;再其次是生,即承认宇宙具有生机;再其次是心与社会。(参见同上,第264页)在写于1948年的《天人简论》中,张先生也有“天人本至”、“物源心流”之说。“本”指本原,“至”指最高成就。“本至”之义多取进化论:“人固为物类演化之所至,然而仍须前进不已,日新无息,进复再进,新而又新,以达到更高更上之境界。”(《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216页)对“物源心流”,他则明确说:“物为本源,心乃物质演化而有,为支流,物源而心流。物为一本,生物、有心物为较高级之物。一本而多级。”(同上,第218页)张先生此思想是一贯的,其唯物主义基础不变;对唯心主义则仅看中其补充唯物主义的作用。如,张先生从中西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着眼,认为唯心论仅为其中间层级。第一级为原始唯物论时期,第二级为怀疑论和唯心论时期。怀疑论之发展为实证论,而解析派哲学即出于实证论。第三级是前二级之综合,即兼综唯心论、实证论的新唯物论。(同上,第265页)故张先生的新综合哲学,便是唯物、理想、解析之综合的新唯物论。对唯心论,张先生虽承认其远有端绪,且在哲学史上占据大宗之地位,但不能作为他的新综合哲学的基础。(同上,第266页)张先生曾对唯心论有如下之评价:“唯心论之根本观点是虚妄的,主观唯心论推至究竟必归于唯我论,绝对唯心论推至究竟必归于上帝创世论。然唯心论乃是哲学史上最发达之哲学,其理论最丰富,其系统最完美,故亦实非无卓然之贡献。唯心论之优长即有见于宇宙之賾,而不以简化为捷径,而其贡献尤在于认识人之力量,心之作用,能知理想之有力,而创立并宣扬伟大的力量以指导人类的前进。”(《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65-266页)很清楚,张先生对于唯心论,只取其“理想”;取其理想,也是将之融合到自己的新唯物论体系中,作为其能动的方面。他的基本思想,在“物为心、生、理之本,而无先于物者。物的世界即一切,无外于物的世界者,即无离物之存在。”(同上,第267页)所以,张先生认为所谓“唯物论”,其名称应为“物本论”(同上)。他的思想的特质,也应是物本论基础上的“列宁、孔子、罗素”三流合一。(同上,第8卷,第585页)
二、逻辑解析
张先生认为,当时所需要的哲学的另一大特征是批评。他所谓“批评”,实际上是他一贯倡导、也是他哲学的方法论——逻辑分析。(同上,第1卷,第240页)因为在他看来,哲学的本质即是批评。哲学必须运用理论思维,理论思维的实质就在于对概念、范畴加以批导、分析、紬绎,从中得出结论。他根据英国现代哲学家博若德(C.D.Broad)的观点,将哲学分为两种:一种是批评的哲学,一种是玄想的哲学。玄想哲学即通过玄妙观想、通过整全的直观的思想活动,进行新系统的创造。玄想哲学是建设性的,不是毁坏性的;主要在立,不在破。批评哲学即对具体哲学问题进行辨析性研究,此种研究是玄想性哲学系统建立的基础,是全部哲学第一步的、预备性的工作。(同上,第3卷,第7页)由此,张先生对哲学的看法便是:
哲学研究之目标,是建立广大而一贯的理论系统,然哲学家之工作亦不必专以建立系统为务。有时专门问题之探索,个别概念范畴之剖析,较之建立一个偏而空洞的系统更为重要。哲学家之工作,与其说是建立系统,不如说是探索问题,发阐原则,即仅就一部分根本问题而充分研究之。(同上)
从这里可以看出,张先生所谓批评实即分析。哲学即是分析问题的学问。分析是哲学的本质。所以,他视为理想的哲学,是以分析为方法的。他提出的一个自认为在当时最可行的综合哲学,就是唯物、理想加解析。哲学的最上乘为“致广大而尽精微”:“致广大”,靠唯物论与理想论;“尽精微”,则靠逻辑解析。所以他希望的哲学方式是:从事于系统的研究而能免于玄想,进行批评性的探索而能免于支离。(同上,第1卷,第271页)
张先生对解析法注重甚早。他进入哲学的门径就是西方的分析哲学。对此他晚年回忆说:“关于西方哲学,在吾兄申府之引导下,读了一些英文哲学著作。最喜读罗素(B.Russell)、穆尔(C.E.Moore)、怀特海(A.N.Whitehead)、博若德(C.D.Broad)之书,对于此派学者的逻辑分析方法甚为赞赏。”(同上,第8卷,第577页)张先生早期在学术文章中表现出的精细分析的路数,还得到中国分析哲学前辈金岳霖的肯定,所以一直坚持下来。(参见同上,第578页)解析是张先生最为重视、讲得最多的哲学方法。他一生所取得的成就几可以说全得自解析。从早年《中国哲学大纲》的写作中对逻辑分析方法的运用,到中年的“天人五论”对分析方法的阐述,再到晚年代表他一生哲学所得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等,在在皆贯彻了分析方法。特别是他27岁时写成的《中国哲学大纲》,是运用逻辑方法分析中国古代哲学的典范。以纵的方法叙述中国哲学发展历史的著作,在30年代的中国学界已经有了几种,其中最著名的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而以横的方法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国哲学问题的,当时尚无有。故张先生将此书的副题定为“中国哲学问题史”,意即在突出横向的、以哲学问题为纲这一点。在此书自序中,张先生说到撰写此书所用的方法,提出四点:(1)审其基本倾向,(2)析其辞命意谓;(3)察其条理系统;(4)辨其发展源流。(《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2-3页)这四个方面皆需要高超、严密的逻辑分析。比如他在对“析其辞命意谓”的说明中即明确指出:
对于过去哲学中的根本概念之确切意谓,更须加以精密的解析。古人的名词,常一家一谊。其字同,其意谓则大不同……对于中国哲学之根本观念之意谓加以解析,这可以说是解析法(analytic method)在中国哲学上的应用。(同上,第2页)
同时,他还以道、性、气诸概念在各派哲学中的不同用法为例加以说明。当然,同一概念在不同哲学家中意谓不同,这是世界各处哲学之通则。只要是能称得起哲学二字的,都得分析同一字面的不同涵义。张先生做得精绝、人不可及之处,在于他对中国哲学问题的分类及其间关系的说明。如将人生论分为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人生问题论;在人生问题论中又分义与利、命与非命、兼与独、自然与人为、损与益、动与静、欲与理、情与无情、人死与不朽、志与功十个方面展开论述。这种分法尤见出其对人生问题把握之深广,充分显示了张先生哲学解析的深厚功力。
张先生运用解析法,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将逻辑解析与辩证法结合起来。所谓“结合”,指逻辑解析需要辩证法,辩证法也需要逻辑解析。对此点,张先生自觉甚早。在写于1933年的《科学的哲学与唯物辩证法》一文中,张先生即吸收郎格(S.K.Langer)夫人的观点,认为逻辑解析最为哲学之擅场。因为有些哲学问题,仅凭逻辑分析其所含的概念就可以解决,如时空问题。还有一些哲学问题,单靠逻辑分析就可以知道此问题无意义,而置其于取消之列。但还有一些哲学问题,通过逻辑分析不能将其解决,却可显现出其中的矛盾而又不能证明其为虚妄,对此便可用辩证法去解决。而辩证法自身也需要通过逻辑解析来厘清问题,克服笼统颟顸之病。(同上,第1卷,第175页)张先生认为,当时中国哲学界最需要的就是用逻辑方法对中国固有思想来一番清理和分析。(同上)
中国哲学概念富于辩证色彩,讲究动态平衡,但又往往具有模糊、神秘、飘忽不定、边界不清、难以下定义诸特质。概念边界太宽不严格,往往易陷入诡辩,故皆有运用逻辑解析为之厘清的必要。(同上,第273页)张先生对辩证法与逻辑解析两方面因为应用不善而产生的弊病,有清醒的认识,他说:
辩证法似乎颇可以说为我们开拓了一可能之域,以前所认为不可能而加以封闭的领域,由辩证法乃明其为可能。罗素常说新逻辑扩大了可能之域,旧逻辑的大病之一在于太限制思想。辩证法是不是可说亦是最能打破旧逻辑之无理的限制的呢?……解析并不是对于事物强加割剖,原是“循物无违”之所必需。如物是辩证的,循物无违,自当不远其辩证的性质。同时,辩证法是不是需要厘清呢?逻辑解析则正是厘清的利器。在现在的情形说来,辩证法实在太需要厘清了。并且,也许非经严格厘清之后,不能为逻辑解析所容纳。(同上,第176页)
此中说到两个方面,一方面,辩证法对封闭的、拘限的旧逻辑是一个打破和拓展,使之由可能变为现实;另一方面,解析对原有的秩序、条理加以遵循,亦即“循物无违”。在这个过程中,对诡辩以及荡越无规矩、混乱无条理等貌似辩证实则无理的状态进行理顺、清整。在张先生的观念中,辩证法和逻辑解析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是哲学活动中的两个有力武器:辩证法是一种慧观,是认识事物的总的立场和态度,它适用于总体之观照;而逻辑解析是一种总的思想方法,处理事物的总的方针,也是一种剖析和分析具体事物的技术。就张先生不喜笼统、好深湛之思、长于深究细察地解剖事物这一思维特点来说,逻辑解析在他的整个哲学活动中居于首要之地位。张先生的特出之处,是他不但始终清醒地、自觉地运用逻辑解析,而且不断对逻辑解析自身进行理论上的阐发和论证。
张先生在1933年写过一篇名叫《逻辑解析》的文章,集中表达了他对逻辑解析的性质、功用、对象等问题的看法。文章开头即说到了逻辑解析的重要性:
哲学中的科学方法即逻辑解析(Logical analysis),或简称解析。逻辑解析可以说是20世纪初以来在哲学中最占优势的方法,而且也是最有成效的方法。多数第一流的哲学著作全是用逻辑解析法写成的。逻辑解析对于哲学实可以说有根本的重要。如欲使哲学有真实的进步,更不能不用解析。作哲学功夫,第一要作解析功夫。(《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77页)
张先生认为,逻辑解析是最基础的工作,但什么是解析则难以有确定的讲法,因为作为一种方法,许多哲学家都在运用,罗素所用不同于斯庖尔丁(E.G.Spaulding),石里克所用又不同于维特根斯坦。解析方法是发展的,不可以限于一隅。只可从总的方面说,它是反对思辨玄想的,反对由宏大的不能证实的想象来代替具体的可证实的经验。从根本上说,解析是一种态度,一种求真实、可验证、避免大而无当的态度。(同上)
从解析的对象上说,哲学上的解析对象并不是事物,而只是概念、命题、意谓。张先生认为,解析“乃是把不同的意谓分别开,把混淆的语言弄清楚。逻辑解析乃是考察常识中科学中的根本概念与根本命题的意谓。”(同上,第178页)“逻辑解析的目的乃是祛除混淆,不使不同的意谓混在一块。解析即厘清(clarify)概念与命题的活动。逻辑解析不是把整个的东西化为破碎的,乃是把混淆化为清楚。”(同上)如讨论本体论,就是将本体、一、多、规律、因果这类概念厘别清楚;讨论伦理学,就是把应当、善、正义等概念及这些概念构成的命题厘别清楚。这就是说,解析是一种态度,一种运思方向。张先生的这种看法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学人中相当普遍,特别是在重视西方哲学的学者中具有共同性。这是出于借鉴西方治学方法改造中国旧的治学方法和著述格局的需要。张先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解析方法和中国学者惯用的重视经验的思维趋向联系起来,把解析从仅仅分析概念、厘清意谓超拔出来,用它来分析经验。
他在分疏了逻辑解析的性质后,对解析与经验的关系特别加以强调:
然而逻辑解析并非不管经验,逻辑解析乃是对照着经验考察概念。所谓厘清概念或命题,也即是把这概念或命题对于经验的关系显示出来。从经验把这概念籀绎出来,把命题翻译为关于今有的简单命题。一个命题有没有意义的标准,即能不能在经验中加以验证,能在经验中验证,便是有意义,否则便无意义。只有在经验中能够加以验证,才是有意谓的;完全不能经验到,全在经验之外,无从判断其真妄,便只是无意谓。所有的有意义的命题都是能够翻译成关于今有或直接可知觉者的简单命题的。(同上,第179页)
这里,张先生的逻辑解析是服从于他的根本哲学观点即唯物对理法的。解析不仅仅是逻辑的,不仅仅要求概念命题的确定与清晰,还要看概念是否符合经验。也就是说,概念之真不仅是逻辑上的无纰漏,而且也是与经验之观察相吻合的。另外,概念形成过程即经验归纳过程,命题确立过程即经验间的关系的考察过程。所以他才有“逻辑解析乃是对照着经验考察概念”的要求,才有从经验中把概念紬绎出来、把命题转译为经验间的关系的要求。严格地说,这种解析已不是纯“逻辑”的,而是加入了经验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先生的哲学确实可称为“解析的唯物论”。但这个名称的内涵绝非外在的唯物论加逻辑解析,或形式上的列宁加罗素,而是从内容上、本质上对逻辑解析加以改造,使之与唯物论融为一体,使解析由形式、方法变为与内容不可分。而所谓经验,也是由对外界的朴素直观而获得。故对中国哲学史重视经验、重视素朴直观、不作纯思辨的逻辑分析,不由逻辑分析而推至极处乃至得出不近常理的结论这一特点,张先生也从展示和分析其优劣,转变为将其融合为其新唯物论的一个方面。
在逻辑解析之外、之后,尚有无其他思维活动?张先生给出的答案是有,那就是哲学性的慧观,即在解析基础上的综合。综合不是把诸多零碎的片段机械拼合为一个整体,而是在解析所获得的确实但分散的经验材料基础上的某种观照,由此得到的思想结论。慧观与解析是整体的思维活动的两个方面:前者为分析,后者为综合;前者指向个别,后者指向一般;前者是基础性的、工具性的,后者则是归宿、结论。两者不可离,共同完成一个片段、一个单元的思维活动。(《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79页)
这里,张先生既受唯物辩证法的影响,也受他所喜爱的博若德的影响。前者给他以相反者必相融的识度,将解析与综合这两个相反的方面融合在一个统一体中。这就是他说的:“在辩证解析之外,尚有辩证的综合,乃是看出两个相反的概念非绝对的相反而可相融,两个相反的学说、观点,亦非绝对的相反亦可融合。辩证综合与辩证解析在应用时,只是一个历程之两段。由辩证的综合,乃能兼摄各方的真理而不蔽于一曲。”(同上,第108页)而后者的影响在于,提出了哲学主要有两种:批评哲学与玄想哲学。张先生反复提到博若德这个观点,且认为此二者中批评哲学更为根本,并用作己之解析法立论之根据。不过张先生又接受了唯物辩证法,认为批评与玄想可融合为一:批评的哲学重在解析,玄想的哲学重在观照、得出结论。于是,在博若德那里截然两分的东西,在张先生这里统而为一了。
笔者在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在辩证的综合方面,张先生又受到了罗素观点的影响。在《逻辑解析》中说到解析之后的工作时,张先生说道:
逻辑解析也非否弃“慧观”,而且极需要慧观,所谓“哲学的慧观(Philosophical insight or Philosophical vision),在解析上实大有重要。逻辑解析最后之得结果,大概大部分是依靠慧观的。逻辑解析而至于无归宿、无结论,即由无慧观所致。没有哲学慧观,虽有精密缜细的解析,也难于有结论。慧观与解析乃是不可离的。(同上,第179-180页)
张先生在阐述他的这个观点之后,引用了罗素《人对外界的知识》中的一段话证明己说:“当用方法所能作的一切事情都已做完,便达到了一个阶段,在此只有直接的哲学慧观能奏效。此时所缺乏者乃是逻辑想象之某种新的努力,以前不曾想过的可能之把握……真正的可能,一般说来,一经想到,便会很迅速地以吸收表面上相冲突的许多事实之可惊的力量证明自己。”(同上,第180页)罗素所说的“当用方法”之“方法”,指逻辑解析;“逻辑想象之某种新的努力”,指解析基础上的综合。“吸收表面上相冲突的事实证明自己”,指哲学慧观。罗素主要是实证论者,但他也讲哲学慧观。张先生甚喜读罗素著作,不仅吸收了罗素的解析法,也吸收了罗素的“哲学慧观”。吸收哲学慧观不仅丰富了他所讲的辩证法的含摄,也加深了他的解析法的内容。从这一点说,张先生善于吸收多元观点充实、强健自己的思想。不过,张先生在所有的方法中最青睐的仍是解析法,就像他自己在《逻辑解析》的结尾处所说的:“无论如何,解析在各方法中总不能不说是最根本、最基础的方法。在用他法之前,应先用解析。要之,在哲学上,说一句话,要先懂得这句话的意思。解析即要求思想之自觉,解析即不同的意谓之厘别。”(同上,第181页)这可以说是张先生对逻辑解析与其他方法的关系的最后结论。
标签:哲学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张岱年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文化论文; 逻辑分析法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唯心主义论文; 理想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