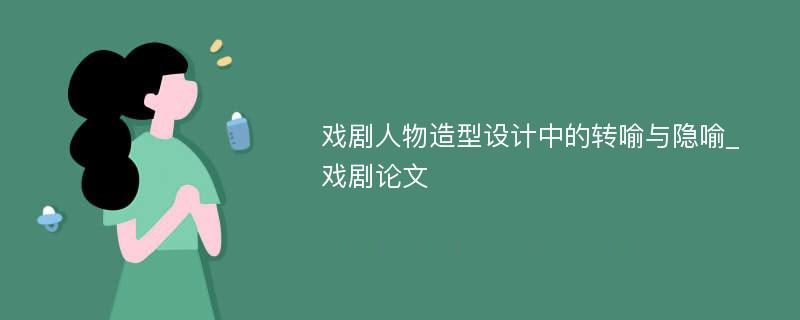
戏剧人物造型设计中的转喻和隐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剧论文,造型设计论文,人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戏剧人物造型设计的概念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前者不仅指服装设计、化妆设计和发型设计等对舞台人物穿着打扮的规定,还包括对演员对人物的动作、语音语气等方面的处理。所以,我们通常说的人物造型设计是狭义的。狭义的戏剧人物造型设计是指为了表达文本中人物的社会属性,性格脾气及心理状态等内在特征而使用造型手段来把它们外化;或者标示在人物个体之外的,属于文本总体的特定思想内涵。服饰、化妆和发型作为中介物具有外化文本思想的职能。人物造型设计所囊括的这些构成要素,为了传达人物内涵而被系统地构建出来,并以物质手段外化设计构思,具体呈现在演员所扮演的人物之上。戏剧人物造型设计形式的决定性因素是戏剧形态。戏剧各个流派之间相互借鉴融合,许多作品难以简单地划分其性质,所谓的流派往往只是一时的划分,在客观与主观,再现与表现之间所作的泾渭分明的区分是难以维持的。引入转喻和隐喻概念就是为了更清晰地分析各种戏剧人物造型设计类型的性质,从而更恰当地应用这一舞台视觉因素。现代语言学家雅各布森认为,转喻和隐喻(注:转喻和隐喻:雅各布森认为这两种修辞都是“等值”的,因为提出的喻体与形成修辞格主体的实体相比具有“同等的”地位。例如,在隐喻“汽车甲壳虫般地行驶”中,甲壳虫的运动和汽车的运动“等值”,而转喻短语“白宫在考虑一项新政策”中,白宫这一特定的建筑和美国总统是“等值”的。广义地说,隐喻是在主体(汽车的运动)和它的比喻式的代用词(甲壳虫的运动)之间提出的相似性或类比为基础的。而转喻则以人们在实实在在的主体(总统)和它的“邻近的”代用词(总统生活的地点)之间是接近的或相继的关系。由此可见,转喻是在两个性质相同的词汇之间进行转换,而隐喻则是在性质不同的词汇之间进行对比。)模式的普遍“竞争”表现在任何符号系统中。在戏剧文本和舞台演出形式方面中,人们通常所说的再现类型的戏剧以转喻模式为主,再表现类型的则以隐喻模式为主。需要说明的是,转喻和隐喻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在艺术作品当中,两种形式往往共生共存,相互映照,即使在同一个人物的形象中,有时也会包含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设计元素,只是比例不同的组合关系才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戏剧艺术形态和舞台人物形象。
(一)转喻形式
作为舞台物质环境的组成部分,舞台人物造型的主要功能是为观众提供识别和理解人物的信息和线索,它不仅帮助观众区分陆续上场的新面孔,而且还顺着这些形象,回想戏剧本体,在对二者参照过程中,产生审美愉悦。因此,转喻的人物造型设计的意义或者说功能是指代,是用确切的有明确含义的造型符号标示人物。就象给每个演员贴上标签,从而限定观众的猜想范围,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故事情节中;它涉及对象的外延,即明确舞台形象所确指的本体对象的范围,而不涉及设计对象的内涵,忽略现实性的较低级的物质形式与较高级形式如思想情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审美过程中,观众的精力主要停留在人物形象的事实层面,而不是意义层面。
戏剧人物造型的转喻形式是指舞台人物形象的造型构成要素及其组合关系作为喻体,与本体——社会历史原型之间,是外在形象类似关系,是设计者把生活中具体实在的形象,以接近的或相继的造型元素及其组合关系进行代替或转换,明示二者之间的相似关系。转喻的创作机制就是以原型为参照,把邻近性的元素放置组合在一起的过程。相继关系是指以生活原型在先,戏剧人物造型的代用品在后,成为对前者的继承。两者性质相同,结构类似。喻体与本体之间邻近相继关系的主要表现为:仿真(机械模仿)、简化(典型化)和装饰。三种表现模式的喻体与本体之间的相似性呈递减趋势。
仿真
仿真原则要求最大限度地再现生活,尽可能详细复印原貌。
自然主义的创作原则恰好是追求细节的真实,创造逼真感。自然主义机械地用生物学的原理来解释社会现象,主张记录式地复写生活的表面现象和细微末节,追求外在真实,拒绝分析与评判。自然主义视觉主义在视觉艺术中尽可能准确地复制物体的形象和行动。人物形象的历史准确性成为戏剧人物造型设计的最高标准,化妆师是说谎者,尽其所能地把假象造得更真实,而观众就是这场骗局的合谋。中国的戏剧创作,如《公用厨房》(注:《公用厨房》:上海戏剧学院,1988年演出。)就是一部明显受到自然主义创作原则影响的作品。它们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状况,不带有浪漫情感的表现,甚至不做评判,用冷静的目光尽可能真实地客观地反映事实。导演要求一切细节都要符合上海公用厨房的真实情况,人物的形象当然越自然越好,人物的服装化妆发型全都要求和生活保持一致,演员以生活中的本来面貌出现在舞台上。
简化
转喻的邻近性在简化(典型化)的人物造型模式中也要求喻体尊重本体的外在真实性,但反对堆砌细节,主张概括性地再现原型。在哲学中,关于个别与一般,部分与整体,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之类的概念,无论解释得多清楚,在实际的人物造型操作过程里,必然把所有这些概念化作一套行之有效的创造机制。这套机制的关键之一是选择和剔除。在前面提到的“自然主义模式”里,其问题就在于忽略了这里提到的“选择剔除”机制,转喻模式的接近性与典型化,否定了为细节而细节,罗列材料简单地复制现实的“加法”操作模式。理论上,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是否坚持艺术典型化。尽管两者都主张真实,但前者主张“细节”的真实,后者主张“典型”的真实。在实际创作中,好的设计不应当只注重表面的真实感,而要从大量的素材中挑选出最具代表性的那一部分。因为:
人类的注意力的本质正在于它具有选择性,我们可以把握视界里的Something,但永远不可能掌握everything,人的回忆能力是很不完善的,为了克服这种不完善,我们已经掌握这样的手段——符号。
(贡布里希《图像与眼睛》第7~8页.)
既然换喻形式的人物造型的主要功能是提供辨认,并且人类注意力具有选择性,那么,人物造型只需要提供足够让他们辨认得出的那一部分就可以了。有时也许只需很小的一部分。例如,布莱希特主张以诗的想象力表现真实,高举“间离效果”的大旗,在他的叙事戏剧里,为表演、舞美等演出模式指引方向。人物以程式化面目出现,演员被要求与人物之间清醒地保持着一定距离。因而他认为舞美设计者的任务无须再去创造某一时代某一环境中特定的视幻觉,只要通过程式化的方法,突出表现最典型化的局部或者整体性轮廓,达到提示性效果就可以了。高度概括性是叙事体戏剧人物造型的特点。追求“真实幻觉”的舞台视觉法则遭到打击。《第十二夜》(注:《第十二夜》:德国法兰克福无为剧团,上海兰心剧院,1993年。)在人物造型方面表现突出:所有女演员的服装只保留了文艺复兴时期女裙的突出特征:裙摆拖地、泡袖、束腰、低胸。一切无关紧要的细节——装饰性的花边、图案、皱褶,表明身份与社会地位的配件都被忽略了,最精彩“减法”是:主要人物的服装只有一种色彩:纯白。设计者以诗意的方式展示了人物和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同时又漂亮地兑现了间离效果的一部分。这种设计模式既是写实的,又高度概况和浓缩。只求“似”不求“是”的人物形象简洁明快,纯净的形式使观众倍觉轻松愉悦,与整部喜剧幽默美好的爱情主张相符。这正是去除一切不必要的视觉因素后所保留的最具代表性的部分,从而使观众产生审美愉悦。
作为转喻,同样以历史原型为本体,斯坦尼式的写实主义戏剧的人物造型形式是尽量多地组合邻近相继性元素,而叙事体戏剧人物造型形式是尽量少地组合邻近相继性元素。
当然,非写实主义戏剧里也有转喻的人物造型形式,而且也不一定是墨守成规的形象,例如百老汇名剧《猫》(注:《猫》;韦伯音乐剧。)、《狮子王》(注:《狮子王》:百老汇音乐剧,设计者:朱利、泰摩尔。)(例图2)等,设计者采用模仿动物外形的设计,即通常所说的动物妆。由于本体和喻体都是具体的对象,所以这种造型形式也在转喻形式之列。
装饰
装饰性的造型风格是在典型化基础上增加许多根本不说明任何问题的造型元素,仅仅是为了悦目而已。歌剧,芭蕾舞剧以及音乐剧多采用此种设计模式。在此,为了让观众尽可能保持轻松愉快的情绪,视觉愉悦感要比历史真实感更重要,舞台人物造型设计的总体风格是:有限地尊重客观事实,最大限度地追求豪华眩目之感,使人物形象放射出华丽的光芒。造型设计主要从色彩、面料和款式着手。例如音乐剧中里程碑式的作品《奥克拉赫马之恋》的女装主要采用西班牙款式,并大面积使用红黄蓝三原色,产生奔放热烈的视觉效果;一些带有闪光效果的材料,如亮片珠宝缀饰或金银色面料等能够产生奢侈感;繁复的装饰图案可以使单色的或款式很普通的服装也变得生动起来;精良的制作工艺也是人物造型的制胜法宝,歌剧《杜兰多公主》(注:Metropolitan歌剧院,1988。)的中国古代的人物形象被设计得有些离谱,然而精工细作的服装和宏大的阵容却令人叹服。
其实,戏剧人物造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就是以装饰风格为主的,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舞台上,即使仆人的服装也必须很体面,常采用丝绒等高档面料。为了保持平衡,主人的服装当然更加豪华。由于当时剧团的收入很低,置装费成为他们最大的开销;一直到20世纪,女演员为自己置办戏服的需要常常使她们的经济状况陷入窘境,阿戴勒 桑德洛克特别希望以其引起轰动的服装挫败那些可能和她争夺角色的女竞争者。(注:参见格尼玛拉《戏剧》第66页,黑龙江出版社2001年。)
(二)隐喻形式
从戏剧发展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到,尽管以转喻模式为主的写实主义戏剧始终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但在它之间和之后的戏剧更有诗意,那就是以隐喻为主导模式的戏剧形态。从原始的戏剧形态到各种现代派戏剧,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戏剧流派的人物造型以隐喻为主要修辞模式,而中国戏曲更是大量采用隐喻设计手法。
戏剧人物造型的隐喻形式是指舞台人物形象的造型构成元素及其组合关系作为喻体,与被喻体——观念,感官感受,思想情感等抽象概念之间是情感逻辑类似关系,以暗示的,联想的方式,把戏剧多重的,多语义的本质外化到人物形象之上。这种外化形式也许不与任何生活原型相联,但与人物及戏剧文本的内在涵义密切相关。隐喻形式中,本体常是抽象的思想情感,它要求设计者用具象的造型元素把内在特征表现出来,人物造型表现的是人物想要暗示的深意,如希望、死亡、压抑等等,也就是说,要在一个抽象之物与一个具象之物之间,找出共同点;在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之间相互对照,相互说明其中的意义,即异质同构。由于需要以可见之物表现不可见之物,所以,隐喻的创作机制采用抽象思维方式。隐喻的人物造型形式经常与现实世界发生冲突,舞台上的形象往往出乎观众的意料,引起强烈的震撼,进而调动积极的思考,用联想的方式,挖掘深层的含义,从而进入到舞台人物形象的意义层面。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象征、零造型和拼贴。
象征
象征形式的应用是十分广泛的。按照被普遍接受的理论,戏剧是由巫傩仪式演变而来,在原始戏剧形态里,生命死亡等抽象概念成为本体。巫师经过装扮之后成为各路神灵的代理人。造型的改变对巫师和信徒都至关重要,在他们看来,没有外观上的改变就不能完成由人及神的改变,一切仪式中的行为都将失去法力。对于当时纯朴虔诚的观众来说,人物造型对神灵的转化是卓有成效的,它完全吸附了无所不能神灵进入他的身体,服装,器具或面具是模拟图腾崇拜物等精神产品常用物质手段。例如,北美洲曼丹族的“牛舞”的意图并非以模拟牛的外在形象从中取乐,而是在扮演牛的狂热舞蹈中,把自己幻化为召来牛群的神灵,身上披着的牛皮隐喻为猎取野牛的愿望,表演越热情,部落实现愿望的可能性越大;与狩猎相比,人的生死是个更重要的问题,许多部落认为人死后的灵魂还与他们继续生活在一起,只要带上特定的面具,庇护他们的祖先就会回来,带面具者实际上是死者的亡灵或祖先,有的部落甚至给这神奇的面具供食,巴厘岛人每年都要拜祭扮演先灵时使用的服装、面具、道具。与转喻形式的直接模仿动物等形象的本质区别在于:隐喻的本体是抽象的,比喻在异质的两种形式之间进行,它创造的是形象之上的精神概念;而转喻的输体和本体都是实在之物,性质相同。
等到戏剧进一步成熟之后,如中国戏剧的形成,人物造型中象征的运用比比皆是。从脸谱到服装,从色彩到款式,几乎没有什么戏剧类型能够象戏曲那样广泛地使用象征手法。这些艺术形式表达了创造者的主观情趣和意志,形成独特的意象化造型。化妆方面,戏曲突出的特点表现在脸谱的应用。脸谱作为不可剥离的面具,在中国戏曲表演中已经被程式化了,艺术台上那些家喻户晓的人物,只有画上象征身份个性的符号之后才会被认可。各个人物大都有自己特定的脸谱,以显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具有“寓褒贬,别善恶”的艺术功能,因而被称为“心灵的画面”。脸谱的线条和色彩具有较固定的象征义。例如,用“法令纹”的上下开合表示气质,用“印堂纹”的不同图案象征不同的性格,“歪脸”用不对称的线条勾画丑陋邪恶的反面人物;色彩也有象征意义:红色描绘人物的赤胆忠心(如关羽),蓝色象征智勇刚义和强悍(如窦尔敦、单雄信),水白色表示生性奸诈狠毒(如曹操),而黄色则意味着残暴(如王英,窦虎);服装款式方面,武将的戎装一“靠”这一样式最具有代表性:靠旗使人从令旗联想到八面威风的军旗,靠杆的锐利直线产生放射感,四面绚丽的旗子在舞台上大幅度飞舞,强烈外化了武将威风凛凛的精神与气质,也象征着率领了成千上万的士兵;男靠的主要纹样是甲纹,鱼鳞纹和浪花纹,寓“翻江倒海”之意。
服装色彩常与人物性格相联系:果绿色表示品行卑劣,无耻或好色(如高俅,蒋干),粉红色象征品格有瑕疵(用于吕布),黑色意味性格粗犷,转义为刚正沉稳(如包拯),白色由纯洁转为年轻(如白蟒白靠用于穆桂英,周瑜,司马懿等)。
当然,有意识地运用象征手法还要等到象征主义。对于象征主义者来说,类似自然主义戏剧演出的那种照相机式的表现方法不仅仅停留于事物的表面,防碍了更深入到事物内部去进行观察。舞台不应去描写真实的环境,而应去探察感觉的范围,它的任务不是描写而是暗示。例如《芸香》(注:《芸香》:讲述叶子与青梅竹马的恋人阿果之间的曲折感情故事。两人从十六岁相恋,婚后,阿果长年在外并移情别恋。叶子因失明无法知道阿果寄来的情书全都是白纸,这些空信成为她的精神支柱,直到六十岁时,才发现真相。上海戏剧学院,1988年演出。)就是一部曾经光受欢迎的以象征手法为主的实验戏剧。主人公叶子和她的丈夫阿果在戏中的年龄跨度很大,从十六岁到六十岁,人物造型并没有遵照转喻原则,即从外部造型具体地写实性地塑造五官形态及年龄的变化,而是将人物的面部脸谱化—整体涂白,再在额头上画上两片叶子,用叶子颜色的变化,从嫩绿、中绿、黄绿到枯黄色,表现植物叶子的生命历程,从而暗示角色叶子的生命历程。人物叶子隐喻生命的苦短情感的脆弱,叶子颜色的变化过程本身就是此种隐喻的表现。
写实主义戏剧的人物造型也包含象征因素,如下列造型元素:
黑风衣/礼帽/墨镜/中分头……特务
王冠/手杖/斗蓬 ……国王
长发/宽松柔软的衬衫……诗人
红印花袄/辫子/平底布鞋 ……村姑
近视眼镜/工作服……科学家
……
尽管这些人物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会有不同的具体的造型,但是上述造型元素已成为象征性符号,它们所指代的人物如国王等已经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功能的体现。例如图6所示,这一国王形象并没有与任何一个具体国王相象,但手杖,斗蓬及王冠却可以象征王权,从而显示了人物的隐喻功能。
由于对隐喻的解释不仅需要充分的想象力,还依赖相应的文化背景。对于不同的观众,同一种造型会有不同的涵义。以色彩为例,利用色彩约定俗成的含义表达情感是极为普通的小把戏,设计师们常常把一套白色西装分给英俊正直的男主角,蓝白相间的斜纹领带送给精明的股票经纪人,把消防队员服似的草绿色便送给疯疯癫癫的神经质,而假如女主角有足够的热情和活力,那么她肯定会有一条红色裙子。尽管诸如此类的用法多半行之有效,但色彩的象征意义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往往会有所差异,例如红色在西方文化里常常象征血腥和暴力,当他们看到中国舞台上红彤彤的喜庆场面就会产生歧义;而他们在《杜兰多公主》的婚礼中使用了白旗白衣,我们中国观众也会感到怪异;再比如,在身体纹上凶猛骇人的形象,原本用来象征力量、勇气,但在今天由于影视剧中时不时的用这一套手法塑造黑帮头目等反派人物,纹身的含义已经发生变化,它似乎总是和反面人物联系在一起。随后纹身含义进一步演变:既然纹身被打上坏人的烙印,遭到了歧视。那么敢于采用它就可以标明自己的离经叛道,于是在现代都市里,纹身常被年轻人来表达叛逆。纹身在几千年之内经历了隐喻—换喻—隐喻—再转变;面具也是这样,在原始戏剧中,它象征神灵及其魔力,而在现代派戏剧中,面具则象征自我迷失和异化,作为有效媒介辅助人物传达他所隐含的社会与哲学涵义,在二十世纪引起较为广泛的注意,形成社会学意义上的广义面具理论。它已不仅仅指狭义的假面,面具与面具化成为不同人生哲学与戏剧形态的象征:戴上面具并不一定意味着虚假,脱掉面具之后露出来的未必是真实。面具有时比自我更重要。隐喻的创作模式和造型手段发挥十分有效的象征力量。孙惠柱的《挂在墙上的老B》,让老B戴上面具来象征他要扮演的那个人,从而陷入角色里不能自拔,用面具象征自我迷失、异化。(注:参见孙惠柱《现代戏剧的三大体系与面具/脸谱》《戏剧艺术》2000年第4期。)
零造型
“零造型”是指一些现代戏剧的演出让表演者无须经过化妆间和更衣室,直接从台下走到台上,或者是让观众(有时是假观众)参与到戏剧表演过程中来的形式。
格罗托夫斯基的“贫困戏剧”排除了布景灯光化妆音乐等一切他认为的“奢侈因素”,只剩下演员和观众两个戏剧必不可少的因素进行演出;在伯奥发明的“论坛戏剧”里,观众可以举手叫停,还可以直接走上台把自己的设想付诸实践;谢克纳的环境戏剧也经常采用观众参与的戏剧表现形式,它的重要特征就是打破戏剧与政治,艺术与生活,演出活动与社会活动,舞台与观众席之间的界限,如《酒神在1969》、《政府的无政府状态》等剧中,几乎所有部分都对观众开放,(注:参见谢克纳《环境戏剧》第46页,71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观众以自然的面貌出现,无须任何造型改变。在这类戏剧形态里,树立人物形象并非是它们的主要目的,而是通过混淆演员与观众、台上与台下的界限来打破真实与虚假的标准。人物造型那看似毫不用心的设计,其实蕴涵了这一类型戏剧的寓意:台上的未必比台下的虚假,台下的未必比台上的更真实。而且,使演区深入到观众或使观众与演员交叉混合起来,异常接近,从而产生一种亲切感,加强了他们的直接交流。谢克纳的环境戏剧的主旨就是“所有空间用于表演,所有空间也为观众所用”,观众的参与成为戏剧的目的,是实验戏剧最感兴趣也是最深入探讨的一个课题。这类造型手法与自然主义的人物造型转喻形式效果看似相同,它们都追求看似真实的效果,然而,在设计理念上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是不同戏剧观念的产物,是观演关系倒置的结果:自然主义理念是试图让舞台等同于生活,然而实际操作上却把舞台与生活,演出与观众严格划分开来,仍然谨尊传统戏剧游戏规则,只是试图依靠视觉方面的真实感达到混淆真伪的目的,即它创造的“真实”是“视觉真实感”;而此种现代戏剧观念试图告诉人们:生活有时也是舞台,生活中的人们就是演员。它的实质是打破传统戏剧游戏规则,依靠改变观演关系、打破舞台界限的方法创造“心理真实感”,“视觉真实”只是微不足道的附属物。作为一种隐喻,这实际是修辞本体倒置。戏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把生活作为本体的,把自身作为喻体,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戏剧成为了本体。这是对传统戏剧概念的颠覆。这种看起来十分简单的造型设计形式是探索性戏剧理念的产物,尽管不一定为所有人接受,但是它强调观众参与的精神是值得借鉴的。
拼贴
拼贴是指造型元素之间的组合关系打破惯例,把旧有的部件以新颖的方式重新组合,阐释全新的含义。类似调侃式的组合方式经常出现在具有讽刺意味的现代戏剧里,例如《天堂隔壁是疯人院》(注:《天堂隔壁是疯人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2001年5月。)总共只有四个演员,却要扮演十来个人物,因此设计者采用拼贴设计。基础造型为中性化简洁黑色的衣裤,角色转换时,就把某个所需造型“零部件”戴上。例如当俗气的咪咪转换成可怕的女疯子时,她只要摘去火鸡尾巴似的五彩发套和粉红太阳镜,代以半米来长的黑发套,披头盖脸垂下来;顾忌“变”杨仁(洋人),只是给他扎上一块有美国国旗图案的头巾,再架上一幅黑色太阳镜;贾华“变”里百(李白)变得也很生动,头上加了一顶“书生巾”式的帽子,胸前搭了一条细长的白围巾,指代书生的长衫,脚踏白色厚底靴,手拿一线装书,一边吟唱李白诗句一边踱着方步走入舞台。这种荒诞不经的搭配方法体现出人物不正常的心理状态。《晚风酋长》(注:《晚风酋长》:2002年小剧场戏剧节,德国法兰克福无为剧团,上海戏剧学院演出。人物造型设计:郦娜。)喜剧式的演出使观众席里不时出现爆笑场面,人物造型设计完全符合这一风格,不仅整体人物形象之间的组合没有必然联系,而且某一人物的造型元素之间也打破常规:肥硕的晚风酋长的“上衣”是由套在脖子上的若干条十分花哨的领带组成,“下裳”也是用类
似的两条花布片来代表。设计者希望用这种样式表现这个食人部落的不可理喻的传统,产生明显的诙谐幽默感。图7(12)是耶稣和唐僧形象的拼贴,耶稣的整体姿态造型一望既知,而腰布则换成袈裟的图案,再加一顶唐僧冠,借此寻找和表达二人共性:自我牺牲精神;而图8、9、10则用全新的造型组合关系,突破人们对这些人物的常规认识,表达微妙的幽默感。
拼贴是对传统意义上的服装的解构,以反常规的组合关系表达反传统的新思想,用轻松自由的形式冲击扳着面孔的传统戏剧观。
在时装表演舞台上,欧洲和亚洲都有定期举办的被称为“梦幻妆”的命题设计比赛。1993年在巴黎举办的一次题目为“我们的大自然”,得冠的作品看似平淡无奇,那只是一件银白两色的曳地晚礼服,款式类似巴洛克时期的女裙,样子虽然高雅,可是与“我们的大自然”有什么关系呢?原来秘密在于它的异乎寻常的材质:它们全都是垃圾箱里捡回的废品:被丢弃的餐巾纸、易拉罐、还有一段段废旧绳索和铁丝。它们经过处理后,居然构成了一件动人的艺术,设计者用废料拼贴的方式揭示了一个道理:人类不应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必须节制贪婪的物欲才能与自然和平共处。大自然其实并非只是“我们的”。以废品的艺术处理积极倡导了环境保护思想。这件作品的取胜之道在于,其它大部分参赛作品是简单模仿动植物的换喻形式,而它则是隐喻的。
由此可见,拼贴的设计要领不是对有型之物的简单模拟,更不是材料、色彩、线条的罗列堆砌,而是要借助其中一些物质表达思想情感,创造富有诗意的形式。因此,它在本质上与绘画、雕塑、装置艺术以及行为艺术是相通的,只不过借用了人体作为媒介罢了。它是整个人物造型艺术另一重要意义的一个缩影:它们被创造出来的目的不是制造转瞬即逝的视觉兴奋,不是对事物表面的模拟,不仅仅停留在形象的事实层面,而是用偏离生活常规形象为了表达思想情感。所以隐喻的艺术形式和创作方法往往比换喻的更能体现人物造型的艺术性。戏剧人物造型不仅仅是技术的,更是艺术的。
如前所述,换喻机制是寻找同类临近关系,而隐喻则以表面的不同类不相近为前提。喻体与被喻体之间相异的差距越大,比喻所产生的视觉和心理张力越大。因此,隐喻是在看似荒诞的比喻中以一反常态的全新组合表达人所皆知的情感。如果说转喻的人物造型形式的主要功能是指代和限定,为内容服务,使观众思路集中,那么,隐喻的人物造型形式则是为了引发观众的想象,进行发散型思维。它主张忽略物质的功能性,关注更高级别的人的内在本质特征。隐喻的修辞方法正是以偏离逻辑的手法显示了比转喻更强烈的艺术本质感染力。
小结
转喻形式成为戏剧人物造型的主要设计形式,而隐喻则是次要的。为什么写实主义风格在舞台视觉设计的其他方面仅仅是一种流派,而在人物造型方面却占据主流地位呢?仔细想来倒也不难理解:人们在进入剧场之前,对舞台样式的期待值比较小,甚至无从设想,所以最后不论舞台背景设计得多么非同寻常,他们都能接受,并且触发了活跃的想象力,而人物造型则不同,人们对它是有预期的。如果被展示出来的人物形象与他们的预期相符,那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与预期相差太远,则会引起极大的震惊。在本本分分的写实戏剧里,导演及演员们显然不愿意让观众们受到这样的刺激,他们宁愿用真实的谎言赢得观众最广泛的认同。
然而,戏剧艺术的现代性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艺术的现代性在于它对这个僵化而疏远的现实的模仿关系中。正是它,而不是对这个缄默的现实的否定,促使艺术开口说话。这种情形的后果之一,就是现代艺术不能容忍任何和现实相妥协的事物……他以原型的经验间接地向现实提出抗议并以艺术的形式作为这种经验的中介。
阿多诺《论艺术社会学》第31~32页
在阿多诺看来,历史情景和社会素材一旦进入艺术品,经由形式律的改造之后,便成为与原先形态完全不同的存在物。这种存在物往往是朦胧多义的,因而“反抗”以审美的方式而非直接模仿的方式反映社会。激进的现代主义必须保留艺术的这种固有本质,它必须以模糊的形式使社会进入它的辖区,使后者似乎成为一个梦。如果现代主义拒绝这样做,那将自掘坟墓。实际上,戏剧是一种语言,更是一种游戏。所有语言游戏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在承认语法规则的条件下,最大限度的从逻辑性的语法规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戏剧中对语言规则的戏拟似的应用,甚至有时是摆脱了一般逻辑规则而进行游戏性运用,不仅不是脱离语言本真特性,而恰恰是对造型语言本根的捍卫和复活。隐喻的戏剧形态及其人物造型形式,正是一个不断打破语法规则建立超秩序游戏的过程。在戏拟和逻辑偏差中传达哲学思想和普遍情感。人物造型艺术如果仅仅用社会历史原型做秩序,做僵化的模仿,并不能抓住戏剧无以伦比的游戏实质。通过打破旧秩序建立的新形式才能真正体现戏剧艺术的独特本性。
责任编辑注:
因原文图例不清,不易印刷,故删去。特告读者,如需要请参阅原刊。
标签:戏剧论文; 舞台服装论文; 艺术论文; 视觉文化论文; 造型设计论文; 演出服装论文; 象征手法论文; 情感模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