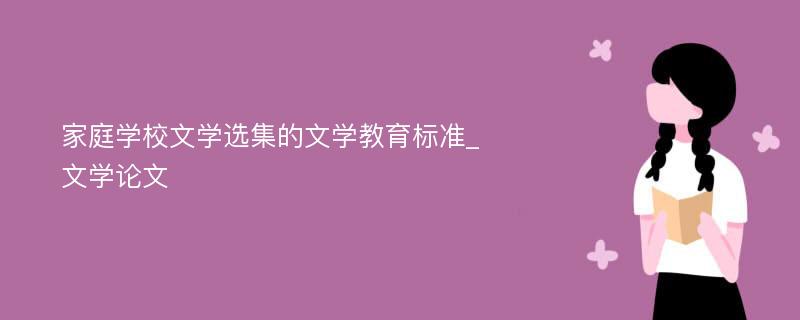
家塾文学选本的文学教育本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塾论文,选本论文,文学论文,本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0)07—091—095
一
“家塾”是中国古代以家族为单位的私人教育机构。起源很早,原是乡学的一种。《礼记·学记》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关于“家有塾”,孔颖达疏曰:“百里之内,二十五家为间,同共一巷。巷首有门,门边有塾。谓民在家之时,朝夕出入,恒受教于塾,故云‘家有塾’。”[1](P1521)可见,家塾原是闾巷所设的公共教育场所,还不是后来意义上以家族为单位的私人教育机构。据俞允海先生考证,其作为私学地位的确立始于汉代。经过长期的发展,至明清而体制大备,成为一种高度普及化的私学形式。家塾主要有两种:一是东家在自己家里设馆,延请塾师。这类家塾专门教育本族或亲友子弟,称为“专馆”。二是塾师在自己家里设馆,自任塾主。因为房舍条件的限制,或是出于生源考虑,不在自己家里,而借祠堂、庙宇,或远离家乡赁房设馆的情况也很普遍。由于其生源很分散,不像前一种家塾专于一家一户,故称“散馆”。
在明清时期,官学只培养生员(含)以上的人才,属于高等教育。生员以下的基础教育则完全由私人教育承担,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塾教育。家塾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杂书(如《三字经》、《百家姓》等蒙养课本)和四书五经。除此之外,也有诗文教育的内容。中国古代诗文浩如烟海,自然不能遍观,这就需要选编文学选本作为教材。如清人许宝善云:“学者束发受书,自四子书、五经而外,左国史汉以及历朝唐宋诸名家,皆不可以不读。然卷帙繁多,寒士或力不足以致之;即力足以致之,而质非能敏,不能遍观尽读。此选本之所以利党塾也。”[2]
许氏分析了家塾文学选本产生的必要性。“家塾文学选本”是指家塾编纂、刊刻或使用的诗文选本。现在通行的“塾刻本”或“塾刻文学选本”这一概念无法将非塾刻的塾编和塾用文学选本包括在内,而“家塾文学选本”则可以涵盖塾编、塾刻和塾用文学选本三种,从而将文学选本在家塾的生成和接受两个环节联系起来。
“家塾文学选本”中的塾用文学选本是家塾所使用的文学教材,而塾编和塾刻文学选本也往往在选篇、注释、评点、体例方面表现出鲜明的教材特征,在教育实践中发挥着文学启蒙的作用,然而却向来不受重视。家塾是中国古代最低端的私人教育机构,因而“家塾”——特别是“乡塾”——是僻陋、鄙俚和浅薄的代名词;在此影响下,家塾文学选本的地位不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遇“乡塾课本”之类,就一概加以贬斥。近年来,《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家塾文学选本已出版多种,而且日益受到读者的欢迎,但是在学界,它们也并不受重视。不但研究此类选本的成果很少,而且大型学术丛书对此类选本的收录也明显不力。例如,《续修》、《未辑》等四库系列丛书就不收《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对于明清时期出现的二十余种非茅坤所选的唐宋八大家选本,也大都不予收录。
二
由于载道语境、科举语境和宗派语境的离心作用,文学选本偏离文学本位的情况是很普遍的。但是,家塾文学选本却适当拉开了与三种语境的距离,坚定地保持了文学本位。
在载道语境中,家塾文学选本采取了循道重文的基本立场。所谓“循道”,就是选篇和评点都不背离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基本的是非标准。例如,清代塾师于光华称其家塾课本的选录标准是:“文以载道。凡忠孝节烈、理学经济、有关世道人心者,方编入集。一切游戏弄笔之文,适足以长初学浮靡之习,虽经传诵艺林,概不敢录。”(《凡例》)[4]另一位塾师林云铭则称:“文所以载道也。是编凡忠孝义烈大节及时务经济,关系于国家兴亡,或小题中立意正大者,方汇入选。其一切排偶粉饰、变乱是非之文,及有碍于时忌者,虽工致可观,概不敢录。”(《凡例》)[4]为了在特殊的时代获得生存权,两个选本都有意表明自己的循道立场,不仅对“有碍于时忌”的文章无条件加以排斥,对于那些“长初学浮靡之习”的“游戏弄笔之文”也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前者从生存考虑,后者从教育考虑,都以“载道”为掩护,牢牢地将选篇框定在时代氛围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所谓“重文”,就是在循道的前提下把选篇的文学性作为核心关切。家塾文学选本就是在这种折中文道的努力中坚持文学本位的。实际地讲,“循道”不过是家塾文学选本的一种生存策略,其实际追求仍在于文学。
毋庸置疑,在科举语境中,家塾文学选本是以举业为指向的。但是,由于这些选本的读者大都是在塾的童蒙,参加举业考试还是较为遥远的事情,所以家塾文学选本还不至于像专供应举者使用的时文读本那样急功近利,而是在选篇和评点上都较为切实。具体而言,就是以文法为中心,以评点为手段,通过典型文本的细读,为塾童写作能力的养成提供一个可资依循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对文学文本的学习是真切的,踏实的;相较而言,举业只是一个潜在的目标,还没有急切地浮现出来,成为压倒性的追求。诚如林云铭《古文析义凡例》所云:“读古或遇不切举业者,辄云不必究心,不知观斗蛇而字法进,观舞剑而画事工,亦思字与蛇何涉、画与剑何涉乎?若不解此,纵全篇学步邯郸,徒来丑妇膑里之诮耳。”[4]林氏批判了一切向举业看齐的教学观,认为童蒙教材应适当拉开与举业的距离,通过基础文法的学习,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这样的思想在其著名家塾文学选本《古文析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宗派语境大都形成于社会上层的学术精英之间,其参与者所争的是是非和胜负。作为一个低端教育机构所编纂、刊刻或使用的教材,家塾文学选本选哪些篇目,如何评点这些篇目,主要是看这样的篇目和评点是否有利于塾师的教与塾童的学,至于上层学术界所争的是与非,并不在其关注范围内。正因为如此,明七子在鼓唱文必秦汉之时,家塾所使用的主流读本仍是唐宋文;清代朝贵宿老宗宋方酣之际,家塾所读仍然是唐诗选本;唐宋八大家散文在清代成为当红的经典时,著名的家塾文学选本如《古文析义》、《古文观止》等仍然大量选入秦汉文。就此而言,家塾文学选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宗派语境的负面影响,很好地坚持了文学本位。
三
在适当拉开与三种主流语境的距离之后,家塾文学选本又很好地坚持了教育本位,这主要表现在其选篇和评注与童蒙教育的自觉适配。
家塾文学选本在选篇上贵精贵熟不贵多。家塾文学选本是塾师施教和塾童学习的课本,因而有着不同于一般选本的特定要求,这一要求是由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传统所决定的。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强调一个“熟”字。吕葆中在《八家古文精选序》中转述其父吕留良的论述云:“夫读书无他奇妙,只在一熟。所云“熟”者,非仅口耳成诵之谓,必且沉潜体味,反覆涵演,使古人之文若自己出,虽至于梦呓颠倒中朗朗在念,不复可忘,方谓之熟。如此之文诚不在多,只数十百篇可以应用不穷。”[5]可见,“熟”既要求“口耳成诵”,又要求“沉潜体味”,并由此达于“若自己出”的化境。清人唐彪又提出了“极熟”的更高要求:“文章读之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6](P92)“凡人一切所为,生不如熟,熟不如极熟。极熟则能变化推广,纵横高下,无乎不宜。”[6](P71)看来,唐氏的“极熟”强调“变化推广”,也即在“与我为化”的基础上达于触类旁通、推陈出新的更高境界。唐氏又云:“凡读文贪多者,必不能深造;能深造者,必不贪多。”[6](P96)选本的篇目太多,自然“熟”读为难,所以“不贪多”就成为“熟”的必要前提。这样,读书“贵熟”与选篇“不贵多”都以教育的实际效果为最终指归,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清代塾师吴懋政在其《论文杂说》中明确提出了家塾教材“贵精贵熟不贵多”的见解“读本贵精贵熟不贵多。明文、今文精选数十篇,朝夕熟诵。每一篇引申触类,便可悟出无数法门,此左右逢源之候也。若爱博不专,旋得旋失,虽读至于万篇,何曾得一篇受用来!”[7]这是就家塾所用的时文选本而言,揆诸实际,家塾文学选本的情况也是如此。清人许耀序其家塾课本《宋诗三百首》云:“人莫不限于质。全集不能读,必取选本读之;选本之繁者亦不易读,必取选本之简者读之。”[8]他之所谓“简者”即指选篇数量少的选本,与吴氏“不贵多”的主张是一致的。
选篇过多的文学选本要成为家塾文学选本,首先必须接受家塾文化力量的简约化改造。李攀龙《古今诗删》(万历汪时元刻本)的《唐诗选》部分选诗738首,而经过王世贞家塾师改造过的《唐诗选》(万历蒋一葵注本)只有465首,结果“海内家传而户习之”(凌濛初《李于鳞唐诗广选序》)[9],清代仍“盛行乡塾间”[10](P2691),并实际上成为《唐诗三百首》之前最为流行的唐诗选本。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抄》原本是家塾课读子侄的文学选本,篇目没有如此之多。万历初刊刻时为了接续文统,体现载道追求,才又增加了许多载道之文,结果全书收文达1313篇。如此多的篇目使其自然无法成为理想的读本,所以崇祯以后出现的所有唐宋八大家再选本都对它进行了大幅删减,其中大部分用作家塾教材。例如:明人钟惺《唐宋八大家选》352篇,孙慎行《精选唐宋八大家文钞》432篇;清人吕留良《八家古文精选》185篇,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248篇,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377篇,王应鲸《唐宋八大家公暇录》120篇,高螗《唐宋八家钞》256篇,程岩《精选唐宋八大家古文正矩》86篇,刘大櫆《唐宋八家文百篇》100篇,陈兆仑《批选八家文钞》116篇。与茅《抄》相比,这些选本的篇目多则为茅《抄》的四分之一,少则不足十分之一。这是熟读法要求下的必然产物。从这个方面讲,家塾文学选本在“选多少”的问题上,是以教育效果为指归的;而这一点正体现了其教育本位。
在“选什么”的问题上,家塾文学选本则贵常不贵新。坊刻文学选本多以新异相尚,以达到吸引读者、增加销量的目的。而家塾文学选本在选文上则不避熟就生,更强调选篇的典型性和有效性。清人吴懋政云:“余塾中课本不欲求新求异,只就外间流传习熟者批示诸生,非谓佳文遽尽于此,要亦此种文皆可传、可读、可学,且学之而万无流弊。此自信,亦为共信者耳。”(《八铭塾抄序》)[7]吴氏所选的《八铭塾抄》不过是家塾所用的时文选本,但其选篇不“求新求异”,只求教学效果(即“可传、可读、可学”)的基本思路实为家塾文学选本所共有。例如,乾隆时期朱宗洛家塾选刻《古文一隅》用作教材,光绪时期庞彦钦重刊于家塾,也用作“家塾课本”。之所以如此,就是看上了它选篇少(46篇),而且都是“人人所诵习”的常见篇目(庞彦钦《古文一隅跋》)[11]。
为原文作注,古已有之;而复加以评语和圈点,则是明清选坛上的新现象。关于评注和圈点存在的必要性,向来有不同意见。据杨慎说,当时就有人主张“诗刻必去注释,从容咀嚼,真味自长”(杨慎《升庵诗话》)[12](P861)。清代姚培谦选《唐宋八家诗抄》即将评注和圈点全部删略,其《例言》云:“旧时读本妄缀细评,付梓概行削去,恐以己意掩古人真面目耳。凡唐、宋、初明原板,悉无圈点,欲览者自得之也。兹仍其旧。”[13]但是,家塾教育工作者从教育的效果出发,大都主张家塾文学选本要有评注和圈点。清初塾师唐彪云:“凡书随读随解,则能明晰其理,久久胸中自能有所开悟。若读而不讲,不明其理,虽所读者盈笥,亦与不读者无异矣。”[6](P10)唐彪主张随读随解,读而能解,反对死记硬背,这就必然要求教材有评注。所以他又说:“读文而无评注,即偶能窥其微妙,日后终至茫然,故评注不可已也。”[6](P96)清末教育家吴汝纶编成《初学古文读本》课读其子,光绪二十九年直隶学校司曾排印此书用作国文教科书。关于评点之于初学的重要性,此书有一段记载:“先生尝谓:欲开示始学,莫过于评点。此区区者,倘亦文字义法所系,而为简省学徒脑力之一端欤?”(胡景桂《重印古文读本序》)[14]评点对于初学之重要,一在于指示义法,二在于提供方便。这两点正是评注和圈点普遍为家塾文学选本所接受的原因。
评注有详略明晦之分,家塾文学选本在注释方面贵详不贵略,在评语方面贵明不贵晦。清人余诚欲“专为初学订一善本”(《凡例》),编成《古文释义新编》。其自序云:“课幼之书,贵详尽不贵简略。俾开卷瞭然,毫无遗义,胸中眼底,触处洞悉,诵读之间,斯能欣欣有得。”这是就注释而言。至于评语,则追求切实明白,反对求新求异、故弄玄虚。所以他又说:“若只称述微妙,措意过高,或亦评陟明显,而讲解未备,纵授诸极聪颖之子,终恐启悟靡从也。”“是编每篇中所应有之义,必悉为释明,绝不敢作一套评间语,以迷眩人心目。惟于文义字义细细详批,切实确当,一若传之释经,直抉发作者不言之秘,俾读者洞彻其义蕴,涣然冰释,应属读古快事。”又说:“如前贤评语果与古人意适符合,正自不妨互相发明,何必妄生议论,专取旧评而翻驳之。”(俱见《凡例》)[15]总起来看,余氏注释求其“详”,评点求其“明”。所谓“详”就是“细细详批”,以求“切实确当”;所谓“明”就是研合众评,参以己意,以阐明篇中“应有之义”为目标,不刻意翻驳旧评以“迷眩人心目”。以射利为目的的坊刻文学选本往往削减注释以降低成本,或者避难就易以节省人力。清人林云铭云:“坊本古文中所引用典故,人人习知者偏加了许多注脚,繁冗可厌;稍有奇僻,则皆阙然不详。”(《凡例》)[4]或者在评语中故作高深以吸引读者。家塾文学选本大都是自编自用的课本,因而能够摆脱这些商业习气。
家塾文学选本是文学教育赖以实施的中介,在当时还没有通用标点的背景下,对原文加以圈点是理清句读、指示章法、标注四声、突出精华的重要手段,对于童蒙有效掌握教材具有极端重要性。唐彪云:“凡书文有圈点,则读者易于领会而句读无讹,不然,遇古奥之句,不免上字下读而下字上读矣。又,文有奇思妙论,非用密圈,则美境不能显;有界限段落,非画断,则章法与命意之妙,不易知;有年号、国号、地名、官名,非加标记,则披阅者苦于检点,不能一目了然矣。”[6](P63)正因为如此,圈点就成为家塾文学选本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非此则很难在家塾中流行。《古文辞类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古文辞类纂》是姚鼐自编的教学用书,“凡语弟子,未尝不以此书;非有疾病,未尝不订此书”(康绍镛《古文辞类纂序》)[16],系其一生“应时更定,没而后已”(吴启昌《古文辞类纂序》)[17]的产物。它有两个代表性版本:一是道光元年合河康绍镛家塾刻本,有圈点;二是道光五年金陵吴启昌刻本,无圈点。二本之刻相距虽不过五年,但其所据底本不同:康本所据是姚氏中年抄订本,吴本所据是姚氏晚年修订本。但从刊刻频率看,吴本远不如康本更流行。李承渊说:“吴氏刊本系先生晚年主讲钟山书院时所授,且命付梓时去其圈点。道光以来,外省重刊,大抵据康氏之本;而吴本仅同治间楚南杨氏校刊家塾,不甚行世。”(《校刊古文辞类纂后序》)[18]至于其原因,周远政先生认为:由于吴本是姚鼐晚年的修订本,故而其字句的考订,目次的安排显然都更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讲,吴本显然优于康本。但是较之于康本,吴本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是它删除了康本的圈点。而圈点之学是桐城派传授文章精义的重要手段。这恐怕是吴本传之不盛最为重要的原因。
清人姚永概亦云:“惜抱先生《古文辞类纂》有二本:康刻全载评点,吴刻承先生意,存评语,去圈点。而世顾多以康刻为便。”(《古文辞类纂序》)[19]《古文辞类纂》是桐城派的经典,其影响力不亚于《唐宋八大家文抄》及其众多再选本,清代后期逐渐成为重要的家塾文学选本。例如,光绪十年朱记荣槐庐本刊于江苏吴县孙溪吴氏家塾,光绪二十七年求要堂本刊于滁州李承渊家塾。而圈点既是“桐城派传授文章精义的重要手段”,又是家塾教学之所需,那么,世人“多以康刻为便”也就不难理解了。吴启昌在删去《古文辞类纂》圈点时说:“本旧有批抹圈点,近乎时艺,康公本已刻入。今悉去之,亦先生命也。”[12]是说去掉圈点系姚鼐意旨。然此说多不能服人,黎庶昌就曾提出异议:“道光初,兴县康抚军刻姚氏《古文辞类纂》,本有画段圈点。后数年,吴启昌重刻于江宁,以为近乎时艺,用姚先生命去之。然观先生《答徐季雅书》,不又有‘圈点启发人意,愈解说’之言乎?”(《续古文辞类纂目录》)[20]这说明,作为一个著名的教育家,姚鼐深知圈点之于教育的重要性,康本中的圈点并不违背姚氏的意图。
可见家塾文学选本的编者和读者,大都能脱去“批抹圈点,近乎时艺”的成见,将圈点作为家塾文学选本发挥其教育功能的重要辅助手段。又有为了塾童诵读方便,为不应加读点的长句加读点者:“又有极长之句,原不可加读点,但学生幼小,念不来,亦须权作读句,加读点,则易念也。”[6](P19)这样的体例自然为家塾文学选本所独有,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家塾文学选本的教育本位。
四
总起来看,诚如清人季福所言,“约而精,简而备,最为塾课善本”(《重订古文翼小引》)[21]。“约而精”是就选篇而言,“约”指数量要少,“精”指质量要好。“简而备”是就评注而言,“简”指文字简省而不繁冗,“备”指内容翔实而无缺略。这是基础文学教育的必然要求,反映了家塾文学选本坚定的文学教育本位,同时也将家塾文学选本与其他文学选本区别开来。晚明和清初都出现了很多重视文学标准的选本,如《媚幽阁文娱》、《唐贤三昧集》等,但它们并不以教育,特别是童蒙教育为指归。明清时期也有专为童蒙教育而编纂的文学选本,如《五伦诗选》、《文章正论》等,但它们所关注的教育主要是伦理教育,文学本身并不是目的。明清时期的各级官学也使用文学选本作为教材,但大都是《文章正宗》之类以“明义理、切世用”相标榜的选本,真正用心学习的人很少。家塾之外的其他私学机构自然也会将文学选本用作教材,但其来源主要以坊刻选本为主,真正用心为这类机构中的受教育者编纂教材的情况很少。家塾教育关系到家族的未来,所以家塾文学选本的编纂和刊刻有可能聚集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家塾文学选本之所以能够坚守文学教育本位,之所以能够在文学教育的效果上优于其他文学选本,原因就在这里。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古代家塾文学选本研究》(项目编号:07JA751002)的成果之一]。
标签:文学论文; 古文辞类纂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唐诗三百首论文; 艺术论文; 古文观止论文; 唐宋八大家论文; 古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