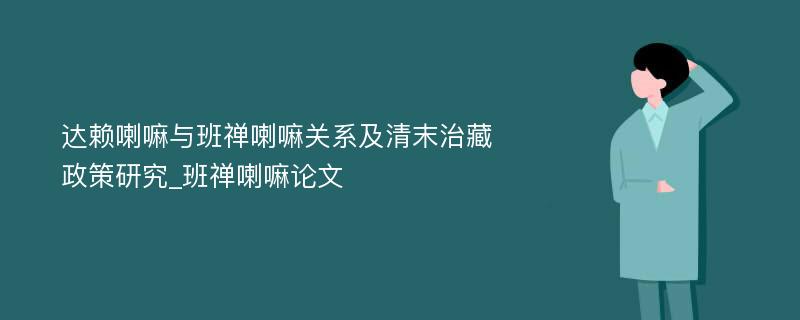
清朝末期达赖、班禅关系与治藏政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达赖论文,班禅论文,清朝论文,关系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两大转世活佛,1904年前的数百年间历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互为师徒,相互礼让,关系密切,有九位达赖拜五位班禅为师,有四位班禅拜四位达赖为师。① 此后,受种种因素影响,两大系统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矛盾冲突时有发生,甚至相互对立,对当时和以后的西藏局势乃至西南边疆的形势、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达赖、班禅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外人士都有所记载,学术界也有一定成果,但较少关注清末双方关系与治藏政策、驻藏大臣的相互作用。② 本文拟依据档案、文献,以驻藏大臣的作用为中心,探讨清末达赖、班禅关系发展的状况,试析中央政府针对双方关系制定的治藏政策、措施及其得失,恳请方家指正。
一
入清以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都由中央政府册封,两大系统之间总体上相处融洽,相安无事。而且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逐步确立了以达赖系统为主导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度,1793年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定达赖和班禅同为“黄教教主”,“互为师弟”,转世时通过金瓶掣签制度确认。③ 这对于维护西南边疆的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从18世纪起,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西藏侵略的不断加深,特别是鸦片战争后英、俄两国对西藏的争夺日益加剧,再加上清政府的对外妥协,西藏僧俗上层内部对英、俄两国的态度出现差异,与清朝中央政府、驻藏官员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微妙变化,逐步出现了裂痕,驻藏大臣已经介入其中。
班禅、达赖两大系统的矛盾至少产生在八世班禅时期(1855—1882)。学术界已经注意到,1875年八世班禅受戒,此后因他热心修习萨迦派教义引起西藏各界的争论,1882年十三世达赖受戒,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未按旧例邀请八世班禅参加。④ 同年,八世班禅圆寂。对于相关事件,英印政府所派间谍达斯(Sarat Chandra Das)记载,当时西藏有人就把八世班禅的圆寂“归罪于他的人民对他不忠,他因此郁闷不乐而死;另有人说他的去世由于达赖喇嘛对他不礼貌,灌顶时没有邀请他参加”;到1887年,因为接待了英印政府所派的间谍达斯,班禅系统的第四世生钦活佛被噶厦处死。⑤ 这些在当时导致了达赖、班禅两大系统之间的矛盾。有学者认为生钦被处死一事是“达赖、班禅这两大黄教系统之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公开的裂痕”,也是长时期以来“英印侵略势力蓄意制造西藏内部矛盾的一个结果”。⑥
在达赖、班禅系统发生这一冲突的过程中,当时担任驻藏大臣的松淮、文硕等人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八世班禅“惑习红教”事件发生时,松淮为驻藏大臣,桂丰为帮办大臣,他们对此颇为关注。1876年12月,松淮奏称:“西藏向遵黄教,奉经念佛,惟后藏之西萨迦呼图克图本系红教,并皆养妻生子,迥异黄教”,不料班禅“被人愚惑,兼习红教,遂致两藏物议沸腾,众心不服”。他感到“体制攸关,诚恐滋事”,他巡视到后藏时多次会见班禅,进行劝说,提醒他:清朝皇帝“特派大臣保卫阖藏,振兴黄教”,应该“上体大皇帝二百余年护持之恩,下慰前后藏数万众生皈依之念,正己教人,表率一方”,怎么能“妄习别教而舍正经,以致人心惶惶,浮言四起”呢?以后应当仍然“确遵黄戒,虔心唪经”,不得“任性妄为,旁习外道,以期仰副圣主保卫全藏、护持黄教之深恩”,如果“执迷不悟,妄知痛改,立即严参,从重惩办”。经过松淮的劝告,班禅“闻听之下,俯首无言”,并按照要求“具结存案”。松溎还表示,他会“随时密察,笞其痛改前习,则阖藏人心自定”,就不再追究,如果“阳奉阴违,始终不悛,自当再行据实严参,请旨办理,并将随侍之札萨克喇嘛一并惩办”。对此,清廷也非常关心,并肯定了松溎的做法。光绪帝在1877年1月谕令,驻藏办事大臣松溎奏“班禅额尔德尼惑习红教,现令具结改悔”,“著随时察看,妥慎办理”。⑦ 很显然,1876年前后,松溎和清廷希望班禅改变“妄习别教而舍正经”的做法,目的是维护黄教内部和西藏僧俗上层的团结,以免激起班禅与西藏僧俗上层的矛盾,避免“人心惶惶,浮言四起”的情况发生,从而稳定西南边疆。至于生钦活佛被处死一事,由于英国侵略西藏,清廷有意妥协,西藏僧俗民众又要求抵抗,驻藏大臣文硕忙于在清廷、西藏地方之间协调立场,似乎无暇顾及,目前笔者所见的文硕奏牍中并未提及此事,《清实录》中未予记载。
1888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略西藏的战争,达赖、班禅两大系统团结抗英,双方矛盾暂时缓和,此后由于英、俄两国的挑拨和清政府的无能,达赖、班禅两大系统在如何处置与英、俄两国的关系,如何对待清政府的治藏方略以及维护西藏地方利益方面出现分歧。1896年,四川总督鹿传霖在一份密折中奏称,英国侵略西藏时“俄人乘间藉游历为名,取道后藏而来,甘言厚币,以诱藏番”,因“语言文字不能相通,特予密函三件,约令遇有急难,将函驰送俄境,即可电达,助兵援应”,达赖方面“欣然信从,结好而去,秘之未敢宣露”。可是,“后藏班禅素与达赖不睦,而附于英”,泄露了这件事,升泰驻藏期间“闻知查究,追出原函存案,惜未及时销毁”,待到升泰离任,达赖方面乘机“贿通司文案者,仍将三函盗去”。鹿传霖还说,此后没再听说达赖方面与沙俄往来的情况,主要因为俄国与西藏远隔万里,“夏秋水潦不能通行,且必道经后藏,若有勾结,则班禅必为泄之,英亦防之甚严”。这些都使达赖方面“遽难通俄”,否则“以达赖之藐抗顽梗,如其能通,不待我驱之,早已外向矣”。⑧ 此事因沙俄原函被盗走已查无实据,但至少表明:在英、俄两国加紧争夺中国西藏,都企图在西藏培植自己的代理人的情况下,西藏地方开始出现了某些上层人士或“附于英”、或“结好”沙俄的传言。这一说法出四川总督之口,四川又是西藏治理的后方基地,表明清朝一些地方官员已对班禅、达赖之间的矛盾有所了解,对他们都有猜忌,并对英、俄在西藏寻找代理人的行动非常警惕。到1902年,双方矛盾逐渐公开化,有汉文文献记载,这年春九世班禅到拉萨“往朝达赖,由布达拉宫前击鼓而过”,十三世达赖颇为不快,认为“班禅过师门而击鼓,妄自尊大”,罚银一千五百两,“自此左右互相谗构,嫌隙日深”。⑨ 此事反映了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两大系统矛盾明显加深,“击鼓事件”仅仅是一个导火索罢了。
二
1904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侵入拉萨,十三世达赖被迫逃离拉萨到内地避难,随后被清政府革除名号。翌年,英国又诱骗九世班禅赴印度;而达赖滞留库伦,其亲信德尔智秘密前往圣彼得堡会晤沙皇,沙俄驻华公使到库伦“看望”达赖。此后,西藏的内外形势急转直下,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的关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06年,中、英两国签订《续订藏印条约》,同年清政府派张荫棠以五品京堂候补的身份前往西藏查办藏事。1907年,英、俄两国签订协议,从各自全球战略出发,对中国西藏的争夺有所缓和,而此时张荫棠建议清政府在西藏推行新政,强化在西藏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达赖、班禅对清政府和英、俄的态度都出现明显差异,达赖方面对清政府无力保护西藏地方利益感到失望,与某些驻藏官员矛盾加剧,希望借助沙俄抵制英国的扩张。但沙俄在日俄战争之后无力顾及西藏,与英国达成协议后又更多地考虑争霸世界的整体战略,只停留于敷衍和一贯的拉拢政策。英国开始希望拉拢、控制班禅,企图把他作为英国在西藏的代理人,但1905年班禅的立场和表现,特别是对清政府的拥护,让它大失所望。此时,达赖和班禅的政治立场已经出现分歧,双方关系也发生显著变化。
面对形势的急剧变化,一些驻藏官员和清政府已注意到处理好达赖、班禅两大系统关系的重要性,力图通过平衡双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保持西藏的稳定,强化对西藏的管理。这也成为1904年以后清政府治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04年十三世达赖逃离拉萨后,驻藏大臣有泰对英国侵略者妥协投降,又致电清政府,指责达赖是中英战事的“罪魁,背旨丧师,拂谏违众”,英军逼近后又“不思挽回”、“遁迹远扬”,责斥他“天威在所不知,人言亦所不恤,骄奢淫佚,暴戾恣睢”,“种种劣迹,民怨沸腾”,建议清政府裭革其名号。⑩ 清政府听信有泰的一面之词,8月26日下令“暂行革去”达赖名号,让班禅“暂摄”达赖职权。(11) 清政府让班禅代行达赖职权,主要考虑班禅与达赖同为有影响力的格鲁派大活佛,希望他在极度混乱的局势下稳定西藏人心,巩固西南边陲。但是,革除达赖名号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已引起西藏和国内其他地方藏传佛教信徒的不满,再让班禅代行达赖职务,无疑会使班禅成为矛盾的焦点,在达赖、班禅之间人为地制造了矛盾。况且,西藏地方政府长期由达赖方面控制,历世班禅主要关注宗教事务,九世班禅本人对于能否控制拉萨局势也有所顾虑,他一再谢绝这一任命。1905年4月,有泰只得表示“后藏地方紧要”,恳请清政府让九世班禅仍然留在后藏,“以资镇摄”。(12)
1905年10月,英帝国主义者又把班禅诱骗至印度,会见英王储,意在拉拢班禅以控制西藏、排斥达赖,让他在政治上取代达赖在西藏的地位,成为英国在西藏殖民统治的代理人。(13) 对于此次英国让班禅赴印,清政府和驻藏官员都认为居心叵测,力图阻止班禅赴印,在阻拦未成的情况下又多次与英印政府交涉。1905年10月,张荫棠在印度得知此事后感到事态严重,立即致电清政府外务部,表示听说英印政府“乘达赖喇嘛未回,已遣人入藏诱班禅”到印度,借迎接英王储为名,实际上是“密谋废达赖图藏”,要求中央政府致电有泰加以阻止。(14) 接到电报后,有泰派人阻拦班禅赴印,并表示:达赖、班禅“虽系同掌黄教,然番人崇奉达赖实胜于班禅”,西藏的“一切事权,均由达赖主持,班禅从不预闻”,认为“英如废去达赖,欲以班禅号令番民,则人心必不服从。英虽强盛,恐彼亦难施其计”,而“达赖、班禅归我所属,似彼国家亦不得越俎代谋”。(15) 这表明,虽然有泰一向采取对外妥协的策略,也尝试过请班禅取代达赖,并且认为英国想以班禅取代达赖控制西藏同样难以成功,但是他也觉得“达赖、班禅归我所属”,事关国家主权,英国“不得越俎代谋”。
在印度期间,尽管英印政府对班禅“以最优相待”,甚至在张荫棠住所“对门盛设行馆,英储预备答拜”,有关舆论又宣传班禅此行“非专迎英储,别有关系”,(16) 但班禅始终不卑不亢,与英王储会见时英方“欲使班禅跪拜,班禅不从,与之抗礼”,与英王储、英印总督“问答之词,均系酬应,未尝一语提及藏事”,致使“英人无机可乘,其谋不遂”。(17) 清政府为此也多次同英国交涉,明确告诉英国,班禅对“藏中政治概不预闻,现因英储赴印,前往致贺”,倘若“擅行约定事件”,中国政府“概不承认”。1906年1月,英印当局不得不把班禅送回西藏。对于班禅回藏后的地位,班禅方面也有所顾虑,回国前通过张荫棠致电清政府,强调班禅此次到印度,“并无与英员私商事件”,只是“未经奏准出境,恐干严谴”,请求免予处分。鉴于班禅在印度的表现,清政府又考虑稳定西藏大局的需要,明确表示班禅虽然此次“并未奏准,擅行出境,实有不合”,但已经启程回国,“念其情词恭顺,尚属出于至诚”,因此回国后“照旧恪供职守”。(18)
清政府让九世班禅“暂摄”职权和英印方面的拉拢,这两件事性质虽然不同,但都是班禅可能取代达赖的两次机会,但在处理这两件事时,九世班禅一直注意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对内与达赖方面搞好关系,努力维护西藏地方上层的内部团结。当然,在复杂的内外形势下,班禅的一些部属与他有不同的看法。1906年,张荫棠奉命查办藏事,11月在江孜会见了班禅派来的扎萨克喇嘛,这位喇嘛在谈话中“微露班禅有欲代理达赖之意”。这一意向显然与1905年4月前班禅的做法相背,但出自他派来的扎萨克喇嘛之口,至少部分地反映他的一部分部属的想法。张荫棠为此让扎萨克喇嘛劝班禅呈请入京觐见,同时又在拉萨把这一情况“告知藏王”,这使噶厦的噶伦们“颇为惊惶,以为班禅来京后达赖必致失位”,情急之下也要求张荫棠转请清廷让达赖入京觐见。(19) 因此,无论是清政府谕令代管藏事,抑或是班禅部属中流露出的某些意向,还是英帝国主义企图利用班禅控制西藏,都让达赖方面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张荫棠有意把班禅部属的某些意向直接透露噶厦官员,更让他们更加明确地感到了班禅方面对他们既得地位、利益的“威胁”,埋下了双方不和的种子。
对于班禅、达赖同时要求觐见,清廷采取了平等对待的立场,1907年2月发布谕令,指出班禅“吁请陛见”,“具见悃忱”,但须待“藏务大定”后“再行来京陛见”;达赖“现在留驻西宁”,也“暂缓来京”,并让张荫棠“体察情形”,考虑“究竟达赖、班禅等来京是否相宜”。(20) 此后,针对他们的觐见要求,又一再谕令暂缓觐见,1908年达赖才被首先批准进京入觐。作为曾经驻藏的官员,时任外务部右丞的张荫棠呈递条陈,建议清帝接见时要注意到达赖与班禅的关系问题。他建议清廷在达赖“提及班禅无论何事”时,要明确告诉他,达赖与班禅“同是黄教,宜同心以御外务,勿分畛域,诸事可由驻藏大臣奏明办理”。他还强调“如提及一切政务”,应告诉达赖“汝是出家人,以清静为主,应遵守历辈达赖宗教,专理黄教事务,凡内政、外交一切事宜,有驻藏大臣自能妥慎筹办。现下藏内大局已定,英兵亦已撤退,可以无虑,汝其勉之”。(21) 同年,达赖进京朝觐,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予以接见,加封他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谕令按年赏赐廪饩银一万两,同时要求他回藏后“所有事务依例报明驻藏大臣,随时转奏,恭候定夺”,以期“疆域永保治安,僧俗悉除畛域,以无负朝廷护持黄教、绥靖边陲之至意”。(22)
张荫棠的建议有两个重点,在清政府的谕令中都有所反映:一是要求达赖协调与班禅的关系,“同心以御外务,勿分畛域”,而清政府强调“僧俗悉除畛域”,也部分地包含了这层意思。二是改变1793年《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的有关规定,剥夺达赖喇嘛管理西藏政务的权力,让他与班禅一样“专理黄教事务,凡内政、外交一切事宜”,由驻藏大臣全权管理西藏政事。这与张荫棠过去的治藏建议有相同之处。1907年2月,他致电外务部电陈奏治藏规划,主张“收回政权”,实行新政,涉及行政管理体制变革、练兵、开矿、办学、外交、经济等多项内容,其中主张“优渥达赖、班禅,恢复藏王体制,以汉官监之”;“特简亲贵为西藏行部大臣”,其“体制事权,一如(英属)印(度总)督用王礼”。(23) 清政府只是部分接受了他的建议,又结合到以往的惯例,要求达赖依照旧制经驻藏大臣转奏政事,限制达赖参与政务的权力,树立驻藏大臣的权威,保障中央在西藏的施政。
张荫棠的新政建议在驻藏大臣联豫任职期间得到了部分的实现。联豫驻藏期间特别是1907年后大力推行新政,包括创办《西藏白话报》、印书局和兴办学堂,设立督练公所和巡警总局,设立曲水、哈拉乌苏等名委员等。(24) 这些措施触动了西藏部分上层人士的利益,与达赖为代表的僧俗封建主发生严重冲突。达赖1909年回到拉萨,不久就与联豫产生矛盾,1910年初川军入藏又让他惊恐,再次离开拉萨,而后逃亡印度。联豫为此奏报清廷,指责达赖“气象矜张,言词傲慢”,“日夜密谋,赶造枪枝子弹,分别调兵”,私设铸币厂、私铸银钱等等。(25) 根据联豫的奏报,清廷在1910年2月下旨,指出达赖“骄奢淫佚,暴戾恣睢”,“跋扈妄为,擅违朝命,虐用藏众,轻启衅端”,革除其名号,“嗣后无论逃往何处及是否回藏,都视与齐民无异”,又下令另选灵童,作为十二世达赖的“真正呼毕勒罕”。(26)
十三世达赖再次被革除名号,达赖系统与驻藏官员的矛盾也再次激化。此后,联豫加紧在西藏推行新政,力图让驻藏大臣衙门接管各项政务,同时又主张让班禅到前藏“暂掌教务”,以稳定局势。作为回应,班禅勉强在拉萨呆了几个月,而后婉言谢绝这一任命,同时还“为已革达赖乞恩”,希望清廷能为十三世达赖开复名号。清廷为此发布上谕,询问联豫:班禅既然为达赖乞恩,“达赖是否确系悔过安分自愿回藏?”如果留班禅在前藏暂掌教务,已革达赖所属的噶伦等人“是否悦服,彼此可以相安”?清廷还表示:“如班禅与达赖消除从前意见,为彼求复职掌”,倒可以“酌量筹商”,但达赖的权限必须明确为“只准管理教务,不准丝毫干预政权”。(27)
九世班禅之所以拒绝“暂掌教务”,并请求清政府开复达赖名号,正如他在事后所解释的:他知道清政府“想教他夺取达赖的位置,这是实在的事情”,但他已经“婉辞谢绝”;他到达拉萨后,与驻藏大臣“办理交涉时,确曾在达赖的宝座上”,这是因为“当时没有预备别的住处,所以他只好在那儿处理一切”。他甚至表示,他到拉萨“完全是被要挟,他宁愿牺牲性命,也不愿对达赖喇嘛有不利地方”。(28) 这表明,在复杂的局势下,班禅努力与达赖方面搞好关系,维护西藏地方上层的内部团结。即使如此,达赖方面仍不放心,据柏尔记述,1910年后流亡印度的达赖及其部属“一直监视着班禅喇嘛的行为。中国当局支持班禅喇嘛,希望加深他和达赖之间的不和,以便更易于维护自己对西藏的控制。这两位高级活佛在各方面都存在着利害冲突,他们的不和几乎不可避免”。(29) 对此,当时在驻藏新军中任职的谢国梁也认为:“达赖出奔大吉岭,驻藏大臣联豫奏请褫夺达赖徽号,尊班禅为教主。班禅出任调停,仍请达赖回藏。协商未妥,联豫接班禅来拉萨,尊礼甚优,达赖愈怀猜忌,致生恶感。”(30) 因此,达赖流亡印度和被裭革名号后,清政府再次要求班禅“暂掌教务”,的确使达赖、班禅关系严重恶化。
直到1911年秋,十三世达赖一直流亡印度,回藏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流亡印度期间,由于英帝国主义的拉拢和亲英分子的煽动,曾意图联俄抗英的达赖转向了亲英,对清政府及其驻藏官员颇为敌视。这期间,柏尔始终与达赖方面保持密切联系,他就此指出:“达赖喇嘛亲英亲俄,但反华”,他的噶伦们“清一色地亲英”,基巧堪布“既亲英又亲俄”,而“班禅喇嘛亲英,但反对拉萨”。(31) 英帝国主义者因此趁机介入,力求借调和达赖、班禅矛盾之机,控制西藏的两大活佛系统,实现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时任英国驻亚东商务委员的麦克唐纳(David Macdonald)称,1910年达赖逃往印度后,“扎什伦布和拉萨两地大喇嘛中间,失掉些许感情”,班禅方面派人到亚东请麦克唐纳进行调解,“向达赖喇嘛解释误会,免得日后两方情感日趋恶化,发生战争”。达赖就此向麦克唐纳表示:他对“师兄班禅绝无芥蒂”,但双方的部属“不免稍有衔恨”。而后,在英国人的联络下,达赖、班禅在拉兰举行会谈。可是双方在会议后矛盾非但没有化解,反而加深,达赖的部属之所以反感乃至反对班禅及其部属,原因包括:其一,达赖逃亡后,班禅被清政府请到拉萨“占据达赖的位置”。达赖方面认为这“形同篡窃”,尽管班禅拒绝清政府的“暂掌教务”任命,但“班禅走近拉萨,政治上已铸成大错”,因为班禅前往拉萨给他们的印象就是班禅对清政府的任命“定有采纳的倾向”。其二,班禅方面的重要官员“有倾向中国心理”。其三,1904年英军侵藏时班禅方面不帮助西藏地方政府。其四,1904年以来班禅辖区就拖欠西藏地方政府税银数十万卢比。(32) 达赖方面的这四条“理由”都是1904年以后产生,很显然第一条是最主要的,因为达赖部属最担心班禅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取代达赖,他们会因此丧失既得的权势;第二条则是达赖部属中的亲英、亲俄分子所害怕的;第三、四条都是借口,第四条尤其站不住脚,因为班禅辖区的赋税自清前期始就由班禅方面支配。
三
从19世纪70年代起,达赖、班禅两大系统开始出现明显的矛盾,清朝中央政府和驻藏大臣又从对达赖、班禅都有所猜忌到公开支持班禅系统、压制达赖系统,使两大系统的矛盾不断激化,达赖方面与清政府、驻藏官员的矛盾也不断加深。这些都对20世纪上半期40多年的西藏治理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
第一,清政府的治藏政策和驻藏大臣的治藏措施使当时两大系统的矛盾更为尖锐。对于达赖、班禅两大系统从和好演变为冲突、对立的原因,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有人加以论述,达赖、班禅本人的差异及其部属之间的冲突是关注的重点。如被称为“西藏通”的英国人柏尔曾在英属印度任职多年,与达赖、班禅两大系统都有交往,他说“拉萨与札什伦布之间妒忌甚深”,西藏人认为两大活佛自己“毫无敌意,惟其部下互相倾轧”。尽管东方人有“凡事有过,则归咎于臣而不归咎于君”的习惯,但他个人也认为,两大活佛“濡染宗教既深,当能超脱于妒忌之情”,而“其部下之敌视,诚较其主更为激烈”。(33) 柏尔还指出,达赖、班禅性格差异很大,“达赖专横傲慢,而班禅却忍让谦恭”,“假如达赖的性格与班禅的性格一样,他就不可能在管束西藏那些难以驾驭的人方面获得他已经获得的成功”;达赖、班禅“个人似乎关系很好,但在他们的下属之间却总是存在着嫉妒情绪”,达赖每次与他谈起班禅“语气总是友好的”,而达赖的心腹极力“反对班禅”。(34)
近年来,学术界对此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有学者指出历史上形成的达赖、班禅活佛的不同特点,特别是他们对政治、宗教关注程度的不同,而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发生了多次的误解和冲突,包括升泰任职期间查获达赖与沙俄往来信件、1902年班禅在布达拉宫门前击鼓事件、1903年英军从班禅所辖的岗巴退出后从噶厦所辖的亚东入侵、1910年达赖逃亡后班禅到拉萨代理政务、1911年西藏变乱后班禅系统的“亲汉”举动等。而英国的拉拢、离间是“导致达赖班禅两大活佛关系破裂的罪魁祸首”,清末驻藏大臣的错误施政加深了达赖、班禅的矛盾,达赖、班禅手下的“相互谗构”又使本已不睦的达赖、班禅关系火上浇油。(35) 笔者赞同这些分析,并认为:英、俄等国为侵略西藏扶植代理人而对达赖、班禅实行拉拢、挑拨,始终是近代以来达赖、班禅关系不和的首要因素和最主要的外因,帝国主义扶植的分裂势力的作用则是最主要的内因;而双方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清政府的治藏政策和驻藏大臣的施政,也都是导致两大系统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
就政治立场而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俄两国加紧争夺西藏,争相拉拢达赖、班禅,又由于清政府对外妥协和某些驻藏官员的处置不当,两大系统的政治立场也逐渐发生变化。最初是拥护中央政府、同心协力抗击侵略者,然而在抗击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后西藏上层逐渐分化,逐步形成了亲英、亲俄势力。这两种势力的影响力在达赖系统中最为强大,甚至有时左右了达赖的言行。班禅系统虽然与英印方面有一定联系,1905年甚至被诱骗赴印,但是该系统的政治立场始终是热爱祖国、反对分裂、维护西藏内部团结和国家统一。1904年以后达赖系统中亲帝分裂势力长期压迫班禅系统,即使是班禅方面的合理、忍让举动也被视为有所图谋,当十世班禅两度拒绝中央让他代管西藏政务的要求时,他们仍无端指责。他们多次无理指责、无端挑衅,激起西藏爱国上层和民众的愤怒,以班禅系统为代表的爱国力量与他们进行了长期斗争,这就使双方的矛盾、冲突超出了两大系统本身,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分裂与反分裂、卖国求荣与爱国爱藏的政治斗争。
从清政府的治藏政策来看,为治理西藏、巩固西南边疆,清政府一直力图协调达赖、班禅两大系统的关系,以取得让双方都效忠清廷以统治西藏的效果;但是,在不同阶段对两大系统的矛盾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使双方矛盾或缓或急,却始终未能使双方和好。1904年以前,虽然鹿传霖等四川、西藏的地方官员对达赖、班禅两方面都有所猜忌,但清中央政府在政策上更多的是维护西藏地方上层的内部团结,维持清前期确立的以达赖系统为主导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对于八世班禅“惑习红教”的处置就表明这一立场。不过,虽然有关官员报告了班禅“附于英”、达赖“结好”沙俄的有关情况,清政府得知英、俄对西藏上层的拉拢、分化的动向,但由于国势日衰和推行对外妥协的苟安政策,并未采取有效措施阻止这一趋向,致使英、俄两国得以有恃无恐地实施培植代理人、控制西藏的阴谋。这就使达赖、班禅两大系统的矛盾日益恶化,特别是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后,加剧了西藏上层的分化:僧俗上层总体上对清政府能否维护西藏各族利益缺乏信任感,在维护统一和维护西藏本地利益上,爱国反帝力量的周围环境日益窘迫;亲帝分子加紧活动,利用西藏民众爱国守土、维护自身利益和反对清政府对外妥协的心理,煽动寻求英国或者沙俄的“保护”,再加上英、俄的拉拢,自然就出现达赖、班禅的部属甚至他们本人是“亲俄”、还是“亲英”的种种说法。
1904至1911年间,面对英军侵入拉萨后西藏的严重形势,清政府采取了利用双方矛盾相互牵制的政策。作为这一政策的执行者,这一时期的驻藏大臣或多或少地采取相关措施,力图取得“以班禅制达赖”、维护平衡的效果。达赖出逃后,有泰、联豫都建议清廷由班禅暂摄或代管藏事;张荫棠是被当时和后世所称道的治藏“贤臣”,但他得知班禅有“代理达赖之意”后竟又把这一情况“告知藏王”,让噶厦的噶伦们极为惊慌,“以为班禅来京后达赖必致失位”。在当时统治者看来,这种做法可以收到牵制双方、共同效忠的效果,但实际上却事与愿违:一是由于历世班禅主要关心宗教,较少介入西藏政务,又一直拥护中央政府,希望与达赖团结一致对抗外国侵略,这种政策使九世班禅被迫放弃重宗教、轻世俗的传统,又背上与达赖争夺名利的心理包袱,他本人及其大部分部属因此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和心理压力。1910年,九世班禅到拉萨后表示自己“完全是被要挟,他宁愿牺牲性命,也不愿对达赖喇嘛有不利地方”,并非毫无依据。二是加剧了双方的矛盾,使两大系统对清廷都有疑虑甚至是不满,尤其是达赖两度被革除名号,与清廷、驻藏官员矛盾日益加深,该系统又握有实权、影响很大,再加上英、俄两国趁机挑拨,显然不利于清政府在西藏地方的施政,更不利于团结一致、反对侵略、维护统一、稳固边疆。
第二,由于清末实施利用班禅系统压制达赖系统的政策,两大系统的矛盾在辛亥革命后总爆发,此后数十年间两大系统纠葛不断,矛盾不断加剧,使西南边疆危机不断。
1911年11月,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西藏后,驻藏川军发动反清起义,由于英帝国主义的挑拨和亲英势力的煽动以及川军内部的派系斗争,出现川军内讧、川军与藏军对抗的局面,并波及川边地区。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中央政府6月命令四川、云南两省派军西征,到9月基本恢复川边辖地,这年底驻藏官员、军队又被迫全部撤离西藏。在这一过程中,达赖、班禅两大系统对驻藏新军及中央政府的态度明显不同,又加深了已有的矛盾。九世班禅在1913年给中央政府的一份电文中就表示自己“久仰中朝,实沾德惠”,藏乱其间“凡在我属汉边军民等,无不力加保护,借饷筹食,无微不至”,已引起达赖系统的不满,西藏地方政府见其“向汉心切,意图他举”。(36) 柏尔的记载也证实了一点,他说:“中国戍兵哗变”后西藏形势混乱,“达赖间谍复煽动之”,致使川军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而“西藏政府之行动大受党派猜忌之阻碍”,“班禅之政府暗与中国人勾结,不援助其拉萨同胞”。(37)
达赖、班禅两大系统在这场变乱中的不同表现,主要是双方的政治立场、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差别造成的,特别是达赖方面对清政府极为不满,对执行这一政策的驻藏官员、军队颇为敌视,在英帝国主义的挑拨、支持和亲英分子的煽动下,力图打着维护西藏政教利益的旗号,把清政府在西藏的军政势力驱逐出去。两大系统的不同立场和表现,又反过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十三世达赖返回西藏后,控制了西藏地方政权,更以强大的军政优势压制班禅方面,导致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在此情况下,北京民国政府及时调整了对两大系统的政策:其一,在1912年10月28日恢复十三世达赖“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的名号,1913年4月又加封九世班禅“致忠阐化”的名号。其二,同时嘉奖达赖、班禅两大系统的上层人士,如1913年8月24日民国政府表彰、嘉奖西藏旅京代表江赞桑布、阿旺根敦、阿旺曲扎等人,其中既有前藏人士,也有后藏的阿旺曲扎。其三,在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中,西藏地方共选出40名众、参两院正式和候补议员,前藏(达赖系统)、后藏(班禅系统)名额相同。这些不仅表明中央政府在政治上平等对待达赖、班禅两大系统的立场,而且从法律上保障了西藏地区人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有利于中央政府恢复、加强与西藏地方的政治联系。(38)
对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治联系的加强,英帝国主义及其扶持的西藏分裂势力极力阻挠、破坏:先在西姆拉会议上炮制分裂祖国的方案和非法的“草约”,接着利用十三世达赖推行新政之机,削弱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又挑拨达赖、班禅两大系统关系,致使1923年九世班禅被迫离开西藏;极力阻挠九世班禅返藏,以致这位爱国活佛在1937年底抱憾圆寂于玉树,此后至1949年间又长期干扰其转世灵童的寻访、十世班禅的确认,使两大系统的矛盾更加尖锐。双方的矛盾无疑对中国边疆的稳固产生了消极影响:西藏上层的内部冲突、西藏地方与历届中央政府矛盾的长期存在和不时激化,中央政府不得不忙于协调达赖、班禅关系和恢复、巩固在西藏主权;英帝国主义则利用这种矛盾炮制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蚕食鲸吞中国西南地区的领土,至今影响着西南边疆的稳定和中印关系的正常发展。
注释:
① 参见张云:《漂泊中的佛爷——九世班禅内地活动的前前后后》,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② 就笔者所见,相关记载有: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1925年铅印本),陈健夫《西藏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英国人柏尔(Charles Bell)《西藏的过去和现在》(Tibet,Past and Present,Oxford,1924)、《十三世达赖喇嘛传》(Portrait of Dalai Lama,London,1946),麦克唐纳(David Macdonald)《旅藏二十年》(Twenty Years in Tibet,London,1932)等。这些著作介绍了相关事实,大多是叙述见闻,难以称为学术上的深入研究。1950年至今相关研究有:李有义《记达赖与班禅》(《历史教学》第2卷第1期,1951年7月),高长柱《西藏概况》(台北1953年版),芈一之《九世、十世班禅与西藏问题》(《藏学研究论丛》第2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金雷《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原因探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黄玉生等著《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版),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班禅额尔德尼传》(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吴丰培、曾国庆著《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版),张云《漂泊中的佛爷——九世班禅内地活动的前前后后》等,都对此有所研究。西文著作中,对此较多涉及的是加拿大学者谭·戈伦夫(A.Tom Grunfeld)的《现代西藏的诞生》(伍昆明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其中第四章根据麦克唐纳的记载简要论及达赖与班禅的关系。
③ 参见《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25—826页。
④ 参见金雷:《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原因探析》;牙含章:《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按:牙含章先生认为八世班禅未被邀请给十三世达赖受戒是因为他当时患病,“不能前来拉萨”(见《达赖喇嘛传》第98页,《班禅额尔德尼传》第198页)。
⑤ [印]萨拉特·钱德拉·达斯、[美]W·W·罗克希尔编,陈观胜、李培茱译:《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页,附房建昌文《达斯、罗克希尔与生钦活佛和仲孜寺》。
⑥ 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8—299页。
⑦ 松溎:《班禅惑习红教现令改悔片》,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2页;《清德宗实录》卷45,光绪二年十二月壬寅。
⑧ 鹿传霖:《瞻对收复请撤回番官并陈英俄窥藏情形疏》,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第1015—1017页。
⑨ 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1925年铅印本,第10页。
⑩ 有泰:《致外务部电达赖潜逃乞代奏请旨褫革其名号电》、《达赖喇嘛兵败潜逃声名狼藉据实纠参折》,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第1190—1194页。
(11) 《清德宗实录》卷533,光绪三十年七月壬辰。
(12) 《清德宗实录》卷543,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丙戌。
(13) 有关班禅赴印的问题,有关论著如牙含章的《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都有所论述,一般认为是英人武力胁迫班禅赴印,近年有学者根据英国档案提出新的认识,参见伍昆明:《英印政府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与九世班禅赴印》,《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14) 参见张荫棠:《致外务部电英诱班禅请电有大臣阻止》,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第1298页。
(15) 有泰:《外务部阻止班禅赴印电》、《英员强逼班禅额尔德尼赴印阻止不从折》,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第1217—1219页。
(16) 张荫棠:《致外部电陈印政府优待班禅并舆论》,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第1301页。
(17) 有泰:《班禅额尔德尼赴印详情川》,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第1229—1230页。
(18) 张荫棠:《外部来电倘班禅擅定条约概不承认请密探班禅举动》,《旨准班禅照旧供职电》,《致外部电奏班禅由印回藏恳免处分》,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第1301—1305页。
(19) 参见张荫棠:《上外部条陈招待达赖事宜说帖》,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第1444—1445页。
(20) 《清德宗实录》卷568,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壬辰。
(21) 张荫棠:《上外部条陈招待达赖事宜说说帖》、《上外部请预筹达赖提议赡事及优加赏赉说贴》,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第1444—1445页。
(22) 《清德宗实录》卷597,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壬戌。
(23) 张荫棠:《致外部电陈治藏刍议》,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第1328—1330页。
(24) 联豫任职期间的西藏新政,可参见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苏发祥:《清代治藏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马菁林:《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巴蜀书社2004年版;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等。
(25) 联豫:《详陈已革达赖私逃情形并请惩番官折》,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第1537—1538页。
(26) 《宣统政纪》卷30,宣统二年正月丁巳。
(27) 《宣统政纪》卷48,宣统三年正月丁巳。
(28) [英]麦克唐纳(David Macdonald)著,孙梅生、黄次书译:《旅藏二十年》,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84页。
(29) [英]柏尔(Charles Bell)著、冯其友等译:《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编印,第116页。
(30) 谢国梁:《班禅被逼出走后规划西藏条陈》,张双志辑:《民国筹藏刍荛集》,收入张羽新、张双志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4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68—70页。
(31) [英]柏尔著、冯其友等译:《十三世达赖喇嘛传》,第115页。
(32) 参见[英]麦克唐纳著,孙梅生、黄次书译:《旅藏二十年》,第76—83页。
(33) [英]柏尔著、宫廷璋译:《西藏之过去与现在》,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54—58页。
(34) [英]柏尔著、冯其友等译:《十三世达赖喇嘛传》,第130、315页。
(35) 参见张云:《漂泊中的佛爷——九世班禅内地活动的前前后后》,第16—27、36—38页。
(3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蒙藏院档案《国务院秘书厅奉发班禅倾心内向电致蒙藏事务局公函》(民国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371—2372页。
(37) [英]柏尔著、宫廷璋译:《西藏之过去与现在》,第79—80页。
(38) 详见孙宏年:《蒙藏事务局与民国初年的边疆治理论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