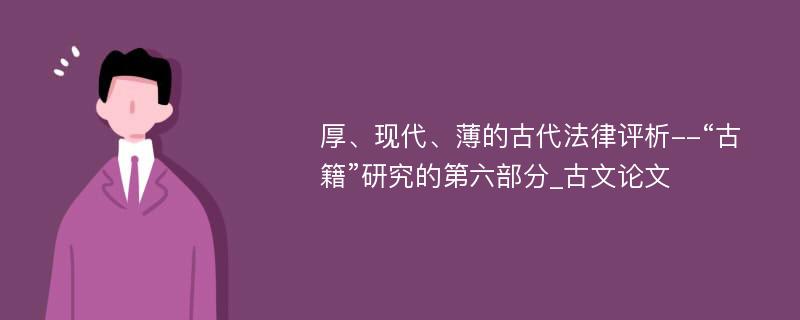
評閻若璩的厚今薄古法——《尚書古文疏證》研究之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厚今薄古论文,古文论文,之六论文,評閻若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閻若璩生當疑古思潮盛行的時期,而定古文《尚書》爲“僞”亦是清朝官方的文化政策。清代學者陳履和述:“伏思我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皆奉高宗純皇帝欽定,刊布海內,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之僞,朝廷早有定論。”①由于這樣特殊的歷史條件,因而當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一出,就受到熱烈追捧。古文《尚書》之僞,遂成“定案”。改革開放以來,學者們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開始對疑古時代的許多“僞書”進行反思。有學者著《先秦僞書辨正》,對先秦四十九部僞書“重新考證”。②有學者著《審核古文〈尚書〉案》,對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作“全面甄別”,認定所謂“僞古文《尚書》”的“定案”無法成立。③雖然有學者提出异議,進行駁難④,但反思的大門已經打開,真理將愈辯愈明。
經過長期研究探索,對于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以下簡稱《疏證》),筆者發現其采用了八種不正當的辨僞方法。“他的絶大部份證據都是似是而非,因而是不能成立的”。⑤
《疏證》的第一種辨僞方法是二難推理。如它把古文《尚書》與其他文獻進行比較:發現相同是古文“剽竊”,若有不同是古文“改竄”,二者都可證明古文之“僞”。這樣的二難推理,共有三種程式,二十三條具體實例。這些推理嚴重背離歷史事實,“只不過是玩弄没有意義的文字游戲”。⑥
其第二種辨僞方法是吹毛求疵。它有“用周禮的規定去尋找夏代、商代文獻的‘僞’證”等五種程式,共二十七條實例,“都是無中生有,是非顛倒,有些是非常可笑的”。⑦
《疏證》第三種辨僞方法是虛張聲勢。它有“胡扯無關《尚書》古文者”、“宣傳懷疑古文歷史”、“開列條目而不作文”、“大談僞書易撰”等六種表現,共六十五條實例。這些超過全書一百二十八條的半數,都是“胡拼亂湊或無內容的空條”。⑧
其第四種辨僞方法是顛倒先後。它有“胡編他籍文字‘竄入’古文書”、“臆造古文書‘忘采用’他籍引文”等六種程式,涉及近五十條實例,“都憑主觀想象,胡扯亂編,嚴重背離歷史事實”。⑨
本文所要集中剖析的,是其第五種辨僞方法。本來,《尚書》有今文和古文之分,是因爲其發現和流傳過程的不同。自秦火之後,漢初伏生從自家壁中發得《尚書》若干篇,他以今文書寫,教于齊、魯之間,此即今文《尚書》。至景帝時,河間獻王從民間徵集,獲得大量古書。《漢書·景十三王傳》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之屬。”⑩武帝時,魯恭王又于孔子宅壁中得古文《尚書》多篇。這些古文《尚書》流傳至魏晋間,形成明確的傳授關係,東晋初由梅頤獻上而公布于衆。應該說,《尚書》中今文和古文兩部份,都具有極珍貴的價值,它們是《尚書》的雙璧或雙翼。可是,閻氏《疏證》對《尚書》的今文和古文,采取完全不同的態度:對今文千方說好,對古文百般說壞。這樣的辨僞方法,姑名之曰“厚今薄古”。經梳耙整理,閻氏的厚今薄古法,約有如下六種表現:
一、祈鬼神盼今文“孤行”
《疏證》“第五十九言《書》之隱見亦有時運,古文盛行已久後當廢”說:“道之行廢繫于命,予則謂《書》之隱與見亦有時運,初非人意料所能及者。嘗思緯書萌于成帝,成于哀、平,逮東京尤熾……焉能料二百載後,其學浸微……又思天下所廟祀者……讀《風俗通義》,城陽景王祠遍滿琅邪、青州六郡……讀《明一統志》,僅莒州一處存耳。懸絶如此,豈非鬼神,亦關氣運、冥報,各有時代。古文《書》二十五篇,出于魏晋,立于元帝,至今日運已極……安知後不更有歐陽氏出,請以删讖緯者删此古文,尊正義者尊伏生(今文)三十一篇,俾其孤行乎!亦《書》之運也,吾終望之維持此運者。”(11)
這一條“疏證”,祈望依靠“時運”、“鬼神”、“氣運、冥報”的佑助,有人出來像“删讖緯”那樣“删此(《尚書》)古文”,而使今文“孤行”,有許多觀點值得評論。
首先,它把《尚書》古文比作“讖緯”,這是極不恰當的。讖緯是一種神學,預言吉凶,把自然現象神秘化,對社會的變動、王朝的更替推波助瀾,造成社會的不安定因素。這種神學,在西漢後期因得到統治者的支持而盛行,但它對社會的發展是不利的,因而“二百載後其學浸微”,乃極自然。而《尚書》古文是記載上古三代歷史事實的史學,它像《資治通鑑》一樣,對人們的行爲、國家的治理有借鑒和懲戒作用,對社會的文明與進步是十分有益的。它不可能如閻氏所說“有時運”,“盛行已久後當廢”。
其次,它把《尚書》古文的流傳比做“廟祀者”,更是荒唐可笑的。其舉例稱,漢代“城陽景王祠滿遍琅邪、青州六郡”,而到明代“僅莒州一處存”,這顯然是由于政治勢力的興衰所致,而絶對不是如閻氏所說:“豈非鬼神,亦關氣運、冥報,各有時代。”古文《尚書》的流傳,當然與統治者的文化政策關係極大,但更重要的,是它的真實性及其學術價值。如果古文《尚書》是真實的古文獻,有珍貴的學術價值,它不可能像“讖緯”和“廟祀者”那樣,盛行一段時間後就遭廢斥或衰落。《疏證》謂“古文《書》二十五篇”,“至今日運已極”,這個如讖緯般的預言,絶不會實現。
再說,閻氏要藉助鬼神、氣運、冥報的力量,請出能人來“删此古文”,並“尊伏生”今文,“俾其孤行”,這對中國文化將是一個不小的灾難。筆者曾撰文論證,“古文《尚書》補充許多歷史事實”,“保存大量格言和成語”,“可考知舊籍引語的背景和用意”,“可訂正舊籍引文之誤”,“可糾正舊注之誤”。(12)歷史上經常引用的警語名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就出自古文《尚書》中的《五子之歌》。有著這樣珍貴價值的古文《尚書》,怎可“删”除和“廢”斥?在閻氏《疏證》行世、“僞古文《尚書》”“定案”後,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學者們從事歷史研究不敢引古文《尚書》了,有些《尚書譯注》的本子乾脆把古文部份删掉,大有使今文“孤行”的勢頭。不過,自改革開放以來,不少學者反思疑古時代的錯誤,古文《尚書》的珍貴資料開始重新得到運用,學術界又呈現出勃勃生機。
還應該指出,閻氏《疏證》對于古文《尚書》,有一種非理性的憎惡,因而往往感情用事,不能實事求是地進行研究。如第十七條對皇甫謐責難說:“皇甫謐,高名宿學……渠實得孔書,載于《世紀》,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書首信于世者,皇甫謐之過也。”(13)按魏晋之際的學者皇甫謐,從其外弟梁柳處“實得”孔傳古文《尚書》,因而在其所著《帝王世紀》中大量載有古文《尚書》之文,計有《五子之歌》、《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君牙》、《伯冏》(即《冏命》)等篇。(14)皇甫謐相信孔傳《尚書》是真古文獻,在其著作中充分運用其資料,進行轉述和論證,他對于中國優秀文化的傳播是有功的,爲什麽要對之責難而稱其爲“過”呢?
《疏證》此條接著又說:“賾雖奏上得立于學官,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微,或鄭行而孔微,或孔、鄭並行。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爲之疏……是使此書更信于世者,孔穎達之過也。”(15)按唐孔穎達相信孔傳《尚書》是西漢以來長期流傳的真古文獻,因而作《尚書正義》用孔傳本進行疏證,並詳細論述該書的流傳過程,指出漢代學者如鄭玄、馬融等因不見古文而造成的錯訛。(16)孔穎達對流傳的各種《尚書》本子進行甄別、選擇,並作詳盡的疏理、論證,他對于《尚書》學以及許多古籍是一大功臣,爲什麽又要稱其爲“過”而加以責難呢?
對于古文《尚書》的憎惡,閻氏《疏證》更有不可理喻者。此條接著又說:“吾族之有敗類,猶吾之一脉也,乃若斯人固循循然,固斌斌然,而終非吾之族類也,吾恐吾祖宗之不血食也!僞古文何以异此!”(17)按學術研究,討論古文《尚書》的真僞:真者評論其價值,放心使用其資料;僞者追究其原因,對其資料必須慎用。但閻氏卻把“古文”比做一個人,“斯人固循循然,固斌斌然,而終非吾之族類也”;若“斯人”繼續存在下去,“吾恐吾祖宗之不血食也”,即祖宗没有人來祭祀,“吾族”就要敗亡。因而他想出了八種不正當的辨僞方法,必欲置“斯人”于死地而後快。這實在不是一個學者應有的態度。
二、虛構古文亡于西晋亂
要證明古文《尚書》之“僞”,首先要證明西漢時發得和徵集的真古文《尚書》已經亡佚。于是,閻氏虛構了一個“古文亡于西晋亂”的論斷,以其證今傳古文《尚書》之“僞”作爲鋪墊。《疏證》“第二言古文亡于西晋亂,故無以證晚出之僞”說:
嘗疑鄭康成卒于獻帝時,距東晋元帝尚百餘年,古文《尚書》十六篇之亡,當即亡于此百年中。後讀《隋書·經籍志》:“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永嘉喪亂,經籍道消……故古文《尚書》之亡,實亡于永嘉。嗟乎!嗟乎!出于伏生之口者,秦火不得而焚之;
出于孔氏之壁者,□亂遂得而滅之矣。(18)
在其他場合,《疏證》還不斷宣傳這一論斷。如第一百十三條說:“原來當兩漢時,安國之《尚書》雖不立學官,未嘗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亂而亡。”(19)第一百二十條又說:“古文《書》至東漢始有訓注……故有時合而爲一,則如《漢志》所載……合則永亡,晋永嘉之亂是也。”(20)
上述關于古文《尚書》亡于西晋永嘉之亂,而且是“永亡”的論斷,突出地表現了閻氏《疏證》厚今薄古的用心。既然《隋書·經籍志》云,“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今文)《尚書》並亡”;閻氏自己也說,“永嘉喪亂,經籍道消”,爲什麽只有古文《尚書》亡而今文不亡呢?《疏證》解釋道:“(今文)出于伏生之口者,秦火不得而焚之;(古文)出于孔氏之壁者,□亂遂得而滅之矣。”這完全是胡攪!此條討論的是,“永嘉之亂”對《尚書》古文和今文的銷毁,而閻氏卻說今文“秦火”不得焚,這不是偷换概念嗎?再看《漢書·儒林傳》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21)可見今文“秦火”不得焚,是因爲“伏生壁藏之”。閻氏謂“出于伏生之口”,乃其胡編亂造。《疏證》千方百計開脫今文而“滅”“亡”古文,這就是其運用的厚今薄古法。
然而,古文《尚書》並没有在永嘉之亂中滅亡,它的傳授脉絡記載于唐孔穎達撰的《尚書正義》中。其引《晋書》云:“晋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皇甫)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當作‘頤’),字仲真,又爲豫章內史,遂于前晋奏上其書而施行焉。”(22)對于這一段傳授記載,著名史學家陳夢家曾作過查證。他說:“自鄭沖到梅頤的傳授,皆有史籍可考,其時、地、人三者都相符合。”(23)據《晋書·鄭沖傳》,沖卒于晋武帝泰始十年,即公元274年。梅頤“奏上其書”,“學者一般推定其事在(東晋)元帝建武元年至太興元年”(24),即公元317-318年。而永嘉之亂發生在晋懷帝永嘉四年至六年,即公元310-312年,其時古文《尚書》正由鄭沖一代又一代傳至梅頤手中,妥爲保管,怎麽可能“滅”“亡”?
况且,古文《尚書》的流傳,還有孔氏家族的一個系統。《後漢書·儒林列傳》說:孔氏家族“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25)根據現代學者的研究:“今傳本古文《尚書》、《孔叢子》、《(孔子)家語》,很可能陸續成于孔安國、孔僖、孔季彥、孔猛等孔氏學者之手,有著很長的編纂、改動、增補的過程。”“東漢中晚期,這種(古文)《尚書》本子逐漸傳播流行。”(26)孔氏家族有著衆多的學者,他們有一種事業精神,長期保存並修訂古文《尚書》,使其日臻完善。因此,古文《尚書》更不可能在動亂中消亡。閻氏《疏證》厚今薄古,虛構“古文亡于西晋亂”,是違背歷史的真實的。
三、藉《孝經》、《禮經》詆毁古文
出于對古文經籍的憎惡,閻氏又在古文《孝經》和《禮經》上做文章。《疏證》“第二十言古文《孝經》以證《書》”云:“草廬吳氏其論始定,曰:‘以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古文(《孝經》)皆不合,參諸邢氏疏說,則其僞也决矣。’愚謂桓譚《新論》足以證今古文《孝經》之僞,豈不足以證古文《尚書》之真哉?”(27)
閻氏上述言論,語意比較含糊。實際上,其標題爲“古文《孝經》以證《書》”,目的就是以古文《孝經》之“僞”來證明古文《尚書》亦“僞”。然而這條路是行不通的。首先是因爲,古文《孝經》的情况與古文《尚書》完全不同。《孝經》的今文和古文,只是文字有异同和章節的增減分合;而《尚書》的今文和古文,有著完全不同的篇名、內容和發現、流傳過程:兩者不能進行類比和由此及彼的推論。
再說,古文《孝經》之“僞”,也是不符歷史事實的。據史記載,關于《孝經》今文、古文之争,唐開元年間,曾“詔令群儒質定:右庶子劉知幾主古文,立十二驗以駁鄭;國子祭酒司馬貞主今文”,找些證據“以駁孔”(28),雙方辯論難分難解。劉知幾議曰:“愚謂行孔廢鄭,于義爲允。”即要行古文,廢今文。司馬貞議曰:“望請準式,《孝經》鄭注(今文)與孔傳(古文)依舊俱行。”(29)可見關于《孝經》今文和古文的真僞優劣,在唐時也未能得出一致的結論。閻氏《疏證》欲以“古文《孝經》之僞”來證古文《尚書》,他的前提就是不能成立的。
《疏證》“第二十一言古文《禮經》以證《書》”又說:“《禮》與《尚書》,同一古文……而在《禮》者……奕代猶知寶之,欲輯爲經;而在《尚書》者,雖卷篇次第,確有源委,甚至明指某句出某篇,如‘載孚在亳’,‘征是三’,‘厥篚玄黄,昭我周王’,皆以爲是僞書。則以《禮》未爲諸儒所亂,而《書》則爲晚出之《孔傳》所屈厭也,豈不重爲此經之不幸哉!”(30)
這裏,閻氏《疏證》藉古文《禮經》而把古文《尚書》貶斥一番。其中列出古文《尚書》中的某些句子,接著就說“皆以爲是僞書”。有什麽證據嗎?没有。不列證據而信口亂說,是閻氏《疏證》的一貫做法。
然後,《疏證》又說:《尚書》“爲晚出之《孔傳》所屈厭”,“重爲此經之不幸”。什麽叫“屈厭”?查遍各種辭書,如《辭源》、《辭海》、《漢語大辭典》等,均未見此詞,應該又是閻氏胡編亂造的詞語。按其字面和邏輯來看,大概是糟蹋、損害之意。前已闡述,《孔傳》是孔氏家族世代專注之業。《孔傳》實包括孔氏家族保存的古文、今文《尚書》各篇文字及其對整部《尚書》的傳解。閻氏《疏證》中有許多條目,因《孔傳》中有些地名出現在武帝之後,就指《孔傳》爲“僞作”。那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孔氏家族的學者自西漢、東漢一直延續到三國,難道他們對先輩的傳解作些修訂,就變成“僞作”了嗎?唐孔穎達纂定的《尚書正義》,稱《孔傳》爲“孔氏傳”而不是“孔安國傳”,應該是考慮到這部傳解是孔氏家族共同撰著的成果,而非成于孔安國一人之手。《孔傳》保存了《尚書》中缺失的二十五篇文字,又對整部《尚書》作了傳解,而且它所保存的《尚書》今文部份,也比伏生保存的今文《尚書》爲優。如孔傳《尚書·禹貢》在叙述“青州”時,有“嵎夷”(31)這一地名。《史記·夏本紀·索隱》“按:《今文尚書》……作‘禺鐵’……鐵,古‘夷’字也。”(32)查《說文解字·金部》云:“鐵,黑金也。”“銕,古文鐵,從夷。”(33)由此可見,今文作“禺鐵”是錯誤的。“鐵”之古文作“銕”,並非“鐵,古‘夷’字也”。今文因“古文‘鐵’從‘夷’”而誤“夷”爲“鐵”,幸有《孔傳》本而予以糾正。且今文之“禺”,也當從孔傳作“嵎”,因爲這是一個山區的地名。
由上述分析可見,《孔傳》對于《尚書》,不但没有“屈厭”,而且彌補了相當多《尚書》缺失的篇章,大大地充實和豐富了《尚書》的內容;又對整部《尚書》作了深入淺出的傳解,爲人們讀懂《尚書》提供了方便;它所保存的今文部份,也較伏生所傳有優勝之處。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孔傳》古文的出現,决非“此經之不幸”,而是《尚書》之大幸。閻氏《疏證》厚今薄古,詆毁《尚書》古文,與歷史事實完全背離。
四、爲堯舜禹名號改今誣古
《疏證》“第五十九言重華、文命與放勛皆帝王號,僞作者不知”云:“堯、舜、禹亦皆有號,放勛也,重華也,文命也,三者即是也。何以別之?《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勛乃徂落。’……他日引堯之言爲‘放勛曰’,則可知其以是爲號也矣。唯至僞古文出,‘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不將‘重華’、‘文命’二字各斷爲句,與今文‘放勛’字面一例,而竟連下文‘協于帝’、‘敷于四海’,自不得解作號,而謂是史臣讚頌之辭矣。予痛其以僞亂真,而並古帝王之休稱鴻號、冠絶千載者亦掩没而不彰,豈不甚哉!”(34)
以上這條論述,有許多不符史實之處:
首先,關于堯號放勛,《尚書·堯典》的記述是這樣的:“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孔傳:“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勛,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35)可見這裏的“放勛”,是史臣讚美“堯放(仿)上世之功”,並非堯的“號”。至于《孟子》引《堯典》“放勛乃徂落”(36),實際應該是“帝乃殂落”(37);《孟子》引堯之言爲“放勛曰”,是孟子認爲堯號“放勛”,故如此說,實際未必。閻氏《疏證》論述堯的名號,不引今文《尚書·堯典》的記述,而以《孟子》所言作爲證據,充分表現了其在學術上不實事求是的態度。
再說,“重華協于帝”一句,見今《尚書·舜典》。孔傳:“華爲文德,言其光文重合于堯,俱聖明。”孔穎達疏述此句的來歷云:“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38)司馬遷《史記》述:“虞舜者,名曰重華。”(39)其根據應該就是《舜典》開頭的這句話,可見它的來歷是比較早的。“文命敷于四海”一句,見《尚書》古文《大禹謨》開頭。孔傳:“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孔穎達疏申述:“禹能以文德教命布陳于四海。”(40)司馬遷《史記》述:“夏禹,名曰文命。”(41)其根據應該也是《大禹謨》開頭的這句話。“重華”、“文命”二句話,它的出現比較早,影響相當大。閻氏《疏證》稱這二句是魏晋間出現的“僞古文”,與歷史事實完全不符。
關于“放勛”、“重華”、“文命”是否堯、舜、禹的名號,在歷史上是有争議的。雖然孟子、司馬遷有上述說法,但不少學者提出异議。朱熹在注《孟子》時說:“放勛,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號也。”(42)觀上引《尚書·堯典》記述,其論至確。《史記·夏本紀》“夏禹名曰文命”下,司馬貞《索隱》曰:“《尚書》云‘文命敷于四海’,孔安國云‘外布文德教命’,不云是‘禹名’。太史公皆以放勛、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名,未必爲得。孔又云‘虞氏,舜名’,則堯、舜、禹、湯皆名矣。”(43)司馬貞認爲,堯、舜、禹、湯都是“名”,而“文命”從《尚書》孔傳來看不是“禹名”,司馬遷把放勛、重華、文命當作堯、舜、禹之名,“未必爲得”,對《史記》之說提出批評。這應該是有見地之論。
閻氏《疏證》在堯、舜、禹名號問題上,隱瞞今文《尚書·堯典》的記述,而改以《孟子》之說當作“今文”;又把《舜典》“重華協于帝”、《大禹謨》“文命敷于四海”,這與《堯典》“放勛欽明文思安安”非常相似且出現較早的二句,誣爲“僞古文”。從《堯典》、《舜典》、《大禹謨》開首的這三句文字來看,“放勛”、“重華”、“文命”分明是“史臣讚頌之辭”,而非“帝王號”。因此《疏證》之感嘆:“予痛其(古文)以僞亂真,而並古帝王之休稱鴻號、冠絶千載者亦掩没而不彰,豈不甚哉”,完全是無病呻吟。所謂古文“以僞亂真”,是根本没有的事。這裏,閻氏的厚今薄古法,表現爲改今誣古,事實十分清楚。
五、查他籍引文保今斥古
他籍引《書》之文,在今傳《尚書》中找不到,這可能是古文的缺失,也可能是今文的缺失。但閻氏《疏證》卻千方百計保護今文,斥責古文,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態度。《疏證》“第七十七言《史記》有《夏書》曰,今忘采用”云:“(《史記》)《河渠書》首引《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余謂‘禹抑鴻水’,與《孟子》合;‘十三年’,與今文(《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合;‘過家不入門’,與《孟子》及今文(《益稷》)‘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合;‘陸行載車’以下,又與《尸子》及今文(《益稷》)‘予乘四載’合。其事事有根據,非苟作如此。魏晋間人竟以世所童而習之之書,書且開卷便見,忘其采用,豈非天奪之鑒,褫其魄,與吾今日以口實也哉!”(44)
按《史記·河渠書》有引《夏書》的一段話,據閻氏《疏證》分析,它有許多地方與今文《尚書》的《禹貢》、《益稷》等篇的叙事相“合”,“其事事有根據”。但這段引文,與今文《尚書》的詞句不同,很可能是今文《尚書》有所缺失,或者司馬遷對《夏書》引用其意而改動了文字。不管屬于何種情况,《史記》這段引文,既然與今文中的多篇叙事相“合”,應該與今文《尚書》關係密切,從今文《尚書》中查找。但閻氏接著筆鋒一轉,稱這段引文,是“魏晋間人”在僞作古文時“忘其采用”,並惡毒地指責是“天奪之鑒,褫其魄”云云。《史記》這段引《夏書》之文,在今傳《尚書》中未見,明明是今文《尚書》的問題,但閻氏只說引文與今文如何相“合”,再指責僞作古文的“魏晋間人”“忘其采用”,並用侮辱性的語言進行呵斥。其實,所謂“魏晋間人”“忘其采用”,完全是閻氏主觀想象的臆造,在歷史上不可能發生那樣的事。這裏,《疏證》查找引文缺失,保今斥古,事實十分明顯。
《疏證》“第七十八言《說文》有《虞書》、《商書》、《周書》等曰,今忘采用”又云:“(《說文》)有安國所不載辭至多……《虞書》曰……《商書》曰……《周書》曰……《尚書》曰……《書》曰……右皆魏晋間忘其采用者。”(45)
這一條與上條同樣,《說文》中有不少引《虞書》、《商書》、《周書》及《尚書》、《書》之文,在今傳《尚書》中未見,這可能是今文的缺失,也可能是古文的缺失,因爲《說文》未引篇名,不知這些引文屬今文還是古文。但《疏證》又采取保今斥古的辦法,對今文的問題隻字不提,而獨指古文,稱“右皆魏晋間(僞作古文時)忘其采用者”。其厚今薄古法,運用爲保今斥古,再一次作了生動的表現。
《疏證》還有一種原文“出自”引文或原文“剽竊”引文的怪論。如其第八條說:“(古文《胤征》)‘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此出《荀子·君道篇》所引《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46)按《荀子·君道篇》所引《書》,即古文《尚書·胤征》。因此,前者是原文,後者是引文。說原文“出”自引文,何等怪誕!但閻氏爲了把古文《尚書》證成“僞作”,不惜發表此種奇談。
按照閻氏《疏證》的手法,同樣可以說:“今文《尚書·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47),此出《荀子·修身篇》所引《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48)”這樣,便可把今文《尚書·洪範》證成“晚出”的“僞作”了。但閻氏《疏證》的厚今薄古法有一條原則:保今斥古。以原文“出自”引文的怪論來證“晚出僞作”的方法,《疏證》絶對保護不用于今文,而只對古文進行證“僞”和斥責。
《疏證》第七條又說:“晚出之古文……亦知剽竊……即于《墨子》,亦知剽竊‘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亦知剽竊……”(49)按古文《尚書·泰誓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50)《疏證》謂古文“剽竊”的《墨子》引文見《兼愛下》篇。(51)對比古文《泰誓》和《墨子》引文兩段文字:古文自然貼切,文句通順流暢;而《墨子》引文較欠强,不通順。《泰誓》是武王的誓師講話,《墨子》引文怎能直稱其父爲“文王”?且引文“乍照光”,語甚淺薄。顯然,古文《泰誓》是原文,《墨子》引文因記憶不清,只引其大意而語詞欠妥。說原文“剽竊”引文,實在是荒謬之論。
依閻氏《疏證》之手法,同樣可以說:“今文《尚書·呂刑》亦知剽竊《墨子》‘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52)今文《尚書·康誥》亦知剽竊《孟子》‘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53)今文《尚書·洛誥》亦知剽竊《孟子》‘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54)”這樣,今文《呂刑》、《康誥》、《洛誥》都成了“晚出”的“僞作”。如依閻氏的八種辨僞方法,作一本《尚書今文疏證》,則整部今文《尚書》,都可證成伏生的“僞作”。但閻氏《疏證》的厚今薄古法,决不對今文作如此論證。它嚴格遵循這樣的原則:保今斥古。其對于今文和古文,實行態度鮮明的區別對待。
六、用不實理由揚今貶古
例1.《疏證》第九十八條抄録姚際恒之言云:“伏書之誓,《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凡五篇。誓辭之體,告衆皆以行軍政令及賞罰之法爲主……若《秦誓》,則因敗悔過,別是一格……今《泰誓》上中下三篇,僅有賞罰二語,絶口不及軍政。惟是張目疾首、洗垢索瘢,若恐不盡。嗚呼,誓辭至此,蕩然掃地矣!”(55)
按此條將今文五篇誓辭,與古文《泰誓》三篇進行比較。其先定一條標準,“誓辭之體,告衆皆以行軍政令及賞罰之法爲主”,然後對今文前四篇誓辭褒揚一番。至于《秦誓》一篇,既没有行軍政令,也没有賞罰之法,因爲其是今文,故稱其“別是一格”,不予貶抑。說到古文《泰誓》,因賞罰之法談得少,稱“僅有賞罰二語”;因未到决戰時刻,軍事政令談得少,稱“絶口不及軍政”。接著加以許多不實之詞,什麽“張目疾首、洗垢索瘢”,甚至“蕩然掃地”云云,極盡污蔑、貶斥之能事。
其實,古文《泰誓》有著許多獨到的優點:一、它保存許多千古名句,如“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等等。二、它有許多哲理性的警句,發人深省,如“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等等。三、它有許多鼓舞人心的誓言,感情充沛而真摯,如“我武惟揚,侵之于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等等。應該說,古文《泰誓》是一篇有著豐富內容的千古奇文。閻氏《疏證》揚今貶古,完全背離歷史的真實。
例2.《疏證》第一百十三條抄録吳 之言曰:“安國所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屈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56)第一百十七條又記鄭瑗之言曰:“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豈有四代古書而篇篇平坦整齊如此”;“(古文)《泰誓》曰:‘謂己有天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此類皆不似古語。”(57)
按《疏證》中有大量關于古文“易曉”、“皆文從字順”,而今文“難曉”、“屈曲聱牙”的言論,言下之意就是古文爲“僞作”,而今文乃真古文獻。實際上,這只是一種偏見,與事實完全不符。如古文《大禹謨》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58)古文《說命》曰:“惟干戈省厥躬”,“惟 學半。”(59)豈不“難曉”、“屈曲聱牙”?再如今文《禹貢》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60)今文《洪範》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61)豈不“易曉”而“文從字順”、“平坦整齊”?
再說,古文《泰誓中》“謂己有天命”的一段話,是《墨子》引用過的。《墨子·非命下》引“《太誓》之言”曰:“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62)《墨子》所引,怎麽可能“不似古語”?可見抱著厚今薄古的偏見去尋找古文的毛病,不可能得到正確的結論。
例3.《疏證》第一百十六條録郝敬之言云:“《堯典》、《禹貢》,其辭簡奥,叙事樸直有體……《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文辭最古,法度森嚴,有頭尾,有血脉,有分段,有照應,爲千萬世史書冠冕……故《尚書》以伏生二十八篇(今文)爲真古文……至于二十五篇(古文),清淺鬆泛……孔《書》諸篇,辭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亳,《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其他皆然……《秦誓》自然處高于《左》、《國》,《費誓》雖列編末而簡奥淵深……若夫《伊訓》、《說命》,風格卑弱,尚不敢望《秦誓》,乃得與典謨並列,真是千古不平事。”(63)
這一條,完全以空洞抽象的詞語對《尚書》的今文和古文進行褒貶:遇到今文,用好詞褒揚,如“簡奥深淵”,“法度森嚴”,“高于《左》、《國》”,“爲千萬世史書冠冕”;遇到古文,則用差詞貶損,如“清淺鬆泛”,“風格卑弱”,“辭義皆浮泛”,還有幾個“不切”、“不敢望”、“不平事”。究竟如何“不切”,則没有具體分析。其結論是:二十八篇今文是“真古文”,二十五篇古文當然是“僞作”了。
實際上,古文中有許多千古不朽的名篇:如《伊訓》是大臣對王初即位時的訓戒,苦口婆心,寓意深刻,所云“三風十愆”,具有警示作用;《說命》記録殷王武丁選拔奴隸說爲相的過程,王與說有許多精彩睿智的對話,讀來令人神往;《君陳》記成王對君陳的教誨,《畢命》記康王對畢公的囑咐,在周初局勢動蕩的背景下,這些都是歷史的極好教材。閻氏《疏證》運用厚今薄古法,盲目揚今貶古,對《尚書》的研究是極不利的。
例4.《疏證》第一百十八條抄録王充耘之言,在褒揚今文和貶損古文數篇後說:“《蔡仲之命》一段絶與《太甲》篇相出入:言‘天輔民懷’,即是‘克敬惟親,懷于有仁’之說;‘爲善同歸于治,爲惡同歸于亂’,即是‘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之說;‘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窮困’,即是‘自周有終,相亦罔終’之說。吾意古文只是出于一手,掇拾附會,故自不覺犯重耳。”(64)
上述言論,有一個證古文爲“僞作”的方法非常簡單:只要尋找兩篇古文,其中有些語句個別詞相同,即可證明“古文只是出于一手”。若依此法,同樣可以說:“今文《多方》與《多士》絶相類:《多方》‘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65),即是《多士》‘予大降爾四國民命’,‘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66)可見今文只是出于一手,掇拾附會,故自不覺犯重耳。”這樣,全部今文便證成伏生“出于一手”的“僞作”了。然而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是疑古時代所玩弄的手法:挖空心思,尋找一點瑕疵,再擴大至全部。其實,今文二十八篇與古文二十五篇,內容都極其豐富。所謂“出于一手”,即由一個人“僞造”,是絶對不可能的。
綜上所述可見,閻氏在《疏證》中的厚今薄古法,運用得相當廣泛,它有六個方面的表現,涉及近二十條具體實例。它或者祈鬼神佑助,盼望有能人出來“删此古文”而使今文“孤行”;或者千方百計保護今文,稱今文“秦火不得而焚之”,而捏造古文“滅”“亡”于西晋戰亂,並反復宣傳;或者藉某些經籍也有今古文之争,詆毁古文《尚書》“皆以爲是僞書”,古文“屈厭”了今文《尚書》,“爲此經之不幸”;或者在堯、舜、禹名號問題上隱瞞今文《堯典》的闡述,而改以《孟子》之言爲今文,又把《舜典》、《大禹謨》中出現較早、影響甚廣的兩句話誣爲“僞古文”,痛加責難;或者在查找他籍引《書》之文時,保護今文只說其好,而把缺失之過全部推到古文頭上,並加以侮辱性的惡毒語言。《疏證》中還有原文“出自”引文或原文“剽竊”引文的怪論,這種怪論和指責也絶對遵循保今斥古的原則,不用于今文而只對古文。還有許多條目摘録他人言論,用一些空洞抽象的詞語或歪曲事實的理由,褒揚今文,貶斥古文。以上林林總總厚今薄古的表現,說明閻氏《疏證》並非在進行實事求是的學術研究,而是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采用一些不正當的手段和方法,去達到證古文爲“僞作”這一不真實的特殊目的。
隨著閻氏《疏證》所運用的二難推理、吹毛求疵、虛張聲勢、顛倒先後、厚今薄古等八種辨僞方法的一一揭露,古文《尚書》這部在國學史上具有極其珍貴價值的古文獻,將撥開“疑古”的重重迷霧,在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重新爲國人所認識和啓用,爲繁榮學術文化事業作出新的貢獻!
①陳履和:《〈古文尚書辨僞〉跋》,《崔東壁遺書》第十册《古文尚書辨僞》,上海:亞東圖書館,1936年。
②劉建國:《先秦僞書辨正》,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86頁。
③張岩:《審核古文〈尚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380頁。
④房德鄰:《駁張岩先生對〈尚書古文疏證〉的“甄別”》,《清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1~21頁。
⑤楊善群:《辨僞學的歧途——評〈尚書古文疏證〉》,《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第396~401頁。
⑥楊善群:《評閻若璩的二難推理——〈尚書古文疏證〉研究之二》,《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四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18~140頁。
⑦楊善群:《評閻若璩的吹毛求疵法》,《中國經學》第十二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
⑧楊善群:《評閻若璩的虛張聲勢法》,《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十一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84~302頁。
⑨楊善群:《評閻若璩的顛倒先後法》,待刊。
⑩班固:《漢書》卷五十三《景十三王傳》,長沙:岳麓書社,2009年,第617頁。
(11)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71、983~985頁。
(12)楊善群:《論古文〈尚書〉的學術價值》,《孔子研究》2004年第5期,第31~34頁。
(13)《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135頁。
(14)楊善群:《古文〈尚書〉流傳過程探討》,《學習與探索》2003年第4期,第120頁。
(15)《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135頁。
(16)孔穎達:《尚書正義》卷二《堯典》,《十三經注疏》第2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4~26頁。
(17)《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137頁。
(18)《尚書古文疏證》卷一,第33、39~41頁。
(19)同上,卷八,第1118~1119頁。
(20)同上,卷八,第1180~1181頁。
(21)《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伏生》,第1009頁。
(22)《尚書正義》卷二《堯典》,《十三經注疏》第2册,第25~26頁。
(23)陳夢家:《尚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17頁。
(24)李學勤:《〈尚書孔傳〉的出現時間》,《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1期,第3頁。
(25)范曄:《後漢書》卷七十九上《儒林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664頁。
(26)李學勤:《竹簡〈家語〉與漢魏孔氏家學》,《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第64頁。
(27)《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129、175~176頁。
(28)《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孝經正義》,《孝經注疏》,《十三經注疏》第26册,第1~2頁。
(29)王溥:《唐會要》卷七十七《論經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65~1666頁。
(30)《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179頁。
(31)《尚書正義》卷六《禹貢》,《十三經注疏》第2册,第169頁。
(32)司馬遷:《史記》卷二《夏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55~56頁。
(33)許慎:《說文解字》卷十四《金部》,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293頁。
(34)《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260、324~325頁。
(35)《尚書正義》卷二《堯典》,《十三經注疏》第2册,第29頁。
(36)朱熹:《孟子集注》卷九《萬章章句上》,《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06頁。
(37)《尚書正義》卷三《舜典》,《十三經注疏》第2册,第84頁。《舜典》原合于《堯典》。
(38)同上,第60頁。
(39)《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31頁。
(40)《尚書正義》卷四《大禹謨》,《十三經注疏》第2册,第103頁。
(41)《史記》卷二《夏本紀》,第49頁。
(42)《孟子集注》卷五《滕文公章句上》,《四書章句集注》,第260頁。
(43)司馬貞:《史記索隱》,《史記》卷二《夏本紀》注,第49頁。
(44)《尚書古文疏證》卷五下,第469、522~523頁。
(45)同上,第469、525~526頁。
(46)同上,第92頁。
(47)《尚書正義》卷十二《洪範》,《十三經注疏》第3册,第368頁。
(48)王先謙:《荀子集解》卷一《修身篇》,《萬有文庫》第一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23頁。
(49)《尚書古文疏證》卷一,第84頁。
(50)《尚書正義》卷十一《泰誓下》,《十三經注疏》第3册,第333頁。
(51)孫詒讓:《墨子間詁》卷四《兼愛下》,《諸子集成》第四册,上海:國學整理社,1936年,第75頁。
(52)同上,卷二《尚賢中》,第37頁。
(53)《孟子集注》卷十《萬章章句下》,《四書章句集注》,第319頁。
(54)同上,卷十二《告子章句下》,《四書章句集注》,第341頁。
(55)《尚書古文疏證》卷七,第981~982頁。
(56)《尚書古文疏證》卷八,第1113~1114頁。
(57)同上,第1157頁。
(58)《尚書正義》卷四《大禹謨》,《十三經注疏》第2册,第105頁。
(59)同上,卷十《說命中》、《說命下》,《十三經注疏》第2册,第297、301頁。
(60)同上,卷六《禹貢》,《十三經注疏》第2册,第191頁。
(61)同上,卷十二《洪範》,《十三經注疏》第3册,第357、359頁。
(62)《墨子間詁》卷九《非命下》,《諸子集成》第4册,第174~175頁。
(63)《尚書古文疏證》卷八,第1145~1153頁。
(64)《尚書古文疏證》下册,第1163~1164頁。
(65)《尚書正義》卷十七《多方》,《十三經注疏》第3册,第545~547頁。
(66)同上,卷十六《多士》,《十三經注疏》第3册,第504~50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