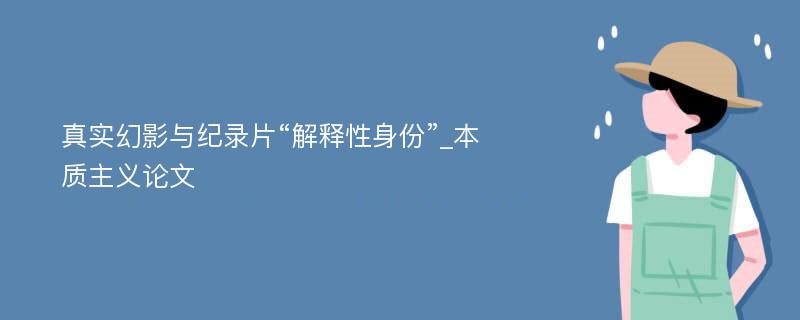
真实幻象与纪录片“解释性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释性论文,幻象论文,纪录片论文,真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迈克·摩尔的影片《罗杰与我》(1989)曾经在美国纪录片学界掀起一翻争议——“迈克·摩尔对于事件过程的重新安排与拼贴已经构成了一种谎言,或者说这已经不是一部‘像样’的纪录片。”[1] 在奥斯卡评委挑剔的尺度下,《罗杰与我》最终未能入围当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面对这一“不得不说的遗憾”,45名电影导演联名向“国际电影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公开信表达自己的“强烈愤怒”,正如著名导演帕莫勒·耶茨所言:“奥斯卡评委对于纪录片的狭隘认识已经完全混淆了纪录片的范畴,他们依然将纪录片刻板地定位在‘客观报道’这个幼稚的阶段上。”[2] 显然,“摩尔事件”并非体现为纪录片审美评价层面的主观分歧,而是对于纪录片本体属性的再一次讨论。那么,当“真实性”引发如此大的争议时,我们不禁要问,纪录片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显然,对于纪录片核心属性的界定,首先并非是一个完全理想化的“美丽假定”,也不是一个过于概念化的“精神想象”,更不是一个纯粹技术性的“形式思维”。本文试图从纪录片技术思维、实践模式、虚构界线、意识形态四方面入手,探讨纪录片的本体特征。
技术思维与解释性认同
纪录片应该被定位为“公共产品”还是“个人作品”?这一问题本质上涉及到纪录片的技术思维特质——影像只不过是纪录片导演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技术工具,导演唯一能够承诺的仅仅是对于物质世界或想象世界的“个人化解释”,而不是对一个预先存在的物质世界的“直接反射”或者“间接制造”。比如纪录片导演弗雷德里克·怀斯曼认为自己影片旨在实现“虚构的现实纪录”——“我更加强调影像背后的话语表达以及观众认同,而非简单形式层面的视觉观照和技术考量……因为在我看来,我的工作是用摄影机去模仿并解释这个世界,这一思维方式与某些小说家用笔和纸去描摹这个世界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3] 从技术思维的角度出发,影像表达的制度环境、纪录距离、认识逻辑、视觉接受是否能够为“真实性”承诺什么呢?
首先,就技术思维的制度环境而言,决定了纪录片是一种社会化的、制度化的表达;纪录片的公共传播渠道决定了导演必须考虑观众的接受趣味;纪录片的功能定位(教育、商业、文化或政治需要)决定了其不同的取舍策略;诸多常规的介入手段(如对政要人物和商业大亨采访权的获得)也往往建立在一定的妥协性之上;同时,作为当下主流的纪录片生产模式——栏目化运作,不仅要考虑高层审查的需要,同时也要考虑栏目自身的规定性……肩负着如此厚重的“责任”和“权力”,敢问,纪录片的真实性究竟何在?
其次,就技术思维的纪录距离而言,传统研究视野中,学者将真实视为纪录片的生命,强调最大化地淡化导演的介入痕迹和虚构成分,然而这只是一种美丽的艺术假定。殊不知,导演要考虑拍摄过程的纪录伦理和程序正义,就必须保持摄影机和拍摄对象之间相对安全的私人距离,然而技术思维的特性却决定了“靠得越近越真实”,显然这一悖论无法通过真实来平衡。因此,纪录片所呈现出的“真实”只不过是导演和拍摄对象之间的默契而已,即一种“授权的表达”。比如中国导演张以庆将个人的政治思考强加给一些小孩子(纪录片《幼儿园》),同时又借助各种虚构手段与被拍摄对象共同“导演”了一部《英与白》……敢问,纪录片的真实究竟何在?
再次,就技术思维的认识逻辑而言,纪录片的策划构思与后期编辑过程都是在封闭的个人空间中进行的,实际上已经为导演主观意志的自由介入创造了合理的“契机”。比如梅索斯兄弟将编辑行为视为对于原始素材的“二次虚构”,甚至认为导演的思维过程本身也意味着一种隐性的虚构——“尽管我痴迷于虚构化电影技术的探索,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编辑已经构成了一种虚构,因为你在现场之外谈论现场。”[4] 这一观点得到简奎斯·奥马特、阿伦·伯格拉、迈克·马瑞尔等学者的一致认同,正如简奎斯·马特借用克里斯汀安·麦茨的观点说道:“如果站在‘真实’的角度去评价一部影片,任何有关影像的表达本质上都只是一部虚构影片。”[5] 约翰·卡勒将认知世界分为三类:客观世界、摄影机前的世界、屏幕前的世界,同时指出三者之间由于认知主体的差异,很难形成特定的“对应与因果”的关系。[6] 如果整个影像思维过程已经抛弃了现实时空而完全构建在作者化的认识逻辑之上,敢问,纪录片的真实性究竟何在?
最后,就技术思维的视觉接受而言,当消费文化和泛影像时代的各种视觉修辞“无缝链接”之后,视觉文化随时随地在构建并塑造个体的认知图式和思维方式,正如社会学家安德鲁·萨兹说道:“在电子媒介时代,我们的思维过程更多地依赖于视觉化的描述信息,尤其是那些充满感情色彩的视觉内容不仅完全主导了我们的认知世界,同时也直接‘制造’了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7] 也就是说,视觉传播支配下的消费文化使得大众对于影像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物质本身,影像背后的叙述话语和拼贴逻辑培育了受众相对排外的接受惯性。所以,影像本身与物质世界之间甚至不存在必然联系,影像与现实之间的意义可以是断裂的,但却是合理的,这是视觉传播的内在特质决定的。伴随着影像与现实之间的意义越来越模糊,作为影像化的表征方式,敢问,纪录片的真实性究竟何在?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技术思维手段,纪录片在制度环境、纪录距离、认识逻辑、视觉接受四方面都无法与“真实性”对应起来,如果试图将纪录片的生命界定为“真实性”,就意味着纪录片概念的消亡,从根本上讲,纪录片不可承受如此之“真”。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纪录片作为技术思维制约下的影像表达方式,纪录片的本质特征是一种解释性认同,这种认同是引导性的、开放性的,认同的客体并非物质世界本身,而是导演的话语方式、主题内涵和个性情感。纪录片所要“纪录”的是导演对于世界的“解释过程”和“主观感觉”,而非纯粹意义上的“物质世界”和“客观存在”。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可以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政治谎言,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其定位为一部优秀的纪录片,因为我们认同的并不是历史本身,反倒是导演个性化的解读话语和政治寓意。进一步讲,导演对于现实世界或想象世界的“解释”可以独立于现实世界而存在,纪录片只是一个技术思维规定下的表达文本,我们不能、也不可能试图用一种文本去“推导”或者“验证”生活本身的真实性,当视觉文化将“文本与意义”的距离逐渐拉大时,每个人都可以构建属于自己的认同,而导演所要传递的正是一种解释性的“存在”,甚至是解释本身,每一种“存在”都有其合理性,每一种有关“存在”的理解也都是合理的。《普通法西斯》、《华氏911》的影像素材东拼西凑,而且不存在任何的史料逻辑,当导演以一种诙谐、幽默的口吻叙述故事、制造矛盾时,历史影像的意义已经完全脱离了其原初的现实内容,导演所要强调的是“解释过程”而非“物质本身”。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既然真实如此云谲波诡,学者为什么还不愿意抛弃“真实性”这个虚无缥缈的指标来谈纪录片呢?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学者对于概念思辨层面的文字游戏依然心存侥幸——哲学真实与心理真实之间的依存逻辑,相对于哲学真实而言,心理真实总会隐隐约约地令人有所“顿悟”。可以设想,一旦抛开了遥不可及的哲学真实,心理真实也就失去了其辨证的依据。与此同时,学者纷纷将个体的生活经验视为心理真实(真实感)的判断依据,这同样有待商榷,大多遥远的影像记录远远超出我们个体的体验范畴和知识范畴,其接受过程实际上表现为另一种话语暴力“劫持”下的被动接受。由此看来,当真实如此不可捉摸之际,固守“真实”只会进一步扰乱我们对于纪录片文本表达的理解,纪录片的生命不能建立在一个模棱两可的真实维度上,抛开真实,纪录片将呈现出一个开放的话语场,一个开放的解释过程和认同过程。因此,纪录片的生命与真实无关,“解释性认同”这一理念却可以很好地回答关于纪录片本质特征的讨论。
实践模式与解释性认同
纪录片学者卡尔·普兰辛格在其经典的著作《非虚构电影中的修辞与再现》中将纪录片的研究领域和纪录模式划分为八大领域[8]:(1)独立制作纪录片(如《美国梦》、《兄弟监管人》);(2)调查性纪录片(如美国PBS《前线》栏目的《坦克人》、《哭泣的卢旺达》);(3)政府宣传类纪录片(如《大河》、《我们为何而战》);(4)政治反思纪录片(如反战、反政府类纪录片《远离越南》、《心与脑》);(5)公共议题纪录片(如《蓝莓之夜》、《自然》);(6)新闻杂志纪录片(如CBS的《60分钟》、ABC的《20/20》节目);(7)编辑类纪录片(如基于档案素材的历史类纪录片《没落的罗马帝国》、《海之胜利》);(8)诗意与试验纪录片(如《曼哈顿岛》、《纽约·纽约》。显然,在这个基本的研究“图谱”中,调查性纪录片、新闻杂志纪录片、编辑类纪录片都带有明显主观烙印,就其叙述语态而言,依然是一种完全“编导化”的结构方式,观众只是被动地跟随着某种“全知视角”下的叙述逻辑和话语导向;独立制作纪录片、政府宣传类纪录片和政治反思类纪录片都旗帜鲜明地在传递一种作者立场,有关现实的素材只不过是服务于特定的认知需要、意识形态和商业目的;公共议题类纪录片是对现实矛盾和历史问题的作者化思考,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激起争议,而非制造共识;诗意与试验纪录片更是在强调一种完全作者化的自由表达,导演可以不受羁绊、信马由缰地自我抒发,一种纯粹个人意志和个人情感可以不对“真实”负责。由此可见,纪录片的八大实践领域都是在强调某种作者化的个人话语,纪录片的核心特征是对现实的解释与认同,而不是对现实的直接表达,导演既可以站在现实坐标上最大限度地发掘受众认同的“最大公约数”,也可以抛弃现实坐标尽可能地实现个人意志的自由表达。相反,八大纪录片实践模式却可以有效地统一在“解释性认同”这一“共同特征”之下,不同的艺术类型一方面对应着不同的解释途径和解释风格(对于现实的解释或对于个性意志的解释),另一方面对应着非虚构影像行为不同的叙述立场和介入方式,导演借助不同的艺术手段来解释物质世界或者想象世界,其所要传递的核心价值是一种“认同”,这种“认同”本身甚至可以超越所谓的现实坐标和真实标准。
虚构界线与解释性认同
非虚构的就一定真实吗?虚构的就一定不真实吗?为了区别于非虚构电影,学者将真实标榜为纪录片的本质特征,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一思维方法实际上却陷入了概念辨析的误区。虚构与非虚构是针对认知主体的创作理念而言的,而真实与非真实是相对于受众接受的心理感知而言的,因此,非虚构与真实并非处在同一判断维度之上,而是位于两个不同的坐标系中。非虚构的不一定真实,而虚构的也不一定不真实,比如现实主义风格的虚构电影往往聚焦于当下社会生态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同时最大限度地寻求虚构情节与个体经验的重合部分,同样可以让观众在虚构影像中感受到某种真实的情感体验,也就是说,非虚构与真实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与此同时,《意志的胜利》、《无粮的土地》、《风的故事》、《罗杰与我》、《永远》、《没有人是一个孤岛》、《华氏911》这些优秀的纪录片进一步否定了真实维度的主导性——影片或许是不真实的,但却是非虚构的。比如哈斯克尔·韦克斯勒的影片《冷酷媒体》(1969)将镜头聚焦于1968年芝加哥那场民主运动背后的政体劫难、新闻谎言与种族歧视,导演一方面通过一种“晃动的真实”去再现这个充斥着暴力与恐惧的政治背景,大部分影像素材都来自于真实的新闻影像与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又完全按照虚构电影的路子引进了几位演员来表演这里的“戏与人生”。学者保罗·坎贝积极肯定《冷酷媒体》是对虚构属性在现实与历史维度上的积极拓展,影片的核心价值并非是其虚构的人物纠葛和戏剧冲突,而是对于政治事件的历史性挖掘和思考——“单单从电影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部自命不凡但却难掩拙劣的传统叙事,然而就其所挖掘的历史真相而言,《冷酷媒体》却远远超越了剧场之外的流派价值。”[9]
类似的影片包括在现实背景和超现实异象之间互为假定的《无粮的土地》(1933)、在田园纪录与惊悚剧情之间无缝布局的《田园春光》(2006)、在主观镜头与现实画面之间自由切换的《风的故事》(1988)、在客观调查与角色扮演之间搭建逻辑的《细细的蓝线》(1988)、在旅行记录与动画模型之间另类游弋的《西伯利亚来信》(1957)、在真实场景与散文叙述之间互为映衬的《没有人是一个孤岛》(2006)……虚构电影,抑或非虚构电影?其实,我们已经很难站在真实的维度上试图划清二者的界线,这是否意味着这种判断维度本身存在问题?
一种表达的类型风格虽然不存在某种公共的、普遍的、绝对的属性定位,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认知图式和心理诉求来判断影像行为背后的作者意图和类型坐标。就《冷酷媒体》而言,对于那些试图追求故事和快感的观众来说,无论是演员阵容还是故事情节,这是一部十足的虚构电影;而对一位试图了解历史、寻求真相的观众而言,其所挖掘的“史料”足以支撑起我们对于1968年那场政治运动的信任和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部完全值得信任的纪录片。同样,再反观《无粮的土地》、《风的故事》、《细细的蓝线》、《西伯利亚来信》、《永远》、《没有人是一个孤岛》这些纪录片,其分别对应的艺术理念——超现实主义、主观意识流、剧情扮演、戏剧结构、散文叙述、时空位移——虽然无法统一在“真实性”维度上,然而却可以有效地统一在“解释性认同”的心理判断依据之上,即在作者表达与观众感知之间产生了某种共通性的认同与信任——影片或许是不真实的,但却是非虚构的。显然,公众认同的并非原始意义或绝对意义上的物质世界本身,而是导演主观解释的物质现实世界或个人情感世界。
意识形态与解释性认同
纪录片影像化表达与生俱来的“虚构性介入”,以及作者化表达不可避免的“假定性元素”都预示着纪录片不可能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现实纪录,潜藏在“非虚构行为”之后的是一套完整的、连续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依照巴赞的纪实主义理论,“现实是可以被纪录的,而且影像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然而当影像表达过程中掺杂了某种人为操控的元素之后,相应的意识形态也随之掺杂进来了”。[10] 同样,学者让-路易斯·卡莫里认为:“电影化的现实捕捉本质上只是对于现实世界的加减运算,距离原初的物理世界依然遥远,任何一种运算方式(失真现实与超现实)最终流露出的是对于虚构电影的暧昧表达。”[11] 也就是说,任何纪录片本质上都是特定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控制”下的作者表达,特定的文化土壤和政治背景决定了导演的认知图式及其潜在的“矛头指向”。比如CNN的纪录片《阿富汗:揭开面纱》、《沙俄普京》、《致命悲剧:伊拉克妇女》、《伊朗:事实与虚幻》、《头脑之战》分别聚焦于一系列敏感的国际政治问题:阿富汗的女性悲剧、俄罗斯的领袖崇拜、伊拉克的妇女处境、伊朗的核武谜团、英国的穆斯林风暴,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纪录片无不暗含了西方价值关照下的文化偏见和政治偏见,与本土民众心中的“真实”也相去甚远;再比如反伊拉克战争的纪录片——《兜售伊拉克:战争奸商》、《美国:从自由到法西斯》、《我们为何如此好战》、《如此战争:伊拉克记忆》、《入住伊拉克:隐蔽的故事》、《伊拉克时刻》、《远离公开:伊拉克战争真相》、《恐怖风暴:政府赞助的恐怖主义》、《恐怖路上:伊拉克》等,导演旗帜鲜明地指责伊拉克战争的罪恶本质,但是布什政府却可以站在国家安全以及人道主义救援立场上去证实这场战争的正义性……由此可见,所谓的“真实”并不是某种普世的标准,不存在超越种族、文化、历史之外的集体共识,也就是说“真实”只不过是文化与政治外力作用下的一块橡皮泥,不可能存在一个“未经留下任何触摸痕迹”的固定形状。因此,纪录片的本质是一种作者表达,我们不能因为以上这些纪录片遭到了一部分人或者一个政党的反对而质疑其纪录特质,每个人都可以站在自身的文化立场和阶级背景上去消费、读解影像之外导演试图传递的意识形态,纪录片是一种开放性的解释文本,是一种开放性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开放性的话语体系。这里的“开放性”一方面承认主体表达与生俱来的个人色彩,另一方面承认个体读解不可避免的功利性色彩,而这正是纪录片“解释性认同”的重要理念。
总之,笔者从技术思维、实践模式、虚构界线、意识形态四个维度入手,分别指出“真实”背后的种种先天性遗憾——个体认知的局限性,实践形态的复杂性,真实界线的模糊性,政治环境的控制性,身份认同的阶级性,产品制造的规格性,议题表达的功利性……进而指出“纪录片的本体属性是真实性”这一命题的错误本质,而“解释性认同”这一理念却可以有效回答纪录片的本质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