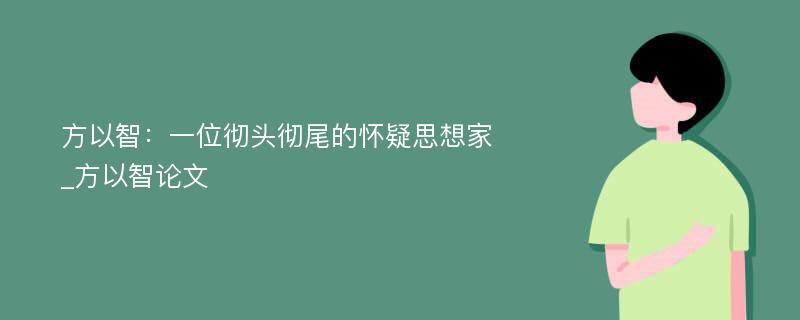
方以智——彻底的怀疑主义思想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家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8.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79(2008)04-0073-05
一、其生涯、时代及著述
方以智,字密之,安徽桐城人。号除曼公外极多,常为人所知的有浮山愚者、无可、药地等。生于明末之万历三十九年(1611),卒于清初之康熙十年(1671),享年六十一岁。
方氏是与姚氏、张氏并列的桐城望族,世世辈出学者官僚,但特别出名者始于以智曾祖父学渐(1540-1615)。他著《心学宗》《性善绎》,被列入《明儒学案》的泰州学派。祖父大镇(1562-1631)是提升至大理寺左少卿的大官僚,并且是在学问上继承学渐的阳明学者,与邵元标辈东林派许多人有来往。父孔炤(1591-1655)成为湖广巡抚,明亡后隐居不仕,沉潜学问,其著《周易时论》,因为集学渐、大镇等方氏历代家学之易学的大成,给以智的思想以深深地影响。
方以智的一生,大概能分为三期。第一期,从幼年、青年时代到三十三岁、明灭亡期间。他从幼年时,就表现出杰出的才能,伴随着成长,不仅学问(精),而且博通天文历法、音律、书画、兵法,是一个知识欲无满足的人。这酷似其父孔炤除了喜好象数易,又如其著《潜草》所显示的那样,从天文历法到动植物,深深的关心涉及多方面。幼年时代的以智,就像这样博学遍览,但以穷理极物为旨而埋头学问。对于他的思想形成,作为家学的象数易是重要的,此外也有不能忽视的人物。首先,是受其师王宣和白瑜的思想影响。王宣除经学、史学之外,博通佛教、医药、音律等,特别擅长于象数易。其著《物理所》(崇桢四年,以智刊行)成为以智《物理小识》著述的动机。白瑜讨厌明末思想界崇尚虚理的风气而重视实学。又,外祖父吴应宾是被当时佛教界重视的憨山德清之门人,学习三教合一学风而著有《宗一圣论》。
以智深深地关心当时来中国的耶稣会宣教师们带来的西洋学问。早在少年时代就读《天学初函》而知西洋的天文历算,并且亲炙精通当时西学的熊明遇。这以后,通过同耶稣会宣教师的来往或其著述受西洋学问思想的强烈的刺激。这一点必须特别注意。
如以上所述,在整个青年期,他所深深的学问关心涉及多方面,但是,他生活的时代,不是能埋头学问的安稳无事的时代。岂止那样,将要“土崩瓦坏,民流政散”(《明末纪事本末》),终于导致灭亡明王朝的大动乱逼近。崇祯初年(1628),李自成们在陕西地域发动的叛乱,不久席卷华北全域,终于让兴起于满州的清兵入侵山海关关内。在以智居住的桐城也发生民变,崇祯三年,乘应天乡试举行(之机),他同应试的同乡诸生一起避难南京。此时,参加联合东林派之流派的复社,同杨廷枢、陈子龙、夏允彝们交往,批判政治得失,更进一步,崇祯十一年(1638),复社成员陈贞慧、顾杲、黄宗羲们,为了从南京驱逐攀缘逆臣魏忠贤的阮大铖,公开集一四○名署名的《留都防乱公揭》,这个时候,以智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流寓南京期间,着手《通雅》《物理小识》的著述,此外留下名为《曼寓草》的记录①。崇祯十三年,因为考中进士而被授予翰林院编修②,故以后他在北京过了约四年。
第二期,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的军队攻陷北京,毅宗自缢、明王朝灭亡之后,到清顺治九年(南明永历六年,1652)期间。方以智在北京被叛乱军逮捕一次,但幸运逃脱,赴福王即位的南京,仕于亡命政权③,但因为受阮大铖的压迫,终于弃官,辗转流浪于浙江、福建,后到达广州,寄身于南海县令姚其胤的官署。这期间,桂王在肇庆即位(改元永历),招以智,授少詹事、翰林院侍讲学士,但眼前所见到的都是宦官的专横与官僚们的党派抗争,他对前途失望,辞谢永历帝的厚遇,隐居于湖南、广西境内的苗峒。但是,随着清兵的南下,不得不流浪于广西各地,终于在永历五年在平乐被清兵逮捕,被强迫投降,但不肯,被释放为僧,居梧州云盖寺等寺院。永历九年,与施闰章一起去庐山;此年末,归省父亲隐居的桐城。这期间,着手著《东西均》,又完成《物理小识》《切韵声原》《医学会通》《删补本草》等。
第三期(晚年),从顺治十年(永历七年,1653)到卒于康熙十年(1671)期间。他一归省桐城,就被地方官要求出仕,他决意不仕于异族,因此赴南京,皈依天界寺之曹洞宗觉浪道盛禅师受法戒,遁身高座寺的看竹轩,埋头著作。这期间,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的秋天,因父孔炤卒而回(桐城)一趟,庐墓三年。此时,编定父亲遗著《周易时论》,并加进自著《周易图象几表》八卷,汇集为《周易时论合编》二十三卷。这以后,六、七年间,居住于江西的南城、新城等的诸多寺院,康熙三年(1664),应庐陵县令于藻之招,继亡故的笑峰大然禅师之后成为吉安的青原山净居寺的主持。在这里,与蘖菴正志(熊开元)、今释澹归(金堡)相识,这对于他后来主张“三教归易”影响极大。
这期间,他于康熙三年刊行《药地炮庄》九卷、《物理小识》十二卷,康熙五年,刊行《通雅》五十二卷。此外,编定《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三十三卷,又与施闰章一起重定《青原志略》十三卷。又,作为收录晚年以智言行的(著作),有《愚者智禅师语录》四卷。
在青原山的生活,对他来说,既安定又充实。但是,康熙十年,以什么不清楚的嫌疑(也被说成与复明活动有关系),被清廷的官吏逮捕,从南昌押往粤西的流放地,溯赣江护送的途中,病死(一说自沉)于惶恐滩附近。
方以智的著述,在清朝人的文章中,引用《物理小识》、《通雅》稀少,其思想一直被埋没至最近几年,反倒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学者早就注意(到他),三浦梅园(1723-1789)在《赘语》中引用《物理小识》,本草学者小野兰山(1729-1810),在《本草纲目启蒙》中屡屡引用《物理小识》、《通雅》,至于新井白石(1657-1725),则仿《通雅》而著《东雅》。又,《通雅》的和刻本刊行于文化二年(1805)之际,方以智作为《通雅》的作者,对江户时代的学者来说,是很清楚的。
二、其思想与评价
1.怀疑主义的态度
正如他关于自己的性格评价那样,“不肖以智有穷理极物之僻”(《物理小识》卷五,以下称《小识》),方以智是一个从年青时就对“物理”感兴趣和探求精神旺盛的人。关于他的学问,或评价为博识遍览,或评价为百科全书派性质的(学问),但(认为他)不仅仅是“博”,其探求的眼光因深邃而彻底,可以说是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他说,即便对作为常理谁也不怀疑的事象,也应该持怀疑的眼光,“善疑者,不疑人之所疑,疑人之所不疑。新应疑,旧应疑;险应疑,平更应疑。因其习常,故诡激以疑之”(《东西均·疑何疑》,以下称《均》);或者断言:“天地之间,一大疑海也”(同上)。如此明确地表明彻底怀疑主义态度的思想家,在中国曾经有吗?反而我国的三浦梅园说“总此天地乃一大疑团”(《答多贺墨卿君书》),从中能发现(以智)真正的后继者。
梅园书云“以天地为师”(同上),以智也强调“学天地”:“人在此天地间,则学天地。若尽人事以不负天地,则言人事而天地之道可推也”(《均》奇庸)。我们除掉作为常理的认识,如实地认识天地动静之真相,那个时候就会明白天地间一个个事物的法则,进而也就明白了成立天地万物的一大法则。
他首先主张一个个事物中,有使之存在的法则。将它称为“物则”。“物中有则(《诗经》语),空亦有则,以费知隐(《中庸》语),丝毫不爽,其则耶,理之可徵者,而神在其中”(《小识》卷一)。即便是空,因为那里充满气,故仍然是“物”。因此为“则”所规定。这个“物则”,是进一步探求高次元性的“理”的依据。关于这一点,后面论述。在这里(先论)“物则”怎样能认识呢?“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会元,小而草木蠢蠕,类其性情,徵其好恶,推其常变,谓之质测”(《小识》自序),即就大量的个别事物进行观察、测量、实验等,在这样的现象的记录之上,推测“其所以然”,将这样一连串的操作称为“质测”。这可以说是分析的认识。
成为如此“质测”之对象者,如上面引文中所划分的那样,是天地间的万物(因为心与物都视为物,故(心也)成为当然的对象)。可以说基于他自身“质测”的结果的著作就是《物理小识》十二卷。此著分为十五类,为了参考,(这里)只揭示其类名:天类、历类、风雷雨旸类、地类、占侯类、人身类、医药类、饮食类、衣服类、金石类、器用类、草木类、鸟兽类、鬼神方术类、异事类。
但是,在探求个别事物之法则性这一点上,朱子(1130-1200)的“格物”也是相同的立场。但是,方以智与朱子不同(点)为:第一,与朱子首先将应该追求的“理”作为伦理的政治的价值与一体不离的东西来领会相反,方以智所追求的究极的(东西),虽与伦理和政治有关,却是根本意义上的物自体之理(在他的用语为“物则”),他关于所谓的“性命之理”,几乎没有论及;第二,朱子所说的“格物”,是枚举地积累关于个别事物的“理”之后,不久在某时点上,飞跃的直观的“豁然贯通”而到达宇宙全体之理(全体大用之理),但方以智关于超越作为个别的事物之探求方法的“质测”之界限的对象,既领会为根据后面将论述的“通几”方法来求的东西,也是将两者领会为相辅的东西。
又,“质测”这一用语,与“通几”一样,大概是其父孔炤的创造的词,不仅以智,他的伙伴,例如《天经或问》的作者游艺辈们也使用。
2.气一元论=火一元论
接着(谈)方以智怎样理解这个存在世界吧?如先从结论说,那么可以说他是坚持气一元论的立场。“一切物为气之所为,空皆气之所实”(《小识》卷一)。不只是万物,被认为空虚的部分也全都充满气,由于这个气的运动变化万物生成。“虚固是气,实形亦气之凝成者。直是一气而两行交济。(中略)气凝为形,蕴发成光,窍激为声,皆气也”(同上)。气虽是一气,但也是阴阳二气,二气互相作用。“本一气也,而自为阴阳,分而为二气,而各各具阴阳”(同上)。但是,像这样的气一元论,不是方以智思想的特色,十一世纪、北宋的张载(1020-1077)在《正蒙》中已经有基本的论述,使方以智的气一元论具有特征的是下面引文中所显示的火一元论的侧面。
天恒动,人亦恒动,皆火之为也(《小识》卷一)。
天道以阳气为主,人生亦以阳气为主,阳绕阴阳,火运水火也。生以火,死以火,病由火生,而养生者亦此火也。(同上)
因为没有详细说明这些议论的余裕,这里只叙述其气论的要点。即一气在根源性上是火,统作为其两个侧面的水火二行(阴阳二行),由于此二行相摩荡而天地万物生成展开。但是,他是基于元代的医家朱震亨(号丹溪。1281-1358)的相火论展开火一元论。朱震亨说:“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格致余论》相火论),以智进一步扩大这一主张,说火与元气同一,即火贯通包含人的万物,认为它是万物生产变化的原动力。以智的这一发想,可以推测是传统儒家的反抗意识,它与以世界的生成为神所创造的来华耶稣会宣教师们的天地创造说相反。
又,我认为,他的火一元论在系谱上既继承其祖父方大镇的说法——如《药地炮庄》里记载的那样,“野同曰:满空皆火,物物之生机皆火,火具生物化物照物之用,而有焚害之祸”(同书卷二《养生主》);也受其师觉浪道盛的五行尊火论(《天界觉浪道盛禅师全录》卷十八)的影响。总之,他们也受朱震亨的相火论的刺激而立说,由此可以想象相火论对明末思想界的意义。
3.“通几”=“合外内、贯一多”的立场
质测之方法作为对象的是由于气(火)运动而形成的个别的事象,而由此所获得的(认识尚)停留在于“物则”的水平。因为“物则”与物一起是多样的,万殊的,所以至今“被物惑”(《小识》卷一)。因此,只有到达更高水平的法则性的“所以为物之至理”(《通雅》卷首之三《文章薪火》),或者“物物神神之深几”(《小识》自序),才能一元的体系的把握世界。这个方法被称为“通几”,这已经不是分析的认识。关于超越分析的认识的“物物神神”的不可知的世界,他说:“各各不相知,但各各互相应”这一因果依存的关系,即“感应”的关系,为了把握它,只有根据“心”。“天地一物也,心一物也,惟心能通天地万物,知其原,即尽其性”(《小识》总论)。
但是,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由于“气几”(气之动静的端几)而显示,为知之只有依靠心。但因为心也是物,故其动静中具有端几,称为“心几”,于是气几与心几互引互触,其瞬间神通就是“通几”。由此就能把握“所以为物之至理”。换言之,他认为作为贯通包含人的世界全体(天地万物)之法则的“理”,在作为小宇宙的人心与万物完全合一的时候才能把握。这不外乎所谓“物心一如”的境界。方以智关于当时耶稣会宣教师传来的西欧的学问评价为“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小识》自序),我认为这是批判西洋的自然哲学以神的创造来说明世界的存在因,而不是根据自然本身的运动变化来论述之。但他自己在以传统的感应原理代替自然哲学这方面,其结束论证也实在不充分。
他说,作为显示气几与心几合一的手段,家学象数易是有效的,依靠它防止“通几”的恣意性。就是说,气的端几,全都被象数六十四卦所显示。因此,如能把握“至理”,就能到达“贯一多,合内(心)外(物)”的境界吧。
但是,以智在《物理小识》中,关于“通几”和成为其对象的世界,几乎没有论述。他以觉浪道盛为师而入禅以后,与著表明三教合一思想的《药地炮庄》同时,著《东西均》,就“通几”的方法与对象(展开)论述。此著作为目标的是这样的构想,即究极的对立物成为均衡调和的世界,即“东西”之“均”,怎样有现实可能呢。现在因没有全面提出他的立论的余裕,故只记要点。首先,考虑作为存在的形式,“交”这一对立者,是既相交又相互相因的关系、“轮”这一时间的推移、“几”这一变化的端几(《均》三徵,以下同)。又,对应这样的存在论的认识过程有三个阶段,“明天地而立一切法”的“随”的阶段,接着经“暗天地而泯一切法”的“泯”的阶段,(“随”的否定),进而达到“合明暗之天地而统一切法”这一“统”的阶段,即统一的认识。以上是到达“均”的世界的过程,这用∴(音伊)符号表示。以智的论证和用语,极难解,大概是学佛教逻辑学的缘故吧,确实有逻辑性。
宛如以上所述,在中国思想家中,方以智可以说是既特异又少有的人物,(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他坚持比谁都彻底的怀疑主义的立场,其次他一元的说明世界的构造与生成,就世界自身探求一切的原因,再次他依照极逻辑化的手法来进行这样的说明。但是,关于他思想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连著作的全貌也不十分清楚,也可以说他是个被忘却了三百年的思想家。因此,关于他的思想,在日本几乎不为人所知,这是实情。
译者按语:我本欲向“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学术研讨会提交《桐城方氏学派的学术特质》一文,但因教务牵制,难以静心写作,不得已译出板出祥伸先生此文以替代。然而要说明的是,所以要译此文以提交本次研讨会,亦非纯为塞责计,而是基于以下考虑:板出祥伸先生将方以智判定为彻底的怀疑主义思想家,是我所认同和重视的,因为我一直认为桐城方氏学派的学术特质之一在于其相当高度的怀疑主义精神,而这一精神作为明末清初之反传统的批判思潮的体现,反映了中国哲学由古代走向近代的早期哲学启蒙,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译文的底本为板出祥伸先生赠于我的抽印本,原收于日原利国编《中国思想史》下卷(鹈鹕社1987年7月出版)。翻译完全依据底本,未参照其它文献,甚至连引文,亦据底本直接译出,未据方以智原著予以核对。
注释:
①译者注:此有误,《曼寓草》非方以智流寓南京时的笔记,而是出仕北京时的笔记,以智流寓南京时笔记取名为《膝寓信笔》。
②译者注:此亦有误,以智被授翰林院简讨。
③译者注:此不确,以智赴南京,固然欲仕于福王朝,但实际上他未能仕于福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