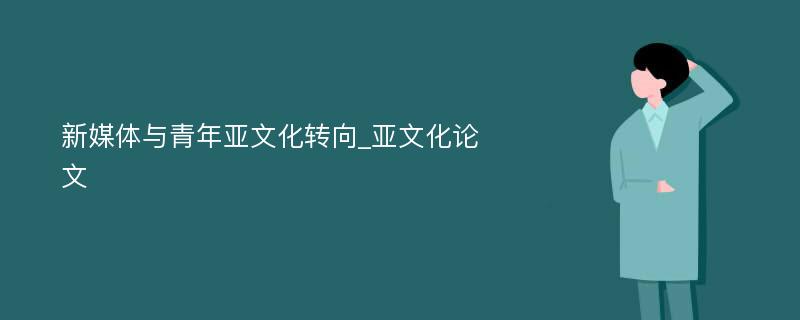
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青年论文,亚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青年亚文化作为一种普遍而又独特的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文化结构中必然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相对于主流文化,青年一代的文化以其青春性、多变性和挑战性的特性有别于位居社会主体的成人文化;而相对于基本认同主流价值的青年文化,青年亚文化则具有非主流、边缘性的“亚”文化或“次”文化特征。事实上,青年亚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青春文化现象,就其实质而言,它所反映的是成人世界与青春世界,父辈一代与子辈一代之间那种永恒的矛盾和张力关系。尽管在不同的时空语境下,这对关系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譬如,反抗、冲突、偏离、协商、另类等等,但是,它所呈现的那种青春期的迷惘、矛盾、寻觅、冲动以及身份认同的困扰始终是青年亚文化的历史宿命,无论社会的意识形态如何整一和强大,这类青年亚文化或多或少总会以某些方式表现出来。
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诸如“五四”青年文化运动、“一·二九”风暴,甚至“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运动,都在一定程度和某个侧面显现了那个时代的青年亚文化症候,但就整体而言,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的青年文化更多的还是以认同和追随主流文化、成人文化的方式出现,那种典型的西方世界普遍出现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并不突出。伴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接轨,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青年亚文化出现了巨大变化,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初的青年亚文化从备受压制到浮出地表,在传统的媒介语境中以多种个性化的另类方式呈现和发展,并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宽容,这主要是受益于经济体制转轨和思想解放运动,那么,进入21世纪的今天,青年亚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是突飞猛进的技术全球化对青年日常生活渗透的必然结果。如今,80年代形成的第一波青年亚文化族群/类型已成为记忆,而新媒介支持下的今日的青年亚文化已拉开序幕。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介对当今青年亚文化的影响,无论在力度还是广度上,都已远远超出了媒介技术的层面,进而关涉到当代中国青年亚文化特质的变异及其走向。
从文化赖以生存的媒介和技术环境方面看,当下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介对社会文化生态的全方位渗透,开始明显地导致今日中国的整体文化在向着开放、民主和多元的方向转变,同时整体文化的存在形态也在向着“数字化生存”转变。新媒介不仅为传统文化类型的“转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且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文化类型,其中,青年亚文化是最为突出的景观。当各种各样的“客”,例如博客、播客、闪客、换客等轮番上演,当各种“社区”、“论坛”喧闹于网上,当IM(即时通信工具)、SNS(社交网络服务)、微博客倍受青睐,当网上购物成为风潮,当“搜索”、“自拍”、“黑客”等等所有这些网络技术实践成为青年亚文化习以为常的社会参与及其表达方式时,青年群体正在参与演绎和展示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虚拟现实”。可以说,网络媒介的前所未有的开放式、无边界、多媒介的物理空间和相对平等、自由、开放的精神空间为中国当代青年文化的分化和亚文化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如今,新媒介已经成为中国青年亚文化生长和扩张、成为新型青年亚文化传播以及亚青年群体寻找志同道合的文化族群和部落的文化场域。
网络媒介的全面覆盖、低廉成本及便捷使用,使中国大量青年群体的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与其牢固地绑定在一起,成为了他们的“亲密伙伴”,甚至发展到须臾不能离开的地步。一项由美国互联网公司IAC(Inter Active Corp)和智威汤逊(JWT)广告公司合作用双语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与美国青年相比较,中国青年更依赖数字技术,有80%的中国青年认为数字技术是自己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其中42%的人觉得自己“上网成瘾”,而美国青年中持这种想法的人则分别为68%和18%。与此同时,该调查还发现,网络在中国青年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77%的受访者说,他们通过网络交友,54%的人表示他们曾经通过网络即时信息进行约会,63%的人认为两个人即使永不见面也可能在网络上建立起真实的关系,而在美国青年人中,相信这一点的只占21%①。可见,这一新的媒介语境及生存方式,的确为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青年亚文化创建了一个全新的生存空间和表现舞台。中国青年亚文化在经历了“文革”时期的“地下活动”和改革之初的“地表活动”之后,终于被媒介技术的推手带入了“无限活动”的新阶段。当下,青年亚文化作为被互联网率先激活的另类文化类型,已全方位地借助新媒介启动了自身的全面的文化转向,并且情不自禁地成为文化与技术深度联姻的实验产品。
从青年亚文化自身的交流系统来看,一方面,新媒介正在历史性地改写着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新媒介对青年亚文化构成要素的技术重组和创建,催生了新型的表达方式。
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传统青年亚文化理论基本上是先验地预设了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抵抗和依存的双重特性。譬如,科恩(Phil Cohen)对伦敦东区工人阶级子弟的研究揭示,青年亚文化对工人阶级母体文化表现出表面的拒绝或反抗,却又有内在的依存和继承。威利斯(Paul Willis)对嬉皮士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表明,青年亚文化与中产阶级文化之间始终存在一种“结构性对立关系”。克拉克(John Clarke)依据对特迪文化的深入研究也发现,“亚文化作为一种非官方的文化形式,拼贴所产生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就必然处于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地位”②。诸如此类的“抵抗”和“依存”诞生于前互联网时代,是现实世界中青年亚文化的一般特点,而新媒介时代的青年亚文化,它们往往更长于表征似乎完全属于自我化或虚拟化的感性世界,不是公然地“抵抗”现实间存在的成人文化形态,更不愿意与父辈或权威文化发生正面的“冲突”;它们不仅抹去了横亘在主流和非主流之间的森严界限,隔断了主体与现实之间的人文关注,而且还经常颠倒真实与虚拟的逻辑关系,将真实虚拟化,虚拟真实化。
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出生并成长于网络时代的青年群体,天生就与网络、手机等新媒介结缘,他们通过新媒介接受的信息远远多于传统主流渠道,比如学校教育、父辈传承、甚至电视,而后者对他们成长的影响或许将日趋式微。与此同时,青年亚文化主体,通过琳琅满目的新媒介产品,比如ipod、手机、社交网络、视频分享站点、在线游戏等,时刻传递着自己创造的文化,在信息传播、交友、玩耍和自我表达的世界中追求自治与认同。正如萨瑞塔·雅迪(Sarita Yardi)所说的,“数字世界为他们开启了挑战社会规范、探索趣味、发展技能、实验自我表达方式的可能性。这些活动让十几岁的孩子们着迷,因为它们提供的场所意味着社交世界的延展、自我导向的学习、独立”③。于是,青年亚文化的实践活动,最终演变为一种自我宣泄、自我表现、自我满足的技术方式和文化意义,网络媒介的开放性、无中心性消解了现实世界中权威、主流、父辈等对青年加以掌控的可能性,或者说,网络媒介为青年亚文化的生成、发展提供了最为自由、宽松的逃避主流文化压抑的“庇护所”。
在青年亚文化构成要素的技术重组和创建方面,网络媒介以“数据”、“图像”、“多媒体视频”等技术特质为基础,创建了一个互动、复制、仿真和拟像的世界,这是一个全然不同于以往的世界。正如鲍德里亚所言称的那样,在符号建构的类像世界里,模型和真实之间的差别被销蚀,形象与真实之间的界限被内爆,人们从前对真实的那种体验以及真实的基础也一起消失。新媒介技术将众多的非自然的、非真实的成分引入赛博空间,并且运用超文本或者超链接技术,为青年亚文化与外部现实世界的断裂创造出了一种“自然”的表现场所,遮蔽了人与现实真实关系的呈现,促成了青年亚文化表达方式的图像化转型。如此,即使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后现代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度里,在人与其所创造出来的各种社会文化意蕴之间,也同样不再有传统媒介时代的那种明晰的主客关系或文化符号与现实世界的直接对应关系,而更多的是通过图像符号的表征系统去消解原有的话语体系,用多媒介符号去解构既存的文化类型和文化理念。
在这种社会和技术语境条件下,中国青年亚文化便以空前活跃的姿态走上了网络空间的前台,从而使传统意义上的青年亚文化类型迅速位移于后台,蜕变成为所谓的前新媒介时代的过气的文化遗存。如果说,“新媒介新技术构成了社会机体的集体大手术”④,那么毫无疑问,青年群体是这种大手术的率先操刀者,他们张开双臂热情拥抱新媒介,并借助新媒介来创造出属于自身的新的文化样式,青年亚文化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介的激发下,正在实现自身的文化转向。
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新媒介对青年亚文化发展的影响力比此前几乎所有的媒介形式都要广泛、深刻、迅捷得多——这不仅包括青年亚文化的多样性和传播方式,也包括亚文化文本的存在形式和功能模式,还有亚文化生存、生长的整个生态环境和文化语境,也就是从这里我们可以很好地观察到青年亚文化的转向。
首先,借助网络媒介的快速成长和普及,青年亚文化实现了从相对封闭的“小众团体”向整体青年社会开放的“普泛化”转向。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数字媒介,从开发之初就预设了兼容和平权的机制,技术的“傻瓜化”强化了“网络世界人人平等”的可操控性,而友好的计算机界面和人性化的网络空间,模糊了现实社会中身份、性别、收入、学历等因素所带来的多重差异,最大限度地吸纳青年群体的加入,激发了社会不同阶层青年群体参与文化创造的热情,从而让亚文化从传统的另类、小团体模式中突围而出,成为青年群体共同参与、共同分享的文化。与此同时,网络、手机等新媒介的普及以及信息资费的低廉化趋势,冲破了青年使用新媒介的经济壁垒,更为青年亚文化的生产、传播和共享的“普泛化”和“即时性”提供了有效的媒介工具。
这里所谓的由“小众”走向“普泛”,其实质就是将青年亚文化的话语权回归青年本体,尤其是将青年的媒介话语权交还给青年阶层。长期以来,青年是被基于成人价值观和世界观所建构的成人文化话语来强行描述的,而不是由青年自己的语言来编码的。比如“芝加哥学派”关注的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伯明翰学派”聚焦的中产阶级青年亚文化,以及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摇滚和地下纪录片的研究等等,这些有关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尽管也突出了青年的边缘化问题,但由于研究者基本上是来自于中产阶级的成人学者,因此,他们难免将青年群体“传奇化”,并且忽略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普通孩子”,从而使青年亚文化的生产和传播被不同程度地圈定在某个阶层或者某个文化小圈子内。同时,由这些成人学者的话语出发,青年亚文化往往被贴上类似的流行标签:非主流、危险人物、反叛性,等等。然而,网络技术传播重构的新公共空间却能够向几乎所有的青年群体,甚至向游离于亚文化圈子之外的青年人群开启,从而确立青年亚文化的“普泛化”存在和传播。尽管目前网络青年群体基本上还囿于“都市青年”、“知识青年”,但也不乏“低知分子”和“打工族”,可以说,网络媒介青年亚文化的“普泛化”趋势是青年亚文化的一大特征,也是青年群体文化创造力的一次解放。这种由青年群体广泛参与的青年亚文化的意义还在于,它削弱了传统媒介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关于青年亚文化评价的“道德恐慌”和“妖魔化”叙述,也溢出了基于意识形态对抗而对青年亚文化的负面界说,它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通过新媒介技术而自我界定、自我指涉,并直接呈现,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属于青年亚文化主体的言说话题和权利。
其次,当代青年亚文化的另一重要转向是,青年群体通过谙熟地使用新媒介技术为自身赢得了更为阔大和自由的“书写”空间。诚如有的研究者所言,“网络具有非常强的游戏性、匿名性、虚拟性,网络中的交流没有那么多文化的禁忌和社会的规范,上网的人没有那么多顾虑,可以尽情地展现真实的自我,展示自己许多不那么理性的、不那么成熟的、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对抗的一些观念,表现一些具有叛逆性的、颠覆性的观点”⑤。网络媒介的虚拟性和匿名性,为青年亚文化提供了表达的自由通路,而自由表达则始终是青年亚文化得以生产和传播的基本前提,它可以使青年据此克服自身的怯弱、羞涩、拘谨和不成熟忧虑,避开成人家长般的监视和压抑,充分自由地去表达自我。同性恋博客“我们的幸福”自述道:“这是两个男人的同志博客。牛牛和屁屁(Pavel)。这里涉及男人间的感情、同志、同性恋、同性爱的故事,不喜请绕道。”⑥在两人分头记录的博文里,字里行间的率真表现、坦诚独白和身体暴露,以及对非同一般爱恋的幸福和焦虑感的书写,迥然有别于网络媒介之前同性恋的地下生存和尴尬处境,一改过去那种处处受“监视”状态下的躲藏和欲说还休的窘境。毫无疑问,这是新媒介为青年亚文化插上了自由的翅膀,为亚文化充分地享受自由,自由提供了无人可以阻挡的强劲表达动力和安全表达平台。
再次,青年亚文化通过新媒介技术的多媒介、多兼容、多互动的诸种特性,突破了传统亚文化风格的表达惯例,获得了更自如的、多样化的表达方式,从而实现了青年亚文化风格的转向。在新媒介中,那些新技术的呈现和表达方式,比如,媒介由语言文字符号、声音符号和影像符号向综合的数字符号的转变,致使文化的表达突破了对单一媒介的依赖,实现了青年亚文化表征符号的“脱胎换骨”。传统意义上的亚文化“符号”,主要体现在他们的衣着方式、独特的言行风格以及所喜欢的音乐类型等方面。赫伯迪格(Dick Heb-dige)笔下的朋克族,“额上的卷发和皮夹克、小羊皮软底男鞋和尖头皮鞋、橡胶底帆布鞋和帕卡雨衣、摩登族的平头和光头仔的步伐、紧身瘦腿和色彩鲜艳的袜子、紧身短夹克和笨重的街斗钉靴,这乱糟糟的一切物体能够既‘各就各位’,又显得‘不合时宜’,这多亏有了惊世骇俗的黏合剂——安全别针与塑料衣、既令人畏惧又让人着迷的缚皮带与绳索”⑦。而当下的青年亚文化却压根儿不借助这些出格的外在“行头”来表达亚文化的风格和意义,它们更青睐于使用网络媒介所带来的新技术手段和新技术装置去表情达意,而将真实的主体形象以匿名的方式掩藏在赛博空间里,如FLASH动画、在线游戏、动态相册、多媒体视频软件,以及MSN、QQ等在线聊天工具、Twitter和微博、搜索技术等等。掌握这些技术的青年人,不再拘泥于某一种表达方式,而是杂糅了文字、图像、影像、声音等多媒介手段,轻松自如地参与到亚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中。
最后,与上一点密切相关的是,青年亚文化的文化类型也迅速由单一向多元转向,致使基于网络新媒介技术的青年亚文化类型层出不穷,此起彼伏。当下,网络媒介上盛行的自拍文化、恶搞文化、迷文化、搜索文化、黑客文化、御宅族文化、同人女文化、COSPLAY文化等等,无不寄生于网络,活跃于网络,而掌握了新媒介技术的一代青年人甚至以网络技术为“武器”,在自我与成人世界之间筑起一道自我保护的“高墙”。这种通过技术壁垒逃避或隔绝主流意识形态以及成人世界的文化钳制,在虚拟“高墙”之内演绎别样人生的文化态势,只有在网络技术时代才能成为现实。
所有上述转向,也促成了青年亚文化传播方式的根本改变。其中最突出的是由单向传播转换为多向交互式传播,由滞后性传播转换为即时性传播。除此之外,青年亚文化实践活动和文本内容的便捷上传、下载和在线生成,传者和受者角色的合成及互为转换,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的互动聚合,均从物质、时间、空间、技术等多方面突破了原有的社会和技术藩篱,真正使青年亚文化实现了近乎无障碍的传播。
毫无疑问,上述新媒介语境下形成的青年亚文化存在和传播方式的转向,最终也将引致青年亚文化崭新的文化实践意义,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青年亚文化“抵抗”精神的弱化乃至失落,以及亚文化自身多样化、娱乐化、全球化与消费主义特质的呈现,从而步入极具后现代特征的“后亚文化(post-subculture)”时代。
后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更深层次上的渗透和均质化。这些过程同时也产生了更进一步的文化碎裂,时空经验的改变以及经验、主体性和文化的新形式”⑧。换言之,网络媒介的无深度感、暂时性、分裂性和全球化特征,促使在其基础上生成和传播的青年亚文化不再可能像传统亚文化同样抵抗任何单一的政治体系、主流价值和成年文化,他们甚至不同程度地弱化了这一文化的某些“抵抗”的特质。如果我们依然在反抗/抵抗的层面上去认识网络媒介下的青年亚文化,便显得圆凿方枘、扞格不通了,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早已发生“裂变”,二元对立和某一主流文化始终居高临下的观念也已被多元文化观念所取代。
新媒介语境中的青年亚文化特质,在传统的“阶级”和“年龄”之外,其可变因素也呈现出空前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诸如身体、性别、种族、民族、时尚、图像等等关键词,不断进入当代青年亚文化的内核和意义场域,也就是说,新媒介催生出的青年亚文化已经不再单单囿于某种风格鲜明而固化的文化类型,相反,许多特征明显不同的青年亚文化类型共时性地呈现,甚至此起彼伏,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不断出现、繁盛,直到消失,终而复始,生生不息。青年人也不再仅仅将自己执著地归属于某一种亚文化类型,他们经常从一种亚文化类型转向另一种亚文化类型,或者同时属于几种亚文化类型。这样的亚文化类型如同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马菲索里(Michel Maffesoli)所说的“新部落”,也即社会群体之间的识别不再依赖于阶层、性别、宗教等传统的结构因素,共同的兴趣和消费方式成为个人创造当代社交以及小规模社会群体的新形式。“新部落没有我们熟悉的组织形式的硬性标准,它更多的是指一种气氛,一种意识状态,并且是通过促进外貌和‘形式’的生活方式来完美呈现的”⑨。这种新社交方式鼓励个人以不同的角色、性别、身份自由地参与多个流动的、临时的、分散的、非固定的“部落”,从而在“部落”之间动态地、灵活地定位自我。
事实上,不同阶层、教育、社会环境中的青年人总是分属于各种明显不同的群体,他们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都有着极大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恰如有着中国和加拿大双重血统的学者卢克(Alan Luke)所指出的,在后现代时期成长的青年,“大约要经历16到18个不同的世界……这就像是在不同文本的海洋里航行一样。每一个文本都试图将你定位,出卖你,定义你”⑩。这样的青年亚文化样本和青年亚文化族群,在网络媒介时代,不仅出现在传统的亚文化音乐生产中,也频繁出现在譬如电影、电视、数码影像、广告、流行文化中,所有这些媒介生产及其产品都参与塑造了青年亚文化的面貌,从而勾勒出“万花筒”般的青年亚文化景观,正如默克罗比所评述的那样:“对表层的关注越来越彰显,意义被炫示为一种有意为之的表层现象。”(11)
在这样的情境下,“抵抗”既模糊了着力的对象,也失去了明确的方向,娱乐的特性则得以放大。“在亚文化族群身上已经看不到那种与社会对立的激烈情绪,而是以相同的兴趣爱好集合到一起,或是借助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介游戏发泄,或是在自己的虚拟社区里持续狂欢”(12)。我们看到,网络文学由“寓教于乐”转向“自娱娱人”,网络视频聚焦重心由“艺术作品”转向“现场直录”,网络语言由“精致合规”转向“生造逗乐”,网络图像被技术率性PS……一切传统、经典、权威、主流的话语、作品和表达都面临随时被颠覆的命运。当代青年亚文化对待权威的方式并不是公然地抵抗和反对,而是采用拼贴、戏仿、揶揄、反讽的手段尽情调侃和讥刺,同时获取自我的愉悦和狂欢。“恶搞亚文化”是最典型的范例,而其他在新媒介平台上活跃的文化类型,也无不充满着这种自娱自乐和无厘头的色彩。尽管这种娱乐化的过程往往不可避免地指向空洞和无意义,但是,那种释放激情、缓解焦虑、宣泄不满的文化心理的意义向度却也凸显出来。也因此可以说,新媒介语境下的青年亚文化,在弱化了抵抗色彩和精神向度的同时,将意义稀释于娱乐化的表达之中。
新媒介语境下的青年亚文化除了具有弱化抵抗、多元发展自身文化和偏重娱乐化的特质外,还显现出向全球化与消费主义倾向。
贝斯利(A.C.Besley)认为,处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后工业社会中,有两大特征影响青年亚文化的生长和传播,“一是被跨国公司而不是被单一国家影响和主导的消费社会,另一个是被信息技术、媒介和服务行业而不是被旧制造业赋予特征的全球化社会”(13)。众多跨国企业,包括微软、苹果、可口可乐、时代华纳等,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绿色和平组织等非政府组织(NGOs)等,都在带动全球化进程,使诸如全球市场、商品、消费、互联网等日渐互相关联,甚至可能转向全球通用。与此同时,多元文化之间的差别和冲突在全球化进程中非但没有被抹平,相反,其因为交流的便利而变得愈发突出。与此同时,被企业控制的新媒介技术同时为弱势群体和个人提供了成本低廉、方便易得的传播场所,给了他们表达自己声音的极大机会。在网络新媒介世界中,谷歌、百度、MSN、QQ、Twitter、人人网、豆瓣、优酷在全球资本、商业利益和中国经济市场化、开放化的驱动下,为持有一台电脑及上网设备或拥有一部联网手机的所有青年人提供了原创或传播自身文化信息的可能。众多跨国企业还处心积虑地将青年群体视为最完美的消费者,他们从市场、人口、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等全方位地对青年加以细分,如网购族、冲浪迷、背包族等,并着眼于这些团体成员的多重文化身份、欲望、需求及购买能力,有预谋地去培养他们特定的消费习惯和价值观念,从而建构起庞大的青年消费市场。
今天的青年更多的是通过消费和市场层面而不是传统渠道,如家庭、社区、学校,发现他们的身份和价值。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跨国公司在他们持续不断的广告活动中将消费身份和消费观念以各种炫目的手法植入青年的认知和价值中,从而消弭青年人在种族、阶级和性别上的区别,取而代之以时尚的风格、新的性别角色、新的价值认同、新的文化实践、新的家庭格局、新的社会团体,等等。格林纳(Tracey Greener)和荷兰特(Robert Hollands)对虚拟迷幻音乐的研究发现,虚拟迷幻音乐迷的国籍遍布全球五大洲,这些音乐团体除了定期在物理空间中聚会外,更经常的活动地点是在“超现实”的网络空间。“虚拟空间对虚拟迷幻音乐来说很重要,因为从这里他们与全球其他的迷幻音乐迷得以建立并保持联系”(14)。事实上,今天的青年亚文化通过互联网络等新媒介的确能够更容易地了解外部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也模糊了他们建立在不同国家、阶层、地域乃至性别基础上的青年亚文化特征。如果无视这一变化,我们将很难深入而准确地把握当今的青年亚文化本质。
综上所述,新媒介技术促成的青年亚文化转向,其文化的意义并不是简单的媒介技术与青年亚文化的交会,而是关系到当代社会总体文化的方方面面。我们从青年亚文化转向的各种症候——反理性主义、犬儒主义和快乐主义的游戏本质,可以窥见阶级、种族和地域等文化特性的淡化,以及全球化色彩趋浓和消费主义全面入侵之后,后现代文化境遇里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新媒介技术促成的当代青年亚文化转向,意味着青年亚文化的“与时俱进”,但需要继续追问的是,新媒介语境中的青年亚文化能否真正延伸成为与主流文化交相辉映、互生互长的文化类型?新的青年亚文化能否为全社会的文化整合、文化调节与文化优化提供良性因子,从而有助于社会在追求民主、和谐中健康前行?
在某种意义上,青年亚文化似乎总是作为社会主流文化中的一种不和谐音而为世人感知,作为一种偏离常规的乱象而令世人侧目。新媒介语境下的青年亚文化也是如此,它每每以“娱乐至死”的行为引发社会的“道德恐慌”,它总是以个人主义的张狂稀释集体性的凝聚力,它还可能在疏离、越轨、颠覆的行为中破坏规范、陷入意义的虚无……所有这些昭示着文化的断裂、社会的失序,也呼唤着文化的调整和文化的矫正。但是,所有这些如果仅仅作为对青年亚文化的指控,那便忽略了一个富有积极意义的观察视角,即将青年亚文化置于文化整体构成及其变迁之中加以观察。
一个显而易见的媒介文化图景是,新媒介的点对点传播、传受互动乃至传受合一的特性,都可能使同质的青年亚文化的呈现强度加大加密,又使不同类型的青年亚文化之间的交流、相融、再生更加便利。如此,多样化的青年亚文化不但丰富了新媒介自身的信息内容,也促使传统媒介和主流文化无法忽视网络上众多的亚文化实践及其文化符号和意义。事实上,网络虚拟空间中的青年亚文化实践活动正在成为传统媒介跟踪、聚焦、报道的重要内容。青年亚文化已经陆续登堂入室,进入主流媒介视野,引发主流媒介关注。仅以近两年为例,始于网络媒介的“艳照门”、“红心CHAIN”、“人肉搜索”、“五毛党”、“山寨春晚”、“贾君鹏事件”、“犀利哥”、“凤姐”等等亚文化事件,无不是经由传统主流媒介介入传播后成为整个社会的文化事件。同时,这些亚文化事件得以传播,也拓宽了传统主流媒介的传播途径,从而促使主流文化吸纳民主和宽容的理念。
不仅如此,新媒介语境下的青年亚文化实践,可能激发对主流文化的重新审视,丰富其内蕴,甚至促成新的文化整合。2009年伊始,由大学生自制的“山寨版”《北京地区2009年春运火车票购买指南》,引发了消费者对铁道部的质疑和拷问,其结果是铁道部接受问责,并在短短几天时间里,首次发布了包括购票、候车、临客开行、学生票办理办法和代售处分布等信息的“官方版”春运购票指南,它使得青年亚文化实现了对传统媒介和主流社会的成功挑战和认同接受。文学样式的创新和整合更是如此。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近些年来遭遇到生产和消费的双重滑坡,呈现出颓势,与此相反,网络空间非但储存了大量数字化的传统文学作品,而且,昔日的纸媒作家也纷纷在网上“安营扎寨”,再加上难以计数的网络草根写手,他们通过文学网站、个人博客、网络社区推出原创文学作品,在语言艺术、文学分类、审美意义、文学观念和传播方式等方面挑战传统,挑战精英,挑战权威。例如,评论家白烨与“80后”作家韩寒的“网络对决”,既是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争取网络话语权的象征,同时也可以视为主流与非主流相互博弈而又协商的仪式化表演。我们看到,“80后”,“90后”的原创作品不仅在网络空间获得了生存权利,而且在传统印刷出版乃至体制内获得了认同和发展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何为文学的问题显然有了不同以往的解答。
可以说,新媒介为青年亚文化的新生存方式提供了可能,它们既在网络世界兴盛并影响主流媒介、主流社会、主流人群,乃至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也在与主流媒介和主流文化的协调整合中进入主流,壮大自身。进一步而言,随着新媒介技术日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参与其间并作为亚文化实践主体的青年群体,其意识或潜意识深处,是否会将“亚文化”视为自然的存在之物,甚至视为一种“主文化”呢?格林纳和荷兰特的研究发现,“虚拟迷幻音乐迷们似乎已经相信他们改造了世界,建立了一个单独的社会,并且认为独特的迷幻音乐活动通过向世界展示另一种生活方式从而促使其他社会形态发生转变”(15)。至少,就青年亚文化本身而言,这种以自身为“主流”的认知是存在的,如果撇开其过于主观的一厢情愿,这里实际上涉及到未来文化的可能性,即青年亚文化为文化的未来发展提供最初的动力、灵感和实验。现在我们可以说,PC的使用绝对是一种主流的技术文化,但是,许多人恐怕忘了,这一个人计算机文化却是肇始于乔布斯等当年充满理想色彩的黑客亚文化实践。
总之,青年亚文化的变异、转型和转向得益于网络新媒介巨大的技术优势,新媒介所拥有的那些实时、互动、跨境、跨文化、跨语言等的传播特点,以及匿名交流、率性而为的虚拟空间特征,都使得寄生于其间的青年亚文化呈现出新的文化实践和符号意义。新媒介语境下的青年亚文化不仅是当下文化情境的症候式表达,折射出主流文化的裂变和离散,而且也是以青年群体特有的方式,构建的与主流文化的沟通与对话,从而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创造和转型提供了多元的、开放的可能。这正是新媒介语境下青年亚文化转向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所在。
注释:
①晓北:《中国青年人依赖网络表达情感》,http://bbs.chinanews.com.cn/thread-82406-1-76.html。
②科恩、威利斯、克拉克的观点请参见Stuart Hall,(co-ed.),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Youth Sub-culture in Post-war Britain.London:Hutchinson,1976。
③Sarita Yardi,Living and Learning with New Media:Findings from a 3-year Ethnographic study of Digital Youth,http://digitalyouth.ischool.berkeley.edu/.
④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00页。
⑤参见CCTV专稿《网络传播与青少年亚文化》,http://vote.cctv.com/tvguide/tvcomment/wtjj/xzlz/7887.shtml。
⑥博客“我们的幸福”,http://zh2hyl.blog.163.com/。
⑦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陆道夫、胡疆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⑧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⑨Michel Maffesoli,The Time of the Tribes,Sage Publications Ltd,1996,p.98.
⑩Alan Luke,NZAC Newsletter,20:3(2000):24.
(11)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12)《当代青年:从愤怒到游戏》,载《环球》2007年9月5日。
(13)A.C.Besley,"Hybridized and Globalized:Youth Cultures in the Postmodern Era,Review of Education",Pedagogy,and Cultural Studies,2003,Vol.25(2).
(14)(15)Tracey Greener & Robert Hollands,"Beyond Subculture and Post-subculture? The Case of Virtual Psytrance,"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Vol.9,No.4,September 2006:393-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