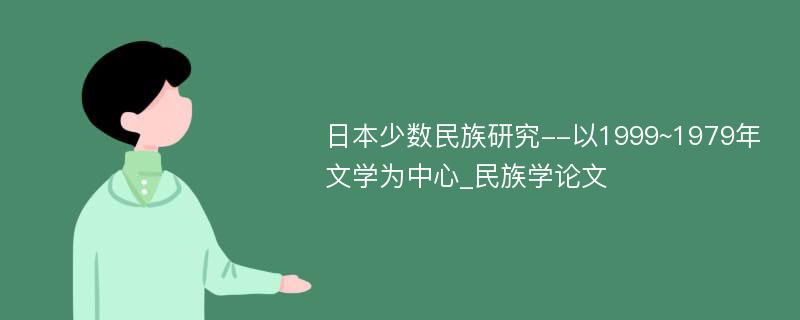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在日本——以1949-1979年文献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中国论文,文献论文,在日本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3)01-0029-10
日本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是与日本国内政治社会形势的变化与中日两国关系的状态密切相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民族学的发展,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和新一代训练有素的中青年民族学者的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了大规模开展世界民族研究时期。但是,由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日之间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70年代虽然中日恢复国交,但直到70年代末研究仍未走上正轨。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分日本研究人员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80年代之后兴起的研究高潮打下了基础。本文拟以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为依据,对建国以来到1979年30年间日本对中国少数民族研究文献进行粗浅的论述与分析。[1]
一、综合性文献
1.日本民族学会
日本民族学学会是以研究人类文化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的发展与普及为目的的学术团体。该学会比较注重对已有成果的全面、系统的总结与展望,在庆祝日本民族学学会成立30周年和50周年之际,发行了《日本民族学的回顾与展望:1934~1963》[2]和《日本民族学:1964-1983》[3]2部著作。书中对日本关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研究成果分别进行了概述,其中中国大陆部分均由竹村卓二撰写。第一部书中的《中国·大陆》部分,分为序、总论、民族史志、神话传说、宗教礼仪、民俗、社会、结论等八个部分。文中按学科对其代表人物、主要研究机构、主要成果及其意义分别进行了论述,并明确指出,与汉族研究相比,日本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很是逊色,今后应加强。第二部书中的《中国·大陆》部分,分为二十年之后(指1963年之后的20年——笔者注)、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会的活动、少数民族研究的先驱——村松一弥和周达生、中国大陆研究的复兴、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中国资料收集与展示等五个部分,写得简明、扼要,又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线索。该学会出版的上述两部书,均有各学科内德高望重的人类学家执笔,很有权威性,常被我国研究人员所引用和参考。
2.《鸟居龙藏全集全12卷,别卷》
鸟居龙藏(1870~1953),日本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是最早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的日本学者。他“先后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国学院大学、上智大学和中国北平的燕京大学任教。他在长达67年的学问生涯中,共写了37本日文、英文专著和549篇日文、法文、英文的各类文章,收入容。此外,还拍摄了2845张感光玻璃干板的老照片,成为跨越近、现代的国际学者中拍摄照片最多的一人。从1895年开始,鸟居一直在中国从事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调查研究,全部著作和照片各有一半以上都是关于中国学问的内容。”[4]1975年-1977年,朝日新闻社出版了《鸟居龙藏全集全12卷,别卷》。在出版这套全集的过程中,日本学界清一色科班出身的著名的专家学者们先后给各卷写了“题解”。鸟居龙藏留下的这些文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但是,他的业绩,“在他的直接继承的世代中,除考古学之外,还没有太大的影响,……其原因是鸟居的记述侧重于体质的特征、语言、物质文化,偏向于考古学的片段报告,而对于社会生活方面谈到的很少。”[5]直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鸟居龙藏的照片的再发现,日本国内开始重新认识其业绩,掀起了研究鸟居龙藏之热潮。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笔者至今没能翻阅此书,无法了解当时出版这套全集的背景。但是,从日本民族学研究的发展上看,当时出版《鸟居龙藏全集》是很有远见的一件事情,它为日后对鸟居龙藏的系统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3.中国少数民族志
村松一弥著《中国少数民族:其历史、文化及现状》(1973),作者在当时信息非常封闭的情况下,收集所有能收集到的资料,经过精心编排,对中国54个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等进行了概述。当时基诺族还没有被正式确认,故该书中尚未提到。如此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全面概述的书,在日本还是第一本,它被学者们喻为“综合民族志”。当时,此书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研究领域的入门书在日本受到很高的评价,而村松一弥也被喻为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先行者。书末附有《中国少数民族名称对照表》和《参考资料》。《参考资料》中,按54个民族分别收录了相关文献目录共300条,其中以中文为主,也收有日文。
4.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6]
这个时期,日本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研究以神话与故事的比较研究为中心,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少数民族尤其是南部和西南部的少数民族神话与民间故事。其主要特点是打破了以往研究中国神话与故事时只依靠中国古文献的限制,直接利用现代少数民族中收集到的资料进行认真的、多方面的分析与比较研究。这种方法,当时被认为是很有创意的,为日本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其中,村松一弥、君岛久子、伊藤清司等人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
村松一弥(1926-)[7],1957年获得东京都立大学文学硕士,后任该大学人文学部教授,专攻中国民间文学与艺术。1967年,在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担任有关中国民间文学讲学的村松一弥先生,组织对中国民间文学抱有兴趣的人们成立了“中国民话之会”(原名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在介绍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其主要成果有,(1)千田九一和村松一弥编《少数民族文学集》(1963)一书,收有新中国建国以来到1961年6月间所收集和整理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汉译文中有代表性的19个少数民族的50篇作品的日译文。这本书对其后日本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影响较大。(2)村松一弥编《中国的民话(上下)》(1972)一书,收有新中国建国以来所收集、整理并发表的,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中一部分有代表性的作品的日译文。这些作品的筛选、翻译均由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承担。(3)村松一弥编译《苗族民间故事选》(1974)一书,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编的《苗族民间故事选》(1962)一书的日译本,由日本中国民话之会的会员共同翻译。此外,1967年该会发行了会刊《中国民话之会会报》,其中也有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论文。
君岛久子(1925-),岐阜圣德学园大学教授,翻译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故事集,也发表有多篇介绍、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文章和论文。如她也参加了上述《少数民族文学集》的翻译,还翻译了《白龙和黑龙》(1964)、藏族故事集《金玉凤凰》(1977)等书;在《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有多篇译文和论文。
伊藤清司,现任日本中国民话之会会长。他长期致力于中日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取得众多成果。在日本对纳西创世神话的解读与比较研究的初期,他被认为是最有成就的。1972年4月,他在《日本神话讲座11集·日本神话的比较研究》一书中,发表了《日本神话与中国神话:其比较研究的视点》一文。其中,第5节《〈古事记〉与纳西族的〈古代故事〉》和第6节《纳西族创世神话诸相》,被认为是这方面的最初研究。[8]他还发表有《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1961)、《有关中国西南诸民族传说的研究与出版动向》(1961)、《神话与民间故事:中国云南省纳西族传说与〈古事记〉》(1976)等文。
其它,有名古屋学园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西胁隆夫,也从1974年起发表有关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文章。其中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1975)、《关于少数民族文学近况》(1975)、《少数民族文学作品》(1977)等文。[9]日本还出版了宇田礼、小野田耕三郎译的《阿诗玛》(1957)、中国文学会编译的《中国民间故事》(1957)、沢山晴三郎编译的《中国民话和传说》(1972)等书,其中也包括中国少数民族的大量作品。
二、有关各民族地区研究文献
1.西南地区
继20世纪初鸟居龙藏出版《苗族调查报告》之后,经过一段时期的沉寂,战后日本民族学界掀起了探究日本民族文化源流的热潮。由于中国西南文化与日本文化之间存在许多相似性,许多学者到中国西南民族中寻找日本民族最早的历史渊源关系,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西南民族史研究,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成果。
白鸟芳郎
白鸟芳郎,日本民族学及东洋史学家,任东京大学文学院、上智大学和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教授,民族学振兴会理事,东南亚史学会会长。在日本学术界,白鸟芳郎被称为开拓中国西南民族学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他原来是东洋史学家,后来转向研究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这一当时还处于未开垦的领域,长年辛勤耕耘,取得了重要成果。
牧野巽和白鸟芳郎之间的论战[3]研究初期,在日本学界牧野巽和白鸟芳郎围绕着云南的民族动态所进行的一场论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从1949年至1953年,他们发表了有关中国南部原住民族系统的一系列论文。其中有牧野巽发表的《南诏·大理·民家的语言》(1949)、《南诏·大理的遗民(上·中·下)》(1950)、《南诏大理的遗民(补充)》(1952)等文,有白鸟芳郎的《南诏与大理的民族及其遗民,民家的语言系统》(1950)、《乌蛮白蛮的居住地和白子国以及南诏六诏的关系(之一)》(1952)、《南诏大理的住民与爨·僰·罗罗·民家的关系(之二)》(1952)等文。双方争论的中心议题是,从8世纪到13世纪在云南建有独立国的南诏、大理的主体民族,其系统构成如何、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与现在的民族集团有何联系。双方都认为民家是南诏、大理国的遗民;但牧野巽认为南诏、大理、民家同属一个语系,即藏缅语族中的南诏、民家语群;而白鸟芳郎则认为,民家在古代原属白蛮,后随着南诏的兴起逐渐乌蛮化,即由白蛮、乌蛮融合而成,他认为南诏属藏缅系的乌蛮之国,而大理则属泰系白蛮统治之国。此次论战虽然最终没有结果,但是它引起人们对民族学的关注这一点上看,可以说意义重大。
对泰国西北部山地民族的调查[10]从1969年11月到1974年2月,以白鸟芳郎为团长的上智大学泰国西北部历史文化调查团,三次对泰国山地民族进行了实地调查。此次调查以泰国西北部山区实行刀耕火种的诸民族为对象,其中特别以历史文化上与华南具有密切联系的瑶族和苗族为重点进行。调查团对这一居住区的自然环境与村落、耕地、道路,社会组织、经济生活、物质文化、习惯、礼仪等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收集了近两千份民族资料,拍摄了数万张照片,获得了一直未被世人察觉、而在瑶族中完整保存着的大批汉字文书,调查取得了重大成果。其中,尤其是《评皇券牒》和十八神画像的发现格外引人注目,博得国际上很高的评价。这些文书“多半为信奉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瑶人在举行祭祀祖先、成年礼、嫁娶、治病、招魂、丧葬等等仪式时,司祭巫师所用的祈祷经文。其中还有有关占星术的天文历、观看风水、农事的指南书。通过这些文书资料,可以看出瑶人的宇宙观、世界观。”[10]这些文书,对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等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次调查被认为是日本东南亚民族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事件,白鸟芳郎也从此在国际上以民族学者闻名。“白鸟氏之所以进行这一艰巨事业,主要是想用泰国山区各民族的实况,对其三十年来关于华南各民族所作的研究成果作进一步的验证。”[10]因此,此次调查也被称为对中国南方民族的间接调查。
对泰国西北部山地民族的调查成果此次调查成果有白鸟芳郎编的2部调查报告。第一部《瑶人文书》(1975)[11]收录了调查中收集到的汉字文书中的一部分。全书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文书》部分收有《评皇券牒》、《家先单》、《招魂书》、《超度书》、《金银状书》、《遊梅山书》、《开壇书》、《叫天书》、《安坟墓书》、《洪恩赦书》、《女人唱歌》等文书的影印件;第二,《解说》部分分为《评皇券牒》、《瑶族的迁徙路线》、《瑶族调查之背景》、《瑶族的大堂神(十八神画像)》、《所收经典之解说》、《瑶族的〈家先单〉》等六个小节,对所收汉字文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解释。第二部《东南亚山地民族志——瑶族及其近邻诸民族》(1978)[12]一书,是关于瑶族、苗族、傈僳等其他山地民族的详细调查报告。全书主要分为瑶族的迁徙路线与种族史、瑶族的自然环境与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组织与礼仪等四大部分。此书的刊行,使白鸟芳郎教授荣获日本昭和五十四年度(1979)的第十六次“秩父宫纪念学术奖”。[13]
此外,白鸟芳郎还著有《父子联名制与彝族的系谱》(1957)、《中国西南》(1960)、《关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1960)、《中国西南诸土司的民族系谱》(1963)、《华南土著民的种族:民族分类及其历史背景》(1966)、《从民族系谱看华南史的构成》(1968)等文。
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会[14]
20世纪60年代初,在日本一群立志研究中国大陆古文化的人成立了《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会》。开始时,成员主要有伊藤清司、大林太良、竹村卓二、常见纯一等。当时,他们当中有的是大学助教,有的是研究生院的研究生,有的刚从欧美留学归来,都是战后新一代研究人员。后来,又有白鸟芳郎、君岛久子、小川博、近森正、斋藤达次郎、量博满、加治明等加盟。该研究会以中国南部为中心,对中国、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广泛的地域进行了扎实的研究工作,取得了突出的业绩。该研究会的活动直到80年代初才终止。
研究会会刊《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从1965年到1980年,该研究会发行会刊《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第1期~第10期。从内容上看,该研究会的研究可分为四大类:一是,关于中国南部少数民族(有时也包含汉族)文化、社会的民族学研究,主要有白鸟芳郎、岩田庆治、大林太良、竹村卓二、斋藤达次郎、常见纯一、加治明等的论文;二是,虽以中国南部少数民族研究为中心,但有时也涉及日本等国,研究范围很广,内容涉及神话、民间传说的研究,利用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少数民族民间传说和中国古代的文献资料等,此方面的研究有伊藤清司、君岛久子、安倍道子、百田弥荣子等的论文;三是,主要以中国史料为基础的历史研究,包含民族史研究,此方面的研究有和田久德、藤沢义美、谷口房男、喜田干生、冈田宏二等的论文;四是,对中国南部以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学、语言学、美术史等研究,此方面的研究有近森正、量博满、青柳洋治、新谷忠彦、伊东照司等的论文。十期会刊中有三期是有关中国民族研究专集。其中,第一集为《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专集》(1965),第八集为《纳西族专集》(1978),第九·十合集为《华南、东南亚大陆山地民及平地民历史民族学的研究》专集(1980)。
研究会的作用。该研究会在日本民族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一是,当时在有关中国南部少数民族研究还处于萌芽状态之时,该学会成了研究的发源地,起了先行者的作用,该会刊也成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基本文献之一。二是,现在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南部地区是日本的稻作文化、照叶树林文化的发祥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该研究会的研究对探讨日本基层文化也有重要意义。进入80年代之后,虽然该研究会的活动终止了,但该会成员继续其研究,作为中国民族研究的中坚力量,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
竹村卓二[15]
竹村卓二(1930-),毕业于东京都立大学,现任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第一研究部教授,专门研究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少数民族,特别是以瑶族为研究对象。他发表了有关瑶族研究的论文数十篇,其中有:《关于瑶族社会组织二、三特征——以广西蓝瑶的家族和婚姻为中心》(1959)、《〈广西通志〉等文献上所见到的瑶族和壮族——广西省山地溪谷种植民的适应方式和共存关系的一个侧面》(1967)、《从族谱看畲民(瑶族)的社会状况——对古文献进行人类学解译的尝试》(1968)、《瑶族各亚种族的差异——华南山地种植民的生态学适应方式》(1968)、《瑶族的姓和村落——种族史资料解说》(1971)、《过山瑶的世界观——客民社会对汉文化反映的社会类型之一》(1972)、《现代家族(东方)——以刀耕火种农耕民族的家庭生活为中心》(1973)、《最近对泰国北部山地民族进行人类学调查的成果(动向和展望)——以瑶族和苗族为中心》(1973)、《泰国北部的瑶族——与华南客民的会见》(1974)、《瑶族的祖先册——资料解说》(1975)、《瑶族的姓和命名法》(1976)、《泰国北部的瑶族起源神话和种族识别》(1977)、《关于瑶族起源的两个神话》(1977)、《和其他种族的关系、姓和亲族、祖先册的构成、祭祀礼仪、积累功德礼仪、盘皇崇拜、过桥的咒术、婚礼、葬仪》(1978)、《过山瑶的两个起源神话〈盘瓠和渡海〉——种族精神的形成和演进》(1979)等文。
其它成果
(1)在当时信息极端封闭的年代,千叶德尔的《华南山岳地带的刀耕火种》(1967)、《中国南部土地的开垦与农耕文化》(1972)等论文,利用各地《方志》对华南刀耕火种的发展进行了研究。(2)藤沢义美围绕唐朝对云南的治理与南诏王国的关系、云南在东亚关系史上的地位、南诏国的政治组织和汉文化的关系等发表了《南诏国的汉文化》(1952)、《关于南诏国的佛教》(1953)、《关于南诏国的统治者》(1956)等多篇论文,对在中国南部称霸一时的南诏王国的历史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藤沢义美《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南诏国史研究》一书,是作者关于南诏国研究的论文集(1969),此书依据严密的史料研究,不仅对南诏国的成立和统治体制,还对其社会与文化也进行了考察。(3)山本达郎《蛮族的山关簿——论古代传说和迁移路线》(1955)一文,对瑶族保存下来的珍贵记录《山关簿》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对其中盛传的盘瓠传说与洪水传说、特许状内容进行了探讨,依此对瑶族迁徙路线与年代提出了不少重要的见解。(4)此外,还有谷口房男的《关于后汉时代的蛮——以武陵蛮为中心》(1969)和《关于唐宋时代的“平蛮颂”——岭南少数民族汉化过程的一个侧面》(1975)、大林太良《对中国边境土司制度的民族学考察》(1970)、加治明《关于彝族的社会组织》(1962)和常见纯一《关于苗族的吊葬礼仪KáGei》(1962)等文。
2.新疆
松田寿男(1903-1983)著《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1956)[16]。此书由陈俊谋依增订版译成中文出版(1987)。据译者介绍,作者是日本著名东方学者,毕生致力于西域史、中西交通史及中亚史等研究,著述很多。此书是集作者多年研究内陆亚细亚史成果之大成,对于研究内陆亚细亚史,特别是对研究我国新疆地区的历史地理有一定参考价值。此书原版约四十万字,由绪论、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以及补考共五部分组成。译者指出,此书出版后受到了国际东方学界的重视,但“书中不少地方把统一的中国与过去西域所建立诸地方政权分裂开来,把我国在西域行使主权说成是‘殖民统治’。这些论点和提法无疑是极端错误的。”因此,我国读者阅读时应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正确对待,批判地加以使用。
佐口透著《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1963)[20]。佐口透先生是日本著名东洋学者,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系。他长期从事中亚史的研究,特别是致力于我国新疆民族关系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发表和出版了大量有关这一方面的论文和专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此书。这本书的篇幅较大,除了序文、序论和结束语之外,共分九章。作者在书中主要依据清朝实录、地志、方略类等史料,并参照西方人士的游记等,对清代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评述,对于我们研究新疆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983年,此书由凌颂纯译成中文出版。
日本的突厥、回鹘文字文献研究[21]。1997年,国内出版了牛汝极著《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一书。作者认为,日本的回鹘文字文献研究,是国际上少有的几个成果较多的国家之一。作者指出,日本早期的突厥、回鹘文字文献研究主要以羽田亨(1882-1955)为代表,50年代他著有《突厥文〈华严经〉残片》(1953)一文,还有石浜纯太郎《回鹘文普贤行愿文残卷》(1950)、《西域文化资料的整理及研究》(1950)等论著。作者指出,日本中期(20世纪60-80年代中叶)回鹘文献研究以山田信夫和护雅夫为代表。其中,护雅夫主要论著有:《回鹘文葡萄园卖契》(1960),《回鹘文消费借贷文书之研究》(1961),《回鹘文买卖文书——就其卖主与买主而论》(1961),《回鹘文消费借贷文书》(1961),《回鹘文买卖文书中买卖担保文词》(1961),《回鹘文契约文书——尤其关于消费借贷文书》(1961),《突厥语文献》(1962),《回鹘文译本〈金光明最胜王经〉》(1962),《元代维吾尔土地买卖文书之一种》(1963),《关于回鹘文法律文书之若干问题》(1965),《再论回鹘文消费借贷文书》(1967)等。山田信夫(1920-1987)主要研究回鹘文契约文书,其主要论文有:《大谷探险队携归回鹘文资料目录》(1961),《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所藏西域出土文书类——特别是回鹘文书》(1968),《回鹘文资料与解说》(1975),《印章杂考》(1961),《大谷探险队携归回鹘文买卖借贷文书》(1961),《回鹘文买卖契约的格式》(1963),《回鹘文中的私人印记和画押》(1963),《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约三种》(1968),《各国所藏回鹘文书综述》(1970),《回鹘文奴婢文书及养子文书》(1972),《回鹘文人质文书》(1972),《Bolmis文书》(1975),《Qayimtu文书》(1976)等。作者还指出,护雅夫和山田信夫开辟了用回鹘文研究维吾尔族社会历史的新途径。
3.东北部
千种达夫著《满州家族制度的习惯》、《满州家族制度的习惯Ⅱ》、《满州家族制度的习惯Ⅲ》(1964,1965,1967)第1、3卷,是从1939年到1942年间为“满州国”亲属继承法的立法而进行的、有关家族习惯调查的基本资料。此调查以居住在“满州国”以内的满、汉、蒙古、回、朝鲜、白俄罗斯等民族为对象,调查项目包括各族共存的问题,如亲属、家族的范围,户主、家产、家族制度、婚姻、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宗祧继承、遗产继承等。第2卷是围绕同性不婚、妾、宗祧继承、嗣子、养子、家产、大家族等问题,对各民族进行了比较研究。此书对了解当时的家族习惯提供了宝贵资料。
4.西藏
长尾雅人著《日本西藏研究概述》[19]。作者在文中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对西藏的研究,最初是作为佛教研究的一个部门发展起来的。而对西藏的语言、历史、民间文学、文化以及人类学等非宗教领域的研究,则是在战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才开始的。作者指出:“1953年,日本成立了西藏学会(简称JATIS),由石浜纯太郎任第一任主席。这个学会的唯一作用就是每年开一次会,出版一本年刊,但却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意义而材料丰富的学术报告和论文。1961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索南嘉错、卡尊桑波和次仁卓玛三个藏族人来到日本,在东京参加了东洋文库的工作。他们的到来为日本的西藏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这三位以及后来又参加东洋文库工作的另一位藏人,与日本学者密切配合,通力协作,促进了日本有关西藏的研究和出版工作。”关于日本的藏学研究成果,该文和佐藤长著、向红笳译《日本西藏历史研究的起源和发展》[20]一文中写得较全面、系统,可供读者参考。
5.台湾[2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台湾归来的研究人员,以在台湾所掌握的材料为基础,发表了不少论文、专著。进入60年代之后,外国人在台湾的实地调查成为可能,马渊东一及其新一代研究人员开始进行田野调查,其成果不仅质量提高了,而且数量也有了迅速增加。
马渊东一(1909-1988),台北帝大土俗人种学研究室唯一的毕业生,其对台湾原住民社会的研究成果取得了国际上的公认。(1)马渊东一主编《民族学研究:台湾研究特集18-1·2》(1954),被认为是一份具有总结性的特刊号,“马渊对于半个世纪殖民地时期的原住民的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流变进行了详细的归纳和整理,并对各个分支领域的研究者以及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也进行了概括、整理。”[22]该特集中收有从战前到战后日本研究人员的台湾研究成果,主要以对原住民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为中心,还包括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研究和台湾汉族研究等论文。其中,有关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论文有,马渊东一的《高砂族的分类》和《有关高砂族的社会人类学》、宫本延人的《高砂族的物质文化》和《台湾民族学研究史概说》等。此外,陈奇禄的《最近台湾出版的人类学相关文献》为题的目录,为了解战后在台湾开始的新的研究动向提供了资料。从总体上看,在日本殖民统治结束近十年之后,该特集通过对日本统治时代的研究重新进行回顾,唤起人们对新的问题的关心,并把它引向未来研究。(2)《马渊东一著作集全3卷》(1974),是集马渊东一主要著作之大成。其中有不少有关台湾研究论文。马渊东一的原住民研究,以丰富的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加上基于坚实的社会人类学理论根底的严谨的考察,给文化人类学者们留下了很有价值的论文。14年之后(1988)又出版了《补编》,书中收有著作目录和年谱。
增田福太郎著《未开化社会中习惯法的建立》(1957)。战前,作者作为台北帝国大学的副教授,曾经对台湾原住民社会的婚姻制度、权力与社会统制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此书以台湾原住民资料为依据,对“习惯法”的建立与其特点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其内容相当于现今的法律人类学研究。
千千岩助太郎著《台湾高砂族的住家》(1960)。此书是集作者从1936年起持续十多年的原住民族房屋建筑调查之大成。书中有各民族的传统建筑物中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或接近于原型的照片和图等,并加以分类与考察。通过此次调查,反映了在日本统治台湾50年间发生的传统生活的急剧变化,为后人留下了一些珍贵的资料。此书的前半部,概述了各民族的分布、移动状况及建筑特征,并对各民族房屋考察结果进行了说明。本书所涉及的民族有泰雅族、赛夏族、布农族、邹族、排湾族、阿美族、雅美族等。作为小结,进行了基于原住民族的房屋研究的分类与分布,阐述了其研究意义等。此书的后半部,按各民族分别收有其房屋的图片与照片。
王崧兴(1935-1995)著《非单系社会之研究——以台湾泰雅族与雅美族为例》(1965)[23]。此文是1964年王崧兴向东京大学大学院提交的硕士论文的缩写,被认为是作者初期台湾原住民研究的代表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国际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曾以太平洋地域研究为中心的有关双系或非单系构成问题一度成为热门话题。“本文为最先系统地讨论台湾土著族中,非单系社会的构成法则是什么。”[23]。文中,作者依据1962年在南澳系统的武塔社进行的调查资料,依次对泰雅族的家族、gaga(遵守同一习惯和禁忌,共同举行祭仪的社会组织)的组织以及战后成立的基督教教会组织等进行了探讨;依据战前、战后的文献资料,对雅美族的家族·亲属关系以及渔团形成进行了再分析。作者用此办法,对这两个民族的社会进行了比较与考察,并得出结论,泰雅与雅美的亲属关系都是双系,只是泰雅的社会是由以宗教关系为主的gaga而组成,雅美是由经济关系而组织其社会的。
松泽员子著《东部排湾族的家族与亲族:以tadjaran(第一路)的概念为中心》(1976)[24]文中作者依其所进行的3次为期2个来月的短期调查的基础上,利用调查资料对排湾族家族与亲属进行了考察。作为同样论述排湾族家族的社会组织的论文,末成道男的《台湾排湾族的“家族”》一文的特点在于从政治、经济角度进行分析;而本文的特点在于从象征性、礼节性方面对家族和亲属进行了分析。
佐佐木高明著《新粟的粽子和丰收的占卜:鲁凯族、排湾族的谷祭》(1978)[25]文中作者结合在台湾进行的短期实地调查和参考日本统治时期有关原住民族的调查资料,对鲁凯族与排湾族的栗子祭礼进行了复原尝试,并从文化史角度进行了考察。
张燿锜《台湾平埔族序论(1)/(2)》(1979,1980)。此文为有关台湾平埔族的文献研究。作者以有关荷兰人的记录、清朝历史书等为主,详细引用了已发表的有关平埔族的论文和高砂族研究论文中有关平埔族的资料,重新补写了平埔族诸集团的分布与迁移的历史。文中作者特别对汉族移民社会的扩大、其对平埔族社会的剥削和侵略以及受其压迫下的种族的迁移与分散的历史表示了关注。文中作者虽没有从人类学角度对社会、文化进行了分析,但作为种族间的关系史,对了解发生在台湾平地的平埔族与汉族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很好的概述。
末成道男(1938-)[26],1962年于东京大学文化人类学科毕业,1971年获得东京大学大学院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为东洋大学社会学部教授。主要研究东亚社会结构之比较。这一时期,他在台湾原住民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从1965年到1969年间,先后四次到台湾,对M村(排湾族)、R村(卑南族)、阿岱尔社(鲁凯族)、石溪(阿美族)等地进行了实地调查。他发表的论文有:在东京大学文化人类学科毕业时的毕业论文《高山族的土地所有制》(1962);东京大学博士论文是《台湾阿美族的社会组织》(1971),此文是依据1968年-1969年对台湾东部阿美族一村落——石溪的社会组织所进行的实地调查进行记述与分析的,后来作者对此进行了修改与补充之后正式出版(1983);《高砂族的社会结合与土地所有(1)》(1962),《台湾卑南族亲属组织的倾向性》[27](1970),根据实地调查的情况对卑南族亲属组织进行了分析;《台湾海岸阿美族的社会结合》(1971)。末成道男在《台湾排湾族的“家族”》[28](1973)一文中,根据实地调查资料对排湾族家族进行了考察。当时对排湾族的研究,除了对首领制的研究之外较多的是对家族的个别研究或习惯法的研究。而本文作者是把家族放在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之中进行了研究。特别是注重对排湾族长子的赠与习惯、亲属组织、等级制等,把家族放到排湾族整个社会中间去考察;还试着通过与日本家族的比较来更加明确排湾族家族的特征。
此外,在为庆祝日本民族学会成立30周年和50周年而分别发行的2部著作中,末成道男撰写了日本对台湾原住民研究的概述。第一部书中的《台湾(高砂族)》部分中,对上述《民族学研究:台湾研究特集》(1954)出版以来到1963年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概述;在第二部书中的《台湾》部分,对1964-1983年20年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概述。2000年3月,他在日本东洋大学亚洲非洲文化研究所1999年《研究年报》第34号上发表了《日本对台湾原住民的人类学研究:1895-1999》[5]一文,对一个多世纪以来所取得的日本对台湾原住民人类学研究成果及其特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与分析,并对21世纪日本的台湾原住民研究进行了展望。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末成道男教授为总代表的日本顺义台湾原住民研究会,在汇集、整理有关日本台湾原住民研究文献方面更是取得了重要成果,很值得我们借鉴。
三、有关各民族研究文献
1.回族[29]
田坂兴道(1912-1957)著《中国回教的传入及其弘通》田坂兴道被认为是推动日本中国伊斯兰研究的第一人。1940年起,他开始了中国伊斯兰研究。战后,他从东西交通史、伊斯兰史的角度,就有关中国伊斯兰文化、制度史、回民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1964年,东洋文库整理出版了他的遗稿《中国回教的传入及其弘通》。全书分为上下二卷共6章。此书是作者利用大量文献对回教传入中国开始、回教势力在元代的飞速发展、直到明代回教徒社会成立为止进行实证的巨作。作者力图对中国回教史进行系统、全面地论述。今天,此书不仅作为先行者的研究很具有价值,而且也成为立志从事中国回教研究者必读之作。
今永清二著《中国回教史序说—其社会史的研究》(1965),全书分8章。书中作者写到,“在本书中,我对回教社会的结构、回民的生产活动、回民起义,汉、回对立问题以及清朝的回民政策等做了一些探讨,提出了个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10]此书出版后,被认为是继田坂兴道之后推动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的又一部力作,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关注。
中田吉信,在日本,他被认为是继田坂兴道之后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第一人,其研究方向是中国的回民起义,尤其是西北回民起义。其早期代表作有《清代回教穆斯林的一个侧面——马承荫和马新贻》(1953)、《同治年间的陕甘回民起义》(1953)等。
2.满族
这个时期,日本学者在满学研究中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关于《满文老档》的整理、翻译和研究。战后不久,由著名清史研究专家神田信夫等组成的《满文老档》研究会,把《满文老档》译成日文,分7册出版(1955-1963)。这使《满文老档》全部原文以及译文可以作为史料进行有效利用。因此项成果,神田信夫荣获1957年日本学士院奖。后来,神田信夫等人又翻译出版了《旧满洲档·天聪九年》的第一、第二部分(1972,1975)[31]、《镶红旗档—雍正朝》(1972)等。
关于满语研究,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有:山路广明《女真文字的构造》及《女真文字加点之研究》(1952-1953)、田村实造等《五体清文鉴译解》(1955)、山本谦吾《满文形态论》和《满洲口语基础词汇集》(1955-1959)、羽田亨《满和辞典》(1973)等。[32]
1967年,日本出版了(俄)史禄国著、大间知笃三和户田茂喜译《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1967)[33]一书。作者史禄国(1889-1939),是俄国著名的通古斯学者,此书与《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书为其代表作。本书是一部对满族血缘群体调查研究的著作。书中作者依据实地调查和文献对满族社会组织进行了研究,内容涉及作为满族社会基础的氏族的结构及其功能、亲属称谓体系、婚姻、家族、继承权等社会人类学的基本问题。此书是研究清朝、女真等历史的研究人员必读之作。
刘小萌《近年来日本的八旗问题研究综述》[39]一文,对以东洋文库为主的日本研究八旗问题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可供读者参考。
3.纳西族
日本对纳西东巴文化研究起步很晚,大规模的研究是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时期主要成果有,(1)西田龙雄著《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文化》(1966),此书被认为是奠基性著作。[35](2)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纳西族特集第8集》[14],收有论文2篇、译文5篇。其中有君岛久子的《纳西族的传说及其资料——以〈人类迁徙记〉为中心》和齐藤达次郎的《纳西族的丧葬制度》等论文。还有和志武整理,君岛久子和新岛翡共译《人类迁徙记》;洛克著,村井信幸译《纳西族文献中的洪水故事》;和即仁整理,君岛久子和伴幸子共译《寻求不死之药》;刘钊搜集,君岛久子和桥本善信共译《纳西族的动物故事》;宋恩常著,百田弥荣子译《纳西族的母系家族》等译文。当时,在有关华南诸民族研究还处于未开拓阶段,该学会作为中国华南诸民族研究的先驱者,围绕会员们所关注的纳西族问题,编辑出版专门载有关于纳西族的论文及相关文献资料译文的特集,为此后大规模研究做了很好的准备工作。
4.蒙古族
在日本对中国少数民族研究文献中,蒙古学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且成果辉煌。其中,尤以历史、语言学研究成果突出。据日本蒙古学会编辑、出版的《蒙古研究文献目录:1900~1972》(1973)统计,该书收有1900年-1950年间蒙古研究文献目录1612条,1951年-1972年间蒙古研究文献目录1775条。后期仅达22年,而所收目录却超过了前期50年闻所收目录的总和。[36]
小沢重男(1926-)的蒙古语研究。小沢重男是首屈一指的国际著名蒙古学家。他于1951年从东京大学文学部语言学科毕业之后,一直从事对《元朝秘史》蒙古语研究,取得众多成果。这一时期他的主要著作有:《蒙古语四星期》(1963);《谈蒙古语》(1978);1978年出版《蒙古语和日本语》,书中通过对蒙古语族语言和日本语的比较研究,发现了蒙古语和日本语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和共同点。1979年,他又出版了《中世纪蒙古语诸形态之研究》一书。他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自己对《元朝秘史》蒙古语研究分成三个部分:一是基于对《元朝秘史》原文的严密的校订之上的译注工作,二是编写《元朝秘史》蒙古语语法,三是编辑尽可能完善的《元朝秘史》蒙古语辞典,此书就是这一系统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
日本的蒙古史研究。有余大钧著《日本的蒙古史研究概略》[37](1987)等文,可供读者参考。
5.彝族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彝学研究主要在彝族的历史、社会制度及语言等研究方面取得了比较系统的成果。这一时期,在日本从事彝族研究的学者很多,有关彝族历史的著作也出了不少。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长西田龙雄博士对彝语支语言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著有《缅甸语与罗罗语:其声调语系之比较研究(1964)、《彝·缅语研究》(1979)等;他在研究明代出版的《华夷译语》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为古代彝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线索。[38]
6.壮族[39]
(1)关于壮族社会、经济研究:有藤本光的《关于南宋的广马交易和西南诸国的状况》(1952)、《关于南宋的广马贸易和西南诸县的情况》(1952)、《横山寨考》(1952)、《关于广马和广监的关系》(1952)、《南宋广马考——关于其发端和结局》(1953);河源正博的《关于宋代羁縻州、洞的“计口给田”》(1969)、日野三郎《唐代岭南的金银流通》(1970)等文。(2)关于民族迁徙研究:有河源正博《蛮酋的内徙》(1955)。(3)关于少数民族反抗斗争研究:有河源正博《依智高叛乱与交趾》(1959)、小川博《宋代依智高的事迹》(1965-1967)和《唐代西原蛮的叛乱:华南少数民族史之一》(1963)、冈田宏二《关于依智高叛乱的几个问题》(1979)等。
7.其他民族
(1)永田珍馨著《北方骑马民族鄂伦春》(1969)一书,是含有相片的游记。战前,作者因从事特务活动,曾在大兴安岭鄂伦春、鄂温克地区进行过调查。此书在战前出版的资料基础上加了一些未发表过的资料再版,对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2)小松格著有《简明乌孜别克语》(1978)一书。
四、研究特点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有如下特点:
1.研究的出发点:“战后,日本民族学通过恢复重建和整顿阶段,完全由狭隘的偏重为殖民主义服务中解放出来,以全世界所有的民族为对象,摆脱了以落后民族为对象的研究,真正站在文化人类学的立场上,走向全球,进入向世界民族展开大规模的、广泛的调查研究的时期。”[40]这使这个时期日本对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与战前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2.研究内容:以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类研究为主。
3.研究区域: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研究明显占优势。
4.研究方法:以文献研究为主。具体表现为:一是对战前和战时的大量资料与论著进行分类整理、开发和概述;二是在历史研究方面,主要是对资料、文献的搜集、运用及考证;三是依据所掌握的文献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研究,包括翻译、介绍和论述。进入60年代以后,台湾、香港等地对海外研究者逐渐开放,这使日本学者在台湾的研究活动活跃起来,发表了不少实地调查报告。他们还通过对中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等国的实地调查,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间接调查,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5.研究队伍:战后成长的新一代中青年民族学者逐渐成为研究的中坚力量。可以说,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会、中国民话之会等团体成了他们的摇篮。多数学者各有专攻,持之以恒,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特色。
总而言之,这个时期日本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有的领域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总体来说,研究基本上是分散进行的,研究面比较狭窄,内容较为单调。可以说,这个时期的研究为日后日本中国少数民族研究高潮的到来做了准备,是研究的启动期。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我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1979年以梅棹忠夫为团长、以白鸟芳郎、铃木二郎、岩田庆治、米山俊直等5位教授组成的日本民族学者代表团战后首次访华,打开了中日学术交流的开端。从此,日本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收稿日期:2002-0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