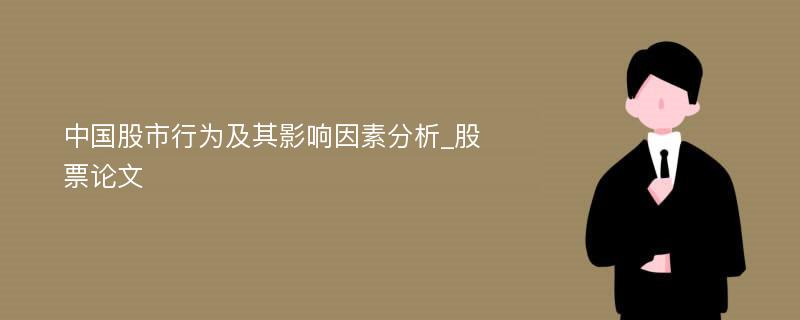
我国股票市场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股票市场论文,因素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献回顾
Tversky和Kahneman为行为金融理论的先驱。Tversky研究了人类行为与投资决策模型基本假设相冲突的三个方面:风险态度、心理会计和过度自信,并将观察到的现象称为认知偏差。Kahneman和Tversky(1979)共同提出了“期望理论”,使之成为行为金融研究中的经典代表学说。
1985年,DeBondt和Thalter发表《股票市场过度反应了吗?》一文,使行为金融理论作为一种新兴金融理论得以兴起。他们研究了1926年到1982年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数据,按照过去3年的累积超常收益率(CARs)对所有上市公司进行排序,以CARs最高的35家公司的股票构成“赢家组合”,以CARs最低的35家公司股票构成“输家组合”,检验在以后3年时间这两个组合收益的变化。实证的结果颇为神奇,简言之“赢家变输家,输家变赢家”。在检验期间内,“赢家组合”的收益低于市场平均收益的5%,而“输家组合”的收益却超过了市场平均收益的19.6%。
Jegadeesh和Titman以1965~1989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及美国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数据为样本,以前期CARs为分组依据,在短期内(3至12个月),买入前期价格持续上升的股票,卖出前期价格持续下降的股票。实证研究证明,这种“追涨杀跌”的策略获得的超额利益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此外,他们还证明了策略的成功并非由于它的系统性风险过高或股票价格对市场的公共因素的滞后反应,而是因为股价对公司特殊信息的滞后反应。
关于过度反应和反应不足的行为金融解释比较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模型:
1.BSV模型由Barberis、Shleffer和Vishny于1998年提出。该模型认为人们进行投资决策时存在两种偏差:一种是代表性偏差(Representative ness),即投资者过分重视近期数据的变化模式,而对产生这些数据的总体特征重视不够,从而导致股价对收益变化的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另一种是保守性偏差(conservatism),投资者不能及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修正自己的预测模型,导致股价过度反应(overreaction)。BSV模型从这两种偏差出发解释投资者决策模型如何导致证券的市场价格偏离有效市场假说。
2.DHS模型由Daniel、Hirshelfer和Subramanyam于1998年提出。该模型认为,市场中的投资者分无信息和有信息两类,前者不存在判断偏差,后者表现出过度自信和自我偏爱两种判断仿差:过度自信导致投资者夸大对股票价值判断的私人信息的准确性;自我偏爱导致对私人信息的反应过度和对公共信息的反应不足。
3.HS模型由Hong和Stein于1999年提出,与前两个模型不同的是,HS模型把市场中的投资者分为消息观察者和动量交易者两类。在预测股价时,消息观察者完全不依赖当前或过去的价格,而是根据其获得的关于股票未来价值的信息;动量交易者则把他们的预测建立在一个对过去历史价格的简单函数上。HS模型认为最初消息观察者对私人信息反应不足,动量交易者试图利用这一点进行套利,但结果恰恰导致股价的过度反应。
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引起学者的关注。张人骥、朱平方和王怀芳(1998)修正了DeBondt和Thaler的研究方法,对上海证券市场1993年6月至1996年6月期间是否存在过度反应进行了研究,得出了拒绝过度反应的假设。赵宇龙(1998)通过对上海证券交易所123家上市公司1993至1996年间的会计盈余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指出,“上海股票市场对预期的好消息存在过度反应现象,而对预期的坏消息存在反应不足的现象”。沈艺峰、吴世农(1999)在严格遵守DeBondt和Thaler(1985)的研究方法下,选取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关于1996年上市公司配股工作的通知》为中心事件,检验深圳股市在配股事件后的46周内的收益表现,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显著过度反应。王永宏、赵学军(2001)对1993-2000年深沪两市1993年前上市的全部股票进行“惯性策略”和“反转策略”的实证研究,发现存在明显的收益反转现象,但没有明显的收益惯性现象。吴世农、吴超鹏(2003)分别对上海股市进行“价格惯性策略”和“盈余惯性策略”研究,却发现存在短期的惯性现象的结论。周琳杰(2002)采用深沪两市1995~2000年的股票交易数据考察了股市“惯性策略”的赢利性特征,发现期限为一个月的“惯性策略”的超额收益明显好于其他期限的策略,但随着持有期的延长,“惯性策略”的收益明显下降。邹小凡(2003)对沪市1993~2001年的交易数据检验出“赢者组合”与“输者组合”月收益率之差在持有期为1年或2年时统计上显著,由此认为我国股市存在过度反应。总的来看,尽管各研究采用的样本时期和检验方法各有不同,除了少数研究外,多数都发现了我国证券市场存在不同程度的反应不足和过度反应。
综观国内目前对我国资本市场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检验是否存在反应过度或反应不足,然后探讨如何应用心理学的原理来解释这些现象。本文除了检验我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还将探讨我国股票市场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超常收益率的影响因素,从而对过去简单地套用行为金融理论对我国资本市场行为进行一般注释进行反思。
二、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公司,样本的时间跨度为2000年1月4日到2001年1月2日,共计240天。另外,为了完整的观察样本的表现,本文将要求每个样本都要有从形成期到检验期共240天的连续交易时间,其中形成期为120天(2000年1月4日至2000年7月10日),检验期设为120天(2000年7月11日至2001年1月2日)。其余没有连续交易数据的股票已从样本中去除。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深圳市国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制作的《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查询系统CSMAR Trading IQS.V2》和《Wind资讯》。
2.模型设计和变量定义
(1)股票组合的构建:在检验期内,将股票按照累计超常收益率(CARs)进行降序排列。然后,取其中CARs最高的30支股票和最低的30支。用CARs最高的股票组成“赢家组合(Winner portfolio)”;用CARs最低的股票组成“输家组合(Loser portfolio)”。
(2)CARs的计算: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的特殊性,β的估计具有不稳定性,因此采用传统的CAPM模型计算超常收益的方法不可行。所以本文将采用市场调整超常收益(Market—Adjusted Excess Return)。值得说明的是,De Bondt和Thalter(1985)认为这两种方法计算所得结论很相近。超常收益率(AR)、累计超常收益率(CAR)和平均累计超常收益率(ACAR)的计算公式如下:
AR[,i,t]=R[,i,t]—R[,m,t]
CAR[,i,120]=∑[,t=1][120]AR[,i,t]
ACAR[,w,120]=1/30(∑[,n=1][30]CAR[,n])
ACAR[,l,120]=1/30(∑[,m=l][30]CAR[,m])
其中:R[,i,t]代表第i种股票第t天的收益率;R[,m,t]代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指数第t天的收益率;t=1,2,…,120;ACAR[,w]表示赢家组合的平均累积超常收益率,n代表该组合中的第n种股票,n=1,2,…30;ACAR[,l]表示输家组合的平均累积超常收益率,m代表该组合中的第m种股票,m=1,2,…,30。
(3)其他变量:为了进一步分析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的未来累计超常收益及其影响因素,本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研究过去120天的累计超常收益、换手率、公司规模、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增长量、公司每股收益同上午同期相比的增长量对未来120天的累计超常收益的影响程度。估计和检验的回归模型为:
CAR[,i,t]=a+a[,1]CAR[,i,t-120]+a[,2]Turnover[,i]+a[,3]ln(size)[,i]+a[,4]△ROE[,i]+a[,5]△EPS[,i]
其中:Turnover[,i]为各股票在形成期的总换手率,即首先计算个股当日的换手率,然后进行累加个股日换手率(t),t=个股日交易金额/个股日流通市值,形成期的个股总换手率turnover=∑形成期个股日换手率;size表示公司规模,是对公司在形成期内的总资产的自然对数;△ROE[,i]是各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增长量;△EPS[,i]是各公司每股收益同上年同期相比的增长量。上述财务指标均按形成期(2000年上半年度)各个公司的报表数据来计算。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1.描述性统计
按照研究设计,分别加总赢家组合与输家组合在过去120天(即2000年1月4日至2000年7月10日的超常收益率)并进行等权平均。分别得到了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的累积超常收益率,其中赢家组合为57.19%,输家组合为-38.18%,相差95.37%。然而在检验期后,赢家组合累计收益低于市场平均收益10.40%,输家组合累计收益高于市场平均收益6.69%,两者相差变为17.09%。
表1表明:赢家组合的CARs由形成期的57.2%转变为-10.4%;输家组合的CARs由形成期的-38.2%转变为6.7%。此外,表2的t检验表明:无论赢家组合或输家组合,其形成期的CARs与检验期的CARs都呈现明显的反向修正特征。
表1 赢家组合与输家组合累计超常收益(CAR)的比较
组 合 期 间 赢家组合输家组合
形成期:2000.1.4.~2000.7.10.57.19%-38.18%
检验期:2000年7.11.~2001.1.2. -10.40% 6.69%
表2 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检验期内平均累计超常收益的显著性检验
分期的检验区间 赢家组合tslg
2000.7.11.~2000.8.21.
—3.37%
—1.668
.106
2000.7.11.~2000.10.9.
—1.94%
—.612.546
2000.7.11.~2000.11.20. —5.54%
—1.692
.101
2000.7.11.~2001.1.2.—10.40% —2.662
.013
分期的检验区间 输家组合t slg
2000.7.11.~2000.8.21.3.86%
1.581
.125
2000.7.11.~2000.10.9.8.20%
2.081
.046
2000.7.11.~2000.11.20 5.50%
1.389
.175
2000.7.11.~2001.1.2. 6.69%
1.435
.162
2.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进一步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CAR[,i,t]=a+a[,1]CAR[,i,t-120]+a[,2]Turnover[,i]+a[,3]ln(size)[,i]+a[,4]△ROE[,i]+a[,5]△EPS[,i]
由表3可知,赢家组合在形成期的CAR与检验期的CAR、换手率和公司规模成显著反比关系,但与两个盈利指标(△AROE[,i]和△AEPS[,i])无关。具体地说,第一,形成期的CAR越大,检验期的CAR越小,说明赢家组合形成期的CAR反转程度越大;第二,形成期的换手率越大,检验期的CAR越小,说明反转程度越大;第三,资产规模越大,检验期的CAR越小,说明反转程度越大。由此可见,赢家组合存在显著的反转趋势,且这一反转趋势主要受到形成期CAR、换手率和公司资产规模的影响。值得指出的是,在赢家组合CAR的反转趋势中,公司资产规模并未发生稳定或缓冲趋势,反而发挥加速反转的作用,说明在赢家组合中,大公司股票CAR的反转比小公司股票更大。
表3赢家组合的回归结果
参数估计 显著性
自变量t值
估计值 标准差 检验值
Constant 2.940
1.138
2.583 .016
CAR[,i,t-120]
-.541.222 -2.437 .023
Turnover[,i] -.004.003 -1.048 .305
in(size)[,i] -.127.056 -2.251 .034
△ROE[,i]
-1.164
1.330
-.875 .390
△EPS[,i] .477.688.693 .495
R[2]
.413 — — —
由表4可知,输家组合在形成期的CAR与检验期的CAR在一定的程度上成正比,与换手率成显著正比,与公司规模成显著反比,但两个盈利指标(△ROE[,i]和△EPs[,i])对检验期的CAR同样没有影响。具体地说,第一,形成期的CAR越大,输家组合在检验期的CAR就越大,说明输家组合形成期的CAR反转程度越大;第二,形成期的换手率越大,输家组合在检验期的CAR越大,说明反转程度越大;第三,公司规模越大,输家组合在检验期的CAR越小,说明反转程度越小。由此可见,输家组合的CAR存在显著的反转趋势,且这一反转趋势主要受到形成期CAR、换手率和公司资产规模的影响。值得指出的是,输家组合CAR的反转趋势中,公司资产规模发生明显稳定或缓冲作用,说明在输家组合中,大公司股票CAR的反转比小公司股票更小。在我国,赢家组合中公司规模越大,形成期的CAR反转程度越大;输家组合中公司规模越大,形成期的CAR反转程度越小。赢家组合的投资者在CAR的反转过程中,并不因为是大公司的股票而更有信心继续持有,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表4输家组合的回归结果
参数估计显著性
自变量
t值
估计值 标准差
检验值
Constant 1.726
.817 2.113 .045
CAR[,i,t-120].450
.548
.822 .419
Turnover[,i] .010
.004 2.332 .028
ln(size)[,i] -.082
.037 -2.205 .037
△ROE[,i] .107
.766
.139 .890
△EPS[,i] .266
.424
.627 .537
R[2]
.648— ——
四、实证结果的讨论
通过实证结果,我们看到无论是赢家组合还是输家组合都存在明显的“反转趋势”,如何解释这种反转趋势呢?
(一)从心理学角度解释
从回归的结果,我们看到无论是赢家组合还是输家组合其形成期的CAR均对组合检验期的反转趋势有影响。De Long等(1990)基于心理学原理提出了投资者“追涨杀跌”导致反转现象,我们认为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De Long等人的观点。
对于赢家组合来说,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上,由于信息披露不对称及个体投资者缺乏信息分析能力,使一部分拥有信息或善于分析信息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往往是股票大户或个别机构投资者)得以获得超额利润。市场上的股票大户或个别机构投资者会利用自己的信息、资金等优势抬高股价来吸引个体投资者的跟进。由于个体投资者“追涨”的心理使得股价高于其真实价值,于是股票大户等投资者便可以从中获得超额利润。之后,股票大户等投资者则将股票抛售,在庄家离场后,股价逐步回归到真实价值,于是赢家组合便出现了“反转趋势”。又由于其余投资者“杀跌”的心态,当他们发现股价的持续下跌时便会抛售自己手上的股票造成股价的进一步下跌,结果反转现象将延续。由表2可见,赢家组合的CAR在检验期中随时间递增而递减且其显著性随时间递增而递增,这证明了投资者的“杀跌”心态造成了股价进一步下跌。
对于输家组合来说,投资者由于受到“自身代表性心理”影响,对近期表现不好的股票会产生“过度恐惧”。于是,这些投资者不但不购买这些股票还将抛售自己所持有的这类股票,最后导致股价低于真实价值,这正是投资者“杀跌”心态的体现和结果。当理性的投资者发现这一“认知错误”时,便会大量购入这类股票以获取超额利润,于是股价攀升。股价的攀升将会引来怀有“追涨”心态的投资者的购买,股价继续上升,最后导致输家组合的反转趋势。
(二)从我国股市自身的机制和特点来看反转现象
在回归分析中,我们观察到形成期的换手率对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检验期的反转趋势具有较明显的作用,这反映了中国股市自身的机制和特点对反转现象的影响。
第一,国际主要股票市场多为机构投资者主导的市场,机构投资者发展比较成熟。通常许多基金持有的投资组合较为稳定,在一段时期内往往变动不大,这就使市场整体表现出股票换手率低、价格波动不大的特征。中国股市则恰恰相反,中小投资者所占比重高,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尚不成熟,而且中小投资者在信息的获取和分析方面处于劣势。这就导致整个市场投机倾向较强,股票换手率过高,股票市场系统风险在总风险中所占比重过高,多数个股的收益与市场收益差距不大,使得多数股票的超常收益率比较小。因此,组合中某些股票的股价大幅上涨或下跌可能会导致整个组合的CAR出现反转。
第二,在我国,限制卖空机制使得投资者的套利行为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在防止过度投机行为的同时也削弱了市场价格的自我调节能力。例如:当许多投资者对某些股票看法发生分歧的时候,看好这些股票的投资者将推动这些股票价格上扬,由于缺乏卖空机制,看空这些股票的投资者仅有意愿却不能形成一股做空的力量。买卖双方力量对比的失衡导致股票价格不断上涨,从而造成股价持续扭曲。这就是形成期内表现好的赢者组合,到了检验期后,一旦投资者发现股票实际价值并没有它的价格所表现得那么好,就纷纷抛出,使得这些股票价格迅速下跌,在这段期间内它们的超额收益率往往就显著为负了。
第三,在实证结果中,不论是赢家组合还是输家组合均没有体现出“惯性趋势”。原因是,在中国,短期投资者远远多于长期投资者,因此投资行为主要是短期的投机行为。
五、结论与建议
作者收集2000年1月4日至2001年1月2日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市场交易的股票,借鉴Debondt和Thaler(1985)的研究方法,发现我国股票市场存在明显的“反转趋势”,同时还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反转趋势的主要因素,并探讨这种反转趋势的心理成因和制度成因。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在2000年1月4日至2001年1月2日这段时间内,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均出现了显著的“反转趋势”。这种“赢家变输,输家变赢”主要是因为投资者“追涨杀跌”心理以及中国股市自身机制和特点所造成的。
第二,从多元回归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赢家组合还是输家组合,形成期的CAR、公司资产规模和换手率三个因素对其检验期的CAR具有明显的影响,说明这三个因素在赢家组合或输家组合的CAR反转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建议市场监管者应努力完善市场机制使之更加健康,降低中国股市的系统性风险,与此同时,还应加强投资者教育,努力减少投资者的非理性投资行为,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