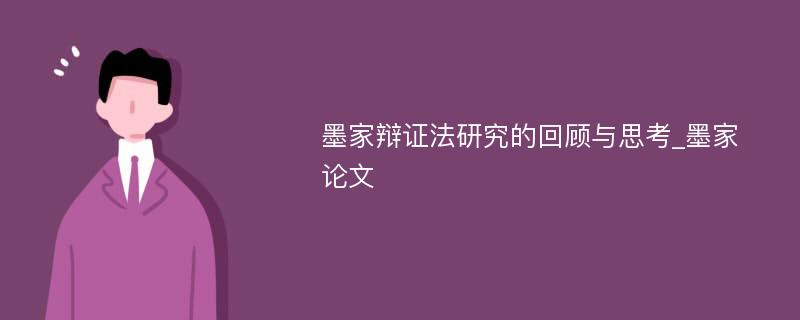
墨家辩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先秦至近代,对墨家辩学的研究曾有过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一研究既有对《墨辩》文字伪误的校勘、字义的训诂,也有对辩学义理的阐发。诸多先贤在这一研究中的卓著成绩,特别是他们的奠基、开拓和诱导之功,为世人公认,受后学尊崇。
然而,“学问之道,进化非有止诣”①。遵循学术发展的规律,我们应当随治墨先贤之后,继续前进,作新的探索。本文拟回顾与思考既往对墨家辩学的研究,以期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些许借鉴。
一、墨家有独到之辩学
研究墨家辩学的前提是,墨家有自己的辩学。对此,我国古今学问家是十分肯定的。
西晋鲁胜,曾刻意研究《墨子》书中《经》、《说》四篇,并为之作注。在《墨辩注·序》中,他第一次称这四篇为《墨辩》:“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通读其文,《墨辩》当为“墨子所作辩经”之称谓。
对于鲁胜以《墨辩》称谓《经》与《说》,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辩经》确实是墨子为自己著述所定篇名之一,鲁胜曾见。他为了明确地陈述这一事实,以《墨辩》称“墨子所作辩经”,“‘墨’以著其人,‘辩’以别其书”②。其二,墨子著书有否《辩经》篇目,鲁胜是否亲见均已不可考。他所以要提出《辩经》之名,以“辩”属“经”,又冠以《墨辩》之名,无非是要表明《经》、《说》四篇的主体是“辩”,而且对“辩”的阐发已成一种专门学问或技艺。这两种情况虽有出入,但它们都表明墨家有自己关于“辩”的专门学问,即辩学。
不仅古代先哲肯定墨家有辩学,今世治墨学者也认定墨家有自己的辩学。
陈启天在《中国古代名学论略》中说:“《辩经》就是墨家的一种辩学而已。”
方授楚认为:“《经》中辩学尤详,乃有《墨辩》之称,其他科学几为辩学所掩矣”③。
谭戒甫称:《墨辩》开“华夏二千年独到之辩学”④。
十分令人惋惜的是,这一中华“独到之辩学。并没有得到持续的研究和发展,而是随墨学的兴衰起落走过了一个曲折的历程,至近代才得以复苏。
二、墨家辩学研究的兴衰及近代复苏的原因
墨家学说及其辩学创建并兴盛于先秦。至秦,始皇忌“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⑤,以焚书之令统制学术,墨学步入衰微。汉时,儒学独尊,百家受黜,包括辩学在内的墨家学说自然也随之沉没。
至西晋,鲁胜以“兴微继绝”之心为墨家辩学文献《经》、《说》等四篇作注。至今,《墨辩注》正文已佚,仅存《序》文一篇,载《晋书》。其后,虽有唐乐台为《墨子》作注一说,但《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不载,难定真伪。可以说,墨家辩学及对它的研究在西晋以后就基本上中断了。
时光荏苒,历史的演进使情况发生了变化。自清中叶起,长期被冷落的墨学重新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重视,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更出现了空前的墨学研究热潮。
在人们重新研究和评价墨家学术思想的热潮中,《墨辩》被认为含有许多未被前人发现的宝贵思想,因而受到了格外的关注。“《经》、《说》诸篇,闳宜眇恉,所未窥者尚多”⑥。“此六千言者,所函义浩无涯矣”⑦。这是当时有代表性的看法。于是,一时间《墨辩》几乎成了“研究墨学之中心,附庸蔚成大国,不久恐此诸篇将发挥无余蕴”⑧。对墨家辩学的研究完全复苏了。
促成这一时期墨家辩学研究再度兴起并形成热潮的原因有二,即清代汉学的带动与“西学东渐”的刺激。约略说来,前者影响于1840年以前,后者则在1840年以后起主要作用。
首先是清代汉学的带动。乾嘉年间,儒士以汉儒经注为宗,承东汉许、郑之学,专从文字学入手,以训诂考据方法治经,形成所谓汉学,并支配了当时的学术活动潮流。治经考据需要广泛搜集资料,于是旁涉了史籍与子书,带动了包括墨学在内的儒学以外的诸子学研究。
“清自中叶,考据学兴。儒生治经,宗法许郑。经所未具,参以诸子。墨子书多载诗书旧文,足以订正经义”⑨。由是,《墨子》及所含之《墨辩》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其次是“西学东渐”的刺激。这是促成墨家辩学研究再度兴起并形成热潮的另一个原因,也是更主要的原因。1840年的鸦片战争,结束了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随着列强的经济与军事入侵,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文化也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形成所谓“西学东渐”。
这种与血、火为伍并带有强制性的西方近代文化冲击,引发了中国知识界的十分复杂的心态。
一方面,民族危机和清政府腐败的现实,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深感清廷提倡的汉学、宋学纯属空洞无用,从而把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在学习西方文化和技术上。“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⑩。于是,“讲西学”以“开民智”(11),就成了他们积极实践的重要内容。
另方面,悠久的历史文明,长期的闭关自守,“天朝上国”和“文化中心”的自我感觉,又使被迫接受西方文化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感情障碍。用胡适的话说就是“决不会感到自在的”(12)。一般士大夫甚至“觉得学问为中国独有”,“对于这种‘洋货’依然极端地轻蔑排斥”(13)。
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中国知识界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矛盾心态:既要学习西方近代文明以强国,又要维护中华民族的自信与自尊;既不否认“西学”的先进,又要显现“中学”比照“西学”的绝不逊色。为了适应这种文化心态,调和“中学”与“西学”的矛盾,一些倡导西学的人士设想借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来移植西方文化。他们以为,这样做不仅可使国人看到外国“所能发明者,安在吾必不能”(14),外国“之所有”“吾亦有”,从而抚慰其受创之感情;同时也可使人们相信“西方的方法对于中国的心灵并不完全是陌生的”(15)。
这样一来,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物色能充任协调中西文化中介的学说或思想,就成了当务之急。相对失去活力的儒学,非儒学派被提上了日程。其中的墨学,尤其是《墨辩》,以其倡兼爱、重科学、讲谈辩和求方法的特点,被认为与“西学”更为相近,是“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16)。“道咸以降,西学东渐。声光化电,皆为时务。学人微古,经传蔑如。墨子书多论光重几何之理,足以颉颃西学”。“光宣之交,博爱之教,逻辑之学,大张于世。而孔门言语之科,不闻论辩之术。孟轲剧口之谈,亦多不坚不可破之论。加以儒克己慎修为教,更无舍身救世之概。惟墨子主兼爱则杀身以利天下,出言谈则持论以立三表。事伟理圆,足与相当”(17)。于是,墨学及其辩学的研究被纳入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之中,受到社会需求的巨大推动,形成了空前的热潮。
三、近代墨家辩学研究的方法
推动墨家辩学再成研究热潮的“西学东渐”。同时为这一研究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即“东渐之西学”。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一些治墨的先贤正是从“西学”中获得了研究辩学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诠释辩学义理的根据与方法。所谓“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18),可算是对这种情况确切的说明。以国学大师梁启超为代表的上述思路与方法,不仅在近代墨家辩学研究中居主导地位,且影响至今。因之,当我们回顾既往对墨家辩学的研究路程并进一步思考其发展时,对上述思路与方法的检讨就应成为重点内容。
“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19),这是梁启超对研究墨家辩学方法的概括。这种以“新知”为凭借对“旧学”做出的“商量”是什么意思?他解释为:“以欧西新理比附中国旧学”(20),“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21)。这种“商量”欲求得之结果则是“旧学”与“西学”的符合。就《墨辩》来说,这种研究方法要尽力确证的是,《经》文“与今日西方学者所发明,往往相印”(22)。
下引《墨子学案》对《经》文的诠解以为例:
今论归纳同异之法。
“(一)求同法 《经》同:异而俱于此一也。”
“(二)求异法 《经》法异则观其异。”
“(三)同异交得法 《经》同异交得知有无。”(《经说》讹误不可读。)
这一条《经说》,共有九十一个字,在《经说》中算是最长。但错得不成话,我绞了几日脑浆,到底无法读通。如此要紧的一条,偏偏遭这个厄。不独我国古籍之不幸,实是全世界学术界之不幸了。但据经文这七个字,用穆勒的方法解他,意思也可以略明。‘有无’像是很容易知道,其实不然,非用同异交得之法,往往不能辩别有无。……归纳的五种方法,《墨经》中有了三种。其实共变法不过求异法的附属,求余法不过求同法的附属,有这三种已经够了”(23)。
上例中,《经》文的“同”、“法异”、“同异交得”诸条皆被纳入逻辑之穆勒五法,与求同法、求异法、求同求异并用法相印。其中“同异交得”一条,明明是“《经说》讹误不可读”,“绞了几日脑浆到底无法读通”,却“用穆勒的方法解他,意思也可以略明。”很显然,这种解释不是以《经》文自身为据以探究其义,而是把另一种思想,即穆勒的理论加诸这条《经》文,并作为它的意义。由此看来,“以新知商量旧学”实际是“据西释中”,即以西方传统逻辑的理论、概念和体系为模式去解释和重构墨家辩学。
“据西释中”,可以印证先秦时期的墨家早已发明了“穆勒五法”,发明了归纳逻辑;可以宣告“吾东方之培根,已生于二千年以前”,慨叹“以全世界论理学一大祖师,而二千年来,莫或知之,莫或述之”(24)。这对于适应既要引入“西学”,又要维护民族自尊的国人心理与感情,自然是再好不过的结果。因此,梁启超视这种方法为“增长国民爱国心之一法门”(25),而备加推崇。
四、“据西释中”方法研究墨家辩学的得与失
近代以西方传统逻辑为依据去解释和重构墨家辩学的方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确有一定意义,但作为科学方法来要求,则有根本缺陷。其得失可分述如下:
其所得有三:
第一,使墨家辩学研究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转换了指导研究的观念,走向全新的发展道路。
乾嘉时期,经学极盛,学人以子通经,引发了校训诸子之风。这种诸子研究必然囿于传统儒学观念,成为经学附庸。墨家辩学研究自不例外。
鸦片战后,社会政治与文化氛围发生激变。在“西学”传播的过程中,诸子学不再附属于经学,而是逐步转化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环。于是,西方文化也逐渐取代传统儒学成了诸子研究的思想武器。
墨家辩学研究中以西方传统逻辑为范本给出的解释与重构,体现并促成了上述的转化。这种“据西释中”的方法,为墨家辩学研究注入了全新的观念,极大地开阔和启发了当时人们的眼界与思路。“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滢;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26)。这很生动地说明了这种方法带给当时学人的感受。由此,墨家辩学研究被引向与乾嘉时期本质不同的发展道路。
第二,推动墨家辩学研究,在校训《墨辩》的同时,更注重辩学思想的系统阐发和整理。
受汉学影响,乾嘉时期的墨家辩学研究侧重于《墨辩》的校注。例如,毕沅的《墨子校注》(乾隆四十八年)据《经上》“读此书旁行”一语,首次恢复《经》文分上下两行横列的旧本写法,使之始现原本之真面目。其后,张惠言有《墨子经说解》(乾隆五十七年),“用鲁胜‘引说就经’之例,将四篇逐条拆开,各相比附,眉目朗然”(27)。这种研究使内容与形式都十分独特,且多有错讹又难寻参证的辩学典籍,得以成为初步可读之文字,从而为后继者进一步校注《墨辩》,以及对墨家辩学思想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到了19世纪后期,人们在以“西学”为武器研究《墨辩》时,发现许多前所未见的东西。这样,在校注《墨辩》文字的同时,对其中所含辩学思想的挖掘与整理就成为需要并且可能的了。
例如,孙诒让靠“近译西书”之助,印证了《墨辩》含有“欧士亚里大得勒(即“亚里士多德”——引者注)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其他科学内容的看法,并希望学术界“宣究其说,以饷学子”(28)。胡适以西方哲学和逻辑学的观念分析后期墨家,认为“这是发展归纳和演绎方法的科学逻辑的唯一的中国思想学派”(29)其思想应予以发扬。基于上述学界人士的认识与提倡,《墨子之论理学》、《墨子学案·墨家之论理学及其他科学》、《<墨子·小取篇>新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别墨》、《先秦名学史·墨翟及其学派的逻辑》等,一批专门研究和系统论述墨家辩学学术思想的著作相继问世。这些论著不仅带动中国学术界不断加深对墨家辩学的研究,而且开启并引导了中国名辩学、中国逻辑思想史以及比较逻辑思想的研究。
第三、切实、有效地在中国知识界传播了西方传统逻辑。
西方传统逻辑早在明末已开始进入我国,李之藻译《名理探》可为代表。然而,这本首译的西方逻辑著作几乎没有在中国知识界产生影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可能是没有借助易被人们接受的载体。到了清末,梁启超等人依照“据西释中”方法阐释墨家辩学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介绍西方逻辑的过程。例如,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五)论理的法则”一节中,用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专门讲述“西洋归纳法”。其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介绍和宣扬西方逻辑,让人们“知道论理学为一切学问之母,以后无论做何种学问,总不要抛弃了论理学的精神”(30)。这种办法,可以使西方逻辑获得适宜的载体并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精华相联结,从而顺应人们的接受心理。事实表明,清末民初期间,西方逻辑所以能系统地输入我国并产生较广泛的影响,其中既有西方逻辑译著之功,同时也不排除借墨家辩学研究介绍西方逻辑之力。
其所失有二:
第一、模糊了对于目的、对象、性质及内容不同的墨家辩学与西方传统逻辑的认识,使二者的比较研究失去了前提。
“据西释中”解释墨家辩学的过程,实际是对墨家辩学与西方传统逻辑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比较是一种认识和研究的基本方法。在历史(包括思想史)研究中,甚至有人认为可能给出的解释方法便是比较。但是,比较绝不是随心所欲的万能法宝。如果不能尽量确切地把被比较的两种事实弄清楚,比较就失去了必备的前提,并将走入歧途。那末,墨家辩学与西方传统逻辑各自是怎样的情形?“据西释中”的方法又是如何认识它们的呢?
西方传统逻辑是由亚里士多德创建的,可以说直到符号逻辑创始之前,“传统形式逻辑的发展,实际只是对《工具论》的修正和补充”(31)。“亚里士多德研究逻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科学研究寻找正确的方法和正确的思维形式”(32)。西方传统逻辑为人们提供认识科学真理的工具,以正确思维形式及其规律为对象,以有效推理的规则为核心内容。对此,被尊为“逻辑之父”的亚里士多德有过自己的论述。
“我们必须说明我们所探讨的主题以及它所属的学科。它的主题是证明,对它进行研究的是证明的学科”(33)。
“所谓证明,我指的是能产生科学知识的三段论,也就是说,……所证明的知识的前提必须是真实的,原始的,直接的,比结论被知道得更清楚、先于结论而存在的,而且结论同它们的关系就象结果同原因的关系一样。……可能会有不具备这些条件的三段论,但这样的三段论,由于不足以产生科学知识,不会是证明”(34)。
“三段论就是议论,其中若干事物被陈述,被陈述的事物以外的某些事物必然因而产生。……也就是说要使推论成为必然”(35)。
以上引述表明,“亚里士多德研究三段论的主旨就是证明。正因为如此,他才把研究三段论这部分学问叫做证明的科学,也就是他所理解的逻辑。但他自己在当时并未把它称为逻辑学”(36)。亚里士多德正是从求取科学真理的证明工具走向三段论推理,走向前提与结论有必然联系的有效推理的规则,走向“就其仅仅涉及形式,或更严格地说,仅仅涉及完善的形式来说,是一种形式逻辑”(37)。
为了深入研究证明或证明的推理,亚里士多德必然要讨论论辩,并对证明与论辩给予严格的区分。他认为,由于论辩是以“被普遍地接受的意见”为前提,而不是以“真实而原始”的知识为前提,所以它不是证明。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不把论辩的推理看成是推理。他说,论辩或论辩的推理,“只能称为‘可能引起争论的推理’,而不能称为‘推理’,因为它似乎是推理,实际上并非如此”(38)。很明显,尽管亚里士多德也讨论了论辩,并且这种讨论从一个侧面“导致了对有效论证……一系列有效推理”的认识,但他并不认为论辩属于证明推理,在他看来论辩不应包含在他所理解的逻辑这门科学的主题之内,逻辑是证明的学科,是认识科学真理的工具,其核心是有效推理的规则。
墨家辩学与亚里士多德创建的传统逻辑明显有别,它提供的是论说和推行某种政治主张或学术见解的工具,以谈辩为研究对象,以谈辩的原则、方法为其基本内容。对此,墨子及其后学也讲得十分明白。
“治徒娱、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为义孰为大务?’子墨子曰:‘……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墨子·耕柱》)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墨子·小取》)。
“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墨子·尚贤上》)。
以上引述告诉我们,“谈辩”是保证推行并实现墨家义事于天下的首项要务;是使社会明晓详知墨家求治去乱治国纲纪的重要手段;因之也是贤士参政治国必备的条件。墨家辩学服务于学派主张的宣传与推行和社会伦理、政治问题的解决。它不是致力于科学真理的认识。它的核心是辩的方法与原则。
从以上简要说明可以看出,墨家辩学与西方传统逻辑是目的、对象、内容、性质均不同的两种学术思想体系。“据西释中”的方法视二者为同一种东西,又直接把西方传统逻辑的原则和模式加诸墨家辩学,这正是对两种不同学术思想自身情形模糊认识的结果。从这种认识出发对墨家辩学所做的解释,其结论的客观性就值得考虑了。
第二、注重墨家辩学与传统逻辑在具体原理与概念上的比照对应,忽略对墨家辩学自身内容及其所由产生并受制约的历史条件的分析,致使对墨家辩学的解释缺乏根据。
近代一些治墨学者认为,墨家的“辩”就是西方的“逻辑”。依据这一定位,挖掘和发现墨家辩学所含有的与西方传统逻辑的对应点,并给出尽可能细致周全的说明,就成了“据西释中”方法阐释墨家辩学的着力所在。例如,名即概念,辞即判断,说即推理,“三物”即三段论,“一周而一不周”即名词周延性问题,“以类取,以类予”即归纳法,“同”、“异”“同异交得”即穆勒五法,“彼”、“此”即变项等等。自然,这种比照对应的不同阐发会有细节的差异,但是,以西方传统逻辑为基准去审视墨家辩学则是它的根本所在。
应当承认,在一个时期内,上述的比照对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活跃学术思想,然而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任何一种思想的倡导者都是生活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所以,我们要理解一种思想,就要在研究其自身的同时,去探求孕育并产生这种思想的根据——思想家置身其间的社会条件及由此生成的社会需求。
墨家辩学是一种学术思想,它所以有这种研究对象、思想内容与阐发方式,而不是另外的一种,同样是反映了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和相应社会需求的结果。因而,要了解墨家辩学这一学术思想的特质,不是把它同另一学术思想加以对比就可得出结论的,而是要深入研究其自身以及决定其自身内容的根据。
对墨家辩学的核心概念“辩”的解释可以做为一个例子。“辩”的真义和本质究竟是什么?按照“据西释中”的比照对应,“辩”等于“逻辑”,也是求真的学问。但是,当我们认真研究墨家自己关于“辩”的论述以及影响墨家思想的相关条件时,就会发现上述解释的失误。
墨家对“辩”有自己的论述:“辩,争彼也”(《墨子·经上》);“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墨子·经说下》);“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墨子·经下》)。这说明,墨家的“辩”,属于是非之谓的论争,其意在“取当求胜”。所谓“当”,就是正确、恰当。如“所染当”、“所染不当”(《墨子·所染》)、“赏罚之当”(《墨子·非攻中》)、“赏罚不当”(《墨子·天志下》)等。墨家的辩,就是要在是非之争中,区分正误,取当求胜。“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墨子·经说下》),正是这个意思。
有学者释“当”为“真”,并把墨家的“辩”说成是求真的学问,这是有悖于墨家本意的。《墨子》中的“真”与“假”有明确的意义,完全不同于“当”与“不当”。例如,“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雌雄也。’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墨子·辞过》)此“真”即真确实在之意。又如,“假必悖,说在不然”(《墨子·经上》),“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墨子·脩身》)。上引之“假”,皆有违背事实和虚妄之意。如果认为十分注重辨析名实关系的墨家会把意义明显有别的“当”与“真”混为同名,其理难通。
墨家所以把“辩”理解并规定为“取当求胜”,而不是探究和认识科学真理的工具,这是由特定的背景所决定的。
首先是墨家思想特定阶级内容的要求。
墨子出身低微,做过工匠,与穆贺辩时曾自称“贱人”(《墨子·贵义》)。墨家代表“农与工肆之人”,其思想反映了属于社会下层的平民劳动者的利益,是一个为劳动阶级呐喊的思想派别。其主要表现有两方面:其一,无情揭露和批判统治者对劳动者的剥削压迫。他们指斥“当今之主”不仅“不以其劳而获其食”(《墨子·天志下》),更要“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华衣、美食(《墨子·辞过》),甚而“攻城野战”、“杀殉”“厚葬”,使百姓“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墨子·尚贤中》),“孤寡者冻馁”(《墨子·辞过》)。其二,为劳动人民的生存权利乃至政治权利而大声疾呼、极力争取。墨家提出,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命下》),“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
显然,墨家的上述思想必定为新老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所不容。他们成了墨子所说的“以其言非吾言者”(《墨子·贵义》),即墨家的反对派。例如,屡饰其言以非墨子的“好攻伐之君”、直斥主“兼爱”的墨家为“无父”之“禽兽”的孟子等,可为代表。此外,作为非“贱人”的一般士人,他们虽然承认墨家思想有难能可贵之处,“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庄子·天下》),但又认为墨家的主张过于理想化,且有悖传统,使人难于接受。这些人成了墨子所说的“舍吾言革思者”或“不知仁者”(《墨子·贵义》)。例如,《庄子·天下》曾指出,墨家“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是好的,但他们“以自苦为极”“其行难为也”;又说,“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
这样一来,“天下莫为义”(《墨子·贵义》)与“天下之士君子之去义远也”(《墨子·天志下》),就成了墨家推行本派所倡“义事”时面对的社会环境。行“义”倡“兼”的墨家思想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立足、传播、实施,除了通过“强说人”和“行说人”(《墨子·公孟》)而使“非吾言者”服,“舍吾言者”信,就别无他途了。由此,“谈辩”被墨家列为成就“义事”的首项大务,并以“取当求胜”为其特征,就是很可理解的了。
其次是反辩和非辩学派的推动。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谈辩远非限于一家一派,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儒、墨、道、法诸家,无一不在进行激烈的辩论,以非人之说而是己之说。但是,在实践中对论辩十分认真的思想家们,在理论上对“辩”的态度却大不相同。墨家主辩、倡辩,孔、孟反辩;老、庄非辩。
孔子以“克己复礼”为最高理想,“礼”也就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在孔子看来,“学礼”(《论语·季氏》)、“知礼”(《论语·述而》)、“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是“复礼”的头等大事;谈说辩论不仅无助于“学礼”、“知礼”,反而会使人们“进退无礼”,因而是不必要的,甚至是可憎的。所谓“立于礼”(《论语·泰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论语·公冶长》),“恶利口之复邦家者”(《论语·阳货》)等,表明了上述的看法。孟子遵孔子之说,同样反对辩。他很善辩,“其辩言与墨同”(鲁胜《墨辩注序》)但不屑于承认“好辩”,“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他反对一般士人的议论辩说,斥之为伴随“圣王不作,诸侯放恣”而来的“处士横议”。对于“横议”中的有影响者,如善辩的墨家,更是仇视有加,必欲消灭其学说而后快。即所谓“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孟子·滕文公下》)。
老、庄并不视辩为可憎,而是认为它无用。庄子眼中的事物与是非都是相对的。“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因此,辩察是非是根本不可能的。“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庄子·齐物论》。对于只能因任自然而体认的大道,硬要过分宣说、辩其是非,就不成其为大道,也达不到对大道的认识。这正是“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和“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庄子·齐物论》)的意思。
面对反辩派对辩的指斥和非辩派对辩的否定,墨家从理论上论证并肯定辩有“明是非之分”的功用,和有“取当求胜”的本质特征,以使自家的“谈辩”立于不败之地,就成为责无旁贷的事情了。
再次是中国古代文化重人文特点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有突出的人文精神。这是指在人、神、自然三者中,以人为本的、十分注意和强调人的生存、发展和人的地位、价值的文化精神。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承认神,但就人与神的关系而言,多有先人后神,神服务于人的主张。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墨子则把神(天志)视同为匠人的工具,用来辨别事情的是非与当否(《墨子·天志》)。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古代思想家虽然承认人要受自然制约,“逆天者亡”,但也强调在协调自然的前提下,人做自然的主人,突出人的价值。“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春秋繁露·服制象》),“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等,表明了这种认识。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不是孤立个体,而是群体中的一分子。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墨子告诫,人要懂“处家”、“处国”(《墨子·天志上》)。孟子更指出,“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膝文公上》)。这是说,只要是一个人,就要百工为他提供必需品;如果一切都自己干而脱离他人,就是率天下人疲于奔命。总之,人是相互依存的,是做为群体而生存的。
这样,人生存、发展和实现价值的基本条件就是群体环境——社会的和谐。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就是这个意思。为了实现这种和谐,以伦理规范为内容的人际原则和以社会治乱为中心的政治问题,就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关注的轴心。中国古代文化的这种人文精神,难于引出科学分析的思想,却必然导向道德方面正误、当否的讨论与辩察,以使人们认识和确立自我在社会关系中的正确位置及相应的行为规范。
墨家自身思想及所处文化氛围均有浓厚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使墨家在用“谈辩”以言诲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墨子·非儒下》)时,只能是明晓“兼相爱”与“交相恶”等的是非、当否、胜负,而再无其他。墨家认定辩为“明是非之分”与“取当求胜”的工具,这是与中国古代文化人文精神的影响分不开的。
如前所述,“据西释中”的方法,是以西方的传统逻辑为模式重构墨家辩学。这种方法是按照传统逻辑的原理、概念去对应和套解墨家辩学,至于墨家辩学自身内容的分析及其生成根据的探究则被忽略了。这是一种“由外视内”的重构。这种重构实质上是西方传统逻辑的中国式讲述,而不是对具有自身特质的墨家辩学思想的阐释。为了克服“据西释中”的不足,墨家辩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应当变“由外视内”为“由内视内”,即以墨家学说、中国古代文化及相关历史背景为根据,对墨家辩学自身特质进行分析与阐释。
“由内视内”不再简单地把墨家辩学定位于西方传统逻辑的中国型,而是把墨家辩学看做墨学和先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以此为研究的基点。
“由内视内”不再着力于按西方传统逻辑的模式重构墨家辩学,而是把分析墨家辩学自身内容作为研究的核心。
“由内视内”不以西方传统逻辑作唯一参照系,而是要以对墨家辩学所由生成并受其制约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条件和因素的探究为参照和依据。
总之,研究墨家辩学自身内容,并把这种研究向中国古代文化认同,是“由内视内”的主要思想。它不排斥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而是要改变那种缺乏深刻认识的简单比附。
注释:
① 梁启超《墨子学案·自序》,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第1至2页。
② 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
③ 方授楚《墨学源流》,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173页。
④ 谭戒甫《墨辩发微》,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页。
⑤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⑥ 孙诒让《与梁卓如论墨子论》,转引自《墨学源流》第219页。
⑦ 梁启超《墨经校释·自序》,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3页。
⑧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载《饮冰室合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31页。
⑨ 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0页。
⑩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70页。
(11) 严复《原强》。
(12) 胡适《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1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载《饮冰室合集》第10卷,第26、27页。
(14)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饮冰室合集》第9卷,第13页。
(15) 胡适《先秦名学史》第10页。
(16) 胡适《先秦名学史》第9页。
(17) 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第140页。
(18)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饮冰室合集》第9卷,第13页。
(19) 梁启超《墨经校释·自序》第3页。
(20)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载《饮冰室合集》第8卷,第55页。
(21)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饮冰室合集》第9卷,第13页。
(22) 梁启超《墨经校释·自序》第1页。
(23) 梁启超《墨子学案》第137页至139页。
(24)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载《饮冰室合集》第8卷,第71页。
(25)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载《饮冰室合集》第8卷,第55页。
(26)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饮冰室合集》第9卷,第13页。
(2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载《饮冰室合集》第10卷,第230页。
(28) 孙诒让《与梁卓如论墨子书》,转引自《墨学源流》第219页。
(29) 胡适《先秦名学史》第58页。
(30) 梁启超《墨子学案》第134页。
(31) 宋文坚《西方形式逻辑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页。
(32) 宋文坚《西方形式逻辑史》,第66页。
(33)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2页。
(34)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第159页至160页。
(35)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第93页。
(36) 马玉珂主编《西方逻辑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
(37) 肖尔兹《简明逻辑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9页。
(38)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第266页。
标签:墨家论文; 文化论文; 思考方法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墨子论文; 国学论文; 读书论文; 科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推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