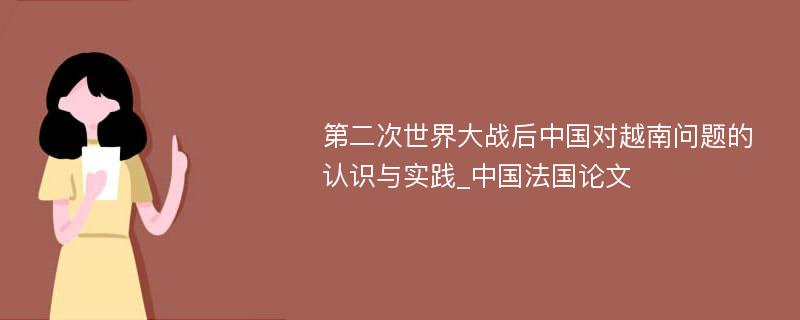
中国关于战后越南问题的认知与实践(1942-194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越南论文,战后论文,中国论文,认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关于战后越南问题的对策,经历了由中国单独托治实现越南独立到同意法国战后重返越南的转变。目前已有研究成果,存在线性解释倾向,揭示了蒋介石从主张“大哥”计划到顺从罗斯福托管计划的转变过程(注:Xiaoyuan Liu,China and the Issue of Postwar Indochin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Modern Asian Studies,vol.33,no.2(1999).)。其实,这一转变并非直线性地一举完成,而是对应战时中国自身所处国际形势,法国国际地位以及美国对越政策的变化,在矛盾中曲折展开。中国政府内部对战后越南问题的认知也意见分歧,致使战后中法关系中出现了条约谈判成功而越南现地却冲突不断的矛盾情形。本文力图在重建曲折历史过程的基础上,透视国民党人其时对自身所处国际地位的认知,并试图探究中国政府外交决策的过程及其与实践运作之间的关系。
从寻求“大哥”的特殊地位到“一如联合国家一员对越之关系”
1940年9月,法、日在越南合作后,中国西南抗战形势骤然恶化。为维护战时国防安全并“为求进出越南作战便利之目的”,中国一面与驻越法军保持秘密情报联络,一面扶植指导流亡在华的越南革命团体。(注:万仁元、方庆秋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第536-539页。关于战时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的关系,详见拙作《抗战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方人士开始关注战后越南独立问题。一篇发表在《中央周刊》的文章称:“世界大战以后,安南之是否能独立,如不能独立,则其隶属问题,实与我国有深切之关系,不能不加以注意与研究也。”(注:竺可桢:《世界大战后之越南》,《中央周刊》第4卷第50期(1942年7月23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盟各国虽对大西洋宪章所揭橥的建设“一个美好未来”的原则表示同意,但根据这些原则引申到具体的事例,则因各国立场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释。战后殖民地问题便是如此。美国为削弱英法在亚洲的殖民势力,增强殖民地人民的抗日力量,明确表示支持战后民族自决。而英国因在亚洲享有巨大殖民利益,首相丘吉尔于大西洋宪章签字后三星期在下院提出限制或保留措施,将英国的自治领和殖民地划除在美国所提议的民族自决范围之外。(注:加里·R.赫斯:《美国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载入江昭、孔华润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9页;惠丹:《英国人的战后世界观》,《中央日报》1943年5月9日;陈立人:《战后南洋的政治问题》,《华侨先锋》第5卷第6期(1943年6月)。)
1942年8月3日,罗斯福通过私人特使古索(Currie)向蒋介石表示:反对战后将印度支那交还法国,主张由两国或三国联合托管。(注:Memorandum on Chiang-Currie conversation,3 Aug.1942,Currie papers,Box 4.本文中的注释,凡未标明出处者,均转引自Xiaoyuan Liu,China and the Issue of Postwar Indochin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一文。)美国之所以提议托管制,是欲借机削弱英法,通过与中国结盟,取代传统欧洲殖民强国成为稳定亚洲的主导力量。(注:Walter La Feber,Roosevelt,Churchill,and Indochina:1942-1945.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80(1975),p.1277.)蒋由于担心联合托管模式有可能被用于处理东北、蒙古和西藏等中国边疆地区的战后归属,同时基于越南战时受敌利用的惨痛经历,主张由中国充任“老大哥”,战后单独托治越南,扶助其获得完全独立。(注:Memorandum on Chiang-Currie conversation,3 Aug.1942,Currie papers,Box 4;Memorandum,Re:Chinese post-war aims,4 Dec.1942,Currie papers,Box5.)美国虽反对将越南交还法国,但对中国单独托管越南的计划也颇为震惊。美国积极扶植中国成为亚洲大国的初衷,是希望战后出现与美合作的亚洲,而不是将美国势力排除在外。由于中国战场的战略价值不容忽视,罗斯福谨慎避免直接与蒋发生矛盾,仅模糊表示:愿意考虑战后在南太平洋和东南亚某些地区采取一国托治,而对另一些地区实施多国监管。(注:Draft of letter from Mr.Owen Lattimore to Generalissimo ChiangKai-shek,December,194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FRUS),1942,China.Washington,1956,pp.185-187.)
至1943年8月,中国对战后越南问题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向。外交部长宋子文在出访英国时,阐明了中国的战后愿望:“(一)中国战后决无领土野心,惟东北与台湾则必须收复,日寇统治下的朝鲜则必须独立。(二)应以同盟国的协力,从速收复缅甸,打开盟邦援华物资大量输入的通路,俾在大陆上展开对日的反攻。(三)中国对越南之关系,将一如联合国家一员对越之关系,决不因中越曾有血缘,遂具有染指越南的心理。(四)中国在战时,需要与盟邦合作,在战后也需要与盟邦合作”。将中国对越关系定位为“联合国家一员对越之关系”,只是为了证明“中国的抗战目的,在消极方面,只是求生存,在积极方面,只是维正义,尽本无所谓‘新秩序’或‘共荣圈’”。(注:《我们的合理愿望》,《中央日报·社论》1943年8月7日。)
从寻求“大哥”的特殊地位到“一如联合国家一员对越之关系”,这一对战后越南问题的重新定位,反映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中国政府对“独立与合作”两大目标轻重缓急认知的变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推重为四强之一的中国认识到自己“在东方的地位及其所负的责任是格外重大”(注:蒋介石:《访问印度的感想与对于太平洋战局的观察》,1942年3月9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以下简称《总集》第19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61页。)。国民党人更是恢复了久违的东方大国的记忆与风范,当时就有人撰文指出:“兴灭既绝,济弱扶倾,是数千年来我国对外政策上的传统精神。为了救助邻邦,中国人在朝鲜、越南、暹缅,且曾兴过仁义之师,流过光荣之血!……我正已踏上复兴之路,宛如旭日东升的中国,起而负救护的责任,实为势所必至,理所固然,任何人无怀疑或反对的余地!”(注:姜季辛:《东亚秩序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三民主义半月刊》第1卷第11期(1942年12月1日)。)
1941年底至1942年初,泰被划归中国战区、中国军队援缅和蒋介石访问印度等一系列事件,激发了中国援助亚洲弱小民族、发扬民族主义的使命感。《中央周刊》宣称上述三事,“是我们援助东方弱小民族,使之一律平等的开端”,呼吁“对于目前发扬民族主义的机会,千万不可轻易放过”。(注:健民:《民族主义的发扬》,《中央周刊》第4卷第32期(1942年3月26日)。)立法院院长孙科在《中央日报》撰文宣传三民主义的世界性,强调:“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不但要求中华民族在国际上得到平等,并且要求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如果单独顾到本身的自由平等,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在国际上得到平等的地位,大家便感觉满足,不管旁的弱小民族,不过问朝鲜,越南,暹罗,印度得到得不到自由,认为那不是中国的事情,那就完全违反我们的民族主义。”(注:孙科:《三民主义的世界性》,《中央日报》1942年7月16日。)此时的中国俨然成为亚洲民族独立运动代言人。
蒋介石访印归来后,便就印度独立一事致函美国友人,请其转告英国,重新考虑对待殖民地的态度。蒋指出:“今后太平洋战事,正在英、荷两国殖民地内进行,所以英、荷两国对于各殖民地内的民众——尤其是对于广大的、有历史有精神和潜伏力量的民族,一定要从速赋予实权,采取切实的方法,使其力量得以充分发挥。然后才能使太平洋所有的各民族,群策群力,来挽救目前的危局!”(注:蒋介石:《访问印度的感想与对于太平洋战局的观察》,1942年3月9日,《总集》第19卷,第58页。)在蒋的授意下,中国舆论对英国的对印政策采取强硬路线。(注:《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7年,第22页。)5月29日,《中央日报》社论公开宣称,中国对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将“由心理上的同情,变而为具体的协助,以促成印度愿望的实现”。
中国之所以以亚洲民族独立运动代言人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除基于东方大国的传统义务感和国民党援助弱小民族的党义使命感外,还出于战时打击日本的需要和对战后新世界的憧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打击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势力,以有色人种“保护者”,自居,利用“扶助亚洲弱小民族之解放”的口号,在英荷殖民地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扶植傀儡政权。东南亚各地居民,则因不满殖民统治,或持消极的中立旁观,或助日人打击英荷。中国援缅部队亦遭到当地人的阻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中方认为:“此固由于日寇之多方诱惑”,“但其最大的原因,却在同盟各国的政治家,特别是英荷两国当局,对于东亚各民族未有充分的认识,至今犹不愿承认各民族悉有自由独立的权利。在所谓‘宪章’及所谓‘公约’或‘宣言’中所规定的‘民族自决’及‘恢复一切丧失自由的国家’,显然未将所谓‘远东’的各民族包括在内”。(注:姜季辛:《东亚秩序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三民主义半月刊》第1卷第11期。)1942年5月31日的《中央日报》社论指出,亚洲民族问题的症结“不在如何使亚洲人民了解战争目的,而在如何使其享有正当合理的地位。战时可以保卫民族的自由,战后可以提高民族的地位”,呼吁“凡是与亚洲有关的欧美联合国家,公开的宣布其战后民族政策,或更进一步以事实来证明其战后民族政策必然本平等的原则,促国际的合作,以奠永久的和平,求共同的繁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战目标,已由“完成建国大业”转向关注“战后和平”问题。从《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等一系列体现同盟国对于战后和平建设原则的文约中,国民党人感受到建构战后新世界的“新精神”,即“国际关系,不当基于暂时的利害,而当基于永久的道义”。这种国际道义之交,“有一点值得指出,即关于若干问题,应不分彼此,全面合作,同时,关于其他若干问题,则彼此应尊重主权,各不干预……以今年元旦二十六国所签字的世界大宪章而论,例如经济上的全面合作,就是向心力,各国家自定其政体,各民族应享受其独立,就是离心力。建立世界永久和平,端赖此两力的均衡!能维持此均衡,就是国际道义之交。”(注:《中国与战后和平》、《中印互助的重要性》,《中央日报·社论》1942年5月17、29日。)
中国亚洲民族独立运动代言人姿态招致西方社会的防范与疑忌,其中尤以英国人的反华情绪最为激烈。据时任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回忆,英国人担心在日本的威胁消灭以后,中国将成为亚洲的新威胁。不少英国官员和商人提出质问:中国本身的政策是不是也变得帝国主义化了。香港、马来亚、缅甸等地有那么多中国人,莫非中国对这些地方心存觊觎?(注:《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71页。)美国各大报“一般地同意蒋委员长访印之行,对于将来作战将有惊人之影响”,同时又感到“西方各国在远东之优越地位,确已成为过去”。(注:郑学稼:《历史的新页》,《中央周刊》第4卷第43期(1942年4月2日)。)一时间,“中国领导亚洲”的论调在西方社会不胫而走。
来自盟国友邦的疑忌引起中国的高度重视,因为这不仅直接影响中国的战时外援,更将成为战后中国建设的极大阻碍。为消除国际社会的疑忌心理,蒋介石一面对内强调“中国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无论对印度、缅甸、越南、暹罗,以及南洋各地民族,都应该一视同仁,尽力扶助,不好存一点‘民族优越’的心理”,要求“大家以后无论说话作文,不可再用‘领导亚洲’字句”,以免引起误会;并宣明中国对处置“战后南洋及高丽、台湾等地”的原则:“我们的原则也很简单,我们对于甲午年以后被日本侵占的土地,必须收回,我们中华民国国民所到之地,必须自由平等,尤其南洋一带我们一般侨胞过去所受种种不平等的待遇,必须彻底改正,今后在经济地位上,必须一律平等。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问题,都要与同盟各国尤其是要与美国,共同开诚的商讨,以谋合理的解决。”11月7日,蒋介石对《纽约前锋论坛报》发表谈话,表示:“最近有中国将来为亚洲领导者之论,一若不成器的日本的衣钵行将传于我国,中国年来历受压迫,对亚洲沉沦的国家自表无限的同情,但对此种国家的自由与平等,我辈只有责任,并无权利,我辈否认将为领导者”(注:蒋介石:《最近一年来外交财政经济军事报告》,1942年10月29日,《总集》第19卷,第347-348页;《呼吁人类建立平等互爱的世界》,1942年11月17日,《总集》第38卷,第165页。)。
蒋所宣明的处置战后南洋及朝鲜、台湾等地的原则表明,面对西方盟友的疑忌,中国发扬民族主义“促进国外诸弱小民族之解放”的激情逐渐冷却,取而代之的,是收回失去生存空间、保护本国侨民的现实利益关怀。此后,中国的舆论宣传,从“扶助亚洲弱小民族独立”的主义立场转向关注“东西合作”的外交需要,强调“东西合作为世界和平之本”,“中国一贯希望与西方合作,为了建设,为了和平,不可不与西方合作”。(注:胡秋原:《东西合作为世界和平之本》,《三民主义半月刊》第1卷第11期。)中国逐渐由亚洲民族独立运动代言人,转变为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合作者,宣称:“要重建战后的自由世界,我们必须先使联合国家在战时的合作加强,而且战后继续巩固这种合作”,“我们必须在这种战时合作的基点上,更发挥罗邱宣言‘尊重各民族自由’的精神,然后全世界各民族尤其亚洲各民族乃能尽其全心全力为争取人类自由而作战”。(注:《自由世界的重建》,《中央日报·社论》1943年2月13日。)
中国对战后越南问题便在这一认知环境中展开。确立在巩固战时合作的基点上谋求亚洲民族独立的方针后,中国对战后越南问题的认识已不见先前“当仁不让”的气势,而是多了一份对国际现势的冷静观察。立法院长孙科在介绍战后殖民地整理问题时,仅客观陈述:“欧洲的许多国家,像英、法、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在海外的殖民地都很多,将来战争结束,这些殖民地,究竟应该由原来的主权国管理,还是交由国际机构接收共管,这是战后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为了避免帝国主义的冲突,某些人士曾提议,设立世界殖民地管理委员会,来统筹管理全世界的殖民地。”(注:孙科:《国际现势及战后自际问题》,《中央日报》1943年6月3日。)
为了消弭战时盟国英国的误解,改善中英关系,便有外长宋子文“一如联合国家一员对越之关系”的重新定位。此后,随着中国战场作为最后反攻基地的战略价值逐渐丧失(注:王建朗:《试析1942-1944年间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的演变》,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364-365页。),其作为“联合国家一员对越之关系”的地位亦无形中受到削弱。1943年的开罗会议,从表面看,“发表中美英三国宣言,认定东北和台湾,都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决定在战后仍要归还中国,这实在是我们中国百年来政治外交上最大的胜利”。但实际上,个中滋味只有身临其境的蒋介石自己知道,“这种胜利,目前还只是我们精神上和道义上的胜利,而不是我们实在的胜利,更不是我们知识和学问的胜利。须知精神道义的胜利,一定要有真实的力量,为之保障,否则我们没有真实的力量来作凭藉,而徒然希望人家自动的取消不平等条约,归还我们过去的失地,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即如此次抗战胜利之后,如果我们的力量不能确保东北台湾,则不仅东北台湾,必将得而复失,而且我们中国整个的领土,都有再受人家侵略的危险!”(注:蒋介石:《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1944年2月10日,《总集》第20卷,第323-324页。)蒋的讲话当然有鼓励军政人员继续奋斗的用意,但又何尝不是他初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所获的苦乐参半的亲身感受。在开罗会议上,表面上荣耀至极的中国领袖蒋介石,实则内心深怕“引起英美之怀疑”,事事均依英美主张行事。关于印度问题,本拟提会讨论,惟美总统罗斯福以为英首相侧重保守,即使讨论亦必无结果,主张于战后再提,故未提出;关于朝鲜独立问题,则依英方建议,在。“使朝鲜自由独立”前,加入“在相当期间”的限定;关于琉球问题,“因我国无海军加以保护,且恐引起英美之怀疑,故本人对收回琉球未坚决主张”;关于越南问题,“本人表示无领土野心,并提议发表宣言,战后由安南独立……惟英国不愿于此时发表文告,故本人主张于战后再议”。(注:《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纪录》第5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95年,第825-826页。)
从同意法国战后重返越南到“查明美方政策后再行与法进行谈判”
1943年的开罗会议虽然表现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但因在美英全盘战略中的价值趋于下降,中国的国际地位实际上受到削弱。在此情形下,国民政府军委会参事厅提供的“战后国际问题的调研材料和处理意见”指出:“我国在越南利益之重大,无待赘言,而自此次抗战所得之经验,深知为国防计,我国更当收回此原属我国之领土,但以目前国际形势观之,我国似无法向和会提出此项要求”,“其惟一方法,只能以兵力将越南之日敌驱除,驻以重兵,然后向同盟国建议,使越南成为半自主国,其制度一如丹齐(即但泽,下同——引者注)自由城,由战后成立之国际联合会派驻高级专员,我国代为主持外交事务,并得出海之交通自由(滇越铁路全线及海防均当割归我国),总之,我国对越南之法定权益,将与前此波兰对丹齐之权益相等,如此我不收回越南,而实际上已得控制之矣。”(注:国民政府军委会参事厅:“战后国际问题的调研材料和处理意见”,1944年5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号(下同):761-213。)然而,由于日本突然发动“一号攻势”,“以兵力将越南之日敌驱除”的打算已无施展之可能。
在国际形势不利、军事占领计划又无实施可能的情形下,中国政府对于战后越南问题,只能被动应付。6月7日,外交部为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拟具“对安南之政策”,主要内容为:军事方面:以兵力占领北圻和老挝,这不仅有利于巩固我国西南国防,而且可以将越南之日敌驱逐,进而统治整个中南半岛,并使暹罗和缅甸受我控制。外交方面:1.力争最惠国国民地位,以增强与法人经济实力相抗衡的能力;2。通过与法越当局的谈判,取消各种限制越南华侨的苛律;3.提高华侨教育质量,增强他们的知识水准;4.在顺化和柬埔寨设置领事,以保护华侨,发展贸易。政治方面:1.鼓励越南青年,增强他们的民族自信力;2.加强中越文化联系纽带,恢复中越之间传统的互助合作与相互信任;3.在战后国际和会中,尽力支持越南代表,防止法国重返越南;4.增派中国驻越特使,以增进中越关系和越南的国际地位;5.广泛宣传大西洋宪章关于民族自决的精神和罗斯福总统在太平洋作战会议上的声明,即:战后越南不应重归法国,而是应在盟国扶植下获得自治,盟国将实施托管计划,帮助越南人民获得独立。(注:外交部备忘录“太平洋上殖民地问题与一般安全问题”,1944年6月7日,Hoo papers,Box 3。)
武力占领越南、对法交涉和与美合作托治越南,中国处理战后越南问题所采用的军事、外交、政治手段之间缺乏连贯性,甚至相互抵触。鉴于豫湘战场上的节节溃败已使中国的国际声誉降至低谷,外交部只得向蒋介石建议,除非由别国首先提出亚洲殖民地问题,否则中国代表团以不提为宜。蒋表示同意,并进一步指示:中国代表团不宜对“任何事情表示坚持”。(注:“宋子文致魏道明函”,1944年7月29日;“蒋介石致孔祥熙函”,1944年8月19日;“宋子文致魏道明函”,1944年9月13日;“顾维钧致蒋介石函”1944年,均见Wellington Koopapers,Box 70。)
1944年8月法国的解放及其国际地位的稳步回升,为中越关系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8月25日,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向外交部报告法当局对中法悬案交涉的立场如下:
……法方深知越南在中国国防上经济上之重要,愿以至大善意交涉此案,使中国满意。现法已决定让步者有三:1.法方愿予中国在越南特殊经济地位。(子)在北圻中国来往货物旅客有自由假道权;(丑)在海防或河内设立自由港,予中国各种特权;(寅)承认中国在越南之经济特殊地位,予华侨各种便利。2.担保嗣后越南不再为任何国家或党派攻击中国之根据地。3.愿予越南广意之自治权,惟此点以涉及法方内政,难容他国干涉,故对中国政府不便用正式方式担保之。至法方希望我方者亦有三:1.对越南之收复,不阻止法方派海陆空军前往协助。倘英美亦不反对,其军事合作方式可由中法军事当局决定之。2.对法在越南之统制权不予反对。3.取缔或最少不协助越南革命党,并不允许该党党员利用中国国境为破坏法在越南政权之根据地。(乙)法侨在华权益,法方希望中国在法律范围内予以保护,已没收者允予发还原主,免受重大损失,影响将来合作。(丙)至中法合作问题,亦有两点:(一)为应付将来和会困难,先事商定某种原则下互相协助,互通消息,以防三强任意操纵。(二)对中国战后各种事业愿予最大协助,如投资及借用技术人才等。以上消息来源可靠,足资参考。所云法方希望我方三点或为美国所注意,或与我国策不甚符合,似
宜从长计议。惟法于战后国际地位相当重要,我在适当范围内似亦宜积极联络。(注:《顾维钧报告法解放会外交当局对中法悬案交涉的立场致外交部电稿》,1944年8月2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汇编》第5辑第2编,外交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50-651页。)
法国考虑到自身地位尚未完全恢复,而且在战时与日合作的行为的确有负于中国,因此,在改善对华关系方面,采取主动示好的低姿态。这无疑令备遭美英冷落的中国感到一丝满足。其中“为应付将来和会困难,先事商定某种原则下互相协助,互通消息,以防三强任意操纵”一条所透露出的欲与中国合作的讯息,尤令中国领导人印象深刻,从中看到了中法联手抗衡英美的前景。于是,正当蒋介石与史迪威关系急剧恶化之时,中法关系出现戏剧性转机。(注:凌其瀚:《我的外交官生涯》,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88-96页;Xiaoyuan liu,前引文,第466-467页。)10月10日,蒋介石接见法国临时政府代表贝志高,在强调中法政治、经济联系的重要意义时,蒋着重指出:“法国人的思想比盎格鲁撒克逊人(不管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更接近中国人”;关于印度支那问题,蒋主动表示:“我要再一次向您肯定,不论对于印度支那或者印度支那的领土,我们都没有任何企图。在这个问题上,我的主张是坚定不移的。如果我们能够帮助贵国在该殖民地建立法国政权,我们是乐意的。请您亲自把我这个意愿正式转达给戴高乐将军。”(注:《驻中国大使贝契柯夫将军致巴黎政府电》,1944年10月11日,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下册,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第336-337页。)
10月23日,中国与美、英、苏同时宣布承认法国临时政府。中国官方舆论对同为盟国中弱国的法国的“成长与强大”盛赞空前:“独立强大的法国之复起,是欧洲的和平保障所需要的,也是世界的和平保障所不可少的,正同为了亚洲的安全与世界的和平必须有一个独立强大的中国一样。”《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欢迎新任驻华大使贝志高,并表示中国愿与行将东来的法军并肩作战,希望中法能以“互助合作的精神”处理两国在远东“相交错”的权益。(注:《法国临时政府的成长》、《法比两使呈递国书》、《迎贝志高大使》,《中央日报》1944年10月24日、1945年1月10日、1944年12月19日。)12月15日,外交部长宋子文致函戴高乐,表示中国“准备以最诚恳的态度解决中国和法国间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注:《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先生致巴黎戴高乐将军函》,1944年12月15日,转引自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下册第397页。)为回报中国的友谊,1945年1月10日,法国临时政府总统戴高乐向蒋介石赠送荣光大勋章(注:《法比两国大使呈递国书,戴高乐赠蒋主席荣光大勋章》,《中央日报》1945年1月10日。此项勋章为法国总统赠与友邦元首的最高荣誉勋章。)。12日,中法科学合作委员会正式成立。
雅尔塔会议的召开令急剧升温的中法关系渐渐冷却下来。此前,中国之所以积极改善对法关系,本欲在未来国际和平会议上与法联合,以张声势。而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公然将中法排除在外,商议决定与中法两国利害密切相关的对日、对德作战问题。这一游戏规则表明,作为盟国中的弱国,即使联合起来也无法与三强抗衡,因为后者可以随时决定将前者开除出局。格于强权政治的现实,中国将对越政策由与法交涉调整为与美国商讨。外交部长宋子文拟具解决中法间各悬案之方针,提请蒋介石签呈时,着意强调“越南问题与美国关系甚大,比次赫尔利大使回国已与商洽探询美国对越南之政策。以上所拟各方案拟俟查明美方政策后再厅与法进行谈判”(注:宋子文:“解决中法间各悬案之方案”,1945年2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61-184。)。
由于微闻美苏关于中国东北问题达成协议,中国处理对越交涉时还多了一层担忧,即担心苏联日后依照中国对法越的交涉办法来处置战后东北问题,军委会参事室在讨论外交部提案时指出:关于中越通运问题,“对于我国在对法越交涉中自属有利,但将来苏联是否将依照此种办法,对我要求通过东北数省之各种运输便利,并免纳税捐。此点似应于事前考虑计之,以免有顾此失彼之虞。”(注:张忠绂:“对外交部解决中法悬案的意见”,1945年3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61-184。)
从“积极扶植越南革命同盟会”到谋求国际托治
1945年3月9日,日军对法印当局发动突然袭击,接管法国在越殖民统治。这一突发事件一度改变了中国在越南问题上的被动地位。考虑到此时盟军很可能入越驱逐日寇,而法军又尚未东来,实为中国扶植越南独立千载一时之良机。14日,蒋介石电令(“寒电”)实际从事对越工作的相关部门,“对法越务须维护盟友并肩作战之关系,表面上予以极友好之印象,而实际上积极扶植越南革命同盟会,务使其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准备于盟军驱除倭寇出境时宣布独立,成立新政权。”(注:“越南政治占领计划”,1945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83-316。)
然而,时局之发展并未如蒋所预期。与中方“伸出热烈的双手来迎接从西方东渡的法军”态度相比,美国总统罗斯福坚持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不与戴高乐发生联系,美国暂时亦无意更改其既定作战计划。(注: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French Ambassador(Bonnet),April 4,20,1945,FRUS,1945,vol.Ⅵ,pp.303,306.)1945年4月,罗斯福的去世使得美国对越政策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提醒蒋介石:罗斯福总统的印度支那政策可能为新总统所修改,但这一问题不宜此时在华府提出,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注:《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听其报告杜鲁门总统仍命其任驻华大使及其离华数日之经过情形谈话记录》,1945年4月2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214页。)6月初,美国政府向赫尔利下发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指令,否认其对越政策有根本性转变,明确表示关于属地的托管问题,赞成由雅尔塔会议所确定的自愿原则。由于法国似不可能赞成托治,杜鲁门总统打算向法国政府提议保证印度支那人民得到更大程度的自由和自治。(注:Grew to Hurly,7 June 1945,Top Secret General Records of Chungking Embassy,China,1945,Box 1.)这一态度反映了美国处理战后英、法、荷等国在亚洲殖民地政策的两重性,一方面,它主张“让这些殖民地的人民得到更大程度的自治”,而在“远东逐步发展成一群自治国家——独立国或自治领”,以便美国势力渗入这些殖民地;另一方面,它又要“避免会严重损害主要联合国家[美国和英、法等国]的团结的任何行动”。(注:Policy Paper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22,1945,FRUS,1945,vol.Ⅵ,p.558.)
明了美国有意对法让步后,蒋介石对越南独立运动的援助转趋消极。6月25日,在接见前来请援的越南国民党代表团时,蒋表示:“中国对于越南当然要援助,不过国际形势复杂,法国之地位现在尚未解决,故续与英美研究,美国一定愿意看到越南的独立与自主”,并以“须与美国详细研究”为借口拒绝越南方面接济武器的请求。(注:“蒋介石接见越南国民党代表团谈话纪要”,1945年6月25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未刊原件。)
见中国方面迟迟无意开始谈判,法方于中国抗战8周年纪念之际,竭力铺张,试图博取中国好感。(注:参见《七七在巴黎》,《中央日报》1945年7月16日。)同时,由法国朝野名流及文化界人士发起组织的“中法协会”在巴黎正式宣告成立(注:《“中法协会”七七巴黎成立》,《中央日报》1945年7月10日。)。中国驻巴黎大使钱泰在给外交部的电报中称:“法方极愿在友好空气中,第一步交换广州湾,然后交换租界,缔结新约,凡此均出自法方自愿,但望我方勿冷漠相待”。钱泰认为“在未来世界均势中倘能与法休战、携手,颇可运用以张声势”。(注:“钱泰致外交部电”,1945年7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8-2077。)8月18日,中法签订了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将交还期提前50年。(注:《法国交还广州湾》,《大公报》(重庆)1945年8月19日。)
由于美国对越政策尚未尘埃落定,中国对法方的主动示好,仍持观望态度。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提前宣明其对越南问题的态度。因为据盟军统帅部“第一号命令”,中国军队即将开入北纬16度以北的越南境内执行受降任务。8月24日,蒋介石出席国防最高委员会议与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宣明:“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已战败而无条件投降,台湾、澎湖,仍归还到祖国的怀抱,东三省领土的恢复和主权行政的完整,亦获得了保证;高丽不久亦必能得到其独立与自由。我们国家的独立,也由此树立了坚实的基础。于是我们民族主义对外一方面的目的已达到了完整的阶段”,“为了世界和平与安全,为了国家巩固与建设,我们对于全世界民族问题的主张,必须依据大西洋宪章与三民主义的精神来求得解决。至此,我对于我们中国西南边疆上的几个民族问题,也是以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关系,不能不表示我们的愿望”,“中国在抗战期间,因安南政府不能自保其主权,并供日本以侵华基地,因之中国的生命财产皆受巨大的损失。但是我们今日除了恪守同盟国的约定,派遣军队接收北纬16度以北地区日军的投降之外,对于越南没有领土的企图。我们的希望是越南民族能从自治以渐臻于独立,以实现大西洋宪章的规定。”(注:《蒋主席重要宣示》,《中央日报》1945年8月25日。)细察蒋之声明,不难看出中国政府对越政策的取向,其一,中央决策层对越问题的关注已非基于民族主义立场,而是出于对世界和平与安全、国家巩固与建设的关注;其二,不主张越南即时独立,独立应为越南的远期目标,目前尚处于自治的阶段。“从自治以渐臻于独立”的方式可有多种,可由中美联合托治,亦可由法国放宽自治限度,允诺越南独立。蒋之声明实为美国对越政策尘埃落定后,中国对越政策的调整预留了转圜空间。但因其声明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致使党政军诸机构在具体处理越南问题时普遍感到“未有明确详密之对策可资遵循”,只好根据各自的理解及其工作范围自行其是(详见后文)。
波茨坦会议后,美国意识到在德国问题上将同苏联有严重的斗争,因此有必要重新调整同法国的关系,缓和相互间的矛盾。(注:《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25页。)于是,杜鲁门邀请戴高乐访问美国。据戴高乐回忆,在8月22日至25日举行的法美华盛顿会谈中,杜鲁门表示,无论如何,美国政府不反对法国军队和法国当局回到印度支那去。(注: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上册,第228-229页。)29日,在美访问的宋美龄向杜鲁门询问美国对越政策。杜鲁门称:他对法国为越南独立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当宋提及罗斯福倡导的托治计划时,杜鲁门表示:据他所知,美国政府从未讨论过在印度支那实施托治。(注: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Aug.29,1945,FRUS,1945,vol.Ⅶ,pp.540-541.)
得知美方准备放弃托治计划,9月19日,蒋介石致电正在伦敦出席五国外长会议的外交部长王世杰,要王设法与美苏交涉,使其恢复托治主张。王向美国务卿贝尔纳斯表示,中国对越政策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将印度支那置于国际托管下;二是法国公开保证10年内允许印度支那独立。贝尔纳斯拒绝中方建议,表示美国只愿使法国采取一种较开明的政策,加速印度支那走向自治的过程。事后,王世杰报告蒋称:“中法谈判宜从速进行”。(注:“蒋介石致王世杰电”,1945年9月19日;“王世杰致蒋介石电”,1945年9月22日。均见Koo papers,Box 57。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577-578页。)同日,法国外交部长与王世杰商谈越南问题,要求中国允其留滇军队入越。王表示可向政府请示,但同时声称中国希望法国对于越南之政治前途能做若干保证。(注:《王世杰日记》(1945年9月19日)第5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178页。)
标签:中国法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自由法国论文; 民族独立论文; 法国殖民地论文; 越南民族论文; 蒋介石论文; 殖民地历史论文; 中央日报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