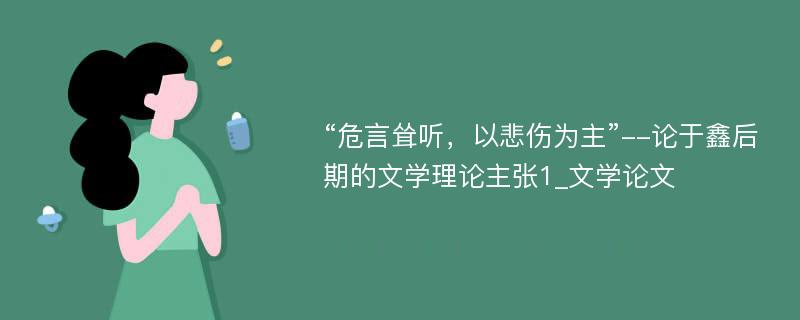
“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试论庾信后期的文学理论主张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试论论文,后期论文,之辞论文,悲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庾信后期集南北之大成的文学成就,为古今研究者所公认。他在文学理论方面有无建树呢?似乎很少有人提及。笔者认为,庾信后期取得较大文学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有着较为明确的文学理论主张的指导。由于庾信的文学理论主张散见于一些作品的序和与他人酬答的文章中,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略。这种忽略,不但影响了对庾信文学理论主张的评价,也影响了对庾信文学创作价值的深度挖掘。本文试陈管见,期望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庾信《哀江南赋》序中说,他写作《哀江南赋》“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并且坚持说,为了充分表达他这种属于“穷者”和“劳者”的“危苦”“悲哀”,即便遭到象陆机、张衡这样的大方之家讥嘲,也心甘情愿。换 句话说就是:为了表达自身情感的需要,不在乎与传统审美习惯与理论形成对立。这就提出了让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庾信“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的情感表达方式,会与传统的审美习惯及理论相悖?既然明知相悖,为什么还要予以坚持?
庾信“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的说法,来自嵇康《琴赋》序:“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嵇康的用意在于反思魏晋时代普遍存在的以悲为主、以悲为美的时代审美偏向,要求超越停留在官能愉悦享受层次的审美方式,以追求纯粹的中和之美。表面看来,庾信的说法好象是与嵇康唱反调了。其实,庾信与嵇康主张追求纯粹中和之美固然不同,也与魏晋南朝以来以悲为美的创作理论有质的不同。下文就此展开讨论。
在《赵国公集序》中,庾信恭维赵国公宇文招“斟酌《雅》《颂》,谐和律吕”,并以屈、宋以来的整个文学发展、演变历史作他的对立面:
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苏武、李陵,生于别离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雕虫篆刻,其体三变。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抢荆山之玉矣。
这似乎是对屈、宋以来的文学传统均作否定性的评判了。但我们从他特意拈出屈、宋之“始于哀怨之深”,苏、李之“生于别离之世”,不难发现,屈宋苏李的文学创作方式,与庾信《哀江南赋》序所追求的“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如出一辙。可知他称赞宇文招是《诗经》文学传统的传人,只是冠冕堂皇的应酬话,值得关注的倒应是他回顾、总结文学发展、演变历史的独特眼光。庾信对文学创作传统的回顾总结受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的很大影响。但沈约对文学传统的认识有两个明显指向:一是认为后世文学虽然“因祖风骚”,但“赏好异情”,所以“意制相诡”,其发展、演变呈现出多元化态势。沈约由此而提出著名的“三变”说:
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
沈约认为,自汉至魏四百余年间,有从司马相如到班固,从班固到曹植、王粲的“文体三变”,并肯定这种“赏好异情”的“意制相诡”。二是作为“永明体”文学理论的代言人,沈约侧重于对中国文学的音韵化发展道路予以总结,因而更关注对文学表现形式发展、演变趋势的考察。庾信则认为,自屈宋以来,文学的发展、演变存在前、后两大截然不同的创作阶段。前期是以屈宋苏李为代表的“哀怨”文学,后期是“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其体三变”的“雕虫篆刻”文学。对前一种文学创作的认识,庾信明显融进了自己的身世感受;对后一种文学创作,庾信则虽借用沈约“三变”说,却将时限由“自汉至魏四百余年”推后到恰好从沈约“三变”时间的末尾开始,包容了“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迄于庾信所处的时代,并对“三变”作出了“雕虫篆刻”的否定性评判。从庾信关注、认同屈宋苏李的文学创作,避而不提自汉至魏的“文体三变”,却贬斥“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的“其体三变”,我们可以了解,庾信后期对文学创作的主张主要有两大方面的内容。
第一,肯定文学创作内容对于形式表现的决定作用,要求创作主体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而不能本末倒置,以末为本。在肯定文学创作内容的决定性作用时,庾信特别强调了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创作主体深度的情感体验是深度的文学创作的前提条件。他标举屈、宋,认为他们文学创作的成功始于他们生活的“哀怨之深”。二是强调创作主体与其所处时代的紧密联系。他认同苏、李的文学创作,认为苏、李处于“离乱”的时代,而能充分把握时代的“离乱”特征,所以取得成就。这实际是说,创作主体不能自外于时代大潮,只有正视与时代、社会的有机联系,直面现实社会人生,深入到时代与社会的重心之中,把握和表现时代精神,才能有深度的文学创作。屈宋与苏李正是由于有了深切的生命体验与强烈的创作冲动,充分把握了“离乱”时代的“哀怨”特征,他们的文学创作才有深广的内涵和震撼人心的力量。显然,庾信这种认为先有生活与情感,后有创作,文学内容决定创作形式的文学理论主张是符合“为情而造文”的文学创作规律的。在《哀江南赋》序中,庾信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这样的文学观念。序中总结桓潭、杜预(按:二人为学者,非文学家)、潘岳、陆机等一些文学名家的成功之道说:
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
桓潭、杜预的“著书”“自序”,是出于人生“志事”这样强烈的生命冲动;潘岳、陆机的才华,用于表达对“家风”、“世德”无比崇敬、自豪的深厚感情。就庾信自己而言,“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梁亡使门阀士族群体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也使附丽于群体之中的生命个体必然处于“离乱”之世。序文追述庾信自己的悲惨人生遭际:“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却始终无法找到解脱的途径:“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飙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亡国之痛与仕敌之耻的交织,使他“《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当生命本身成为悲剧的化身,多种排遣方式都无以消解这深重的悲怨之情时,创作主体唯有借文学之助,来达“穷者”之“言”,歌“劳者”之“事”,文学创作遂成为生命的一种迫切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主体不可能无视自己与时代的密切联系。把握和反映时代精神,也就成为创作主体的强烈呼声和自觉行动。序文特意提出:“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哀王室”与“悲身世”——表现群体生命与个体生命悲剧命运,正是庾信后期文学创作的自觉追求。为了能充分表达这种“哀王室”“悲身世”的强烈思想感情,当固有的艺术表现形式不再适宜于这种新的情感表现时,序中申明,只要能达“穷者”之“言”,歌“劳者”之“事”,即使“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可见,庾信为了达情的迫切需要,以至于渴求突破旧的审美习惯与理论的束缚,不再对形式的雕琢作过多的关注了。
从这样的文学观念出发,庾信对“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的文学创作给以“雕虫篆刻,其体三变”的否定性评判。“雕虫篆刻”语出扬雄《法言·吾子》。扬雄认为汉代的辞赋创作是孩童的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到了梁代,裴子野专门作了《雕虫论》,对东晋南朝至梁以来,忽弃情感内容表现,“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这种追求形式表现的唯美主义创作倾向进行了理性批判。庾信虽没有确指“三变”究竟是哪“三变”,但从“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这一笼统的时间界定来看,所指与裴子野当相差不多。值得注意的是,从建安之末到晋太康时代,从太康、南朝至梁,正是门阀士族价值观念系统趋于形成并得到强化的时代。在门阀士族文化价值观念指导下,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走上了忽视文学创作内容而重视形式表现的道路。从西晋太康作家的专重结构主义,到刘宋元嘉作家的“极貌以写物”、“穷力以追新”,从萧齐永明作家的音律主义到萧梁的“宫体”作家偏嗜描摹女性之美,虽繁复多变,求新逐异,“情”淡而“采”浓,“气”浮而“骨”弱,却是其共同的表现特征。西晋迄梁政局动荡无已、政权更迭频仍,门阀士族知识分子却大都回避自身与时代的关系,普遍忽群体而重个体,他们生活圈子狭窄,生命意志脆弱,脱离实际生活而寄浮于现实生活的表层,每每以旁观者的身份看待宇宙自然与社会人生。这种“为文而造情”的文学创作方式与屈宋苏李相比,确乎存在深而广与浅而窄的明显差别。作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庾信前期的文学创作也是在这种“为文而造情”的文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应该说,是悲剧人生使他后期文学创作观念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根本性变化使他矫正了将文学创作内容与形式本末颠倒,以末为本的创作方式,而自觉认同屈宋苏李的创作传统,着力于对“离乱”时代本质特征的把握和对“哀怨”之情的深度挖掘,从而使后期文学创作取得巨大成就。
第二、突出强调文学创作以悲为主的重要价值意义,“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成为他后期文学创作的理论宣言。
(一),从强调创作主体与时代社会的密切联系出发,庾信要求把握和表现时代精神。庾信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离怨”之情的“离乱”时代,因此表现“离乱”时代门阀士族群体生命与个体生命的“悲怨”之情,成为时代审美新变的核心内容。庾信敏锐把握了这一时代审美新变的内容,而强调文学创作应以表现这种审美新变为主。庾信“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的主张与魏晋南朝迄于梁代普遍流行的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有着质的不同。即以梁代而论,“宫体”文学的理论家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就认为,宫体诗有“微蠲愁疾”的功用。但是这种疾愁应是轻微的,是门阀士族知识分子充分愉悦人生、追求感官愉悦享受时的一缕淡淡的如云似烟、令赏鉴者心旷神怡的“愁疾”。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界定“文”的标准是:“吟咏风谣,流连哀思之谓文”。但从他同篇中对“文”的补充说明“至如文者,惟须绮毂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来看,“情灵摇荡”之中既有对若有若无、不绝如缕的“哀思”的流连,更有由对美的形式表现之“绮毂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的高度欣赏所引起的“情灵摇荡”。所谓“哀思”,只是“为文而造情”的附生物。因此,庾信的以悲为美是要求将时代的“悲怨”之情与创作主体自身生命的悲怨哀愁转化为艺术美,魏晋南朝迄梁的以悲为美,则强调调动艺术想象,从知识技巧进入文学创作,以追求感官愉悦享受为其审美目的,审美目的不同,审美效果必然迥异。
(二)梁亡使庾信等门阀士族知识分子遭受了国破家亡、被迫由南入北而屈仕北朝的人生苦难。从更深层次看,庾信等的这种痛苦是南朝门阀士族文化价值观念系统与北朝文化价值观念系统冲突碰撞的产物,它给庾信的文学创作也带来直接的影响,使他前期在门阀士族价值观念系统指导下形成的创作思维方式和心理图式,随着门阀士族价值系统的坍塌而遭到破坏。这样,后期“情纷纠以繁会,意杂集以无端”②的丰富人生体验与两大文化价值系统碰撞所产生的巨大矛盾痛苦很难运用旧有的艺术表现形式予以淋漓尽致的表现。新的创作内容需要新的艺术表现方式,这就意味着创作主体必须形成新的创作思维方式与心理图式。可见,庾信后期的文学创作实际面临着“转型”。庾信以艺术家的敏锐与直觉,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新的情感内容的表现,而不惜与旧的创作传统、审美习惯对立,就是庾信要求变革旧有思维方式与心理图式的宣言。
从审美视角看,庾信前后期的创作思维方式与心理图式有着质的不同。前期与沈约、徐陵、梁元帝同调,合于西晋南朝文化精神与审美习惯。这种创作思维方式与心理图式虽也承认并欣赏以悲为美,但从根本上说它追求宁静和谐的艺术境界,仍不出悦乐为美的范围,乏“力”重“采”是其重要特征。后期则欣赏悲怨沉郁而不流于浮浅的审美感受与经验,以冲突、失衡的心理、情感世界为主要表现对象,执着追求展现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矛盾与冲突,歌“劳者”之“事”,达“穷者”之“言”。因此,庾信虽从《雕虫论》受到启发,但他并不象裴子野那样维护儒家审美和谐论,而是刻意突破儒家的审美和谐论,着力表现冲突与对立之美,这意味着要求对乏“力”重“采”的文学创作输入震撼人心的力量,改变“宫体”文学浅层次的情感渲泄和旁观的欣赏愉悦特征。庾信因此而自觉认同苏李屈宋的悲怨文学传统,否定西晋南朝迄梁的乐感文学创作方式。
(三)庾信的人生悲剧使他后期的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认为世界的存在是无目的性的,没有什么天道公理可言,世界的秩序也充满着混乱与冲突。③因此,人生从本质意义上来说是以悲为主的,悲剧是主宰生命的根本存在方式,生命悲剧的普泛性、永恒性诸特征,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他在《思旧铭》中就认为,“人之戚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宁有春秋之异”。当人生的各种悲剧接踵而来时,生命个体“无假穷秋”,“于时悲矣”!《伤心赋》认为这种普遍的人生悲剧与文学创作有着深刻的联系:“婕妤有自伤之赋,扬雄有哀祭之文,王正长有东郭之悲,谢安石有东山之恨;斯既然矣。至若曹子建、王仲宣、傅长虞、应德琏、刘韬之母,任延之亲,书翰伤心,文辞哀痛,千悲万恨,何可胜言。”就庾信自己而言,后期的悲剧人生经历使他如《伤往·其一》所说:“见月常垂泪,花开定敛眉”,形成一种恒定的审美思维和情感价值取向。庾信因此而强调文学创作应该充分发掘这种悲怨之情的美学价值,要求排除那种以娱乐为审美目的的浮浅轻清的审美情感,进而主张将欢乐之情逐出文学的表现园地,而“惟以悲哀为主”。显然,这种认识有对屈宋苏李文学创作传统的认同,也有对司马迁发愤为文说与刘勰“志思蓄愤”说的自觉承继。同时,强调以悲为主也不无矫枉过正的倾向,矫枉过正的类似情形,我们在中外文艺理论中都不难找到例证,如傅山的以丑为美、西人波德莱尔对“恶之花”的欣赏、日人厨川白村“文学是人生苦闷的象征”说等。
(四)要求借文学创作进行深度的文化反思。庾信《哀江南赋》将自己与司马迁的身世经历相提并论:“信生世等于龙门,辞亲同于河洛;奉立身之遗训,受成书之顾托。”这说明庾信强调作家对时代历史文化所担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认为自己负有总结梁朝兴亡的历史责任。从《哀江南赋》序看,这种文化反思的核心内容指向“身世”之“悲”与“王室”之“哀”,也就是对门阀士族群体生命与个体生命悲剧命运的反思。他的《哀江南赋》正是为梁亡的“江南”之“哀”而作,而他对“江南”之“哀”的溯源正好从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晋室南迁开始,故这种反思实际涵盖了整个门阀士族兴衰时代的历史。因此不仅可以视为对梁代兴亡的反思,也可视为对西晋南朝以来门阀士族历史兴衰的反思。《哀江南赋》序思考: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纵缔交;锄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之王气,终于三百年乎?
庾信因此而自觉探讨梁代兴亡的根本原因,提出了“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的著名结论,对梁代以至西晋南朝偏激的文化至上,重文轻武,轻忽实际生活的弊端进行深刻剖析,并予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同时,庾信明确表示要为“穷者”达“言”、为“劳者”歌“事”。这实际是要通过对个体生命悲剧的艺术表现,来探究个体生命的悲剧根源。“怨恨之至,遂识事物之真”。庾信对自我和门阀士族个体生命心灵痛史的展示,不仅艺术再现了门阀士族个体生命的苦难灵魂,也使他成为门阀士族个体生命灵魂的审问者。可见,庾信不仅强调对悲怨情感的挖掘和拓展,同时也崇尚理性主义的艺术表现。正是在这种思想认识指导下,庾信的文学创作才具有了对历史文化的强烈反思意味。
综上可见,庾信后期确乎有着较为明确、系统的言“悲”文学理论主张。在这种言“悲”文学理论主张指导下,庾信才自觉建构了有较完整系统的言“悲”文学大厦。他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与表现,对群体生命与个体生命悲剧的认识与反思,对悲怨情感的深度表现与挖掘,使他登上了时代文学的峰巅。倘没有较明确、系统的文学理论主张或思想的指导,这种成功是难以想象的。同时,庾信这种言“悲”文学主张也是时代审美新变的必然产物,它明显不同于沈约、徐陵、梁元帝诸人的文学理论主张,而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对他这种言“悲”文学理论主张的价值意义,从古至今的研究家尚缺乏足够的重视。笔者认为这种忽视是不应该的,因为它不但妨碍了对庾信文学理论主张之价值意义的评价,也妨碍了对庾信后期文学创作价值的深度挖掘与科学评价。
最后,还需要提出的是,庾信后期也多次谈到对儒家诗教原则的认同问题。笔者认为,这一现象有较为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不管怎么说,庾信“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的文学理论主张,明显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教原则,无疑是指导他后期言“悲”文学创作的最主要方面,因此,笔者不能同意将他的言“悲”文学理论主张与儒家诗教原则混而不分或使二者平分秋色的做法。④限于篇幅,对儒家诗教与庾信文学创作的关系,以及庾信文学理论主张与颜之推文学理论主张的异同等问题,⑤只有另文详论了。
注释:
①本文为笔者庾信研究专著《庾信十论》(即将出版)中论述庾信文学理论一章的部分内容。
②见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三十三。
③参看拙作《走向文化反思的逻辑起点——从庾信看由南入北文士的文化幻灭感》(《西北师大学报》94、1期)
④参看钟优民《庾信文学思想初探》(《社会科学战线》86、4期)
⑤参看拙作《关于〈论魏晋六朝作家“文心”与“人心”的分裂〉一文若干错误的订正》(《西北师大学报》专辑91、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