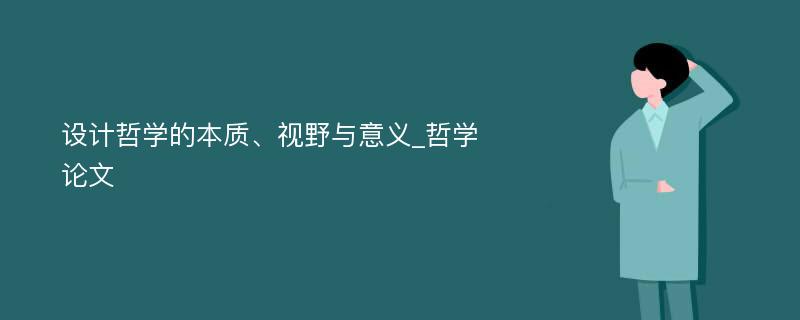
设计哲学的性质、视野和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野论文,性质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0)06-0072-08
关于设计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以及建立“设计哲学”的可能性和意义,约十年前笔者曾有专文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①。近年来,尽管工程哲学等个别相关领域由于工程界和哲学界的共同推动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②,但是,关于设计哲学的根本意义,设计哲学在整个哲学体系中的地位,设计哲学与其他哲学领域和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设计哲学在当代知识和文化体系重构中的作用,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仍然是哲学本身在观念上的迟滞和视野上的封闭妨碍了我们对这一领域的探索。因此,本文重点探索传统哲学的弊端和缺陷是如何导致对“设计”或“创制”这一重要哲学主题和领域的漠视或遮蔽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设计哲学的当代视野和意义。
一、设计与设计哲学
到底什么是设计?为什么要提出和建立设计哲学?设计和设计哲学在人类最基本的范畴和思想体系中占有什么地位?设计哲学与其他哲学主题或领域的关系如何?笔者在题为“‘设计哲学’的可能性和意义”的论文中对此已经作了基本的界定。
尽管在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后,设计在工业制造和工业设计,以及一般的人类活动中的根本地位和作用才得以逐渐显现,但是,从一般的意义上说,设计与认识一样,也是人的基本技能、品质和活动之一。
设计产生于人类发现和创造有意义的生存方式、生存手段和生活秩序的需要,是人基于生存和生活的需要而对事物在观念上和实际地加以构造和组织的过程。设计的根基在劳动、生产之中,但是,设计并不局限于物品的设计或工业产品设计,而是人类生命存在和社会文化活动中的基本方面。
狭义地说,设计是一个与造物和技艺直接相关的概念,但是,从今天的技术和生产方式来说,即使在简单的造物的意义上,设计也包含着技术、工艺、美学、伦理学、文化学、价值学等多方面的内涵,是联系工业与自然、技术与艺术的桥梁。从广义上说,设计是贯通能动性、创造性、目的、计划、价值和理想等概念的重要哲学范畴。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设计的本质就是创造,广义的设计是基于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对一切事物,包括物的结构和功用、人类的生存和生态环境,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以及民族和社会的文化形象、文化理念进行改变和创造的过程及其机制,是改变“事”和“物”的结构、状态使之合乎人的需要和愿望的美和自由的状态。
设计像求知一样,也是人的天性和内在的需要。从人类的活动领域来说,“创制”或设计是与认识、伦理或政治活动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哲学是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思想活动和知识体系,关于设计和创制的哲学,理应具有与认识论和伦理哲学同等重要的地位。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应该是由认识论、道德哲学与设计哲学共同组成的。从其独特和内在的规定性上说,设计是一种区别于认识探索和价值判断的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活动。如果说认识上的探索侧重或追求客观和“真”,价值判断或伦理和政治意义上的“实践智慧”追求“善”,是一定社会历史时期内特定社会制度和规范的合理性和公正性,那么,广义的设计活动则是要构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方案和模式,既包括物质方面的方案,也包括社会制度以及精神生活上的方案。设计活动的最高状态和境界,就是自由,就是美,就是对无数可能性的权衡与选择,是对新的生活状态和模式的创造。
设计或创造的活动固然要以认识的客观性为前提,也必须遵循社会的规范,展现为社会交往的过程,但是,设计与纯粹的认识活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又有明显的区别。认识以客观地反映和符合客观世界,以真理为目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以伦理和政治上的明智和善为准则;而设计则需要尽可能地发挥人的主体性、创造性,按照人对理想生活状态的追求而实际、有效地改变事物的结构、状态和属性,功能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形式或艺术上的美、和谐的生活空间和环境、公正而有效率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丰富而生动的文化氛围,是广泛的设计活动的追求。从人类活动的完整的过程和内在的合理性来说,设计或设计学或许是把认识论和伦理学与人的现实生活过程联系起来的主要渠道,实际上,纯粹的认识或“凝神观照”以及纯粹的伦理(即康德式的“绝对命令”)都是不存在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认识论和伦理学的规定性最后也只有在设计的过程和设计学中,在与人类实际的生活的联系中,在实际生活的功用中才能得到说明和确证。
同时,在一定的意义上又可以说,设计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以认识论和道德哲学的先在为前提的。或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传统的哲学更关注或集中于这两个方面。同样,我们也由此可以推断,只有在相对晚出的设计和创制的哲学中,传统哲学的诸多二分式的分立,如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自由与必然、形式与功能、科技与人文、艺术与技术等等,才能得到现实的统一。在设计哲学中,哲学将实现自己完整的存在;也只有在设计哲学、道德哲学和认识论的统一中,当代知识和文化的诸多形态和要素才能摆脱分裂的状态,达到合理的沟通和联系。设计哲学的提出和发展,符合哲学自身的逻辑,也是当代文化重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哲学的基本主题、领域以及传统哲学的弊端
设计,毋庸讳言,是哲学中一个被长期忽视和遮蔽的主题。对设计的漠视,是传统哲学的弊端和缺陷之一。关于设计哲学的探讨,一方面需要我们立足于当代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实践,感悟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需要我们重新探索哲学的主题和应有的视野,在合理的哲学视阈之中界定设计哲学在总体哲学中的地位及其与其他哲学主题和领域的关系。对哲学主题和领域的一般探讨,对我们今天厘清人类知识和文化的脉络,克服知识和文化领域中的诸多片面性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曾经从人性,从“理性灵魂”的内在规定性来分析和探索人类的活动。他认为,人类的理性灵魂可分为两个部分,即以不变事物为对象的认知部分和以可变事物为对象的核计部分。以不变事物为对象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或以外部实在为对象的认识。核计,就是“有所为的理智”,可以进一步分为明智或实践(“明智—实践”)与制作或技艺两个方面。这样,人的活动一般地说不外乎三种:认识、实践行动、制作(“创制”),与此相关的“真理”或知识、理性的能力和品质也可相应划分为相关的三个方面,即理论、明智和技艺。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与制作(或创制)的区别,对于澄清我们在把握人类活动的结构及其内在的关系时所发生的混乱,对于把握人类的知识和活动的结构以及哲学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技术(艺术)或“技艺”是“制作品质”的表现,而“实践品质”的表现是“明智”、善恶。“明智”或“实践品质”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而技艺则来自人的创造。
亚里士多德说:“可变化的事物中包括被制作的事物和被实践的事物。但是制作不同于实践,实践的逻各斯的品质同制作的逻各斯的品质不同。其次,它们也不互相包含。实践不是一种制作,制作也不是一种实践。例如,建筑术是一种技艺,是一种与制作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品质。如果没有与制作相关的品质,就没有技艺;如果没有技艺,也就没有这种品质。所以,技艺和与真实的制作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品质是一回事。所有的技艺都使某种事物生成。学习一种技艺就是学习使一种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的事物生成的方法。技艺的有效原因在于制作者而不是被制作物。因为,技艺同存在的事物,同必然要生成的事物,以及同出于自然而生成的事物无关,这些事物的始因在它们自身之中。如果制作与实践是不同的,并且技艺是同制作相关的,那么技艺就不与实践相关。在某种意义上,技艺与运气是相关于同样一些事物的。”③ 这里,亚里士多德不仅清晰地界定了“实践”与“制作”的关系,也非常清晰地说明了“制作”与“认识”的区别。“认识”作为以不变的外在事物为对象的过程是以事物的不变性、外在性和客观性为最基本的前提和规定的,而“制作”或设计则更多的是制作者的主动的创造过程,服从于制作者或设计者的内在需要、主体性和创造性,因而也就具有功用性、多样性和选择性的特点。
从西方思想史的发展来看,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活动的分类,与康德的“三大批判”是有对应性的,这表明了哲学在主题、方法和观念上的稳定性和普遍性。但是,在这一比较中,我们也会发现西方哲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越来越走向抽象和思辨而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逐渐失去了希腊时代的感性的丰富性。朱光潜指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活动”指城邦公民所应尽的职责,也就是伦理和政治方面的活动。至于“创造”(或“制作”)则是艺术活动,这里“艺术”包括一切人工制作在内,不专指我们所了解的艺术④。康德的“第一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对应于亚里士多德昕说的认识或理论观照;《实践理性批判》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对应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或“明智”,但是,康德的“绝对命令”体系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相比显然要抽象和思辨得多,无视伦理规范的感性的生活基础,也不再把政治活动包括其中;《判断力批判》中探讨的“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更是无法包容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制作”和技艺。甚至最具历史感的黑格尔,在其美学中,也把人类真实而普遍的“创制品质”和“技艺”抛诸脑后。
实际上,康德和黑格尔对创制活动的漠视是西方理智主义传统的产物,这种传统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创制或制作活动的忽视在希腊哲学中就已发端。亚里士多德尽管看到了“创制”(或“技艺”)与认识、实践或明智的区别,但是,他对“创制”也持歧视的态度。造成这种片面性的原因,主要是社会历史本身(首先是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古代哲学和文化的经济技术背景和基础是自然经济。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更多地受制于自然过程,如农业生产,更多地受自然气候和时令的限制。在那种生产条件下,人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十分有限,生产活动以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的社会地位无疑也是最低的。因此,这类社会活动以及从事这类社会活动的人,在文化中,包括在哲学中,得不到应有的反映和重视,更不可能成为哲学反思的对象和主题。
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科学知识和“明智”生活或道德—实践知识具有优先地位,而“包括打散工、务农和手工劳动的生活以及家庭里的奴隶劳动和生儿育女在内的生产劳动”往往被排除在哲学视野之外,最多也只是被看做维持自由民(公民)的生活享受和国家存在的“手段”,是由“必然性”构成的领域⑤。希腊哲学和文化中目的和手段、自由和必然的分离以及哲学体系中对人的不同活动的态度上的区别,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中自由民(公民)与奴隶和平民的阶级区别和对立。
轻视生产劳动和技术或制作,抬高认识或理论的文化地位,必然牺牲哲学的感性基础,导致哲学思辨化和道德化。或许这就是古希腊所谓“诗与哲学之争”发生的原因和背景,也是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以哲学(或认识和理论)吞并艺术,以先验的伦理德性否定现实幸福的根本原因。朱光潜曾指出:“我们须记起希腊人所了解的‘艺术’(tekhne)和我们所了解的‘艺术’不同。凡是可凭专门知识来学会的工作都叫做‘艺术’,音乐,雕塑,图画,诗歌之类是‘艺术’,手工业,农业,医药,骑射,烹调之类也还是‘艺术’,我们只把‘艺术’限于前一类事物,至于后一类事物我们则把它们叫做‘手艺’,‘技艺’或‘技巧’。希腊人却不做这种区别。这个历史事实说明了希腊人离艺术起源时代不远,还见出所谓‘美的艺术’和‘应用艺术’或手工艺的密切关系。”⑥ 但是,对生产劳动以及其他创制活动,包括对从事这类活动的人的歧视,最终导致艺术与技术、乃至哲学与生活的分离。
以柏拉图为例,尽管没有作技术与艺术的明确区分,但是,从他关于人的等级划分中可以看出技术与艺术分离的征兆。在柏拉图的心目中,存在两种诗和诗人。柏拉图把人分为九等,第一等人是“爱智慧者,爱美者,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此外,还有所谓“诗人和其他模仿的艺术家”,列在第六等。朱光潜说:“这里就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第一等人和第六等人的分别在哪里呢?彼此有没有关系?如果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我们也就可以看出柏拉图的艺术概念和美的概念都建筑在鄙视群众,鄙视劳动实践和鄙视感性世界的哲学基础上。”从柏拉图对第一等人的所谓人生境界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柏拉图,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的古代思想家看来,“人生的最高理想是对最高的永恒的‘理式’或真理‘凝神观照’,这种真理才是最高的美,是一种不带感性色彩的美,凝神观照时的‘无限欣喜’便是最高的美感,柏拉图把它叫做‘神仙福分’。”柏拉图所说的这种美,正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所批评的从“直观”而不是从“实践”(这里所说的“实践”主要是指生产劳动,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伦理和政治活动)去掌握现实。朱光潜也说,这种思想的一个要点是“凝神观照”,这是审美活动的极境,美到了最高境界,就只是认识的对象而不是实践的对象,它也不产生于实践活动。朱光潜针对柏拉图的“理式说”(即理念论)指出:“凝神观照理式说的第二个要点是审美的对象不是艺术形象美而是抽象的道理。他对感性世界这样轻视,正是要抬高他所号召的‘理式’和‘哲学’,结果是用哲学代替了艺术。这是他从最根本的认识论方面,即从艺术对现实关系方面,否定了艺术的崇高地位。在这方面,他对后来黑格尔的美学思想起了深刻影响。黑格尔不但也把艺术看得比哲学低,而且在辩证发展的顶端,也让哲学吞并了艺术。”⑦
西方哲学的局限性不只是表现在对艺术本身的观念上,更表现在哲学的整体精神之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用理念、用“形而上学”,准确地说,用哲学的认识论吞并和否定艺术,开理智主义或认识论的本质主义之先河。到康德,伦理学也被塑造成“绝对命令”的体系,西方哲学可以说最后封闭在先验论的甲壳之中,造成了对生产劳动、技艺或技术的放逐,造成了文化诸多方面,如感性与理性之间、理念与现实之间、技术与艺术之间的内在分裂。
传统的理智主义和认识论主义,在近代,演变为“物理学的帝国主义”和科学主义。西班牙哲学家何·奥·加塞尔曾经指出:“近百年来,欧洲的知识界饱受‘实验室的恐怖主义’所蹂躏。”“哲学家震慑于物理学的气焰之下,感到十分羞耻——因为自己不是物理学家而感到羞耻。由于真正的哲学问题不能用物理学的方法来解答,哲学家只好把它们搁在一旁;他遗弃了他的哲学,把它压缩到极小的范围内,任由物理学把它摆弄。他认定了唯一值得探索的哲学题材就是对物理学所涉的事实作出沉思;也就是说,哲学只不过是‘认识论’。”⑧ 甚至整个一部哲学史也被看做只不过是一部认识史。
由于近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物理学知识)在技术、工程和生产领域中的一定程度上的应用性,更由于物理学理论的重大实用价值适应和满足一个正在兴起的阶级——中产阶级攫取财富的需要,因此,物理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知识在人类知识和文化体系中获得了霸权地位。不仅如此,甚至全部人类知识和文化都被看做是认识自然,进而控制自然以获得财富和利益的工具,全部哲学的使命和意义都被看做是寻求认识外部自然的工具和方法而已。这尤其是近代认识论主义哲学家对知识和哲学的基本观点,同时,也是近代西方哲学和文化的根本的局限性。
在这种哲学的观念和模式中,人类多样的知识和文化活动,被抽象和简化为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或理论与实践(这里的实践不再包括伦理和政治行动,而是指单一的改造自然的活动和过程),即理论与应用的关系。在这种模式中,哲学是一种唯一的或统一的“世界观”,是对宇宙一般规律的探索和揭示,其他知识和学科则是个别事实和现象的把握,是哲学的一般知识或普遍规律在具体的或个别的事物和领域中的运用(或应用)。似乎有了一种一元论的哲学或哲学世界观就有了一切,一切其他的知识和文化都是,或都应该是这种世界观和宇宙观或作为“太上科学”⑨ 的哲学的推论和演绎。知识论上的这种一般与个别的哲学思维模式,实质上是“物理学帝国主义”的一种表达形式,是近现代科学主义使自身合法化的哲学推论过程。这是“科学主义”的实质,也是当代“知识状态”和“文化处境”中的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尔曾经指出,现代哲学就是科学制造的关于自身地位合法化的一种元话语,我们所使用的“现代”一词实际指称的就是这种依靠元话语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⑩。由此可以看到,科学对其他知识和文化包括哲学的殖民,“科学帝国”的存在,是以遮蔽和否定别的知识形式的合法地位,牺牲知识和文化的多样性为代价的。
三、设计哲学的视野和意义
如前所述,理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根本局限是否定人类活动、知识和文化的多样性,遗忘和牺牲了思想和知识的感性生活基础。因此,恢复和凸显发源于生产劳动的感性创造活动在哲学视野中的地位,并在具体的生产劳动中以及广义的多样的创制和设计活动中实现技术或“创制”与艺术、理性与感性、真理与创造(或客观的外部制约性与主体的内在创造性),以及不同知识和文化之间的统一(相互渗透与相互作用),将是哲学以及一般文化发展的重要课题和方向。
设计或创制作为一个哲学的主题或领域的确立,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哲学观和知识观,克服传统哲学中根深蒂固的认识论的本质主义或理智主义,以及空洞、僵化的道德先验主义,开拓哲学的视阈,复兴和激活哲学的话语和文化能量。具体说来,设计哲学的意义或潜在的思想空间和视野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设计哲学的探索和发展将有可能重新界定认识和科学的疆域,对物质文化的内部机制作出更全面的把握。
“认识论主义的”或“科学主义的”哲学思维模式和文化的一个为人熟知的表达形式,是在物质文化领域中虚构的科学(科学理论)、技术和工程单向演绎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技术和工程就是科学理论的应用和推广,是完全被科学或理论所决定的,由此,否定技术和工程的独立性,更否定技术和工程中伦理和社会的考量以及创造性的思想和设计的重要性。因为在这种认识论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模式中,认识或所谓的客观真理就是一切,或者说,掌握了外部世界的实在性或规律就是一切,主体本身、创造本身是没有什么独立性的。实际上,科学理论与技术和工程各有其独立的文化和社会地位,也各有其知识论上的独立性。“自然科学家发现前所未有的东西。工程师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两者都是大胆地走在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上,但是两者又具有各自的原创性途径。”(11) 近年来,国内学者提出的科学与技术“二元论”或科学、技术和工程的“三元论”也是对科学主义的有力解构,彰显了设计和创制在物质文化领域中的根本意义。
今天的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已经充分揭示出,即使在物质文化领域,除了认识(或外部客观世界)的实在性和客观真理性之外,生态的复杂性和可持续性、技术和工程的效用和价值,以及技术和工程的伦理和社会等方面同样具有独立而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文化的创造中,我们不仅要认真研究客观的自然过程和自然规律,而且要仔细思考技术和工程的效用、生态和经济的合理性、文化的脉络和社会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创造过程和设计过程,而不只是现有自然知识的单纯的应用和物的功能的简单开发。自然科学或自然知识、物质技术和工程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单线演绎或自然知识的简单应用的过程,而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科学——无尽的前沿》一书的作者,美国工程师布什曾经指出:“在工程师与科学家的所有关系中,工程技术与其说是科学的产儿不如说是科学的伴侣。”(12) 《工程学——无尽的前沿》一书的作者欧阳莹之更进一步指出:“工程技术作为一种创造性和科学性的活动,它通过改造自然以服务于大众的需求和愿望,具有自然的和人为的双重维度。工程师为了能够有效地改造自然,需要对自然界的现象和规律了如指掌,因而他们合用了自然科学的内容和标准。为了确定什么样的改造过程才合乎需求,需要懂得人性和社会经济的各种因素,所以工程技术又在它的实用性和服务性的使命上超越自然科学。”(13) 可以概括地说,技术和工程以及广泛的物质文化建设都是物性与人性、理想与现实、服从于自然与创造文化的统一,贯穿于其中的思想力量就是创造,就是设计。
其次,设计和创制哲学的探索,也将使我们对社会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的内在结构和机制作出更合理的解释和重构。
以往的哲学思维模式以及科学主义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就是我们过去哲学教科书中所讲的“三观”理论,也就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其实,在所谓“三观”中核心的东西只是“世界观”,因为在这种思维模式中人生观和价值观被看做是由世界观一维地决定着的。这里的所谓世界观实际上就是自然观,有世界观即宇宙观之说。在这种世界观所决定着的知识体系中,社会科学只是哲学世界观在社会领域中的运用,如果关于社会的知识要成为科学,也只能是自然科学那种模式的知识,或者是自然知识在社会领域中的简单应用。
以往的哲学中还有所谓世界观就是方法论的说法,这种观点把创制和“做”的问题与认识或“真”的问题混为一谈,看不到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真正意义。在知识论上,这种理论或观点,看不到设计和创造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看不到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形成,以及广泛的社会决策和社会治理,实际上都是包含多重知识和文化因素的复杂过程,其中既包括对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科学认识,也包括对人们的社会行为与社会制度的伦理和政治合理性的考量,更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超越性的批判和思考,对未来社会的一种设计和筹划。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立足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的知识体系,与实际的社会生活、社会政策的制定、社会组织的管理有着积极的互动。因此,社会研究和社会决策的过程,既是一个科学的认识过程,也是一个艺术化的创造过程。社会科学和社会研究的更高的形态,绝不是彻底的实证主义,而是把复杂的实际社会生活过程和社会决策过程中的科学因素与人文因素结合起来而生成的一种具有现实性的智慧。人们之所以把邓小平称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就是对他在制定改革开放的社会政策时所表现出来的高超智慧所作的崇高赞誉。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把政策经济学看做是把实证经济学的认识与规范经济学的目的结合起来的“经济学的艺术”,可以说非常精到地把握了经济学的复杂的内容和内在的思想机制。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文化,同样是认识与目的、事实与价值、现实与创造等因素的统一,也只有放在人类完整的活动过程中,在多样性的知识和文化因素的统一之中才能对这些知识形式的属性和意义作出合理的界定和把握。
与社会科学知识相比,人文文化在以往的哲学中更常常被看做仅仅是精神性的文化形态。实际上,人文文化,从最具象的物质产品设计、建筑和环境设计,到比较抽象的音乐和绘画,再到社会的文化形象和文化理念的设计,无不包含着对物或自然(包括人自身的自然)的机理、人文产品的伦理和社会内涵的深刻理解,绝不只是一种单纯的主观性和精神性。只有在认识、目的和艺术,或事实、价值和理想的统一中,人文文化才能实现精神的超越,达到文化的理想,实现文化的追求。一个好的诗人、画家、音乐家,一个好的建筑师、产品设计师,等等,一定在自然知识方面有深厚的储备,对伦理文化、艺术的精神有卓越的理解和感悟,同时一定对变革和创造有深切的好奇和追求。
再次,设计哲学或创制哲学的确立将推进教育观念和教育模式的变革。知识和文化与人类未来最直接地关联和沟通的领域和途径就是教育。知识领域和知识论的混乱更直接地导致教育和文化传承中的诸多偏失。今天,困扰中国教育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看待和处理科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当然,如前所述,实际的教育过程中还应该包括一个重要的领域,即道德和政治的教育。[把道德和政治教育(今天往往被称为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混同起来也是中国教育中的一个值得引起思考的问题,这需要另文讨论]。美国思想家赫伯特·西蒙曾经清晰地界定了设计在教育中的普遍而根本的地位,强调设计是职业教育的核心,是区别科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标志。他说:“工程师并不是唯一的职业设计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种人类行动,只要是意在改变现状,使之变得完美,这种行动就是设计性的。生产物质性人造物品的精神活动,与那种为治好一个病人而开处方的精神活动,以及与那种为公司设计一种新的销售计划、为国家设计一种社会福利政策的精神活动,没有根本的区别。从这个角度看,设计已经成为所有职业教育和训练的核心,或者说,设计已经成为把职业教育与科学教育区别开来的主要标志。工程学院、建筑学院、商业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等,全都是以设计过程作为核心内容。”(14) 由于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教育学(认识论主义和科学主义在教育领域中的表现)的影响,以往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往往用科学教育取代或否定职业教育的独立性和意义。这是我们国家的教育严重滞后于经济和技术发展需要的原因。实际上,科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各有不同的内容和功用,科学教育以及理论思维能力的培养,指向的是对象的世界,是对象性世界(包括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和文化的世界)的内在机制,而职业教育的核心是对象世界的“属人性”,是如何利用各种外部的因素(包括自然的因素、社会的因素和文化的因素)为人的现实生活服务,着眼的是对象世界的有用性、合目的性和艺术性等等。如何合理地处理和重构科学(或学术)教育、道德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是今天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三者不可偏废,不能用一个方面取代和否定另一个方面。
最后,设计哲学的探索还将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变革以及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重构发挥积极的作用。
毋庸置疑,由于中华民族长期处于农业文化和封建家族血缘文化之中,我国传统文化存在泛道德化的倾向,传统主流思想,如儒学和道学,都对制作和劳动生产持轻视的态度。《论语·子路》:“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里明确地表现出作为古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学和儒家文化对体力劳动和生产活动持歧视的态度。《庄子·天地》:“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把技能、技艺斥之为“奇技淫巧”,是老庄哲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征。
文化的泛道德化或文化中的道德先验主义,其影响和局限性不只是表现在物质文化和劳动生产的方面,还表现在国民的行为模式和文化心态中,具体说来,包括保守,缺乏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害怕变革,不善于创造;在社会行为方面,缺乏契约精神、民主的精神和个性自由的精神,等等。从哲学的层面来说,这些文化现象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因为缺乏对设计机制的理解,缺乏设计品质和能力的培养。当然,这种缺失本身又是由文化的历史境遇造成的。
概括地说,当代中国文化精神的重构和发展,不仅需要着力于道德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而且迫切需要加强创造、创新和设计的品质和精神的培养,此外,当然还包括科学精神和学术精神的培养。只有具有这样全面的精神和文化要素和体系,才能适应当代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需要。一个好的产品,一项好的制度,一个好的环境,甚至一个好的社会,一定同时是科学的、道德的和艺术的,是客观的知识、良善的道德和理想的构造或实施的统一,一句话,是真善美的统一。这是一项具体的物的设计活动、组织决策活动,以及整个民族和时代的精神都必须努力追求的一种境界。
[收稿日期]2010-07-15
注释:
① 见《“设计哲学”的可能性和意义》,《哲学研究》2001年第10期。
② 2002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李伯聪出版《工程哲学引论》一书。以此为基础和契机,2003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了工程与社会研究中心,并出版题为《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的年刊。2004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程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并主持编辑《工程与哲学》的连续刊物。按照中国工程哲学研究的主要倡导者李伯聪在《工程哲学引论》一书中的定义,工程是指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和过程。工程概念是广义设计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工程和工程哲学不包括社会政策与社会制度的设计,以及文化精神和理念的设计等更广泛的范围。
③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71页。
④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⑤ 参见[英]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马音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144页。
⑥⑦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47-50页。
⑧ [西]何·奥·加塞尔:《什么是哲学》,商梓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2页。
⑨ 参见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⑩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页。
(11) 欧阳莹之:《工程学——无尽的前沿》,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12)(13) 参见欧阳莹之:《工程学——无尽的前沿》,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14) [美]西蒙:《人工科学》,武夷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1页。
标签:哲学论文; 认识论论文; 世界观论文; 柏拉图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哲学家论文; 生活教育论文; 活动主题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