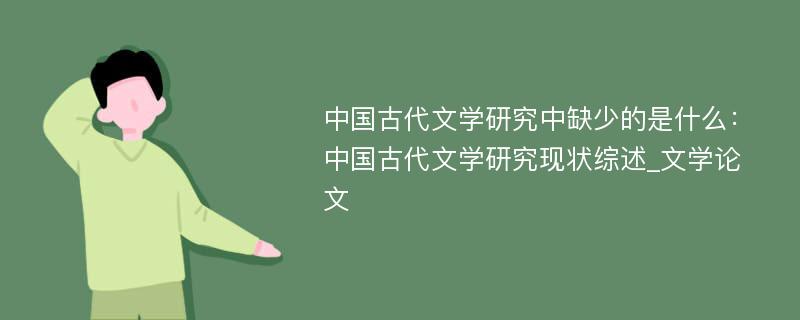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缺失什么——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状的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文学论文,缺失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者之间,品评学界风气总是有意无意间的一个话题。刘跃进、蒋寅、李昌集、郭英德、左东岭、赵敏俐等几位学者,有这样一个设想:来一个坐而论道的神仙会,对当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不足发表看法;在座谈中相互激荡,声气相通者呼应之,看法不同者争论之。这一想法得到了陶文鹏、黄霖等先生的赞同和诸位学者的响应。4月上旬,“21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论坛”在徐州师范大学举行。来自二十余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学者三十余人聚集在云龙湖畔,展开争鸣。言谈既热烈又轻松,话语既中肯又尖锐。我们将学者们的观点概括阐述其要,以飨广大学人。
——编者
我们所缺的首先是学人的尊严,学术的尊严
古代文学研究,当前最缺的是学人的自尊自重意识。
学者们认为学术研究是人做的,学术上能取得多大成功,首先看你怎么对待它。古代文学研究与别的文学研究的不同,是面临着几千年的文学史和学术史,哪怕一个小问题,也要寻找很多历史资料,把已有的相关研究弄清楚,需要长期的知识涵养和功夫的修炼,厚积薄发才能出精品。而现在读书粗疏、急功近利的情况却十分普遍。学人扪心自问,每天定定心心看原典能有几个小时?弄上几条资料,就写大文章,真正爬梳原典把资料搞透的不多见,弄了半天,人家早就说过了,而且说得比你还要好。
如果真正是自己搞出来的东西,倒还说得过去。学力有欠,见识不广,与过去的研究“暗合”,还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有意识的抄袭。抄现在的,偷过去的。把张三李四论著的材料和观点拼一下,语言上换一换,就成了自己的“成果”。这种“软剽窃”,没有“硬伤”,说起来只是“新意不多”,没法定剽窃。聪明一些的抄袭上世纪初学者的成果,偷了一时能瞒过一些人。在参考文献中,凡是与自己的“论文”直接相关的反而故意不提,不关痛痒的倒列上一大堆。
这些情况,恐怕和现下的科研管理制度有关系。现在什么都是“量化管理”,只看数量,只看发表的刊物的级别。科研成果的时效最多只有5年,5年前的东西表上就不算,圆寂了可以算总账,活着的时候只能算5年。学人也要吃饭,要职称啊,古代文学又这么难,只有抄一点呗。钟敬文先生说他最得意的文章只有两篇半,两篇是自己发现问题自己解决的,半篇是人家提出的问题由他解决的。两篇半,副教授都评不上。钟老是谦虚,但给我们很多启发。现在评了教授还要评岗,每年没有成果就下岗,下岗太没面子了,能深思熟虑出精品么?万不得已只好用老“思想”包装点新货色。再说现在评职称,当评委的很犯难。有的实在水平够不上,但要体现人道主义啊,老大不小了,不给职称,面子上也不好看。条件又是死的,5年之内,核心刊物要8篇,专著可以抵三篇,古代文学研究又不能信口胡来,“理论”一番就完事,不参考一点怎么办?像陈寅恪一篇文章还没有,梁启超就推荐他做清华国学导师,现在哪个校长和人事部门敢批?
学风浮躁,外部条件是一个因素,但学人甘于自轻自贱更可怕。古代文学研究的职业化,最堪担忧的是学人缺失了一种虔诚的生命投入和学术激情,“著书只为稻粱谋”。哪个学人愿意偷,但久而长之变成一种心安理得的职业习惯和潜意识,老是喜欢把人家说过的问题再“发挥”,比如“玄学”对六朝文学的影响之类,说了又说,你的新意在哪里?把人家说的交代清楚,你有一点新见就讲一点,没有就不说,硬要正儿八经说一通,结果是重复性阐释游戏太多。没有自己的问题,老是习惯于跟风,这样下去,学术贬值必不可免。如果不注意扭转,总有一天,我们会为今天的学术脸红。
文学研究的“文学”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太热心为别人打工?
学者们还对学术“内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说到“内部”,现在有些人开玩笑说,古代文学研究需要来一个“清理门户”。古代文学研究中“文学”的迷失,已成一个大问题。很多古代文学的研究,实际上成了文化学、哲学、历史学的附庸,文学作品成了解释某种文化或历史的资料,文学研究在为别的学科打工。比如研究汉赋中的“都市文化”、戏剧中的“民俗文化”、晚明小说中的“商业文化”等等,算不算“文学研究”?我们当然需要多学科的贯通,但最后的归宿是“文学”。我们当然需要对文学作哲学、文化学和历史学的理解,需要在研究中融入科学精神,但如果把文学研究简单理解为某种“科学”,则违背了文学研究的本性。
“打工热”的深处,恐怕是古代文学的研究者缺乏“文学的自信”,忽略了文学的重要功能在于解构科学,解脱人生的重压,文学的灵魂是人生。当前文学研究的“文化热”和某种“科学化”倾向,有积极的一面,但必须警惕其负面影响。
说到“清理门户”,“回归文学”,请问文学的“门户”是什么?文学的门户本来就是开放的,凡所见、所闻、所感的一切,都是文学表现的对象。文学没有一个绝对的自身世界。勉强说起来,那大概只有“文体”和“艺术手法”算是自家的。但“文体”也不是为了“文学”产生的,而是由文学所服务的那个对象决定的,比如诗吧,最初是为了口耳相传,便于记忆才成为这个样子,大约经过仪式歌唱和书面记录而定型。我们要解释文体的生成,就要把它服务的对象说清楚,为什么要如此服务,服务的过程又是怎样一一弄明白,这样才能知根知底,否则便只能仅仅停留在形式表层上。艺术手法,也和古人的思维习惯以及对世界的认知方式相联系。谈艺术,分析它的手法和效果是一个层面,但所以形成这样的艺术方式,所以能够取得效果而对接受者产生影响,没有个“文化语境”怎么行?是不是对这些内容的研究就算“外部研究”?
大家认为,我们要对“回归文学”的涵义有一个恰当的理解。所谓文学,艺术表现方式和美学意味是根本要义之一,大概不会有争议,否则文学和行政通知、产品广告还有什么区别?西方美术界的“波普艺术”乃至“行为艺术”宣称要解构艺术,取消艺术样式和一般样式的界限,好像并不成功。文学界这样的尝试不多,说明文学还是有一个自己的世界,虽然这个世界并不是靠文学自己独立营造的。诚然,目前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普遍缺失,是对文学如何生成的解释。比如研究唐诗怎么写出来的,唐代类书与唐诗的关系便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课题;研究汉赋,则离不开对汉代宫廷文学活动的考察。而研究诸如古代神话中的“水文化”、明代小说中的商业文化等等,算不算“文学研究”,当然不必太拘泥。但我们从文化角度展开对文学的研究,探究的是“文化中的文学”,而不只是“文学中的文化”。
人间的一切几乎都可以在文学中找到,但这“人间”毕竟是文学反映的人间,而不就是人间本身。文学本身也是人间的存在,但文学根本精神通向一个理想世界,古代文学描绘的人间,最终指向的大多是当时现实生活中没法存在和没法实现的,所以“文学”和“历史”不同,文学不仅满足求知欲,更在宣泄人们的失望和追求。这大概是文学魅力的根本所在。所以,文学研究“回归文学”,根本精神之一,就是注重“文学世界”和现实人生现象的比较阐释,说明文学是怎样创造自身世界的。正是在这一点上,过去我们所做的研究太肤浅。“回归文学”,不是回到单纯的鉴赏式的文学解说,把文学解释弄成标本展览,解释得越多越象医学解剖,林庚先生早就批评过,现在这样的东西学术刊物是很少发了。但我们也不能把文学弄得无所归依,只有从题目上看出和文学作品有关系,内容上和文学一点挂不上钩。古代文学的“外部研究”,也要从文学研究的需要出发,现在我们的“外部研究”不算少,但缺失对文学生态的细致考察,缺乏对古代文学的生成和传播过程的生动解说。我们应当提倡各种研究共存,为人家打工固无不可,但不能忘记最终目的是把自己的活儿干得更好。
学者们认为共同点在于,“打工”作为一个比方,很生动形象,让人一下子抓住“回归文学”的要义。但我们自认为替人家打工,人家未必领情。现在的学科分类,门户过于森然,但各个学科有自己的行规,有自己的专门问题和学术指向还是必要的。我们说文学研究需要超越文学,才能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回归文学,并不是要消解文学的自身性,所谓“外部研究”,真正的问题应当都是从文学研究中生发出来的,是研究文学之需要。这样,虽然有些研究看起来和文学关系很远,但文学研究者关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问题,和这些专门学科的人想法还是不大一样的。当然,探究其它领域的问题,比如文化上的问题吧,就得遵守文化学的学术规范,遵循其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如果发现不够,就会有补充,有扩展。比如佛学研究界所著述的佛教史,有一点不太充分,就是不大关注民间对佛教义理的接受和理解。而在文学中,比如小说吧,其反映的民间对佛教的理解,与佛经上所说的有许多其实并不相同。佛教史对佛教世俗传播中教义的变异,目前的阐释似乎不多。但在小说戏曲中却可以发现不少。一些在中华本土产生的佛教宣讲经义的文本,也许在文学中可以发窥其思想根源。所以,仅从研究佛教的专著或者从《佛教大辞典》之类的书上讨点资料,然后去解释若干作家和文学作品中的佛教思想,这样的“打工”,其实人家很不屑。如果你能把文学作品中的佛教思想与佛教的正宗教义有什么异同说清楚,这才是有价值的“打工”。把人家说过的东西往文学上一套,这算什么“打工”?人家不会给你发工资。
做到这一步,当然很好,但恐怕太难,汲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为我所用,是正常的。当然,仅仅用文学印证一些诸如思想史、文化史上的某些常识,算不上是高明的研究,这不就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了么——倘若这样的研究最终导向了对文学深层内涵的理解,就是好的“文学研究”。怕就怕既没有替人家打什么工,也没有替自己干多少活儿。
实际上,所有学科,都是互相支持的,大家都在为自己打工,也为人家打工,大家扯平。
理论指导研究还是研究建构理论?
学者们还指出,在近二十多年的古代文学研究中,曾有过一段时间衷情“方法论”的热潮。但近几年来,古代文学研究中“理论”的名声却不太好。不少“文学研究”,变成了某钟“理论”的解释题,研究文学作品,先用西方的某理论设定一个框架;阐述文学现象,以西方的某理论作为既定的结论,作品和文学现象本身反而不加深究,用洋酒瓶装中国酒,“理论阐述”成了贴标签。
与一些国外搞汉学的友人,尤其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谈起来,他们现在对中国大陆的论著,最不感兴趣的就是玩理论的一类。这给了我们一个警告:我们自认为很有“理论”、很有“思想”的东西,在人家眼里却既没有理论,也没有思想。因为这些“理论”和“思想”都是人家已经说得熟烂的东西,一点新意也没有。现在,像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那样,直接用“系统论”、“耗散结构”解释文学史、用弗洛伊德学说分析《牡丹亭》什么的,是不大看到了,但以西方文化人类学、阐释学等等为框架的研究却不少见。将西方文艺学、美学的一两条理论拿来,把古代文学的“艺术”说得玄玄乎乎,也时而可见。西方理论+中国事例,成为一些人的“学术”秘诀。有人说,这就是“深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们所说的这些现象也算目前古代文学研究的某种特征吧,只不过是一种负面的表现。从上世纪以来二十多年的新一波西学东渐,是当代学术品格形成的重要背景,一些学人对西学有些食而不化,可以理解,投机取巧的也不是没有。但我们不要过分夸大负面。西学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如此大规模地涌入中国,研究中出现中学与西学不同思维习惯的碰撞是必然的,刚才诸位的意见也是碰撞的表现。我们的传统理论重人生经验和直观感悟,习惯于综合性的融会贯通,与西方重在归纳抽象和逻辑分析有所不同。古代和今天书面语言的不同,也使我们很难直接运用传统的理论语言和表述方式,出现“洋瓶中酒”的现象并不奇怪。
现在我们的一些研究生,论文不用上一串洋化术语就不甘心。比如现在大家都在说的“解构”吧,问是什么意思,说了半天也没有说得清,以为“解构”就是拆散和抛弃,其实“解构”是对被解构者内容结构的分解、剥离和重新提取,“解构”和某种“重构”是紧密相联的。文学史上的新旧交替现象,能不能都理解为解构,要看情况,比如汉末魏晋的抒情小赋与汉大赋,非要说小赋是对大赋的“解构”,不贴上洋标签就觉得不过瘾。为什么非得用“解构”这个概念,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新见解,似是而非地用一些新术语,就能使研究高明起来?其实并不然。理论上的术语,归根结底是一种对存在的理解和研究方法的指示,而不是让你贴标签用的。
理论的滥用、误用是一回事,研究中的理论指导又是一回事。我们不能因为有滥用理论的现象便排斥理论,拒绝西学,西方也在吸收中学嘛。理论的问题,不单是中西方的问题,更在于时代需要新的理论。王国维早就说过,从根本上说,学无中西。当代的古代文学研究,理论建构的缺失仍然是个大问题,考据遮蔽思想、技术伪装学问的现象相当普遍。我们应当提倡以思想为出发点的有意味考证,提倡发现问题中的现象描述。这里就有个理论指导、理论建构的问题。
问题在于怎样进行理论建构。“以思想为出发点”,这“思想”从哪里来?“意味”是什么?“理论指导”,就是从某种理论来的吗?“理论指导”还是谨慎一些好,“理论指导”和“理论意识”并不是一回事。理论的目的和价值是为了认识事物,把握事物,光是理论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主张把各种理论——包括西方的理论和传统的理论,理解为一种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得意忘言”,解决研究中的实际问题。高水平的研究,其实都包涵着一种内在的学理建构,只不过不是摆在脸上,而是融化在整个研究的分析材料、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之中。如果同意也是一种理论建构的方式,那么就是研究建构理论而不是理论指导研究。如果一开始就想到用某种理论来“指导”,很容易变成一种贴标签,美酒饮而醉,不是看到“此乃百年威士忌”就醉的。
大家认为,有人说的“理论指导”和“理论意识”好像没有根本分歧。只不过“指导”容易让人误解“理论先行”。大家关心理论问题,实际上是要求学术品格的提升。其实,学术品格的提升,根本标志并不在理论的新旧。我们所接受的西方理论,其实新的也不是很多,相当部分恐怕已经是“旧”的。其实,新理论未见得就全高明,“旧”理论也未见得都不管用,善用之则灵。要谈理论建构,我们还没有自己很像样子的当代“文学理论”,学界不少人呼吁建构中国自己的理论,虽然这是理论研究家们的事情,但古代文学的研究也应该出点力。目前一些学者探索从古代文学创作中提炼理论内涵,与传统的和西方的文学理论加以融会整合,是有创意的。当然。古代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不是构造理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建构,在于把思想的结晶融化到具体的文学研究之中。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意识,第一条就是关注中国文学本身,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出发研究中国文学。离开这个“理论指导”,恐怕不行。有了这个“指导”,大概就不会生搬硬套某个现成的理论来指导研究,才会有真正融化在研究中的“理论意识”。理论,说到底是对存在方式、存在结构、存在演化的一种认识的提炼,所以,任何理论都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加以理解。落实到具体研究中,就是怎样对待研究材料的问题。所以,无论是“理论指导”还是“理论意识”,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理论出发,乃是一切学术研究的根本原则。
找回历史感,探寻文学史书写的空白
学者们认为,既然理论的问题要在研究中体现,我们就回到古代文学研究本身。
古代文学研究,面临的是几千年的文学。从事实存在的角度说,是一个既定的存在。这笔遗产实在是太丰厚了,但现在不少搞古代文学研究的都在感叹,研究课题不好找。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生,论题难找也是最头疼的问题。这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现在,作家作品的研究已经很难做,大家都在说,一流的作家作品都研究透了,“出新”的空间实在是太小;公认的二流的作家也几乎没有什么漏掉的,寂寞山中花自开的恐怕已经没有。有人力图定出几个“新”的大家来,能真正引起注意和学界一致公认的实在不多,三流作家吗,似乎研究价值不大,花了大力气,怕产生不了影响。所以,现在做纯粹作家作品论的越来越少。这是目前大家都感到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之一。
这种情况,恐怕并不是作家作品已研究透了无可再研究,而是我们没有找到一个作家作品研究的新路径。老一套的生平、思想、艺术、影响的阐释框架已引不起人们的兴趣,在这样的框架中,确实已出不了什么新意。一段时间里,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风行过一阵,但还是在这个框架中转圈子,把已有的研究拼在一起,当然也引不起人们的多大兴趣。但我们如果开拓一下思路,可能就会发现一些新的课题。比如说吧,屈原流放中所作的《离骚》,是怎么流传出去的?如果不是司马迁的高度赞扬,屈原还会像今天这样活在后世直到今天人们的心中吗?也就是说,古代文学“家”究竟是怎样出名的,评价机制又是什么?这评价机制在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情况又有哪些同异?苏轼成人是他老子调教出来的,老子的名气本来并不比儿子小,为什么欧阳修一下子就看中了苏东坡。这些耳熟能详之事,其实大有深意焉,但至今好像并没有说得很明白。作家作品的研究,不是一点空间也没有。关键是我们的思路要拓宽。
大家认为这实际上已经不单纯是作家作品的问题,而是文学史的问题了。当然,古代文学中的每一个点,其实都和文学史有关。现在,我们有了好多部文学通史,也有各种词史、诗史、散曲史、小说史等等专体文学史,专题文学史如山水诗史、专类文学史如女性词史、女道士的诗史等等,也开始出现。但是在“史”的框架上还是大同小异,差不多都是以作家作品的静态流程为“史”的纲目。这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我们能不能考虑另一种书写方式呢?一些学者预测,文学的传播研究将会成为21世纪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是有理由的。因为文学的生命和价值的体现,是在传播中实现的。文学既是私人化的创作,也是一种社会的存在,与社会的各种活动交织在一起,但我们现在通常只是把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作为映衬,缺乏生动具体的文学生态环境的描述。现在不少论文倒是注意“小环境”的描述,但似乎还很不够。
这里说的实际上是找回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感问题。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先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学”,是“古代”的文学,而我们的研究者总是非常自然地以现在的“文学”观念去理解古代文学。20世纪初,就有人试图从古代的文字作品中分出诗啊、抒情散文等等“美文”一类,和诸子散文等等政论文分开作为真正的“文学史”,结果没有行得通。80年代,陈伯海先生提出古代文学观念是一种“杂文学”观,即把所有的文章和诗词小说都看作“文学”,很有启迪。但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种现象,怎样在“文学史”中恰当地描述和分析这种现象,其对“文学史”有何影响?至今似乎也还没有一个好说法。这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们既要立足当代的文学观念,又要把握古代的文学理念和“文学”实际,怎样沟通当代文学观与古代文学现实,怎样对待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章”的模糊关系,如何描述古代文学的多元生存样态,至今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目前的古代文学史书写,还只能把历史散文、议论散文和抒情散文作为同一个系列,用差不多的分析方法评析。如果不深入到古代“文学”的生态环境中去,对各种不同“文学”的具体功能进行一番探究,想要深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恐怕不容易。
学者们对“文学生态学”和“文学功能学”这两个概念很感兴趣。如果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我们的文学史书写,可以拓宽的地方就很多。比如戏曲和小说吧,二者的功能有许多相似性,但又有若干不同,古人对此就有过不少表述。小说转化为戏曲,戏曲转化为小说,也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过去已作了一些这方面的基础性资料工作,但从“理论意识”上去进一步研究,从小说戏曲的生存状况中探究个中缘由,可以说还没有很好地展开。这样,我们在文学史书写中只能以思想啊、形象啊、矛盾冲突啊等等同一模式对小说戏曲做分析,更不用说对戏曲的场上形态与文本形式的关系有所开掘了。中山大学研究戏曲的同仁对戏曲的场上形态研究下了很大的功夫,听说徐州师大的同仁准备把戏曲的文本传播研究作为一个重点,把场上传播和文本传播的相互关系作为中心,不容易做,做起来很有意义。
当代文学史书写的拓宽和改观,最大的问题恐怕是对文学史链的重新理解。刚才谈到的“文学生态学”和“文学功能学”,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角度,有助于在“文学史”静态的描述中增加对文学生存状况的动态描述。现在的文学史作为大学教材,还是有它的优点。现在的文学史著述,一种是做教材用的,一种是给专家们看的,一种是普及性的,三种写法,各有不同。我们不妨保留多样化的格局。现在通行的文学史,主要陈述基本的系统化的文学史知识,感受古代文学的意境情趣,这也是很重要的。“静态”的文学史,也有静态的好处。动态的书写,怎么个“动”法很重要。现在是静的动不起来,动的静不起来,怎么将动与静有机地结合,是个课题。
当然,文学史书写只有多样化才能使文学史书写更丰满。所谓“动态”的文学史,重要的一条就是把文学置于人们的社会活动中去展示,以寻求我们过去文学史书写所建立的文学史链中的空缺,努力寻找那些文学史书写中失落的历史环节。比如“诗三百”从先秦隶属于礼乐文化到汉代成为官方确定的经学,在文学史上有何重要意义?文学在古代的童蒙教育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对文学家幼年的成长具有怎样的影响?在上层文化圈与下层文化圈,文学的生成和运行机制有何差异?文学传播的渠道和方式的历史变迁对文学演进具有怎样的影响?清代“花部”的形态远远不如杂剧和传奇“高级”,却为什么能上下风靡?如此等等,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究。做这样的研究有一点要注意,就是把我们所习惯的那种总是盯着大传统的“整体叙述”改变为对小传统的细致考察,先不忙总结某种“规律”,把一个个历史细节先搞清楚,然后再看看“宏观叙事”是否有可能。所以,我们今天讨论文学史的书写,只是一种方法上和书写原则的探讨,不必匆忙地定出什么“体例”。“历史感”是个大原则,每个书写者的历史感不会一样,每个人寻找失落的历史,也可能不一样。葛兆光说:历史总是不断地既做加法,也做减法。我们要在文学史书写中做加法,一个重要的视角也许就是把过去的减去的历史再加上去。从而增加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具体做什么样的加法,见仁见智,共同的目标则是追问历史的本来。对历史认知的变迁往往是一个时代文化精神变迁的标志,所以,一个变革时代的人们往往体现着一种自觉的反思精神,这也许是我们今天反思“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缺失什么”最根本的动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