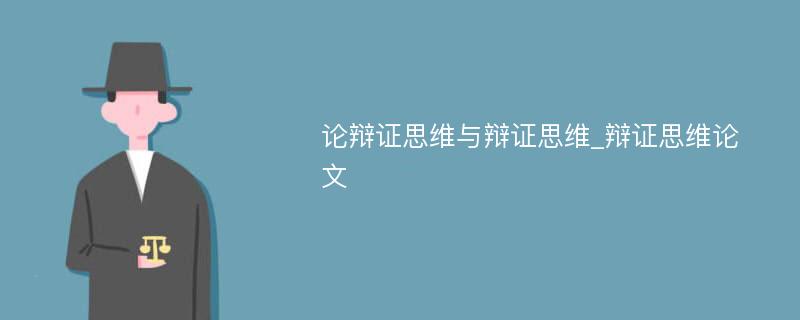
论辩证思维与思维辩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00]05—0076—02
辩证思维是思维的一种类型,是一种高级思维方式,属于逻辑范畴。思维的辩证则是一种方法,属于哲学方法论的范畴。然而,在一些辩证逻辑教科书中却没有将二者解说清楚。有的辩证逻辑教科书认为,辩证逻辑是研究辩证思维的科学,同时又将辩证逻辑说成是“关于辩证法的学说”,“论述思维形式(概念、命题、推理)的辩证法,是辩证逻辑最基本的内容”,如此云云,不一而足。这就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模糊印象甚至于发生错觉,即思维的辩证(法)就是辩证思维。笔者认为,辩证逻辑研究的基本内容是辩证思维而非思维辩证(法)。辩证思维同思维辩证(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本文主要解说辩证思维与思维辩证(法)之间的关系。
一
首先,辩证思维与思维辩证(法)有其内在一致性,并且体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在人的认识中,理论的逻辑行程应该反映着客观现实中对象发展的历史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由此可以说,人的认识中的逻辑应该是客观现实的历史的反映,只不过这种反映是以理论的形态对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反映而已!同时由恩格斯的这段话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的辩证关系。逻辑应与历史一致是指从内在规律性上、从本质上符合,并非毫无差别的、完全的符合。现实的历史发展是个十分复杂而又充满曲折的过程。而逻辑的东西则是摆脱了历史本身的这种自然形态,撇开历史进程中大量次要的、偶然的东西,集中地反映历史发展中的规律性东西。
其次,研究辩证思维的逻辑与历史一致性的另一层含义则是反映在思维领域中的辩证方法即思维的辩证法(简称为“思维的辩证”),这种思维的辩证也同样建立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基础之上的,同样强调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思想史、科学技术史上的成果,都毫无例外地反映着思维的辩证途径及其意义。正如列宁所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注:《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只有懂得这个人类认识的规律, 才能使我们的认识符合外界不断变化着的客观世界,避免或少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错误。要想使我们的认识与外界变化着的客观实际相符合,首先要做到对事物进行调查研究,使我们的思想、认识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事物的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过程中概括出事物的规律,从而使认识反映客观,使主观辩证法过渡到客观辩证法。掌握思维的辩证法,对于总结工作、分析问题都大有裨益。
辩证思维与思维辩证(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整个辩证思维的某些模式中可以看出,辩证思维是对思维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它也是作为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并在概念、命题与推理中表现出来的。它不是客观事物自身的矛盾运动,而是概念、命题与推理的矛盾运动。列宁曾指出:“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好象在一个基层的‘单位’(‘细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萌芽,这就表明辩证法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注:《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第410页。)可以说,离开了概念、命题和推理的辩证法, 也就弄不清什么是辩证思维。思维的辩证(法)不承认事物绝对分明的界限,在一定条件下,任何事物既是自身又是别的什么东西。多值逻辑也好,概率逻辑也好,模糊逻辑也好,它们建立的前提都是承认亦此亦彼现象的存在。这种建立在亦此亦彼存在基础之上的思维模式,正是思维辩证(法)的具体运用!辩证思维与思维辩证(法)的内在同一性方面反映着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谐调与统一,主客观认识的对立统一。我们知道,辩证法既包括主观辩证法又包括客观辩证法,而主观辩证法实际上就是辩证思维。概念、命题、推理都是对事物的反映,而辩证法则把这种反映搞得更正确、更符合实际。“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注:《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4页。)这才是对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关系问题的正确答案,也是辩证思维与思维辩证(法)内在联系的纽带与源泉。
二
辩证思维与思维辩证(法)除了相互联系的一面,还存在着诸多不同点:
首先,二者的内涵与外延不相同。辩证思维属于逻辑范畴,它是思维领域中具有最大普遍性的概念,也是思维把握客观世界的极为重要的思维形式。它在人的思维活动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辩证思维就是对思维辩证(法)的认识与运用,是运用思维辩证(法)而进行的思维。它是以具体概念为起点的,由于具体概念反映整体,因此,又可以说辩证思维的起点是从整体出发的。这种从整体出发、顾及全面的思维就叫辩证思维。
思维辩证(法)则是对自然辩证法和社会辩证法的反映。被反映的对象是辩证法,当然反映得到的影象也是辩证法,只不过是存在于思维领域而已。作为哲学方法论,思维辩证(法)在思维领域内有各种具体表现。就概念而言,其内涵与外延都带有主观性,但它们所反映的东西则是客观的。由此可以说,概念本身与它所反映的对象就表现为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统一;概念的本质是事物共性的抽象,而这种共性是建立在个性基础之上的,因此它又表现为共性与个性的对立统一;人的认识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其认识的变化又会带来概念的不断变化,但在一定条件下它又总是有确定的内涵与外延的,由此又可以说,概念又表现为确定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命题、推理等各种思维形式的辩证法也是如此,这些都是思维辩证(法)在思维领域内的具体表现。
其次,辩证思维富于主观能动性,而思维辩证(法)则具有客观意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注:《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页。)这说明了“辩证法在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领域普遍存在。”作为辩证法的一种具体表现形态,思维辩证法(主观辩证法)存在于人的思维活动之中,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到它,它都在以客观必然性的形式起着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了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因此,思维辩证(法)虽然是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但它自身却具有客观必然性。
而辩证思维则与此不同,它带有浓厚的主观性,是人脑的一种能动的思维活动。思维的辩证(法)是一种工具,只认识到它的职能与使用方法,如果不去真正使用它,就不能形成辩证思维。只有能动地使用这个工具,才能使之用起来得心应手,其中,主观能动性不可缺。也可以这样说,辩证思维过程就是能动地使用思维辩证(法)这一工具的思维进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辩证思维具有主观能动性。
再次,思维辩证(法)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其本身具有普遍性,而辩证思维由于它是思维的高级阶段的产物,并非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因此它具有特殊性。
思维辩证(法)作为一种方法,人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它。无论在普通思维还是在辩证思维中往往都有这种方法的运用。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说,原始人就已经能进行普通思维了。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人类不能认识事物的质的规定性、事物之间的质的差别,就失去了人类认识世界并赖以生存的基础。即使是最原始的渔猎活动,也必须首先认识到一些鱼类、兽类的特有属性及其相互差别,反之就不能适应环境,就无法生存下去。人们要区分事物,就需要概念、命题、推理等,而这些思维形式一旦出现,其辩证因素也就应运而生。只要有思维就会有思维形式,就会有思维辩证(法)。因此,辩证思维的辩证法是人类的思维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其本身具有普遍性。
辩证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高级形态,它并非自始就有的。就儿童的思维过程而言,在他(她)幼小的时候只能说出电影中出现的好人、坏人,大人如若告诉他(她),某人既是好人又是坏人时,就会感到莫名其妙,更谈不上什么辩证思维了。从整个人类发展史的角度看,辩证思维的出现也是较晚的事。在中国古代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交替时期,出现了老庄哲学的思维辩证法以及用这种方法所进行的辩证思维。当时那种关于“相反相成的”观点和事物无限可分的思想(“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以及中国古人所讲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的两点论思想,都是富有辩证思维的。在西方,古希腊时代就出现了辩证思维的萌芽。朴素唯物主义者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上没有静止不动的东西,一切都在永恒地变化着。他说,万物的本原是火,由火变成万物,由万物回到火,世界就是永远在燃烧着又熄灭着的活火。他还说:“在我们身上,生与死、梦与醒,少与老,都始终是统一的东西。”他又说:“土死则水生,水死则气生,气死则火生,反过来也一样。”这种思维过程,蕴涵着丰富的思维辩证法,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之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正象人们远在散文这一名词出现以前,就已经在使用散文讲话一样。”(注:《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 第140页。)不过,这时候人们所进行的思维尽管有辩证思维的成份,但只能称之为自发的辩证思维。因为这种思维还是不系统、不全面、不彻底的辩证思维,或者说,只能是辩证思维的偶尔闪光。这种思维与成熟的自觉的辩证思维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恩格斯指出,辩证思维“只是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完满的发展则更晚得多,在近代哲学中才达到。”(注:《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