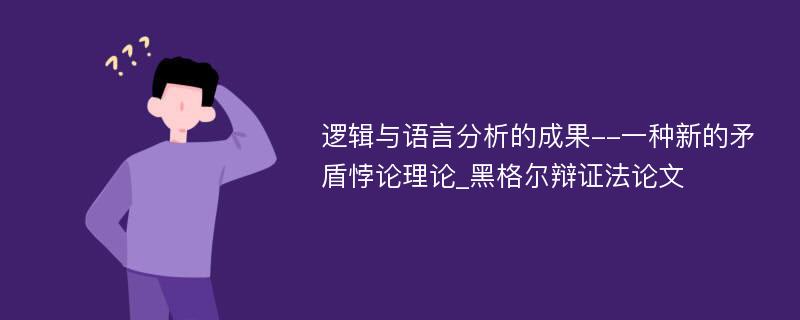
逻辑与语言分析的硕果——推介《矛盾与悖论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悖论论文,硕果论文,逻辑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大陆逻辑学界青年学者张建军教授和香港学者黄展骥教授合著的专题学术论集《矛盾与悖论新论》,最近由一向重视文化积累和学术研究,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读罢全书和一些有关资料,甚感这是一部具有多层面重要意义的高水准学术著作,应当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广泛重视与研究。
《矛盾与悖论新论》(以下简称“《新论》”)编撰完成交付出版之际,正值香港回归祖国之时,两位作者在“前言”和“后记”中均明言以该书纪念“回归年”,表现了两地学者高度的爱国情怀。同时,《新论》的出版,亦为两地学者于“一国两制”环境下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展示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黄展骥先生自幼在港台受教育,后长期在香港做逻辑教学、研究和普及工作。他师承著名哲学家与逻辑学家殷海光先生,而殷先生则师承我国哲学与逻辑泰斗金岳霖先生。在哲学观点上,黄先生曾经坚决拒斥辩证法,是富有代表性的形式派学者。然而,自他在80年代末开始与大陆学界进行学术交流之后,其观点逐步有了颇大的转变,承认辩证学派理论中含藏不少他过去不曾认识的真知灼见。本着“开放、客观、求真”的学术精神,黄先生把自己的研究心得陆续交内地学术期刊发表,得到了包括《人文杂志》在内的十余家著名刊物的大力支持。收入本书的多篇文章,便集中体现了黄先生的这种转变。这些文章曾引发不少内地著名学者一连串的热烈讨论(迄今仍在持续),有力地推进了内地学界“矛盾与悖论”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张建军先生则是内地在“文革”结束后新的历史时期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学者,目前是著名的高等学府南京大学的逻辑学教授。从《新论》可以看出,张先生的知识架构中有浓厚的辩证法背景。在“后记”中张先生坦承,他在逻辑学习与研究过程中有两个始终不能摆脱的“思想情结”——“辩证法情结”和“科学方法论情结”。据笔者了解,在大陆学界“逻辑教学与研究现代化”旗帜下长成的,具有扎实深厚的现代逻辑学养的新生代青年学者中,如此关心当代辩证法之命运者,张先生是最具代表性中的一位。他的突出风格是提倡一种面向逻辑的现代发展的,引入严格的逻辑分析方法的辩证法与辩证逻辑研究。他以悖论研究为“切入视角”研考现代逻辑、现代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并形成了明确的运思指向:“一种建立在现代逻辑、现代科学与哲学发展基础上的新型辩证法学说——‘悖论辩证法’,是辩证法与辩证逻辑理论革新的一个重要方向。”他表示“愿在继续深入考察当代逻辑悖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为此进行不懈的探索。”(《新论》409页)
有如此多层面差异的两位学者能两度联手合作(1992年曾在香港合作出版《矛盾与悖论研究》一书),不但基于黄先生的上述转变,而且基于他们关于逻辑基本法则在人类理性思维中根本地位的共识。这个共识可以说是形式派的一贯立场,黄先生在其转变路程中并没有改变这一立场,而张先生基于其对现代逻辑长足进展的把握而接受并牢固确立了这一立场。这是张先生与许多辩证派学者的一个重要差别。他在《新论》中明言,现代科学、社会与文化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悖论性或类悖论性问题,以及声势颇大的后现代运动对人类理性的冲击,都使得当代比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时代更加迫切地需要辩证思维。然而他又指出,只要辩证思维是一种理性思维,就必须遵循一般逻辑思维的基本法则,否则,只能导致自我消解。他认为,在一个缺乏严密的逻辑思维传统因而缺乏浓厚的理性化氛围的国度中,尤其需要强调这一点。这一理念得到黄先生的强烈共鸣。两位作者站在这样的高度从事矛盾与悖论研究,亦使这部《新论》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新论》一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贯穿全书的“分析风格”。两位作者无论是正面申论自己的学术见解,还是与学界不同意见展开商讨,都始终注意厘清概念,分清层面,追求逻辑上的清晰与融贯。而这种风格正是我国学术文化界所缺乏的。不过,两位作者在学术风格上又有很大的差别,大体说来,张先生更具有逻辑分析学派的风味,而黄先生则更具有日常语言分析的特点。但是,两位作者对于各自不同特色的分析方法是相互尊重而不是相互排拒的,在许多情况下取得了殊途同归的结果。从总体上说,《新论》可称为我国学者运用逻辑与语言分析方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新论》收入的文章(不含附录)绝大多数是90年代的作品,唯一的例外是全书的开篇——张先生写作于80年代中期的《如何区分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讨论评述与刍议》。这篇曾被桂起权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称为“对多年来学术界有关辩证矛盾的各类定义与判别标准,最早最系统的细致辨别和彻底清算”(注:《矛盾、辩证法与逻辑》,载《逻辑与语言学习》1994年第5期。)的鸿文, 迄今仍是笔者所见到的关于区分两类矛盾问题最精细系统的作品。该文把国内众多学者的见解熔于一炉,严格的语义和层面分析归纳出“辩证矛盾”的7个定义及区分两类矛盾的12条标准, 后来学界有关该专题的讨论均无出其右。该文对于“辩证矛盾”三层面(绝对客观层、相对客观层、主观层)的明确划分及作为主观层认知范畴的“辩证矛盾”特征的明晰刻画,构成了此后张先生关于矛盾与悖论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因而,该文的收入为读者研究张先生的新作提供了便利。同时,该文也是黄先生介入辩证法矛盾理论研究的主要“触媒”之一。黄先生在90年代初读到该文后,以其谙熟的常识分析方法对文中提供的各家观点进行了剖析,最后把视角集中于辩证学派公认的“亦此亦彼”说,并提出了试图消解辩证派和形式派之纷争的“可此可彼”说,这就是引起学界广泛瞩目的《辩证派击中形式派“要害”了吗?》一文(《新论》黄先生文组首篇)的核心理念。而“可此可彼”说,亦构成书中黄先生全部新探索的一个基石。
力图把逻辑分析方法引入国内哲学研究,是张先生在《新论》中表现的一个重要诉求。在有关文章中,他以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一篇阐述“辩证矛盾”含义的文章为解剖对象,运用逻辑语法与语义分析方法,令人信服地澄清了在哲学界长期存在的一连串概念、层面混淆问题,显示了逻辑分析的威力。特别是他运用自弗雷格以来逻辑分析学派对于语言层面与思想层面的清楚区分,探讨了两种矛盾的语言形式与思维形式问题。在此基础上,他又运用谓词逻辑工具进一步提出了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的一种无恶性循环的递归性定义,使得在辩证哲学研究中引入逻辑分析方法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有鉴于语言表达对于思维运作不可怠忽的反作用,张先生在上述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拒斥“既是又不是”之类在辩证哲学发展史上产生重大负面作用的“悖论性语言”的主张。(《新论》92页)这个意见恰与黄先生一贯坚持的“拒斥语无伦次”的命名原则相吻合。黄先生还进而提出了把“矛盾”一词单义化(逻辑矛盾),“辩证矛盾”另行命名的主张。(《新论》316 页)而张先生又曾通过“二律背反”概念申论“辩证矛盾”称谓的历史合理性。(注:《科学的难题——悖论》(修订增补本),淑馨出版社(台湾)1994年11月版,第226页。 )究竟如何处理为好,笔者认为学界尚可继续研析。但在实质上承认两类“矛盾”之区别的情况下,如何对它们做出正确区分的考量,就是任何关心辩证法之命运的人所不可回避的。
黄先生独出心裁地把辩证学派的内部分野概括为“鹰”、“鸽”两派,即把20—40年代在辩证学派中盛行的否定形式逻辑法则,把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混而为一的观点视为“鹰派”,而把自50年代以来在辩证学派中占了主导地位的主张区分两类矛盾,使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并行不悖”、“和平共处”的观点称为“鸽派”,并试图论证他的“可此可彼”说同样可以平息辩证派的这种内部纷争。黄先生还透过对几位著名辩证学者新近著作的检视,把主张取消两类矛盾区分的邓晓芒教授,承认这种区分的必要性但主张在特定情况下突破不矛盾律而包容某些逻辑矛盾的桂起权教授,以及突出强调区分两类矛盾却又认为不矛盾律在“质变”思维中失效的马佩教授统称为“新鹰派”。这个界定引发了学界一场热烈论争。虽然《新论》中只收入了张、黄两作者的有关文章,但从中亦可看到整个论争的脉络:在上列三位学者中,只有桂起权先生欣然接受“新鹰派”的称谓,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形式派、辩证鸽派、辩证旧鹰派、辩证新鹰派可以排成一个家族谱系”的重要见解。邓、马两位则坚决拒绝“新鹰派”的称谓。而张建军先生以其逻辑分析的犀利解剖刀剖析论战各方见解,指出邓晓芒先生的观点实质上仍是旧鹰派观点新的再现,而对于鸽派的观点亦需划分新与旧:自认属于鸽派的马佩先生实际上是坚持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初等与高等”关系说,其理论内部具有不协调性的“旧鸽派”的代表。而张先生自认身置其下的“新鸽派”旗帜的特征是:放弃初高等之说,把不矛盾律的普适性贯彻到底,真正把拒斥逻辑矛盾作为辩证思维的一项基本原则,主张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针对桂起权先生曾把黄先生的“可此可彼”说引为新鹰派同道的论点,张先生指出,二者其实貌合神离:新鹰派承认“真(逻辑)矛盾”存在,而黄先生正是为了杜绝“真矛盾”的出现才采取了“可此可彼”这种“技术补救措施”。张先生认为,黄先生的“可此可彼”说与他本人提出的“强化的排中律”在精神上相通,而后者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金岳霖先生。笔者认为,张先生的分析是颇具说服力的,而这场论争的深入展开,势必对我国逻辑哲学与辩证哲学发展的走向,产生长远影响。
悖论研究是两位作者长期探索的专题,由其矛盾观自然引申出来的悖论观及相关研究成就,构成这部著作的主体。黄展骥先生早在60年代初即认真思考了悖论问题,他敏锐地觉察到,从日常语言运用的常识出发,仅使用普通逻辑学与普通谬误学工具便可消解“悖论之冠”——说谎者悖论;而所谓悖论在数学基础理论中出现导致“数学大危机”之论,其实是犯了“假值保留”谬误。这项研究后因故中断。直至十多年前,他看到内地学界先后出版了两部悖论专著:已故杨熙龄先生的《奇异的循环——逻辑悖论探析》(1986年初版)和张建军先生的《科学的难题——悖论》(1990年初版)。治文学出身的杨先生的著作充满丰富的想像力,他十分推崇“亚相容逻辑”(这是张先生的译名,杨先生的译名为“超协调逻辑”,现在学界较通用桂起权译名“次协调逻辑”)的“真矛盾”理论;而张先生的著作则以逻辑学者的严格清晰、脉络分明见长,他在书中强烈否定“亚相容逻辑”学者所自认的“真矛盾”理论的辩证性质,对于一些没有打出“辩证”旗号的解悖方案的辩证性质,却又给予了充分的释示与肯定。黄先生透过这两部书看到辩证学者的观点之间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同时也看到了悖论研究“很具历史性和世界性”的极其重要的价值。这激发他把长期积压心中的见解重新思考并发展,写作并发表了数十篇专题研究论文。这些论文的主要成果已收入与张先生合作的《矛盾与悖论研究》和这部《新论》。前者已得到内地学者的专题研究和高度评价,(注:参见桂起权:《日常语言学派风味的逻辑分析——评黄展骥的“悖论研究”》,载《人文杂志》1996年第3期;张金兴:《独特的研究视角,鲜明的学术个性》,载《哲学动态》1995年第11期;刘粤生:《类比逻辑与悖论》,载《丝路学刊》1994年第3期。)而在《新论》收入的文章中,黄先生又在与内地学者的讨论中多方面发展了其悖论观。比如,他继续运用基于日常语言用法的常识分析法消解“强化的说谎者悖论”,运用被称为“日常语言学派基本精神中国化”的“舍繁取简、返璞归真”两项元方法论原则提出“简朴的悖论定义”,特别是从前述矛盾理论研究成果出发提出了“亦此亦彼悖论”(黄先生以其常识化笔调又名之为“亦人亦猿悖论”),该悖论由辩证派的“亦此亦彼”法则对形式派的“非此即彼”的挑战而构成。黄先生认为它应与“说谎者悖论”并列,同为“悖论之冠”。
收入《新论》的张先生的悖论研究论文,则承袭了《科学的难题——悖论》一书史论结合的风格。以前这部专著对由古及今的悖论研究史特别是本世纪30年代之前当代西方悖论研究的第一次热潮作了全面清晰的评述,而在《新论》中,他又在综融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7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悖论研究的第二次热潮给予系统评论,并对当前西方学界逻辑悖论研究的主动脉作出了“回归自然语言,在语形、语义、语用的统一中深化悖论研究”的概括。为方便读者研究,张先生在阐述其学术观点时提供了许多背景资讯,如在研讨对角线引理、知道者悖论、强化的说谎者悖论与真值间隙论时,都提供了这些理论提出者的原始论述。作为主持两项国家级悖论研究课题的学术领头人,张先生在这一学术前沿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深刻的或富含启发价值的学术创见,例如,他根据悖论研究的最新发展,把通行的逻辑悖论二分法改造为集合论一语形悖论、语义悖论、认知悖论、合理行为一对策论悖论四分法,并建立了它们与辩证存在观、真理观、知识观、行为观的对应关联,他关于“逻辑点的形成与打开”理论的阐述,关于语境敏感解悖方案及“语义学黑洞”实质的分析,以及在这些研究基础上对悖论作为一种特殊的逻辑矛盾之特征的系统申论等等,更使得该书成为国内悖论研究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张先生所倡导的悖论研究的科学逻辑方向,在《新论》中也有突出体现。他把严格意义的悖论分为哲学悖论、逻辑悖论和具体理论悖论(或称科学悖论)三大类,而科学逻辑方向就是对第三大类悖论的统一性、综合性研究。他在《新论》中全面阐发了悖论作为“特殊的反常问题、重要的证伪手段、难得的变革契机”的科学方法论意义,探讨了悖论的发现机理,厘清了科学佯谬与严格悖论的关系,由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与悖论的关联表明了该定理的科学逻辑推论:科学悖论与科学理论的层次跃迁紧密关联,有力地论证了“悖论是解放思想的杠杆”的命题。他对于黑格尔的本质论范畴“同一—差异—对立—矛盾—根据”的思维方法论解读:“确立对象—把握差异—探索对立—实行互补—达成飞跃”,会有许多争议,但这种新颖解读的启发意义不言而喻。
《新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其行文风格。尽管两作者在行文特色上差别很大,但在如下两点是共同的:一是均力图使自己的研究工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吸取,整合各家有益见解,因而书中多数文章参考文献丰富;二是均与学术界老中青学者(包括两作者之间)展开了平等求真而且指名道姓的商讨,很少使用我国学界常见的不知出处之“有人认为”的说法,这也是十分难能可贵而值得大力提倡的。
标签: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逻辑分析法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辩证思维论文; 逻辑与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鹰派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