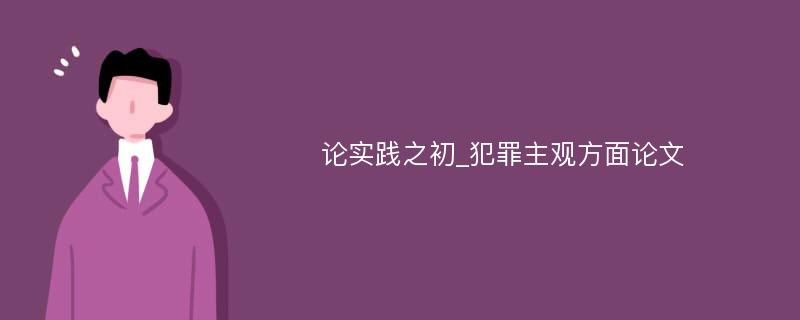
论实行的着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行行为的着手问题是刑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对这一重要问题,学界仍存在不少争议,甚至“被某些刑法学家悲观地认为是‘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① 本文拟结合我国刑法的规定,对着手问题的常见学说进行评析,以求学界批评指正。
一、主观说及其评析
主观说以主观未遂论为基础,认为由于犯罪是行为人反社会性格的表现,由于未遂犯的处罚根据是行为人以其行为体现出来的对法的敌对意思,因此当行为人的犯罪意思通过行为客观地、确定地表现出来时,即可认定为着手。法国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主要采此说,② 赞同主观主义的学者通常也采此说。如牧野英一认为:“犯意的成立,由于其遂行的行为而确定地被认识时,于兹可为着手”;宫本英修认为:“犯罪实行的着手是有完成力的犯意的表动,这种犯意的表动应解释为犯意的飞跃表动,详言之,即实施了一段飞跃的紧张的犯意的表动”;木村龟二认为:“行为表示出行为者的犯罪意思没有二义、不可能取消的确实性的场合,是着手。”③
对于主观说,多数学者持批判态度,认为该说存在理论本身有破绽、判断标准不明确、使着手的认定过于提前、理论根基错误等问题,④ 并且过于注重社会防卫,也有影响人权保障之虞。⑤ 但也有学者认为,“主观说着眼于从行为者的主观要素认定实行的着手,而忽视了客观的要素,这种观点确实是片面的,因而已为今日的学者们所不取;但它也有不能忽视的合理因素。按照该说,认定实行的着手,应当考虑行为者的主观的因素——故意的内容,只要不把它绝对化,可以说这种主张是妥当的,它正好弥补客观说的不足,也不应加以否定。”⑥
笔者认为,从总体上看,主观说是不足取的,它的确存在使着手的认定过于提前的问题,因为许多在社会观念上被认为是犯罪预备的行为,根据该说完全可能由于确定地表现出行为人的犯罪意思而被认定为已经着手,因而不符合立法与司法实际。并且,着手的认定说到底无非是一种犯罪构成要素的认定,因为着手作为实行行为的起点,认定了着手即相当于认定了实行行为,而对实行行为的认定当然不能脱离客观构成要件,脱离客观构成要件的限制,仅从犯罪意思方面去认定着手,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但是,主观说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其重视行为人的主观意思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脱离人的认识和意志,就不可能有犯罪行为,就缺乏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并且实际上,如后文所述,客观说与折中说也不可能舍弃主观说的合理内容,不可能不考虑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因为构成要件行为的性质,取决于行为的主观面而非客观面。至于对主观说的其他几点批判,大体上并不成立。
第一,认为主观说偏离了其根据行为人的意思的危险性去认定着手的一贯立场而使用“遂行”、“飞跃”等概念,实际上是偷偷地在客观方面谋求着手的认定,因而理论本身有破绽的批判并不成立。因为任何主观主义者,无论其思想如何坚决,都不至于认为刑法惩罚的是脱离行为的纯粹的犯罪意思,更不至于认为可以脱离外部行为去认定犯罪意思,即便认为刑法惩罚的是行为人而不是行为,行为只是行为人危险性格的表现,也总得有“行为”这一“表现”存在。同理,主观说使用“遂行”、“飞跃”等概念,不过是表明要根据客观行为去认定犯罪意思,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着手是指犯罪意思的着手而非实行行为的着手。
第二,认为主观说的判断标准不明确的批判也不成立。因为判断标准不明确实际上是包括客观说与折中说在内的所有学说的通病,并非主观说的专利。例如,实质客观说中的结果危险说认为,只有“发生了‘作为未遂犯的结果的危险性时’,即‘侵害法益的危险性达到了具体程度(一定程度)时’,才是实行的着手。”⑦ 其所谓发生了一定危险、危险性达到一定程度,同样是极不明确的,对于危险达到何种程度即已跨越预备阶段进入实行阶段根本无法回答。究其原因,在于着手本身具有相当的模糊性,究竟在犯罪发展过程的哪一时间段可以认定为已经着手,不可能如数学般精确,更多的还需根据社会通常观念具体个案具体分析,理论上所能做到的,只是提出一个大致的标准而非代替司法实践进行精确的判断。
第三,认为主观说的理论根基在于主观主义,因而理论根基错误的批判同样不足取。因为是采客观主义还是采主观主义,主要是个人偏好问题,不能因为自己赞同客观主义就认为别人的理论根基有误。实际上,主观主义并非毫无用处,许多客观主义解决不了的问题,主观主义可以轻易地解决。例如,对于长期困扰客观主义的原因自由行为、间接正犯等特殊犯罪形态的着手问题,采用主观主义可轻易解决。
二、客观说及其评析
客观说以客观未遂论为基础,认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在于行为侵害法益的危险性,即行为实现构成要件结果的高度或然率,而对于如何理解行为具有法益侵害的危险性或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又有形式客观说与实质客观说之分。
(一)形式客观说
形式客观说认为,开始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时是着手。如小野清一郎认为:“犯罪的实行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着手’即是该符合构成要件行为的开始,或多少实现了一部分。”⑧ 我国通说亦采此说,认为“所谓已经着手实行犯罪,是指行为人已经开始实施刑法分则规范里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犯罪行为。”⑨ 不过,也有持形式客观说者认为,不仅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时是着手,而且实施与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有密接关系的行为时也属于着手,但由于这种观点容易使实行与预备的界限变得模糊,因而难以得到赞同。
形式客观说受到持实质客观说者的诸多批判。批判之一是,说实行的着手是指开始实施构成要件行为,实际上并未回答什么是着手,即对于什么样行为才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并未说明。批判之二是,根据形式客观说不可能区分预备行为和实行行为,因为它并未提出认定实行行为的标准。⑩ 批判之三是,形式客观说理论根基有误,因为它以行为无价值论为基础,并以规范违反说为犯罪本质。批判之四是,形式客观说可能使着手过于提前,例如为了诈骗保险金而开始杀人放火时即可认为是保险诈骗罪的着手,也可能使着手过于延后,例如认为只有扣动扳机时才是枪杀行为的着手。(11)
我们认为,以上批判均值得商榷。
第一,认为形式客观说实际上并未回答什么是着手,是对该说的误解,因为该说明确提出了应以开始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为着手。至于什么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由于各种犯罪的构成要件各不相同,当然不可能一一加以描述,而只可能提出一个总的标准。不能因为实践中仍需具体认定某种行为是不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就否认形式客观说的合理性。该批判实际上混淆了抽象层面的着手标准与具体层面的着手认定之间的层次。如果这种批判能够成立,则这种批判同样适用于实质客观说,因为实质客观说同样只能提出诸如“开始实施具有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性的行为”、“行为已经具有侵害法益的具体的紧迫的危险”等抽象标准,而不可能提出更加具体的标准,在判断标准的抽象空洞上,实质客观说与形式客观说实际上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
第二,认为根据形式客观说不可能区分预备与实行不符合实际。首先,由于受著名学者小野清一郎、泷川幸辰、团藤重光等人的影响,形式客观说曾是日本的主流学说,其司法实践也曾长期根据这种学说区分预备与实行;我国刑法通说及司法实践也一直采用形式客观说,并未发生预备与实行不分的问题;(12) 即使采取主观说,比如法国,也不影响正确区分预备与实行。其次,之所以根据形式客观说也能区分预备与实行,是因为从根本上讲,任何抽象的判断标准都必须辅之于具体的判断、权衡,而这种判断、权衡主要是根据社会通常观念进行的,抽象的判断标准本身并不能也不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各种学说莫不如此。即使是学说主张最彻底的实质客观说的结果危险说,其“行为必须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紧迫危险时才是着手”也只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标准,仍必须辅之以具体的判断。例如,在持枪跟踪被害人以伺机杀害的例子中,是跟踪还是掏出手枪、开始瞄准或开始射击时才具有发生结果的紧迫危险,不能不考虑具体案情。尽管通常情况下应以开始瞄准为着手,但如果是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则可以说瞄准时还不具有紧迫危险,因为只要还没有开始射击,就极可能被其他行人挡住视线而重新瞄准;而如果是跟踪被害人进入一条无人且无法通行的死胡同,则一进入该胡同即可认为具有紧迫危险,因为从掏枪到瞄准到射击不过是一两秒之内的事,不可能因为这一瞬间间隔而影响危险的程度。因此,对于判断具体行为有无导致结果的紧迫危险,实质客观说本身并不能有所作为,最终仍得根据社会通常观念这一甚至更加空洞的标准而定。再次,形式客观说之所以极其空洞却能在我国长期处于通说地位,是因为它一方面最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一方面正是因为抽象空洞才无懈可击,正如说“物质就是客观实在”无懈可击一样。正因为它只是一个抽象标准而无具体内容,才使其最具涵括力,能够包容最错综复杂的情况。反之,如果硬要提出一些更为具体的标准,既不现实也容易导致错误。
第三,以所谓结果无价值论、法益侵害说来批判形式客观说理论根基错误更是不妥。因为结果无价值论、法益侵害说本身就是一种极具争议的学说。首先,不仅刑事违法,任何违法都是侵害法益的,用法益侵害并不能说明刑事违法与其他违法的本质区别,甚至不能说明不同犯罪的刑事违法之间有无不同,最终仍得以行为是否违反刑法规范为区分标准。其次,从过失致人重伤与过失致人死亡的区别来看,可以认为过失违法的本质在于结果无价值,因为正是先发生了重伤或死亡结果,才能考虑行为人是否违反了不得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注意义务,而不是先认定行为人违反了哪种注意义务再认定他构成了何种犯罪,也即过失犯的成立及其性质的确是由损害结果决定的。但是,故意杀人罪不仅惩罚发生了死亡结果的既遂,而且惩罚未发生死亡结果的未遂、中止以及根本就未实施杀人行为的预备,故意杀人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刑相差极大,能说违法性的本质仅在于结果无价值吗?再次,之所以处罚未遂犯是因为行为人有对法的敌对意思,明知不当为而为之,为了预防犯罪,有必要从规范上价值上对行为人进行伦理道义谴责,而不是因为有发生结果的危险才处罚。因为既然是未遂犯,其没有造成结果、没有侵害法益就是绝对的,如果仅从保护法益与结果无价值立论,必然不可以处罚,正如未被枪击中的被害人在民事上不会获得分文赔偿一样。认为有侵害的危险也是一种侵害、甚至认为“危险状态”也是一种犯罪结果,不过是自圆其说而已。
第四,认为形式客观说会使着手的认定过于提前或者延后,更是对该说的曲解。因为形式客观说只是提出了“开始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这一极其抽象空洞的标准,对于认定具体行为是预备还是实行,可以说一无用处,必须辅之于更具体的判断标准才能发挥作用,并且无论判断结果如何,都可以归之于是否开始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之内,因此它本身不可能使着手的认定过于提前或者延后。相反,实质客观说更容易使着手的认定过于提前或者延后,因为它仅考虑行为或结果的危险性而不受构成要件行为性质的限制。至于以为了诈骗保险金而开始杀人放火以及为杀人而扣动扳机之例来论证形式客观说的不合理,可以说从根本上搞错了方向。因为杀人放火是不是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并不在于它对保险诈骗罪的保护法益有无现实的紧迫的侵害危险,而在于它属不属于保险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行为,而对于判断某行为是否属于某种犯罪构成要件行为起决定作用的,是行为的性质而不是行为的危险。例如,尽管盗窃1元钱不会构成盗窃罪,但不可否认其仍属于盗窃行为,这是行为性质使然。在为诈骗保险金而杀人之例中,由于生命权重于财产权,其杀人行为即使对财产权尚无具体紧迫的侵害危险,但却已经侵害了比财产权更为重要的人的生命权,若从危险的性质及程度来看,没有理由不认定为已经着手,但问题在于,杀人行为并不属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因而不可能属于保险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杀人与诈骗在性质上的区别,是天然地决定的,并不因刑法是否把它们规定在同一种犯罪中而有所改变;换言之,杀人行为天然地不可能侵害保险诈骗罪的保护法益,诈骗行为也天然地不可能侵害杀人罪的保护法益,决不是侵害的危险程度高低问题。至于这里的杀人放火行为可以作为保险诈骗罪的预备行为,是因为预备行为本身没有什么定型性,凡是为实行某种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都可作为该种犯罪的预备行为,而不是因为杀人放火行为也属于一种保险诈骗行为。至于批判形式客观说认为只有扣动扳机时才是枪杀行为的着手也是不正确的,的确不排除个别形式客观说者会这么认为,但认为所有形式客观说者都这么认为,就毫无根据了,因为形式客观说除了就着手的认定提出一个总的判断标准以外,并未就具体犯罪一个一个地提出标准,更不可能就某一犯罪的某一种具体行为提出标准。再说,既然从掏枪到瞄准到扣动扳机很可能不过是一两秒之内发生的事,显然这一两秒钟不可能影响行为对法益侵害的危险性程度,为什么不能以准备掏枪或者扣动扳机时为着手,而一定要以瞄准为着手呢,这难道不自相矛盾吗?
(二)实质客观说
实质客观说认为,应从实质观点考察实行的着手时期,以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或法益侵害的现实危险为着手的标准。对于实质客观说的分类,也有多种观点,有人认为包括必要行为说和现实危险性说,有人认为包括实质的行为说和结果说,有人认为包括现实的危险说与具体的危险说,(13) 有人认为包括行为危险说和结果危险说。(14) 从具体内容来看,必要行为说、实质的行为说、现实的危险说都强调行为对实现构成要件的危险性,因而大致相当于行为危险说,现实危险性说、结果说、具体的危险说都强调发生结果或法益侵害的具体紧迫危险,因而大致相当于结果危险说,因此,我们在此采取陈子平的分类。其中,行为危险说认为,“实行的着手是开始包含着具有实现犯罪的现实危险性的行为”;(15) 结果危险说认为,未遂犯是具体危险犯,只有当行为发生了作为未遂犯结果的具体的、迫切的危险时,才是着手。(16) 即行为危险说重视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性的行为,结果危险说重视行为已经造成的作为未遂犯处罚根据的危险状态(危险结果本身)。
该说受到的批判主要有:第一,该说的判断基准不明确。因为危险是一种有程度或幅度的概念,从侵害法益的很小可能性到很大盖然性之间,往往具有很大幅度,达到哪一程度才可以作为实行的着手,并不明确,况且,脱离形式判断的限制,其实质判断标准不可能明确。第二,该说容易扩大未遂犯的处罚范围,因为对于许多并不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由于没有形式判断的限定,也可能因为被认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具体紧迫危险而受到处罚。(17) 第三,若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意思或犯罪计划,而想从纯粹客观面去认定着手,实际上行不通。(18)
笔者认为,以上第一点批判大体上是不成立的,如上文所述,作为判断着手已否的总体标准,任何学说都不可能足够明确,即使如形式客观说一般有构成要件行为的限制,仍不可以说是足够明确的,故不宜以明确已否作为取舍依据。以上第二点第三点批判则是成立的:其一,由于脱离构成要件行为这一行为性质的限制,该说很容易使着手的认定过于提前或者延后,因为一方面,即使是为了犯罪而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如果被认为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具体紧迫危险,或者感情上被认为很有处罚的必要,也可能认定为实行行为;另一方面,即使已经开始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如果被认为尚未达到值得作为未遂犯处罚的发生结果的具体紧迫危险,也只能认定为预备行为,从而有随意认定预备与实行之嫌。其二,由于行为性质取决于犯罪意思而非客观行为,故不可能脱离行为人的犯罪意思或犯罪计划去认定行为的危险性。例如,甲朝乙开了一枪,如果甲是以杀人故意而开枪,则为杀人实行的着手,如果甲只是开玩笑而没有杀意,则谈不上杀人实行的着手。其三,判断着手已否不可能仅考虑客观要素而不考虑主观要素。正如黄荣坚所言,“如果从纯粹客观的角度来看未遂的行为,其着手永远谈不上犯罪行为的着手,因为一个人做一个行为而未实现其预想的结果,客观上永远有未实现的原因。……而一个客观上无法造成结果的行为,客观上自然不是在实施不法(侵害)行为。”(19)
此外,该说尚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该说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因为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有责行为,或者说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在判断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属于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时,必须严格依据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而定,否则极易出入人罪而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而着手是实行行为的起点,着手的判断实际上是实行行为的判断,实质上也是一种构成要件符合与否的判断,只是判断的要素比一个完整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判断要少而已,故判断时不应抛弃犯罪构成要素而仅仅分析行为对法益有无侵害的危险及危险程度。离开“构成要件行为”这一行为性质的限制,则或者将非构成要件行为(主要是预备行为)认定为实行行为,或者将部分构成要件行为认定为非实行行为(也主要是预备行为),无异于从根本上抹杀了非实行行为与实行行为的质的区别,是违背犯罪构成理论的。不可否认,行为发生了侵害法益的具体迫切危险可能刚好与行为符合基本犯罪构成相重合,但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重合的,因为提出实质客观说的初衷,就在于将那些形式上符合构成要件但被认为不值得作为未遂犯处罚的行为排除在未遂犯处罚范围之外,这在结果危险说中至为明显。
第二,该说不可能单独适用。因为在判断着手已否之前,必须首先确定所要判断的是何种犯罪的实行行为的着手,这显然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而单纯地以行为或结果的危险性去判断。换言之,必须首先确定应以哪种犯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为标准,才能判断具体行为是否符合这种犯罪构成、是否属于这种犯罪的实行行为以及着手已否,这显然不能脱离构成要件行为这一形式的限制。例如,必须首先确定具体行为的性质是属于盗窃还是杀人,才能考虑该盗窃或者杀人行为的着手已否,而对于诸如在雷雨交加之际怂恿被害人外出致其被雷击死之类的例子,由于无法事先确定它属于何种犯罪性质的行为,也就不可能去讨论它的着手已否。
第三,该说赋予着手标准过重的负担,因为该说意在通过考察行为有无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性甚至是否已经对法益造成了具体紧迫的侵害危险来限定实行行为的范围,这与其说是为了区分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不如说是为了区分可罚的未遂与不可罚的未遂及不能犯,实质上是企图在着手的认定标准中一并解决可罚的未遂与不可罚的未遂及不能犯的区分问题。对于可罚的未遂与不可罚的未遂及不能犯,形式的客观说并非不予区分,并非认为着手还包括不能犯的着手,只是认为这不应是着手理论所应解决的问题,而是其他理论所应解决的问题而已。换言之,提出着手理论的目的,应在于区分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不在于区分可罚的未遂与不可能的未遂甚至不能犯。对于未遂犯与不能犯的区分问题,自有不能犯理论去解决;对于可罚的未遂与不可罚的未遂的区分问题,自有实质的构成要件理论、可罚的违法性等理论去解决,在我国甚至还可以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为由,直接否认行为的犯罪性,根本无需通过将实行行为解释为预备行为等比较极端的方式去否定行为的可罚性,故不应将着手的判断标准与未遂的处罚范围问题混为一谈。
第四,结果危险说认为只有当行为产生了侵害法益的具体紧迫危险(发生了危险结果)时才是实行行为的着手。(20) 其缺陷至少有三:其一,认为不管行为在性质上是否属于构成要件行为,只要它还没有产生危险结果,就属于预备行为,实际上是“规范地”将构成要件行为一分为二,将前半段划入预备行为,将后段划入实行行为,而在行为中间寻找着手点,这到底是在寻找实行行为的着手还是在寻找危险结果的着手,令人疑惑。其二,认为只有发生了危险结果才是着手,是从根本上否认从着手实行到行为造成紧迫危险之间存在任何时间间隔,实际上是将行为的着手与行为所造成的危险状态混为一谈,也混淆了着手与否与可罚的未遂犯成立与否这两种不同的判断。其三,在间隔犯场合,结果危险说会得出不可思议的结论。例如,在甲为杀死乙而暗中向乙的药酒中投放毒药一例中,结果危险说认为,只有在乙将要喝下药酒时,才会产生死亡的紧迫危险,才可认定着手,在此之前只能算预备。(21) 也就是说,尽管甲只实施了投放毒药这一行为,但他的行为属于杀人的预备还是实行,并不取决于他的投毒行为,而取决于乙将要喝下毒药与否!这与其说是在判断甲的实行的着手,不如说是在判断乙的死亡的着手。而对于相似例子,日本有学者作了另外解释,认为投毒行为是预备行为,但投毒之后就产生了取走有毒物的作为义务,在被害者想喝而拿到手上以后,违反这种作为义务就变成了不作为杀人的实行行为,因此,投毒者对同一案件中被毒死者成立杀人既遂,对因为未喝毒药而未被毒死者成立杀人预备。(22) 如此则是否所有的故意作为犯都同时违反了禁止规范与命令规范,即在违反禁止规范而实施了犯罪行为之后,又违反了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呢?其之所以不像我国上述观点那样在本来没有行为的阶段寻找实行行为,是否因为觉得这样做确有不妥,因而在作为与不作为之间另辟蹊径?其实在此例中,刑法所禁止与评价的,都是投毒行为,并非投毒之后取走毒药或者静观被害者死亡的行为,抛开作为刑法禁止与评价对象的投毒行为,在被害人将喝未喝之际认定着手,虽然有坚持一己之见的痛快,却违背了基本的论理常识。
三、折中说及其评析
折中说认为,认定着手时应当一并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与法益侵害危险的客观方面,认为根据行为人的整体计划,当法益侵害的危险性存在时,即为实行的着手,其突出特点在于强调行为人的犯罪计划。其中,主观的客观说认为,“应以行为人的‘整体的计划’为基础,对构成要件的保护法益造成直接危险的行为明确地表现出行为人的犯罪意思时,就是实行的着手”,判断的重点在于主观面;个别的客观说认为,“从行为人的整体犯罪计划来看,侵害法益的危险性迫切时,就是着手”判断的重点在于客观面。(23)
需要说明的是,许多学者所主张的折中说,实际上仍是形式客观说,因为他们的学说并不强调行为人的犯罪计划,而是建立在误认为主观说与客观说均片面强调主观或客观而“割裂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有机联系”的基础上。实际上,主观说并不排斥客观行为,因为要根据客观行为去表现、认定主观犯意;客观说也不否认主观犯意,因为行为是主客观两方面的统一体。正如形式客观说者小野清一郎所言,“我的观点,要说是客观说的话,也是不排除行为主观方面的‘客观’;构成要件理论,就是在贝林格、M·E·麦耶尔那里,也是这种意义上的客观说。……犯罪的‘实行’,在其主观方面包含有对结果的认识和对结果发生的意志。未遂犯和既遂犯在主观方面是完全相同的。”(24) 大塚仁也认为,“这可以看成是属于实质的客观说的一主张,但我同时也想主张:基于行为人的犯罪意思的那种行为的开始才是实行的着手。”(25) 而这一问题在有些学者之间是以判断行为或结果的危险时应否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来展开的。赞成者认为,由于实行行为是主客观的统一体,不考虑主观方面并不实际,只是仅需考虑故意过失就够了,不需要考虑故意过失之外的行为人的意图、犯罪计划以及性格的危险性;(26) 反对者则认为,“(若考虑主观方面)实质上是一种折中说,应当直截了当地明确其旨趣”。(27) 修正客观说则认为,危险性的判断,除外在行为与外在情况之外,行为人的意图、计划及危险性格均应考虑。我国虽有学者同时批判主观说、客观说与折中说而主张主客观有机统一说,但其观点是建立在误认为三说均割裂了主观与客观的联系的基础上,其主张的实际上仍然是形式客观说。(28)
对于折中说,批判者认为,第一,犯罪计划并非主观的违法要素,考虑犯罪计划没有理论根据;第二,根据折中说,只有完全查明证实了行人的犯罪计划才能认定着手,这极难操作;第三,该说存在与主观说、实质客观说同样的缺陷,例如判断行为何时才具有侵害法益的迫切危险就不够明确;(29) 第四,强调犯罪计划既有欠明确也脱离实际,因为许多突发性犯罪并没有什么犯罪计划。(30)
我们认为,以上对折中说的批判意见大体都能成立,并且由于犯罪计划并非犯罪构成要素,强调犯罪计划实际上是主张认定着手时必须考虑构成要素之外的因素,既违背犯罪构成原理又容易出入人罪,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因此折中说并不足取。
四、综合客观说之提倡
如上文所述,主观说、实质客观说及折中说均由于具有种种缺陷而难以担当着手标准的重任,形式客观说也由于抽象空洞而饱受批判。那么,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意大利1889年刑法典曾区分预备和未遂,以是否“着手执行”作为两者区分的标志,但1930年刑法典则取消了这种区分,也不再以“着手执行”作为未遂的法定特征,而首创了以“行为的明确性”和“行为的适当性”作为可罚行为的起点的立法模式。(31) 受此启发,我国也有学者试图抛弃传统的着手理论而创立所谓“可罚行为的起点”理论,(32) 但其仍是从主客观两方面去限定所谓可罚行为的起点的,并没有什么新意,况且否认预备与未遂的区分,也与我国立法和司法实际不符。为此,我们赞同以形式客观说为基准、以实质客观说为补充的综合客观说,理由如下:
首先,如同犯罪构成理论只能为犯罪的认定提供一个抽象的标准,而不可能就具体个案一一指出它是否符合某种犯罪的犯罪构成一样,着手理论所应提供的,也只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标准,而不是可以代替个案分析的灵丹妙药。因此,指责学说的抽象空洞是不对的,要求着手理论能够简单地套用于具体案例是对理论的误解。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理论都是抽象空洞的,并且这些理论在具体运用时都必须以一些甚至比理论本身更为抽象空洞的标准为补充,例如一般人的认识经验、社会通常观念、公平正义、国民的预测可能性等,舍弃这些抽象空洞的理论与补充标准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事物本身的复杂多样性及人类思维的特点所决定的。例如,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中对于相当不相当的判断,就不可能找到具体的规则,最终还是得回归到社会通常观念上去。(33) 在这一点上,形式客观说之所以饱受批判而又无往而不胜,至今仍在我国占据通说地位,正是因为它仅提出了一个最符合犯罪构成原理的基本标准而未企图提出一些更具体的标准。
其次,在我国不存在采用实质客观说的必要。这除了实质客观说具有种种缺陷之外,还具有以下原因。
一方面,在我国没有将预备性质的行为认定为实行行为的必要。在日本,由于其刑法只规定处罚内乱、外患、私战、放火、伪造货币、杀人、强盗、以勒索赎金为目的的略取或诱拐(相当于我国刑法中的绑架罪)等八种犯罪的预备行为,因而对于其他犯罪的预备行为,无论从实质上看多么值得处罚,都由于法无依据而不能处罚,因此,作为现实的选择,要么放任这些行为逃脱处罚,要么承认“与构成要件密接的行为”、“从整体上看属于构成要件的行为”等与形式客观说自相矛盾的观念,要么以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性为由直接认定为未遂犯。而在我国,由于刑法原则上规定处罚所有犯罪的预备行为,因此对于那些从实质上看值得处罚的预备行为,完全可作为预备犯进行处罚,没必要大费周折地将其认作实行行为。
另一方面,在我国也不存在将实行行为认定为预备行为的必要。
其一,对于那些从实质上看不值得处罚的未遂行为,我国刑法一则有第13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出罪规定,二则对于大多数犯罪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方式,导致大量的犯罪未遂行为可以很自然地不受处罚。而日本刑法由于没有类似规定,因而对于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实质上被认为不值得处罚的行为,不得不以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实质的构成要件等理论作为补救,甚至像实质客观说那样,直接将实行行为认定为预备行为。显然,由于立法规定不同,我国没有必要采取这种违背犯罪构成原理的极端方式。
其二,对于不能犯与未遂犯的区分,我国理论与司法实践长期采用抽象危险说,除了认为迷信犯不可罚之外,并不认为其他不能犯不可罚,实际上相当于否认了不能犯的存在。(34) 这与日本通说为具体危险说有很大不同。况且,即使同样采用具体危险说,也不是必须在着手理论中一并解决未遂犯与不能犯的区分问题,在诸如于雷雨交加之际怂恿被害人外出致被害人被雷击死之类的例子中,否认行为的可罚性,也并不是通过将行为看作预备行为,而是直接否认行为的实行行为性或犯罪故意来达到的;这种客观上危险性极低的行为,不仅不存在着手实行的问题,而且也不存在预备的问题,认为它永远是预备行为同样不妥。因此,企图在着手标准中一并解决未遂犯与不能犯的区分问题,是将论域不同的理论搅和到一起,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导致新的混乱。
再次,形式客观说虽然抽象空洞,但它是唯一符合犯罪构成理论、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也提出了符合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开始实施构成要件行为这一标准,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言是“什么也没说”或者“割裂了主观与客观的联系”;实质客观说虽然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嫌,但毕竟为如何认定着手提出了相对明确具体的标准,无疑可作为形式客观说的补充。因此,我们应当首先肯定形式客观说的基准地位,肯定“以开始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为着手”这一命题的科学性,至于如何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构成要件行为,除了受该行为本身性质的限制之外,不妨参考实质客观说的判断。例如,在扒窃案中,行为人从靠近被害人,到用手触摸被害人衣服口袋以试探口袋中有无财物,到决定扒窃而将手伸向被害人口袋,根据形式客观说,无疑应以开始实施盗窃行为为着手,但是具体到那一阶段的行为才可认定着手,则不妨参考实质客观说的内容,而从实质客观说来看,决定扒窃而将手伸向被害人口袋之时即具有侵害法益的具体紧迫危险,即可认定为着手;又如,在前述枪杀一例中,行为人是一跟踪还是掏出手枪、开始瞄准或开始射击时才可认为已经开始实施枪杀行为,不妨参考实质客观说的结论,以行为是否具有侵害法益的紧迫危险而定。但无论是在哪一阶段认定着手,都可解释为已经开始实施了构成要件行为,而不是如实质客观说所批判的,是在构成要件行为开始之前或者之后认定了着手,认为形式客观说者一定会认为枪杀行为是以扣动扳机为着手、扒窃行为是以触摸到被害人财物为着手,不过是实质客观说者的误解。因此,在综合客观说看来,着手虽是一个确定的点,但却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僵化的点,这一着手时点的确定,并不排斥考虑其他因素,并不排斥实质客观说乃至主观说与折中说的合理内容,但最根本的,恐怕还是社会通常观念这一取决定作用的因素。
最后,之所以不强调加入主观说及折中说的合理内容,是因为综合客观说本身就是一种主客观相统一的学说,其中必然包括犯罪故意等内容。因为着手是实行行为的着手,实行行为又是在主观犯意支配下实施的,并且实行行为的性质,例如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还是过失致人死亡,本身是由主观犯意决定的,因此,说“已经开始实施构成要件行为”,当然是指开始实施主观客相统一的实行行为。此外,实行与着手中的所谓“构成要件行为”,确切地说,是指“基本构成要件行为”,因为预备犯也有其独立的犯罪构成,也有其“构成要件行为”,本文只是为了表述方便,而从通说使用“构成要件行为”来指称“基本构成要件行为”。
五、综合客观说在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如前所述,综合客观说认为在判断是否着手时应以形式客观说为基准,以实质客观说为补充,强调着手是指开始实施构成要件行为。因此,在适用时应特别注意认定某种行为是否属于构成要件行为。一些实质客观说者之所以老是认为形式客观说不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存在误解。
例如,对于投递恐吓信要求被害人于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地点接受奸淫的行为,有观点认为行为人虽已实施了作为强奸罪构成要件行为的胁迫行为,但由于该行为对被害妇女的性法益的侵害危险还不紧迫,因而仅属于预备行为;(35) 另有观点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无论侵害法益的危险是否紧迫,都已经属于实行行为而非预备行为。(36) 实际上,两者都误解了作为强奸罪实行行为之一的胁迫。由于只有当场以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才足以压制被害人的反抗以便当场实施奸淫,故只有这种胁迫才属于强奸罪中的胁迫,除此之外的胁迫都不属于强奸罪中的胁迫,正如只有当场以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的胁迫才属于抢劫罪中的胁迫,而非一切形式的胁迫都属于抢劫罪中的胁迫一样。对这一点,考虑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胁迫的区别就很清楚了。或许有人会问,如此界定强奸罪、抢劫罪中的胁迫,不正是考虑了胁迫行为对法益侵害的紧迫危险性,因而不正是实质客观说的观点吗?决非如此。这里所考虑的,是行为本身是否具有作为实行行为的资格,而非行为对法益有无具体侵害危险,而这一资格是在进行着手判断之前就必须判断的,因为着手是实行行为的着手,对于危险性极低的行为,例如强迫被害人乘飞机旅游致被害人在旅游途中摔死,一开始即应否定其作为实行行为的资格,而将其排除在着手已否的判断范围之外。
又如,对于诸如诬告陷害罪、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诽谤罪等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并列规定在同一罪状中的犯罪,经常被人误作复行为犯,即认为这些犯罪的实行行为是由捏造行为和散布、诬告、诽谤行为组合而成的,因而引发应以开始实施哪一个行为为着手的激烈争论。(37) 其实,这些犯罪中的捏造行为只是一种预备性质的行为,根本不能与告发或者散布虚假事实等直接侵害法益的实行行为相提并论,自然应以开始实施告发或者散布虚假事实的行为为着手,因此,应特别注意区分规定在同一罪状中的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此外,在前文论述的为了诈骗保险金而杀人放火之例中,杀人放火显然属于保险诈骗罪的预备行为,并不因为出现在保险诈骗罪条文中就变成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否则,实行行为就根本没有任何质的规定性可言了。
再如,对于原因自由行为与间接正犯的着手问题,争议也较为激烈。但是,既然它们与通常的直接故意犯罪在行为构造及犯罪形态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为什么一定要将着手问题与责任能力问题捆绑在一起呢,甚至,为什么一定要认为这些犯罪形态也有实行行为从而有着手问题呢?如果一定要认为它们也有实行行为,也应认定着手已否,则也应当将着手问题与直接实施者的责任能力问题分开而论,因为这完全属于两个不同论域的问题。从而,原因自由行为与间接正犯中的实行行为,也应当与通常犯罪中的构成要件行为一样,例如,仍然是故意杀人罪中的杀人行为、盗窃罪中的盗窃行为,而不是之前的饮酒行为或唆使他人犯罪的行为,认为形式客观说者一定会以饮酒行为或唆使他人犯罪的行为作为着手,(38) 又是一种想当然之见或以偏概全之见,不仅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头上,而且曲解了构成要件行为理论。
因此,在具体运用综合客观说以判断着手时,应当特别注意实行行为本身的质的规定性,不应将一些根本不属于实行行为的行为当作基本构成要件行为,否则必然影响判断结论的正确性,甚至因此否认综合客观说的合理性。
注释:
① [意]杜里奥·帕多瓦尼著:《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② 参见[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著:《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4-235页。
③ 参见马克昌著:《比较刑法原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3页。
④ 参见张明楷著:《未遂犯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2-54页。
⑤ 参见陈子平著:《刑法总论(下)》,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2页。
⑥ 马克昌著:《比较刑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6页。
⑦ 张明楷著:《未遂犯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⑧ [日]小野清一郎著:《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王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⑨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页。
⑩ 参见马克昌著:《比较刑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0页。
(11) 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86页。
(12) 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页。
(13) 参见马克昌著:《比较刑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0-532页。
(14) 参见陈子平著:《刑法总论(下)》,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3页。
(15) [日]大塚仁著:《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0页。
(16) 参见张明楷著:《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页。
(17) 参见张明楷著:《未遂犯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2-63页。
(18) 参见林山田著:《刑法通论(上册)》(增订十版),林山田出版发行,2008年版,第468-469页。
(19) 黄荣坚著:《基础刑法学(下)》(第3版),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522页。
(20) 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86页。
(21) 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页。
(22) 参见[日]西原春夫著:《犯罪实行行为论》,戴波、江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23) 参见张明楷著:《未遂犯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3-64页。
(24) [日]小野清一郎著:《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王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25) [日]大塚仁著:《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0页。
(26) 参见[日]大谷实著:《刑法总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
(27) [日]西原春夫著:《犯罪实行行为论》,戴波、江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28) 参见赵秉志主编:《犯罪总论问题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页。
(29) 参见张明楷著:《未遂犯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6-67页。
(30) 参见马克昌著:《比较刑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6页。
(31) 参见黄风译:《意大利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32) 参见高艳东:“着手理论的消解与可罚行为起点的重构”,载《现代法学》2007年第1期。
(33) 参见许玉秀著:《主观与客观之间》,许玉秀出版发行,1997年版,第270页。
(34) 参见张明楷著:《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页。
(35) 参见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364页。
(36) 刘仕心:“论刑法中的复合危害行为”,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4期。
(37) 参见王明辉:“复行为犯研究”,吉林大学2006届博士论文,第77页。
(38) 参见张明楷著:《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