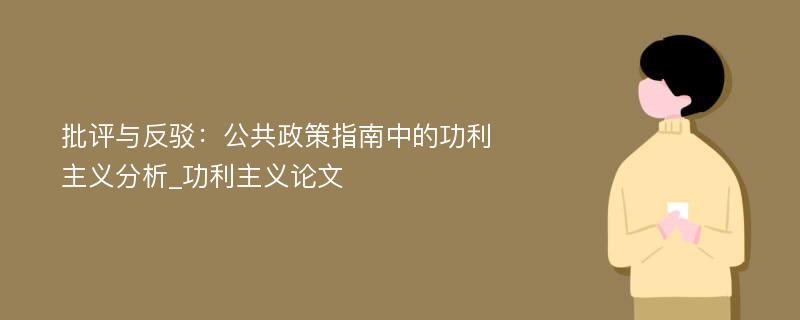
批判与反驳——对功利主义作为公共政策指南的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利主义论文,公共政策论文,指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功利主义最初由边沁开创其现代形式,再由诸如穆勒(John Stuart Miller)、杰文思(William Stanley Jevons),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艾奇沃斯(Francis Edgeworth)、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庇古(A.C.Pigou)等理论大师所继承。长期以来,功利主义一直主导着公共领域的政策选择,统领着传统的福利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经济学的基本取向。这是一个令那些试图颠覆功利主义“统治”的当代理论家们所痛恨的事实。譬如,尽管汉普希尔(1972)宣称“它现在正在失去这种地位,成为一种障碍”,但他不得不承认,“功利主义哲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乃至之后的数年内……仍然是一种大胆的、创新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原则。”(注:Hampshire,Stuart,1972.Morality and Pessimism,Leslie Stephen Lecture,University of Cambridge.Rprinted pp.1—22 in Suart Hampshire,ed.,1978.Public and Private Mor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功利主义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辉煌的历史,肯定有其明显的合理性。那么,这种合理性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再者,功利主义理论自其提出以来一直受到批判,那么,功利主义又是如何回应、化解这些诘难的呢?这些批评言论是否有一定的道理,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呢?最终,功利主义是否应当作为制定公共政策的理论指南呢?如果不能,更合理的替代理论又是什么?应当说这些问题是公共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必须深入讨论和反思的基本问题,然而却被我们给忽略了。本文拟评注西方学者已有的正反两方面的观点,为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思考提供一些参考。
志在公域的功利主义
可以说,现代功利主义自其伊始,就将其主要旨趣定位在对公共生活的指导。这一点可以从有关文献资料和功利主义理论奠基者的个人生活史中得以窥见。边沁是当时法制改革的著名人物,其经典文献《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流传后世,其思想影响宪法、刑法改革等;詹姆斯·斯图亚特·密尔是著名政论家,其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既是当时的议会议员,也是社会改革家和政论家,著有《代议制政府》、《论自由》、《政治经济学原理》等经典著作;约翰·奥斯汀是位法官。后学大师西季威克尽管在有些方面的观点与边沁相左,但仍然坚持了功利主义对于公共事务的高度关怀。J.S.密尔在一篇纪念边沁的文章中写道:“像边沁理论这样的哲学,它所能做的就是教给人们组织和规制社会事业的手段和方法。”(注:Mill,John Stuart,“Essay on Bentham”.London and Westminster Review (August 1838),Reprinte in Warnock,Mary ed.(1962),John Stuart Mill,Cleveland:Meridian,P.106.)有人认为,“功利主义是一种具有政治后果的伦理理论。”这一论断包括两层涵义:首先,功利主义是一种伦理学理论,因为它告诉我们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其次,它是政治的,因为这种理论的许多中心论点都涉及到公共生活。事实上,它从一开始就试图为我们提供一种完整的政治理论、一套指导公共事务的规范。这从政治学与伦理学的一般关系来讲也是合理的,因为“政治学必须依托于伦理学”——任何试图指导人们行为的政治学理论都需要某种伦理正当性论证的支撑。(注:Goodin,Ronert(1995).Utilitarianism as a Public 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4,p.4,p.22.)
旨在指导公共生活的功利主义理论有三大要件:“后果主义”、“福利主义”和“总和排序”。(注: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0页.)“后果主义”主张,一切公共选择都必须按照其后果来评价;而且,除了结果之外,没有任何考虑能作为最终的检验标准。它与“十诫”式的道义论截然不同。后者将某种行为规定一种义务,而功利主义理论要求人们必须对他们的行为结果负责,给行为留有如何达成这种结果的自由处置权。
以“后果主义”作为公共政策的指导原则和评价标准,有个很重要的优点,那就是可以避免那种不计成本的“政治策略”,确保国家财赋的有效开支、而非无偿奉献,确保公共政策关注人民的利益、期望或偏好。而如果按照道义论的指导,则可能产出为义务而义务、没有什么实质性好处的政策。甚至可能的是,“义务”成为奢侈、腐败和不负责任的幌子。这种为义务而义务的行为,在私人生活中是允许的甚至是应当的。然而,若公共官员也这么做,则就错了,至少人们不会认为这样做是合理的。功利主义之所以较之其他伦理学理论更好地指导公共政策行为,是由公共决策者特殊的角色扮演和活动情景决定的。国家、政府及其公共官员,从根本上届于“工具性”和“功能性”范畴,其行为合理性的根本理由是能较之公民个体和私人企业更有效地实现社会总体福利——最终落脚在个体福利——最大化。
结果取向的功利主义作为政策评价标准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避免纯道义论政策讨论中可能出现的议而不决现象。这一点在当今这个价值多元主义的时代中,显得尤为重要。对此,阿马蒂亚·森举了一个关于产权的例子。有人珍惜其对于个人独立性的构成性意义,因而主张神圣不可侵犯,甚至否定征收财产税或所得税:而有人看到的是产权的不平等,因而持相反的主张。那么,到底是自由重要还是平等重要呢?这一问题从道义规范论的角度是争论不清的。然而,我们可以通过估算和比较在某一具体社会环境中不同产权政策的不同后果(即按照功利主义的后果论原则),进行政策选择。
功利主义的“福利主义”倾向表现在,它对事物状态的价值评价限制在它们的效用上。结合前述后果主义取向,功利主义认定,任何政策选择都必须按照它所产生的结果的效用来评价。然后,根据各个政策方案的总效用的大小,将它们进行“总和排序”。最后,将效用最大的方案作为最佳选择付诸实施。显然,功利主义的三大要件之综合,构成了典型的政策分析简易模式:问题的界定与分析——列出备选方案一计算每种方案的结果(成本效益分析)——进行效用比较——付诸实施。
值得说明的是,一般讨论作为公共政策制定标准的功利主义,指的是“福利功利主义”(welfare utili-tarianism)。尽管其“最大化”信条依然如故,但是“最大化”的内容已超越了边沁简单的苦乐计算法则,不再是那种粗糙的“享乐”哲学。边沁功利主义最大化内容主要是某种心理状态;“快乐”(happiness plea-sure)和“痛苦”(Pain),因此又称“享乐主义”(hedonism)或“享乐功利主义”(hedonic Or hedonistic utilitarianism)。后来人们认识到,从那些其本身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精神快感的事情上,有时也能获得满足。于是,最大化的对象变成了“偏好满足”(Preference satisfaction),故命名为“偏好功利主义”(Preference utilitarianism)。再后来,人们又认识到,一些不能立即奏效的资源占有或能力增长也能给人们带来满足,于是又产生了福利功利主义。(注:甚至有人提出过“理想功利主义”(ideal utilitarianism).其核心观点是:人们的一些理想(事物或道德品质)本身就是一种善,不管人们是否期求过这些理想.)
批判与反驳之一
对于功利主义作为公共政策的指南,人们似乎有种本能性的反感,为什么呢?因为它在私人生活中的适用往往会让我们感到人情冷漠、生活没有情调、社会缺乏真情。在功利主义的评判体系中,既没有感性与情感的空间(有的只是计算理性),也没有爱心与妥协的余地。甚至连人的一些道德义务也成了可以权衡的东西,连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都有可能成为效用的牺牲品。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这种“计算机式的社会”,所以,我们厌恶功利主义。
然而,我们从情感上反抗功利主义对私人生活的占领,是否意味着我们同样也反对它对公共生活、公共决策与选择的指导呢?为了捍卫功利主义作为公共生活指导地位,美国学者R.E.古丁专门写了一本题目就叫做《功利主义作为公共哲学》的专著。该书的核心观点是“作为一种规范理论,功利主义能够成为公共事务的好的规范性指南,不以它成为个人最佳行动指南为条件。”(注:Goodin,Ronert(1995).Utilitarianism as a Public 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4,p.4,p.22.)公私行动逻辑的不同,公共生活情境的特殊性增强了功利主义原则成为其行动指南的适恰性。
社群主义者往往批判功利主义的非人格化(impersonality)。认为它关于福利效用的计算,既忽视了个体的独特性(包括其独特的成长历史、人际关系、忠诚感、归属感等),也忽视了人与人的相互影响——每一个人都有其独特的社会居所,任何个体都是特定社会关系的集结点;没有人是真正的“原子人”。然而,尽管功利主义的“冷酷理性”假设不完全符合对人的社会现实状况的描述,就私人身份的个体而言,似乎也不应该如此计较和冷酷。但是,当功利主义适用于公共官员(或更广泛地说,承担公共事务的公民)时,这一缺点反而成了优点。也许正是因为我们知道,任何公职人员都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因而可能利用职务或公共权力之便,为裙带关系者谋取不当利益,所以,人们总是希望公务执行者、公权行使者能够超脱个人恩怨、无视私人社会关系远近,尽量保持公正、中立,秉公办事。同时,我们还希望公职人员不要感情用事,要理性多于感性,秉承对人民钱财和公共事业认真负责的态度,精确地计算、科学地规划公共事务。我们甚至极力要求我们的官员一定要仔细考虑每一项公共政策的利弊得失,并对其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具体行为和抽象行为承担责任。就这样,那些在私人生活中受人鄙夷的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理性压制感性等等,到了公共生活中反而成了官员们的应有品质。而这正是功利主义所主张的。正是由于公私行为情景制约的不同,所以,于私看来“冰冷”的计算理性对公却表现为一种负责任的理智。公允地说,功利主义的后果敏感性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尽管完全的后果主义看来是太极端了”;功利主义“注意人们福利的想法显然具有吸引力,即使我们不同意评价福利时采用以效用为中心的心理测度方法”。(注:Goodin,Ronert(1995).Utilitarianism as a Public 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4,p.4,p.22.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51页、第53页、第56页、第53页、第52—53页、第48页、第71页、第69页.)
批判与反驳之二
对于功利主义来说,行为结果是其唯一的判断标准。行为本身本无是非善恶之分,关键要看行为产生的结果。(注:Pettit,Philip(1991).“Consequentialism”,in Singer,Peter ed.(1991).A Companion to Ethice,Oxford:Blackwell.)功利主义的这种结果论自然会受到义务论者和善恶本源论者的批判。几乎每个民族、每种宗教都有一些公理性的道德原则,有些甚至成为禁忌(taboo)。譬如著名的“摩西十诫”和一些宗教或民族对某一动物的崇拜和禁食。这些道德律令是不容(从后果上加以)辩驳的,人们唯有遵守和履行。就私人生活而言,人们都能理解、遵行并用作辩护的理由。
然而,现代国家中却很少见到哪个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存在这样绝对的道德律令。现代公共生活似乎必须满足两大基本要求,那就是公开性和可说明性(accountability)。启蒙运动对现代公共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之一就是,一切公务行动和公共政策都必须经得起理性的批判和审视。也许是出于对人性的怀疑,人们对于公共官员的评价标准越来越客观化——以实绩论优劣——而对那些可是可否、捉摸不定的主观标准(譬如行为动机)越来越不相信,除非能用结果证明。在公共事务和公共管理中,人们似乎并没有为公职人员的个人信条留下什么空间以证明其某种“偏执”行为的合理性,那种在个人生活中无比宝贵的浪漫情怀和审美情绪——许多政治美学家正是在这个方面对功利主义进行了抨击——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中,却往往被人民视为玩忽职守和政治幼稚。这无疑又证明了功利主义(结果主义原则)作为公共事务伦理的合理性。典型的功利主义者习惯于问“这对我有什么用?”(或用有些公共精神的句式说,“这对我们有什么用?”),而这难道不是我们经常用来质疑公共官员的问句吗?!
功利主义的上述辩解固然有理,但是,倘若依据公共选择情景的特殊性,将结果主义推至极端,那么,将从根本上瓦解公共生活。因为这种极端的福利式结果主义,否认权利和自由有其自身固有的重要性(它们只是间接地,而且只是就其影响效用而言是有价值的)。公共选择机制之为社会造福的基本前提条件和构成性要件是个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注意幸福是合理的,但我们不一定愿意做幸福的奴隶或者快乐的陪臣。”(注: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51页、第53页、第56页、第53页、第52-53页、第48页、第71页、第69页.)
在关于自由、权利与福利的相对重要性方面,功利主义受到了当代自由主义尤其是自由至上主义的挑战。被誉为“最有影响——而且在很多方面是最重要的——当代正义理论”的罗尔斯正义论,提出必须坚持“自由的优先性”(the Priority of liberty)原则。被罗尔斯列入优先地位是那种被称之为社会“基本善”的基本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它们不能因为经济需要的考虑而权衡。然而,罗尔斯赋予“基本善”的绝对优先性地位不久就受到了有力的挑战。哈特(1973)的质疑“强烈的经济需要可以是生死攸关的事,其地位为什么就应该低于个人自由权?”,(注:Herbert Hart,“Rawls on liberty and its priority,”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40.(Spring 1973)。)在罗尔斯后来的《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得到了承认。相对而言,罗尔斯的自由优先论主张还算温和;以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主张毫不妥协的、绝对的优先性,无论形式的、精神上的自由,与权利所带来的“权益”保障可能给社会和个人的实质性自由带来什么样的恶劣结果。正如森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所揭示的,即使大规模的饥荒也可以在任何人的自由权利(包括财产权)不受侵犯的情况下发生。像失业者或赤贫者那样的穷人所拥有的完全合法的“法权资格”恰恰是他们现时贫困处境的守卫者。(注: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1年.)不顾后果的自由优先性建议必将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漠视了人们最终能够享有(或不享有)的实质自由而陷于困境。”(注: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51页、第53页、第56页、第53页、第52—53页、第48页、第71页、第69页.)这种辨证的讨论表明,功利主义关心人们的生活福利是对的,但是,不能走向极端。自由不仅具有工具性的意义,而且其本身就是人类正当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自由权和基本政治权利的保障应该具有程序上的优先性;但不具有绝对的、不可妥协上的优先性——这一点对于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尤为重要。相反,后果性考虑可以也应当赋予实现或侵犯个人自由权利很大的重要性(甚至可以给它特别的优待),而同时不忽视其他的因素,包括特定程序对人们实际享有的实质性自由的实际影响。总之,后果主义对于公共政策评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必须加进权利因素以拓展其理论的关怀。(注:关于这一点的深入讨论,可参见Amartys Sen的“Rights and Agency”(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Ⅱ,1982)以及Freedom,Rationality and Social Choice:Arrow Lectures and Other Essays(oxford:Clarendon Press,2000 ).)
批判与反驳之三
对于功利主义作为公共哲学的第三方面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其效用计算的可行性和合理性问题上。起初,有人批判功利主义的效用计算建立在完全理性的基础上,因此,在技术上和政治上都是不可行的。首先,我们知道,正如西蒙的“有限理性”原理所解释的,人类的现实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一般不可能穷尽解决问题的一切可能方案,即使仅对既有政策方案的价值或效用的准确计算也常常是不可能的。另外,有时完全理性的要求可能致使决策成本超过政策收益,结果适得其反。就个体私人行动而言,人们在行动之前往往并不会遵照功利主义的指导进行计算以求效用最大化,而是按照惯例常规、模仿或随众,甚至凭感觉行事。在公共领域,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通常遵循的都是林德布洛姆的“渐进主义决策”模式。(注:查尔斯·林德布洛姆:《决策过程》(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针对此种批判,功利主义的支持者提出,功利主义的总和排序并不以各种选择方案的基数效用值为必要条件。当将功利主义运用于政策方案的评价或比较选优时,我们可以借用帕雷托最优来避开逐个计算每个政策方案的精确值,而只需满足帕雷托最优条件——没有任何一方因此而受损、但至少有一方因此而受益——即可基本适用功利主义的“效用最大化”原则。现实政策生活中,我们通常会运用“卡尔多——希克斯补偿检验”(hypothetical compen sa-tion test of Kaldor and Hicks)来检验一项公共政策是否合理,即只要政策受益者的利益改进总和大于受害者受损利益之总和,那么,这项政策就是(经济)有效率的。我们认为,这种辩解虽然基本有效地回应了纯数学上的挑战,却正中了对功利主义的另一条批判,即:个体偏好具有不可比的特性,因而,功利主义的偏好加总是不可能的。
由于大多数的公共政策都将使一部分人获利,使一部分的利益受损;或者即使每个人都受益,要评价何种分配方案能最大化总体效用,都需要进行人际效用比较。然而,一个普遍的事实是,人们的偏好和兴趣千差万别,各式各样。他人是无法真正设身另外一个人的境地,无法准确理解其酸甜苦辣的感受。用杰文思的话说,“每一个心灵对另外一个心灵来说都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不可能存在任何情感的公分母。”(注:Jevons,William Stanley(1911).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4th ed.London:Macomillan,P.14.)这种独特性,使得个体间的偏好具有不可加总的特性。
针对这一诘难,功利主义者指出,一方面断言,人与人之间在根本利益和福利效用上肯定存在着可比性和共通性,因为这是社会和政治得以现实存在的前提——政治归根到底是而且必须建立在公民之间存在共同性这一基础上。人作为一种类的生物,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在文化价值、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共同性,使得他们的需求在较为抽象的层次上、在更根本的福利需要方面存在着一致性。可以说,正是由于他们共同的根本利益,使得(他们的)公共领域得以建构、公共政策得以通过、公共管理成为可能,所有公共生活的共同目的,就是促进成员共有利益的最大化。同情原则可以在这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另一方面,当代功利主义者往往会主张避开人们的主观偏好或欲求(desire),转向那种较为客观的福利需要(welfare interests),或者是罗尔斯所谓的“基本善”(primary goods),亦或是森的实质性可行能力 (capability)的基础条件。从而绕开那种人际不可知的困境,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可以达成共识的偏好比较之上。这似乎是向马歇尔和庇古“物质福利”学派的回归。在那里,“人际效用比较意味着需要(needs)的比较,而不是主观欲望(desires)的比较”,并且这种比较的指标是那些看得见的“工业效率”指标,比如食物的短缺、疾病发生率和死亡率等。(注:Cooter,Robert and Peter Rappoport (1984).“Where the ordinalists wrong about welfare ecnomiscs?”Journal of Ecnomic Literature,22:507—530,p.516.)当然,正是这样一种简化和抽象,使得在功利主义指导下制定的政策具有不精确的特性。然而,这一缺陷可以通过建立和健全公共政策对话与讨论的方式基本上得以弥补。功利主义并不反对政策讨论和政策民主,相反,它认为,通过政策讨论和辩论,可以修改各种利益的加权系数,使之更具政治可行性,或更符合人民利益的现实格局。
也有人对功利主义的公式化政策分析逻辑提出批评。那些接受功利主义作为公共决策指南的人们,往往会简单套用功利主义分析的一般模式:问题的界定与分析→列出备选方案→计算每种方案的结果(成本效益分析)→进行效用总和排序和方案选优。这种简单的政策制定模式招来了学者的批评。有人认为,这种简单化的成本效益分析既帮助肯尼迪政府成功地进行了国防部的改革,但也使它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深渊。这种批评固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若我们考虑到公共政策制定的现实,即实际工作中的政策制定大多受到时间、资金以及人员的知识和精力的制约,这种简便也可以说是功利主义的优点。特别是针对那些问题比较简单、方案后果比较明确的政策制定过程而言,不失为一种可取的模式,许多数理经济学的公式和结论在这种政策模式分析中可以得到简便的运用。更何况,功利主义指导下的公共决策或政策分析并不一定就是一种简单化的套用公式。功利主义有时仅仅只是一种精神,一种在必须决断、必须找出政策问题解决方案的终极性判断方法,那就是较好的政策方案必须实现相对较大的社会福利总值。
批判与反驳之四
除了前述自由与权利视角的批判以外,对于功利主义真正有力的批判还有两点:一是批评它忽视分配公平;二是批判它无法处理适应性行为和心理调节现象。功利主义的效用计算方法关心的是社会福利总量的大小,而不管它们是如何分配的,这种态度用之于政策分析与评价,往往会导致对政策代价与收益分配不公平的现象漠视甚至认可。对此,支持功利主义作为政策评判标准的主要有三点辩解:由于考虑到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功利主义者在进行效用加总并力求最大化时,不会促成而是试图削弱“马太效应”结局的出现;功利主义实际上是极力赞成那些有助于实现平等的政策、制度和惯例的;特定政策利益的分配格局往往是一个社会总的利益格局产生的特定结果,因此,如果出现政策利益分配不均的现象,其罪魁祸首是社会的基本制度造成的,而不是采用功利主义原则的后果。(注:17)这些辩解似乎有些道理,但明显地不充分,或是有些牵强,或是有些推脱责任之嫌。
由于我们的愿望和享受快乐的能力随具体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在逆境中我们会调整自己以使生活变得易于接受一些,即如果你不能得到你所要的,那么就可能修改自己的偏好,使得你的愿望能够容易得到满足。特别是社会中那些受剥夺的人群,譬如等级社会中最底层的人,不宽容社群中:长期受到压迫的少数族裔,严重性别歧视文化中无望地屈从的家庭妇女等等,出于单纯的生存需要,他们通常会调整自己的偏好以适应剥夺性环境,……甚至会把他们的愿望和期望调整到按他们谦卑地看来是可行的程度。(注: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51页、第53页、第56页、第53页、第52—53页、第48页、第71页、第69页.)这就是所谓的“适应性偏好”(adaptive preference),适应性偏好又可以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有些东西即使得到满足了,你不会有满足感,因为它太容易得到满足了。但是,也有些偏好你从来不会不感到满足,如果它们是经过功利主义的社会改革家精心挑选和设计、由某种外在的组织或社会化手段灌输到你身上的。还有许多目标不是我们有意想达到就能达到的,相反,它们只能作为一种行为的副产品被间接地获取。这就是艾尔斯特(Elster)所谓的“实质性副产品”概念,譬如睡眠和自发反应。(注:Elster,Jon (1982).“Utilitarianism and the genesis of wants”,in Sen,Amartya and Bernard Williams eds.(1982).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适应性偏好的存在使得快乐或愿望的心理测度具有太大的弹性,因此,偏好的观测值既难以准确地反映人们偏好的真实值,更不能成为被剥夺和受损害状态的可靠反映,因为这些人的偏好扭曲更为普遍,更为严重。由此可以提出两个重要的问题:效用测度时,如何处置适应性偏好现象?更为重要的是,理论规范上如何支持创造条件以使人们能够有真正的机会去评价什么样的生活是他们所向往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古丁提出,可以通过调整功利主义的应用模式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功利主义理论在公共政策实践中的应用可以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古典的,其最大化的偏好是所有人所有可能的偏好;第二种模式中,功利主义理论将自己的研究视点固定在当前研究对象之当前偏好的满足上。无论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应用模式,似乎都无法处置“适应性偏好”问题。然而,功利主义理论应用的第三种模式至少在政策分析中是比较可取的。它以给定人群作为研究对象,但其最大化的内容囊括他们所有可能的偏好。这种安排的关键是要引进动态偏好分析模式,以应对人们偏好随时间的变迁。一种完全可能的情况是,人们在做出决策时的偏好函数,与在决策结果出来之后的偏好函数之间存在差异。第三种模式虽然实现了对人们偏好的动态分析,但是,依然无法触及“适应性偏好”问题的社会性实质——归根结底是一个社会公平与发展的问题。
结语:森的评价与建议
尽管阿马蒂亚·森既不是功利主义批判的第一人,也不是功利主义的盖棺定论者。但是,本文以为,因对经济伦理学(核心主题是自由、民主与发展)的杰出贡献和卓越研究而荣获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对作为公共哲学的功利主义的评价既系统又中肯,且最为切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政策评价。
首先,森高度肯定了功利主义视角的两大优点,“按其结果来评价各种社会安排的重要性”;“评价各种社会安排时,需要关切所涉及的人们的福利”。同时,森又指出功利主义视角的三大局限性:漠视分配;忽略权利、自由以及其他非效用因素;无视适应性行为和心理调节。(注: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51页、第53页、第56页、第53页、第52-53页、第48页、第71页、第69页.)森对功利主义的评价可谓全面而精辟。但这并非其独创。森的批判的特色在于他的理论视角。
森独辟蹊径,从对各种理论尤其规范性理论的信息基础的剖析入手,去评判它们的利弊得失及其原因。“每一种评价性方法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以其信息基础为特征来说明:即采用这一方法做出判断所需要的信息,以及——同样地重要的——被该方法‘剔除’在直接的评价性作用之外的信息。信息‘剔除’是评价性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剔除的信息不能对评价判断有任何直接影响。尽管这种剔除通常以隐含的方式做出,对那些被剔除的信息的不敏感性会强烈影响一种方法的特征。”(注: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51页、第53页、第56页、第53页、第52-53页、第48页、第71页、第69页.)功利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上述三个方面的缺陷,是由于它最终仅仅依据结果的效用信息去评价事物状态,或判断行为及规则;并对那些被剔除的其它各种信息丧失了敏感性,譬如福利的分配情况、弱势群体的适应性偏好、自由与权利的价值等。
在综合考察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实践性理论的优点和缺点之后,结合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际,森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可行能力(capability)视角”。如以这种视角指导政策分析和评价,则将集中注意关于个人自由(而不是效用)的信息基础,但也包含对于后果的敏感性——这正是功利主义视角的优点。可行能力分析视角能够较好地解决自由、权利与效用的兼容问题,能同时兼顾社会福利总量增大与利益分配均衡两方面,因为它“集中注意人们去做他们有理由珍视的事情的可行能力,以及去享受他们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自由。……不仅能够关注自由的重要性,它也能够充分注意作为其他方法基础的、并使之有实际意义的那些动机,特别是,以自由为基础的视角能够兼顾功利主义对人类的福利的兴趣,自由至上主义对选择过程行动自由的关切,以及罗尔斯理论对个人自由权、对实质自由所需的资源的集中主义,等等。”(注: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51页、第53页、第56页、第53页、第52-53页、第48页、第71页、第69页.)
如果有人坚持一定要用功利主义作为公共政策评价的标准,那么,森不会劝他全盘抛弃功利主义思想,而会劝他多多关注自由权利和分配公平,会建议他不妨先试行用实质性自由的视角作为功利主义方法的补充,或是将“收入之外的可行能力决定因素”调整其效用指数,譬如,家庭收入水平可以因文盲而下调,因教育水平高而上调,使之反映可行能力成就。(注: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51页、第53页、第56页、第53页、第52—53页、第48页、第71页、第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