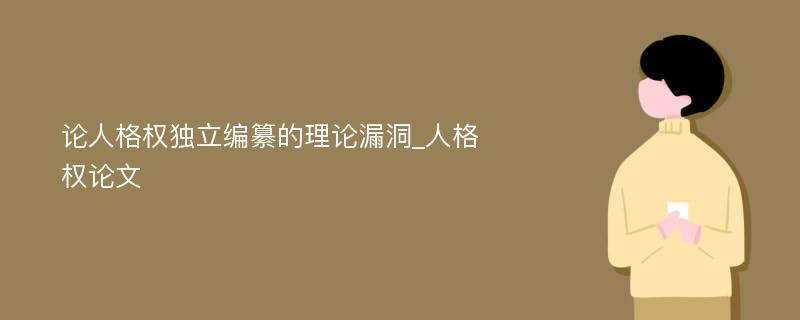
论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理论漏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格权论文,漏洞论文,理论论文,立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中国民法典的起草过程中,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是重大争议问题之一。对此,笔者曾站在否定立场,提出了两个基本看法:其一,人格权本质上是一种宪法性权利而非民事权利,与民法上的物权、债权以及身份权等非属同类,在民法典上不应作为民事权利的一种类型予以并列规定;① 其二,自然人人格与法人人格具有本质上的不同,自然人人格权为伦理性权利,所谓“法人人格权”实为财产性权利,无任何伦理性价值,故法人无人格权。②
前述观点,主要是在对自然人人格的历史变迁以及人格权立法的发展历史的分析基础之上,通过揭示人格权的创设依据和人格权保护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而形成。笔者充分注意到大陆法系各主要民法典对于人格权仅设置了保护性规定而无赋权性规定这一现象,并认为我国某些理论将这一立法现象草率地解释为“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制度,存在重物轻人的现象”③,应属主观臆断,毫无根据。笔者更注意到伴随当代人格权保护浪潮而出现的“一般人格权”,其创设依据竟然并不是民法而是基本法(宪法)。由此,笔者通过以自然人人格的法律属性的分析为基点而展开的逻辑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自然人人格为自然人的一般法律地位,不仅包括其私法地位(权利能力),而且包括其公法地位,此种一般法律地位只能由宪法赋予;而人格权为自然人人格构成要素中非财产性要素(包括政治要素与伦理要素④)的权利表达,系基于人格的获得而当然产生,故其创设依据为宪法而非民法,其性质应为宪法性权利而非民事权利。因此,民法应以侵权责任法对自然人的人格权予以保护,而不应将人格权作为民事权利类型之一进行赋权性规定。
就前述关于法人无人格权的观点而言,其论据主要是通过对团体人格的立法目的和法律价值的分析而形成。笔者注意到,德国民法塑造团体人格的唯一目的,是使具备一定条件的组织能够成为财产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独立承担者,借以限制投资人风险,鼓励投资积极性。所以,法人之所谓“人格”,不过是被用作区分或者辨认团体有无民法上独立财产主体地位的纯法律技术工具而已。因此,法人人格仅在私法领域有意义,而在社会政治生活以及伦理生活的各种关系中,不存在法人人格。各种团体在公法领域依公法的规定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其法律适用并不因团体是否具备法人人格而有所区分,故法人人格并不包含享有任何政治权利或其他公法权利的资格。此外,尤为重要的是,团体之“人格”是一种无伦理性的法律人格,与自然人人格所表现的尊严、自由、安全以及伦理道德无关,故其仅为一种单纯的财产权主体资格。据此,法人只能享有财产权利而不能享有精神权利。而在人格权的发展史上,此种权利保护的一直是且只能是精神利益而非财产利益,故法人无人格权。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信用权等不可能包含任何精神利益,其只能是一种财产权,具有可转让性,法人也不得主张任何精神损害赔偿。
笔者提出的上述理论在学界引起很大争论,但迄今为止,尚未出现具有针对性的、系统的学术批评意见。
笔者认为,在中国民法典中对人格权独立成编予以规定,应属对大陆法系民法理论和立法的一项重大突破和创新,此种大胆创造,仅以“应当加强人格权保护”这一理由作为基本依据,是草率和不科学的,也是没有说服力的。而有关人格权在民法典中应否独立成编的论争,绝非仅是一种体系安排之技术上的分歧,而是涉及到人格权保护的发展以及民法理论的科学建设与司法实务的操作效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应当看到,既有人格权理论将人格权描述成为一种与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以及身份权具有相同性质的权利,是其主张将人格权在民法典上独立成编的基本理论依据。为此,既有人格权理论全面套用了民法有关民事权利以及法律关系的基本原理,对人格权进行了理论阐述,由此必然产生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理论漏洞。为此,在对人格权本质进行正面分析的基础上,就既有人格权理论的漏洞以及人格权独立成编后所有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予以反面分析,也许更有助于廓清理论界在人格权问题上的诸多模糊认识。
二、关于人格权来源之理论的漏洞
依据民法调整对象理论,民事权利(民事法律关系)是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产生的,即先有民法调整对象的存在(即客观发生和存在的民事生活关系),经民法规范之后,方有民事权利义务(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换言之,相对于每一种具体的民事权利(民法调整的结果),总是存在着某种与之相对应的具体的民事生活关系(民法调整的对象)。据此,有关理论断定:“人格权是民法调整人格关系而产生的。”⑤ 但是,作为自然人法律地位或者法律资格的“人格”,是一种法律现象而非一种自然的社会客观存在,基于人格而产生的“人格关系”,当然应届法律关系,而法律是不可能去调整法律关系的,故人格权并非源于民法调整所谓人格关系所生之结果。
如果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自然人的法律人格先于人格权产生(“人格”的概念最早产生于古代罗马法,而“人格权”的概念产生于19世纪欧洲民法理论),但如果从事物本质的角度来看,则近代意义上的法律人格与实质意义上的人格权同时产生。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格权概念在产生之时仅仅是对近代意义上的法律人格⑥ 之诸多构成要素(亦可称为“人格利益”)中伦理性要素(包括生命、健康等人格利益)的表现,并未包含人格要素中的政治要素与财产要素,即使在“一般人格权”出现之后,人格权保护范围被扩张至财产以及民事身份之外的一切利益,我们仍然不能说“人格和人格权是一枚钱币的两面”。但人格与人格权存有密不可分的本质联系,表现为:无人格者绝对无人格权,有人格者必定有人格权,在人格与其当然生成的人格权之间,并不需要借助其他任何法律媒介,即人格权的产生并不依赖于民法或者其他任何法律规范的“调整”。诚如有的学者所言:“人格权是存在于主体自身的权利,不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权利。人格权就像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出生、死亡一样,属于主体自身的事项。只有人格权受侵害时才涉及与他人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属于侵权责任关系,为债权关系之一种”。⑦ 因此人格权是自然人人格(法律地位)的一种权利表达。
由此可见,运用民法调整对象的理论,可以正确地解释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以及身份权等民事权利的来源,但根本无法解释人格权的来源。事实上,依据自然法理论,自然人的人格和人格权当然存在;依据实证法理论,则自然人的人格和人格权系由基本法(宪法)赋予。而根据笔者所提出的且迄今为止尚未遭到任何反驳的学说,自然人的人格不仅在罗马法上是一个公法概念,⑧ 而且在近代法上也是一个公法概念,⑨ 据此,表现自然人人格的人格权,亦应为一种宪法性质的权利而非民事权利,此种权利的发生根据与民事权利的发生根据完全不同,不可能用民法调整对象的理论予以说明。
前述理论障碍在既有理论阐述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和来源时,显得更为巨大和无法克服。对于同类事项的归纳与抽象并以此形成上位概念,是民法技术所采用的最基本的逻辑方法。据此,民事权利的基本类型,均是通过对各种同类权利的概括抽象而形成的。正因如此,既有人格权理论在引入“一般人格权”概念的同时,将之解释为“自然人和法人享有的,概括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尊严全部内容的一般人格利益,并由此产生和规定具体人格权的基本权利”,⑩ 亦即一般人格权是法律列举的生命权等具体人格权和其他应受保护的人格权利的“产生根据”或者是对各种具体人格权的“归纳抽象”。但此种理论最为明显的漏洞在于:如果一般人格权是各种具体人格权的产生依据,则一般人格权作为一种权利类型必定创设在先,但我们知道,“一般人格权”概念的出现,在时间上大大晚于“人格权”概念的出现。(11) 而如果一般人格权为对各种具体人格权的归纳抽象,那么,此种抽象而成的概念应为“人格权”而非“一般人格权”(如同对所有权和他物权的归纳抽象,其产生的概念是“物权”而非“一般物权”)。据此,一般人格权究竟是各种具体人格权的创设依据抑或系对各种类型化以及尚未类型化的具体人格权的归纳抽象,既有理论同时存在相互矛盾的两种说法,且两种说法都不符合一般人格权的产生历史。有关资料表明,由德国司法实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创制出来的“一般人格权”,根本不是对既存的各种具体人格权的概括抽象,其创设目的亦非为各种具体人格权的创设提供基础和依据。一般人格权所要保护的,是《德国民法典》列举保护的生命、健康等人格利益之外的其他全部人格利益。(12) 因此,一般人格权与该民法典列举保护的各种具体人格权,是两种互不包容、互不隶属的权利类型,两者之间既不存在归纳抽象关系,亦不存在创设依据关系。
再者,德国司法实务创制一般人格权所依据的法律并非民法而是其基本法(宪法),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人格权并非民法调整私法生活关系的结果,否则,此种权利完全可以依据民法理念和基本原则加以创设。概言之,生命权、健康权等类型化的人格权是对个别人格利益的保护,一般人格权则是直接依据基本法的规定,对此部分由民法典列举的人格利益之外的全部人格利益的概括保护,其不仅保护自然人在民事生活中的人格利益(如未被《德国民法典》予以列举保护的“隐私”),而且保护自然人在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的人格利益(如男女性别平等、民族感情和自尊、劳动就业、接受教育以及公民在宗教信仰、文化活动、新闻出版等方面享有的自由等等)。
可是,既有理论在阐述一般人格权时,不仅无视此种权利表达的历史来源,而且在错误理解此种权利与类型化的各种具体人格权之间关系的基础之上,对一般人格权的基本功能进行了错误的阐述。在其使用的“人格权”、“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三个概念之间,并不存在概括抽象的递进关系:如果“一般人格权”是对各种“具体人格权”的概括抽象,则“人格权”便不可能是对“一般人格权”和各种“具体人格权”的概括抽象,“一般人格权”与“人格权”应属同义,毫无存在的必要。
三、关于人格权基本权能之理论的漏洞
如果将人格权定性为一种民事权利,则其必然应当具备民事权利的一般特性。以往的研究已经发现,民事权利无论因当事人的行为或法律直接规定而取得,原则上均可根据权利人的意思,依法律行为而予以处分,但人格权仅因自然人出生而当然发生,仅因其死亡而当然消灭,当事人的意志对于人格权之得失变动无任何决定余地。(13) 除了对人格权的此种外部特征的分析之外,就民事实体权利(14) 而言,无论财产权或是身份权,其基本权能总是表现为权利人得实施一定的行为(或为对财产及其他利益的支配,或为对特定人的请求)以实现某种利益,不作为的民事权利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既有人格权理论在将人格权定性为一种“支配权”的同时,却无法对之予以正确的阐明。
(一)生命权的客体与“支配性”
生命权位居已被命名的各种具体人格权序列之首,是最基本的人格权,但因自然人本身即为一种生命现象,生命与“人”实为同一,而权利主体不可以其自身作为客体,故生命在逻辑上不可能作为生命权的客体。此外,民事权利的本质特征在其法律保障力,亦即在权利主体丧失权利所载之利益时,可以获得法律救济,故早已有人指出,当生命权遭受侵害时,权利主体已不复存在,亦不存在任何法律救济之途径,故生命非为权利。(15) 对于上述质疑,既有理论根本不能回答。而就生命权的基本权能而言,基于民法理论对民事权利的基本分类,既有理论在不得不将生命权归于“支配权”的同时,却无法正确说明其支配权能的具体表现:鉴于自然人对生命的所谓“支配”只能表现为允许他人剥夺其生命或者自杀,而此两种对生命的“处分”均不可能为法律所保护,故既有理论不得不寻出“为正义而慷慨赴死”以及“安乐死”或者“因见义勇为而牺牲生命”等情形作为例证。(16) 但我们知道,生命权的意义在于保护人们的安全和生存,而绝对不在鼓励或者保护人们的“献身”,故“慷慨赴死”可以被理解为生命权遭受不法侵害,但不可以被理解为主体在主动放弃生命;“见义勇为”的目的也绝对不在抛弃生命,故亦非主体之生命支配权的行使。至于允许他人对自己实施“安乐死”,姑且不论多数国家尚不将之视为合法,即便法律允许,其固可视为一种对自己生命的“处分”,但以此特例作为生命权的一项基本权能,亦与生命权的立法宗旨背道而驰。
(二)健康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身体权的“支配性”
首先,如果将“健康”、“名誉”以及“荣誉”视为此三种权利的客体的话,那么,除非将健康权、名誉权以及荣誉权的“支配权能”描述成对有权允许他人损害自己的健康以及名誉或者荣誉,或者有权自己损害自己的健康以及名誉或者荣誉(如吸毒、拒绝治疗、允许他人对自己造谣诽谤等等),否则,对于自然人如何“支配”其“健康”和“名誉”,如何以民事权利的行使方式行使这些人格权,任何理论阐释都是强词夺理、无法成立的。在这里,既有理论将健康权的支配性描述为“健康维护权、对劳动能力的支配权”(17) 或者“体育运动员参加竞赛就是处分自己的生命、健康”(18);将名誉权和荣誉权的支配性描述为“利用其良好名誉或者荣誉称号获得财产和其他利益”,(19) 姑且不论这些阐述如何文不对题,其至少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果自然人的这些对其劳动能力、健康损害风险、良好名誉或者荣誉的“利用行为”遭受他人妨害,绝对不可能构成对其健康权、名誉权以及荣誉权本身的侵害!
其次,隐私权的支配权能被描述为允许他人或者权利人自己公开其隐私,(20) 而捐献血液或器官、出卖头发等行为,则被认为是自然人对其身体支配权的行使。(21) 但鉴于法律规定隐私权的目的在于保护自然人的隐私不被他人非法公开,而绝非保护权利人不受妨害地公开其隐私;法律规定身体权的目的在于保护自然人的身体不被他人非法侵害,而绝非在于保护权利人不受妨害地自行或者允许他人取除其身体某些组成部分,且妨害主体公开隐私、捐献血液等行为亦绝对不构成对其隐私权或者身体权本身的不法侵害,故前述理论,同样是不能成立的。
(三)姓名权和肖像权的“支配性”
有关人格权之“支配权”性质的理论阐述,在涉及姓名权和肖像权时,似乎找到了某些更具有说服力的论据:自然人自己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姓名或者肖像,为姓名及肖像支配权的行使。然而,此种理论殊值存疑。
首先,姓名权究竟是一种人格权还是身份权,理论上存有争议。一个重要事实是,在法国、德国、瑞士、日本等典型大陆法国家以及地区的民法典上,均设置了有关自然人姓名或者姓名权的相关条文,此种规定,一直被认为是这些民法典对作为人格权之一种的姓名权进行了具体规定。但笔者认为,鉴于以下理由,在多数国家或者地区的民法典上,姓名权实际上是作为一种身份权而非人格权加以规定的:(1)在法国、德国、日本以及台湾地区的民法典中,自然人姓名的相关条文均被设置于有关自然人民事身份之部分,亦即自然人姓名被视为与自然人的出生或者民事身份相关的问题予以规定;(2)在《德国民法典》有关自然人人格利益保护的侵权责任相关条文中,其所列举的事项并不包括自然人姓名(该法典第823条及第824条所列举保护的事项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信用以及妇女贞操”);(3)前述民法典在未对生命、健康等最为重要的人格权予以赋权性规定的情况下,单独将姓名权作为人格权之一种类型加以规定,是不可理喻的。
从实质上看,自然人的姓名直接体现了自然人的人格尊严,故其应当具有人格利益的性质,但姓名的选择、使用以及更改又与自然人的身份直接相关,为婚姻、亲属关系中所包含的重要事项,故其同时亦具有身份利益的性质。因此,笔者认为,自然人对其姓名的选择、使用以及更改,通常情况下涉及其身份利益,但有时则同时涉及其人格尊严。但法律将姓名作为人格利益加以保护,其主要目的在于保障自然人的姓名不被歪曲、冒用、篡改或者污损,而非保障自然人得不受妨害地使用其姓名或基于商业目的许可他人使用其姓名。据此,以姓名权所具有的某种支配属性作为支配权能为姓名权基本权能的论据,仍然不足为信。
其次,与其他人格权不同,肖像权似乎具有强烈的支配属性,表现为自然人对其肖像享有制作、使用以及许可他人使用等权利。但须看到,正是基于肖像权在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此种越来越广泛的“支配性”,使此种人格权具有了“财产权化”之倾向,亦即自然人的肖像一旦被作为商业使用的标的,立即蜕变为一种无形财产,不复成为人格利益的载体。鉴于法律将自然人的肖像作为人格利益保护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保护自然人对其肖像的使用,而在于使其肖像不被他人损害,且妨害主体自己制作、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肖像并不构成对肖像权本身的侵害,故以“财产化”之肖像权所具有的强烈的支配性质作为支配权能为肖像权的基本权能的论据,同样不足为信。
(四)一般人格权的“支配性”
民法上的支配权所支配的利益总是具有特定性质。由于一般人格权所保护的人格利益具有概括、抽象之特点,故既有理论完全不能用“支配性”解释其基本权能。依照既有理论,“一般人格权”的客体为“人格独立、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但对于自然人以何种概括的或者具体的方式“支配”其“独立”、“自由”和“人格尊严”,既有理论只能避而不谈,讳莫如深。事实就是,如果说在某些具体人格权中尚且可以找出一些“支配”内容的话,那么,自然人对其“独立、自由和尊严”完全不能使用,更不能转让和放弃,一般人格权根本不具备任何“支配权能”。
四、关于法人人格权之理论的漏洞
主张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理论所遇到的最大障碍之一,是法人人格权的安排问题。
法人制度的创设目的是为了限制投资者风险以鼓励投资积极性,为此,法律赋予具备独立财产的社会组织以民事主体资格。如果将民事活动区分为财产活动与伦理活动两大类的话,则法人只能参加财产活动而不能参加任何伦理活动。因此,与自然人的人格不同,法人的人格不具有任何伦理价值,团体因其民事主体资格而享有的名称权与名誉权,亦不具有任何伦理属性,其只能或者主要具有财产属性(一种无形财产)。由于自然人的人格权具有伦理性质而不具有财产权性质,故自然人人格权与法人人格权的性质和内容完全不同。但是,为了达到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目的,既有理论无视法人人格权的财产属性,强行将之与自然人人格权在性质上视为同一,而此种做法完全忽略了法律保护人格权的基本目的和人格权特有的法律救济手段,由此导致以下两项理论谬误:
1.人格权是一种伦理性权利,其保护的是自然人的精神利益而非财产利益,故侵害自然人人格权必然会导致精神损害。换言之,如果一项利益遭受损害之后,只能导致财产损失而不能导致精神损害,则此种利益绝对不属人格利益。因此,权利受到侵害后是否导致精神损害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是辨认人格权与非人格权的基本标志。而法人为无伦理性的拟制人格,其名称权、名誉权以及信用权等遭受侵害之后,无发生精神痛苦之可能(至于既有理论为强行阐述法人人格权的“精神属性”,将其名称或者名誉遭受侵害后其成员个人的精神痛苦置换为法人的“精神痛苦”的做法,完全混淆了法人与其成员之不同人格),故法人的这些权利,非为原本意义上的人格权,这些权利遭受损害之后,均不得主张任何精神损害赔偿。既有理论在将法人人格权的特性混同于自然人人格权的同时,却无法对法人何以不得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做出说明,不能不陷入无法自拔的理论困境。
2.人格权的伦理属性在一般人格权所保护的“自由、安全与人格尊严”等基本人格利益上得到更为充分的展示。如果说法人享有人格权的结论可以通过偷换不同“人格”概念的简单方式得以证明的话(即“法人有其人格,则当然有其人格权”。而在这里,法人的“人格”与自然人的“人格”,虽然同文,但并不同义(22)),那么,当对法人之“应当”拥有的“一般人格权”进行理论阐述时,既有理论则陷入灾难性的理论泥潭:如果不承认法人享有一般人格权,则无异于承认法人人格权为无源之水;如果认定法人享有一般人格权,则在理论上阐述法人如何享有“自由、安全与人格尊严”,又必然成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五、结论
上述分析表明,自然人人格权为伦理道德乃至社会政治理念的载体,其目的在于保护自然人的自由、安全和人格尊严不受侵害。此种权利不是基于民法调整民事生活关系而产生,其存续和消灭亦不受自然人意志的支配。同时,此种权利的实现完全依赖于法律提供的保障,一般情况下无需借助于自然人自身的积极行为,故此种权利通常仅仅具有一种消极权能(人格利益不受侵害的保障性),故对之多数情况下无法采用物权、债权以及身份权等民事权利的定义方式予以定义,也无法运用民法有关民事权利的一般理论予以阐释。因此,无论一般人格权或者具体人格权,原则上均不适用民法总则的各项具体规则,其自身亦不适用民法有关权利得失变动以及权利行使的一般规则。人格权非为由民法调整民事生活关系所生之权利,但为民法所保护。民法在规定人格权遭受侵害所生之民事侵权责任的同时,也有必要将某些民事生活中常遭侵害的具体人格利益予以类型化处理并由此扩大具体人格权的范围,但就整体和实质而言,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均非由民法确认而产生,对之,民法有保障之力,却无创设之功。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固然可对人格权的重要性起宣示作用,但由此导致自然人人格权性质的误认及其所保护之人格利益范围缩减至民事生活领域,导致自然人人格权与法人人格权性质的混淆,导致民法理论科学性的降低,弊大于利。而人格权在民法典中之不独立成编,固然使中国民法理论少了一项自主创新,但如在侵权责任中将应予保护的人格利益及其保护方法予以缜密安排,则民法对人格权的保护功能不会有丝毫减弱,且浊水澄清,利大于弊。
注释:
①尹田:《论人格权的本质》,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
②尹田:《论“法人人格权”》,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
③王利明:《我国民法典重大疑难问题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72页。
④笔者认为,自然人人格除包含生命、身体、名誉等伦理性要素之外,还包括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的自由、安全等政治性要素,以及表现为自然人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即被称为“广义财产”的财产性要素。尹田:《论无财产即无人格》,载《法学家》2004年第2期。
⑤王利明:《我国民法典重大疑难问题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72页;杨立新:《人格权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2月版,第10页。
⑥罗马法上的人格为同时具备“自由人、罗马市民和家父”三种身份而赋予的法律地位,是一种区分身份等级的工具,而近代的人格,是基于天赋人权的思想而为一切自然人平等具有的法律地位。
⑦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15页。
⑧徐国栋:《“人身关系”流变考》,载《中国民法百年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文集》,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版。
⑨尹田:《论人格权的本质》,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
⑩杨立新:《人格权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2月版,第122页。
(11)“人格权”概念产生于19世纪,“一般人格权”概念产生于“二战”以后。
(12)[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806页。
(13)梁慧星:《松散式、汇编式的民法典不适合中国国情》,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1期。
(14)笔者认为,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以及身份权为“实体性”权利,形成权、抗辩权等为“程序性”权利,代理权、代表权等为“资格性”权利。
(15)龙显铭:《私法上人格权之保护》,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42页。
(16)杨立新:《人格权法专论》,第143页。
(17)同注(16),第161页。
(18)赵秉志等:《中国刑法的运用与完善》,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377页。转引自杨立新:《人格权法专论》,第146页。
(19)同注(16),第254页。
(20)同注(16),第339页。
(21)同注(16),第180页,第307页。
(22)依笔者所见,自然人人格为自然人的一般法律地位,法人人格仅为团体的民事主体资格。尹田:《论“法人人格权”》,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
标签:人格权论文; 民法调整对象论文; 独立论文; 独立人格论文; 民法基本原则论文; 民法典论文; 自然人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生命权论文; 法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