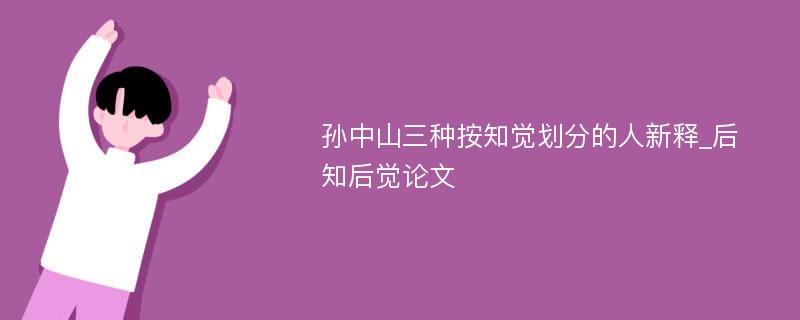
对孙中山以知觉分人为三种之新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种论文,知觉论文,新解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中山在其论述中,常以“知觉”的不同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种。这种观点长期以来被视为抹煞了人的阶级性和劳动人民的力量,是唯心主义英雄史观。今天,当我们从人的认识和历史实际出发重新审视这种观点,则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合理的成分。
一、关于人分三种
孙中山多次把人分为这样的三种:
首先,他在回答人类是如何进化,即“以时言之”的时候,提出了这个观点。他说:“夫人群之进化,以时考之,则分为三时期,如上所述:曰不知而行之时期,曰行而后知之时期,曰知而后行之时期。”(《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01页)具体说,“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同上,第199-200页)
在孙中山看来,人类不是停滞不前的,更不是倒退的,而是不断进步的,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其进步的轨迹是从“不知而行”,到“行而后知”,再到“知而后行”。他划分的标准不是别的,而是“知”与“行”,是不同的知与行在时间上所留下的不同的记录。
其次,孙中山在回答“文明之进化”成于何人,即“以人言之”时,也提出了这种观点。他说:“上所谓文明之进化,成于三系之人:其一,先知先觉者即发明家也,其二,后知后觉者即鼓吹家也,其三,不知不觉者即实行家也。”(同上,第203页)这是从“知行”中人的“知觉”的向度所作的划分。
孙中山认同人类进化是由野蛮进入文明的。文明是人类进步所不断追求的目标及其价值之所在,所以,他在肯定“人类进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文明之进化”。
最后,孙中山根据“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再次提出了分人为三的观点。他说:“我对于人类的分别,是何所根据呢?就是根据于各人天赋聪明才力。照我的分别,应该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叫做先知先觉。这种人有绝顶的聪明,凡见一件事,便能想出许多道理;听一句话,并能做出许多事业。有了这种才力的人,才是先知先觉。由于这种先知先觉的人预先想出了许多办法,做了许多事业,世界才有进步,人类才有文明。所以先知先觉的人是世界上的创造者,是人类中的发明家。第二种人叫做后知后觉。这种人的聪明才力比较第一种人是次一等的,自己不能够创造发明,只能够跟随模仿,第一种人已经做出来了的事,他便可以学到。第三种人叫做不知不觉。这种人的聪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虽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他还说:“照现在政治运动的言词说,第一种人是发明家,第二种人是宣传家,第三种人是实行家。”(同上,第9卷,第323页)
孙中山在这里明确提出,把人一分为三的根据是“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并对“绝顶的聪明”、“次一等”的聪明、“更次”的聪明逐一加以说明,特别是对第一种“有绝顶的聪明”的“先知先觉者”评说得最多,肯定得也最多。
除去上述对人类进化和文明进步所作的划分不论,孙中山这种以人的天赋划分人群的观点有无“合理性”呢?毋庸讳言,人的聪明才力先天就存在差别,它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遗传”或者“基因”不同的结果,这应该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论语》里有一个故事说,有一次孔子问学生子贡:“你和同学颜回相比,谁的能力更强一些?”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同颜回相比呢?颜回‘闻一以知十’,听到一个道理可以推知十个道理,我‘闻一以知二’,听到一个道理只能推知两个道理。”孔子说:“是不如他,我同意你说的不如他。”(参见《论语·公冶长》)颜回的天资在孔子三千弟子中最高,名列第一,是大家公认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的天赋观并没有到此为止,他明确提出“后天力学”可以超过“天赋聪明”:“若由学问上致力,则能集合多数之聪明,以为聪明,不特取法现代,抑且尚友古人,有时较天生之智为胜。例如甲乙二人,甲聪明而不好学,乙聪明虽不如甲,而好学过之,其结果乙之所得,必多于甲。此则由于力学也。”(《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7页)可见,孙中山认为人的聪明实有两种:除了“天赋”外,还有“后学”。“天赋”是与生俱来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天赋的厚薄不同”是无法改变的,否则就无所谓“天赋”了。但是,只有通过后天的努力学习,才能够从无知到有知,从少知到多知,从模仿到创新,从专家到大家,最后甚至超越“天才”。从这个意义上讲,“后天力学”往往比“天赋聪明”更重要。可见,孙中山虽强调了三类人的差异性,但对三者的统一性还是有足够的认识。
二、三种人“相需为用”
孙中山虽然认为人分三种,但他并不认为这三种人是毫无关系的,或者只有消极的、甚至是互相排斥的关系;相反,他认为三者的关系是积极的、互补的或不可或缺的。他说:“有此三系人相需为用,则大禹之九河可疏,秦始皇之长城能筑也。”(同上,第201页)又说:“就是世界上的大事,也都是全靠那三种人来做成的。”(同上,第9卷,第323页)“世界上如果没有先知先觉,便没有发起人;如果没有后知后觉,便没有赞成人;如果没有不知不觉,便没有实行的人。”所以他得出结论说:“世界上的进步,都是靠这三种人,无论是缺少了哪一种人都是不可能的。”(同上,第324页)“文明之进化,成于三系之人。”(同上,第6卷,第203页)
孙中山还深入讨论了三种人各自的作用与独特的贡献,尤其对第三种人的作用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他说,就人数而言,大部分的人都是实行家,都是不知不觉的;次少数的人是后知后觉的宣传家;最少数的人才是先知先觉的发明家。办事之前,特别是办大事、难事之前,想好、说好很重要,否则,别人不知道不理解就没有人会给你办。但是,关键在于把所想的和所说的付诸实践,具体将所想和所说落实,才能把事情办成。光想不做,只能是空想;光说不做,只能是白说。所以,就事情最终能否办成而言,第三种人最重要。孙中山强调指出:“天下事业的进步都是靠实行,所以世界上进步的责任,都在第三种人的身上。”(同上,第9卷,第323页)可见,孙中山对社会实践及其主体的广大劳动者的作用,是很肯定很尊重的。
孙中山虽然也强调第一种人发明家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与贡献,但是他并不认为第一种人是世界进步的“原动者”,而只认为他们不过是“因势乘便之人”而已。这从他对美国的华盛顿和法国的拿破仑这两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证实。他针对有人说:“华盛顿有仁让之风,所以开国之初,有黄袍之拒;而拿破仑野心勃勃,有鲸吞天下之志,所以起共和而终帝制”,精辟地指出:这些人是“不知一国之趋势,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势已成,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转移也。夫华、拿二人之于美、法之革命,皆非原动者。美之十三州既发难抗英而后,乃延华盛顿出为之指挥,法国革命起后,乃拔拿破仑于偏裨之间,苟使二人易地而处,想亦皆然。是故华、拿之异趣,不关乎个人之贤否,而全在其全国之习尚也。”(《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07页)简言之,孙中山并不承认英雄造时势,而是主张时势造英雄。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革命后的建设,是靠孙中山本人和少数人,还是靠广大同志和全国人民?孙中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很清楚的。他在《建国方略·孙文学说》的“自序”的开篇里,先回忆了自己数十年对革命的追求与奋斗:“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紧接着,便把辛亥革命获胜之功归之于全国人民:“卒赖全国人心之顷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翻专制,创建共和。”随后他说到建设也要依靠人民:“以后之建设责任,非革命党所得而专也。迨夫民国成立之后,则建设之责任当为国民所共负矣。”(同上,第157、159页)
后来,孙中山对唤起并依靠民众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深刻。他在临终前夕的《国事遗嘱》里,极其深刻地总结毕生的经验,语重心长地嘱咐:“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同上,第11卷,第639页)
孙中山也曾把人民群众比作“阿斗”,这似乎降低甚至否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其实,阿斗之说是借用古代三国时期蜀国后主刘禅与丞相诸葛亮之间“权”与“能”的差别所做的比喻。他认为,“在君权时代,君主虽没有能干,但是很有权力,像三国的阿斗和诸葛亮便可以明白,诸葛亮是有能没有权的,阿斗是有权没有能的。”(同上,第9卷,第326页)“现在民权政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所以这四万万人都是很有权的;全国很有权力能管理政治的人,就是这四万万人。”(同上)但是,有权力的人们并非人人也有能力,能够担当起国家大事的人绝非是普普通通的人,而只能是少数出类拔萃的精英;至于具有领袖才能的,更是稀若晨星。可见,孙中山认为,广大群众有当家做主的权力,却并非都有管理国家大事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说四万万人民是有权的,但是无能的,是阿斗。这种说法虽然不中听,但却是事实。
三、知觉的普适性及其价值
用“知觉”将人分类,并非始自孙中山,而是古已有之。商初名相伊尹就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上》)这表明,伊尹认为:(1)人可以分为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两种;(2)他本人是先知先觉的人;(3)先知先觉的人应该帮助后知后觉的人,他即以“斯道”去帮助后知后觉的人。所谓“斯道”,即“尧舜之道”。孟子认为伊尹是“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同上)所以,孟子高度评价说:“伊尹,圣之任者也”(同上),即伊尹是圣人中最富有责任感的人。这个故事在古代影响很大,所以《墨子·尚贤上》、《庄子·庚桑楚》、《史记·殷本纪》以及《吕氏春秋·本味》都有所记载,其中以《吕氏春秋》记述最详。
宋代时,有人问程颐什么是佛氏所说的“一宿觉”和“言下觉”?他回答说:“何必浮图,孟子尝言觉字矣。曰‘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知是知此事,觉是觉此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若于言下即悟,何啻读十年书?”(《二程集》第1册,第196页)所谓“一宿觉”和“言下觉”,都是禅宗的顿悟法门。《传灯录》:“永嘉禅师诣曹溪,语契六祖,六祖叹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时谓之一宿觉。”“言下觉”,指禅宗参一句话头,当下便豁然觉悟。程颐认同孟子所言说的知觉,并诠释为知觉此事理。
“知”与“觉”,也是佛教中的重要理念。佛教创立者释迦牟尼与我国老子和孔子是同时代人。当他经过苦修获得“觉悟”后,被尊称为佛陀。而佛陀的意思就是“觉者”或“智者”。佛教认为世俗世界的一切,本质上都是苦的。人生有生、老、病、死、怨憎会(与不喜欢的人或事相会)、爱别离(与可爱的人或事相别)、求不得(得不到所渴望的东西)、五阴盛(佛教认为众生是由色、受、想、行、识这五种生灭变化无常的因素即五蕴构成的,因而充满痛苦)八种苦,所以人生是苦海。那么如何才能“离苦得乐”呢?佛教提出的首要方法是“破迷开悟”。所谓“破迷”,就是破除妄念;所谓“开悟”,就是提高觉悟。赵朴初把觉悟解释为三种,他说:“佛字是‘佛陀’的简称,是Buddha的音译,如果用今天的汉语音译,应当是‘布达’,佛陀的意义是‘觉者’或‘智者’。‘佛陀’是印度早就有了的字,但佛教加了三种涵义:一、正觉对一切法的性质相状,无增无减地、如实地觉了;二、等觉或遍觉不仅自觉,即自己觉悟,而且能平等普遍地觉他,即使别人觉悟;三、圆觉或无上觉,自觉觉他的智慧和功行都已达到最高的、最圆满的境地。”他又说:“佛教认为……一切人都有得到觉悟的可能性,所以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得成佛。’”(赵朴初,第12页)虽然人人都可以成佛,但是关键在于是否能悟:“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坛经·般若品第二》)所以,竺道生和禅宗还强调“顿悟”;进而演绎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云云。
“知觉”问题在冯友兰的“新理学”的哲学体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称之为“觉解”。“觉”是自觉,“解”是了解。他认为:“有觉解是人生的最特出显著底性质。”因为,“这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处。他举了吃、筑室和打仗的例子,这些对于人是有意义底,对于禽兽则是无意义的。因为,动物出于本能,“本能是无觉解底”;而人是出于心,“心是有觉解底”。“宇宙间有了人,有了心,天地万物便一时明白起来。”“宇宙间若没有人,则宇宙只是一个混沌。”(冯友兰,第4卷,第471-483页)冯友兰为了使人生过得有意义,创建了人生“四种境界”说。他说:“人对于宇宙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底觉解,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底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人所可能有底境界,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同上,第496-497页)哲学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学问,这是冯友兰的一贯主张。他在这里换而言之,认为哲学是“自觉解其觉解”之学。他说:“哲学与科学的不同,在于哲学底知识,并不是常识的延长,不是与常识在一层次上底知识。哲学是由一种自反底思想出发。所谓自反者,即自觉解其觉解。所以哲学是由高一层底觉解出发者。”(同上,第489页)
张岱年把人的“自觉”的思想,提到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核心”的高度。他认为,人的自觉就是对于人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特点的明确认识。中国古代哲学的中心议题即是如何做人,研究“为人之道”。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为人之道”在于提高人的自觉,实现人的价值。因此,张岱年进一步把人的“道德自觉性”的思想断定为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中“最重要的”思想和“精华”。他说:“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中还有一些精湛思想,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以和为贵’等,然而最重的是关于人们道德自觉性的思想。这确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他强调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变革的时代,应有一系列的观念转变,但是人应该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仍然是确定不疑的。”所以,“要而言之,古代思想家对于道德自觉性的高度宣扬,在今天仍应加以提倡。”(转引自《张岱年哲学研究》,第460-462页)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对于无产阶级而言也是一种先知先觉者的理论,它要靠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给无产阶级。列宁说:“各国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宁全集》第6卷,第29页)因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同上,第76页)若按照孙中山的分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就是先知先觉者,而接受教育的无产阶级是后知后觉者。
综上所述,孙中山以知觉分人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种的积极意义,主要在于:
其一,他希望对于新的“世界之潮流”和“人群之需要”,至少能有一些人先认识到,然后带领大家共同奋斗。他说:“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28页)
其二,他希望“先知先觉者”把自己“先知先觉”到的新的“世界之潮流”和“人群之需要”之真理,广为告知暂时还不觉悟的人,让他们成为后知后觉者,这是“先知先觉者”义不容辞的使命。
其三,他对于“不知不觉者”,也相信其中的大多数人经过教育和学习,可以由“不知不觉者”转变为“后知后觉者”。在知行观上,他虽主张“知难行易”,但也强调“行”对于知的意义,主张“行而后知”,“行其所不知以致其知”。(同上,第6卷,第222页)这表明他的知觉观始终没有脱离实践的视野。
总之,孙中山作为“三民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他本人当是此学说的“先知先觉者”。他以身作则,毕生不遗余力地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主张,以唤醒人们的觉悟,从而使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载入了史册。如果他的“三民主义”始终不为众人所知所行,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就不会发生,而没有人民大众的积极响应和参与,革命也不会获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知先觉者”与“后知后觉者”、“不知不觉者”都是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