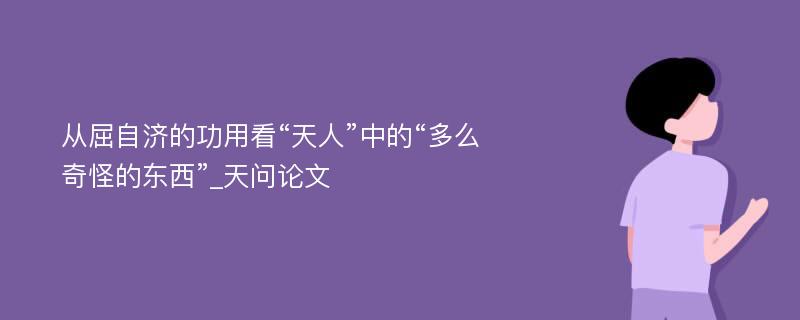
由屈子职司看《天问》“多奇怪之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司论文,之事论文,天问论文,奇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1)02-0056-05
“语怪”是儒家“不语怪”新传统观照下表示思想区分的语汇,与之对应的是“非语怪”传统。屈原《天问》即“非语怪”传统的产物。[1]“语怪”是《左传》《国语》所记录时代周人重要的政治生活方式,这两部书为记载大量外交辞令的经典之作。通过陈述“奇怪之事”,使者达到了自己出使的外交目的,或是维护了本邦权益,或是为父母之邦赢得荣誉。《史记·屈原列传》记录屈子曾为“左徒”“三闾大夫”之职,又载其出使齐国,屈子政治生涯对其“多奇怪之事”诗风形成是否有所影响?下文就屈子外交和职司对此作一推考。
一、屈子使齐与“多奇怪之事”
屈子具有良好的外交素养,文献可考。《史记》记载屈子为楚使齐,《说苑》谓结强党,齐楚结盟关系战国之世大势所在,如此重任而委之屈子,可见其力能胜任外交之职。那么,外交“辞令”是否影响《天问》的风格?《天问》和稷下学术有何关联?
(一)“辞令”与“怪力乱神”。《史记》记屈子“娴于辞令”。所谓“辞令”与“多奇怪之事”关系如何?外交“辞令”有一种形式为“训词”。《国语·楚语下》记王孙圉对赵简子曰“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注谓:“言以训辞交结诸侯”,“口实,毁弄也”。[2]卷一八,526注未解“训辞”为何,经典有“训语”“遗训”之说,或是先王之言,或是往古悠远之事,往往寓有训诫教诲之意。推究起来,“训词”当有与“铸鼎象物”相似的“语怪”叙述。
战国外交辞令中“语怪”并不占有春秋之世那样重要的位置,从《战国策》等文献反映的情况看来,“赋诗言志”和“语怪”作为外交辞令的方式业已式微。这一方面与礼崩乐坏、诸侯竞相追求实用政治的社会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重积累的王官之学下降为重创造的诸子之学的学术风气相连。外交场合代替“语怪”“赋诗”之风的是游辞逞辨、纵横捭阖,这使依傍“稽古”“遗训”的“赋诗”“语怪”政教传统再无合适的土壤。战国时“语怪”之风鲜有其迹,但并未绝迹,比如墨、道两家交接诸侯时就多有“语怪”之辞。据此我们推测屈子“多奇怪之事”的文风形成与其“辞令”仍有一定关系,从《离骚》《天问》以及《九章》(比如《惜往日》)等篇章看,祖述前修、稽考故典乃是屈子常用的说理方式。以此逆推,“语怪”很可能也是屈子独特的外交方式,其“娴于辞令”当包含不少怪力乱神内容。这一判定,可从邹衍学说与《天问》之关系加以蠡测。
(二)稷下学派“语怪”与《天问》“多奇怪之事”。汤炳正依从郭沫若《管子·内业》乃稷下学派道家黄老之说的观点,指出屈原《远游》“于‘道’之外,亦提出‘精气’”之说,正与《管子·内业》相符,故说屈子受稷下之学影响。①其说可参考。《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稷下邹衍之说:
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3]卷七四,2344
邹衍书已经亡佚,赖史迁之记可考其一二。所谓“怪迂之变”之“怪迂”,意同《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李少君死后汉武帝“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3]卷一二,455。“怪迂”意思也就是“迂诞”或“迂怪”:《孝武本纪》载公孙卿对天子之辞,谓仙者“言神事,事如迂诞”[3]472而“《归藏》之经,大明迂怪,乃称羿毙十日,姮娥奔月”[4]卷四,11。意思就是荒诞不经之谈、漫衍无根之说,当然包含语怪叙事。邹衍其说虽以阴阳五行、五德终始为旨归,而杂有“怪力乱神”之谈,以儒家眼光观之,邹子之书乃是“语怪”之作。所以“折中于夫子”的司马迁称论述阴阳五行变化推移的邹衍学术为“怪迂之变”,显有贬斥之意。
邹书的整体结构形式可依据文献还原如下:《史记》云“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就其总体方法言之,大概是总序或概说;“先序今以上至黄帝……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胪列现在以至黄帝进而开天辟地的“谱属”,是古史之类;“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胪列中国及海外风物,是地理风俗,《山海经》整体结构与之相似;“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是结论。
屈原《天问》自“邃古之初”到楚之先王逐一发问,而问题之中又“多奇怪之事”,与邹子“先序今以上至黄帝……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这一部分内容相似。但不同之处是,邹子采取“先序今”“推而远之”的“逆推”之法,而屈子则从“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的“邃古之初”问到楚之先王,顺序恰恰相反。但是整体形式却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参照《管子·九守·主问》“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后,荧惑其处安在”[5]卷一八,1043的问难方式,对比《天问》与邹衍遗说,可确信管子后学与屈子《天问》相通之处。[6]管子、邹衍和屈原都按照天地人三才的大局来结构文章和问难,“天地人”(或者“人地天”)是一种较为流行的问难形式,且这种形式最终要落于人事上。例如,邹子意在推究五德转移为人间政治服务;而上引《管子》之说“人之”,房玄龄注“言三才之道,幽邃深远,必问于贤者而后行之”,“左右前后”后夹注“凡此皆有逆顺之宜,故须问之”,“安在”后注“又须知法星所在也”②:说明管子问难也有深切的人情关怀。此处附带指出,《天问》主题也自然归因于人事。
问难形式上相似,固然可以用文化普遍特征解释,而对“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与“邃古之初”的关注,在先秦却并非普遍;系统的“谱属”式著述则更属罕见,屈子和邹氏是其中最显著的两个例子。这种相似似乎不宜采取文化普遍说解释,倒很可能是文化交流造成的:即便屈子与邹衍未曾相逢,独一无二的“谱属”《天问》的存在与邹衍遗说相似,是否可以说明这是齐楚文化交流的结果?“语怪”正是交流的重合之点。至于究竟是《天问》影响邹衍学说,还是邹衍影响屈子,则难以考据。姜亮夫从文化背景角度评价说:
当屈子之世,稷下诸子彭蒙、田骈……邹衍之学盛于齐;惠施、庄周之论盛于宋、楚……屈子两使于齐,身为楚人,则齐人迂怪之说,惠、庄漫衍之词,林林总总,所闻必多。……盖屈子所陈乃齐楚所习闻,与《老》《庄》《山经》相近,与三晋之《竹书》,韩非、《吕览》等书,同为古史之一系,故不与儒墨之言应也。然观其评骘之言,则多明善恶天道之义,于迂怪之说,复(引按:原作“後”,据延海校改)多疑虑……(屈子)嗜好与孔丘同,则此等乱神之说,迂怪之传,所谓言不雅驯者,屈子盖有整齐百家、諟正杂说之意耳。[7]1005
按照姜氏之说,似乎屈子《天问》是出于伸张孔子“雅驯”之旨,其说是。我们已经说过,语怪叙事本来就充当着和雅驯之言相同的教化功能。姜氏指出屈子使齐与其“语怪”诗风的关联,值得关注。
综上,推知屈子作品的“语怪”特色与其外交当有一定关系,“语怪”乃是齐楚文化交流的重要特征之一。那么,屈原职司是否与“多奇怪之事”有关?
二、屈子职司与“多奇怪之事”
屈原担任过左徒和三闾大夫,这与“奇怪之事”诗风的关系是本文的重点。为此,我先就这两个职司作简单介绍,而后再过渡到《天问》诗风的问题。
(一)屈子职司之检讨。左徒之职,《屈原列传》载之,《楚世家》亦载之:“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3]卷四○,1735这两条记录,为研究左徒官职第一手材料;依据山东出土“左徒戈”阴文,推测楚国遗物13,说可从。那么,左徒之官相当于中原官制何职?今人赵逵夫归纳为六说,为:唐张守节“左右拾遗”说,王汝弼“左史”说,林庚“太子之傅”说,段熙仲“司徒之佐贰”说,姜亮夫“莫敖”说,赵皆驳之而另立“行人”说。[9]不过,诸说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通过相似性论证其同一性。实则,先秦文献中,找出与《史记》所载左徒职责相对应的其他职官并非难事,在“相似为一官”的逻辑下,结论多难以信据。要之,楚国官制见于史传者本极复杂,且多因时代地域变迁有所更革,将之与中原官职比拟,若无明确文献证据而欲下定谳,实非易事。《史记》所记“左徒”职司本已明白,何须另取他官加以比附?
赵氏提出行人之说,可能是受屈子使齐的启发。屈子左徒之职当非行人,但屈子确有行人之能,这便是说,屈原即以“左徒”的身份也可以作为“行人”交接诸侯。如果推定“语怪”是屈子外交方式之一,而“娴于辞令”乃是史迁对“左徒”职司的要求,我们便找到“左徒”与“语怪”联系点之一。但若欲探求屈子作品“语怪”特色的形成,尤其《天问》“多奇怪之事”问题,不妨考虑屈原的另一称谓“三闾大夫”与此有何关联。
有人以为三闾大夫所掌“王族三姓”为熊渠所封三王之后[10],据《史记·楚世家》载,周厉王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3]卷四○,1692,则此说实难信从。又以三闾大夫为莫敖③,然战国之世莫敖之职已非屈氏袭任。
或说“三闾大夫”即“公族大夫”,说似可从。后一名屡见于《左传》。比如《宣公二年》:“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注:“宦,仕也;为置田邑,以为公族大夫。”[11]卷二一,1867《宣公十二年》:“晋魏锜求公族,未得。”注:“锜,魏犫子,欲为公族大夫。”[11]卷二三,1881则公族即公族大夫之省称。《左传》之“公族大夫”权位不低,如郄犨为公族大夫,以主东诸侯。[11]卷四二,2029但“主东诸侯”是否“公族大夫”职责难以考据。公族大夫似多由老年人充任,如宣公二年使屏季、襄七令韩无忌[11]卷三○,1869,则公族大夫非止一人,且由退休的长辈担任。《左传·襄公十六年》:“张君臣为中军司马,祁奚、韩襄、栾盈、士鞅为公族大夫”,注:“祁奚去中军尉为公族大夫,去剧职,就间官。”[11]卷三三,1963据此看来公族大夫是从要职退下来之后的清闲差事。
有人怀疑“公族大夫”即“同姓大夫”,证据是《新序·节士》记载“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12]卷七,42和《史记》“楚之同姓”相应,引《国语·晋语七》“厉公之乱,无忌备公族,不能死”韦昭注“公族,同姓也”为证。[13]56不过古语尚简,一词多义现象很多。《小雅·鹿鸣之什·伐木》“既有肥羜,以速诸父”句,《毛传》云“天子谓同姓诸侯、诸侯谓同姓大夫皆曰父”,《笺》云“今以召族之饮酒”[14]卷九,411。此处所谓“同姓大夫”,原只是诸侯“族人”泛称而已,并非官职。《史记·三王世家》公户满意谓燕王旦:“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异姓也。”《索隐》:“内云有异姓大夫以正骨肉,盖错也。‘内’合言‘同姓’,宗正是也;‘外’合言‘异姓’,太中大夫是也。”[3]卷六○,2118汉代称天子族人“同姓大夫”,则《新序》“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就和《史记》记载“楚之同姓”并无二致,很可能是首先交代宗族关系,再述官职。因此并不能据此断定“同姓”“同姓大夫”就是官职,指“三闾大夫”。况王逸《离骚经》小序:“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15],足证《屈原传》“同姓”并非官职。
要之,左徒交接诸侯,三闾大夫教育子弟。两职与“语怪”是否有关?
(二)“序其谱属”、“辩昭穆”和“多奇怪之事”。《离骚经》王逸序说:“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15]1-2此是叔师对三闾大夫职掌的叙述。如果三闾大夫相当于中原诸国之公族大夫的比拟可以成立,则由公族大夫职掌也就可以大致推定三闾大夫的司掌。
1.“序其谱属”与“辨昭穆”。《礼记·文王世子》:
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爱,明父子之义,长幼之序(注:正者,政也。庶子,司马之属;掌国子之倅,为政于公族者)。[16]卷二○,1407
此处公族指公之族属而言,非官职之谓,而庶子“正于公族”,却似后世公族大夫。《左传·成公十八年》:“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11]卷二八,1923“共俭孝弟”也就类同于《文王世子》所说的“孝弟睦友子爱,明父子之义,长幼之序”,其实就是做好教育工作。此意《国语·晋语七》描述得最详细:
栾伯请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襘文敏,黡也果敢,无忌镇靖,使兹四人者为之。夫膏粱之性难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谂之,使镇靖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则遍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则婉而入;果敢者谂之,则过不隐;镇靖者修之,则壹。使兹四人者为公族大夫。[2]卷一三,40
由于公族大夫重任在肩,关乎公室继承人的素质,故此《国语·晋语八》载公族大夫祁奚之语才说:“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内事之邪,大夫之贪,是吾罪也。”[2]卷一四,424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公族大夫主要主掌庶子的教育,“公族大夫”与“庶子”之官职司相应,据公族大夫或庶子也可以推考三闾之职。《春秋》内外传之义,王逸以“率其贤良,以厉国士”括之。王说可注意的是“序其谱属”一语,或以为即“序昭穆”[17],可参。
《诗经·魏风·汾沮洳》“殊异乎公族”,《毛传》:“公族,公属。”《笺》:“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14]卷五,357则传笺义殊,传意以为是公之族属,而笺意以为公族大夫之官。《诗》本意如何与本题关系不大,不作申述。郑笺道出公族“主昭穆”职司,关于“序昭穆”,《礼记·中庸》“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16]卷五二,1629《周礼》“小宗伯”之职“辨庙祧之昭穆……掌三族之别,以辨亲疏”,注“祧,迁主所藏之庙,自始祖之后,父曰昭、子曰穆”,“三族,谓父子孙人属之正名”。[18]卷一九,766看来这个“谱属”与三族父子孙的“正名”相关。
王说“谱属”,自是“王族三姓曰昭景屈”之谱。至于“王族三姓”,洪兴祖、王应麟说同④,《庄子·庚桑楚》谓“是三者虽异,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陆德明《音义》以为:“虽非一姓,同出公族”。[19]卷八,804则三姓之说不无依据,王说不宜轻易否定。至于“三闾大夫”之“闾”,汤炳正援引《战国策·齐策》(六)“东闾宗族离心”等语,以为“考公族相聚而居,乃战国时期各国之通例,不专为楚国所特有。盖当时贵族与其它官吏平民,界限极严,不能同闾”。[20]53其说甚是。
如上所述,“序其谱属”可与中原文献“序昭穆”相互参拟,那么,这两者和《天问》“多奇怪之事”有什么关联?
三闾职掌即公族大夫——庶子之官具体职司虽无直接文献证据,依据相关材料也可以作一推想。《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公九教”可考见楚国教育之一斑,庄王使士亹傅大子箴,辞而不得,王卒使傅之,所教的典籍有《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注云:
“以天时纪人事谓之《春秋》”,“《世》,先王之世系也”,“《令》,先王之官法时令也”,“《语》,治之善语”,“《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训典》,五帝之书也,族类谓若惇叙九族;比义,义之与比也”。[2]卷一七,485—486
而中原教育与楚国不同,《礼记·王制》《文王世子》记录中原教育曰: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16]卷一三,1342春诵、夏弦,太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16]卷二○,1405
此即“乐正四术”,“术”“教”用词虽略有区别,然所记当是反映周室太子教育内容。
将乐正四术与申公九教合而观之,中原和南楚教育不外乎礼乐诗书等;但楚国教育极为重视包括《世》在内的历史叙述,而《世》就是《世本》《帝系》之类书籍。战国之世楚国教育制度即有变更,亦不会脱离诗书礼乐以及世谱等主要方面,三闾大夫“序其谱属”之司,似乎亦与申公九教重视世谱教育有渊源。
从以上楚国太子的教育看来,古史占据了显著位置,《春秋》(可能是《梼杌》之类)《训典》《世》等古史内容正是儒家视为多含“怪力乱神”之书,或者就是“多奇怪之事”的文化来源。这些典籍都是儒家确定“不语怪力乱神”观念、删定诗书之前“非语怪”传统下的产物,因此说楚国教育中多有“语怪”叙事可能并无大误。如果“三闾大夫”确相当于“公族大夫”一类职务的话,我们就找到了屈原的这个职司与《天问》“多奇怪之事”的联系。
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序其谱属”,此点或可以比拟于中原之“序昭穆”,我们必须避免的问题是将掌管“谱属”“世”归于三闾独有之职,实际先秦职司交叉、一官多职的情形文献所载并非罕见,似乎应当破除某种职司一定归于某官的胶柱鼓瑟之见。由于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本文只探求屈子政治生涯对其“语怪”特色形成的可能性。
2.“序昭穆”与“多奇怪之事”。关于“序昭穆”之事,汉儒已不得其详,今不具说。然“序昭穆”意思应当理解为排列先公先王列祖列宗之次则属无疑,故此事必与“谱属”有关,屈子职掌为何虽不得其详,然仍可依据其他类似职司推想大略。比如《周礼》“小史”“大史”也掌管昭穆之事:
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注:“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瞽蒙讽诵之。”疏:“云辨昭穆者,《帝系》《世本》之上皆有昭穆亲疏,故须辨之”)。[18]卷二六,818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注:“大祭祀,小史主叙其昭穆,以其主定《系》《世》、祭祀;史主叙其昭穆,次其俎簋”)。[18]卷二六,828
申公九教之《世》和此处所引之《系》《世》,皆可用以解释“谱属”,乃是关于帝王或者诸侯世系族谱等历史著述。孔疏指出“序昭穆”实与《帝系》《世本》等“谱属”有密切关联,那么屈原“序其谱属”就应当有机会接触大量《帝系》《世本》一类的经典。而“奠系世”又与“志”密切相关。《周礼订义》“小史中士八人……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句引用郑锷之说以为:
若夫邦国之《志》非杂记邦国之事,乃志诸侯所出之世系与其庙祧,昭穆之《志》如鲁出于周公、郑出于桓公、晋出于叔虞,世系绵远,传序寖多,昭穆久而或乱,王朝亦有《志》以记之,小史掌其志、奠其本系之所出与世数之远近。[21]卷四四,75
郑锷之义,小史所掌邦国之《志》乃记“世系”“庙祧”之书,则此《志》亦《世》也。而《周礼》有所谓外史之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疏:
彼《三坟》三皇时书,《五典》五帝之常典,《八索》三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国之戒。[18]卷二六,820
依据上疏,如果三皇五帝之书是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话,外史所掌,与诵训有关⑤,与其说更近于儒家常道⑥,毋宁说因其甚古而更近于“非语怪”的传统。屈子“序其谱属”自不能简单等同于小宗伯或小史之“辨昭穆”或是外史之掌“三皇五帝之书”,但掌管与《帝系》《世本》一类有关“谱属”的书籍当可确定。这些书籍当多“语怪”之作,成为《天问》“多奇怪之事”的“谱属”诗形成诱因之一。
总之,通过屈子职司的考察,可知《天问》“多奇怪之事”的诗风打上了屈子仕宦经历的烙印,屈原的“语怪”根植于当时的政教传统,而非空穴来风之作。理解了这点,也就能够更好地把握《天问》之诗学特质,而不是仅仅将其当作史料。
注释:
①汤炳正:《远游与稷下学派》,载《楚辞类稿》,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383页。又,自清中叶胡浚源(《楚辞新注求确·凡例》)认为《远游》“明系汉人所作”后,学者多否定或怀疑王逸之“《远游》者,屈原之所作”说。不过,笔者认为否定或怀疑屈原作《远游》的种种理由均难成立,然此前汤炳正(见《屈赋新探·论〈史记〉屈、贾合传》及《楚辞类稿·〈远游〉与“四荒”“六漠”》)与力之(《〈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远游〉考辩》等)辨之甚明,兹不赘。
②黎翔凤校注引王念孙之说:“‘荧惑’犹眩惑也”,他并据《鬼谷子·符言》校“四曰”为“四方”,认为“‘四方上下’承天地而言,‘前后左右’承人事言。‘荧惑’谓不明于天地人之道也”,“非谓法星安在也”。俞樾注“荧惑”同于王说。检《鬼谷子》,陶弘景注亦以“荧惑”为天之法星,与《管子》房注一致。陶注以为“夫四方上下,左右前后,有阴阳相背之宜。有国从事者,不可不知。又荧惑,天之法星,所居灾眚吉凶尤著。故曰虽有明天子,必察荧惑之所在,故亦须知之”(许富宏:《鬼谷子集校集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182~183页)。陶注之意,则荧惑实际不单单指星占,而是有天人合一的政治文化背景。故而以其为“法星”并不错误。诸家所校皆非。
③参左言东《楚国官职考》(《求索》,1982(1))、刘先枚《楚官源流考索》(《江汉论坛》,1982(8))。
④《楚辞补注》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困学纪闻》卷一一:“汉兴,徙楚昭屈景于长陵,以强干弱支,则三姓至汉初犹盛也。……三闾之贤者,忠于宗国,所以长久。”(《四库全书》本854册第365页下栏。)
⑤孙诒让以为:诵训所掌“方志”即外史四方之志,所以识记久远掌故,外史掌其书,诵训为王说之,“告王使博观古事,二官为联事也”(《周礼正义》卷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96页)。从这一角度也可以理解“非语怪”传统与王官之学的关系。
⑥《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赞左史倚相之语:“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关于这几样书,《正义》曰:“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五,第2064页中栏)所说“大道”“常道”,其实就是所谓的雅驯之道,本身属于“非语怪”传统分化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