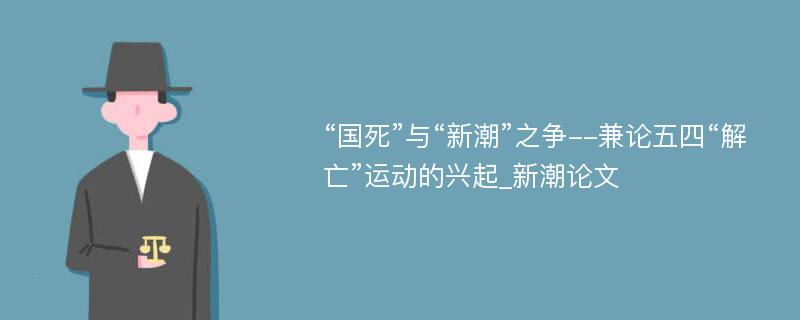
《国故》与《新潮》之争述评——兼论五四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故论文,新潮论文,述评论文,之争论文,兼论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4)01-0039-06
“整理国故”作为一种广义上的个人学术活动,或许不妨说是古已有之,然而作为一场学术文化运动,尤其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及其延续,“整理国故运动”肇始的标志则无疑是胡适《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的发表。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胡适首次鲜明揭橥了“整理国故”的口号。而溯其根源,该文与《国故》与《新潮》之争不无相关。
一
1918年11月,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新潮》社,旨在“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注: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岳玉玺等编《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6页。)并请胡适担任顾问。而与傅斯年同班的薛祥绥、张煊、罗常培等,则“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遂于1919年1月26日,在刘师培宅内成立了《国故》月刊社,标明“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注:《国故月刊社记事录》,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1912-1937)第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15页。)
所谓《国故》与《新潮》之争,缘起于1919年5月,毛子水在《新潮》发表了《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对《国故》的办刊旨趣提出了尖锐批评,傅斯年还为此撰写了一段编者附识。当月,《国故》社编辑张煊也随即刊发了《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回应毛子水的批评。10月,毛子水又在《新潮》上发表《〈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一文,并同时附录胡适8月16日《论国故学》一函,对张煊的观点再加批驳。此后,由于《国故》社的解体,双方争论也自然终结。
关于这场论争,已不乏有论者详加论述,(注: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因此本文在此不再多赘,仅拟就争论双方观念的异同,做力求简明的概括。综合来看,毛子水、张煊之间的互相辩驳和傅斯年、胡适的先后介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国故之生死”的性质判分上,双方的论断针锋相对。
一方面,毛子水将“国故”断定为“过去的已死的东西”。(注: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1919年4月19日),《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以下凡引本篇,不再注明出处。)而另一方面,作为《国故》成员的张煊,自然难以接受这一结论。在驳文中,他首先质问:“毛君乃谓国故为已死,夫生也死也,果何所准?”接着,他提出并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国故之生死,将视治之者之何如。使国人皆弃置之勿复顾,或即治之而但为陈死人之陈列,不求进步,不肯推故演新,则信乎其且死矣!使国人之治之者尚众,肯推已知而求未知,为之补苴罅漏,张皇幽眇,使之日新月异,以应时势之需,则国故亦方生未艾也。”尤为关键的是,在他看来,“今之治国故者尚大有人在,以抱残守缺为已足者固偶有之,而肯精益求精不甘自封故步者,亦未尝无其人,谓之已死可乎?”(注:张煊:《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国故》第3期,1919年5月,以下凡引本篇,不再注明出处。)
第二,在“国故与欧化”的地位比较上,双方的估量也不无悬殊。
毛子水认为:“国故是过去已死的东西,欧化是正在生长的东西;国故是杂乱无章的零碎智识;欧化是有系统的学术。这两个东西,万万没有对等的道理。”由是,“国故虽然应当研究,但是比较起现在世人所应当研究的科学起来,直是‘九牛一毛’。……现在我们中国人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吸收欧洲现代确有价值的学术”。傅斯年更是在《附识》中,对此予以了进一步的精确化。他说:“研究国故好像和输入新知立于对待的地位,其实两件事的范围,分量,需要,是一和百的比例。”(注:傅斯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附识》,《新潮》第1卷第5号,以下凡引本篇,不再注明出处。值得一提的是,罗志田先生将傅氏此论视为“在比例上大大发展了毛的说法”(参见其《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一文),似乎不确。因为如果相对毛氏“九牛一毛”的说法,傅氏此论应是大大缩小。究其缘由,罗志田先生的论断似乎是相对毛氏“十五和一的比”而言,但毛氏此说的所论对象是“西洋文明和东洋文明”,并非“国故与欧化”,而且是在后来《〈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撰于1919年8月15日,刊《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一文中才提出,从时间上看是在傅氏之后,所以谈不上傅氏对毛氏的“大大发展”,罗志田先生于此或存在着史料顺序的误解。)
对于这种明显贬低“国故”地位的观点,张煊起而申辩说:“国故,东洋文明之代表也;欧化,西洋文明之代表也。今日东西洋之文明,当然处对等地位。”他还以“造纸”为喻论证说:“譬诸造纸,将来之新文明为新纸,国故犹败布,欧化犹破纸,为造新纸故,破纸固不可弃,败布亦所当宝,败布与破纸其能改造为新纸则一也。……收拾国故与输入欧化,皆为拾败布收破纸之事业,……二者正宜相助而不宜相斥。”并且申明:“吾敢正告今日之学者曰:凡学无论其属于国故,抑属于欧化,皆有研究之价值,皆当尽力发挥。”不过,或许出于对世人群趋“欧化”的忧虑,他又呼吁道:“在世界学术方面观之,与其得一抄拾欧化之人,毋宁得一整理国故之人。抄拾欧化,欧化之本身不加长也;整理国故以贡诸世界学术界,世界反多有所得。”
张煊这番议论,立即招致毛子水的辩驳。他语带讥讽地批评说:“张君的文章,说来说去,不过要把‘国’和‘故’争一个地位”。与此同时,他敏锐觉察到张煊在争论中偷换了概念。关于“国故”与“欧化”的概念,他原来的界定分别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以及“欧洲现代的学术思想”,而张煊却易之为所谓“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之代表。对此,毛子水表示:“国故为东洋文明代表的说话,我不敢承认。我以为国故还不够代表中国的文明,——因为国故只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分,——怎样能够代表东洋的文明呢!欧化为西洋文明代表的说话,亦有语病。‘欧化’的广义,就是全副的西洋文明,有什么代表不代表。”
至于张煊所谓“今日之东西洋文明,当然处对等地位”的论断,毛子水也不予认可。他详细分析说:“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怎样能够处于对等地位呢?照我的意思,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无论在程度上面或在分量上面,都不是立于对等地位的。就算将来世界的文明是从东西洋文明配合而产生的,我们亦不能就说他们立于对等的地位。一两和十五两成为一斤:这个一两和这个十五两,除同为加法中的一个相加的数目外,并没有对等的道理。现在西洋文明和东洋文明的比,何止十五和一的比呢!”
随后,毛子水仍然回到“国故与欧化”地位比较的正题,申明:“再退一步说,就算东西洋文明处于对等的地位,我们亦不能用此证明国故和欧化是出于对等地位的;因为国故并没有代表东洋文明的资格。”况且,“国故和欧化对于究竟的真理,有阶级的区别。将来的新文明,应以这个究竟的真理——或离开这个真理最近的‘真理’—为根据:所以国故和欧化对于将来的新文明,并不是败布和破纸对于新纸可比。……我们的国故学者,多存一种国故和科学并立的意思,实在是很不对的。”(注: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罗志田先生认为“毛子水一度疏忽而接受了张的概念(‘东西洋文明’——引者按)来展开讨论”(参见其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一文),其实毛氏对此始终十分警觉,始终未曾离开过“国故与欧化”的主题,他之所以谈论“东西洋文明”,无非是为了使其反驳更具针对性。既然说不上是“毛子水一度疏忽而接受了张的概念”,那罗志田先生所谓“傅显然觉察到毛已从自己的立场上移位,故婉转地将比较的对象回缩到‘研究国故’和‘输入新知’之上”的推测,则或属无据,而且在时间顺序上,亦存在着错次现象。)
第三,在“研究国故”的目的上,双方的认知亦截然异趣。
关于“研究国故”的目的,毛子水曾经说明:“一是因为国故特有的长处,一是因为国故偶有的长处。”具体说来,前者指“研究国故”犹如“解剖尸体”,他认为:“我们倘若用这样目的去研究国故,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从前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所以不很发达的缘故;我们亦就可以知道用什么法子去救济他。”至于后者,则指的是“国故的研究,大半的事情就是疏证。……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研究国故,养成一种‘重征’‘求是’的心习,亦是有点好处的。”毛子水同时还尖锐针砭说:“现在有一班研究国故的人,说他们的目的是‘发扬国光’,这个意思,最为误谬,要知道,研究国故能够‘发扬国光’,亦能够‘发扬国丑’。……我很希望研究国故的人,照这个意思做去!知道这个意思,那‘古训是式’‘通经致用’等许多学术思想上阻碍的东西,就可不言自破了。”
但是,张煊并未就此“不言自破”。相反地,他还针对毛子水所谓“养成一种‘重征’‘求是’的心习”的说法,以研究声韵为例反驳道:“譬之研究声韵,其目的非为得声韵学史也,亦非为欲得‘重征’‘求是’之心习也,为欲知声音变化之通例,知将来之声音究应如何也。以古音推古通借字而得古书之真诠,特其副产品耳。……非特研究声韵为然也,其余各学,莫不皆然,但整理之使为学术史之材料,实未足以满吾人研究斯学之望也,实未足以得研究斯学之最后果也。”
鉴于毛子水在此后《订误》一文中,未能直接击中张煊上述言论的要害,胡适特意致信声援。他指点毛子水:“张君的大病是不解‘国故学’的性质,……‘补苴罅漏,张皇幽眇’,还可说得过去。‘使之……应时势之需’,便是大错,便是完全不懂‘国故学’的性质。‘国故学’的性质不外乎要懂得国故,这是人类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若说是‘应时势之需’,便是古人‘通经而致治平’的梦想了。”(注: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1919年8月16日),《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321页。)
第四,在“研究国故”的方法上,双方对“科学的精神”的理解也大相径庭。
正如毛子水所自述:“我那篇文章,意在提出一种研究国故的方法,……我写出《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那篇文章,就是要向那班梦梦的国故学者说法。”(注: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他在文中一再强调:“倘若要研究国故,亦必须具有‘科学的精神’的人”,并指斥说:“近来研究国故的人,多不知道国故的性质,亦没有科学的精神。他们的研究国故,就是‘抱残守缺’。”他甚至还直接点名批评:“至于国内讲国故学的杂志,前有《国粹学报》等,最近有《国故》,用意皆很好。但是他们里面所登的,有许多亦似乎缺点科学的精神。”傅斯年也在《附识》中说:“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决不是‘抱残守缺’的人所能办到的。”
由于当时“科学”一词风头正劲、几乎无与匹敌,张煊虽然不无微辞,却也未便与之正面抗衡,于是他采取了颇费周章的迂回策略,(注:毛子水就指出张煊在此是“笔锋纵横,意在言外,兼有一唱三叹之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转而对毛子水关于“科学的精神”的界说提出质疑。毛子水曾经诠释说:“这个名词,包括许多意义,大旨就是从前人所说的‘求是’。凡立一说,须有证据,证据完备,才可以下判断。对于一种事实,有一个精确的公平的解析;不盲从他人的说话,不固守自己的意思,择善而从。这都是‘科学的精神’。”对于这种界说,张煊首先从称谓上加以推敲:“其所谓科学之精神者何?即从善服义是也。……从善服义之精神,与人性有关,而与研究之学科无关系,与其称谓科学之精神,不若称谓问学之正道之为当。”继而,他斟酌道:“夫从善服义,固问学之正道,假令其所谓善者非善,而所谓义者非义,而责人从、责人服,是谓纳人于邪,非正道也。”
对于张煊这番质疑,毛子水立即纠正其中的误读之处:“‘科学的精神’这个名词,包括许多意义,并非专指从善服义,……张君的文章,似乎有误解名词的毛病。”经此“订误”,他再次重申:“怎样的人、用什么方法才可以整理国故呢?我现在敢说,不是曾经抄拾过欧化的人,不是用科学的方法,一定不能整理国故。”(注: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
显而易见,在诸多问题上,双方的观念均相互抵牾,《国故》与《新潮》之间的对峙也由此凸显。当时便有舆论介绍说:“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注:《请看北京学潮思潮变迁之近状》,《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转引自《北京大学日刊》第338号,1919年3月21日。)
但在这场论争中,双方实际上也表现出某些共通之处。鉴于长期以来的研究对此似乎有所忽略,本文拟就此展开一番探讨。
第一,双方都将“国故”视为“材料”。
毛子水曾申明:“我们把国故的这一大部分,不看作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看作中国民族过去历史的材料。”他继而直截了当地提出:“我们简直可以用‘中国过去历史的材料’代替国故这个名词。”傅斯年也在《附识》中强调说:“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事实上,张煊也认同这种观点。他甚至还进一步加以发挥,将“国故”形象地比喻为“造纸”的材料——“败布”。(注:应该指出的是,毛子水所谓“材料”主要是指“整理国故”的材料,而张煊所指的则是“再造文明”的“材料”,二者并不直接等同。至于傅斯年所说的“材料”,似反而与张煊较相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后来亦表示:“我今日从事研究整理,好似到了造纸厂中做拣理破布败纸的工作”(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1926年4月20日,《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06页),这或许也是受到张煊的感染。)
第二,双方都主张“输入欧化”。
在此同题上,毛、傅二人自不待言。毛子水还以章太炎《原学》和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为例,论证说:“他们所以有这个意识,欧洲的学术史亦应当有点影响。”而张煊同样也指出:“夫以国故为至高之学,谓即此已足,无事外求者,信乎其无世界眼光矣!”并声明自己“非反对输入欧化也。输入欧洲物质文明,实亦今日当务之急”。与此同时,他还就如何吸收西方“精神学术”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第三,双方都承认“整理国故”的必要性。
毛子水虽确信“国故在今日世界学术上,占不了什么重要的位置”,不过他也承认:“照得我个人的意思,国故是应当研究的”。他并且表示:“从已有意思生出新意思来,在国故学里,亦是常有的事情”,这显然意味着对“温故知新”的肯定。(注:罗志田先生认为“温故知新”之意是张煊所提倡而毛子水反对的(参见其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一文),似不尽合毛氏本意。)傅斯年则不仅将毛子水所谓“九牛一毛”的比,明确缩小为“一和百”,而且说:“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中国是个很长的历史文化的民族,所以中华国故在‘世界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等等的材料上,占个重要的部分。或者因为中华国故的整理的发明,‘世界的’学问界上,生一小部分新采色,……亦未可知。”尤其在他看来,“中华国故里面或者有几项可以提醒我们(Suggestion)。”(注:傅斯年在1950年曾说:“传统是不死的,在生活方式未改变前,尤其不死,尽管外国人来征服,也是无用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它的缺欠已经成为第二天性,抹杀是不可能的,然而必须拿现代的事实衡量一番,其中应改的东西,不惜彻底的改,应扩充的东西,不惜彻底的扩充。战前有‘本位文化’之说,是极不通的。……与此相反,便有‘全盘西化’之说,这又不通之至。一个民族在语言未经改变之前,全盘化成别人是不可能的。前者一说是拒绝认识新时代,后者一说原不能自圆其说”(《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傅斯年全集》第6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124-125页)。这番议论表明他虽较趋新,但并非全盘否定传统。)
对于“整理国故”的意义,张煊更是不遗余力地予以彰显。他说:“学者之所孜孜以求者,未知者也,新也;其所根据以求未知与新者,已知者也,故也。……故以进化言,新者未来之称号,故者求新之根据。”这正与毛子水“温故知新”之意相合。他还进一步比喻论述道:“收拾国故之材料者,犹之拾败布之工人;整理国故,犹之退败布各种色彩污秽之化学工作,虽非亲自造纸之人,而其有功于造纸,则与造纸工人正等”。
此后,毛子水虽在《订误》一文中仍断言:“倘若我们把国故整理起来,世界的学术界亦许得着一点好处,不过一定是没有多大的,……就世界所有的学术看起来,比国故更有用的有许多,比国故更要紧的亦有许多”。但是,他也肯定:“国故有研究的价值”,并不无认可地说:“国故也有国故的好处,我们当然不可绝对的蔑视他。凡是绝对的蔑视国故的人,就是没有方隅的眼光。我们要评论一种学术的价值,要具世界的眼光,亦要具方隅的眼光。”
至于胡适,则更明确指出:“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注: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1919年8月16日),《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321页。)他甚至批评毛子水:“你的主张,也有太偏的地方。……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由此出发,胡适认为:“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
第四,双方都具有“再造文明”的潜在目标。
毛子水曾明言:“现在我们中国人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吸收欧洲现代确有价值的学术,一来医治我们学术思想上的痼疾,二来造成一个能够和欧化‘并驾齐驱’的‘国新’。”傅斯年也说:“我们若要做古人的肖子,也当创造国粹,(就是我们自己发明点新事物),不当保存国粹。”此处二人所谓“造成国新”与“创造国粹”,当然代表了他们内心中的某种目标。
有意思的是,张煊也表示:“吾人之研究国故,非为保存败布,实欲制造新纸。……造纸工业不当止于收拾败布及退其色耳。……收拾国故与输入欧化,皆为拾败布收破纸之事业,虽俱有功于造纸,而其非即造纸则一。”这番言词明显流露出他对所谓“新文明”的孜孜以求。(注:应该指出的是,关于“新文明”的实现手段,双方主张不同,张煊注重于“整理国故”,毛、傅则强调“输入欧化”。)
由此可见,在某些方面,双方的观念实际上相当接近。刘师培即澄清说:“《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注:《刘师培致公言报》,《北京大学日刊》第341号,1919年3月24日。)
今天看来,这场论争的意义正在于:双方经过激烈的交锋,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拓展了再思考的空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自发地萌芽了某种“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意识,而这对胡适显然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和启发。正是在此基础上,胡适经由自觉总结,撰写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
二
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该何去何从?《国故》与《新潮》之争以后,新文化派对传统文化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面对这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1919年11月,胡适撰写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在该文中,胡适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毋庸置疑,其中对于“研究问题、输入学理”关系的解说,仍主要是此前“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余音绕梁。(注: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即曾建议读者参看此前围绕于此的四篇论战文章,可见该文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延续,参阅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一集,第532页,以下凡引此文,不再注明出处。)但就“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而言,则更多的是对刚刚结束不久的《国故》与《新潮》之争的反思和总结。
在此文开篇,胡适劈头就阐明:“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由此出发,他具体分析说:“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这两项是新思潮的手段。”
接着,胡适针对“新思潮的运动对于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持什么态度”这一问题明确表示:“我的答案是:‘也是评判的态度。’分开来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
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在他看来,“盲从是评判的反面,我们既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自然要反对盲从。……因为评判的态度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
与此同时,胡适还申明:“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他并且阐释说:“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至于如何“整理国故”,胡适提出了四个步骤,并分别加以论述。他指出:“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因为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故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因为前人读古书,除极少数学者以外,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因为前人对于古代的学术思想,有种种武断的成见,有种种可笑的迷信,……故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他还批评说:“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
最后,胡适总括说:“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
对比于《国故》与《新潮》之争诸文,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论述所谓“整理国故”四个步骤时,他对“国故”的看法,显然是汲取了毛子水认为“国故”是“杂乱无章”的观点。(注:毛子水这种观点,包括以下“科学的方法”与“历史进化的眼光”等等,当然有可能原本便是受胡适的影响,但胡适在此重申,则应是受到《国故》与《新潮》之争的触动。)他一再强调的“科学的方法”,也无非是重申了毛子水、傅斯年的见解。至于他主张用历史进化的眼光寻出学术思想的渊源,则明显是对毛子水、张煊二人所达成“温故知新”共识的肯定。而他之所以在此时重提“再造文明”,更无疑是受到了《国故》与《新潮》之争的直接触动。(注:诚然胡适早在留美期间就已萌发了“造新文明”的设想,不过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毕竟不见他提及,而此时重提,则应是对《国故》与《新潮》之争的总结和反思。)
但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胡适也对“整理国故”做出了独特贡献。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明确提出了“评判的态度”以及“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主张,从而高屋建瓴地制定了“整理国故”的指导思想,而且还系统完整地揭橥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提纲挈领地阐明了“整理国故”的宗旨。缘是,“整理国故运动”得以骎骎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