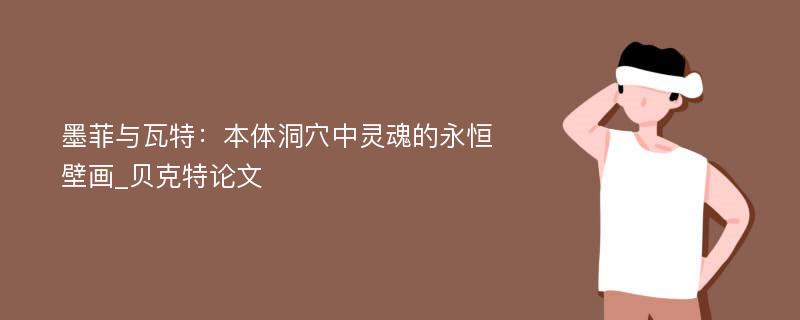
《莫菲》与《瓦特》:“本体论洞穴”中永恒的心灵壁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洞穴论文,壁画论文,心灵论文,莫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萨缪尔·贝克特:本体论洞穴学家
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以独特的艺术形式——“边界景观”对存在的根本特征和精神心灵的问题进行了最严肃的反思。对他而言,“自我是不可知的,所以当人面对自己时就是在瞭望深渊”。①在当代艺术中不乏引人进入边界之外世界的作品,但如何洞悉当代的“人类状况”,却只有贝克特为我们提出了许多恰当的问题。他似乎具有天生的能力,能够感觉深渊之外、“冥河”以远、墙壁或门槛以外的精神世界。所有这些词都是一个心理现实的图画,都是恐怖的边界地带,它们划分出两个意识领域,这样的意识领域通常不是被我们意识到的,而是由像贝克特这样的熟谙现代经验的“复活人”和诗人向我们报告的。从他始于精神绝境的“荒诞”旅行我们发现贝克特真实地描写了事物在临界处的真实状态。这些被揭示出来的真相令人震惊,它们并非与我们日常的意识相吻合,却像我们在心灵深处感到的那般纯真。在这条内在化和沉思之路上,贝克特发现了进入我们内心另一世界的边界线,并自觉地诗意地跨进了不可知的彼岸。在这个超越了更为主观的经验的边界领域,贝克特“用一种内心经验进行创作,这类内心经验自从伟大的神秘主义者的时代以来就被人们忽视了”。②这是一种虚空的经验,它表现为一种想象力和直觉的创造力的源泉,凭借这种力量他深入到未出生和死亡的世界,并通过他的文本把他的内心经验从所谓的虚无的前语言世界转变成词语的存在。
贝克特义无反顾地躲进本体论的“洞穴”记录人类状况或人类困境,在“心灵地图”上绘制“虚构地形学”,以哲学幻想重新创造形而上学寓言。同时,他试图突破“洞穴”墙壁这条边界线,因为他认为高明的作家“让那种令自身名誉扫地的‘空无’原封不动,在上面一个接一个地钻孔,直到潜伏在背后的东西——不论那是有还是无——从中渗出”。③贝克特所作的这一突破是通过他最执迷的意象——光明与黑暗来进行的。在他这里,光明与黑暗的相互变化是两种基本的运动。贝克特构筑的边界地带的典型特征就表现为这两种运动的同时性所产生的悖论。从这位内心世界的探索者的文本中(也从贝克特研究的文本中),我们发现几个可以称为光明与黑暗对立运动的“边界隐喻”,诸如“球体”、“头盖骨”、“子宫”、“坟墓”和“嘴唇”,而这些意象又可以看成是“洞穴”的不同表现形式;因此,不妨把“洞穴”隐喻作为阐释贝克特美学的出发点。
贝克特文本对光明与黑暗交替运动的一贯描绘,他对心灵、自我与他者的不懈寻觅都可以同柏拉图的“洞穴之喻”相比。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二卷中把陷于现象世界的人类比作一个被关在地下洞穴的囚犯。囚犯试图逃离洞穴对应于人对启蒙和智慧的追求。如果“洞穴”之中的世界相应于可感的或非理性的世界,洞内的囚徒与我们相像,代表人类的状况,那么贝克特则是一个从洞外的理智世界赶往洞内去“刻画”,去“拯救”我们自己的人。为此,他将跨越界限也将建构起一个“边界地带”,并发现自己早已身在其中。
要阐释贝克特经历或体验的这一过程,我们最好常常到雅克·拉康那里去拜访。我们发现拉康延伸并改变了柏拉图的洞穴寓言:“上述地点正是通往那个著名的洞穴的入口,据说柏拉图在其中引导我们走向出口,而人们想象他们看见精神心理分析学家正往里走。但是情况远非那么简单,因为这是一个直到它们马上要关闭时你才能抵达的入口(这个地方永远也不会吸引游客),因为将之打开的唯一方式是从里面大声叫喊。”④马尔科姆·鲍伊(Malcolm Bowie)解释说,“每当我们到达无意识的洞穴总赶上它关门的时间;我们进入的唯一方式是已经在里边了。无意识的结构只有对于那些准备接受和拥抱它难以穷尽的移置的能力的人才是可以认知的。”⑤贝克特无疑正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批评家认为,“他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可称为本体论洞穴学家(onto-speleologist)。”作为“总是触动理智的艺术家”,贝克特“把他的内心探索,他的精神寻觅,描写为一个科学的洞穴居住者、一个挖掘者的探索,与世隔绝地居住在一个黑暗或朦胧的洞穴内,在墙上作画”。⑥这个“洞穴”应该是内在与外在、自我与他者的一个边界王国。这使他获得了一个穷尽式地分析某一特殊经验区域的本体论场所,并最终建构起一个“精神之乡”。
对贝克特而言,个体意识成了行动的竞技场。他对一个内在化的剧场的寻觅,不是使他接触到旧时代和遥远之邦的诗情画意的传说,而是带他到自己内在现实的现象学。从这个意义上讲,贝克特声称他看中的最好的作品写于1945年到1950年间,⑦从而把《莫菲》(Murphy,1938)和《瓦特》(Watt,1953)排除在外,掩盖了他的主要的痛苦的主题源于心灵和精神的困惑这个原初的事实。尽管这两部小说也许可以看作是摆脱乔伊斯影响的最后练笔之作,但《莫菲》的世界几乎没有我们在象征主义小说中期望看到的试金石。康拉德、劳伦斯和乔伊斯的象征主义作品似乎是日常问题的现实主义投射,而《莫菲》更像是展现一个哲学问题,而非普通意义上的小说。而且,作为贝克特的第一部英语小说,《莫菲》包含着一些将在后来作品中详细展开的要素,也是一个展现前期和后期创作区别的参照点。
《瓦特》作为贝克特最后一部主要的英语小说和“他的第一部关于嘲笑和悲痛的史诗”,标志着他的作品一个特别重要的过渡,“它是那种混乱世界的肇始,这种混乱世界随后将被认为是典型的贝克特的世界”。⑧该书写于1941至1945年间,但与《无法称呼的人》和《等待戈多》同年出版。这样,《瓦特》就与《莫洛伊》和《马龙之死》一样,或被束之高阁以备今后仔细玩味,或被愤然弃之如敝屣。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会觉得它要么混乱不堪要么构思精巧,要么无聊乏味要么魅力不凡,要么毫无意义要么意味深长,要么荒诞不稽要么悲情恣肆。这部作品究竟属于哪一种情况,不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贝克特而在于如何正视我们自己。
综合起来看,贝克特低估了这头两部小说的价值。除了预示着“三部曲”主要关心的问题,《莫菲》和《瓦特》也是优秀的喜剧作品;它们是关于认识论问题的戏仿和阐述他对自我及其认知界线的解读的“元小说”。
二、《莫菲》:在“洞穴”里描绘“精神之乡”
在《莫菲》中,莫菲在马格德林精神病收容所(Magdalen Mental Mercy-seat),寻找介于精神和物质之间的中间物。Magdalen是Magdalene的变体,后者有妓女收容所之义;Mercy seat语出《圣经·出埃及记》,是按在约柜上的金盖,被视为上帝休息的地方。因此,应该把这个所谓的精神病院看作是介于心灵与世俗之间的一个边界地带。
在这部小说中,年轻的贝克特描绘了“莫菲的心灵”,即他意识的三个地带,为在黑暗的内心世界中寻觅的“我”找到一幅适当的图画。莫菲的“心灵经验与身体经验被隔绝开来……它由逐渐化为黑暗的光明构成……在其光明与黑暗之间他感觉不到流动,光明没有吞噬黑暗的必要。必要的是时而在光明中,时而在半光明中,时而在黑暗中。仅此而已”。⑨他的心灵不是面向伦理的,因此其唯一的运行规则就是在光明、半光明和黑暗的状态间不断地变动。在光明地带,心灵经验与身体经验“并存”。这个光明地带是大多数人度过大部分人生的地带。莫菲只把它看作是“悲惨人生的一个灿烂的摘要……在这里,整个身体的惨败成了一个极大的成功”。在半光明地带,心灵经验不与身体经验为伍。这是大部分贝克特主人公断断续续存在的地带。在这里,我们客观地沉思我们的身体经验。然而,肉体生命就在那儿,是卓别林式的惊诧的源泉。在第三个地带,心灵经验完全是自我封闭的,它是“一个只受制于自身的变化原则的封闭体系,它自给自足,是身体的无穷变化所无法通过的”。⑩贝克特的描写详细而意味深长:
第三个,黑暗地带,是形式的变迁,是形式永恒的汇聚和分裂……只有形式生成又崩溃为一种新的生成的碎片,没有爱或恨或任何清晰的变化原则。这里只有混乱和纯粹的混乱的形式。在这里他并不自由,而是在绝对自由的黑暗中的一粒尘埃。他不运动,他是无休而绝对的生成中的一个点和界线的终止。(11)
通过光明和黑暗的形象贝克特描写了莫菲的心灵。对莫菲来说,“真实世界就像柏拉图的表象洞穴,而他自己的‘内心洞穴’才是实在的世界。”(12)另一方面,在贝克特和他的主人公看来,黑暗表示安全、包围、庇护、沉默,因此它也是一种处于洞穴中的状态。莫菲似乎是从黑暗中被抛出或从洞穴中被驱赶出来,他渴望从光明中走回洞穴,而在疯子恩东先生身上他发现了拯救的希望和回归之路。莫菲发现他看护的精神病人成功地从真实世界隐退到他们自己的“疯狂”世界。他恰恰站在这个边界线上把精神病学家所称的流放地看作避难所,作为一个旁观者倾听恩东先生内心的声音:
恩东先生是最友善的那种精神分裂症患者,至少对像莫菲这样谦卑而又心存嫉妒的旁观者来说是这样。他没精打采地消磨时光,时而情绪低沉到良久保持某种魅力十足的姿势,不过倒也没深沉到一动不动。他内心的声音从不向他高谈阔论,它谦虚悦耳,在他幻觉的整个合唱队它是柔和的低声部。他态度古怪却不外乎炫耀优雅。简单地说,他是一个清澈见底、沉着冷静的精神病,像那喀索斯被他的泉水所吸引,莫菲也为之神往。(13)
莫菲把恩东先生当作自己的“灵魂伙伴”,恩东的形象就是他自己本末倒置的生活,他像那喀索斯站在水旁顾盼自己的影像那样由表及里地观察和倾听恩东先生。他发现与恩东先生意气相投,终日与之默默对弈。在他们下最后一盘棋时,从第一步起莫菲(白棋)就试图取悦对手(黑棋),就看出了黑棋的破绽,就想效仿黑棋,但越走越乱,并渐渐意识到此弈不会有结局。无论他怎么拼命弃子让棋黑方都不予理睬。他把自己的王棋向前提,期望被对手将死,黑方却置之不理。狂怒之下,他威胁着要将军,但恩东先生没看出来规避了风险,此后莫菲再也不想赢了,他选择了认输,因为面对恩东先生泰然自若的冷漠,他“顿悟”到自己更深的失败。
莫菲是这样一个人物,对他而言,看见的是现实的一个必要的障碍,看不见的才是真实的。他理解了非逻辑的东西,仿佛昭示他不久将开始步入遭受堙没无闻的常态。这就是处于边界线上彻彻底底的双重存在。棋局结束了,棋盘上恩东先生的黑棋整齐如初,只有王棋和两个卒子挪了地方,完成了一个优美的怪异精妙的芭蕾舞动作,而莫菲的白棋则一片狼藉,一如马上要侵入他两肺之中的煤气的“超级混乱”。漠视他的存在的恩东先生的优雅在绝不逊色于初见之时的印象中停留片刻:
随后,这一点也烟消云散了。莫菲开始看到虚空,那种属于难得的产后乐趣的苍白,成了不是感知而是被感知(权且滥用一下这美妙的差别)的缺场。他的其他感官也进入了平静状态,这是意外的快乐。不是感觉本身中止感觉的那种麻木的平静,而是当某些事物让位于虚无,或者也许逐渐变成虚无时而出现的积极意义上的平静。这种平静比那个阿弗季拉镇人的无的狂笑更真实。(14)
对弈之后,莫菲感到自以为重要的东西坍塌为虚无或增添了虚无时所发生的那种确确实实的平静,这种平静比阿弗季拉镇的(Abderite)无的狂笑更真实。有的批评家发现“Abderite”指的是“发笑的哲学家”,即和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阿弗季拉镇的德谟克利特,他是哲学原子主义的主要鼓吹者,也是个原始怀疑论者。因而,贝克特的“乌有”代表充满原子的德谟克利特式的虚空,原子虽微小不为人所见却是“实有之物”。它也代表博学的无知,万物均依成见且确立习俗,故真理无从说起;万物皆笼罩于黑暗之中,遂一切乃不可知。(15)
只有在被两极牵引的边界地带才会产生这样的“顿悟”。莫菲最执著的雄心是斩断与他耿耿于怀的身体的联系,飘进沉默的内心世界的“洞穴”,他达此目的的方法是无休止地摇晃。小说第二段告诉我们莫菲自愿并亲手将自己赤身裸体地捆在一把摇椅上,然后让椅子摇晃起来,从而进入一种了无牵挂、绝对自由的境界。他悲惨的人生只能靠精神的快乐来救赎。他喜欢攻击身体,放纵心灵。但是,在存在与虚无的边界地带,身体无法跨越边界线细密的铁丝网。小说结尾时,回到疯人院的现实社会中来的莫菲又把自己紧紧地绑在摇椅上,企盼摇晃着进入极乐境界,却不幸死于火灾。在边界线的另一边,在所谓的现实生活中,妓女希莉亚莫名其妙地爱上了终日无所事事、到处游荡的莫菲,他却为了寻找心灵的愉悦抛弃了她,使她成为陷入失落无望境地的愁思绵绵的怨妇,只得用自己的痛苦丈量着那抛弃她的逻辑。神话的逻辑是,那喀索斯因拒绝回声女神的求爱而受到了惩罚;现实的逻辑,按照小说中的验尸官所说,这是“一次典型的意外事故”。(16)
莫菲渴望的第三地带是无理性的地带。在小说的结尾处,莫菲在恩东先生的心目中瞥见了它,大概在自己的死亡中实现了它,那时煤气的“超级混乱”使他最后平静地睡着了。第三地带是一个只有在疯狂或死亡时才能进入的状态。这与贝克特的一个基本悖论正好吻合,即人同时存在于理性和非理性的世界。理性数字的领域是历史、形式的领域。休·肯纳指出还有另外一个领域,非理性数字的领域,“我们可以思考它但我们的意识进不去,它比无限多的有理数还多。正是从这些相互渗透但不可通约的领域之间的类比中,贝克特为艺术家的工作和人类的状况识别出他的主要类比”。(17)这与柏格森理性与直觉对立的世界相去不远。理性活动靠的是稳定的状态、形式,类似理性的数字。直觉使我们接触不断变化的创造性发展,类似理智无法阐释的非理性王国。
贝克特创造的非理性王国,或者说他的边界景观,除了莫菲心理的三个地带,还突出表现为如下两个特征,一个是阿诺德·赫林克斯(Arnold Geulincx)的“在你一文不值的地方,正是你应该什么都不缺的地方”,另一个是德谟克利特的“没什么比空五更真实”。(18)在这个存在与虚无的边界地带,只有光明与黑暗的悖论式的同时运动。在那里莫菲最终经历了“乌有”;他未能驯服冷漠使之服从于世俗的目的。尽管芸芸众生的俗事凡尘频频撞击莫菲的注意力,他却力求从中退却。《莫菲》之后的小说的主人公看不到这种希望,无论他们如何摒弃外在世界,它还是侵犯他们,他们只有奋力生存于其中,却仍然是在边界地带,绝望地理解它,用言词表达它,叙述它。
莫菲从真实世界中退却,努力生活在心灵之中,他把心灵当作一个可以动身前往的洞穴。他尽量闭上眼睛和心灵隐退到幸福的黑暗地带;他只能靠精神的愉悦来补偿所过的悲惨生活。他实际上是个唯我论者,他所在的类似疯人院的地方大致相当于他自己心灵的唯我论空间。总而言之,相对于贝克特所有后来的作品,《莫菲》是“元小说”,阐述了贝克特自己对自我及其认知界线的解读。作为最具乔伊斯风格的贝克特作品,《莫菲》是对一场心灵冒险全面而大胆的记录。它旁征博引、才气横溢、放荡不羁。拉伯雷、斯坦恩和乔伊斯同台共舞。然而,贝克特与乔伊斯不同,他是卓尔不群的怀疑论者,是满腹经纶的爆笑大师。“《莫菲》中高扬的否定精神是愉悦而无穷尽的。”(19)的确,它的阴郁的暗示无处不在,但其字里行间并未散发着悲剧或地狱的气息,而是不时迸发出鲜活清新的抒情性,这种绵延不绝的活力不断把阴郁的暗示驱赶到边缘,仿佛一个地道的现代人走进远古人类居住的洞穴,燃起一盏充满怀疑论真理的明灯,挥笔刻下永恒的心灵的壁画。
三、《瓦特》:心灵洞穴中的求索之歌
贝克特的人物抛弃行动,忙于在自己心灵的黑暗中创造神话。莫菲不愿工作而耽于沉思,渐渐脱离了自己周围的世界,去观察和倾听恩东先生;瓦特则不断地在自己的内心中听到各种陌生的声音。外在世界之于莫菲是“巨大的失败结局”,之于瓦特则是巨大的威胁和灾难。因此,与瓦特重复和退却的模式化思维相适应的是一种混乱的叙述文本。《瓦特》的结构以破坏叙事秩序的传统原则为特征。按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最后一章应在倒数第二章之前,这说明线性叙事已被取缔。贝克特制造了一种偶然性印象。人物分裂为词语。小说主要由一系列层出不穷的微小的逻辑选择组成,瓦特试图根据这些抉择紧紧抓住他所经验到的东西。这部喜剧小说的荒蛮与绝望令人胆战心寒。
一种颇具诱惑力的司空见惯的“疯人院理论”(20)把《瓦特》看成是由一个精神病患者(山姆)讲给另一个精神病患者(瓦特)的故事。(21)有的批评家在《瓦特》中发现本体论和认识论这两个主导性的哲学模式。瓦特在诺特先生家中隐约地经历了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区别以及认知与非认知之间的差异。(22)我们可以用心灵洞穴的边界隐喻来平衡这种不同的定位。贝克特身居边界之地,潜入神秘的洞穴,描绘在光明和黑暗之间的神秘旅行。我们不仅应该把他作为当今最重要的作家来评价,也应该把他作为一个新的现代入门人来赏评,他再次开启我们的精神世界之门。
贝克特的确是个神秘的临界状态的入门者。他发现自己与“一直抗争着试图控制的黑暗”(23)有难以毁掉的联系。黑暗最终成为他创作灵感的源泉,使他的心灵向自己内心的阴暗面开放。实际上,这一点早在《瓦特》和《莫菲》中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了。
瓦特本人是贝克特最执拗的逻辑学家,是他最固执的意义寻觅者。他的故事开始于逐渐减弱的光明之中:“夜幕正迅速来临,戈夫说,天马上就全黑下来了。然后我们将全都回家,哈克特先生说。”(24)哈克特起到从尼克松夫妇的“外部世界”向瓦特的世界过渡的作用。哈克特先生向地平线望去,在黑暗中所有的方向都变成了一个方向。贝克特的世界是一个方向、疑问、理由、沉思的“光明逐渐减弱”的世界,一切都充满希望却又徒劳地逐渐变为无法持久的黑暗。在光明“衰弱”,白昼“将尽”,“最后的花朵”即将被“吞噬”之时,(25)瓦特走近车站,马上要开始他的第一次旅程。瓦特的出场表明一种对某种真实的东西的不由自主的回忆,我们已经与这种东西疏远了。尼克松先生“不喜欢太阳落山因为它至少暗示着疏离”,(26)但我们与哈克特一起在黑暗之中哭泣,即将进入瓦特的世界。在这种阴暗的世界里,“我们将不但与外部世界、思想和行为习惯以及语言相疏离,也将同我们再也无法返回的纯粹的黑暗相疏离”。(27)
火车旅途开始了,瓦特背对着目的地;然后旅程突然结束。铁路线上布满一系列“静止状态”(车站),这是贝克特表现人类存在苦难历程的一个意象,我们从生到死艰难度日,背负着意识的沉重负担。在赶往诺特先生家中的路上他掉到路沟里,发现自己正在听一首奇怪的合唱曲。那是“他身后篱笆内夜晚可爱的天籁……永无安息的呼吸”。他听见的是纯粹过程的声音,是无数终究无变化的小变化,是叶枯与花荣,是无风向的风。接着这种声音又卷土重来,“清晰分明地,从远处,从外面,是的,真的好像从外面……其性质冷漠、无动于衷,像混杂的唱诗班”,(28)这唱给他的歌声是关于无理数和人类过程的。这是场意识的戏剧,它从黑暗中醒来走向光明。在路沟里我们听到的关于存在的夜晚的天籁渐渐变成了一支求索之歌。
随后,瓦特在潜意识中跨越门槛进入诺特先生的家,开始了他在生存另一头的经历。阿尔塞纳斥责瓦特在诺特家的厨房里游手好闲,等待天光破晓:
这个人来了!那黑暗的路全都甩在了身后,全都装进了心里,那漫长的黑暗之路,在他脑海里,腰中,手和脚上,他坐在深红的幽暗中,抠着鼻子,等着天光破晓。黎明!大阳!光明!嗯!……然后夜晚安息于宁静的家中,再没有路,再没有街,你在窗边躺下,窗子俯瞰着安全岛,传来微弱的声音,无所求,无所规定,无所解释,无所建议……秘密的去处绝不雷同却总是单纯而冷漠,它始终不过是个场所而已,一个忙忙碌碌的地方,岂止是来来去去,那是一个轻盈自由的存在之所,一如乌有之本质。(29)
阿尔塞纳感慨和嘲讽的是,摆脱生活的黑暗之路就是丧失生活,而非摆脱肉体,居于永恒的生活。这样,瓦特的处境是悖论性的。他寻找诺特,渴望经历无,一个躲避变化的避难所,最终静止下来。阿尔塞纳继续津津有味地描述瓦特的状态,“他一辈子浮光掠影,四处游荡,同时又无私地追求奋斗。经过这种痛苦和恐怖之后,他发现自己终于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认识到只有无所为才是最重要、最有意义的行为”。(30)之后,阿尔塞纳一语破的:“这个傻瓜!他已经学会了乌有。乌有。”(31)这即是说瓦特什么也没学会,也是说他领会了虚无。因为变化必将发生;黑暗将变成光明,光明将变成黑暗。在贝克特的世界里,欢乐与恐怖,希望与绝望是同一认识理解的两个方面。瓦特只能在无法与诺特找到避难所的过程中经历诺特。如果他不寻求诺特,那作为习惯的生活将把他同化。然而,如果他寻求诺特,他就无法在寻找中找到他。因为寻觅就是使自己来来去去,忙忙碌碌。
在诺特家中,我们得知“来在去的控制之下,去在来的阴影之中”,只有一个人不必像仆人那样被呼来唤去,可谓“永恒”:“然而有一个人既不来也不去,不用说我指的是我以前的雇主。”(32)也就是诺特先生,一个从不现身的戈多式人物。“诺特的家是一个真实与非真实的奇特的混合物,像个卡夫卡式的城堡。”(33)诺特的内心世界依赖于外在世界。除非用词语包裹虚无,否则虚无便不存在;只有用词语包裹起来虚无才能变成实在的东西。瓦特别无选择,他必须甘心去追求意义,这既是因为和诺特的家一样,瓦特也靠外在世界才能“继续”下去;也是因为“从无中引出有”(34)是他的遗传特征。
瓦特透过一块深色玻璃看到了诺特,也在日落与日出中窥见了他。而且,至少从拟人方面来说,诺特先生这个“戈多”在某些时刻成为可见的了。各种不同等级的仆人围拢着他,他则端着主人的架子,若即若离。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存在,诺特先生的“形象”和行为只能通过瓦特薄弱的观察能力加以描述。至于整个诺特世界的不合逻辑,也只能表明整个“意义”的概念已经改变了,因为现在事件不但在其发生的过程中而且按照在反思时它出现的方式来表示意义。贝克特把瓦特的非理性冒险变成理性话语,把让瓦特失语的词语变成词语。“贝克特渴望无言的状态,因此杜撰一个默默无语的主人公,然后与他攀谈。”(35)瓦特在底楼和顶楼听候诺特先生发号施令,对那个匪夷所思的世界有所体验,在那里,思想、词语、句子,甚至人都倒行逆施。我们发现的关于这个古怪世界的一切都是由瓦特讲给山姆,由山姆记录下来的。随着瓦特和山姆我们进入边界以外的世界,又回到“车站”,再次进入平常世界。“正如他趁夜色而来,他也在夜色中离去。”(36)
贝克特选择的意象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两个意识领域。瓦特和山姆各有各的用栅栏隔开的小花园,在各自的意识领域各自活动的方式也有典型的不同。两个人肩并肩地走路,一个向前,一个向后。这里,身体运动等同于精神游历。向后走只是倒着说话的另一形象,倒着说话又指思维过程的逆转。整篇小说也由四种运动构成。每一部分都以意识到“乌有”而结束,都在一定程度上向后通向它的开始,像四个连续的波浪,造成首尾相遇。这也正是黑暗与光明的对立运动。
在贝克特的心灵景观中,大部分场景都发生在黎明或日头垂垂西逝一天将尽之时。即便正午也有阴霾当空,而夜里则往往明月高悬,泼银辉于瓦特身上,尽管他并不喜欢。山姆在提到岁月给瓦特的帽子和外套留下痕迹时说,“时间也一样,照亮黑暗的东西,遮暗光明的东西。”(37)瓦特在天欲破晓之时来到诺特家中,又在苍茫夜色之中离去。人来人往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旅居诺特家中让瓦特知道,试图给事件强加意义是徒劳的;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些事件和讲述这些事件的话语感到我们不堪驻留的无变化和沉默。诺特不是瓦特的港湾或避难所,那些宅邸也不是。但瓦特一离开诺特家似乎就茫然无语,似乎就对非诺特的东西,对“实体”发痴。但这些“单子”是“无实在意义的”,在消极的空虚中,瓦特的心灵“忙碌着,忙于惊奇疑惑……”(38)通过他的语言的荒诞性和必要性,贝克特发现了维持人继续下去的东西的荒诞性和必要性。如果瓦特的名字(Watt)意味着无名之辈,那它更意味着意义的探索者;如果诺特的名字(Knott)意味着否定,那它也意味着乌有。瓦特在诺特的家——这个缺乏意义和无意义的封闭的世界打洞,并把它当作一个避难所,这虽是荒诞的“老家”,却组织有序还有几分慰藉。但一方面瓦特要赋予它一个逻辑的意义,另一方面他最终离开了它,剩下的是一个除去时间、地点和情节这些外部的形式要素,完全用言语构建起来的虚构的混乱的精神现实。
《瓦特》记录的是实际发生的内心事件,是走向沉默的天路历程,是贝克特在心灵洞穴所作的求索之画,所唱的求索之歌——即聆听他者的声音。《瓦特》推进了《莫菲》提出的问题,并使之成为理性方法的更加绝妙的戏仿。它是步入混乱世界的开始,这个世界随后将被认为是贝克特的典型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精神分裂与身体卑贱相伴而生:从《瓦特》起,有一种愈演愈烈的混乱。模糊的人物越来越意识不到时间、场所和外在世界,越来越专注于自己的意识,而同时主人公又越来越无法控制自己的意识,到了《无法称呼的人》人物已经沦为脱离身体的声音,并遭到其他声音的侵害。但是,意识到另一现实就意味着继续跨越边界。在《莫菲》和《瓦特》中,贝克特详细阐述了他自己对自我及其认知界线的解读。作为元小说,它们预示着他的伟大作品不但将以无形式的反形式持续不断地解构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也将继续悲壮地把这个分裂作为人生一个不可逃避的状况——边界状态来对待。这使他在《无法称呼的人》的著名的绝境之后又能“继续”。他依然如故地一头扎进内心深处的存在,一心在洞穴里作画,让他自己的内心生活普遍化。作为一位烛光学者,一位本体论洞穴学家,他既怀疑生命意志又坚信在意识的洞穴中内在之光的闪耀;通过对语言的反思,他从“边缘”向“核心”发出惊人的一瞥。我们沿着他开辟的边界地带浏览这种“心灵的景观”,也是在激发我们心灵的“内在之光”。
注释:
①Paul Foster,Beckett and Zen:A Study of the Dilemma in the Novels of Samuel Beckett (London:Wisdom Publications,1989),p.46.
②③⑥Bruce Stewart ed.,Beckett and Beyond (Buckinghamshire:Colin Smythe Limited,1999),p.46,p.13,p.46.
④⑤Malcolm Bowie,Jacques Lacan,in John Sturrock ed.,Structuralism and Since:From Lévi-Strauss to Derrida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119,p.119.
⑦Frederick J.Hoffman,Samuel Beckett:The Language of Self (New York:E.P.Dutton & Co.Inc.,1964),p.119.
⑧Tom Bishop,From the Left Bank:Reflections on the Modern French Theatre and Novel (New York and London: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7),p.171.
⑨⑩(11)(13)(14)(16)Samuel Beckett,Murphy (London:Pan Books Ltd.,1963),p.64,p.64,pp.65-66,p.105,p.138,p.147.
(12)Frederick R.Karl,A Reader's Guide to the Contemporary English Novel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p.21.
(15)Lance St John Butler & Robin J.Davis eds.,Rethinking Beckett: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London:The Macmillan Ltd,1990),p.162.
(17)Hugh Kenner,Samuel Beckett:A Critical Study (New York:Grove Press,1961),pp.108-109.
(18)Lawrence Harvey,Samuel Beckett:poet and critic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pp.267-268.
(19)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391页。
(20)L.Ben-Zvi,Samuel Beckett (Boston:Massachusetts,1986),p.66.
(21)(22)Vivian Mercier,Beckett/Beckett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166,p.166.
(23)Deirdre Bair,Samuel Beckett:A Biography (London:Thames & Hudson,1978),p.350.
(24)(25)(26)(28)(29)(30)(31)(32)(34)(36)(37)(38)Samuel Beckett,Watt (London:Calder & Boyar,1963),p.16,pp.7-12,p.23,p.33,p.39,p.41,p.42,p.56,p.79,p.215,p.218,p.133.
(27)(33)(35)Fled Miller Robinson,The Comedy of Language:Studies in Modern Comic Literature (Amherst,Mass.: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0),p.144,p.154,p.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