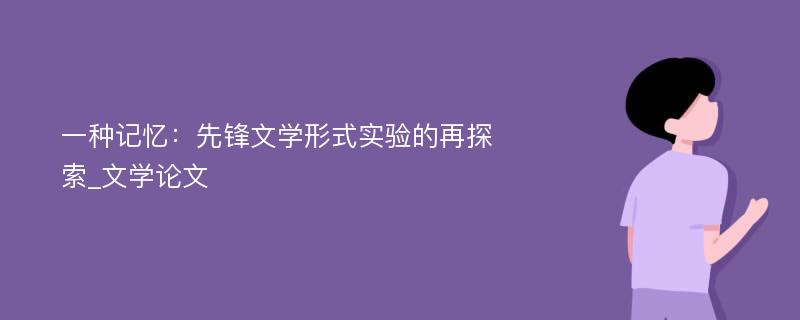
一种缅怀:先锋文学形式实验的再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锋论文,形式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当代文学的历史似乎在不经意之间又画了一个圆:从极端地重视内容到极端地重视形式,现在又回到了极端地重视内容。与近20年前极端地重视内容相比,唯一的差异在于:前者的重视内容有着其浓厚的现实的政治化动机,而后者的重视内容则有着显见的商业化的目的。
这一个圆的完成,是有着让人哭笑不得、奈何不得的谐谑成份的。它似乎有着阿Q所画之圆的那种风骨,但仔细斟酌,也就是一个“似乎”罢了。在更为宏阔的时间之轴上,它让我想起的倒是当代中国先锋派文学曾极力奉为大师级人物的博尔赫斯所挚爱的圆形迷宫。在博尔赫斯那儿的圆:既代表着一种结构的完美,同时又意味着一种宿命的循环和困境。
促使我撰写本文的动机也正是:我们能够走出这种循环吗?或者质言之,倘若我们注定不能够走出这种循环的话,我们能不能把一个圆的终点当做另一个圆的始点,也就是说,在几乎所有的人将文学的内容(不管它如何披上形形式式的商业包装)当做文学的唯一目的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再一次探索并研究文学的形式意味呢?
事实是,即使在先锋文学最为辉煌的时期,我们的文学批评也很少涉猎于形式批评,我们也缺少对于“形式实验”的宏观把握和微观解析。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这篇小文也可以算作一种补救,一种努力把一个过去的“圆”画得更圆一些的痴幻的执著罢了。
还是引言
当我们谈到“形式实验”这一题目时,克莱夫·贝尔关于“有意味的形式”的著名论断将会意味深长地浮现出来。而苏珊·朗格对贝尔的进一步阐述也不会为我所忽略。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一书中说,“正象科学常规支配我们的学术思想那样,人们在理解艺术时也常常认为形式与本质‘内容’相对立。不过,根据这种不加鉴别的设想,关于形式和内容的整个概念就要遭到厄运,艺术分析也会以艺术是‘赋予形式的内容’(formed.content)即内容与形式同一这样夹缠不清的论断而告终。关于形式与内容的这一似非而是的问题,是可以找到解答的。因为,第一,艺术作品是一种其相关因素常为本质和本质特征(如它们强度的大小)的结构;第二,本质进入了形式,本质从而与形式合二为一,如同本质所具有而且所仅有的关联一样;第三,说本质是形式在逻辑上赖以被抽象的“内容”毫无意义。形式借本质特有的关系而建立,本质是艺术结构中的形式因素,而不是内容。
苏珊·朗格的话,无疑是我们进入先锋派文学形式探索和实验之门的一把钥匙。即先锋派文学的形而上主题方向,它可以构成内容的层面,而它的情感本质却又与形式相关联。因而,当我们力图对它的形式探索和实验作某种评价时,我们将必须考虑它与情感本质的一种联系,如同苏珊·朗格进一步所述:艺术形式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内容,即它的意义。在逻辑上,它是表述性的或具有意味的形式。确实,我们在下面也将探析到的先锋派文学对神秘感的追求,它将典型地表现出形式本身的意味,并使形式成为“有意味的形式”。不过,现在,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宁愿暂且将“意味”搁置一边,从纯形式或曰技法的意义上开始我们的探讨。
1.意象——形式实验的斑斓之花
“意象”进入先锋派小说之中,首先具有的恐怕是纯形式或曰技法的意义。意象,它是主观情感、情绪与客观事物的一种契合。倘若用庞德在《关于意象主义》一文中所述即为“意象可以有两种。意象可以在大脑中升起,那么意象就是‘主观’的。或许,外界的因素影响大脑;如果如此,它们被吸收进大脑熔化。转化了,又以与它们不同的一个意象出现。其次,意象可以是‘客观’的。攫住某些外部场景或行为的情感,事实上把意象带进了头脑;而那个漩涡(中心)又去掉枝叶,只剩下那些本质的、或主要的、或戏剧性的特点,于是意象仿佛象那外部的原物似的出现了。”
引用了庞德关于意象的划分之后,我们似乎可以进一步指出,尽管意象进入小说并非从先锋派文学始(比如,王蒙的《春之声》、《海的梦》,孔捷生的《海与灯塔》,在尝试意识流小说的实验时,已将意象引入其中。倘若再作探索的话,三十年代的沈从文诸人的小说创作,均不乏这方面的实例,如《边城》),但先锋派小说引入的意象却有着它自身的诸多特点。
A.先锋派小说喜欢引入庞德所称的“主观”意象(这是与王蒙、孔捷生或沈从文喜好客观化意象恰好相异)。苏童在他的成名作,也是先锋派小说的重要作品之一的《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中写道:
灵场与我远隔千里,又似乎设在我的摇篮旁边。我小小的生命穿过枫杨树故乡山水人畜的包围之中,颜面潮红。喘息不止。溺死么叔的河流袒露在我的目光里,河水在月光下嘤嘤作响,左岸望不到边的罂粟花随风起伏摇荡,涌来无限猩红色的欲望。一派生生死死的悲壮气息,弥漫整个世界,我被什么深刻厚重的东西所打动,晃晃悠悠地从摇篮中站起,对着窗外的月亮放声大哭。
远(远隔千里)与近(摇篮边上);回忆(童年)与实在(父母家人的惊讶);死亡(么叔之死)与新生(婴孩之哭声);恐惧(死者与世界的关系)与欲望(以罂粟为象征的生命的原生力量)……是那么和谐地被统一在一起。而这一组组对比前者之存在,皆是主观性极强的意象。“我”并没有见过么叔,在“我”出生没多久,么叔就在枫杨树故乡死去了。但我却清晰地看到了么叔,并感到么叔周围的一切,包括河流猩红色的波浪、包括大地、包括大地上弥漫的生生死死的气息。是幻觉吗?又不是,它是“我”在清醒之中所浮现于脑际的意象;是回忆吗?又不切实,“我”那时尚在哺乳期,似乎没有记忆可言。但不论它是什么,它意味着什么,它怎样产生,它只能是一种主观化极强的意象。
B.先锋派小说喜欢在小说中引入“主干意象”,并在“主干意象”周围形成意象群。
费莱曾指出,在许多作品中存在着一种“意象光谱带”,比如,在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血的意象就有着“意象光谱带”的作用,在诗歌创作中尤其被经常运用。艾略特的《荒原》,其“荒原”就类似于《麦克白》中“血”的意象所起的作用。我们也把这类意象称作为主干意象,即这样的意象往往起着统摄全篇的枢纽作用,将其它散漫的意象串联起来,并暗示着主题方向。它与其它意象的关系就如同树之主干与树之枝桠、叶瓣的关系。
曾进行过先锋派诗歌实验的苏童对这一点也并不陌生。我们仍以他的《飞越我的枫扬树故乡》为例。
在我们上述的引文中,曾出现了许多主观化极强的意象。倘若我们作进一步辨析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这短短的引文中“红”的意象占有不小的比重:罂粟花的颜色是红色的,甚至连抽象的欲望也被赋予了颜色——“涌来无限猩红色的欲望”。确实,“红”在《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中占用突出而醒目的位置,换句话说,“红”是《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的主干意象。在小说的开首,一两句平实的叙述之后,主观性极强的“红”的底色就大面积铺开:“春天的时候,河两岸的原野被猩红色大肆侵入,层层叠叠、气韵非凡,如一片莽莽苍苍的红波浪鼓荡着偏僻的乡村,鼓荡着我的乡亲们生生死死呼出的血腥气息。”而小说极重要的两位主人公的死亡也伴随着红色:么叔死于“罂粟花最后的风光岁月里”;穗子死于一条河中,她死时“涟漪初动的水面上冒起好多红色水泡,渐渐地半条河泛出红色”。
当“红”成为《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的“意象光谱带”时,作品的形而上主旨也隐约浮现出来。它是一种生命的颜色、欲望的颜色和死亡的颜色,“红”统一了生与死、统一了精神与欲望、统一了回忆的虚无与实在、统一了超验与经验,用作品的话说就是“红”完成了“一个死者与世界的和谐统一”。
需要指出的是,在小说中引进“意象光谱带”,引进主干意象,并非先锋派小说的首创,费莱已经在传统的莎士比亚那儿找到了“意象光谱带”就证明了这一点。但主干意象的操作实践在先锋派小说那儿被屡屡运用,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比如莫言《球状闪电》中闪电与光的意象;孙甘露《信使之函》中的信的意象;张献《屋里的猫头鹰》中“沙沙沙”的听觉意象…皆有着这方面的功能。究其原因,这可能与先锋派小说喜用“变形”、喜好拒绝有限的实在事物,而追求幻觉、梦觉、错觉等有关。而大量非常态的、非知觉的、抽象的意象进入作品,倘若没有一个主干意象的话,作品在整体上必会出现一种散漫,结构上容易出现一种失衡。还是苏珊·朗格说得有理,“意象真正的功用是:它可以作为抽象之物,可作为象征,即思想的荷载物”(重点号为笔者所加)而我们可以再补充一句:“主干意象在荷载能力上更有着非同一般的作用——它是大吨位级的。”
C.先锋派小说喜欢在表象的叙述或描摹中,突然嵌进意象,从而形成表象与意象、具象与抽象、叙述或描摹与象征和隐喻的张力关系。
余华在《四月三日事件》中,以一种平静和客观的语言交代“四月三日事件”的起始:一个很平常的早晨,主人公“他”站立在窗口开始了对世界的眺望。这种眺望姿态的被描述是在一个漫不经心的语态和表象真实的过程中完成的,即它是经验的、实在的,被感官正常感知着的。但极其主观化的意象在这时却突然插入了,它迅速使事件的过程具有了一种荒诞感、一种虚拟性,从而使经验世界的客观真实变得恍惚起来。余华这样写道:
他将手伸进了口袋,手上竟产生了冷漠的金属的感觉。(这时的感觉仍停留在常态的感官能力的把握之中)他心里微微一怔,手指开始有些颤抖。他很惊讶自己的激动。然而当手指沿着金属慢慢挺进时,那种奇特的感觉却没有发展,它被固定下来了。于是他的手也立刻凝住不动。(客观化的叙述正在向主观化的意象过渡)渐渐地它开始温暖起来,温暖如嘴唇。(迅速进入意象范畴,重点号为笔者所加)可是不久这温暖突然消失。他想此刻它已与手指融为一体了,因此也便如同无有。它那动人的炫耀,已经成为过去的形式。(意象的抽象性被凸现出来。尽管意象的空间占用极其有限——它仅仅是一把小小的钥匙——但它的抽象意义却具有了某种扩张性和无限性。能指,亦即表示成分“钥匙”在所指的层面上获得了想象性空间的充分余地。“炫耀”及“过去的形式”之下的重点号系笔者所加)
那是一把钥匙,(回到实在的表象世界)它的颜色与此刻的阳光近似。(再以一种过渡姿态进入意象范畴)它那不规则起伏的齿条,让他无端地想象出某一条凹凸艰难的的路,或许他会走到这条路上去。(钥匙和路的勾连,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也是一种描述的客体与隐喻性意象之间的关系,即一种喻体和喻意的关系。)
综合上面刮弧中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余华极其自由地运笔于客观—主观,经验与超验、表象的真实与意象的真实、叙述描摹和象征隐喻、具象和抽象之间,或进或出,或淡或浓,或拘谨或洒脱,但在“钥匙”这一变异了的客体、具有浓重陌生化意味的意象之统摄之下,矛盾着的一个个板块被强有力地粘和成一个“场”——即有着张力关系的整体效应。“钥匙”在所指的抽象层面上,已经契合着“四月三日事件”的主题方向:它在不自不觉中营造出一种充满坎坷和怪异的氛围。它(钥匙)与一扇扇紧闭的心灵之门发生了联系。而正因为一扇扇拒绝“他”进入和介入的心灵之门的存在,一个封闭的世界才迫使他逃亡——企图逃逸出由门制造的窒息青春生命的空间,从而让人的生命形态成为毫无羁绊的存在。
2.摇曳多姿的先锋文学结构形态
在我们传统的理解中,小说的叙事结构往往意味着情节结构。叙事结构与情节结构形成同构对应关系。而情节又通常被解释为性格的演变史、发展史。叙事结构在这时也悄悄地变化成人的性格的塑造和描摹的过程。叙事结构由于服从着性格的演变轨迹,从而也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的、凝固的模式。
在这样的模式中,情节的走向(即叙事结构的板块运动过程)与时间的线性轨迹是相吻合的,亦即情节呈现出时间的线性运动轨迹。“起承转合”或曰开端、发展、高潮、结尾,只不过是这种线性时间外化为一种艺术形态的必然。而在这样的艺术形态中所呈现和传递的历史感、沧桑感或曰使命感,只不过是这样一种艺术形态在内涵上的必然。“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个人的命运”,这句箴言似的总结成为这种艺术形态企盼的境界和必然归宿。
但从意识流小说始,这种坚硬的、凝固了的模式被打破了,性格的意义淡化了乃至于无。而随着性格意义的缩减,小说的结构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情绪的位置渐渐凸现出来,一种情绪型的结构随之出现。比如王蒙的《春之声》,彭见明的《那山 那人 那狗》、周立武的《巨兽》、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戈壁》,刘索拉的《蓝天绿海》、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
毫无疑问,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缘起与意识流小说有相当多的关联。即意识流小说在小说的结构上也给予了先锋文学极大的启发和借鉴。早期的先锋文学在结构上与意识流小说的结构上有极大的相似性(它们所相异的恐怕更多地体现在对世界的理解、对形而上主题方向上的不同趋附),即使发展到晚近的先锋文学,在结构上也同样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它们都共同否定了情节结构模式,小说文本中缺乏首尾相顾的、具有明显、必然的因果联系的主干情节;它们都对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抱着一种随意的、即时的态度。当然,掠过这一系列结构表象上的相似性,我们还会发现先锋文学在结构上所作的一种努力,即努力超越已有的艺术经验,开辟小说艺术结构的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归宿。
A.对比性结构及其张力
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在先锋派小说结构方面的开创性意义显然不能低估。三个似乎独立的故事,在“诱惑”的标题之下被统摄在一起。其一,狩猎的故事。故事的走向与喜马拉雅雪人,与狩猎中自然浮现的大自然倔强峥嵘的精神有一种契合对应的关系。说到底,这一故事关系到的是人在大自然中所占有的位置。其二,陆高、姚亮与央金的故事。这一故事实际上并不能算故事,因为陆高、姚亮与央金关系很陌生。倘若硬要说其中有什么联系的话,只不过是一个充分符号化了央金(很美,但突然地死去了)所涵盖着的死亡的突然性、不可预期性的价值意义与陆高、姚亮的灵魂一隅发生了一种碰撞。其三,顿月、顿珠与尼姆的故事。这是普泛化的生活形态,因而,在顿月、顿珠与尼姆的故事背后,隐藏着两方面的价值依附:即向着大自然精神的一面,它凸现的是一种生命的原始激情和力量;而另一面则向着现存物质世界的贫困和粗糙,它发出的是一种道德和世俗的声音。
马原显然意识到了三个故事的疏散和分离。他直接在小说文本中装入了一段批评性的说明性文字(在小说结构学的意义上,这段文字本身也对一种秩序和规范做出了一种解嘲式的姿态):“关于结构。这似乎是三个单独成立的故事,其中很少内在的联系。这是个纯粹技术性的问题,我们下面设法解决一下。”
马原的技法(技术性)就是在结构上让它们成为一种自我满足的存在,即按它们故事显示的内在要求,形成各自的结构风貌,然后让它们共同存在于一个“诱惑”的母题之下,从而产生一种结构上的张力。质言之,这是一种对比性的结构。
在第一个故事中,马原强调的是故事的形而上意味。这一故事的结构处理也就变成了情绪性结构。在文本中,不断地有抒情性意象的片断和块面出现。如:你就生在那山里。山势多半是平缓的,只有地衣和矮棵的几种叫不出名字的植物是标志季节变化的自然色彩。这种叙述语言和描摹语言本身也染有浓重的非日常化的抒情色彩。而在第二个故事中,马原强调的是生活的日常形态,主题归宿也在于死亡在日常生活中所显示的意义。因而,马原在结构上也处理成以“悬念”(央金如何天葬和陆高、姚亮观看天葬成功与否)来串连起整个事件的过程。而叙述语言也带有一种平淡和琐碎,象日常生活形态本身的单调和乏味一样。到了第三个故事,由于故事本身所具有的两重性,即向着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两重性,故事的结构也就具有了一种两重性价值。在叙述和描摹语言上则是跳跃式递进的抒情性语言风格与平淡的无色彩的铺排性语言风格互为观照,交替出现。
三个故事(或曰三个子系统)三种结构,但它又最终构成了小说文本的大结构。这种结构方式类似于音乐中的复调结构,但又要比复调结构更为复杂。它在三个子系统(三种结构)的相异中求得了统一,它在子系统的排斥中获得了一致,它不是彼此的提问和应答,而是彼此的冲撞和矛盾,它应和着的声音来自于喧嚣的尘世又来自于寂静的灵魂;或者说,它响应着的声音来自于灵魂的纠缠又来自于自然的静穆——这种结构本身就是一种悖论,它唯一能够对应的是我们现存在之中的实在和虚无、“烦”(如海德格尔所用之意)与“空”(如禅宗所述之意)……
B.回忆的套叠式结构所蕴含的结构力量
回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文学的本质所规定着了的。除了幻想小说,文学所叙述、所描摹的总是时间上已经消逝的事情。因而,几乎可以这么说,任何一篇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和摹写的小说文本,都相当容易给人一种展开回忆的感觉,或者说,事实上它们都是一种回忆。
不过,在传统的写实主义那里,回忆是以插叙或倒叙的结构形式展开的,在意识流小说那儿回忆是在人物的意识流程中展示的。不论怎么说,回忆遵循着的是常态的时间逻辑。但在先锋派小说那儿,回忆改变了它的这一性质,并进而改变了小说文本的结构形式。即以苏童的《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为例。
在小说开首处,我们的阅读感觉似乎是“我”在展开回忆。小说写道:直到五十年代初,我的老家枫杨树一带还铺满了南方少见的罂粟花地……我的么叔还在乡下,都说他象一条夜狗神出鬼没于老家的柴草垛、罂粟地、干粪堆和肥胖女人中间,不思归家。我常在一千里地之外想起他,想起他坐在枫杨树老家的大红花朵丛中……(重点号系笔者所加)这段文字中的三处“我”字,已经勾勒出一种回忆什么的氛围。然而,事实上我那时尚年幼,尚难以有翔实具体的回忆内容。于是,小说接下来进入回忆的另一个层面。
“祖父住在城里,老态龙钟了,记忆却很鲜亮……”;“可以从祖父被回忆放大的瞳孔里看见我的么叔……”(重点号系笔者所加)这两段文字表明,小说开始由“我”的回忆而进入到“我祖父”的回忆境界,即由“我”→“我祖父”→“我么叔”,从而构成了一个枫杨树故乡的世界。不过,在这里,小说的结构仍然恪守着常态的时间逻辑,是在被经验认同的范围中进行的。在小说的继续运行中,这种回忆的经验性质将被超越。
“一九五六年我刚刚出世,我是一个美丽而安静的婴孩。可是在我的记忆里,清晰地目睹了守灵之夜。”(重点号系笔者所加)从常识我们可以知道,刚刚出世的婴孩是不可能有记忆的,也就是说,从这时开始的回忆,由于回忆主体的改变,带有了一种明显的超验的性质,回忆的结构变成:
“我”→“我祖父”→“我么叔”→“我”
这种回忆主体的循环或复归,不仅使得小说结构形态出现了令人触目的变化,同时也使结构本身具有了一种意蕴。常态的时间逻辑被打乱,回忆遵循的也不再是一种线性时间,而是非直观的时间。在这时,我们的心灵世界将就这种回忆的套叠式结构所蕴含的力量所打动,我们将会联想到东方神秘主义的时间观和现代物理学所阐明的时间观——存在着一种不能为我们的经验所把握的时间。用德·布罗意的话来讲就是:
“每一个观察者当他的时间过去时就会发现一段新的时—空,对于他来讲好象是物质世界的后继方面,虽然在实在中,构成时—空的全体的存在先于他对它们的认识。”
而用高宾达喇嘛的一段话就是:
“……在这种空间的经验中,时间的序列转化为同时的共存,是事物的并列存在。”
这种回忆的套叠式结构所蕴含的力量,在先锋派小说中不仅为苏童所重视,它同时也是许多其他作家的选择。比如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上的魂》,洪峰的《极地之侧》、《瀚海》等等。这种结构的内在力量和外在的艺术魅力也就可以想见了。
C.颠覆性结构——埋伏在通俗文学格局中的特洛伊木马
有一个作家及其作品在中国的遭际是意味深长的,无论是先锋派作家或是后来的新写实主义作家都将其奉为至宝。他就是罗布·格列耶及其代表作《橡皮》、《嫉妒》。
《橡皮》堪称颠覆性结构的范作。《橡皮》从其外在的结构形态来看,极似一部侦探小说。然而,恰恰是它将侦探小说的结构意义破坏得支离破碎,换句话说,《橡皮》以貌似侦探小说结构完成了对其通俗意义的超越,在这部小说里,不是人物支配情景,而是以物作为结构的支撑点和叙述视点,因为这一结构支点的改变契合着罗布·格里耶对于人和世界关系的哲学见解:人生活在物质世界的包围中,时刻受其影响。
在当代的先锋作家中,余华可能是较早地自觉地进行“颠覆性结构”尝试的作家。他的《鲜血梅花》是一场成功的冒险。
从作品的外在结构看,《鲜血梅花》有着武侠小说的最普通化的包装形态。其一:复仇。十五年前,一代宗师阮进武死于两名武林黑道人物之手;尔后,其妻念念不忘为其夫复仇,在其子阮海阔十五岁那年让他踏上了为父复仇之路。其二,悬念。要为父复仇的阮海阔,不知道杀害他父亲的凶手究竟是谁,而阮进武之妻将“丈夫生前的仇敌在内心一一罗列出来,其结果仍是一片茫然”。正是在这样的悬念之中,阮海阔踏上寻找杀父仇人的道路。其三,传奇性。胭脂女的花粉能使人一丈之内闻之即亡;白雨潇在堆满枯叶的小径上行走居然没有点滴声响;阮进武遗留给其子的梅花剑,即使沾满鲜血,只须轻轻一挥,鲜血便如雪花般飘离剑身,只留一滴永久盘踞剑上,状若一朵袖珍梅花。
然而,透过这一系列武侠小说的表面形态,余华所埋伏的“特洛伊木马”显现了。富有传奇色彩的梅花剑,偏偏握在没有半点武功的阮海阔之手;没有半点武功的阮海阔要找的杀父仇人却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高手,这一巨大的矛盾构成了阮海阔的生存背景,并显现了他生存目的的某种荒诞感。他唯一能做的是不断地寻找,不断地走路,如同海鸥乔·纳森在不停地飞,不停地寻找——飞往哪里,寻找什么已不再是重要的了,行为本身构成了目的。因而,阮海阔为父报仇的使命也可以被轻易地改变,他最终代人打探消息去了。这时,余华也完成了他的颠覆:哪儿还有什么传奇性?整个过程只是一个少年郎精神和肉体的漂泊。武侠小说的结构形态也变成了对武侠经典内涵的超越。
似乎是为了与余华相呼应,叶兆言在他的《艳歌》中完成的是另一种颠覆。透过题目,我们已经明了他颠覆的通俗文学品种是言情小说。一见钟情,相见恨晚,三角恋爱,缠绵不能自拔,巧遇……这一系列言情小说的模式与规范在《艳歌》中也是应有尽有。然而,只有当结尾处“阳光象一幅油画”时,叶兆言才将他的特洛伊木马杀将出来:他要借此而凸现主人公的“尴尬”状态和情态。情已非言情,“尴尬”才是一种生存的本真境界。也就是说,这一人的本真境界既可以通过“言情”的包装而体现,也可以通过《枣树的故事》那样苍凉的历史来体现。用叶兆言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写言情小说的同时反言情小说”,“常在关键时候破坏言情小说的规范”。而这种颠覆性结构的内在动力则源于叶兆言“不愿写非常现成的东西,而是调侃各类小说,从中得到写作的乐趣”,换言之,对通俗文学文本结构的颠覆已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性操作的需要,而是变成了作家精神生存的一种方式,一种精神自洽的需要,一种精神自娱的需要。
也正是出自于这种精神自洽和自娱的需要,对通俗文学文本结构的颠覆,继余华、叶兆言之后又有了长足的进展。为了文学王国的海伦,特洛伊木马曾经频频出击,并留下骄人的战绩。在雨城的《洪高梅》、述平的《凹凸》、陈染的《嘴唇里的阳光》……等篇什中,我们到处可见颠覆的努力,颠覆的艰难和颠覆之后的废墟以及立于废墟之上的艺术宫殿。
3.先锋文学形式实验的式微及简短的结语
先锋文学在形式实验上曾经占有的辉煌是一个巨大的题目,它绝非本文的篇幅所能够容纳的。我们所能够做到的,也就是择其要者对其作一简单的回顾和考察。
然而,辉煌之后的黯淡毕竟让人为之心疼,为之茫然,为之凄然,如同太阳消失之后的旷野上的寂寞、静穆和苍茫。
仿佛是打了一个盹,醒来时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已成昨日黄花。当一个形而上的主题群落丧失时,形成实验的式微其实也是必然的事,是题中应有之义。[①]
在苏童的《妻妾成群》中,我们还能够发现那情绪饱满的、富有张力和弹性的意象块面吗?在结构上,还有那跳跃式的意象块面的组合吗?显然这一切已经消失了。代之的是一个老头和四个妾的关系史,是一个妾的视点构成了小说的视点。颂莲,这一个曾经是女学生的妾,她进了陈家的门,然后变疯的情节史构成了小说的传统结构形态。“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个人的命运”,这一传统的箴言再度在苏童身上显灵。
而与此同时,新写实主义文学、新状态小说,以及形形式式的新潮流正汹涌澎湃。不过,这显然是另一个题目了,而它与先锋派文学的直接关联就是一批先锋作家转入了它的阵营。唯一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系列冠之以“新”的文学口号的崛起与先锋文学的式微在时间的线性序列上,刚好有一种承继关系。这是巧合,抑或是必然?
来稿日期:1996年8月13日。
注释:
①参见拙作《形而上主题:先锋文学的一种总结和另一种终结意义》,见《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
标签:文学论文; 先锋派论文; 先锋文学论文; 先锋艺术论文; 艺术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橡皮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