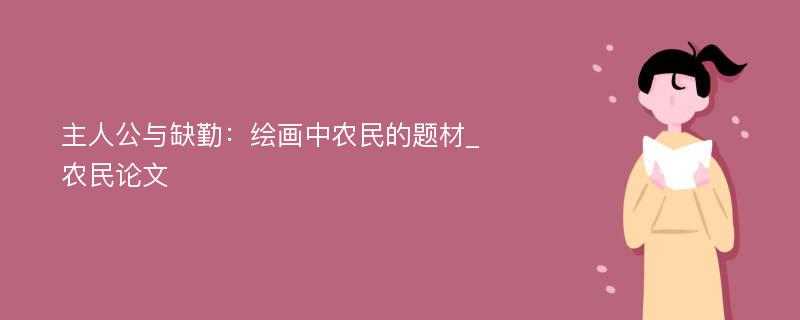
主角与缺席者:绘画中的农民题材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题材论文,主角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3年,就在王式廓逝世的前一个月,他在河南山区的一个小山村里,画出了中国美术史上著名的农民油画肖像写生,这批写生给农民题材绘画创作遗留下来许多悬置问题。这时,他去世了,对他和他同时代的中国美术来说,有许多需要在创作和理论中解答的问题。在中国,艺术创作领域中的农民意味着这样一种精神取向:它首先是中国最广大人口的现实写照;其次它是与新的社会思潮,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左翼文化思想、新民主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一场社会革命运动。它的一切根基都源于在中国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艺术家所具有的内在农民气质,并且这个内在气质又与中国广大人口中发生的现实相呼应。在中国社会历史特定时期的变迁中,农民题材的创作成为中国现代艺术运动中最重要的存在经验。
由于各种政治、经济、艺术界内部的不断革命和欲望,使得农民绘画多次经历从主角到缺席者的起落过程,今天,正是因为它不断地遭受这个过程的侵扰,我们才有可能回转身来,看看它是如何在艰难的条件下,呈现它的状态。在这片土地上,它的根没有断过,它深埋于严峻的生存现实中。当我们看到它的起伏和缺席时,可以认为它是仅仅存在于农民主题持续期中的暂时状态。这种起落和缺席过程深植于现代思想的开始,深植于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它把人文的世界卷进技术和意识形态漩涡中,人越来越没有位置,并把人生的、活生生的世界置之度外。
尽管如此,在中国,关于农民题材的绘画创作,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确定它的存在,确信它或是潮流中的主流,或是潮流外的潮流,它的存在根深蒂固,有时候我们可能叫不出它的名字来,可是它始终存在于中国绘画创作的五脏六腑里,在中国诞生的各种艺术风格都有这个农民国家的特征。
中国几千年来的农业社会本性特征冷静而不可抗拒地体现着自己的规律,艺术如果和它发生冲突,就无法生根。如果不是现代艺术潮流冲刷过我们这个以农业文明为根本特征的创作堤岸,农民主题的许多问题几乎不留痕迹地就翻过了二十年。
追溯百年历史,为什么在中国二十世纪初,会有文化历史的风云变幻,同时,为什么出现新版画运动,新连环画运动,以表达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和艰苦的斗争;为什么会出现蒋兆和、司徒乔、王式廓这样的中国美术史中的重要人物?列强的入侵,五·四的启蒙,对中国文化的再省是发韧的重要力量。同时,与当时西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有重要关系,真正的人本关怀是19世纪文化哲学运动的产物,要把人建构成为一门可能的学问对象,辩证法思想唤起了人文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人类社会底层的人成为人作出了辉煌而悲怆的努力”。(福柯语)
在中国,一批自西方留学归来的文化学人接受了西方的多种理论和思想,其中辩证理性成为最符合当时中国历史情况的思想,即以个人与社会,实践与生活,有生命体和无生命体的关系为参照,它首先成为当时激进文化人的知识网络,这些思想出现在瞿秋白、鲁迅、陈独秀及其关怀中国危难国情的学者论著中,最终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阶层的分析。当时的中国实在是壮烈的中国。唤起一场与农业社会有关的历史转折的辉煌而悲怆的时代背景,浸淫到绘画中的是:在山河破碎、生死存亡的关头,只有选择具有革命性、战斗性的绘画语言,只有倾情于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存现实,才能做到不无视现实。只有描绘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的绘画选择才符合对最广大劳动阶级的认识,我们就可以把解放区的版画、宣传画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它是辩证理性思维在中国现实中的具体绘画体现,它在农业中国绘画史中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地突显了“人”的价值。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思想中,绘画创作最令人赞叹的地方是有了农民的位置,因而我们才会在这条道路上走过百年。
绘画,在这时是关于人民和斗争的百科全书,是驱除艺术创作中特定时代的非本质问题,获取此时代关于人物和现实的最本质问题,这些努力加深了对人和中国国情的认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直到五十年代,左翼文化传统中的画家们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
当战火逐渐远去,人的非本真状态也逐渐复原。战争期间,善与恶的较量是唯一的真理,它迫使民族为创立和平的新秩序而努力,农民也高兴地离开了保家卫国的战场,来到一个宁静温馨的土地上,生存重新显示了价值的多元。政治的更新、国家的建设、经济的发展,多种价值观开始呈现。农业国家历史的最新纪元,出现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结构。农民地位的提升,农业国家的新形象,必然催生农民题材创作成为现实的主流。除了与国家百废待兴的建设高潮同步外,这类绘画与人民内部问题,人民的分工问题,人民的权利问题相结合,由战时状态转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日常生活状态。这种日常状态显然不同于80年代后兴起的农民绘画是饱经人民内部创伤后的荒凉感、沉重感、伤痛感。建国后的日常状态是心气高昂的日常状态,就连最普通平凡的生活都被激越的情绪照亮,人们愿意把自己最卑微的生活放在理想的光照下,心态平和满足,一切都会是成功的,一切都是值得自豪的。这样饱满的状态下产生的农民题材绘画一定是中国绘画史上再也不可能有第二个时期的阶段。那时的问题简单明确,绘画的主题也就简单明确。人心简单明确,绘画也简单明确。那些意气风发的农民绘画创作,就是那时,在那样的季节,在那样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由普罗大众文化问题到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一种重大的中国绘画主题得以形成,这种主题不是别的,它正是对被遗忘的中国底层群落农民存在的探寻。这个主题在上一个世纪,新中国文艺世纪的绘画创作中得到表现、探寻和澄明。以绘画的方式,通过形象的刻画,绘画创作一个接一个地发现了中国广大人口中农民生存的各个方面。经由司徒乔、符罗飞那批留洋归国的画家,深入探寻了灾难中人的生存颤栗。经由王式廓,发现了农民在社会运动中的阶级根基;经由振奋人心的五十年代,表现了人民共和国的新兴人群;经由陈丹青,审视了农民在存在与生活中的位置;经由罗中立,讨论了农民的真实身份;经由九十年代,农业文化气质中的理性存在穿行其后。农民绘画的创作探寻人生:连环画处理了稍纵即逝的现在,宣传画处理了热情至上的非理性。而通过“文革”时期的农民绘画创作,全面表露了控制中国绘画的神话理论和教条规则。各种不曾预料的变形态势,都是中国艺术做了它应该去做而且必然会做的事情。
正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早期左翼美学理论的倡导者们考虑到最广大人群的利益抓住了绘画,并影响它考察中国底层的具体生活,抵御艺术中对人性的遗忘,而将农民置于绘画的主角地位。那时,艺术有它社会意义上的纯洁性,正因如此,可以理解并赞同瞿秋白在二十年代的系列文章中反复坚持的观点,文艺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在于发现只能为进步文化人发现的东西,如果艺术未能发现人民大众这个群体,就缺乏现实意义和道德品质。以这样的思想为主线,产生了大量的作品,每个作品互相参照又形成一个整体,进而形成绘画史上一个悲情壮阔的运动。
像五十年代那样,把农民作为人民的主角,并敢于独立面对世界,在五、六十年代是一种被唤发出来的英雄姿态。
像“文革”那样,把人置于之上,并把人作为万能的物,这样一种姿态在七十年代是一种“超人”的姿态。
像陈丹青那样,把世界作为多面的,相对价值的世界,面对人性在社会中的复杂变化,始终保持个人之“流动的智慧”。
像“生活流”和农民作为商品画主角那样,生活涵义是抽象的重复,结果是许多商业技术人员的产生,互相在各自的影子中生长。
像九十年代那样,农民是被抽象了的绘画风格,绘画重新紧缩在自己的内核中。
上述情形使我们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农民绘画创作作两种判断:从内部提出问题,同时又作为一种遗产继承。也就是要看清它作为主角和缺席者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出现状态,这就使得我们今天来谈论关于农民的绘画创作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每一次都有它的时代意义,而每一次都会将问题推进到新的深度。那么多画家那么多作品在短短半个多世纪中就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代背景,而且每个背景都使这个题材处在争论和质疑的最前沿,这是偌大的世界只有中国的这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经验中才有的独特现象,是世界美术史中最性格鲜明的一段美术史。其中的思想基础是既有别于中国文化传统,也有别于西方文化传统的独立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方式、话语方式、行为方式。它也是其后中国艺术获得多种可能性的发端。一些人看到了人民崇高的理想主义,另一些人看到偏安土地的隐忍;一些人看到了政治教化的巨大潜力,另一些人看到了财源滚滚的商机;一些人看到了农业传统的强大力量,另一些人看到了农业文化的当代没落。农民在相当的范围内,在绘画中被定位为三种形象:要么是顺民,要么是流民,要么是英雄。要么农民是苦难的代表,要么农民是道义的化身,要么农民是头脑狭隘的牺牲品,要么农民是胸襟远大的主人翁。同时,由于农民曾被政治化地提升为国家的主人,提升为绘画创作的主角,而不是顺应自然展现它的宽广的农民气质,必然要经历巨大的落差,隐身在各种潮流背后。
中国绘画创作的遗产是如何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新一轮现代思想启蒙中发现了农民问题,并且如何在农民作为主体:“人”开始,又作为非主体:“人”的缺席,是指这个主体由中心向边缘位移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农民多次地消亡并让位给绘画语言、形式、观念的那个过程,在它们说话的地方,人就不存在,这正如王式廓之于他的时代,现代画家之于现在的时代是最具代表性的。王式廓致力于人的思维中的再现思想,他正好把人的形象定位在辩证理性思维寻求的那个点上,现代画家则把构成绘画的要素和观念置于农民的形象中,农民作为后现代的一种文化进入了绘画,它的意义只是绘画本身,而非人物,是文化的显身,而非人物的在场。在内容繁多的观念演绎中,绘画只剩下自己语言的声音。
打开王式廓延安时期的素描,农民正在进入一个在他面前有许多可能性的世界,他可以高兴地踏上土地,也可以无遮拦地诉说感情。早期的农民绘画创作都是关于人生的语言。人生的世界广阔无边,我们知道这些人物来自何处,一系列作品构成了农民,我们认识农民就是在这样一系列作品中形成的,描绘继续下去,又不断出现新的图景,潮涨潮落,始终是一种移动和回归原位的工作,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介身于中国农民这个广大的人口中。
在延安时期之后的二十年,同样在王式廓笔下,这条没有边界的绘画道路分岔了,它消失在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需要中。他经历了一个农民画家身处不同时代的多重演变,他给了我们关于正义和斗争的解释。压迫、血衣、政权、军队、国家,这一套完整的社会制度体系。在跟政治斗争有关的农民绘画里,人物不再象王式廓的素描和董希文的藏民那般悠然进出,它已经被定格在称为历史的事件里。这些事件对农民至关重要,也身不由己。这还不要紧,毕竟人还有它的面目,事件本身也有动力,它允许人们通过斗争取得地位和生活。
从反击胡风反党集团开始,中国艺术家就开始被迫近病态的边缘,一种内部斗争的紧缩,言论的约束开始形成,真实爽朗的语言退隐了。反右运动确立了这种病态在中国的成立。发自内心的,辩证思维唤起的人文主义思想,与现实世界的对话中断了。农民题材逐渐被分离出它的本真形态,它的真实语言开始沉寂,一种非理性的状态,用来创作有着固定概念的,只能在面对政治风暴时才有的那种绘画样式。
从此,中国农民题材的绘画开始与一种隐藏在背后的非艺术本质思想发生联系,几十年来就再也没有安宁过。
当现实完全主宰人的时候,个人的梦想毫无价值。“文革”来临的时候,历史不再允诺农民题材的绘画有土地的脉脉温情,它只给了它一份政治指导员的工作。农民能干什么呢?不多了,他不能象王式廓素描中的农民那样做自己的事情吗?不能。他不能象靳之林笔下的农民那样安然的拣拣青菜吗?不能。他是和工人、军人一起挥舞拳头的战斗者。他是战荒山间隙手捧毛选的老书记,他是修筑大寨田的农民英雄陈永贵。这里有大时代的滚滚洪流,农民的朴素品性只是它的附属物。
这不仅是一个题材的悖谬,《父亲》也许是最后一张农民画作品,曾一度被认为是八亿中国人民的父亲,其内涵具有苦难的意味。这二十年来人们不要这个父亲了,这一点难道不令人惊奇吗?如果连人生及底层都能被轻松解构,那么其中发生了什么呢?
在司徒乔的油画或贺友直的连环画里,生活有可以充分理解的意义,人们或是放下你的鞭子,或是成为时代的子民,生活有一种不可逃避的意义。人们为生存战斗,我们随着这些角色从土地上起身,走向生活领域,再回到土地,那个土地的背景始终强大地存在。近几十年来绘画中的农民却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活着,甚至连对生活的震惊也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他们漫无目的地漂游在绘画的形式中,风格中,对人这个中心已失去了兴趣。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关于文艺工作者责任问题的著名演讲,是指革命的文艺家要与自己灵魂中的不纯洁性斗争。这个不纯洁就来自自身,斗争的历史就是文艺革命的历史。老一代画家都长期经历过这个文艺革命的风风雨雨。王式廓最后一批油画写生是关于农民题材绘画可能消失的艺术遗嘱。他的那些作品产生在人民的热情和人民的迷信之断裂点上,它开始定位到真正的农民绘画消亡和虚假的农民绘画兴起的那个症结上。在七十年代,就是绘画创作不断地让位给教条主义的那个场所,在教条出现的地方,人就避而不见,或被部分肢解。那是在一个红色的中国,人们坚信伟大领袖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衰弱的中国失去了自信心的平衡。其中标语口号式的艺术创作加大了情绪的宣泄却贬损了农民题材的元气。与此相反,文革结束后,以陈丹青为代表的青年画家却发现了“只能用绘画表达的东西”,他们的创作证明了在政治情境,社会人格的情况下,绘画怎样改变了它们的含义。如果“进城”中的男人带着政治属性被拉进阶级斗争的范畴,那么“人民”意味着什么?如果“康巴汉子”对产生在中原大地上的革命风暴有明确觉察,那么“生活”意味着什么?如果“牧羊人”中的青春男女,甚至在接吻时也处在革命道德领域控制之下,那么“私人”生活又在哪里?如果刘文西笔下的农民不仅与毛泽东同乐,而且忘记了当时的斗争,那么“革命”意味着什么?如果大头像“父亲”只把人物当作布景,那么“现实”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政治、革命、现实成为一种制度深深地渗透在整个社会系统中。今天的商业制度下,艺术家跟随这个制度而行,就能给予合法化的身份,所有能够做后现代文化工作的人,他的存在也是这个制度的产物。农民如何呢?农民在中国任何制度下都是最庞大的人群,到2050年,中国仍有8亿农民,有5亿在劳动力层次上。农民在50年、100年后仍是绘画创作应该关注的主题。但是,今天的事实已经表明,全球化、经济化才是目前政治制度下艺术创作最合乎标准的东西。农民在文化中成了最局部和边缘性的东西,这正是这个题材在目前中国阶段的命运。
如果意识到农民也是现代进程的奠基者,那么每次我们忧虑它的气息虚掩时,就会知道它与以各种名义出现的价值体系相悖,包括政治、文化、市场、消费,这种种人类进步的苦心经营与农民题材相对广义的世界有时是冲突的。政治、经济运动会损伤情感,损伤绘画精神的东西。它给生存境遇带来另一种存在观,它只给予人们在政治或金钱中穿行的狭窄道路,它们通过全社会人人都在说的东西,用绘画的方式证明社会系统的强大力量。对于我们这个曾经出现过优秀农民绘画的国家,一次次的停滞、缺席、断裂、分岔,是一个重大事件,它没有消失,却一次次地抛弃了自己的历史——产生过伟大的经典创作的历史。
农民:中国绘画创作的主角,在全球化的新一轮热潮中,将经历一次更大的缺席,成为被遗忘的第一对象。虽然说我们的农业已逐步演变为郊区的历史,农民的身份也逐渐演变为打工者的身份,其中有数不尽的题材,它仍可作为已被改变了身份的农民绘画。可是,现实是艺术家们并没有多少兴趣对此作出反映——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农民文化的巨大力量作出反映。如果农民题材要继续发现它尚未发现的新的精神领域,那么它就不能与当今单一的资本经济价值观苟同,而是仍然要在人性、情感领域的现代经验下寻找真正的价值。
当今情境下,也许我们觉得是在艺术领域中最后谈论农民,谈论农民绘画的创作。今天,农民的声音的沉寂,使得艺术家要成为记忆和历史的承担者。我们已一代比一代更少有历史感了。历史中的伤痕和创口,以及随之而来的要在历史感中观察当下的断裂和缺席的历史,使得农民绘画创作问题不仅仅是艺术领域的纯粹意义上的谈论,它至少短暂地恢复了我们对现实主义的农民绘画创作的现代理性关注。
标签:农民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王式论文; 文化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美术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