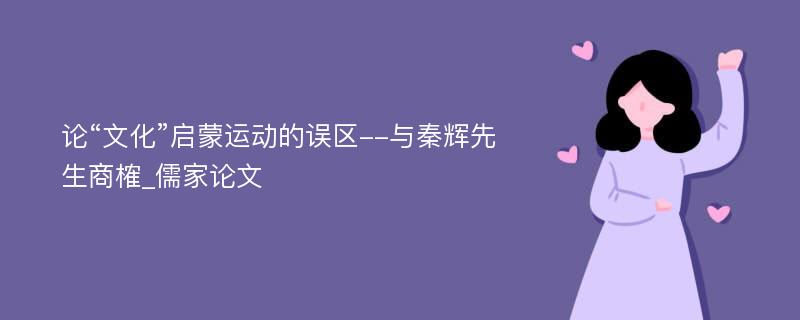
再论“文化”启蒙运动的失误——兼与秦晖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蒙运动论文,文化论文,再论论文,秦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导论
秦晖先生在《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5期上发表了《文化现代化与中国知识人》一文,挑战了我们对中国传统的一般性认识,并进而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化启蒙“由黄宗羲—谭嗣同式的援儒援西而批法道,逐渐转向集中批儒,并从章太炎开始兴起崇法扬秦之风。中西族性对立之说与西儒理论对立之说共同构成的文化决定论俨然成为共识。五四以后兴起的援儒批西的文化保守主义只是这种共识的另一种表达。其结果,使文化批判与文化保守形成了主观互悖而客观互证之势,法道互补的祸根却被漠视乃至得到新的激励。最终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与儒家的传统道义同归于尽,而强权哲学与犬儒哲学的互补却变本加厉,在制度上大共同体一元化控制也发展到空前的程度。”[1] 显然,秦晖认为20世纪的文化启蒙存在反儒(在中国历史上并未占据主导)不反法(支配中国传统政治运作的实际理念)的失误,并进而导致中国历史进程的曲折往复。笔者认为,20世纪的文化启蒙的确存在失误,但并不能简单的如秦晖所说的那样归咎于对儒家的过度批判和对法家的忽略。笔者的阐述将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对中国传统的重新考辨,二是在前者基础上探讨二十世纪的“文化”启蒙运动是否存在秦晖所说的失误。
二 “儒表法里”还是“儒法互补”
秦晖通过大量的篇幅论证中国的传统实际上是儒表法里,法家才是造成中国历史落后的真正原因。因此20世纪的文化启蒙倾向于批儒实际上是个失误。但笔者认为,秦晖的论证有失严谨,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儒法互用而非儒表法里,才是中国真正的传统。
所谓儒表法里,即是指中国历代的传统主要都是在口头上宣扬儒家思想,而行的都是法家理念。笔者认为,如果秦晖的这种论断是为了达到一种矫枉过正的效果,即诚如他自己开始所说的,“人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共同体本位特质注意不够,而过分夸张了所谓家本位与个性解放之间的对立。相应地,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法道互补的特质也注意不够,而过分夸张了西儒冲突……宜乎为之反思也”,[2] 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不过,秦晖接下来却以似乎很有力的论据论证了中国传统中的制度化思想是以法家为主导的,这实际上把儒家思想剥离了与中国传统制度的内在关系,无疑会误导我们对儒家之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真实影响的恰当认识。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对中国传统制度的思想解释,论证儒家不仅是古代中国口头上宣扬的治国理念,更是在制度层面上主导着传统中国,也即儒法互补而非儒表法里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
其实很多争论都涉及对所使用的概念的不同理解。当我们都在谈儒表法里或者儒法互补时,我们很有可能对何谓儒和何谓法这些概念本身的理解存在重要分歧。譬如秦晖所理解的儒家,他实际上是把主张“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派思想视为纯儒的标志。当然,他在文中有时又用理想主义从道不从君等来指称儒家的真义。总之,这些所谓纯儒思想都是与君主专制思想相背离的,因而不可能成为传统中国的主流。可见,秦晖通过把民本思想界定为纯儒的标志而抹煞了儒家在古代中国应有的影响。因为儒家作为一种成体系的理论,不可能用简单的民本思想加以概括的,而是具有比较复杂的思想内涵的。只有这样去认识那些儒家的代表人物,我们才不会产生疑惑。比如,正如秦晖所讲,孔子、孟子和黄宗羲是真正的民本派儒家。但孔孟的思想远远不能用民本派所能涵括。在他们的思想谱系里,民本观念的确存在,但其他同样重要甚至是与民本相冲突的思想却同时存在,从而与民本思想在儒家的思想框架下构成一种必要的张力。孔子一日无君便惶惶不可终日,孟子则坚持“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种对君王的强调无疑与民本观念相异。顺便提一句,以往很多学者都是在坚持儒家思想内部逻辑一致性的前提下把民本观念纳入到儒家对君主制的推崇下,从而弥合两者间的裂缝。但是笔者认为,儒家思想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里面可能存在不相和谐甚或是相互冲突的观念。因此民本观念与重君思想在本质上即使相互冲突,然而可以并存于儒家的思想脉络里。由此可见,与其说存在民本派儒家,还不如说存在民本观念。因为民本派儒家不能真正指称任何一位儒家代表人物。可见,秦晖对纯儒的界定无疑存在弊病。这种片面的认识无疑导致其进而认为“自秦以后纯儒几绝,而世儒基本上被同化为法儒(有为之儒)与道儒(无为之儒)两大支。”[1] 此处重要的不是法儒与道儒是否存在,而是法儒与道儒在本质上是否为儒,抑或是法或道。关于法儒或道儒的阐述,秦晖只是从他们的经济思想是否抑兼并的角度进行了初浅的描述,并未触及对他们在本质上是否为儒这一关键性问题的必要论证。如法为儒用和儒为法用就存在区别。其实自从百家争鸣的时代起,儒家思想就不可避免的受到道家法家甚至是佛家的影响。这种影响不能成为儒家不复存在的理由。比如通常讲的“朱子道,陆子禅”就反映了朱陆承袭道家和佛家思想以发展儒家。显而易见,这并没有影响朱陆在真正儒家代表人物中的正统地位。再比如,作为儒家的经典,《易传》和《中庸》明显反映了儒家认真汲取道家思想努力建构儒家的形而上学。相应地,我们也不能因此视这些道儒为非儒。因为儒家的道与道家的道依然存在本质区别。可见,用民本派儒家这个概念来一笔勾销法儒道儒作为儒家的合法性无疑是草率的。
在对概念进行论证之后,笔者将直接进入对儒家思想是否主导中国传统制度的探讨。秦晖认为儒家和法家分别构成传统的典籍思想和制度思想。然而正如陈寅恪所说:“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3] 其实自汉以降中国并未真正实行过法家之治,而基本上是援礼入法,把法家那种追求普遍主义理性转化为重人伦重情感的伦理立法,百代都行秦政制的说法脱离历史真相。法律儒家化开始于董仲舒等人的《春秋》决狱法,即以儒家经典尤其是《春秋》的微言大义来判决案件。这无疑对中国传统的司法制度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前者指道德成为法律。比如汉代法律允许近亲属之间互相隐瞒罪行而不受惩罚,甚至是对向官府告发父亲罪行的儿子判以重刑。这无疑体现了儒家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思想。后者意指法律的制定和执行要符合儒家的道德。古代流行的“存留养亲”制度,即犯死罪者或判流刑者,若父母年龄在70以上,家中无他人赡养,经“上请”,可暂不执行,犯人发放回家,待老人死后,再加以执行。[4] P29-30
二是礼成为立法司法的基础。司马迁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字也。”而《春秋》的根本精神就是维护尊卑贵贱差别的礼制。汉代创立的上请制度就规定,凡皇室贵戚勋爵高官犯罪,地方官无权判决,而要报请皇帝裁决。上请制度无疑一改法家的“法不阿贵”的原则,使权贵在法律上享受特殊待遇。
三是对无讼精神的推崇。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5] 这种思想渗入古代司法官员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如有兄弟争讼,县官不问谁曲谁直,但令兄弟互呼,此呼弟弟,彼呼哥哥,未及五十声,已各泪下沾襟,自愿息讼。判决书强调“不能以身外之财产伤骨肉之至情”。[6] P166所有这些都是强调用人伦关系来感化人心,解决诉讼。
由上可见,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由儒家理念所指导。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合理地解释中国为什么最终没有走上法家所要求的那样普遍主义的理性原则,而是倾向采用特殊主义和情感原则来治理国家。
笔者注意到,秦晖主要是从吏治角度阐发法家对中国传统制度的影响。如他认为传统中国实行的分权制度和防人之术就是体现了法家的性恶论。但是荀子作为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也主张性恶论,为什么不说受到儒家的影响?即使主张性善论的孟子也承认“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可见,这种性善论也并不与现实中的分权制度截然相斥。更重要的是,正是儒家对传统制度的主导影响才能真正回答秦晖所提出的疑问,即“为什么中国法家这么理性的原则最终没有导向西方那样的对专制制度的反动”?秦晖给出的解释是法家本身坚持的皇权本位使然。但这只是个表面化的解释。因为在对皇权本位的影响上,儒家必然超过法家。由于儒家的君权神授观念必然拥有法家所缺乏的形而上意义,因而对古代君主的吸引力更大。此外,儒家思想本身就充满着对皇权本位的推崇。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善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7] 可见,荀子实际上是主张由君主来实行具体利益在民众间的分配。儒家这种理念在现实制度层面便顺其自然的导致君主制在传统中国的长期实行。
由于在现实操作上,君主制很容易导向专制。因此儒家主张的道高于君又成为防范君主专制的制度设计的思想资源。事实上,自秦汉以下大一统的皇帝像传说中所渲染的桀纣一类的暴君其实很少,中国君主专制的程度较之同时期其他文明的君主专制统治要温和一些。这种历史现象绝非法家那种主张绝对专制的思想所能解释的,而恰恰是儒家的影响所致。诸如历朝历代实行的谏议制、史官制等制度都是防止君主专制的重要屏障。儒家在吏治层面上无疑发生了很大影响,与秦晖的过激之论显然不符。至于秦晖的科举制乃儒的吏化也即体现法家思想的说法也值得质疑。因为只规定天下人只有读儒家经典才可能当官一方面可以说成是儒的吏化,但另一方面又可说成是吏的儒化,即儒家对古代官员的主导。
其实单从法家的理论内涵来考察,我们也难以同意古代中国是由法家支配实际运作的观点。因为法家所宣扬的“法术势”不可能被古代君主全部接受。其中的“术势”由于适合君主驾御群臣和民众的权术需要而能被君主采纳。但作为代表普遍主义的“法”却不可能真正得以施行。因为皇帝难以做到法所要求的那种绝对理性,因而不能影响实际的政治运作。事实上与之相反的是,特殊主义与情感原则主导着现实。
总而言之,中国的传统绝非一个“儒表法里”所能解释的。儒家不仅仅是所谓的典籍思想,更是制度思想。而秦晖所说的“说的是一套(儒家),做的却是另一套(法家)”未免有失妥当。因为即使从常识上讲,一种观念若只作为一种矫饰而被宣扬,大家实际上却又都不认同,这种观念便不可能长期地受到哪怕是表面上的重视。欺骗只能在短期意义上存在,长期的欺骗实际上不可能存在。长期存在必有其真实的意义。
三 如何解释历史上反儒而不反法的现象
既然中国真正的传统是儒表法里,儒家不仅在经典的典籍思想上,而且在制度思想层面上实际处于支配位置,那么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在反儒方面并未存在方向性错误,相反有其一定的历史与逻辑上的合理性。但秦晖却在坚持儒表法里的前提下,认为近代以来反儒的历史事实并不能说明儒家本身在古代中国占据主导地位,反儒本身有着其他一些原因。笔者认为,秦晖一方面坚持儒表法里是中国传统,另一方面又不能回避近代以来反儒之声日涨的事实,两者间的张力与冲突促使秦晖匆忙找了五个方面的原因来解释20世纪为何力在反儒。笔者认为,其中的论证有失妥当。
秦晖列出的第一个原因是儒表,也即中国的传统在表面上是尊儒。这个理由无疑很牵强,因为既然大家都知道儒家只是在表面上受到尊崇而实际上并不具有主导位置,那么多仁人志士缘何不去反法?秦晖自己恐怕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举出第二个原因,即在20世纪时人对于构成儒家伦理核心的家族本位或曰小共同体本位的强烈感受有关。秦晖继续阐述道,当时中西冲突导致无论西人观察中国还是国人观察西方,的确常有西方“个人本位”与中国“家族本位”的区别。于是以家族伦理为核心的儒家自然就被等同于“中国文化”而受到大举鞑伐了。这个理由看是有理,实际上是秦晖的自相矛盾。一方面说中国主流传统并非儒家,另一方面又认为时人对于儒家伦理的核心——家族本位感受犹深,故而要求反儒。其实时人对家族本位感受很深恰恰体现了儒家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性影响,而这无疑推翻了秦晖对中国传统的判断。
秦晖举出的第三个原因是救亡对启蒙方向的影响导致了五四式的个性解放主要是冲着小共同体桎梏即“宗族主义”的束缚而来,而在强国梦中很难产生对大共同体本位的“国家主义”传统的深刻反思。但是反宗族主义不反国家主义,并不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只反族长不反皇帝,五四时代人们对皇权的批判不亚于对宗族的批判。秦晖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不过他认为当时对皇帝的批判只是把传统专制当作皇帝个人的家天下来反的,而缺乏对大共同体扼杀公民个人权利的批判。似乎只要不是一姓之国而是人民之国,就有理由侵犯乃至剥夺公民个人自由。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但依然存在前面所指出的逻辑矛盾,即反倒体现了中国传统是儒家的家族本位。此外,人民专制也并不能和大共同体本位划等号。救亡压倒启蒙并不必然导致人们对人民专制的认同。与其说历史最终导致人民专制的原因是时人反儒而未反法所致,还不如说是一个属于现代性的问题,即我们在追求民主自由的同时,如何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人民专制。可见,用救亡影响启蒙的观点来论证时人反儒的原因同样有失妥当。
第四个原因是,中国人当时接受的西学中存在的“问题错位”,即西方的启蒙是针对他们小共同体本位的中世纪传统,到了20世纪,国家主义恰恰是种近代思潮。于是当时输入中国的种种国家主义思潮,更进一步加剧了只反宗族不反国家主义的倾向。反映在文化批判上,就是反儒不反法。笔者认为,这个理由同样站不住脚。因为众所周知,虽然20世纪国家主义有甚嚣尘上之势,但同时与之相斥的其他思潮同样声势浩大,与国家主义完全相反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一度得势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还有诸如自由主义等思潮同样具有很大影响。为何国家主义能够最终得胜并不能简单的归于西方产生的某种思潮本身,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当时具体的各种力量的角逐所致。因此秦晖用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做法无疑会忽视对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的深刻考察。
秦晖对最后一个原因的论证尤其失于严谨,即认为法家那一套厚黑学式的性恶论,中国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私制私,法治学说很容易与现代政治理论中的人性局限假设进化史观分权制衡与法治主张鱼目混珠。照这样说,我也可以同样运用这种思路论证时人应该对儒家大加赞扬了。因为儒家的民本思想于主张专制的法家相比更容易同西方的民主学说鱼目混珠了。因此,儒家应该比法家更有资格受到褒扬。但历史事实无疑推翻了这种假象,因而也就反衬出秦晖论证的缺陷。
四 结束语
由上可见,秦晖认为20世纪中国文化启蒙的失误在于反儒而未反法的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中国传统的主流依然是儒家思想。因而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对儒家的批判并未像秦晖所说的那样犯了方向性错误。“文化”启蒙运动之所以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批判对象的错置,更多地应该是批判武器本身的问题,如时人多是在对西方思想未加深入思考的情况下盲目拿来用以批判传统文化。因此,在反思历史上的文化批判时,我们一方面不应忽视对传统的关注,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对思想本身包括西方舶来理论的深刻检视上。唯有这样,也才会提醒我们在中西融通上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
标签:儒家论文; 秦晖论文; 国学论文; 法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启蒙运动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中国法制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