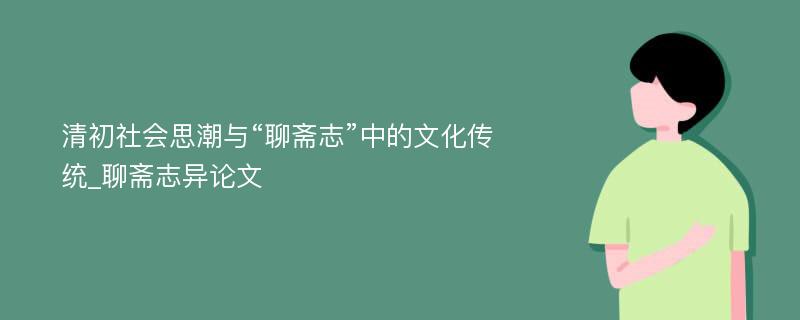
清初社会思潮与《聊斋志异》所蕴涵的文化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聊斋志异论文,清初论文,思潮论文,蕴涵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以志怪为主要内容的文言小说创作传统,经过宋、明两朝的继续,至清代仍方兴未艾,而其中最为突出的作品则应推《聊斋志异》。该书的问世,就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发展史而言,似是一个有力的总结和辉煌的句号。从作品思想方面说,这是一部深刻的社会批判著作;而在艺术上,该书又从非常广泛的方面继承了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和史传文学的传统,在祖法晋唐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境界和艺术风格,超越了既往的文言小说的成就。遂作为一种艺术成就甚高且蕴涵有丰富文化意蕴的作品,而卓立于古代文学史上。
《聊斋志异》的如此思想和艺术成就的取得,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思潮背景下,由多种文学、文化传统的结晶的成果。
一、清初社会思潮与蒲松龄
《聊斋志异》是一部社会批判小说,它的出现首先是一定时代特殊社会思潮的产物。
其作者蒲松龄(1640-1715)山东淄博人。根据生平情况,《聊斋志异》大致是作者晚年的创作,其具体写作时间,似可断限在1671年至1715年之间,也就是作者屡试不第和绝意科举以后的这段时间。这是康熙皇帝统治(1662-1722在位)的后期。该书的出现便首先与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特点密切相关。
满清入主中国以后,直到康熙三年(1683)才最终统一全国,而在这个漫长的统一过程中,明末清初的汉人绝大多数是采取了双重的人生态度:一方面是抗清反满的遗民态度,另则是在高压之下对于清统治者的臣服;在士人那里,这两种态度更为明显。清初文人社集之盛和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应该是对此的明确注释;而钱谦益(1582-1664)等士人的依违于仕清与自以为耻的思想,又是比较典型的表现。正是在这样较普遍的社会意识下,清统治者很快地恢复明代的社会统治思想和一些统治措施。当然,这也与满清民族的汉化有密切的关系。在思想和政治上恢复明朝统治的举措中,最为注重的是满清统治者恢复的程朱理学的思想统治地位和实行科举考试。事实上,对于统治中国古代士人而言,没有什么能比这两种方式更有效且深刻了。
满清统治者在这两方面均作了不遗余力的努力。就前者说,康熙皇帝“夙好程朱,深潭性理”(昭连《啸亭杂录》)推崇理学,居常讲论,无不以朱子之学为正宗。御旨编纂《性理精义》,重刊了明代的《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书,颁行全国;执行了“表彰经学,尊重儒先”、“一以孔孟程朱之道训迪磨厉”的文化政策;优宠理学名士,选任理学家出仕为官。在后一方面,恢复了科举制度,仍按明代旧制:八股取士;在尊重程朱理学的过程中甚至出现了有的学者因为在著述中没有采用程朱学说,而是运用古典经书被责罚的事情。康熙十七年(1678)又开设博学鸿词科,以罗致天下名士,并增加了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跟这两个措施相羽翼的是文化上的高压统治:严禁文人结社、大兴文字狱;科举考试的内容完全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等。这里举例的是文字狱:清初康熙、雍正、乾隆(1662-1795)三朝前后见于记载的文字狱有七、八十起,仅康熙二年(1663)的“明史案”就杀70多人,株连200余人;戴名世《南山集》之狱死100余人。经过上述的努力,清初社会上就形成了以恢复程朱理学并至兴盛,伴随政治高压和推崇科举为特色的社会思潮。
就对文学创作影响而言,这一社会思潮首先笼罩了《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进而作用和影响着他写出了此书。其中的关键是,蒲松龄在此一社会思潮之下所造成的,对于时代而言的双重人格和双重人生选择。
蒲松龄屈身并乐意在他的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和文化政策面前低下头颅,但他后来又背叛了自己的人生选择并对此深恶痛嫉、厌恶乃至否弃,而这其中的动力居然是他科举考试的屡试不第,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求做奴隶而不可得。唯其如此,他才能对社会有严厉的批判;对科举弊端有深刻的揭露:对人生有重新的评估;对与人生相关的内容有美好的祈望。
跟明末清初的许多士人不同,蒲松龄最始所走的人生之路,是完全遵从了其时社会思潮所划就的辙印。蒲松龄出身于没落地主兼商人的家庭,还是在他祖父时家道就衰落了,其父亲不得不弃儒经商;到他出世时,家庭更为贫破。这样的家庭背景下,蒲松龄尽管也处在明末清初这个改朝换代之际,但他没有像另外一些出身名门大家的青年如吴伟业(1609-1671)、顾炎武(1613-1682)、屈大均(1630-1669)那样对旧王朝怀有深刻的留恋、对新的王朝产生强烈的批判意识,并用某种方式寓托出故国之思;而是从小就热衷功名,以图在这方面兴盛家道。就人生的选择而言,在某种意义上说家庭的背景是起着较大的作用的;许多本来是志向高远、才华横溢的人,往往因为其家庭贫破的关系而隳颓了自己的志向,这也往往符合中国人常说的那句“人贫志短”的话。
上述种种迹象说明,在清初社会思潮的进行中,蒲松龄是一个顺从者。
二、《聊斋志异》与不平而鸣文化传统
蒲松龄在作了求取功名的选择后就醉心于科举,而且在十九岁时,连取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可是这以后却命途多舛、屡试不第。所以,即使他一直坚持科举考试到五十岁,也未能金榜题名。在长达三十年的应举路途上,蒲氏可以说是越陷越深,几近不能自拔。“三十功名尘与土”换来的除了失望之外更多的就是愤愤不平。
从蒲松龄的生平和其他著述中我们可以很明确地见出:他是一个“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且又耿介正直、不阿权贵的人;同时还有一些侠气;在思想方面他更是一个怀有非常复杂观念的人。择要而言,他具有朴素的民生意识、有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像《水浒传》中所写的那些起义者一样,他对于社会的不满仅只表现在对于贪官污吏和霸道的土豪劣绅,而对于封建社会制度和最高的统治者却存有幻想、抱着忠诚。另外,在一些其他方面的观念上也同样表现出矛盾的情况:比如在爱情思想上,他既宣扬爱情自由、主张真爱,又对一夫多妻、妇女附属于男人表现出肯定;对于科举制度他一方面持着严厉的批判态度,而这批判也更多地是指向不公正的考官或他们的糟糕水平;另方面则对科举抱着极大的热情。或许主要是因为后者的缘故,在蒲松龄的思想中充满了郁愤不平的情绪,此种主要是因为蒲松龄的才华横溢和科举考试中的屡屡名落孙山之强烈反差所造成的情绪,是贯穿在蒲松龄的人生始终的,同时也是深刻影响了他对于社会和人生的态度和取向,以及评判的重要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聊斋志异》就是这一思想情绪的主要载体。所以,如果说该书包含着非常深刻和丰富的传统文化的意蕴,那么首先的和第一位的就是其中的不平而鸣的抒愤传统。
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很早就表现出一种不平而鸣的抒愤传统,关于此一传统,韩愈在他的《送孟东野序》里有一段相当精辟的概括。言: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呜。……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闽能够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乎?其抹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藏孙辰、孟轲、荀卿,以其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也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杂乱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耶?何为乎不鸣其婶鸣者也?
在此段描述中,韩愈将来自自然界的和中国古代社会的不平而鸣的现象作了纵向的归纳,揭示出不平而鸣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现象而存在的事实,同时也指出:人的不平而鸣总是有所假借的或曰有一定方式的。
就人类社会而言,不平是人在遭遇不公平现象时所引起的愤怒或不满的情绪。为了此种情绪的表达,作为情绪的主体总是不能无动于衷;总是要采取一定的方式和方法来将这一情绪发泄出来,用以维持自己的心理平衡和情绪稳定,否则其生命或身体就会受到伤害。对于士人而言,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韩愈上所述及的内容就是此方面的最好例证;其实,早在汉代,司马迁就发表过类似的见解。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言: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诌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在《报任安书》里,他又对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许多士人和政治家的不平而鸣作了概括性的描述。言: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违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在司马迁看来,很多政治家和文学家的著作都是痛苦灵魂的呼叫,是对于不合理的现实的控诉。他还在《伯夷叔齐列传》中记叙了二人因愤而作歌的事迹。这样从中国古代文化史和文学史的角度看,不平而鸣的抒愤传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创作很显然是对于此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因为尽管在人生的遭遇上,蒲氏非是上述韩愈和司马迁所描述的那些人的遭遇那样轰轰烈烈,但一个非常近似的质点是,他们都是遭遇了不公平,都是在心里郁积了愤怒和不平的情绪。
如上所述,蒲松龄从少年时代起便热衷功名,置身科举,并曾取得过非同凡响的成绩。在他的心里一种于此获取成功的定势已然造成;而就客观事实发展趋向言,其科举上的成功应该是水到渠成。可是,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中所固有的不公正和黑暗,破坏了他的既定的成功趋向和必然。如果说这种不公平只是一次、两次则蒲松龄也不会有如此的不平和激愤,恰恰相反,在蒲氏的生命里程中,这种不平居然延续了三十年,所以在蒲松龄那里,不平的情绪就犹如久积重压的火山那样,时刻在寻找着喷发口。用他自己在《与韩刺史樾依书,寄定州》中的话说,就是:
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
只是他没有哭向南山,而是写出了一部《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这部书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尽管也有不少的有关爱情、商业、社会上的罪行和民生苦痛的描写,但它的主题内容却毫无疑问是针对他所最为投入、也最感不平的封建科举所作出的描写和批判。在这本书中无论其他的内容占有多大的篇幅,但有关科举考试和这个制度的内容应该是它的核心。易言之,《聊斋志异》也许表面上是一个五花八门的杂货摊,但作者在这里所本来要出售的却是他在科举考试经历和在感受科举制度中所郁积的忿忿不平。这正如《聊斋自志》所说:
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这也就是说,在《聊斋志异》作者那里,或许还有其他方面的成书因素,比如《聊斋自志》所言的:
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
但这并不影响该书的发愤为作之性质。因此,在《聊斋志异》书中我们最先所见出的,就是它所蕴涵的不平而鸣的抒愤传统。
三、《聊斋志异》与温柔敦厚的诗教
如上所论,《聊斋志异》在很大的方面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诗人很早就已经形成的不平而鸣的抒愤传统,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却是,蒲松龄的抒愤方式和方法上与他人有较大的不同。因此,这又涉及了该书及其作者秉承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蒲松龄的不平而鸣之抒愤方式的与众不同,并非是指他用了小说而非诗非词,而在于他鸣的过程中是遵循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士大夫那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诗教传统。
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很早就形成了一个为上层社会所遵行的文化范式,这就是贵族式的平和与冷静的为人处世方法,此一方法延展到诗歌领域,则造成了温柔敦厚的诗教。它在《诗经》时代,即有了相当充分的表现。其时那些“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大都作到了怨而不怒;而那些明确地见出国将不国的士大夫在作雅诗时又作到了哀而不伤。此一传统经过屈原的发扬而被广大。屈原在其遭遇不平时,能吟出非常“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诗,连司马迁都叹为观止,《史记本传》云: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
蒲松龄很好地继承了这个传统,并且是通过小说的方式。如上所论,《聊斋志异》主要是一部揭露和批判性质的书,它的主要指向是封建科举考试及其制度,同时也旁及其他内容,但在批判的过程中,本书却非锋芒毕露,而是采取了相当委婉或巧妙的方式,有的则是用寓言的形式。这也就是作者所说的“寄托如此”。
《聊斋志异》写作上所采取此种方式有与其时社会思潮相关的因素,那就是政治文化上的高压和严酷的文字狱;可这并不是主要,主要的则在于作者对于传统诗教的继承。蒲松龄是一个“本分”的封建知识分子,积三十余年之功而对封建科举考试一往情深就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这样,尽管在《司文郎》、《于去恶》、《王子安》、《贾奉雉》等篇章中对于科举考试作了揭露和批判,但他用的是曲笔,是寓言,是浪漫的笑话。在《促织》、《席方平》、《梦狼》、《商三官》、《窦氏》等篇中,他尽管是在暴露社会的黑暗和封建官吏、土豪劣绅的罪行,但《促织》却是一个因祸得福的半神话故事;《席方平》则是在阴曹地府展开的斗争;《商三官》则主要是欣赏女侠的作风。像这样的作品其实在理解上是可以发生许多歧义的,而之所以有歧义,根本点在于作者写作上的曲笔;也就是他采用的是委婉、巧妙的批判和暴露方法。
最可见出《聊斋志异》温柔敦厚作风的是那些作者用丰富的想象把花妖狐仙人格化以后所造就的那个浪漫而神奇,并令人向往的世界。
《聊斋志异》是从生命一体化观念出发去表现各种狐妖鬼魅的变形、转生,重视灵魂的流转。只是各种事物的情态毕竟有所差异,所以蒲松龄在展示狐妖鬼魅的转生和变形的过程中,特别地注意到对于对象本质特征的表现,在表面的漫不经心的描述中,将它们表现出。《绿衣女》、《阿英》、《婴宁》、《阿宝》是这方面的代表;在《聊斋志异》中,很多的故事是发生在人和狐妖鬼魅之间的,书中,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是相通的。作者采用恍惚迷离的手法,使得两个世界的畛域显得模糊不清;从而出现了亦真亦幻的景象。《画壁》中的画中人可以飘然与人共寝,又可入画,完全成为画人;《成仙》中的周生自己梦自己成仙又自视己身之存在等等是其代表。还有《瞳人语》中的谏淫;《赌符》中的谏赌;《酒狂》中的谏酒;《田七郎》的复仇都是借助狐妖鬼魅的超凡力量,通过他们来解决世人无能为力的难题。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蒲松龄在描写这些内容的时候是平静的,甚至是带着微笑的。这表明他虽然有“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的怨愤,但他能做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他在浪漫的、幻想的世界里沉浸下去了。这毫无疑问是温柔敦厚诗教的力量使然。因此,在《聊斋志异》中我们亦可见出此一传统文化意蕴。
四、《聊斋志异》与“以幻为真”的文言小说传统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很早就造成了一个“以幻为真”的创作传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家在选取描写内容和写作材料时其价值取向是在于实存现象的。就是说在作者这方面,虽然所写的是神怪内容,但作家所秉持的却是传真传信的原则,所以他们都有目地去记录那些听之某人,见之某地,发于某时或某人可证的玄怪故事;所以尽管他们所写的是神仙鬼怪,但主观的愿望却是在“发明神鬼之不诬。”
到唐代,文言小说大多以“传”和“记”来名篇。如《李娃传》、《会真记》、《补江总白猿记》。“传”和“记”在记述内容上虽略有不同:“传”以人物为主,以传主的生平为线索,写其卓而不群的事迹;“记”以事物为主,以事物变化为线索,记其奇幻曲折的经历。但两者更多的是相同:写人必须有事,记事必然会表现人。所以到唐代后期,“传”与“记”就渐渐合一,即大多以“传”来命小说之名。如《任氏传》、《柳氏传》、《莺莺传》、《谢小娥传》、《柳毅传》、《东城老父传》等。以“传”专记一人之生平事迹,创始于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中用了几十个“传”来描写历史人物。小说家此时钟情于以传写人,颇可说明他们在择取描写对象上还是依恋于史家那种“以实而取”的价值取向的,尽管小说的“传”与史书的“传”在内容的严肃和崇高上有极大的差异,可作者那里并没有放弃“实录”的原则,因此在唐传奇中我们仍然可见到大量的声明是出自某地、见之某人或证于某人的作品;明代的文言小说,也一仍其旧。这样“以幻为真”就作为文言小说的一个叙述传统而传承下来。《聊斋志异》也非常突出地表现着对这一传统的发扬。
在《聊斋志异》中,作者是通过浪漫的、丰富的想象能力来创作他的世界的。在这个世界里,最主要也最多的是那些女鬼和女性的狐仙。显然这一切都是非真的内容,但在作者,却是“以幻为真”的。《聊斋志异》中的女鬼主要是作者描写被压迫被迫害妇女的载体。她们是精灵。往往以一个女仆的身份出现,从而把自己的不幸告诉活着的人们;或者死去的心上人又回到情人的怀抱,并为他生儿育女。在这些具有浓厚人情味的小说中,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不怀疑她们的真实,因为那些女鬼和狐仙是那样地令人吃惊地通晓人性、那么惊人地可爱:她们有嫉妒之心,也爱别人,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在该书中,上述的鬼怪并不是让书生们晚上独自一人呆在书房而感到害怕的鬼怪。当蜡烛即将燃尽,书生昏昏欲睡之时,他听到丝绸衣服悉挲作响,睁眼一看是一位十六七岁娴静少女。一双渴望的眼睛,一副安详的神色,她看着他笑。她通常是一位热情的女子。蒲松龄就这样按着他自己的意愿,非编造而是真实地写下去:这女子能通过各种把戏给书生带来金钱,帮助他摆脱贫困。书生病了,她精心服侍,直至痊愈。其温柔的程度,超过了一般的现代护士。更为奇怪的是她有时还为书生攒钱;在书生外出时,她可以在家里耐心等待,一等即几个月,乃至几年,而且也能非常贞洁。这种共同的生活可长可短。短到几天、几十天,长则几十年,直到她为书生养育了儿女。儿子科举高中之后回家探母,结果发现豪华的宅邸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古老的坟墓。地下有一个洞,里面躺着一条死去了的老狐狸;有时她会留下一个纸条,说她很不愿意离开他们,但她是一条狐狸,原不过想享受一下人间的生活。现在他们既已经兴旺发达,她深感欣慰。她还希望他们原谅她。
很显然,蒲松龄的想象力没有在上帝的世界里翱翔,而是认真地赋予这些幻想的人物以人类的感情和人类的愿望。作者所秉持的是一种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品格,他既承认想象也承认现实,他甚至完全地相信他所构造的世界的存在。当然这也同时包括他不时地在作品中宣称此事见于某人、发生于某地。
关于这一点我们尚可通过地理文化学方面进行一定的解释。那就是因为作者所处生活地域的封闭使得作者的世界观也处于封闭的状态;而此一封闭也影响到他创作小说时“以幻为真”。《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家于山东淄川县城东七里许之满井庄。清初的淄川县交通很落后,离当时“国道”(北京至山东)至少有200公里。而蒲松龄本人除一度游幕苏北外(约一年),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活动在淄川和济南之间,其主要工作为在“缙绅先生家”“设帐教学”。因此,他没有更多接触商品经济社会的社会,对其时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所知甚少,这一切自然与他所住的地区不便的交通条件分不开。蒲松龄本人一生怀才不遇,命运偃蹇,这使他形成了宿命论思想,同时封建迷信影响也相当严重。这些都自觉与不自觉地成了他创作《聊斋志异》的思想基础。
再者,《聊斋志异》虽有部分作品出于作者的亲身见闻,如《地震》、《跳神》等,有的则是继承过去题材,经再创造所发展出来,如《续黄粱》(本《枕中记》)、《莲花公主》(本《南柯太守传》)等。但绝大多数作品却是记叙当时传播于民间和下层文人中的故事传说和自己创作。对于这些阴曹地府、花妖鬼魅和人神恋爱故事,蒲松龄是抱着相信的态度的。这从他“才非干宝”、“情类黄州”的习惯秉性上可窥见一斑。此外,清人冯镇峦《读聊斋杂说》也写到:
此书多叙山左右及淄川县事,纪见闻也。时亦及于他省。时代则详近世,略及明代。先生意在作文,镜花水月,虽不必泥于实事,然时代人物,不尽凿空。
也就是说《聊斋志异》的绝大部分是“以幻为真”的。
结语:
《聊斋志异》所蕴涵的文化传统并不止于上述,但,仅从上所论及的内容中我们却可见出其文化意蕴的丰富与深刻。通过以上的描写和说明,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和领略出以下几点有关文学发展、文学思想发展的理论质素。
首先,一部小说蕴涵的文化传统丰富深刻与否是与其时的社会思潮有密切的关系。《聊斋志异》之所以有如此的文化传统意蕴,根本的原因乃在于它与清初社会思潮的密切联系;该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时代社会思潮压迫下的士人心灵的曲折表现。《聊斋志异》所蕴涵的不平而鸣的抒愤传统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从中我们还可见出作者的生活环境及生活水平在某些方面也可影响到小说作品,使它带上特定的文化痕迹。《聊斋志异》的作者因为出身的卑微和生活的贫迫,使得他自觉与不自觉地继承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最后,一部小说的文化蕴涵还与小说作家所生活的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生活在封闭地域环境的作家和生活在开放地域环境的作家因为受环境的影响而导致世界观的不同,遂在对于神鬼怪异的认识上有与今人相反的观点。正因此,《聊斋志异》因其社会在封闭地域的环境中使得他继承了“以幻为真”的文言小说叙述传统。
收稿日期:2001-0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