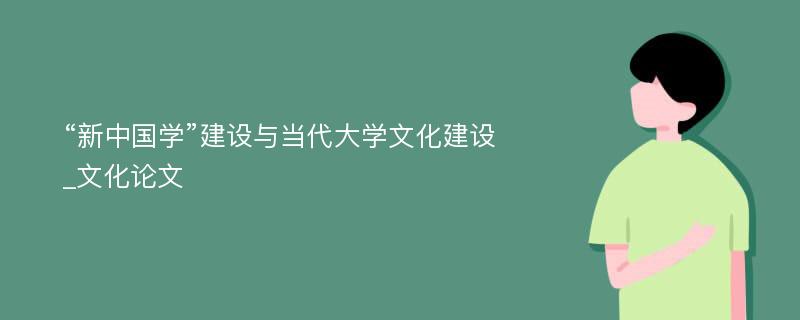
“新国学”建构与当代学院文化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建设论文,国学论文,当代论文,学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0257-5876(2007)03-0032-09
时至今日,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发展主要立足于学院文化的建设,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化不断进行的阐释更是从发展学院文化的中国学术出发的。我认为,王富仁的《“新国学”论纲》的一个主要之点即着眼于当代学院文化的建设,针对的是中国学院知识分子的学术观念存在的缺陷,以及由此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正常发展的影响。基于这种认识,我准备从对“新国学”理解出发,谈谈《“新国学”论纲》对当代学院文化建设的价值和意义。
“新国学”是通过对“五四”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化的重新认识建构起来的。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在西方,文化都是适应整个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发展起来的,文化与社会之间在整体上是统一的,体现的是一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关系,但是,中国现代文化与“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之间不存在结构性的“毛皮”关系。毛泽东青年时代直接受到“五四”新文化倡导运动的影响,他把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概括为“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这个概括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都是十分精确的。“五四”新文化倡导者对此显然有更深刻的体验,他们明确认识到中国社会较之1840年前的状况在整体上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枪,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此外如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自命‘胜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拿钱;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这许多事物挤在一处,正如我辈约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开饭店一般,即使竭力调合,也只能煮个半熟。”① 鲁迅1919年的这一观察和认识,起码可以说明如下几点:一、1840年中国国门打开以后,西方事物和西方话语是通过中国文化并不认同的方式强行置入中国社会的,肢解了中国固有社会生活方式,这固然是民族“被动挨打”境遇的结果,但却反映出中国固有价值观念已经不可能维系变化了的整个社会生活,同时,夹杂于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这些西方事物和西方话语又不可能使中国固有价值观念发生根本变化。二、这就是说,中国社会既不可能延续固有文化模式存在下去,也不可能通过“全盘西化”沦为西方社会的附庸,现实社会生活中羼杂着的中西事物和中西话语具有彼此无法相融、无法取代的性质和特征,而这些脱离其文化结构“整体”而以“部分”呈现的中西话语,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中间又不可能引起中西文化的整体观照和比较,这带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的失衡和信仰危机,鲁迅针对这一现象说:“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② 显然,改变这种“二重思想”,有赖于“五四”中西文化整体比较中的中国现代文化创造。
更主要的是,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在整体上是互为隔绝的,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依照各自的结构逻辑发展起来的,建立在各自独立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中西文化的发展不存在彼此之间的影响而产生的困境;中国现代文化则是在中西文化碰撞背景下产生的,甚至可以说,离开了中西文化碰撞和影响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化发生的可能,但前述脱离其文化结构“整体”而以“部分”呈现的中西话语充塞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中,带来中国现当代文化发生和发展的特殊艰难性,时至今日更是通过中国学术表现出来的,体现在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化的认识上,反映了离开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中西话语的影响带来的我们认识上的混乱。如果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整体上既不是为“发展”也不是为“颠覆”中国现当代文化而存在的,在整体上与中国现当代文化根本不同,那么,怎样看待中国现当代文化与中西文化的关系,就不能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就此而言,大致可以区分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首先,应该看到,中国现代文化并非是在1840年后的中西文化碰撞中自然萌生的,其发生过程更体现了新文化倡导者在中西文化整体比较中的主体精神作用,他们与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在直面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切实感受和体验中建立起来的,这同时也是他们的精神主体建构和创造过程,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不再以其固有形态呈现,而转化为他们开拓的中国现当代文化缺之不可的组成部分。鲁迅和郭沫若与一些中外作家有非同一般的精神的联系,如鲁迅与嵇康、阮籍,与果戈理、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如郭沫若与歌德、惠特曼、泰戈尔,与屈原、庄子,离开了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难以形成他们作品“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但也显而易见,这些外部影响因素是在他们对中西文学整体感受和认识中形成的,在他们作品中是浑然一体表现出来的,成为他们感应中国社会人生的创作主体的构成因素,内化为他们精神主体建构和创造的有机成分——所以,我们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出发显然难以领悟鲁迅同名之作的“忧愤深广”,楚辞或者庄子的作品自然也不可能引领我们真正感受和认识《天狗》中“我的我要爆了”的博大意蕴。我认为,看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即在我们的认识中,与中西文化相联系的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发生和发展,一旦离开了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主体境遇感受,离开了中西文化整体比较中的精神主体建构和创造,中国现当代文化与中西文化的关系就会发生“主体”的位移,表现为“主体”向在自身“结构”中显示其意义的中国古代文化或西方文化的偏移。诸如“五四”后出现的新儒家学派无疑是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这使它离开了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现代文化形态的表现,但它却是倚仗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对立而产生影响的,新儒家学者站在对古代文化直接继承的观念和立场上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断裂了中国文化,反映了他们的“身首分离”,言说话语与实际境遇感受相悖反,说明他们的思想文化观并不是建立在他们对中国社会文化应有的切实体验和感受之上,他们难以感同身受认识到中国文化变革的必要性。这更是一个文化发展观的问题,实际上,即使是中国古代文化,或者西方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化,其发生和发展与固有传统之间联系的形成都不是通过直接继承实现的,都不能不建立在变革基础上,欧洲文艺复兴通过对欧洲中世纪文化的整体变革使古希腊文明焕发了新的生命,章太炎对先秦思想文化价值的发现是通过对时至清末独尊孔子的宋明理学的反拨实现的,鲁迅与魏晋文学联系的形成更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整体变革要求之上,体现的是以“立人”为宗旨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开创。对比之下可以看出,作为现代文化形态表现的新儒家学派仍然坚持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直接继承,体现的是一种文化退化和消亡的观念,这种颠倒了的价值评判形式在中国文化的实际发展中是具有虚幻性的。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倡导者通过“文化变革”使中国古代文化发生了整体结构上的破裂和重构,而使我们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化更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一种真正发展,那么,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之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化,需要的则是一种“文化转换”,这不仅是语言文字符号上的,更是通过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体验与认识实现的,体现的是在中西文化整体比较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化精神主体建构和创造过程。杜威的实用主义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是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两种相对立的思想学说,同时也是对当时留学欧美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更大影响的两种思想学说,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学者接受和运用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对“五四”新文化倡导运动的根本否定,是从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出发的,更建立在新人文主义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对立之上,他们既难以认识到二者在西方思想文化整体结构中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又没有能够使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在他们应该有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体验和认识中发生转换,他们落在了一个“不中不西”的尴尬境地,较之新儒家学派更为突出地表现出“身首分离”,他们也因此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反对派,在文化观念上具有更大的虚幻性。如果考虑到学衡派与新儒家学派相一致是由学院中的一些以对中外文化传统的阐释、研究、传承为主要职能的学者构成,相一致地强调中国现当代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之间的直接继承关系,是可以看到“五四”后出现的以知识论生产为主要职能、更具有国家主义性质的现代学院文化,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和中国现当代学术发展中所起到的“内部分裂”作用。留学美国的胡适的情况则与此有所不同,他早年在上海编辑《竞业旬报》期间对中国现实社会问题就有了深切体验和认识,并带着这些体验和认识到美国求学,他又在《新青年》变革话语氛围的影响和感应中从美国回国,这使他接受的杜威的实用主义不是通过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对立来表现,而在参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开创中发生了转换,具有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变革意义,他成为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胡适与李大钊是在《新青年》直接影响下集合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他们更是在鲁迅坚持并发展的现代社会文化中表现出文化变革观的一致性的,李大钊不久走向现代革命文化建设,胡适在对文学革命倡导成功的自信中本有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特征愈益突出,而致力于现代学院文化的开创,这是与西方文化相联系的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空间不断扩大的表现。但是,以“五四”为根基的现代社会文化、现代革命文化、现代学院文化各自的独立发展,需要建立在彼此之间“相对统一”而并非“绝对对立”基础之上,以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化的整体发展。但实际情况又并非完全是这样的,1919年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不仅表现出他们原本具有的现代社会文化倾向的弱化,而且他们更是在西方出现的两种极端对立的思想学说的直接影响下,把根源于“五四”而可以相统一的学院文化与革命文化的差异和矛盾绝对化,如王富仁在《“新国学”论纲》中所分析的,这“标志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内部差异和矛盾开始以西方不同思想学说差异和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常常是以相对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苏联和美国几乎构成了思想的两极,假若说当时的苏联猝然成了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策源地,当时的美国、特别是当时美国的学院文化则几乎成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桥头堡……正是马克思主义和当时美国学院文化的这种两极对立的性质,将中国这两个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撑向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两极,几乎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大分化、大动荡的震源”,而使在中国“原本具有互补意义的两种文化”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出现了“可悲的分裂”③。鲁迅对此则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在胡适与李大钊发生“问题”与“主义”之争后,他继续通过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参与现代学院文化开创,并与胡适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又不断地把自己的小说投给已然转向现代革命文化建设的《新青年》,这建立在他对中国现代文化整体发展的独立思考和认识之上,而寄希望于分裂后的现代学院文化、现代革命文化与他所坚持的现代社会文化在“相对统一”而并非“绝对对立”基础上的发展。
中国现代文化“内部裂变”之借助西方不同思想学说差异和矛盾的形式,实际上更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内部深刻差异和矛盾的表现,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困境更主要来自这一方面。诸如从日本输入的指称西方不同思想学说的“象牙之塔”和“十字街头”,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不同体验和认识的表现,由此形成的是几乎贯穿中国现当代文化的“‘象牙之塔’与‘十字街头’截然对立”的话语形式④。但在西方思想文化中则不是这样的。在西方,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集合了那个变革时代的社会文化、学院文化和革命文化所提供的全部思想文化资源,这在卢梭的思想学说中有集中体现,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开创亦如此,卢梭和马克思是以各自时代的社会革命家而著称的,维尼虽有着与法国大革命相对立的思想倾向,其“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虽被称为“象牙之塔”的始作俑者,但维尼思想的价值又恰恰是被法国大革命所照亮的,在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对“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的阐释中,维尼思想体现的是“理智”地要求在法国“公众空间”中建立一个“自我空间”,是“抛弃了不成熟的羁绊之后”要实现“为自己而思想”所做出的选择,以“传播每个人为自己而思想的职责”⑤,是那段历史时期最富有启蒙意义的——可见,在法国以至欧洲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维尼与卢梭、维尼与马克思之间在思想观念上虽有明显的矛盾和差异,但却是“历史形式”上的,而不是“根本内容”上的,是欧洲思想文化“结构”多元对立统一的表现,体现了欧洲思想文化的整体发展,但中国现代文化的“内部裂变”之对西方不同思想学说的借助中,维尼与卢梭、马克思的思想学说“历史形式”上的差异和矛盾是作为“根本内容”上的对立被理解和运用的,“‘象牙之塔’与‘十字街头’截然对立”实际上是“五四”发展起来的学院文化和革命文化自身蜕变的表现:如学院中的一些学者教授不敢正视1927年国民党执政后更为专制的社会现实,对在社会上争取合法的物质生活保障、生存权利和思想自由的左翼知识分子不仅不予理解,相反一概视为“十字街头”上的“党人”或“引车卖浆之徒”的哄闹,以“象牙之塔”维护者的身份加以鄙薄甚至攻击,在这方面,新月派的理论家梁实秋的表现更为典型。他在有关“翻译”、“言论自由”以及文学是否有“阶级性”等问题的批评文章中,夹杂着“拥护苏联”或“到××党去领卢布”一类言词,无论如何也不能视为他自炫的“为艺术而艺术”,他的“新人文主义”主张在这时候更暴露出国家主义本质,称之为“贾府”中的“焦大”⑥、“‘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⑦ 是毫不过分的。1926年北伐革命过程中的革命文化所操“十字街头”与“象牙之塔”根本对立的话语形式,主要针对的也是立足于“五四”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文化,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突变”的革命文学倡导者几乎相一致地以立足于“十字街头”自居,而把致力于社会文化变革的新文学作家斥为“蜗居”于“象牙塔”中的“感伤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唯美主义”者而加以讨伐,究其实质,仍然是“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的表现⑧。在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对“‘象牙之塔’与‘十字街头’截然对立”的话语形式给予最有力、最坚决的拒绝和批评的是鲁迅,但鲁迅言辞激烈的拒绝和批评,既是从坚持和发展现代社会文化出发的,同时更是通过对这种话语形式的剥离来认识和推动中国现代文化在20世纪30年代的整体发展。我们看到,他在30年代的全部思考、言论和所做出的全部工作仍然是把中国现代文化发生的分裂视为一种“内部裂变”,视为“历史形式”的变化而不是“根本内容”的变化,更是从中国现代文化“内部裂变”独立出来的社会文化、学院文化、革命文化发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出发的,要求中国文化不致因为“内部裂变”失去整体上的统一,而始终致力于推动分裂后的学院文化、革命文化与他立足的社会文化在“相对统一”而非“绝对对立”基础上的发展——这是“五四”后新文化向不同领域分流发展过程中鲁迅与其他新文化倡导者的最为明显的差异。
显而易见,中国现当代学术缺乏对鲁迅关于中国现代文化整体发展的独立思考和追求的深入认识,更多地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化“内部裂变”分化出来的话语形式,学院文化、革命文化、社会文化在中国现当代学术中截然对立而难以统一的现象十分突出。我认为,这主要根源于中国现当代学院文化的学术观念上的缺陷,可以追溯到留学美国的胡适开创的现代学院文化传统,如王富仁所分析:“当时的美国,政治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早已完成,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也已成历史,在和平发展过程中美国迅速成长为一个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学院文化在相对自由民主的气氛中与当时的国家政治权力有着更加和谐和协调的关系,较之当时欧洲大陆的文化,具有更明显的国家主义性质。像欧洲18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潮、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和其他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尼采的超人学说、列夫·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等等,在美国学院文化中并不具有主流的地位。胡适就是在这样一个学院文化的氛围中接受教育、形成自己的社会观念和文化观念的。”⑨ 中国现代学院文化主要为留学英美归来的知识分子所坚持和发展,其国家主义性质加强起来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倾向,带来的是他们对中国社会性质、思想文化传统和历史境遇与英美的根本差异的愈益隔膜,这不能不导致现代学院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根基的游离。在20世纪的中国,学院文化始终难以建立起与现代革命文化、现代社会文化之间可以相统一的基础,这更是通过学院文化在外观形式上与革命文化的分裂和对立表现出来的,如“问题”与“主义”之争,如颇具影响也更为典型的“‘象牙之塔’与‘十字街头’截然对立”的话语形式,究其实质,就是学院文化和革命文化与现代社会文化分裂后相互对立的表现形式,反映出现代学院文化与现代革命文化相一致在“建构基础”上与现代社会文化的根本不同⑩,这种情况在1949年后发生的相反变化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现代革命文化上升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后,胡适思想虽然被批判,但胡适开创的现代学院文化传统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研究活动中仍然有所发展,而中国左翼文化和左翼文学则不再具有社会文化性质,鲁迅更被简单化为一个立足于革命文化发展起来的纯粹“战士”形象。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既体现了现代社会文化与现代革命文化的深刻联系,又反映出二者在“建构基础”上的根本差异。左翼文化是在二者的联系和差异中发生和发展的,是通过二者的根本差异体现了左翼文化作为现代社会文化的独立性质和独立特征的。但是,“文化大革命”后在我们重新恢复和建立起来的当代学院文化的学术研究活动中,由于我们对学院文化传统与中国现当代文化不相适应的特征缺乏必要的审视,对现代学院文化、现代革命文化与现代社会文化之间在“建构基础”上的根本不同缺乏必要的认识,在我们对革命文化所批判和否定的研究对象给予更合理的阐释过程中,不仅现代革命文化在中国现当代文化以及中国现当代学术中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未能得到切合实际的认识和总结,而且带来我们对与革命文化不无联系的现代社会文化不尽合理的认识,自觉或不自觉地遮蔽了左翼文化和左翼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化以及中国现当代学术中的独立价值和意义。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学术在外观形式上依附于中国现代文化分裂的历史形式,在我看来,其更深刻的根源,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化以及中国现当代学术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严重不足。无论从人类的整个历史看,还是就任何一个民族个体的历史进程而言,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古老中国”的现当代历史都不能不说具有某种特殊性,即,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是在中西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产生,并在西方思想文化的直接影响下发展的,甚至可以说,离开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就没有中国现当代文化以及中国现当代学术发生和发展的可能,这几乎别无选择地带来中国现当代文化以及中国现当代学术(从个体到整体)建设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不足,难以在短暂的历史中建立起我们认识中的西方或者中国古代那样一种具有自身完整性和独立性的思想文化体系以及学术思想体系,这势必带来20世纪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超负荷地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话语形式的压抑、扭曲以至异化,带来中国知识分子“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的极度艰难,这在学院派知识分子身上有更为突出的表现,即像前述学衡派、新儒家学派特别是英美派知识分子那样,思想文化观和学术观念与实际社会历史境遇感受的脱节、游离、断裂以至对立,表现出“‘身首分离’的窘状”。这种状况更主要表现在上世纪末我们恢复和重新建立起来的学院文化的学术研究活动中,表现在王富仁的《“新国学”论纲》分析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陆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的“‘现代热’—‘西学热’—‘国学热’三部曲”中,这样一种自主性和独立性不足的学术文化,既难以通过“文化转换”来认识和汲取西方文化,也难以立足于“文化变革”来认识和肯定中国古代文化。面对90年代突然而至的“全球化语境”,在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回应中势必加强的是西方话语霸权倾向,更是借助西方话语形式来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化以及中国现当代学术,在对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回应中势必复活的是中国文化本有的复古和保守倾向,更是从这种复古和保守倾向出发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化以及中国现当代学术,由此建立起来的价值评判形式已经难以区分中国现当代文化与西方文化或者中国古代文化有什么根本区别了。或者把中国现当代文化看成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的表现形式,或者把中国现当代文化看成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顺其自然的发展过程,这就抹杀了中国现代文化得以发生的根基,丧失了中国现当代文化在中西文化整体比较中建立起来的主体创造精神。由此而带来的是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愈益严重的隔膜乃至对立情绪,带来我们对“五四”新文化以及新文化分化出的“历史形式”不断反思和批评中的“忏悔心理”和“原罪感”。似乎“五四”对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开创是一个不该出现的历史失误,我们的学术研究似乎仅仅是为了对此澄清根由和承担责任,替“五四”赎“罪”——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为典型的一种“‘身首分离’窘状”,我们的学术研究运用的是“五四”发展起来的语言形式,贯穿的是“五四”使我们得以面向西方建立起来的思维形式,而我们置身的仍然是只有通过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发展才能改变的中国社会现实,我们不满于近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化未能像我们认识中的西方文化或者中国古代文化那样发展起来,而更是把在我们这些“后代子孙”身上出现的历史失误归源于曾经哺育过我们的“母亲”,在学术研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倡导者视为一个“罪人”来思考和认识。由此而带来的结果,不能不是王富仁在《“新国学”论纲》中提出的“中国知识分子归宿感的危机和由此而来的自我意识形式的混乱”。在我看来,这是由于“自我意识形式的混乱”而导致的“归宿感的危机”,即我们不能不因此而对我们自身的、一个民族的以及人类的学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究竟是什么产生疑惑,不能不对我们通过这样的学术研究是否能够激发我们的精神资源和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产生怀疑。
假若我们看到这一点,可以认识到王富仁立足于当代学院文化建设提出的“新国学”的价值和意义。
如前所述,时至今日我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发展,更是通过学院文化中的中国现当代学术建设实现的,我们对中国现当文化不断进行的阐释也是从发展中国现当代学术出发的。王富仁的《“新国学”论纲》从对鲁迅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出发,对历时百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化以及中国现当代学术的整体发展进行的重新缕析和阐释,就是为了改变时下我们学术观念上的整体感的缺失。在他看来,在中西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化正是通过内部不断分化和裂变,形成当代更为完整的学术研究格局,“就其内容,不论这种裂变采取了多么激烈的形式,但仍然是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学术内部的裂变,裂变的结果构成的仍然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的整体。这正像宇宙的大爆炸,爆炸的结果是宇宙存在形式的变化,而不是宇宙本身的毁灭”(11),这就是说,无论是胡适开创的现代学院文化,即一个世纪以来学院中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和对外国文化翻译、介绍和研究创造出来的大量学术成果,还是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陈独秀、李大钊开其端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化,还有新儒家学派、学衡派学者实际从事的学术研究,还包括一个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等等,构成了“五四”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化以及中国现当代学术的整体,这个整体是当下的“国学”这个学术概念所无法涵盖的。正是这个概念有意或无意地将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化以及中国现当代学术排斥在“国学”之外,有意或无意地抹杀了近百年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是在“五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事实,使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的内涵和意义封闭和凝固了。可见提出与旧有“国学”观念不同的“新国学”框架的必要,即,在“新国学”框架中,我们可以真正感受和认识到中国现当代文化以及中国现当代学术发生和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这同时也为学院文化建立起了一个与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在整体上相适应的更大学术研究空间。
在我看来,王富仁的“新国学”建构对于当代学院文化建设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中国现当代学术所能够实现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化在学术意义上的总结和超越,体现了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学术反过来对于实际所发生的文化的主体能动作用。对此的认识,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人类的、一个民族的以及具体到每一位学者的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究竟是什么?不论我们怎样认识人类的、一个民族的以及具体到每一位学者的学术,如王富仁在《“新国学”论纲》中所述,它都具有“穿透社会常识的覆盖层”和超越与“现实实践”的关系这些基本特点,它都是为了最终实现我们更加理性地认识和把握世界,使我们的认识不断推进到人类的以及一个民族的学术整体发展的“境界”中,体现的是人类的以及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真正发展。“新国学”立足于“五四”,是通过王富仁概括的“五四”以“立人”为宗旨的“个人—社会”的思想文化框架和学术框架建立起来的,这既是在中西文化整体比较中对人类文化思考和认识的结果,又有着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切体验和认识,而使我们更为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发生的根基,同时也为我们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化以及中国现当代学术的发生和发展建立起一个超越性的价值标准。正是这个标准使直接继承孙中山革命文化传统的陈独秀、李大钊,原本带有美国学院文化倾向的胡适和更注重通过国民性改造实现社会文化整体发展的鲁迅、周作人,能够紧紧地“结构”在新文化倡导运动中,从而建立起一个适应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整体发展要求的认识和阐释框架。在这个“和而不同”的“结构”中整体永远大于个体,同时也不可能取代个体,是通过个体带动整体发展的,新文化向现代社会文化、现代学院文化、现代革命文化的独立发展更具有了合理性和必然性。如果我们从这种认识和阐释框架出发,在整体上思考和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化以及中国现当代学术的发展,就可以看到,“五四”后新文化向社会文化、革命文化和学院文化的分流发展,即使它们彼此之间在历史形式上的矛盾和差异不断拉大,甚至以截然对立的方式不断发生裂变和分裂,仍然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化的“结构性”表现,我们仍然可以在它们分裂后的“历史形式”中感受到它们彼此之间共享的价值和意义,仍然可以通过根源于“五四”的超越性价值标准把它们统一起来。《“新国学”论纲》之于当代学院文化建设的意义,更主要表现在这种认识和阐释框架所体现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方式上,如王富仁在文章中对近百年以来的现代学院文化、现代革命文化、现代社会文化以及其他类型的文化各自的独到贡献、各自具有的独立价值和意义所进行的系统分析,在我看来,这是对“五四”新文化倡导者的整体概括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方式(12) 衰退后的“复活”和“发展”。与王富仁认识中的陈独秀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方式具有的革命性意义一样,在这种思维方式和论述方式中的“新国学”建构,使我们固有认识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化以及中国现当代学术发生了整体上的重构,这不仅与“五四”建立起来的超越性价值标准更具有内在联系,而且更是通过中国学术这样一种建构实现了中国文化的真正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新国学”是立足于“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中国学术”历经一个多世纪发展的认识基础上的整体建构,是在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感应和认识中提出的。时至今日的中华民族没有理由不去建立凝聚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文化观念的精神家园,在“全球化语境”中这一共同的精神家园的建立显得更为迫切也更为重要——如我们所看到,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的独立思想文化体系的建构,正是“五四”涌现的一代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鲁迅从他所致力的现代社会文化发展出发力求实现这个目标,毛泽东更是从他所承续的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开拓的现代革命文化建设出发推动这个目标的实现。《“新国学”论纲》则是在对胡适开创的现代学院文化传统的必要审视和认识基础上,通过对近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化以及中国现当代学术的整体建构,体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贵努力。
注释:
①②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四》,《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345页,第345页。
③⑨⑩(11)(12)王富仁:《“新国学”论纲》,载《新国学研究》第1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以下一段分析参见陈方竞《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中的左翼理论资源》(载《新国学研究》第5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的六、七、八部分,引文和对引文的理解亦可见此。
⑤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66页。
⑥鲁迅:《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鲁迅全集》第5卷,第115页。
⑦鲁迅:《二心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全集》第4卷,第247页。
⑧鲁迅:《三闲集·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4卷,第84页。
标签: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国学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读书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新青年论文; 鲁迅论文; 学术研究论文; 现代社会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