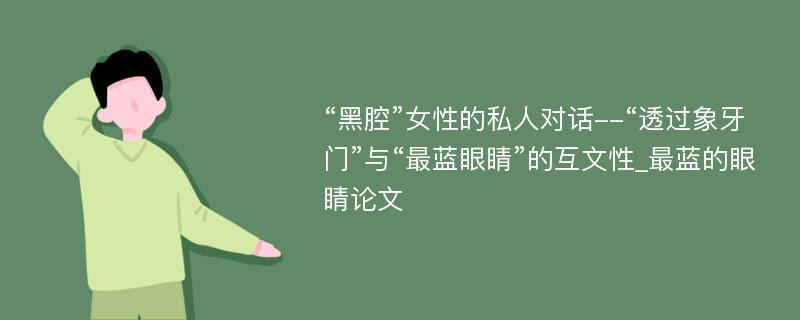
一场“黑人内部”的女人私房话——《穿越象牙门》与《最蓝的眼睛》的互文阅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私房话论文,象牙论文,黑人论文,眼睛论文,女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2-2643(2013)03-0087-07
1.0 引言
1993年对于美国非裔文学,尤其是非裔女性文学而言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岁月。这一年美国非裔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 )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比她年轻21岁的美国非裔女诗人丽塔·达夫(Rita Dove,1952- )成为美国的桂冠诗人。前者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后者是第一位摘得桂冠的黑人女诗人。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机缘巧合吧,两位年龄相差悬殊的黑人女作家颇有渊源。二人均出生于俄亥俄州,因此她们不但“分享相似的生平历史”(Walters,2007:171),而且共同拥有了美国中西部地区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并转化成为各自作品中特色独具的背景和氛围。当然,两位女作家施展才华的领域不同:莫里森的才华主要体现在小说创作中,而达夫的领域主要在诗歌创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美国的桂冠诗人却写出了一部被认为具有“鲜明托尼·莫里森风格”的小说——《穿越象牙门》(Through the Ivory Gate,1992)。(Greasley,2001:152)或者更确切地说,《穿越象牙门》是一部与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1970)形成了鲜明互文性的后文本。对于两位女作家和两部作品之间的渊源,达夫本人的表述自然是最具权威性的。在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穿越象牙门》的“序幕”中关于洋娃娃的情节是否是呼应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时,达夫坦言莫里森以及《最蓝的眼睛》对她的影响巨大:
我真的读过《最蓝的眼睛》,而那本书之所以深深打动我有几个原因。当我读大学时,我在图书馆的一堆书里面偶然发现了它。我不知道作者是谁,我甚至不知道作者是黑人。我只是看了看书名,拿起了书,就读了起来。我想,啊,上帝啊,她讲的是我的生活。这是我第一次读到讲述中西部黑人生活的书。当时我感到很孤立,因为我遇到了很多情形,人们要么认为我来自哈莱姆,要么认为我来自南方。你想知道,我要不要自找麻烦去解释,或者我能就从我自己开始,写下这段历史?这个人就正在做这件事。因此我突然感觉不是孤立无援的。(Pereira,2003a:160-161)
可见,《最蓝的眼睛》对达夫的影响不仅是对她个人的成长,也关涉到她的文学创作。这就不奇怪《穿越象牙门》在风格、情节、人物等诸多方面与《最蓝的眼睛》形成了巧妙的互文关系。
鉴于国内读者和研究者对达夫的这部小说尚不熟悉,在此有必要首先交代一下该小说的主要情节。《穿越象牙门》的情节并不复杂。小说以第三人称叙事,讲述了女主人公弗吉尼亚·金的成长历程。这位出生于俄亥俄州的黑人女孩热爱音乐,从小学习大提琴,并从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了戏剧表演学位。然而,毕业后她却发现很难找到适合黑人女性饰演的角色。为了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她做过颇多尝试。后来她加入了名为“木偶和人民”的木偶表演剧团。不过好景不长,由于经营困难,剧团解散了。她作为住校艺术家返回自己的故乡,在阿克伦(Akron)的小学教孩子们表演木偶,并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木偶夫人”。重回故乡,触景生情,记忆的闸门悄然开启。在弗吉尼亚的记忆闪回中,我们看到了她大学时代的恋人克雷顿,一位才华横溢的大提琴手,却是一名同性恋者;她的父母艾米和贝利为了挽救婚姻,突然决定举家迁居凤凰城,致使年幼的弗吉尼亚从此远离故乡;多年后,她才得知举家突然迁居的原因是父亲与姑妈之间的乱伦关系。与弗吉尼亚的回忆交织在一起的是她在困顿中不断成长和成熟的当下生活:弗吉尼亚与学生和学生家长之间围绕着制作木偶和木偶表演等发生的有趣故事,以及她与一位单身学生家长之间的恋情。最终,弗吉尼亚决定到百老汇追寻自己的表演梦。
同样是关于黑人女性的成长,同样以美国中西部地区黑人生活为背景,同样的当下和过去闪回交织的叙述声音,同样诗一般的语言,《穿越象牙门》仿佛处处回响着莫里森的声音,闪动着莫里森的身影。然而,细读小说文本,我们却发现《穿越象牙门》在至关重要的“身份情节”(Identity Plot)②上偏离并修正了《最蓝的眼睛》。那么,《穿越象牙门》以何种方式偏离了《最蓝的眼睛》,个中的原因何在呢?笔者带着这些问题,走进了两个文本之中,并在互文阅读的基础上尝试寻找答案。
2.0 洋娃娃桥段
在《穿越象牙门》的十六章主体部分之前,有一个长达10页的“序幕”,而该部分的内容颇耐人寻味。在女主人公弗吉尼亚9岁生日时,她得到了两只娃娃作为生日礼物:一只是外婆送的黑人娃娃,另一只是凯瑞姑妈送的白人娃娃。白人娃娃制作精巧:长长的红色头发,还配有粉色的小发卡和一把小梳子。相比之下,黑人娃娃有粗制滥造之嫌:她的眼睛不能闭上,更要命的是,她居然没有头发,只是在头部画上了几缕黑线,充作头发,而且整只娃娃看起来粗笨得像一只“被翻过来的螃蟹”。(Dove,1992:7)③更让弗吉尼亚反感的是,外婆和母亲异口同声地说,这只黑人娃娃长得很像她。弗吉尼亚的反应令母亲和其他人始料不及:她把黑人娃娃扔出了窗外。
对于弗吉尼亚扔黑人娃娃的举动,母亲的解读颇具代表性:她“耻于”做黑人。(P7)更让母亲不能忍受的是她“显然更加喜爱肥嘟嘟的红头发而不是她自己的肤色的[娃娃]”。(P7)那么,到底如何来理解这个“洋娃娃桥段”呢?达夫曾经谈到,这是一个自传性情节,这一举动不但令他人费解,连达夫本人都曾经困惑不已。多年之后,达夫对此进行了反思:“洋娃娃的故事是一座桥”,“因为在小说中这是一个自传性的时刻……这是在我的生命中,我一直感觉惭愧的时刻,为我把洋娃娃扔出窗外而感到惭愧。我为什么要那样做?这不是为我为什么把一个娃娃扔出窗外找理由,而是找到这向我们表明社会在一个小孩子身上施加了什么期望和判断。对我而言,[这是]一个自白。它是对托尼·莫里森的回答,但是它更像一声‘阿门’,如同说,‘我知道人们来自哪里;这对我们很多人都发生过’。”(Pereira,2003a:161)
达夫这里提到的对托尼·莫里森的回答,指的就是《最蓝的眼睛》中关于洋娃娃的情节。在《最蓝的眼睛》中,洋娃娃也是中心意象之一,而围绕着洋娃娃发生的故事也是该书最重要的情节之一。尽管在小说中只有讲述人克劳迪娅有过真正的洋娃娃,但是女主人公皮克拉却一直生活在白人洋娃娃那金发碧眼的梦魇之中。皮克拉与克劳迪娅对待金发碧眼的洋娃娃形象态度迥异:皮克拉不但疯狂地接受了金发碧眼的白人洋娃娃形象,而且做梦都想自己也能拥有这样的形象。可以说金发碧眼成为皮克拉“摆脱生存困境,向往幸福人生的理想象征,成为她灰暗生命中的最后一丝曙光”。(王晋平,2000:104)克劳迪娅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每逢圣诞节,克劳迪娅都会收到一只金发碧眼的洋娃娃作为礼物。克劳迪娅对这个礼物并不领情,因为这并非她希望得到的礼物:
洋娃娃按理说是应该带给我巨大快乐的,但是结果却恰恰相反。我把洋娃娃带上床时,它硬邦邦的四肢顶着我的皮肤,让我很不舒服——长在肉乎乎的小手上的锥形的指尖怪抓人的。……我只有一个愿望:把它拆开。……我没有办法爱它。(Morrison,1970:20)
克劳迪娅抱着价格不菲的洋娃娃,没有丝毫的快乐感,相反心里激荡着一种要“肢解”它的欲望,她要看一看到底是什么秘密使得人们认为她比黑人美丽。显然,皮克拉和克劳迪娅对待白人洋娃娃的不同态度是有着深刻的文化象征意义的。具言之,她们的不同态度代表了黑人女性对白人主流文化审美观的不同认识:皮克拉代表了种族主义的内在化,一种“白化的黑人自我”(王守仁、吴新云,2004:35);而克劳迪娅则代表着对白人文化的“抗拒态度”。(同上:45)评论界一致认为皮克拉和克劳迪娅一个毁灭,一个成长的不同命运即源于她们对白人主流文化的不同态度。而这也正是莫里森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1994年再版的《最蓝的眼睛》的“跋”中,莫里森提到她写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是“与毁灭性的观念的内化作斗争”,从而打击种族自卑神经的痛处,其目的是向人们展示在这个人人都不同程度受害的世界上如何完整地生存。(Morrison,1994:210-211)
然而,在种族主义泛滥的社会氛围中,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真的能够完整地生存吗?《最蓝的眼睛》中的克劳迪娅是否真的实现了完整生存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就人物成长的层面而言,克劳迪娅实现的只是肉体的成长。个中的原因还要从克劳迪娅对白人洋娃娃抗拒心理的本质来分析。尽管克劳迪娅与皮克拉对白人娃娃的态度表面上看起来有着天壤之别,然而本质上却是相同的。无论是皮克拉对金发碧眼的痴迷和渴望,还是克劳迪娅对白人洋娃娃的厌恶和憎恨,本质上反映的都是黑人女性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她们对白人洋娃娃形象的不同反应事实上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心理机制,那就是自我认同的“他者”。正如著名评论家海伦·文德勒所言:“对黑人性无法逃避的社会指控,让尚未成年的孩子无从抵抗,成为内在自我定义的一种强大因素。”(Vendler,1995:61)皮克拉之所以疯狂地接受白人洋娃娃的形象,是出于彻底的“自我否定”;而克劳迪娅拒绝白人洋娃娃,是害怕会因此“自我否定”。皮克拉以疯狂的方式接受了白人洋娃娃形象,“肢解”了“自己”;而克劳迪娅以疯狂地方式抗拒着白人洋娃娃,“肢解”了“对方”。无论哪一种情况,她们的异常举动反映的都是黑人儿童的心理被畸形审美观所扭曲的现实,以及由此产生的致命的暴力冲动心理。童年的克劳迪娅抗拒白人审美标准,却并没有因此树立起可以替代的黑人审美价值体系。从小说中成年后的克劳迪娅的叙事声音可以依稀看到一个日渐成熟,却也与主流话语体系越发靠近的黑人女性的身影。这说明克劳迪娅为了实现完整的成长不得不与主流价值标准达成某种妥协。这是黑白对立的种族主义社会中黑人女性成长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达夫的确是参透了《最蓝的眼睛》中两位女主人公成长困境的读者。这也是《穿越象牙门》开篇就以白人娃娃和黑人娃娃直截了当地呈现出黑白对立模式的原因所在。然而,达夫所呈现的却是一种全然不同的黑与白之间的关系。前文提到,《穿越象牙门》中的女主人公弗吉尼亚面对白人娃娃和黑人娃娃的时候,选择了前者,扔掉了后者。这一选择从表面上看与《最蓝的眼睛》中的皮克拉相同,而与克劳迪娅相左。然而,无论是相同还是相左,弗吉尼亚的选择都由于时代的变化和黑人心理机制的变化而与皮克拉和克劳迪娅均迥然不同。达夫与莫里森在洋娃娃桥段上的不同策略,也是很多学者感兴趣的话题。马琳·派瑞拉与达夫的访谈中就问到了这个问题:在莫里森的小说中,洋娃娃表征的是对于黑人女孩的成长具有极大破坏性的白人审美标准,那么你的小说中的洋娃娃又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呢?对此,达夫的回答是:
是的,我同意她[的观点]。在那样的层面上,我与她观点一致。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在我的小说中的两个娃娃,白人娃娃有真正的头发,你可以梳理的,而黑人娃娃是画上的卷发,它是黑人娃娃大规模生产的最初尝试,模样不佳。它不漂亮,不是因为它是黑人,而是因为那个制造它的人认为黑人娃娃看起来就是那个样子。它看起来不像人的模样。当我回望过去,开始回忆那个场景并开始写作时,我意识到那就是当时困扰我的事情。很多年来我感到羞愧,因为我认为我拒绝了那个黑人娃娃。但是并非如此。只不过是因为它不是一只漂亮娃娃。他们造了一只丑陋的小娃娃,一无是处:我不能梳理它的头发。那才是真相!(Pereira,2003a:61)
这段话是达夫本人对自己当初拒绝黑人洋娃娃的原因思考多年的结论。可见,与其说弗吉尼亚拒绝的是种族,不如说拒绝的是“平庸”。(Steffen,2001:116)通过拒绝一个缺少美感的黑人娃娃,她走出了隐喻的殖民的自我,并拉开了自己与母亲为代表的前辈的距离,也同时拉开了以莫里森为代表的文学之母的距离。
两位非裔女作家迥异的洋娃娃写作策略反映了她们对黑人女性成长模式不同的诠释方式。在黑人民族文化熏陶下长大的莫里森认为种族身份的确立是非洲裔女性成长的核心问题。莫里森的此种观点在非裔女性成长小说创作中是颇具代表性的。传统非裔女性成长小说提供的女性成长模式的初始阶段,即人物的觉醒期,就是对其族裔身份的质疑和逃避。④无论是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还是玛雅·安吉罗的《我知道笼中的鸟儿为何歌唱》(I Know Why the Caged Birds Sings),抑或是吉恩·瑞斯的《黑暗之旅》(Voyage in the Dark)等经典非裔女性成长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莫不如是。从这一角度来看,达夫偏离和修正的不仅仅是莫里森,还有传统非裔女性成长模式和非裔女性成长小说的创作模式,而这才是“洋娃娃”桥段改写策略的真正意义所在。
3.0 乱伦情节
《穿越象牙门》偏离《最蓝的眼睛》的第二个“身份情节”是乱伦情节。之所以说乱伦情节是一种“身份情节”是因为乱伦禁忌是建立在人类对血缘身份的认知基础之上的。事实上,《俄狄浦斯王》等作品从本质上说探寻的就是身份问题。乱伦之于叙事文学创作似乎具有一种神奇的魅力,“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神话传说中几乎都有关于‘乱伦’的叙述”。(杨经建,2000:59)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黑人女作家的作品中,乱伦一直是一个重要母题,而且往往是基于“种族逻辑”(racial logic)(Michaels,2002:1),并以性暴力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一点在黑人艺术运动时期的女作家作品中更为突出,原因就在于黑人艺术运动和女性权力运动赋予了黑人女性作家更多发声的机会,同时也赋予了她们反抗男权暴力和追求自我解放的力量。艾丽斯·沃克的《紫色》(The Color Purple)、盖里·琼斯(Gayle Jones)的《爱娃的男人》(Eva’s Man,1976 )、安德洛·罗德的《赞米》(Zami,1982)以及前文提到的安吉罗的《我知道笼中的鸟儿为何歌唱》等都触及了这一主题。
《最蓝的眼睛》也是黑人艺术运动的历史氛围中催生的作品,因此也就不奇怪其乱伦母题也是基于“种族逻辑”的,因为父亲乔利对皮克拉的暴力强奸是乔利在种族暴力的重压之下混乱的情感转嫁给女儿的结果。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家族的乱伦强奸是黑人女性遭受到最惨痛的经历,来自黑人男性的性暴力承载着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暴力,黑人和女性的身份是她们遭受厄运的原因,使她们成为种族暴力下的另一个层次的受害者。”(蒋天平,2011:41)为了凸显黑人男性的性暴力是种族压迫的结果,莫里森在父亲乔利这个人物身上不惜浓墨重彩。例如,他在白人的手电光照射下,在白人的辱骂中被迫与自己心爱的女孩做爱等场景的描写,均揭示出他人性形成过程中种族暴力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最蓝的眼睛》中的乱伦情节从本质上说是种族压迫的一种变体。皮克拉就是这样变形的种族压迫的受害者。乱伦行为使得皮克拉的自我认知出现了障碍,并最终走向心智的迷失和疯狂。很多黑人女作家都认识到乱伦行为对黑人女性自我认知的致命伤害。在黑人女权主义诗人安德洛·罗德(Audre Lorde)的诗歌“链条”(Chain)中,被父亲强暴的黑人女孩面对父亲、母亲以及自己与父亲所生的孩子,自我认知出现了可怕的扭曲,血脉之链断裂了:“我是他的女儿还是女朋友/我是你的孩子还是情敌/你希望从他的床上被赶走?/这是你的外孙女妈妈/在我入睡前给我你的祝福。”(Lorde,1997:246)可见,比黑人女性的身体受到的伤害和侮辱更为严重的是乱伦带给她们的心智的刺激和迷失。正如塔玛拉·加发-阿格哈(Tamara Jaffar-Agha)所言,乱伦不一定意味着一种暴力的、物质的进入女性的身体,然而,“它一定包括一种对我们心智的暴力侵入——一种不可避免地改变我们并使得我们永无回头之路的进入”。(Jaffar-Agha,2002:145)
乱伦母题也出现在达夫的多部作品中,并且跨越了诗歌、诗剧、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多种文类。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集《第五个星期日》(The Fifth Sunday)中的短篇《凯瑞姑妈》(Aunt Carrie)中姐弟乱伦的故事几乎又被完整地搬到了长篇小说《穿越象牙门》之中。⑥这一现象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注意。例如,在与达夫的访谈中,马琳·帕瑞拉就围绕着这一话题进行了提问。当帕瑞拉如数家珍地罗列出达夫涉及乱伦主题的主要作品时,达夫颇有些意外,因为她本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作品中如此多地触及这一母题,以至于她说“我没有办法解释这一现象”(Pereira,2003a:163),而帕瑞拉也不得不用“它是无意识的”结束了这一话题。(Pereira,2003a:165)
然而帕瑞拉不会不知道,“无意识”在人的心理结构中,虽然“隐而不现”,却是起“决定作用的部分”。(陆扬,1998:16)因此,达夫作品反复触及到乱伦母题的现象不能用“无意识”,“没有办法解释”来敷衍了事。对于《穿越象牙门》中的乱伦情结更是不能如此粗暴地下结论,原因在于这部关于女主人公弗吉尼亚作为女人和作为艺术家成长的小说中插入一段她的父亲与姑妈乱伦的情节着实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事实上,很多评论家均对这段乱伦情节表示不解。例如,最早为该书撰写书评的盖比瑞拉·弗瑞曼(Gabrielle Foreman)在“木偶夫人小姐”(Miss Puppet Lady)一文中就表达了自己的困惑:“我不明白达夫为何似乎想让凯瑞姑妈的故事成为小说本身的关键事件”(Foreman,1993:12),因为弗瑞曼认为,这一姐弟乱伦事件只是对凯瑞姑妈本人的一生影响甚大,对弗吉尼亚却并未产生重要影响。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这部关于弗吉尼亚的成长小说中插入凯瑞姑妈和父亲之间乱伦情节的用意何在呢?在《最蓝的眼睛》中,乱伦是导致皮克拉的精神走向崩溃、自我身份认知出现混乱的诱因之一,那么,在《穿越象牙门》中,乱伦情结是否也具有身份认知的意义呢?
答案恐怕还要在两个文本的互文对照中寻找。细读文本,《穿越象牙门》中的乱伦情节在角色定位和表现方式上均与《最蓝的眼睛》有所偏离。这场姐弟之间的不伦关系的主导者是姐姐凯瑞。寡居在家的凯瑞被不谙世事,青春帅气的弟弟厄尼所吸引,主动发生了性关系。一年后,当她意识到这样做太“疯狂”了,主动停止了这段不伦之恋。角色的互换产生的意义是巨大的:
其一,在这段恋情中,凯瑞一直占据着主动的位置:从开始到结束,一切均在她的掌控之中,而弟弟厄尼却一直处于被动状态:“我想他从来没有把这个当回事。这令人愉快,一旦结束了,他也就忘了。”(P245)尽管凯瑞对于这种关系也十分“困惑”,但有一点她自己是十分肯定的,那就是不要伤害到弟弟。于是,在第一次发生关系之后,凯瑞给弟弟写了一张字条,告诉他“他现在是男子汉了”,“应该一直挺直腰杆”。(P246)从凯瑞姑妈的这段自白,我们对这场姐弟之间的不伦之恋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女性不但一直控制着这段关系的发展,而且对于男性的成长起着引领作用。这一点从弟弟处理这张字条的做法可以得到印证。厄尼看完字条,不但没有销毁,反而小心翼翼地收藏了起来,而收藏的地点竟然是母亲的照片相框的背面,并带着母亲的照片和这张字条结婚生子。厄尼的做法显然具有象征意义。对他而言,姐姐凯瑞充当的是如母亲一样的引领和教导的作用,是让他成为男人的力量。这段姐弟乱伦体现的男女关系的颠覆性变化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而这也是这段情节对于成长中的弗吉尼亚的意义所在。性在自我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身体始终保持着与其主体不可分离的关系”。(Ponty,2002:232)女权主义者清醒地认识到性禁忌是男权中心论的核心因素之一,因此女性解放首先就是摒除对女性的性压抑和性禁忌,在性关系上应更主动、积极、大胆。黑人女性更是如此。基于此,黑人女作家往往在创作中将性别意识的觉醒作为女性成长的关键环节,小说人物期望通过对性爱的主动把握来实现自我的成长。在《穿越象牙门》中,这段姐弟乱伦的情节被插入的时机十分耐人寻味。当时弗吉尼亚与一位单身的学生家长开始了一段若即若离的恋情,并发生了关系。然而这段恋情让弗吉尼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是留在家乡享受富足、平凡的家庭生活,还是继续追寻自己虽然渺茫,却美好的艺术之梦?面对来自异性火热的追求,弗吉尼亚一度被动地投入到了这段感情之中。恰在此时,弗吉尼亚拜访了姑母,之后,弗吉尼亚斩断了刚刚开始的恋情,决然追寻自己的艺术之梦。从这个角度来看,姑母在两性关系上的主动和决然正是帮助弗吉尼亚走出两性关系迷茫期的关键。
其二,乱伦固然是令家族羞耻的秘密,“但当凯瑞讲述给她的侄女时,它变成了一个故事,表面上看是姐弟之间的混乱和丧失,但是其比喻的意义是一首短小精致的家庭田园诗”。(Pereira,2003b:44)这一点从达夫书写这段往事的抒情笔触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段自白仿佛是一首抒情诗,充满青春的萌动和亲情的温馨。姐弟一同收带着阳光味道的雪白床单,清风拂动,床单轻舞,青春逼人的弟弟和柔美可人的姐姐,一切仿佛梦幻般美好。这与《最蓝的眼睛》中的性暴力乱伦有着本质的不同。尽管如此,姐姐却也深知这种行为的不齿,为了家庭的利益,她小心地收藏起自己的情感,毅然结束了这种不伦关系。因此对于弗吉尼亚而言,聆听来自姑妈心底的声音,了解这段家族历史并不是耻辱的时刻,而是一个人生“顿悟”的时刻,因此这段故事是“一个黑人家庭的故事”,是“世代传承的束缚和自由”。(Righelato,2001:68)可以说,从弗吉尼亚成长的视角来看达夫作品中长达30余页的乱伦情节具有解释“家庭渊源”的“叙事效果”。(Pereira,2003b:44)这对于正处于成长的迷茫期的弗吉尼亚而言是弥足珍贵的。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穿越象牙门》中乱伦情节脱离了黑白对立的“种族逻辑”,回归了人性本身。同时,这段被家族深埋的往事以一种传奇的方式,由长辈讲述给晚辈,承载了黑人家族和历史传承的深刻意义。
4.0 身份情节与身份建构
达夫在“身份情节”上对莫里森的偏离和修正耐人寻味。“身份情节”是小说建构人物身份的重要策略,因此达夫在身份情节上的偏离意味着身份建构和身份定位的偏离。那么达夫在“身份情节”上对莫里森的偏离和修正到底要定位何种黑人身份呢?通过前两节的论述,我们已经得到了初步答案。洋娃娃桥段的偏离和改写颠覆了黑与白二元对立的文化身份,而乱伦情节则颠覆了黑人男性和黑人女性之间的主从关系,从而隐含了黑人男性气质和黑人女性气质的对立建构。从表层含义来看,达夫在两个“身份情节”上对莫里森的偏离和修正是出于黑人女性族群身份和性别身份的建构理念和策略的不同,勾画的是黑人作家从“黑人民族主义”到“黑人世界主义”⑦的身份意识的嬗变。从深层含义来说,达夫对莫里森的偏离超越的正是“种族逻辑”。阿尔特·B.密歇尔斯(Walter Benn Michaels)在20世纪末呼吁现在到了超越“种族逻辑”的时候了(Michaels,2002:1-15),达夫则以《穿越象牙门》对《最蓝的眼睛》的互文写作告诉我们,非裔美国作家将如何实现这一超越。
这一超越从两部作品的标题意象:“蓝眼睛”和“象牙门”的象征意义的不同也可清晰洞见。此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意象实则具有某种内在相似性。莫里森以“蓝眼睛”意象的创设完成了对小说主人公人生悲剧的象征和寓意,其象征意义毋庸赘言。但有一点要强调的是,皮克拉之所以对“蓝眼睛”情有独钟,原因在于一个虚幻的命题:她认为如果她能够拥有一双白人女孩的蓝眼睛,她就能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她也将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与“蓝眼睛”几乎显而易见的象征意义不同,达夫的“象牙门”的典故源于西方经典。这也是评论家艾卡泰瑞尼·乔高达凯(Ekaterini Georgoudaki)指出,达夫是作为“一位宣称世界文明都是她的合法遗产的艺术家的权威”来述说的原因。(Georgoudaki,1991:433)在希腊神话中,梦通过两个门进入到梦乡中的人:一个是号角之门,一个是象牙之门。事实上,此两个门的名字是一种文字游戏:在希腊语中,“号角”的发音听起来像“实现”,而“象牙”的发音听起来像“欺骗”。此两种意象后来频繁出现在西方经典之中,其中就包括荷马史诗《奥德赛》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在《穿越象牙门》中,达夫是通过弗吉尼亚在木偶剧团的同事帕克(Parker)朗诵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诗句来点明主题的,幽灵般的梦有两个门:一个诚实号角之门,另一个是象牙门,它代表的是幻象。那么,象牙门所代表的幻象到底是什么呢?象牙的颜色自然使人联想到白人的肤色。这也是评论家马琳·帕瑞拉断言,“象牙”意味着“白人文化”和白人价值的原因。(Pereira,2003b:44)以上的论述表明,“象牙门”和“蓝眼睛”事实上承载了十分相似的文化表征,那就是白人文化和白人价值体系。更为重要的是,两位黑人女作家均鲜明地表明了自己对白人文化的观点,那就是它们都是“幻象”。
然而,在如何对待这一“幻象”的问题上,两位女作家分道扬镳了。从某种程度上说,皮克拉的毁灭和弗吉尼亚的成长的根源正是在于对待幻象的不同态度和不同选择。皮克拉屈服于白人的权力之下,使自己内化于白人优越的迷思之中。“在过去的二三百年中,白人为主的美国社会与文化,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殖民地的精英分子当中,美与价值都以‘白色’标准为依归;这种肤色所产生的‘白色饥渴’,也使得白色或浅色高高在上,而黑色与深色自然低低在下了。”(伊罗生,2008:85)在这种强大的主流认知体系中成长的皮克拉理所当然地认为,“肤色黑就意味着成为牺牲者,所以如果不想成为牺牲者,就不能成为黑人”。(Sumana,1998:57)在白人社会所形成的镜子里,皮克拉进入了象征秩序阶段,标志着她的身心的破坏。被父亲强暴,被母亲鄙视的巨大打击使得皮克拉在内心营造一个幻象,即拥有一双最蓝的眼睛。她相信这双眼睛能从根本上改变她的命运。她开始“存在于幻象之中,专注于幻象,无法摆脱幻象”,并进入了一种谵妄状态,最终走向疯癫。(Foucault,1967:89)
《穿越象牙门》中的弗吉尼亚则走了一条全然相反的路。她通过执著于钟爱的艺术而穿越了幻象之门。换言之,她超越了黑与白形成的种族对立的门槛。穿越了白人文化和价值之门的弗吉尼亚回归了人性的普遍追求,关注的是人性的升华和人生的完善。有研究者指出,达夫在多首诗歌中“证明对美的热爱和艺术想象是共同的人类品质,而并非白人上层阶级独享的特权”。(Georgoudaki,1991:429)在她的小说中,这一策略再次得到应用。马琳·帕瑞拉这样解释了小说的标题:《穿越象牙门》暗指弗吉尼亚的单程旅途,那没有回头路可走的旅途。这条人生之路不同于以往的黑人女性的道路,因为这是一次穿越传统上被认为白人独享的,接受大学教育,寻求美和艺术的中产阶级的人生之路。摆脱了“种族逻辑”的弗吉尼亚既走出了皮克拉对蓝眼睛的饥渴,也走出了《最蓝的眼睛》中的讲述人克劳迪娅对“黑即是美”的朦胧的追求,开始以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审视种族问题。
这一偏离表明《穿越象牙门》在美国非裔成长小说的领域内是革命性的,达夫具有逆时代精神创作的勇气。当大家都不厌其烦地书写“爱”,或者是非裔美国家庭“可怕的片段”的时候,《穿越象牙门》却唱响了一曲“通过教育”艺术地成长的颂歌。(Steffen,2001:121)达夫认为,21世纪的美国黑人并非没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更多地是基于阶级不平等,它们也同样出现在其他群体”。(Johnson,2010:116)跨越二元对立族裔文化身份对于美国非裔艺术家的创作具有的重要意义恐怕没有人比达夫认识得更为深刻。达夫指出,“在某一时段,为了获得任何形式的尊重强调‘他者’是必要的,然而坚持强调差异也要求一个人树立起某种墙或者遵守某种准则——所有这一切都是艺术家的诅咒”。(Steffen,1998:108)“达夫的普适性的美学反映了她对自我的非种族化,非性别化的独特定义。”(Walters,2007:134)尽管达夫通常被划归为黑人作家,她的作品也被认为是美国非裔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她却“毕生都致力于构建一个独立于种族和性别的个人和艺术身份”。(同上)《穿越象牙门》可以说是达夫建构个人和艺术身份的一次全面文本之旅,是她“修正主义的黑人美学”(revisionist Black aesthetic)的一次具象化实践:“在她的作品中,人们发现一种急迫,也许甚至是一种焦虑,以更具包容性的感受力去超越——如果不是真的摈除——黑人文化民族主义。”(Rampersad,1986:53)这种“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布鲁姆所言的“影响的焦虑”,只不过这一焦虑发生在黑人族群内部。从这一层面而言,达夫对莫里森的偏离和修正更像一场“黑人内部”的女人之间的私房话。
5.0 结语
尽管达夫不是“种族诗人”(Baker,1990:574),但是作为黑人作家,达夫并不回避种族歧视问题,即便是在《穿越象牙门》中,达夫也触及了“种族偏见主题”。(Walters,2007:119)然而,达夫的自我形塑的身份挑战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黑人艺术运动的“黑人本质主义”,因为“尽管达夫知道一种往往被认为赋予了黑人身份和文化核心的‘策略的本质主义’认同在确保非裔美国人在一个种族歧视的社会中生存下来功不可没,她还是清楚地认识到那种认知的局限性”。(Pereira,2003b:1)而这正是达夫与莫里森的本质不同。如果说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以黑人民族主义的立场跨越时空与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进行了一次种族之间的对话,那么达夫与莫里森的对话则是在“黑人内部”,并在去“族裔化”的基础上建构了黑人女性独特的文化身份。
注释:
①“黑人内部”是耶鲁大学教授伊丽莎白·亚历山大提出的颇具后现代特征和时代精神的种族身份建构的文化空间。详情参见拙文(王卓,2010)。
②耶鲁大学教授Amy Hungerford在《1945年之后的美国小说》的授课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身份情节”(Identity Plot)的概念。Amy Hungerford总结了身份情节小说的几大要素:1)身份情节小说的叙事围绕着如何定义并理解人物的身份问题;2)人物应当是一个更大的社会环境中的少数群体中的一员;3)该人物与他/她身处其中的少数族裔群体也格格不入,而且该人物为保持自己与主流社会和少数群体的差异而抗争;4)在人物寻求个人身份的过程中,即使真实性和出身看似缺场,也一直处于危机之中;5)身份情节有喜剧和悲剧版本等。Amy Hungerford在讲解“身份情节”时,就曾以《最蓝的眼睛》为例证。参见耶鲁大学外国教程的美国文学系列之《女勇士》课堂讲解。http://wenku.baidu.com/view/37689108763231126edb11a3.html.
③Rita Dove,Through the Ivory Gate(1992)。以下出自该小说的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译文由笔者自译。
④关于非裔女性成长小说提供的女性成长模式以及四个阶段的划分参阅Clifford J.Kurkowski(2004)拙著《美国女性成长小说研究》也有提及(2008:109-110)。
⑤在诗集《托马斯和比尤拉》,诗剧《农庄苍茫夜》,短篇小说《凯瑞姑妈》,长篇小说《穿越象牙门》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⑥《第五个星期日》中有两篇故事得以在《穿越象牙门》中再现、改写和扩展。除了《凯瑞姑妈》外,还有《二手男人》(Second-Hand Man)。
⑦达夫的“黑人世界主义”文化身份是评论家Malin Pereira对达夫诗歌研究的结论,是对以达夫为代表的当代美国非裔诗人文化身份的概括。参见Rita Dove’s Cosmopolitanism(Pereira,2003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