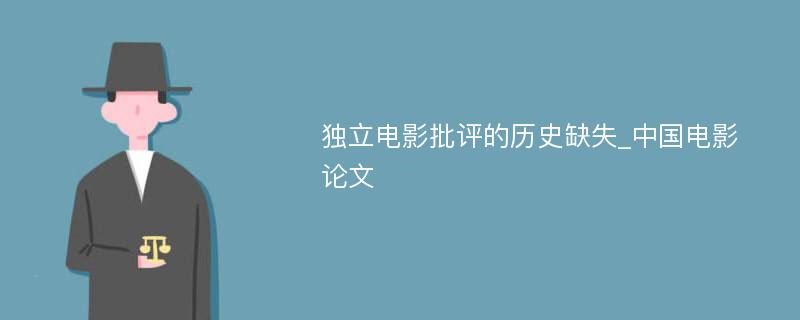
独立电影批评的历史缺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独立论文,历史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娱乐时代的中国电影批评,始终没有获得健康生长的机遇。跟文学、音乐或美术等其它的艺术形态相比,电影显示出更加鲜明的工具主义特性。长期以来,电影一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和规训工具,这是电影本体的异化,不仅如此,它还影响了电影批评的自我发育。而在一个全民娱乐的狂欢年代,包括报刊、电视和互联网在内的各种媒体,每天都在发布大量关于电影的喧嚣,但我们仍然听不见独立电影批评的声音。这种独立属性的缺席,就是专业电影批评所面对的最大困境。
不妨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婴儿期电影的分裂景象。在卢米埃尔兄弟和爱迪生那里,视觉媒介技术因技术分野而形成两种消费模式:以“西洋镜”为轴心的独观式街头消费和以放映机为轴心的共享式游乐场消费。基于游乐场比街头具有更大的商业利润空间,电影最终被统一到集体观看的旗帜之下。资本主义大众由此获得了最廉价的视觉美食。
但出人意料的是,这项资本主义的伟大发明,却在西方世界遭到知识分子的蔑视,在其出生后的漫长岁月里,它只是下层民众的娱乐项目,活跃于那些廉价的游乐场,成为庸俗趣味的象征。只有法国和苏维埃俄国改变了它的低贱命运。大批先锋艺术家参与电影制作的狂潮,迫使它提前完成蝶化,获得崇高的“艺术”地位。除了法国,似乎只有原苏联实现了这种美学飞跃。
但这种改变不能证明电影实现了自我独立,恰恰相反,电影在原苏联受到礼遇的唯一原因,就在于它被选定为政治宣传的首席工具。
电影的视觉叙事特点,令其拥有革命所需要的煽动模式。在20世纪初叶,没有任何技术媒介比电影更具感染力。越过夸张的活动图像、煽情的音乐和字幕,领袖的意图有效地渗入了民众的心灵。电影观看方式和左翼政治集会之间,存在着某种惊人的相似性。观看电影是被动而温顺的接受,显示出对规训者(演讲者或影片)的无条件服从。另一方面,电影一旦和广场集会结合,就成了传播革命思想的最美妙的方式。人民被集体送进叶卡捷琳娜风格的会场以及各种露天广场,从那里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学习和模仿红色暴力,而影片所提供的专政模式,就此像火焰一样在全国蔓延。
从媒介技术的角度看,电影拷贝比戏剧演出更为方便,不会因不同剧团的演绎而令主旋律变调失真。所有的拷贝都是一模一样的。它们只需要审查一次,就可以被大规模复制,在各地广泛发行和放映,并有效地掌控宣传和规训的节奏。
基于这样的理由,列宁在1919年签署法令,将照相、电影生产及其发行,全部移归人民教育委员会管辖,此举标志着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苏联电影的隆重问世。列宁公开宣称:“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正是在列宁的直接授意下,苏联人拍摄了大批“宣传鼓动片”,如《镰刀与斧头》、《红小鬼》、《死光》和《马克辛》三部曲等。1924年,俄共(布)十三大作出关于电影的决议,宣布加强对电影的领导,并取缔私营发行公司,成立“革命电影协会”和由契卡首领捷尔任斯基领导的“苏联电影之友”协会。
这是一个电影大跃进的辉煌时代。1925年,苏联已拥有3000多家电影院,1928年增至9800家,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其电影院(包括流动影院)的总数竟达2.92万。与此同时,仅在1924—1925年短短两年里,前苏联便制作了142部影片。其中除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和普多夫金的《母亲》之外,其余大多是政治宣传的粗劣之作。但电影作为工具的功能,则已经被坚硬地确立起来。此后,杜甫仁科、普洛塔占诺夫、柯静采夫、艾尔姆列尔和维尔托夫等导演大批涌现,他们是工具主义美学的代表,为电影工作者提供了大量范本。爱森斯坦甚至发明了一种可用以直接陈述红色思想的“电影语言”。他指望让电影像文学一样说话,使用各种象征、隐喻和对比的修辞技巧,以实现对民众的政治规训。①
电影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俨然是苏联历史的一个精确镜像。毛泽东对电影的高度重视,可以通过下列细节窥见。著名电影摄影师徐肖冰回忆道,1949年10月拍摄开国大典时,他从人群中选择了一个高个子的肩膀来放置沉重的手提摄影机,而高个子欣然出借了自己的肩头。事后,摄影师本人惶恐地发现,这个高大的肩膀,属于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用自己的肩膀,充当了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宣传的底座。[1]
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意味深长的借喻。毛泽东不仅娶了一名电影演员为妻,还准许她担任文化部电影局顾问,同时以“委员”身份主持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的工作,而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电影大批判之后,江青在1960年代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电影革命。所有这些历史细节,都在书写中国电影的坎坷命运。
这种热切的政治关注本身,大力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设定了中国电影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属性。这种工具化电影的历史,还可以上溯到联华等影业公司的抗战影片,而后,经过新中国的资源整合,成为电影发展的主流,并在文革期间达到巅峰状态。那是电影作为工具的“火红的年代”,谢晋导演的《春苗》,就是这种工具主义电影的最高样板,它不仅完成了激烈的斗争叙事,还展示出导演本人的政治忠诚。
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举办的“中国电影百年”庆典,其实是一场电影工具史的热烈回顾和自我颂扬。那些获得表彰的影片与人物,毫无例外都是20世纪下半叶的产物。当那些获奖者们兴高采烈的时刻,电影却依旧戴着沉重的镣铐。
娱乐资本主义时代的降临,是否会引发这种陈旧的历史场景的倒塌呢?在剧烈的商业化转轨进程中,大陆电影业引进大批港台乃至好莱坞的演员和技术人员,表演及其制作技巧都有重大提升,但在这日益精致的假面舞会背后,电影的工具主义特性,并未得到有效的改善。
我们已经看到,在喧闹的票房门外,云集着大批非理性的观众,他们一方面狂热消费着“情色文化”,一方面执意扮演政治伦理民兵的角色。2008年1月,鉴于《色·戒》的公映,大约有3千万个帖子在互联网上涌现,其中大多数在痛斥李安是卖国贼、汉奸和台独分子。把一部文艺片直接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然后以匿名群众的名义加以围剿,这种情形向我们展示了中国民众解读电影的基本逻辑——电影首先是一种政治工具,而评判电影的标准,并非是它的艺术特点,也不是情欲在人性中所扮演的暧昧角色,更不是六克拉钻戒所营造的复杂心态,而仅仅是它的民族主义立场。
电影消费的这种政治伦理立场,加剧了中国电影的依附性人格。包括电影在内的任何媒介样式,都注定跟意识形态有着深刻的关系。电影就是一面破碎而明亮的镜子,映射着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总体文化状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一种健康的文化形态中,电影的这种意识形态表达应是完全独立的。电影必须摆脱作为工具的仆从地位,转而成为自由表达社会生活的独立媒体,惟其如此,电影才能更深刻准确地展开意识形态叙事及其政治反省。尽管基于审查者或投资者的利益,这种人本主义理想在现实语境中变得困难重重,但跟这些因素没有直接关联的电影批评,却可以绕开障碍,率先自立起来,为电影制作的未来独立开辟道路。
但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与上述逻辑推断正好相反。电影批评的工具主义状况,甚至比电影本身更为严重。长期以来,中国电影批评一直处于“工具的工具”的卑贱地位。它是那个“作为工具的电影”的工具,以一种谦卑的方式向这种媒体示好,或者反过来,成为严厉的意识形态棍子,对电影实施严酷无情的打击。电影批评的这种“谄悍两重性格”在文革中一度达到了高潮。它一方面奉命击打那些触犯原则的影片(如《创业》和《海霞》),一方面又奉命为那些符合原则的影片歌功颂德(如《春苗》和《艳阳天》)。作为官方电影的舵手,江青制订的美学原则,一度支配了批评的基本语法。
这种极端的工具化态势,曾在1986年有过终结的迹象,这就是关于谢晋电影模式的争鸣。在那场激烈的争论中,一些青年批评家企图对谢晋电影的工具主义理念进行反省,藉此打开独立电影批评的大门。尽管这场争鸣在理论上相当稚嫩,甚至以好莱坞模式作不适当的借喻,偏移了批评的主要方向,但它还是标志着独立影评的诞生。[2]耐人寻味的是,这场批评的发起者都来自文学界。正是这种圈外身份,使批评者避开行政迫害,为批评的独立性提供了戏剧性的保障。
但谢晋模式争鸣却制造了一场出乎意料的分裂:圈外批评家批评谢晋模式,而圈内批评家坚定地捍卫谢晋模式。这种激烈的价值对抗,最终以圈外批评的退出而告终。由于身为电影行政主管的夏衍先生的干预,这场活跃的争鸣遭到打压,以至电影批评未能完成独立进程,反而退回到原初状态,加剧了自身的奴性。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电影圈卷起了更加恶劣的“擦皮鞋”之风,各种甜蜜的赞语甚嚣尘上,把批评进一步推向颂歌式工具的深渊。
20世纪90年代晚期,随着资讯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中国电影发生了向市场的剧烈回归,也就是回归到电影诞生时期的那个状态,再度成为消费市场的娱乐工具,由此导致了中国娱乐大片的泛滥。电影一方面保持了意识形态工具的强大惯性,另一方面又成为投资商的盈利工具。以大片导演张艺谋为例,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导演,曾经提供过改变中国电影视觉语法的希望(《红高粱》),却最终踏上了高度媚俗的道路,也就是利用其视觉造型才能,演绎色情暴力和名人隐私,以迎合大众的庸俗趣味。电影尚未从一种工具牢笼中逃脱,又急切地演变为另一种资本集团的工具,由此构筑着双重工具化和“一仆二主”的尴尬格局。
基于电影生产的双重工具性,本来就毫无独立性可言的专业电影批评,必然要更深地陷入这种“一仆二主”的格局。它既要服从行政指令,又必须响应消费市场的召唤,效忠于娱乐资本的权力。中国电影批评的现状,大致就是如此。
有人在某次研讨会上曾经乐观地宣称,学院批评完全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但事实却是,学院批评要么成为一堆自我封闭和自说自话的废纸,要么就在介入电影制作的过程中丧失主体性,再度成为权力的工具。学院影评家担任电影节评委,原本是独立意志影响电影制作的良好契机,但当百花奖组委会玩弄程序游戏,把主旋律电影以“观众评委”的名义强加给公众时,[3]影评家究竟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而在评奖结果公布之后,又有多少学院影评家站出来,质疑那些显而易见的猫腻?只要批评(审查、判定、选择、评价)的权力是另一种更高权力的附庸,电影批评就永远无法获得独立的品格和尊严。
众所周知,上海影评学会的负责人,是由电影集团的官员兼任的,这种体制内部的联姻,注定了电影批评的附庸身份。而没有独立的批评,任何关于电影人及其作品的谈论,都将变得无限可疑。电影研究者也许无法回避跟电影圈的各种私人关系,但电影官员兼任电影评论协会的主席,只能暴露出体制本身的恶性病症。它制止了电影批评走向独立的全部可能性。只要打开该学会的网站就会发现,在那个庸俗的容器里,只有一堆自我吹捧的文字。
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缺乏主体的独立性,这意味着作为独立存在、思考和言说的主体,没有到达存在的现场。虽然文章是以某人的名字发表的,但实际上它的作者不是此人,而是其身后的那些强大的行政权力、标准和原则。毫无疑问,这不仅是电影评论界的问题,更是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困境。这使我们更加缅怀那些已故的独立知识分子,诸如顾准、陈寅恪和施蛰存等等。
这些屈指可数的文化英雄,主要来自学术界和文学界,而在民众中影响巨大的电影领域,却从未诞生过一个公认的独立知识分子。
杰出的电影批评家钟惦棐,仅仅因为婉言批评了当时的电影时弊,并对电影本体论(非工具论)有所指涉,就迅速沦为反右斗争的牺牲品,陷入几十年的苦难生涯。[4]独立电影批评在其萌发之际,便遭到无情的摧毁。但耐人寻味的是,20多年以后,电影圈出现了另一个独立的声音,它来自演员赵丹。在疾病缠身的晚年,他以卓越的勇气和痛切的反思,艰难地填补着电影圈的人格空白。
2005年以来,以张元等人为代表的“地下电影”导演相继成为国家主义阵营的中坚力量,从而令独立电影的前景变得更加黯淡。与此呼应的是,专业电影批评也在穿越历史上最艰难的瓶颈:它不仅受到了来自电影圈(官员、投资商和电影工作者)的强大压力,同时还要被迫面对互联网哄客的多头夹击。尽管“博客”为民间影评人提供了新的话语空间,但那些来自民众的混乱无知的噪音,遮蔽了他们的微弱声音,从而使那些关于电影的批判性阐释无法获得有效的传播。也正是基于这种严峻的现实,对批评之独立性的探究,才变得更为迫切。
这是因为,如果没有独立的电影批评,就不会有真正的独立电影的诞生。
注释:
①以上关于苏联电影史的叙述,均参见乔治·萨杜尔著,徐昭、胡承伟译《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