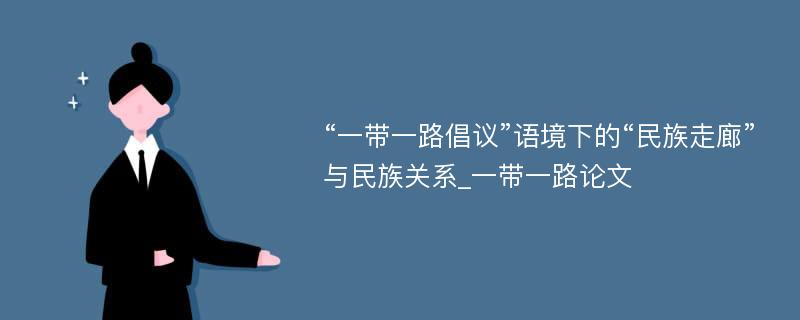
论“一带一路”语境中的“民族走廊”及民族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语境论文,走廊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6.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6959(2016)01-0005-05 DOI编号:10.139651j.cnki.gzmzyj10026959.2016.01.002 一、“一带一路”语境中的“民族走廊” (一)时空背景与主体过程:“一带一路”与“民族走廊”的关系 “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目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提出的,国际合作发展的理念、倡议以及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1]目前来看,能够参与到“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地区可分为三部分:以古丝绸之路(包括南方丝绸之路)为基础的北线和南线诸省份(北线为陕西、甘肃、宁夏和新疆,南线为四川、重庆以及云南),以及基于中国古代沿海地区特别是南海方向主要对外贸易通道(广东、广西、福建和海南)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简言之,“一带一路”将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促进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率先转型升级,进而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与民族学的“民族走廊”理论中的诸多部分是相交的,因为“带、路”沿线区域多为少数民族生存、活动和迁徙之地。“民族走廊”理论源于费孝通先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三次重要讲话。按照费先生的观点,“民族走廊”大体在新石器时代开始进入形成过程,以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确立为其形成的重要标志;其活跃期一直延续至唐宋时代,而在元代实行土司制度之后进入休眠期;明清以后,成为了少数民族顽强维护自身仅存的生存地带和文化传统的区域。随后,李绍明先生对“民族走廊”做了定义:“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条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2]十多年后,又有学者将之梳理并根据历史上的民族活动情况与地理方位,将“民族走廊”进一步划为“二纵三横”的构架,即南北纵向的“藏彝走廊”和“土家—苗瑶走廊”,东西横向的“壮侗走廊(或称南岭走廊)”、“阿尔泰走廊”与“古氐羌走廊”。[3] 从“民族走廊”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除北线主要包括“阿尔泰走廊”中的突厥语族诸民族以及“藏彝走廊”中少部分的“藏”外,其余“民族走廊”中的少数民族则多数在南线,且以云南、广西两省区最为集中:广西主要居住着“壮侗(南岭)走廊”中的“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而云南则兼具“带”与“路”的特点——它不仅是中国民族成分最多的省份,还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进言之,在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条由北往南流的大江及其众多支流流经之地,从地理上而言包括滇西北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和滇西高原区等在内的“藏彝走廊”西部地区,迄今有着藏缅语族的各族如藏、彝、白、纳西、傈僳、普米、独龙、怒、阿昌、景颇、拉祜、哈尼和基诺等民族;其下游则有壮侗语族的傣族和孟高棉语族的佤、布朗和德昂等民族,以及苗瑶语族的苗、瑶等民族聚居其间。这个区域自古以来就是藏缅语族诸民族南下和壮侗、孟高棉语族诸民族北上的交通走廊以及他们会合交融之所。而本文中所探讨的问题,也主要是基于笔者近年来在云南的调查、研究情况而言。 由此可见,以“加强同中亚、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为核心理念的“一带一路”战略,将大幅度提高沿线区域内民众的生活质量,并进一步促进其与周边国家和人民的经贸往来,由此民族内部以及民族间的人口流动、文化交流、经济互动会更加频繁,因而“民族走廊”的意义将被赋予时代和发展的内涵。有鉴于此,笔者将“民族走廊”做动态性的解释即“蕴载着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民族迁徙和流动的地理路线和过程”。简言之,国家的发展战略构成了作为区域内活动主体的民族的具体现实的社会生活情境,而这一时空背景下民族的生存与迁移过程及轨迹则是“民族走廊”的阶段性展示。 (二)“一带一路”理念下的“民族走廊”研究 其一,历时性和共时性兼具的研究。也就是说,要尊重民族历史的连续性,既要客观地考证、梳理沿线各族群在历史上的发展脉络——即源流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注重挖掘现阶段各族群社会的发展特点、文化变迁状况、族际交往及人口迁移(包括民族人口的国际性流动)的途径等内容——即“现实”依然是“历史”的一个过程与阶段;此外,还要能够总结规律,做出必要的预测性研究。 其二,“一带一路”理念下的“民族走廊”研究,要求具备开放性思维和国际性视野。以云南为例,境外如在中印半岛各国亦有众多藏缅语族的民族:在缅甸,主要民族为缅族。缅甸北部和西部山区有钦族和克钦族(在中国境内称景颇),都建立了自己的邦政权。此外,在缅北山区还分布着哈尼、傈僳、拉祜、怒等民族;越南讲藏缅语言的各民族主要有哈尼、拉祜等,居住在越北山区;泰国北部山区,藏缅语族的民族有阿卡(哈尼)、傈僳、拉祜等。老挝西北部居住着哈尼、拉祜等民族。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印半岛的藏缅语族各民族的先民是从中国云南或西藏的东部逐渐迁居到现居地的,这其中的主要通道当然是“藏彝走廊”。所以,现阶段的研究要立足云南,又不能局限于云南,要将问题放置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东南亚地缘政治或者更为宏观的区域中来审视。 其三,既要强调少数民族所处现实社会的具体情境,又要体现国家安全的战略思考。一方面,研究要力图弥补长期以来存在的政府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对当地人自身文化及心理诉求关注不够的遗憾。更多地从当地人的视角出发,理解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实现的意义及影响。另一方面,“一带一路”规划中的区域和民族与国家的边疆利益紧密联系,因此,要深刻剖析“民族—经济走廊”与国家边疆安全的互动关系,从文化角度阐释经济发展之于边疆民族社会的深层意义。 二、新时空背景下“民族走廊”中的民族关系 众所周知,农业时代“民族走廊”的分布是以中原向四周发散至边疆的格局,因为远离中央王朝政治中心的边疆通常是不易被控制和开发的地带,也是历史上少数民族人口迁徙、流动的通道和自我保存的庇护之地。而进入现代社会,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流转,尤其是在以便利的交通、网络化以及城镇化为特征的国内布局(“带、路”涉及国内与国际两部分)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新时空背景下,“民族走廊”中的少数民族人口正进行着与历史流向相反的足迹历程,即由西部边疆向政治经济中心与发达的沿海地区、由乡村向城市大规模流动。而作为“多民族国家中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4]的民族关系,在“一带一路”语境中的“民族走廊”中亦会随之发生“日新月异”的改变,事实上随着近年来国内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并取得阶段性成果,变化已经部分地产生了。 首先,高速铁路、公路改变了传统的民族间接触、交往的方式。在“一带一路”的发展框架下,道路及相关设施的建设被认为是基础工作。以云南为例,“计划中的项目包括连接缅甸、老挝的公路,以及各种铁路、港口和码头工程等,目标是成为辐射南亚和东南亚的大通道,届时丝路基金和亚投行都将参与”[5]。而民族关系是通过具体的民族交往加以实现和展现的,在便利的交通条件下,传统的民族间接触与交往的方式即基于地理区域相邻或在经贸往来的长途中而产生的直接交流不再占有优势,地理距离的阻隔已不能成为民族间交往的真正阻碍:古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因异国商人与马帮穿梭其中而与沿途居民产生的匪夷所思的各类民族交往事件成为了历史记忆;前工业社会时代,因长期直接接触而形成的各个层面、不同程度的民族间的联系,被点对点的有形与无形轨道上的短期“偶遇”或“应酬”所取代——尽管空间位移仍然是不同地域间不同民族交往的重要条件,但民族间交往的方式却因为交通工具更加动力化、交通网络更加便利和周全,而发生了实质性地改变。 其次,网络媒体为不同民族成员间的交往提供了新空间,成为了发展民族关系的重要的有效途径。我们要承认,多年来广播、电视一直作为主要的传播媒体为边疆少数民族提供大量、各方面的社会信息,却并没有真正成为替代民族间直接往来、互动的有效的民族关系形式。然而,随着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在内的IT产品和互联网络的发展,内地与边疆的界线被模糊起来,一方面对于边疆少数民族而言,国家的权威性有了更好的展现平台,因为网络社会令人们深切地感受到生活的家园已不再是“山高皇帝远”的“蛮夷之地”;但另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存在亦会使得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间经济信息分布的不对称程度进一步扩大,加之民族间利益需求和文化诉求的不同,在传播过程中易令已经存在的各种民族问题有所激化从而加大影响,随之民族间的隔阂加深。简言之,互联网络导致民族成员间的交往越来越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它在为不同民族成员间开辟一个新的交往空间的同时,在结果上却也是把双刃剑——不同民族背景的社会成员在网络上的直接互动显现出了不确定性和多向度发展的特点来。[6] 再次,民族关系的利益性凸显。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民族利益决定民族关系。雷振扬教授也曾指出“在民族利益体系中,经济利益是最根本性的利益,经济利益决定着其他利益的实现与发展”[7]。特别是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浸染,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的社会生活与价值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昔日与世无争、较为封闭、安于贫困的生活态度逐渐被对利益的关注与追求的价值理念所取代。而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内发展规划中,新一轮的对外开放和经济结构的深化调整,无疑会令沿线的民族地区和区域内的少数民族对资金与物资的需求加强,并且更加倾向于向政府要求支持地区和民族发展的政策等(比如,资源开发中的利益补偿和分配机制及相关合法权益的社会保障问题、网络时代要求国家加大对通信传播基础设施的投入等)。进言之,在新的时空背景下,民族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更易引发不同民族间围绕利益得失而产生的民族事件和民族冲突,进而对民族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伴随着民族成员利益意识到与观念的增强,民族关系的利益性更加突出。 最后,城市民族关系会较以往更加复杂。城镇化无疑是“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国内布局的重要内容。但在包括大量边疆少数民族在内的乡村人口从居住地涌向中东部发达地区的外出务工潮中,人口城市化的趋势已非常明显——城市化某种程度上说代表了城镇化。而“城市生活方式要求市民以职业交往为主要途径扩大自己的交往范围,从而大幅提高了民族交往的可能性和必要性。”[8]换言之,城市民族成分和混居情况不断增加的事实,表明在未来的发展中城市民族关系将更为复杂:其一,民族关系发生地向城市的转移,意味着城市新旧体制的碰撞、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利益格局的调整都较乡村激烈、明显的状况,易激发涌进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其内在的民族意识,进而可能引发民族分界明显、民族隔阂加深。其二,在国家发展战略进一步实施的过程中,尽管“带、路”沿线区域内各族民众的物质生活质量将得到切实提高,但原有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以及城市与乡村生活方式的迥异等问题,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得到根本解决。因而,在各种社会资源有限而民族意识增强与民族利益抱团的背景下,有可能增加城市涉及民族因素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概率。其三,城市民族关系趋于复杂,并不代表问题的负面性增多。事实上,城市化也可以成为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个契机,很多原本棘手的问题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可能会因为遇到适合的条件而迎刃而解。所以,民族关系与城市化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也是具有两面性的研究课题。 三、文化戍边:应对“一带一路”战略南线民族关系问题的国家安全策略 “一带一路”战略是国家利益和意志的体现,国家利益的安全是其最为核心的价值观。因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就是少数民族参与国家间经贸往来的通道,所以,其间“民族走廊”的内部活动、延伸路线等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出这一核心价值——在这条以经贸、文化交流为主的“民族走廊”中,国家的边疆处于中心,各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则属于利益终端。由此可见,边疆安全是“一带一路”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而边疆安全的实质是边民(即边疆地区的居民)安全,[9]边民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因历史上“民族走廊”中的人口流动、迁徙和现代国境线的存在而分隔不同国家的跨境民族。笔者认为,相对于西北地区应更加注重边疆的传统安全问题而言,在西南边疆倡导加强民族文化边疆软实力的文化戍边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只有通过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特别是跨境民族的文化优势,在西南边疆地区社会稳定与繁荣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更好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首先,进行文化产业建设,以文化“固边”。“‘民族走廊’是一种特殊的自然与历史文化景观”(费孝通语)——高山峡谷奇特优美的自然景观与民族历史文化沉积的人文景观的结合,令“民族走廊”沿线区域成为可开发的高品质的文化旅游景点。而实践也已证明,以民族旅游业为代表的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够使得社区居民快速地摆脱贫困[10]——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为边疆少数民族提供了就业机会,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口外流,提高了戍边人口的质量,从而巩固了边防。 其次,做好“文化边防”,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用文化“守边”。一方面,要抵御境外宗教和文化渗透,不给境外的渗透活动留下可乘之机。比如,对境外广播电视信号加强压制,改变边境沿线在境内可以直接收听、收看到境外的无线广播电视节目的现象,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另一方面,要有效扩大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宣传覆盖面,增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类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以确保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特别是跨境民族间文化交往的安全。笔者在怒江做调查时亲见,当地政府引导傈僳族、怒族基督教徒把一些革命歌曲翻译成傈僳文在教堂里演唱——这一做法很大程度解决了跨境民族的宗教文化安全问题,值得推广。 再次,依靠民族文化提高边疆居民的“精神生活幸福指数”,以文化“安边”。还是以怒江的调查为例,电脑网络、电视、KTV以及智能手机等现代媒体令傈僳族酒歌、情歌有了更为广阔的传播空间:KTV里人们唱着“三江组合”(傈僳族的流行音乐组合)结合了民族传统与时尚音乐元素的傈僳酒歌;每天晚间在福贡县的石月亮广场人们跳着带有傈僳“锅庄”舞步的健身舞;而几乎每个村寨都有一个广场供休闲时人们在其中对唱、打跳等等——民族文化能够赋予边疆居民精神安逸的状态,这也是边疆社会安定的重要条件。 最后,通过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实现“文化拓疆”。对于边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并促进其发展,不仅仅在于文化本身的意义,事实上还实现了国家边疆利益的拓展。因为尤其对于跨境民族而言,对于共同历史文化的认同是其维持民族整体性的基本要素。他们的传统歌舞、饮食、服饰以及节日等文化符号,是民族凝聚力的保证。当我们看到,境外的同源民族到中国来寻找祖居地、学习民族的历史与传统文化,再将之带回到居住国,这一过程事实上使得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化有了更为广泛的传播空间,伴随其中的还有国家的价值观、理念等。 古丝绸之路既是一条通商互信、经济合作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文明对话之路,“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就是要继承和弘扬这一具有广泛亲和力和深刻感召力的文化符号。[11]而作为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沉积地带的“民族走廊”,在“一带一路”的语境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从“休眠期”中逐渐“苏醒”—其间充满生机,但也面临问题。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南线,民族间的人口流动、经贸与文化往来历史悠久,在新的时空背景下“民族走廊”及民族关系的文化内涵更显突出,因而,通过发挥文化尤其是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非传统安全功能来治理边疆,也是“一带一路”题中应有之义。 收稿日期:2015-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