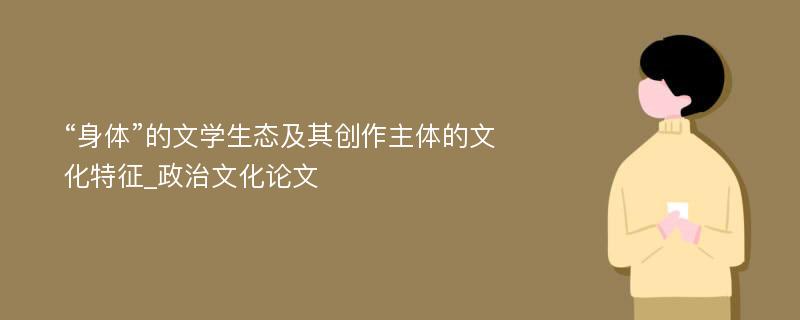
“崑体”文学生态及其创作主体的文化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论文,特征论文,生态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历了唐末五代近一个世纪的文化残毁之后,“西崑体”的产生标志着北宋文坛复兴的序幕正式开启。虽说“白体”和“晚唐体”的影响仍在继续,但那毕竟是五代余音,难以适应新政权文化建设的根本需求;惟有“崑体”作家能够宣导“王泽”、推尊《雅》《颂》,尽革五代以来芜鄙之气,反映出国家统一后的气象和魅力。正如欧阳修所云:“盖自杨、刘唱和,《西崑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①只有全面考察“西崑体”赖以兴盛的生态环境和创作主体的政治、文化特征,才能够对该流派的时代价值作出较为公允的判断。
皇权重建过程中的赋颂需求
“西崑体”的产生是以国家统一、皇权重建后的政治文化需求为背景的,它所表达的文化价值和审美追求,和那个万象更新的时代息息相关。宋太宗在统一天下之初就表现出对“赋颂之作”的强烈渴望。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二云:“五代之际,天下剖裂,太祖启运,虽则下西川,平岭表,收江南,而吴越、荆、闽纳籍归觐,然犹有河东未殄。其后太宗再驾乃始克之,海内自此一统,故因御试进士,乃以‘六合为家’为赋题。时进士王世则遽进赋曰:‘构尽乾坤,作我之龙楼凤阁;开穷日月,为君之玉户金关。’帝览之大悦,遂擢为第一人。”借科举之机以倡导颂声,明确透露出新王朝极为迫切的舆论需求。不错,在国家分裂近百年之后,士大夫群体人格与新建皇权之间的严重疏离必须得到迅速改善,新王朝也需要用一种太平盛世的气象来稳定人心,而皇权的威严和气势更有待张扬。因此,太宗和真宗两朝大量赋颂之作的产生,绝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侍臣的奉迎阿谀,而是新时期政治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
太宗一代是“西崑体”文学的形成期。当日中原地区的文化基础近似荒漠,师道废弛既久,文人数量很少,图书资料又极度匮乏。宋初文坛的权威人物如窦俨、窦仪、范质、陶毅、张昭、李涛、王溥、薛居正、赵普、李防等都是由五代入宋的旧臣,他们曾亲历过不止一次的改朝换代,五代中原“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②的苦难历史,使修、齐、治、平的传统士人格久遭残毁,“皇权”观念更是荡然无存。宋初三朝,持禄混世、因循守旧的士大夫心态仍然制约着社会政治文化的重建进程。以李防为例,他于后汉乾祐中进士及第,历汉、周而入宋,太平兴国中拜平章事;《宋史》卷二六五本传称:“崑和厚多恕,不念旧恶,在位小心循谨,无赫赫称。”《青箱杂记》卷一复云:“李文正公防,深州饶阳人,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名,及即位,用以为相,常语防曰:‘卿在先朝,未尝倾陷一人,可谓善人君子。’故太宗遇防亦厚。年老罢相,每曲宴必宣赴赐坐。防尝献诗曰:‘微臣自愧头如雪,也向钧天待玉皇。’”很显然,入宋以后的高官厚禄并没有改变他消极因循的处世态度;虽说他也曾入主秘阁,主持《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及《册府元龟》等类书的编纂,但资料汇辑本身对于开创新的文化风气并无重大意义。再如范质,后唐长兴四年举进士,历唐、晋、汉、周,宋初继为宰相。《宋诗纪事》卷二录其《诫儿姪八百字》,略曰“学而优则仕,不患人不知”,“戒尔毋多言,多言众所忌”,“举世重任侠,俗呼为义士;为人赴急难,往往陷死刑”云云,世故老成,充满沧桑之感;联系到范质为相期间的依违作风,真可谓文如其人。对李防、范质等五代遗臣来说,拥有这种保守的政治文化心态,原本无可厚非,但要让他们承担起宋初文化重建的使命,却未免艰难。太宗、真宗都渴望用一种文质彬彬、富艳精工的诗文来张扬新朝盛世,而当朝文臣却依然维持着自晚唐五代以来弥漫了近百年的“白体”作风,敷衍斗凑、浅近鄙俗,与现实需要可谓南辕北辙。
虽说要建立与新政权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并非易事,但从太宗到真、仁两朝,思想文化的重建仍然在两个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是柳开、孙复、石介等人大力宣扬儒家大一统的思想,积极推崇以仁义、礼乐为基础的“王道”观,强调通经致用,希望对加强中央集权有所裨益③。二是以杨亿为领袖的“西崑体”文学创作取得了“耸动天下”的辉煌成就。从表面上看,“西崑派”仅仅是一个“更迭唱和,互相切劘”④的诗歌唱和群体,实际上该流派“润色鸿业”的政治效果,远比柳开、孙复等人宣扬的“王道”观要直接、显著得多。
杨亿的出场在宋初文化重建中具有非凡的意义。早在雍熙初年,年仅十一岁的他就以超众的才华获得了朝廷赏识,太宗曾赞许说:“汝方髫齿,不由师训,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景绝尘,一日千里,予有望于汝也。”即授秘书省正字,特赐袍笏。淳化中复诣阙献文,改太常寺奉礼郎,仍令读书秘阁。杨亿献《二京赋》,试翰林,赐进士第,迁光禄寺丞⑤。表面看来,天资过人是这位少年才俊偶获激赏的主要原因,其实,善为讴颂之作才是他平步青云的政治资本。从献《二京赋》到作《承天节颂》,杨亿正是用这种方式,逐步确立了“西崑体”与当代政治文化的特殊关系,而这种关系又决定了“崑体”文学的发展命运和审美取向。
作为一代文宗,杨亿“首变诗格”,重新确定了文学在整个文化重建进程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其《承天节颂并序》可以被看作“西崑体”诞生之前的一篇纲领性文章。文曰:“恭惟五代之季,实启圣宋,囊括席卷,混一区宇。三叶之盛,实生哲后,聪明文思,对越穹壤。涵育万汇,功成而不宰;总制九有,神行而无方。四隅底宁,百度大治。群公卿士,望清光而惟勤;缙绅诸生,颂盛德之靡暇。……若乃赋颂之作,臣之职也。”⑥能够自觉地为盛世气象提供“赋颂之作”,并全神贯注于那些颂美文辞的创作,这是“西崑派”有别于此前所有文学流派的最显著的特点。在杨亿看来,诗人诗作能否“宣导王泽”,是判定其艺术价值的基本准则。譬如,《武夷新集》卷七《温州聂从事云堂集序》称聂茂先诗“恬愉优柔,无有怨谤,吟咏情性,宣导王泽,其所谓越《风》《骚》而追二《雅》,若西汉《中和》《乐职》之作者乎”。同卷《送人知宣州诗序》复称屯田郎某君“以治剧之能,奉求瘼之寄,所宜宣布王泽,激扬颂声,采谣俗于下民,辅明良于治世,当俾《中和》《乐职》之什,登荐郊丘,岂但‘亭皋’、‘陇首’之篇,留连景物而已”⑦。由此可知,杨亿既不提倡《风》、《骚》怨刺之作,也认识到‘亭皋’、‘陇首’一类留连光景的作品实不足以为颂扬盛世,他所倡导的是二《雅》诗歌的“无有怨谤,吟咏情性,宣导王泽”,推崇的是《中和》《乐职》一类宣扬风化的乐音雅调。
杨亿、刘筠及钱惟演等人追求“雕章丽句”的诗文创作,对荒凉已久的北宋文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相对于李防、范质、徐铉、王禹偁等前辈文臣的诗文创作,“西崑体”作为北宋文学的面目更加清晰。宋人周必大曾说:“惟本朝承五季之后,诗人犹有唐末之遗风。迨杨文公、钱文僖、刘中山诸贤继出,一变而为崑体。”⑧田况则云:“杨亿在两禁,变文章之体,刘筠、钱惟演辈皆从而学之,时号‘杨刘三公’,以新诗更相属和,极一时之丽。……其它赋颂章奏虽颇伤于雕摘,然五代以来芜鄙之气,由兹尽矣。”⑨不过,杨、刘“崑体”得以盛行的原因,多半是由于宋初文化和政治建设的时代需求;与其说“西崑体”是对“白体”及“晚唐体”文学的变革,倒不如说“西崑派”是对所有五代遗臣的文化反动。
文学风气的转移,除了帝王的极力倡导与领袖人物的率先示范外,文化精英阶层的审美价值认同是至关重要的。“西崑体”诗文之所以能够在太宗、真宗两朝一枝独秀,其最直接的推动力量还来自于注重才学、偏尚用事的唱和风气。这种风气源自秘阁,波及朝野,构成了宋初文化与文学复兴历程中一段极富色彩的乐章。需要指出的是,“西崑”文学风气的播扬,远远超出了《西崑酬唱集》的作者范围,即便是在杨亿主持文坛的时候也是如此。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帝王对唱和诗风的有力倡导。《庚溪诗话》卷上即云:“真宗皇帝听断之暇,唯务观书,每观一书毕,即有篇咏,命近臣赓和。”当此之时,奉和应制已经成为士大夫政治生活的有机成份,他们对此津津乐道,上行下效,影响不能不深远。其次,“酬唱”原本就不是“西崑派”的专利,用事、精对亦非“崑体”作家所独能。譬如曾被杨亿誉为诗歌“争奇逞妍,更赋迭咏,铺锦列绣,刻羽引商,烂然成编,观者皆耸”⑩的宋浞即未入“崑体”名册。《西崑酬唱集》的编纂问世,仅仅标志着杨、刘“首变诗格”的成功,而并不意味着“崑体”诗风的终结。
杨亿、刘筠谢世以后,晏殊、夏竦、王珪、胡宿、王琪、宋庠、宋祁、赵忭、文彦博等人并以显要达官继而为富艳精工之诗,被称为“西崑余绪”,或谓之“后西崑体”。这几位诗人当中,晏殊声名最著,欧阳修称其一生“由王官、宫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辅道圣德,忧勤国家,有旧有劳,自始至卒五十余年”(11)。前人论其诗作,往往与杨亿、刘筠相提并论,如曾巩《隆平集》卷一三即云:“真宗常谓王旦:‘(杨)亿词学无比,后学多所法则,如刘筠、宋绶、晏殊而下,比比相继。文章有贞元、元和风格。”刘攽《中山诗话》亦云:“祥符、天禧中杨大年、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尚李义山,号‘西崑体’。”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则称“晏同叔自以‘梨花柳絮’取称,然实‘西崑’之一也”。凡此种种,不烦赘引。就晏殊对北宋文学的贡献而言,其雅致闲淡的歌词创作似乎更为后人所推重,至于他作为“西崑余绪”的诗作,反而受到忽视。其实,这二者之间保持着内在风格的一致性。
“后西崑体”的主要作者中,宋庠、宋祁兄弟与晏殊的关系最为密切。方回《桐江续集》卷三二《送罗寿可诗序》已将“二宋”归入“西崑”阵营,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三复云:“宋莒公兄弟,并出晏元献之门,其诗格亦复相类,皆去杨、刘诸公不远。”与“二宋”比肩的还有“二王”,即王琪和王珪,他们系从兄弟。琪为晏殊门客,诗学晏殊;珪历仕仁、英、神宗三朝,以文章致位通显,“掌文诰二十年,每一篇出,四方传诵之”(12)。另有夏竦,长晏殊六岁,王珪称其“为文章闳衍瓌丽,殆非学者之所能至,凡朝廷有大典册,屡以属之,其誉满天下”(13)。三人诗风颇为近似,同属“崑体余绪”。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称夏竦、王珪、丁谓、胡宿所为应制诗“皆典实富艳有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五二《华阳集》提要则云王珪“其多而且工者,以骈俪之作为最,揖让于‘二宋’之间,可无愧色”。相对而言,胡宿、赵忭、文彦博三人,诗风虽系“崑体”,但与晏殊并无深交。清王士禛在《带经堂诗话》中议论说:“宋人诗,至欧、梅、苏、黄、王介甫而波澜始大,此前杨、刘、钱思公、文潞公、胡文恭、赵清献辈,皆沿西崑体。”又云:“世人谓宋初学西崑体有杨文公、钱思公、刘子仪,而不知其后更有文忠烈、赵清献、胡文恭三家,其工丽妍妙不减前人。”(14)
从晏殊、“二宋”、“二王”、夏竦到胡宿、赵忭、文彦博,其仕宦与创作的黄金时期都在仁宗朝。和前“西崑派”相比,“后西崑体”作家所处的政治环境已有所变化。“庆历新政”以后,宋初三朝相沿已久的政治格局被打破,文学群体的政治主体意识也得到明显的加强,所谓“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15)的士大夫群体人格特点日趋成熟。同时,作为“庆历新政”的文化表现形态,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要求把“知古”、“明道”与“致用”结合起来。在这一理论主导下,从仁宗天圣年间开始,欧阳修就和友人尹洙、梅尧臣、苏舜卿等结成了一个锐意改革的文学集团,“同为古文歌诗”,以有益时政。由于受到时代思潮的冲击和震荡,“后西崑体”作家在追求博学典雅、“雕章丽句”的同时,并不仅仅把“激扬颂声”作为艺术的出发点,唱和酬答的创作模式也不再受到杨亿式的推崇。同样是典实富艳的诗作,“后西崑体”所表达的思想及情感内容,明显比杨、刘诸公有所拓展。随着欧、梅诗风的不断加强和巩固,“后西崑体”诗最终只能彻底退出北宋文坛。
“崑体”文学作为宋初政治文化的一种外化形式,形象地展示文人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过程。
重北轻南的政治偏向与前“西崑”唱和主体的文化特征
“崑体”文学原本属于南方文化的表现形态,它所追求的“雕章丽句”是以其创作主体的博学多才和善于用事为前提的。入选《西崑酬唱集》的十位诗人当中,杨亿来自福建浦城,其他诗人如杭州钱惟演、钱惟济,江左舒雅、升州刁衎、江陵崔遵度、蜀人薛映、苏州丁谓等等,并为南国英才,更是西崑酬唱的主力军。刘筠“初为杨亿所识拔”,方得“居文翰之选”(16),其虽自大名登第成名,所师却并非北人。后“西崑体”作家之中,晏殊乃抚州临川之神童,夏竦为江州德安之才俊,王琪、王珪来自四川成都,宋庠、宋祁起于安州安陆,胡宿生在常州晋陵,赵忭长于衢州西安,只有文彦博一人籍贯为汾州介休。由此便不难看出,在“西崑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南方作家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他们既是创作的主体,同时也是将南方文化向北推移的生力军。不过,“崑体”作家群体在地域分布上的上述特点,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宋初政治文化发展中的某些深层矛盾。事实上,从建国之初一直到真宗继立,赵宋政权一直坚持重北抑南的用人政策,南方士人在政治上长期承受着不公平的待遇,仕途充满艰辛。至少在杨亿和钱惟演的时代,“西崑体”华艳工巧的“颂声”后面,的确隐含着无数南方士人身受排斥和压抑的无奈;于是,以文学为进身之阶便成了他们普遍的选择。为了客观分析前“崑体”作家群体文化心理特点所以形成的政治历史原因,我们的讨论还必须从南北文臣政治待遇的差异开始说起。
赵宋政权对南方士人的轻视和排斥,源自南、北方政治文化的对立与冲突。唐末五代,在旷日持久的兼并战争之后,杨吴及南唐相继称雄于江淮,前蜀及后蜀先后割据于两川,湖南马氏、吴越钱氏、闽中王氏、南汉刘氏及荆南高氏亦皆裂土自立,与中朝政权分庭抗礼,史称“九国”。和中原大地战火不息、朝代频繁更替的混乱状况相比,南中国地区,尤其是江淮、两川及吴越,却长期保持着相对稳定,经济和文化建设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南、北方在政治及军事方面的长期对峙,导致我国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全面南移。赵匡胤代周自立之初,群雄割据、南北对立的态势依然如故,所谓“天下未一,宋亦列国耳”(17)。在此情形下,赵宋皇室及其文武臣僚对南方各国君臣的敌视和对立心态便自然产生。此外,在南北对峙之中,中原王朝一直以正统自居,南方诸国如吴越、南唐等则奉中朝为正朔;政治心态的差异也会导致文化特点的同源异质。北方士人念念不忘维护“道统”、推行“王化”的传统理想,视南方各地为蛮夷“下国”,以华采绚烂之南方文学为妨道误国之雕虫小技。南方文人则富于学问,凡诸子百家之说、异闻杂记之书、音韵句读之学,往往兼收并取,颇有几分重文轻道的意味。宋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仅仅结束了政治及军事上的分裂与对抗,南北文化的对立冲突却仍然在继续。
北宋初期,北方士大夫是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早在建国之初,宋太祖就确立了重北抑南的基本国策(18),直到太宗末年,凡中书、枢密、三司之首脑以及作为“人主之耳目”的台官和谏官,几乎都是由北方人担任。各级官吏往往相互交结,徇私枉法,穷极奢靡。譬如,王溥乃后汉乾祐中进士,自周太祖至宋初,“十年为相,三迁一品,福履之盛,近世未见其比”,其家“所至有田宅,家累万金”(19)。石守信之子石保吉,“累世将相,家多财,所在有邸舍、别墅,虽馔品亦饰以彩缋。好治生射利,性尤骄倨,所至峻暴好杀,待属吏不以礼”(20)。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奢侈需求,权贵近臣竟不惜矫制牟利。太平兴国中,“近臣戚里遣人市竹木秦陇间,联巨筏至京师,所过关渡,矫称制免算;既至,厚结有司,悉官市之,倍受其直”。三司使王仁赡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遂具奏以闻,结果触怒了权门贵戚,就连宋太宗也要清算他的旧账,谓“王仁赡领邦计积年,恣吏为奸,诸场院官皆隐没官钱以千万计,朕悉令罢之,命使分掌。仁赡再三言,恐亏旧数,朕拒之。未逾年,旧获千缗者为一、二万缗,万缗者为六七万缗,其利数倍”(21)。于是贬王仁赡为唐州防御使。京师汴梁的这种骄奢风气,甚至还波及到地方州郡。雍熙时,陕州州富民李益,“家饶于财,僮奴数千,恣横持郡吏短长,长吏而下皆畏之。民负息钱者数百家,郡为督理如公家租调”;又“厚赂朝中权贵为庇护,故累年不败”(22)。毫无疑问,北方士人在政治上享有的种种特权为他们牟取社会财富创造了条件;反过来,既得的物质利益又在不断强化着这种特权。不过,在国家完全统一之后,这种自五代沿袭而来的政策显然不利于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甚至会导致国家政权机构的僵化和腐朽。于是从真宗朝开始,重北抑南的既定国策便开始有了松动。
和中原士大夫的养尊处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方士人的困顿与艰辛。作为亡国降臣的南方才俊大多有过见疑见弃的仕宦经历,他们中绝大多数初被闲置于“三馆”之中,从事《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广记》等类书的编纂工作,如徐铉、张洎、汤悦、张秘、郑文宝、陈彭年、龙衮、乐史、周惟简、舒雅、邱旭、吴淑、刁衍、钱俨、钱易、钱昱、钱昆、钱惟演、钱惟济等等,他们以皓首群书的清闲,排遣着政治上被冷落的无奈。为了掩饰朝廷对南方士人的疑弃态度,宋太宗也曾让其中几位久负盛名的降臣担任过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职。如张洎就曾“直舍人院,考试诸州进士”(23)。徐铉北归之后,初为太子率更令,不久即坐事出陕右,遇刺史柳开,不被礼遇,备尝艰辛。太宗即位后虽受诏回京,但也只能担任给事中和左散骑常侍一类的小官。李煜被毒死后,即有人欲借徐铉受命撰写《吴王神道碑》的机会陷害于他,未能得逞(24);但到了淳化二年,“庐州女僧道安诬铉奸私事,道安坐不实抵罪,铉亦贬静难行军司马”,次年即不禁寒苦而卒(25)。所谓道安诬告,不过是朝中权贵构祸陷害的阴谋而已。
就在徐铉因盛名而招致北方权臣嫉妒谗毁的时候,杨亿已于雍熙元年步入文坛,七年后赐进士第,那时他才十九岁。在世人眼中,杨亿是一位学富位显的达官,但作为南国文臣,他也不能不面对类似于徐铉的宦海沉浮。欧阳修《归田录》卷一云:“杨文公亿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刚劲寡合,有恶之者,以事潜之。大年在学士院,忽夜召,见于一小合,深在禁中。既见,赐茶,从容顾问,久之,出文稿数箧以示大年,云:‘卿识朕书迹乎?皆朕自起草,未尝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对,顿首再拜而出,乃知必为人所潜矣。由是佯狂奔于阳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顾无比,晚年恩礼渐衰,亦由此也。”面对人心叵测、危机四伏的仕宦人生,杨亿只能通过唱和酬答,抒发其忧谗畏祸的无奈心声。
真宗一代,随着“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岂限遐迩”(26)的用人理念的形成,南方士人的政治待遇略有改善,但重北轻南的做法却依然如故。这一点在科举取士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洪迈《容斋续笔》卷一三云:“予家藏咸平元年孙僅榜盛京所得小录……此榜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刘烨为河南人,余皆贯开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亦然,不应都人士中选若是之多。疑于方外人寄名托籍,以为进取之便耳。”无论方外人托籍于开封是否属实,这一届进士中没有一个南方人却是极明确的。类似的情形在咸平五年的科举考试中再次发生,其年知贡举者乃是洪州南昌人陈恕,“恕自以洪州人,避嫌,凡江南贡士悉被黜退”(27)。这一方面说明朝廷重北抑南的用人政策已为天下所共知,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陈恕作为南方人急欲取媚北方权臣的卑微心理。其实,对于更多的南方学子来说,所谓“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28)的政治偏见,以及解送名额的严重不足,共同限制着他们通过科举步入政坛的机会。直到英宗即位之初,时为参知政事的欧阳修还指出:“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盖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东南十倍。”(29)如此悬殊的比例,再加上考试过程中的种种不合理因素,南方学人应举入仕的艰难便可想而知。
南北方士人政治待遇上的上述差异,必然会影响到宋初文学发展的总体风貌。以南方文人为创作主体的“西崑体”文学能够在太宗、真宗两朝兴盛起来,绝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现象,在它艳丽精工的“颂声”背后,尚有许多急待破译的谜团。从某种意义上讲,前“崑体”文学特征的形成与南方士人群体试图改善其政治处境的努力密切相关。
首先,宋初政治的重北抑南与文化发展水平的北轻南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差,南方文化的发展优势必然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充分的体现。“西崑体”作家正是以博学多闻的文化自信与北方权臣的政治特权相抗衡,而在具体手段上却选择了不易招致政治迫害的文学唱和方式。杨亿在《广平公唱和集序》中指出:“善歌者必能继其声,不学者何以言其志!故雅颂之隆替,本教化之盛衰;傥王泽之下流,必作者之间出。君臣唱和赓载而成文,公卿宴集答赋而为礼,废之久矣,行之实难,非多士之盈庭,将斯文之坠地。”(30)“王泽”、“教化”之语是对现实政治文化的一种美誉,而他所强调的首先是诗文作者应该博学多闻,认为“不学者”很难承担起振兴雅颂之文的使命。至于君臣之间的唱和赓载,自元、白以降蔚然成风,虽五代乱世亦盛行不辍,宋初北方文臣如李防、李至、扈蒙、李穆、郭贽、王禹偁、宋白、赵邻几等莫不谙于此道。然其作者大多缺乏足够的才学,唯务浅近流易,谓之“白体”。杨亿对此深为不满,认为只有博学善歌之士充盈朝堂,才能有效地振兴雅颂之文,而从《西崑酬唱集》的入选作者来看,所谓“多士盈庭”,绝大多数实为南方才俊。
其次,面对朝廷重北轻南的既定国策,南方文人群体为了博得最高统治者的赞赏与支持,共同选择了“激扬颂声”和“宣导王泽”的文学之路。同时,为了使这种富有时代特点的文学创作独领风骚,他们还创造性地运用了南方文学固有的表达方式,以精巧用事来展示博学,借繁词丽藻以表现才情,注重音韵偶对以创造美文功效,从而达到了“白体”及“晚唐体”作家难以企及的颂美境界。假如没有南方士人在政治上的被动处境,要使“润色鸿业”成为他们自觉的艺术追求,其可能性是值得怀疑的。略晚于杨亿的道学家石介曾指责“崑体”诗人“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刷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蠢伤圣人之道”(31),此说颇为后人所征引,以为“崑体”贬语。其实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西崑”文学以颂美为主的艺术功能与道学家以圣人之道、圣人之言匡救时弊的济世目的背道而驰,故而受到责难。同时,类似的指责也反映出北方士人对南国文臣以“颂声”媚时的强烈不满。
第三,以文学为进身之阶乃是迫不得已的人生选择,“激扬颂声”并不意味着“西崑体”作家自我生命意识的消退。相反,“崑体”诗所展示的人生画卷自有其斑斓的色彩和丰富的内涵,值得细心品味。以杨亿诗为例,《西崑酬唱集》开篇《受诏修书述怀感事三十韵》即非纯粹的颂美之作。该诗首段先用华丽的笔调描述了自己的修书生涯,随之则慨叹道:
抚已惭鸣玉,归田忆荷锄。池笼养鱼鸟,章服裹猿狙。圜府愁尸禄,天阍媿娩弊裾。虚名同郑璞,散质类驻樗。国士谁知我,邻家或侮予。放怀齐指马,屏息度羲舒。寡妇宜忧纬,三公亦灌蔬。危心惟股觫,直道忍蘧篨。往圣容巢许,先儒美宁蘧,晨趍叹劳止,夕惕念归欤。秦痔躁杯酒,颜瓢赖斗储。如谐曲肱卧,犹可直钩渔。
作为文学侍臣,虽晨夕劳顿却终是尸禄无为。“直道”既不容于朝,谗言毁语复令人股觫,思乡难归,退隐如梦,锦绣文章的背后却别有一种“国士谁知我,邻家或侮予”的辛酸。同样的人生感叹,类似的情感表白,还出现在《偶怀》《即日》《直夜》《偶作》《鹤》《萤》等不同作品中。这说明杨亿的生命历程中除了皇恩浩荡,还充满忧谗畏祸、彷徨失路的危机感,那种身处孤危的惶惶不安,欲退归林泉而难寻归途的迷茫,的确透露着作者复杂而真实的心声。当然,并不是所有参加西崑酬唱的南方诗人都能像杨亿那样直抒胸臆,相同的主题,表达方式往往会有所不同。譬如钱惟演在和《宣曲二十二韵》中就借杨妃幽魂倾诉自己的心声:“掩鼻谗难诉,披图悔岂追。只应金带枕,聊为达微辞。”作为吴越降王之子,他深知李煜招致“牵机药”之祸的根由始末,假使稍有不慎,即有可能因诗而致祸,正如其《无题》所云:“误语成疑意已伤,春山低敛翠眉长……合欢不验丁香结,只得凄凉对烛房。”托物言志,意在言外。
毋庸讳言,南方士人倍受压抑的政治现实是“西崑体”文学得以兴盛的时代土壤;南方文化的固有风采与南国文臣以文学为进身之阶的创作实践,共同造就了“崑体”诗含英咀华的颂美品格。“颂声”之外,“西崑体”诗人还抒写着忧谗畏祸、退归无门的种种隐忧,这既是一种真实的生命感受,更是艺术创作的必然。
望族文化心理的成熟与“西崑余绪”
仁宗一代是北宋政治文化及文学艺术发展的转折期。从天圣到嘉祐,随着晏殊、夏竦、胡宿、王琪、王珪、宋庠、宋祁、赵抃、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苏轼、苏辙、曾巩等一大批南国新人成功地登上国家政治舞台,重北轻南的用人政策基本被打破。由范仲淹发起实施的“庆历新政”,拉开了政治改革的序幕,它标志着改革与保守两种政治势力的斗争从此将成为北宋历史的核心。与此同时,作为“庆历新政”的文化表现形式,欧阳修和梅尧臣等人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气势和力量。它所承担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用有破有立、考证详密的新学术代替北方道学家柳开、穆修、孙复、石介等人空谈儒道、脱离现实的旧学术(32);二是全面总结自五代宋初以来相沿已久的“白体”、“崑体”和“晚唐体”等诗歌流派及骈体文创作的得失教训,以此为基础,进而开创了一种能够将“知古”、“明道”、“致用”合而为一的文学创作新风尚。“庆历新政”因保守派的强烈攻击而宣告失败,但欧、梅诗风却一扫阴霾,取得了里程碑式的巨大成功。值得注意的是,从仁宗到神宗时期,政治待遇获得明显改善的南方文人竟分化为政治文化态度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一个是以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为代表的革新派,另一个则是以晏殊、夏竦、宋庠、胡宿、王珪等人为代表的保守派。所谓“后西崑体”的几位作家大多属于后一阵营。当然,保守并不足以解释晏殊等人在诗文创作上所拥有的华贵气派,时代背景也仅仅是解读“后西崑体”文学的参考因素之一。
按照通常的理解,“西崑余绪”纯粹是一种文学创作方式的延续,与政治文化的发展关系不大,但这种见解明显简单了些。“后西崑体”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无疑有着鲜明的贵族特色,而这种特色与当日社会已经发展成熟起来的望族文化心理密切相关。本文所谓“望族”,是指在北宋政治及文化生活中几世显赫的名门大姓,它不是六朝隋唐时期士族豪门的后裔,而是有宋以后成长起来的朝廷新贵。譬如李防一族。崑父超,后晋时官工部郎中、集贤殿直学士。防于太平兴国及淳化中两次荣登相位;弟李至也于太平兴国八年拜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真宗即位,拜工部尚书。兄弟二人长于歌咏,有《二李唱和集》传世。防子宗讷、宗诲、宗谔、宗谅等亦皆显贵。宗谔举进士第,真宗朝预修《太祖实录》,深于礼仪,通晓音律,著述颇多,名列《西崑酬唱集》内。孙昭逊官太子中舍,昭述累迁至尚书右丞。“李氏居京城北崇庆里,凡七世不异爨,至昭述稍有丰殖,为族人所望,然家法亦不隳”(33)。再如河南吕蒙正,祖梦奇,仕后唐为工部侍郎。蒙正于太平兴国二年擢进士第,太宗朝三次入相。真宗即位,蒙正“奉家财三百余万以助用”;子、孙多历显官(34)。蒙正侄夷简,仁宗天圣、景祐间两践相位,子公绰、公弼亦名显于时(35)。其实,类似于李、吕两族显宦迭出恩荣几世的情形,在北宋中期以后屡见不鲜。
名门望族的重新出现是北宋皇权政治的必然结果;望族势力既已形成,就会产生相应的文化心理需求。早在先秦时代,以《诗经》中的《雅》诗和《颂》诗为艺术载体的贵族文化就已经相当成熟;六朝隋唐时期,随着士族门阀势力的不断扩张,远古的泛贵族文化逐步演变为一种集政治特权、经济实力及家规家法于一身的封建家族文化。唐代《氏族志》的编纂,即体现着皇权政治与高门大姓之间互为依托的密切联系。有唐三百年间士人普遍重地望而轻占籍,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氏族文化心理的约束。唐末五代,随着皇权的解体,氏族门阀势力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顾炎武《亭林诗文集·文集》卷五云:“自唐之亡,而谱牒与之俱尽。然而裴枢辈六七人犹为全忠所忌,必待杀之白马驿而后篡唐,氏族之有关于人国也如此。至于五代之季,天位几如奕暮,而大族高门降为皂隶。”到了这种地步,以郡望门第为政治资本的士族阶层便不得不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宋初几十年,在太平盛世之中沐浴成长起来的朝廷新贵日益增多,他们虽没有世系谱牒,却拥有比谱牒更重要的现实政治优势;家法族规的缺失并未影响到他们对隋唐士族风采的向往。杨徽之知杨亿嗜学,遂为之叹曰:“兴吾门者在汝矣!”(36)寇准则不无自豪地宣称:“吾家嗣儒业,弈世盛冠裳。桂籍冠伦辈,天下知声光。有才无其命,不得步玉堂。”(37)毫无疑问,在历史传统与现实政治的交汇中,北宋望族文化心理正日臻成熟。
“西崑体”文学的产生,客观上为满足正在形成中的望族文化需求提供了可能。如果说杨亿等人对《雅》《颂》诗歌的崇尚还只是出于歌功颂德的艺术本能,那么“后西崑体”作家“博赡瑰丽”的诗文则更加接近望族文化本身。创作主体社会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及其对望族文化心理的真切体验,无疑使“崑体”文学的演变和发展获得了主客观结合的艺术契机。晏殊、夏竦等人的仕历创作主要在仁宗天圣、景祐以后,其共同特点是学富才高、富贵显达。晏殊“出东南,起童子,入秘阁读书,遂赞名,命入翰林为学士。真宗特宠待之,每进见劳问及所以任属之者,群臣莫能及”。仁宗即位以后,“遂筅国枢要,任政事,位宰相,其在朝廷五十余年,常以文学谋议为任,所为赋颂、碑铭、制诏、册命、书奏议论之文传天下,尤长于诗,天下皆吟诵之”(38),遂成为继杨亿之后的又一位文坛宗主。欧阳修曾为晏殊作挽辞云:“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一时闻望朝廷重,余事文章海外传。”(39)可谓的评。夏竦长晏殊六岁,仁宗初迁知制诰,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庆历七年为宰相,旋进封英国公。王珪谓其“少好学,自经史百氏、阴阳律历之书无所不学,其学必究古今治乱天人灾变之原。其为文章,闳衍崑丽,殆非学者之所能至”,“出入荣华四十余年,可谓盛矣”。(40)胡宿及宋庠、宋祁兄弟同为天圣二年进士。宿累官知制诰、翰林学士,嘉祐六年拜枢密副使。后以尚书吏部侍郎、观文殿学士知杭州。一生颇以博学闻,尤精阴阳五行、天人灾异之说。宋庠于庆历八年拜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迁工部尚书,后因包拯参奏去位;嘉祐三年拜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复为枢密使,封莒国公。宋祁亦以文学显名,屡为翰林侍读学士、史馆修撰、龙图阁学士。兄弟二人同为一朝显宦,各得其宜,从而为形成一个新的名门望族奠定了基础。王琪和王珪的仕历创作与“二宋”相类似,琪于仁宗景祐中直集贤院,为两浙淮南转运使。后以龙图阁待制、知制诰、枢密直学士的身份先后出知扬州、杭州及润州等地,终以礼部侍郎致仕。珪于庆历二年举进士后,累官知制诰、知审官院,先后为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神宗熙宁三年拜参知政事,九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以文章致位通显,“掌文诰二十年,每一篇出,四方传诵之”(41)。“后西崑体”作家中另有赵扑及文彦博二人,前者累官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等,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谥清献;后者则更极显贵。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六称其“更事四朝,洿历二府,七换节钺,位将相五十余年,平章事四十二年。历任侍中、司空、司徒、太保、太尉,再知秦州、大名、永兴,五判河南府,两以太师致仕,为本朝名臣福禄之冠”。
如果没有对“后西崑体”作家的富贵人生进行通盘考察,我们便很难就其所展示的望族心态作出准确的判断。也许他们并非名门之后,但他们对显达人生的切身体验与李公弼、吕夷简等望族子弟并无二致。“崑体”文学流派的形成固然与赵宋政权点缀升平的政治需要有关,但“后西崑体”不绝如缕的创作却是北宋中叶以后望族心理积淀与成熟的必然反映。假如不从这个角度去解读“后西崑体”存在的合理性,那就只能回到所谓“形式主义”的指责与批判中去。至于晏殊以后的“崑体”文学创作与北宋望族文化之间互为表里的深层联系,或许可由以下几方面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望族文化与皇权政治之间的依存关系,决定了“后西崑体”文学必须直接地为皇权政治服务,赞君德,扬颂声,全心全意。杨亿宣称“赋颂之作,臣之职也”,夏竦则云“王道兴而颂声作,士大夫之职也”(42),这说明“崑体”文学的赋颂传统是一贯的。王珪在《御制龙图天章阁观三圣御书诗序》中也说:“臣读《诗》至《小雅》之什,见周之盛时,乐贤人之在位,而君道益自尊显。既饮食之,又有笙簧鼓舞、币帛侑酬之礼,恩勤返复,以尽其欢心。且君能下其臣,则为臣者未有不感发忠诚,思以归报乎上。上下相交,四海蒙泽,以致太平,使国家万寿之福无期极,其诗传于后代,犹歌而取法,顾匪盛德之事欤?”(43)正是从尊显君道、感发忠诚的基本目的出发,“后西崑体”作家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歌赋颂辞,且将赋颂的精神广泛运用到制诏、册命、碑铭及书奏议论等更为广泛的领域;凡是能够体现皇恩浩荡及朝廷威仪的地方,都能为“后西崑体”作家歌咏王道、颂美君德提供良好的创作田地。
与杨、刘诸公以歌功颂德为主的翰苑酬唱有所不同,“后西崑体”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明显的超越,也更加符合望族文化的表现需求。北宋望族不同于隋唐时期的世族门阀,他们不再拥有干预地方政务、掌控部分地方武装的政治军事实力,而所谓“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44)的社会转型,又使他们失去了垄断土地、蓄积财富的经济特权。因此,作为新型望族,若欲尊显其门第,便只有通过喜文乐士、附庸风雅的途径张扬其文化优势。宰相沈伦之子沈继宗,“喜结宾客,终日宴集无倦”(45);王质颇以能入范仲淹党籍为光荣(46),皆其显例。不过,从总体上看北宋望族本身的文化积累还远没有隋唐世族那样丰厚,若要凭借自身的才识学养实现张扬门第文化的目的,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西崑体”作家正好从两个方面弥补了这种不足。其一是创作主体本身的显贵心态,客观上与望族文化心理源流相同;其二是“崑体”之作以其典实富丽的特性,为望族文化的张扬提供了最佳方式。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三云:“宋初之西崑,犹唐初之齐梁;宋初之馆阁,犹唐初之沈、宋也。”倘若就文学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而言,这种类比无疑是恰当的。以王珪《宫词》为例,其镂金刻玉璀璨锦绣之文,令人目不暇接;满纸充斥着玉阶、金缕、朱弦、玉腕、金殿、锦帐、玉浪、金床一类的字眼,内容则多与望族生活密切相关。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云:“唐王建以宫词名家,本朝王岐公亦作宫词百篇,不过述郊祀、御试、经筵、翰苑朝见等事;至于宫掖戏剧之事则秘不得传,故诗词中亦罕及。”其实,王珪《宫词》不及宫掖之事的根本原因,乃是由于他眼中的望族生活与王建笔下的唐宫嫔妃并无太大区别;而叙写郊祀、御试、经筵、翰苑朝见等事更能体现其学识与文采。“后西崑体”契合北宋望族文化心理的艺术发展轨迹,由此即不难得到明确的验证。
“后西崑体”文学作为望族文化的艺术载体,自然不会与苏、梅领导的文学革新运动同步共振,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同一时代各种文学流派之间的借鉴与互补也是必然的。譬如,同样是以“典雅丽藻”见长的夏竦,对宋初诗坛的整体看法却与欧、梅有着惊人的相似处。他说:“近岁学徒,相尚浮浅,不思经史之大义,但习雕虫之小技,深心尽草木,远志极风云,华者近于俳优,质者几于鄙俚,尚声律而忽规箴,重俪偶而忘训义。”(47),这既是对时风的批评,同时也有自我反省的深意。他希望“后西崑体”作家能够超越杨亿诗“如锦绣屏风,但无骨耳”(48)的不足,多一点“气壮”、“语峻”的创新与提高。胡宿诗虽充满富贵气,但他却称赞邓国公“缀文根道,尤邃于诗,峻整平淡,通有二体”(49),欣赏僧长吉“平淡犹古乐,于言虽未忘,在理已能觉”(50)的淡雅境界。晏殊在文学思想上与欧、梅截然对立,他坚守“西崑”阵地,主张雅颂宗旨,反对用诗歌反映民生疾苦。但他“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气象”(51)。所有这些,都是“后西崑体”作家受到欧、梅文学改革思想影响的明证。正如望族阶层不得不直面范仲淹、王安石等人的政治改革一样,“崑体”文学也无法回避欧阳修以后新文学思潮的冲击。新、旧两种政治文化及文学理念的对话与冲突,表明北宋历史正在进行着全方位的文化转型。
在近似荒漠的宋初文坛,“西崑体”的产生不仅意味着文学自身的开拓与超越,更意味着南方文人群体政治文化意识的悄然觉醒。前、后“西崑体”的历史传承与自我更新,看似单纯的文学现象,实际却有着更为深广复杂的社会心理原因。望族文化心理的积淀和成熟,无疑为“后西崑体”文学的兴盛提供了最直接的现实基础,而北宋中期波澜起伏的政治文化变革,又对其存在价值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西崑体”的兴衰,折射出北宋历史文化演进的某些深层思致,本文的分析讨论也仅仅涉及到冰山一角。
注释:
①《欧阳文忠公文集·诗话》,《四部丛刊》影印本。
②两条分别见陈师锡《五代史记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五代史记》卷首;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6《唐废帝家人传论》173页,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③柳开门人张景在《河东集序》中说:“先生生于晋末,长于宋初,拯五代之横流,扶百世之大教,续韩孟而助孔周,非先生而孰能哉?”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明确表示其研究目的在于“尊王”。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七《二大典》亦云:“《周礼》、《春秋》,万世之大典乎……呜呼!《周礼》明王制,《春秋》明王道,可谓尽矣。”
④杨亿《西崑酬唱集序》。
⑤(36)《宋史》卷305《杨亿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⑥《武夷新集》卷6。
⑦所谓《中和》《乐职》,乃是西汉王褒所作“宣风化”之诗,颜师古注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乐职》者,言百官各得其职也。”详参《汉书》卷64下《王褒传》。《南史》卷三八《柳恽传》云:“恽立性贞素,以贵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为诗云:‘亭皋木叶下,垄首秋云飞。”“亭皋”、“陇首”,代指流连光景之作。
⑧《跋宋待制崑宁轩自适诗》,周必大《文忠集》卷4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田况《儒林公议》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广平公唱和集序》,《武夷新集》卷7。
(11)《观文殿大学士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赠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铭(并序)》,《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22,《四部丛刊》影印本。
(12)(41)叶清臣《王文恭珪神道碑》,《名臣碑传琬琰集》上集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40)《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王珪《华阳集》卷4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两条分别引自《带经堂诗话》43页、2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点校本。
(15)《宋史》卷314《范仲淹传》,10268页。
(16)《宋史》卷305《刘筠传》,10089页。
(17)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凡例》以开宝八年为北宋正统之始,明人周礼作发明。
(18)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云:“太祖御笔:‘用南人为相、设谏官,非吾子孙。’石刻在东京内中。”
(19)《宋史》卷249《王溥传》,8801页。
(20)《宋史》卷250《石保吉传》,8813页。
(21)两条并引自《宋史》卷257《王仁赡传》,8957、8958页。
(22)《宋史》卷257《元载传》,8949页。
(23)《宋史》卷267《张洎传》,9209页。
(24)宋魏泰《东轩笔录》卷1云:“太平兴国中,吴王李煜薨,太宗诏侍臣撰《吴王神道碑》,时有与徐铉争名而欲中伤之者,面奏曰:‘知吴王事迹,莫若徐铉为详。’太宗未悟,遂诏铉撰碑,铉遽请对而泣曰:臣旧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义,乃敢奉诏。’太宗始悟让者之意,许之。”
(25)《宋史》卷441《徐铉传》,13045页。
(26)宋真宗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0,5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27)《钦定续通志》卷308《陈恕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4载,大中祥符八年三月,腰水人蔡齐与新喻人萧贯争为进士第一,“齐仪状秀伟,举止端重,上意已属之。知枢密院寇准又言:‘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齐遂居第一。……准性自矜,尤恶南人轻巧,既出,谓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
(29)《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四部丛刊》影印本。
(30)《武夷新集》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徂徕集》卷5《怪说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详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第2章第3节之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3)详参《宋史》卷265《李崑传》及子、孙各传,9135-9145页。
(34)详参《宋史》卷265《吕蒙正传》及子、孙各传,9145-9150页。
(35)详参《隆平集》卷5《吕夷简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忠愍集》卷上《述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曾巩《类要序》,《元丰类稿》卷1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晏元献公挽辞三首》,《欧阳文忠公文集·外集》卷6。
(42)夏竦《景德五颂序》,《文庄集》卷2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3)《华阳集》卷4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4)南宋袁采《袁氏世范》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5)《宋史》卷264《沈继宗传》,9116页。
(46)《宋史》卷269《王质传》,9245页。
(47)《厚文德奏》,《文庄集》卷15。
(48)范镇《东斋记事》卷3,第23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49)《太傅致仕邓国公张公行状》,《文恭集》卷4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0)《读僧长吉诗》,《文恭集》卷1。
(51)吴处厚《青箱杂记》卷5,第46页。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