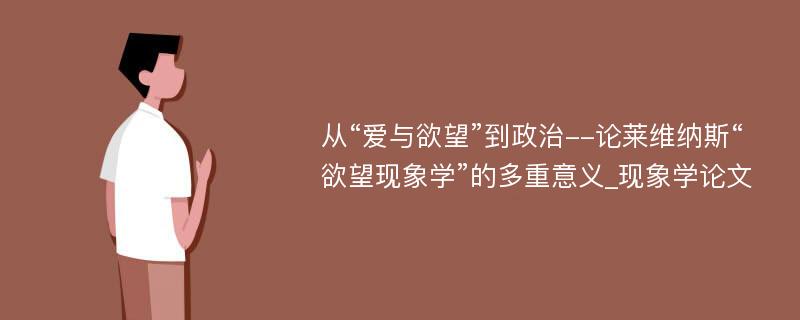
从“爱欲”到政治——论莱维纳斯“爱欲现象学”的多重意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欲论文,维纳斯论文,现象学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莱维纳斯思想的研究,大多对集中在他关于“他者之脸”的论述上。“他者之脸”将“我”从生存的经济性中警醒出来①,从生存走向了伦理,从而打破了自我生存的封闭性和内在性,使哲学迈向“无限”成为可能。这便是我们对于莱维纳斯哲学的一般理解,也是关于“他者之脸”的分析成为莱维纳斯哲学中最著名篇章的原因。一些讨论莱维纳斯哲学的文章著作,也常到这儿就戛然而止。但是,为什么在《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中,在讨论了“他者之脸”以后,莱维纳斯还要继续讨论“超越脸”② ?面对“他人之脸”不正是其哲学的核心思想吗?难道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超越脸”呢?这部分内容在什么意义上才是关于“他者之脸”论述的逻辑后承呢?《总体与无限》中这部分内容多少显得有些“怪异”。这是因为莱维纳斯最终把超越“脸”的向度指派给了“爱欲”(Eros)。并由此延伸出一系列新的概念如“繁殖”(fecunditv)、“父性”(paternity)、“子女性”(filiality)、“兄弟之爱”(fraternity)等。这些概念与莱维纳斯其他思想究竟构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一些学者似乎也深感迷惑,甚至有学者认为这部分内容乃是莱维纳斯的信手之作③。
事实上,莱维纳斯本人在书中对此有过相当明确的界定:“我们必须标示出一个平台,既预设了在脸中他人的显现,又超越这种显现,在这种平台中我背负自己超越死亡,从返回自身中得到恢复。这个平台就是爱和繁殖的平台,在其中主体性被置于这些运动的功能之中。”(TI 253)显然,这部分内容对莱维纳斯来说极为重要,因为一方面他在这里似乎要进一步说明面对“他者之脸”的种种伦理可能性的秘密来源;另一方面“他者之脸”尽管重要但并非莱维纳斯论述的终点,通过“爱欲”与“繁殖”,莱维纳斯指出了超越“死亡”的向度,标识了一种指向“未来”的时间。同时,这一指向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对于超越传统以个体为本位的哲学非常重要。
一、关于“爱欲”问题
事实上,我们在莱维纳斯早期哲学中已经见识过他关于“爱欲”的分析,“爱欲”被他视为与他者关系的原型,上述的一些概念也曾在早期哲学中出现过。但这些概念在早期著作中表现得很不充分,还只是一些线索,不过却已经见证了“爱欲”问题早已在其现象学视野之中④。应该说,这些主题只是到了《总体与无限》中才得以完成,并显现出其政治的意涵。在《总体与无限》中,莱维纳斯将“爱欲现象学”置于全书最后一部分,就是为了在一个更完整的体系中加以更深入的分析。
“爱欲”问题为什么那么重要,笔者以为可以从内在与外在两个方面来考虑:就外在因素来看,一是针对海德格尔的,海德格尔以“面向死亡”作为此在存在的必然环节,在莱维纳斯看来,死亡决不是生存的绝对限制,他借用《圣经》诗篇中的“爱比死亡更有力”的比喻,来说明“爱”之于生存的重要意义,与其说生存的特征在于“有限”,不如说在于“无限”,是“爱”使有限的主体具有一种开放性和无限性;二是针对萨特的,萨特在《存在与虚无》对“爱欲”问题同样作了细致的论述,萨特将自我与他者的“冲突”关系具体化到“爱欲”的论述中,并以极端的施虐和受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也是莱维纳斯所要批驳的,在他看来冲突不是与他者的本真关系,爱是一种既“享受”,又超越享受指向“未来”的活动。这正是莱维纳斯与海德格尔和萨特对立的地方。
就莱维纳斯哲学的内在方面来看,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领略“爱欲”的意义:首先,当强调“爱欲”是与他者的关系时,正如我“在家”遇见女人一样,她打破了“我”的孤独性,帮助人处于面对他者的层面,尽管这种关系始终低于伦理层面,显示了某种自然性,同时也显示出某种超越的可能性⑤;其次,就“爱欲”的自然性而言,“爱欲”强调专注于“享受”,它处于自我“需要”的层面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停留在自然“需要”的层面,而低于形而上的“欲望”⑥,是一种非社会性的关系,他称之为“相爱的人们在社会中的非社会关系”;其三,就“爱欲”的超越性而言,恰恰是在这种“自然性”的关系中,他借助“爱欲”引发出新的“超越”向度。“爱欲”的独特性在于“同时达到他,超越他;同时是需要和欲望,同时是色欲和超越。”(TI 255)这“超越”也就是他所说的“繁殖”,它昭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爱欲”恰是这超越的基础,一方面她是趋向“尚未存在”(not yet)的未来的动力和保障;另一方面,她指向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也即显示出其政治的意涵。“爱欲现象学”是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起点,因此,莱维纳斯不能不花浓重的笔墨来论述这一问题。
“爱欲”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在莱维纳斯的叙事中,“他者”指称的对象是神秘而多变,曾经指向过死亡、上帝、善性、他人等等;在对“爱欲”的分析中,莱维纳斯所谓的“他者”则被具体化为“女性的他者”(femininity)。在此,莱维纳斯很明显的是以男性为立场来言谈女性他者的,这一立场曾受到女性主义者们的诟病⑦。
在此之前,他者的形象是一张召唤道德的“脸”,莱维纳斯更多的是用“陌生者、孤儿和寡妇”来表示。在《总体与无限》的第二部分中,也曾经出现过作为女性的“她人”,“她”具体化了“居住”的概念,她是“在家”概念的一部分。莱维纳斯的“我”从世界元素中诞生之后,他首先遇到的就是有性别的她者,也就是“女人”。由于“女人”的出现,“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就不只是自然的关系,虽然还没有达到社会的关系。这中间地带就是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不过莱维纳斯依然偏向于将其置于我的“经济性”中,在那里“女性的他者”帮助我退缩在我的世界中。这里“女性的她者”不是通过她的“脸”来表达的,她甚至不需要说什么。这个“女性的她者”只是代表了“谨慎”和“欢迎”,她是在“经济”的世界中唯一欢迎我的他者。
在《总体与无限》的第四部分再次出现这“女性的她者”,意义则有所不同。“她”出现于“他者之脸”之后。她不同于他者之脸,尚没有显现出任何的伦理意义,而是被描述成一种非道德的力量;一种脆弱的、娇嫩的同时却是放荡的形象,这样一个女性的他者显然不是道德呼唤的源泉。而“爱”既是去怜爱这娇嫩脆弱的身躯,同时也是深入其中的放荡。在莱维纳斯对于“女性”的描述中,显示出某种神秘性。他突出的是对于“女性的他者”是不能用知识性来加以把握的,被爱的女性显示了某种隐藏的本质,以及不可被把握的特质,莱维纳斯在早期曾称之为“谜”,这恰是莱维纳斯强调“他者”时所特别看重的特质。
莱维纳斯对“爱”的这种理解,与黑格尔在“爱”的问题上有着某种非常不同的看法。在黑格尔在早期神学著作《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曾提到“爱”是融合的途径。但就“爱欲”而言,莱维纳斯坚决反对这种“融合”的观点,他认为是“一种错误的浪漫观点”(EI 66)。他强调,即使在“爱欲”中,他者也仍旧是他者,我也不是完全地忘我。通过“爱欲”,他强烈地表达了“爱欲”的相异性,而“女性”恰恰说明了“相异性”概念的起源。但在另一个意义上,我们还是在莱维纳斯关于“爱”的论述隐约看到某种辩证综合的影子,这就是莱维纳斯既把“爱欲”看作一种自我享受,又将其看作一种超越,“爱欲”是两者的结合。当一个男性的“我”出于欲望趋向一个女性的被爱者时,这既类似于感性的“需要”,又类似于形而上学的“欲望”。我们看到,莱维纳斯在其哲学中区分了“需要”和“欲望”,其自我的“经济性”与他者之“脸”的篇章分别对应于这两种不同的关系;现在在“爱欲”的问题上,莱维纳斯试图将过去分离着的“需要”和“欲望”结合在一起。
二、关于“爱抚”的描述
那么在“爱欲”中如何触及女性呢?莱维纳斯通过对“爱抚”(caress)的现象学描述来确立“爱欲”的关系。在他看来,男性是通过“爱抚”来回应“爱欲”的召唤。“爱抚”的特质在摸索一种永不能被捕捉到的神秘对象。“爱抚”的现象学意义在于,一方面它是感性事物,另一方面却超越感性事物。这一点与他对于“脸”的分析十分相似。一如他强调“他者之脸”不是一种认知对象,这里他也强调“爱抚”不是一种知觉对象。因为在知觉中已经包含了理解和领会,这些都属于传统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范畴,是追求“同一”,抹杀“他者”的伎俩。他认为,“爱抚不在于捕捉到什么,而在于它引诱某种东西不断从自己的形式逃向一种未来,也不只是未来;在于它引诱某种溜走的东西,就好像它还不存在。爱抚在探求,在搜寻。它不是一种显露的意向性,而是一种探寻的意向性,是一种朝向不可见事物的运动”(TI 257)。这就是莱维纳斯对于“爱抚”的界定,他特别指出了“爱抚”意向性的特殊性,“爱抚”试图表达爱,但又无法说出;渴望表达,一种不断增长的渴望,这是“爱抚”的一个基本的特性,它把男人引向女性。
通过“爱抚”的分析,莱维纳斯引伸出“身体”这个概念,“在爱抚中,这种关系一方面还是感性,但身体已经剥去了它自己的形式,奉献自身为爱欲的裸体。在肉体给予的柔软中,身体退出了一种存在者的身份”(TI 258)。这个“肉体”指的是女性的身体,莱维纳斯在其中想继续捕捉某种特殊而隐秘的东西,以供他作现象学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莱维纳斯强调在“爱抚”中人从其存在者的身份中退去,那么随后呈现的又是什么呢?
莱维纳斯强调的是女性的“贞洁”(virginity):“被爱的女性,是可被把握的,但在其裸体中又是未受触摸的,这超越了对象、超越了脸,也超越了其存在,而保持其贞洁。女性本质上既是易被侵犯的又是不易被侵犯的,‘永恒的女性东西’就是处女,或者是一种贞洁的不断再次开始,是在与肉欲(voluptuosity)的接触中不可触摸的,是在现在中的未来”(TI 258)。在莱维纳斯对与女性爱欲关系的暧昧描述中,突出的却是女性具有不可侵犯的“贞洁”。通过“贞洁”这个概念,莱维纳斯强调的是“她”之不可被我完全支配和占有。我们知道,在莱维纳斯对“脸”的分析中,他强调他者之“脸”对于“我”的抗拒性;这里他则强调她者“贞洁”的不可被剥夺和不可被把握,这同样是对“我”的抗拒。莱维纳斯通过这个“概念”表明:即便在“爱欲”最亲密的关系中,“女性的他者”依旧是不可被把握的,“贞洁”阻碍着女性被彻底的把握。
莱维纳斯说:“被爱的女人对立于我,不是作为一种与我争斗的意志,也不是屈服于我,而是作为讲真实言语、无责任的动物性与我对立着。被爱的女人返回无责任的幼年阶段——俏丽的头、年轻、纯真的生活,‘有些傻’退出了她作为人格的身份。脸消褪了,在无人称的、无表达的中性中,通过暧昧,而延长到了动物性。与他人的关系在游戏中发生,——与她人的游戏就像是与年幼动物的游戏”(TI 263)。这里,莱维纳斯提出了一种不同于“自我”存在的逻辑,这个“她”不是作为另一个自由意志来对抗我,或屈服于我;这里的逻辑是,“她”低于我,这“低于”意味着在两人世界中形成了一种抗拒社会公共关系的“亲密性”。“在肉欲中建立起来的爱人关系,根本上抗拒着普遍化的力量,是与社会关系完全相反的。它排除了第三方,留下的是亲密、是两人的孤独、封闭的社会,是最大程度的非公共性。女性是与社会相抵抗的他者,她是两人世界、亲密的世界,是没有语言的世界”(TI 265)。正是这种亲密的关系才会蕴育出新的可能性。
“爱欲”不是存在的逻辑,即不是在经济世界中“我”对于事物的支配;也不是伦理的逻辑,即确立我为伦理主体的“他者之脸”。在“爱欲”中,他者的裸露与“他者之脸”呈现出相反的意义。我们知道,“他者之脸”本质上是一种表达,他渴望着我的回应或者说是我的责任;而“爱欲”的裸露取消“脸”所具有的表达能力。“爱抚”开创了一种超越“能动”与“被动”的东西,在暧昧中形成一种浑然的东西。“爱欲的裸体是一种反转的意义,是一种错误指称的意义,明晰转向了激情和夜晚,是停止了自我表达的表达,是放弃表达和言语的表达,是消失在沉默的闪烁其辞中的表达,它预示的不是一种意义,而是展现”(TI 263)。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莱维纳斯早期通过对于黑夜的描述达到对于“存在一般”(i1 y a)的理解。存论述“爱欲”时,他再次诉诸“黑夜”这一意象。我与女性他者的“爱欲”关系将使我们再次沉没于“黑夜”中。如果说他者之“脸”使我具有伦理的责任,那么“爱欲”似乎是破坏性的,它造成了对于社会关系的破坏而重新进入两人世界。但问题是,这里的两人世界并不受存在逻辑的支配,沉没于“黑夜”也并非单纯地回到il y a,而是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一种新的超越,莱维纳斯称之为“繁殖”。
三、关于“繁殖”与“跨实体化”
莱维纳斯关于“爱欲”的论述强烈地吸引着现代女性主义的极大关注,从第一代女性主义者波伏娃开始,女性主义者们就热衷于谈论莱维纳斯的观点⑧。尽管莱维纳斯对于爱欲现象学有着非常深入动人的描述,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莱维纳斯论述“爱欲”并不仅仅局限在“爱抚”上而是有着多重意涵,他指向“繁殖”、“子女性”、“父性”和“兄弟之爱”等概念。这一点在笔者看来非常重要。西方自近代以来,“主体”这一概念从来就只局限于“个人”,无论是人生的意义,还是任何社会化的建构都建基于原子化的个体之上,但“繁殖”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父性”、“兄弟”等概念,却让人看到了超越西方个体主义主体观的希望。据笔者的理解,前面我们看到的是莱维纳斯从横向的角度来探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甚至“爱欲”关系也只是一种与女性他者的横向关系;但以这种横向关系作为一种基础,“蕴育”了一种新的,以纵向的角度来理解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那就是与下一代的关系,这非常关键。莱维纳斯有三重重要意义寄托于这纵向的与他者关系之中:其一,是“超越”的意义,生命存在的意义有时并不只是在当下建立的,并不只是局限在个体之中的,它可以通过下一代来传递;其二,是“时间”的意义,在“爱”中期待一种“尚未存在”的未来,那就是“一个儿子的诞生”,莱维纳斯展示了“生存”中超越海德格尔式面向“死亡”的“未来”;其三则是“政治”的意涵,在共同的“父亲”下,“兄弟”之间建立起来的平等关系,这不是现代社会在抽象个人之间确立起来的那种平等关系所能涵盖的⑨。
因此,莱维纳斯的“爱欲现象学”并非止步于“爱欲”本身,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男性在“爱欲”中期待着“尚未存在”的东西,那就是“孩子”,甚至更明确地说是“儿子”。严格说来,关于“繁殖”的论题,才是莱维纳斯这部分内容的关键⑩。事实上“爱欲”问题只是整个“超越脸”的一个起点,这个过程将由“繁殖”来完成的,“爱欲”的超越向度最终是依赖“繁殖”来完成的。但所有这些关系,都必须首先通过与女性的关系才成为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讲,将《总体与无限》最后一部分的主题定位为“爱欲现象学”是不够充分的,他有一种更高的指向而且有着极深的政治意涵。
莱维纳斯认为“繁殖”的意义在于其有超出仅仅“在存在上雕刻”的可能性(EI 70)。也就是说,“繁殖”有雕刻“尚未存在”东西的可能性。通过“繁殖”可以使“超越”问题有一个现实的和具体的维度。正如他所说:“儿子正是无限性的一种具体化”。通过自我与“爱欲”的中介“出生”了“儿子”;于是就出现了“儿子”与“父亲”的关系。他强调:“父亲”与“儿子”的这种纵向关系既是一种与他者的关系,又是一种与自我的关系。“我不拥有我的孩子,我是我的孩子。”他称之为同一性中的二元性。父亲的自我所面对的相异性就是他自己的,但这种自己性并不是一种占有,一种财产,一种他所谓的“经济性”。“子女”代表的可能性虽然不就是父亲的可能性,但在某种意义上却仍然是父亲的可能性。这一点非常奇妙,这在整个西方传统哲学中从来没有被考虑过,却被他点化出来。父子关系给伦理关系带来了无限时间的向度,也带来了真正的超越。这种超越不单单像“脸”那样,强调其空间上的“无限”,是一种“外在”性的侵入;而是强调在时间上的“无限”。因为莱维纳斯把“孩子”视为“未来”。这样有限的“我”通过“繁殖”打开了“无限的时间”和“绝对的未来”。“孩子”虽然不是我,但却是我的超越。
在莱维纳斯早期哲学中,他强调“我”对于超越的经验,也就是自我在il y a升起的过程,他称之为“实体”(hvpostasis),其实质是一个“实体”或一个“位格”的实现过程。这里,他提出了另一个新的概念,叫做“跨实体化”(transubstantiation)。“我完全地爱只有当他者爱我,不是因为我需要他的承认,而是因为我的肉欲在他的肉欲中快乐,是因为在这种未曾有过的同一性的联结中,在这种跨实体化中,同一与他者不是统一,而恰恰是产生了孩子。这超越了任何可能的筹划,超越了任何有意义和有智能的力量”(TI 266)。“跨实体化”是莱维纳斯杜撰的一个术语,指的是爱人出生的孩子。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种时间关系,在爱的结合中经验着一种“尚未存在”的未来,在“跨实体化”中显示自身为一个孩子。海德格尔通过“筹划”指出“未来”;但孩子是不能筹划出来的。“父”与“子”不是一种“筹划”关系,也不是一种可能性的实现,而是有着某种不确定性。对于父亲而言,儿子既是自己的,同时也是一个陌生者。儿子对父亲来说既意味着一个未来,但又不是他所能占有的(11)。这种超越既在其中又是超出其外。莱维纳斯一再强调,我就是自己的儿子,在存在论中,这意味着“我”存在于儿子中,意味着“我”在儿子的实体性中继续存在着。由此说明“自我”在“儿子”这个他者中的超越和延续。恰恰是这种关系,他称之为“父性”,“父亲对于儿子的爱在他与他者的唯一性之间形成了唯一可能的关系。”
这其实涉及的是一个时间性问题,是实体之间的跨越代际的问题。如果说,在“逃避存在”的过程中,实现的是从无边的“存在一般”中实体化的话,那么在“爱欲”的过程中实现的则是“跨实体化”的过程,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是一种新的、物质性的对无限的看法。“超越就是时间,就是走向他人。但他人不是一个终止。他并停止欲望的运动。欲望所欲望着的他者再次成为欲望,向着超越着的他人超越的超越——是跨实体化,是父亲所进行的真正冒险。通过这种冒险让人有可能在主体无法避免的衰老中超越可能性的简单更新。超越、为他人,与‘脸’相关的善,构成了更深刻的关系,而产生繁殖的繁殖完成了这种善。这就是孩子的怀胎,给予力量的‘赠予’,超越了赠予时所作出的牺牲”(TI 269)。这也就是伦理中的时间观念,它带出了时间的一个新向度:未来。事实上,不是“爱欲”,而是“繁殖”建构了一种新的时间观,“在繁殖中与儿子的关系并没有在这种封闭的光和梦,在认知和权力中保持我们。它清楚地表达了一种绝对他者的时间,正是他的实体的改变,——他的跨实体化”(TI 269)。这里我的时间没有改变,但是它蕴育了另一种时间。这里他者的时间对于父亲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于父亲来说,儿子既是他的有限性的表示,又是他重生的表示。父亲对于死亡迫近的经验一下子被儿子诞生的经验所改变。
通过“脸”,我对他者有一种伦理性的关系,是对存在关系的超越,是无限对于存在的一种切入。莱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中一再强调对“无限”的欲望,在此这个问题再次成为主题,对“无限”的“欲望”在“繁殖”中,通过作为“未来”的孩子,通过对自己生命的超越而无限持续下去。“繁殖”通过他者与“我”的一种辩证法完成了“超越”,欲望成了无止境的事物。他这里显然针对的是海德格尔对于此在的有限性的论述,针对此在的“向死而生”所做出的反抗。主体因为年老而走向死亡,由此陷入了海德格尔所说的“有限性”中,但莱维纳斯的“繁殖”超越了这种有限性。“繁殖继续着历史,而不会产生旧的时代。尽管无限时间不能带给老去的主体带来永恒的生命;但通过跨越代际的不连续性,通过孩子无尽的年轻来给生命标点,这样更好”(TI 268)。如果说,海德格尔以“死亡”作为理解生存的极限的话,那么莱维纳斯恰恰是以“生”为理解生存的可能。这里的“生”不单单是一个生存的概念,更是诞生和生养的意思,恰恰与汉语“生”这个词中所蕴涵的诸种涵义相吻合,首先强调的不是生存的概念,而是生育和养育的概念,这是在理解生命问题上的根本不同。
非常有趣的一个情况是,莱维纳斯自己也承认,“爱欲”、“繁殖”、“父性”等都是一些非常生物化的概念,有某种非常强烈的自然化描写嫌疑(12)。对此,菲力普·奈蒙(Philippe Nerno)曾问他,这种论述是否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学上的偶然,或只是一种生物学上的诡计?他的回答是,正是人的存在论的结构显示出这些特点(EI 70)。莱维纳斯视之为超越存在的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结构,他认为这是存在论意义上繁殖的“原型”。借助于此,我们展示的是自我与他者的某种特殊的存在论结构,而且在这种结构中展示出“超越”的可能性。因此这既是一种生物关系,又超越生物关系。一方面似乎是后退了,是把“爱欲”、“父性”、“拣选”、“子女”、“兄弟”这些亲情化的主题硬加到伦理上面,使伦理问题亲情化了;另一方面则是向前了,在这些的基础上,莱维纳斯走出单纯的伦理层面,试图重新建构社会存在的基础。可以说,这是从伦理到社会生活的一个过渡。这也是莱维纳斯式伦理必须面对的问题,“爱欲”问题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跨过这一裂缝。
四、“兄弟之爱”与社会关系基础的重构
当莱维纳斯通过“繁殖”的概念而提出“父子”问题时,其所涵盖的内容已经非单纯女性主义论题可以概括,莱维纳斯进而以“父性”、“兄弟之爱”和“拣选”等概念重构社会性的基础,这是其哲学中非常有意思的思想。这里,莱维纳斯借由“父子”问题,让其某种带有生物性倾向的论述重新转向为伦理的和政治的解读。换而言之,他要借助这个论题,从亲情的层面跳越到更广泛的范围,跳越到部族和民族的层面。他说:“这种诉诸过去的做法,儿子在他的我性中与之破裂,将民族与连续性中分开界定,这是一种恢复历史线索的做法,具体在家庭和民族中。”(TI 278)
我们知道,近代哲学强调以个体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关系,努力破解传统的父权政治或君权神授的思想(13),而莱维纳斯在这里的努力则反其道而行之,在以他者问题解构了现代的个体主义之后,试图建构某种以父性和兄弟为基础的政治结构。用家庭概念来说明社会关系的基础,重新揭示出社会性平等关系的伦理根源,这一点尤为值得我们探讨。尽管莱维纳斯一再强调,这不是纯然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关系,而是一种隐喻,但在这种类似于对于家庭关系的分析中,莱维纳斯引伸出了现代的社会性关系,这非常不同于现代抽象的个体主义论证模式。其间的关系可谓错综复杂,但莱维纳斯处理得比较简洁。
在“儿子”与“父亲”的关系中,莱维纳斯展现出了这种关系的社会意涵。如果说,与“女性”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使我们脱离社会,并沉没于“黑暗”之中的话,那么与“儿子”的关系则完全不同,它意味着一种向未来的敞开,同时也意味着进入某种社会关系。需要注意的是,“父性”之于“儿子”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自我通过与儿子的关系有一种超越和延展的关系;另一方面,父亲的存在是兄弟之间关系的一个“中介”,也是兄弟之间平等关系的一个保障。因此,莱维纳斯迅速从“父性”这个论题转向了讨论“子女性和兄弟性”。从父亲的经验转向儿子的经验。
由此莱维纳斯从“父性”这个概念过渡到“兄弟”这个概念,以此说明兄弟间的平等和兄弟之爱,并进而引伸到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首先,莱维纳斯认为,“兄弟之爱”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他者之脸”所打开的伦理关系,“兄弟之爱正是与脸的关系,在其中,我的平等与选择,也就是由他者对我行使的支配,被同时完成了”(TI 279)。莱维纳斯毫无顾忌地认为,他者之“脸”所打开的伦理向度完全可以和“兄弟之爱”相一致。“人类的我被置于兄弟之爱中:人人皆兄弟,这不是作为道德征服而强加于人的。它形成了人的‘我性’(ipseity)。因为作为我的我的位置是在兄弟之爱中形成的,由此‘脸’才可能作为脸而显现在我的面前。在兄弟之爱中,他人必然显现为与所有他者的团结关系,在兄弟之爱中,与‘脸’的关系构成了社会秩序。但是,所有对话都涉及的第三方使我们——或者是党派——包涵了面对面的对立,而且使‘爱欲’面向社会生活”(TI 279—280)。也就是说,“他者之脸”之所以具有伦理意义,其隐秘的基础在于“兄弟之爱”,之所以面对他者之脸,我们能够肩负起道德的责任,起码在这里,莱维纳斯把其根源赋予了“兄弟之爱”这个概念中,他使兄弟性成为伦理上欢迎他者的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兄弟之爱”的概念,兄弟之间的关系延续到了对于整个人类的责任(14)。在家庭内的兄弟关系一下子就置于家庭之外了,由“兄弟之爱”引伸到社会秩序上去。莱维纳斯关于父性和兄弟性的探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个体责任和社会存在交叉融合的模式,这完全不同于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模式,却有着很强的东方色彩。
人类的团结、普遍的平等、社会的秩序都已经预设了在普遍“父性”的形式下的人类的社群。所有人类的兄弟之爱,不仅是社会的基础和条件,而且也是在面对面中实现善的条件。莱维纳斯用“兄弟之爱”代替个体的平等作为社会基础的意义在于:如果个体只是种和类的一个例证,个体在这种框架中势必湮没在总体之中,而不能保持个体与人类父母之间的相异性和相关性,这样人类就成了一个互不关联的原子集合体;而莱维纳斯认为人类是一个由兄弟构成的大家庭,他们都来自于共同的父亲。由共同的父亲构成了他们的统一体,但相互之间又是有差异的,而不是普遍本质中的一个例证。既不是面对面的两人关系,也不是群体中的一员,而是唯一的、独特的兄弟组成的共同体。
在这一论述中,莱维纳斯从面对他者之伦理关系,过渡到了兄弟平等之社会关系上去了。从这里我们看出,莱维纳斯式社会生活起源于伦理。他认为,现代政治被认为是对立于伦理的,被认为是暴力的和自我主张的,被认为是存“计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他则要在伦理基础上重建政治。他要论证在人的状态中已经蕴涵着兄弟之爱,这恰恰是新的政治基础。“人的状态蕴涵了兄弟之爱和人类的观念。兄弟之爱的概念彻底地与相似性构成的人性概念对立,不同家庭的多样性来源于丢卡利翁扔的石头,这对立于人的自私,而形成了人的城市”(TI 214),他寻求的不是一个家族的问题,而是探求保持多元性的共同体。
与他者之“脸”所产生的“不对称”关系不同,在“兄弟之爱”中则产生了某种对称性的关系。这意味着当一个“共同父亲”出现时,所有的人就都能成为兄弟,兄弟之爱就是“博爱”,就是“人类之爱”。尽管莱维纳斯强调自己只停留在现象学的分析之上,并不涉及神学,但一如显现在他者之“脸”上的神圣“微光”,暗指超越的上帝所在;对于共同“父性”之下,所有的人皆兄弟这样的论述,同样有着某种犹太神学思想的影子和嫌疑。
在《总体与无限》第三部分论述“他者之脸”时,莱维纳斯认为作为构成人类社会力量的兄弟之爱是语言(TI213)。但是这种语言组成的共同体中的对话者还是相互分离的,并没有构成一个人类整体。而这里,莱维纳斯认为事实上,人类之间其实是一种亲缘关系,不是因为他们的相像,而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起源,有着“共同的父亲”。
这之后,莱维纳斯提出了另一个具有很强神学意味的概念“拣选”。他认为“自我”之于父亲而言,我是被“拣选”的;每一个儿子都是被“拣选”的,都是唯一的,这是由“繁殖”决定的。“拣选”构成了儿子的自己性(ipseity)。由此,父亲赢得了另一个未来。在莱维纳斯那里,“父性”就是有另一种未来的人,而兄弟之爱就是与脸的关系,在其中我的被拣选和与其他兄弟的平等被同时完成(TI 279)。从儿子的视角来看,一个主体在好的权威下发现了他自己的,而这个好权威就是创造他和选择他的父亲,此外这个主体也在兄弟们中发现自己是一个兄弟。“父性是作为无数的未来而产生的,产生出来的我同时是唯一的,也是众兄弟中的一个。我是我,我是被拣选的,但是哪里我可以被拣选呢?如果不是从其他的被拣选中,在其他的平等中?”(TI 279)因此,“平等”概念也从“拣选”中引伸出来。他认为“平等”乃政治生活中最为首要的特性,这发端于“兄弟性”的关系中。
“拣选”的概念来自于圣经,亚伯拉罕是被上帝“拣选”的,以证明他的信仰。在莱维纳斯的访谈中,他并不讳言他在现象学的框架下来研究犹太人的圣经经验。如何理解这“拣选”呢?“拣选”的自我发现自己在其他被拣选人中的结构是问题的关键。一方面,我是享受、需要和劳动的主体,是自足的;但另一方面我也与选我的人有关系,我与他是被造物与创造物的关系,我是被选的。同时,我作为被拣选的,同样发现被同一个人选择的其他人,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与被选兄弟的关系,也是一种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模式。这里,兄弟性被理想化为“我们”,在其中我服侍他者,也为他者所服侍。莱维纳斯的“我们”这不是海德格尔式“肩并肩”的我们,而是兄弟般“面对面”的我们,从“面对面”的关系中产生出社会关系,而不是从生物意义上断言所有的人都是兄弟(15)。
至此,莱维纳斯的“爱欲现象学”告一段落。由此可见“爱欲现象学”并非当代女性主义者们所热衷的那样只局限在男女问题上,而是有着多重的维度。尤其是通过父子的关系揭示出人类兄弟关系的实质,以及这种关系之于政治的基础地位。由此展现了破除西方原子个人主义之后,现代政治重新建构的基础所在。
注释
①⑤ 参见拙作“‘经济’与生活世界——莱维纳斯对‘我’的现象学描述”,《生活世界理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
② 参见Totality and Infinity,第Ⅳ部分。
③ 有学者甚至质疑这一部分是后加上去的,参见Bettina Bergo,Levians Between Ethics.and Politic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9.p108;也有学者在讨论莱维纳斯这些论述时,语焉不详。
④ 参见拙作“存在,还是逃避存在——莱维纳斯早期哲学初探”,[北京]《哲学门》2001年第2期。
⑥ 在莱维纳斯的哲学中,他以“欲望”与“需要”相对立,“需要”是自然性层面的,而“欲望”具有超越的向度。
⑦ 参见cbanter,Tina.ed.Fenllnlst Interpretations of Emmanuel Levians,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1.事实上,莱维纳斯强调的女性在于其脆弱和柔嫩的一面,而不在于是男还是女。
⑧ 不同的女性主义者对莱维纳斯有着不同的评价,波伏娃批判他的男子主义立场,而克勒则赞扬他对于女性特点的体察。
⑨ 近代个体主义的政治哲学就是通过消除传统的父权制而建立起来的,参见霍布斯、洛克对于父权的批判,而莱维纳斯恰恰在某种意义上回到了以父亲为基础的政治思想。
⑩由于莱维纳斯对其准备阶段“爱欲”有精彩的描写,加之女性主义者们集中在莱维纳斯关于“爱欲”问题的论述,因此在一般的论述中,重心有所偏颇,更侧中莱维纳斯关于“爱欲”的描述。
(11) 这里的父子关系可以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比如教师和学生也可以在类似的意义来看待。
(12) 这个论题对于中国人有着特别的意义,和中国人传统的思想有着很强的亲和性,并且对于破除西方单子式理解人的问题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3) 参见洛克《政府论》,在那里,洛克对父权政治做了彻底的批判,并以现代的个体主体建构了现代的政治的基础。
(14) Bettina Bergo认为:由于莱维纳斯在这里的论述,现实暴力的人类历史早已被父亲的拣选和兄弟的侍奉所驯服,这样莱维纳斯后期所讲的“末世论”之于人类历史的意义就变得多余了。因此,在后期哲学中,莱维纳斯放弃了这一关于父与子的论述。
(15) 莱维纳斯没有探索其他角色,如母亲和姊妹。全书只在一处提到了“母性”(TI 278),但通篇没有提及“姊妹”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