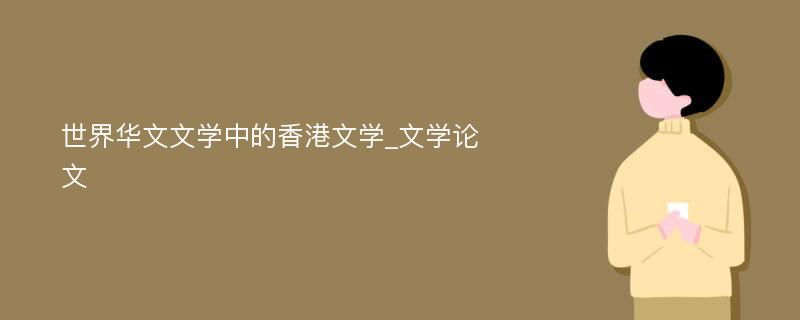
世界华文文学中的香港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世界论文,文学论文,文学中论文,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历史上看,香港文学是中华文明的延伸。关于香港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格局的一部分的观点,近年来已为学术界普遍认同,故在此不赘。我要指出的是:无法回避的时代潮流造成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和祖国大陆的隔离状态,此后,香港文学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与中国文学分流的时期,“九七”回归,使香港文学开始了与中国母体文学重新整合的新阶段。(注:有关1949年以后的当代香港文学的发展,请参阅拙文:《当代香港文学铸形》,刊于《香港文学》月刊第147期,1997年3月出版。)下面我想从世界华文文学的全球坐标的方位上探索一下香港文学的定位问题。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是一门新兴学科,从学科建设方面的轨迹来看:从“港澳台文学研究”、“台港澳文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到“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从这些名词的频繁更变中可以窥视这个新兴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之一斑。然而,无论怎么称呼,这个新兴学科,在八十年代以前是中国研究界的一个空白点和盲点。1980年,在曾敏之先生等人的推动下,港台文学研究会于广州成立。1982年6月,在广州召开第一届港台文学学术研讨会。 1986年7月初,中国文学的大同世界学术会议在西德举行。而1986 年12月26~29日在深圳大学举行的第三届年会更名为“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这表明研究界已开始以全球性的整体意识来思考中国(包括台港澳)和中国以外的华文文学。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1988年。因为,这一年的12月5日~8日,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主办了“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会前会后,会上会下,以刘以鬯先生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一开始就从世界华文文学整体格局的坐标上为香港文学定位,突出香港文学特有的优势。刘以鬯认为香港特殊的历史和地理条件是其他华人地区不可能取代的,它在沟通海峡两岸文学和世界各地文学的交往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刘以鬯提出应该在香港成立一个世界性的华文文学协会,推动各地华文文学的交流和发展。(注:详见香港《大公报》1998年12月11日星期日增刊上所刊出的陈培笙的《香港文学具有三大特色》一文。)台湾李瑞腾先生认为,随着“九七”的到来,与内地的文学交往日渐增加,建立一个以香港为中心的世界华文体系的意念应该逐步形成。他指出香港文学已有自己的传统。各地区的华文文学可以在这里尽心对话,它有条件和能力去检验各地华文文学的成就。(注:详见香港《大公报》1998年12月11日星期日增刊上所刊出的陈培笙的《香港文学具有三大特色》一文。)
我认为,所谓世界华文文学的核心不是华文,而是文化,也就是华人的文化。因此,华文文学实质上应该是代表华人文化的文学,正是世界各地代表华人的文化的文学共同组成了世界华文文学这个球形的立体结构,作为软组织部分的文学,都受制于球心的那个文化内核。我觉得葛浩文教授的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中国作家,包括国内外的汉学学者,一般关心的应该不是语言问题,而是作品里表达的情感、内容与精神内涵:只不过他们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举例来说,一般提到法国文学、英国文学,主要是以‘文化’为主,而不是‘文学’,不是光分辨它‘用什么语言’来写。所以当人们说到ENGLISH LITERATURE,我们立刻的反映是‘英国的’,而不是‘英文的’文学。 (美国文学也用英文)。”(注:引自台湾《文讯》革新第48期82页。)
因此在世界华文文学的球体结构里,香港华文文学的确切含义应该是代表香港地区华人文化的文学。
香港文学的定位,实质上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和世界华文文学的全球格局的双重制约下的定位。值得注意的是在双重格局制约下的香港文学,无论是在中国文学还是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格局中,它都是一个独特的形态。所以,当美国、欧洲和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华人作家为华文文学难以进入当地国家文学主流而苦恼时,香港文学在文化传统、文题范式和文学精神等方面,从来都认同于中国文学母体,它对自己的生世毫不隐讳——它是中国文学的延伸,偶然的分流,是暂时的;必然的整合,则是它的归宿——它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一章,特殊的一章。
我认为,以独特形态为标志的当代香港文学的模式是香港文学在双重格局——特别在世界华文文学的球体结构中——角色到位后的产物。换言之,是香港文学与中国与母体文学暂时分流时期的产物。由于历史的原因,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和祖国大陆呈现隔离状态,香港文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游离于中国文学发展轨迹的分流时期,香港文学在保存母体基本素质的同时,又在这特殊的时空条件下形成了它自己独特的文学新质:“香港性”。香港的社会风貌、港人的思想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中西文化碰撞所产生的火花……等等,都是这一文学新质(“香港性”)的重要内涵。正是在这分流时期,香港文学以自己特有的形和质定位于世界华文文学大文学圈格局之内。
香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伸延,源远流长。开埠以来,不仅东西文化在这里互相碰撞、渗透、交融,而且,各种文学形态多元并存。“分流”之前的丰富多彩的文学现象是中国文学宝库里的珍贵财富,而“分流”之后的“香港性”的特征是香港文学在双重格局里定位的依据。由于文学的“香港性”的形成是文学内部运动的产物,有其发生发展、开花结果的过程。
有的评论家认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香港只有南来的作家、移民作家和难民作家以及他们所创作的“移民文学”、“难民文学”,而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香港文学,充其量只能称是香港的文学。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阳》和《樱子姑娘》、徐于的《江湖行》、李辉英的《乡村牧歌》、端木青的《故国的春天》等作品,因为所写的人是中国内地移来的,故事的背景也是中国内地,所以,被认为是“移民文学”。在这些“旅港作家”所创作的作品中,“对香港的环境若缺乏投入感创作小说时,就算以香港作为背景,亦一样缺乏香港的色彩。”(注:请参阅黄康显的《香港文学的发展与评价》,秋海棠文化企业出版社,1996年4月5日。)什么是“投入感”?这是一个很朦胧的概念,作为一个文学的判断的标准,在操作上有许多许多难以逾越的困难。我认为,移民文学不仅是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若回到文学作品的原生现象上来看,那些反映移民心态、移民生活的作品,往往有很浓郁的香港色彩,香港性。不要忘记——香港本身就是一座移民城市,真正的“土著”有多少,不过是移民时间的先后罢了。
上述论者对文学的“香港性”的标准是相当苛求的:即使以香港生活(人和事,以及环境)为描写对象,但如果缺乏对香港命运的投入感,也仍不具有文学的“香港性”。这是很难使人认同的,因为若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文学的“香港性”的高扬只能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九七”回归的“过渡期”。
政治冷感曾是八十年代以前的香港人在商品社会的生活方式孕育下所形成的思想观念和和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1979年香港回归问题提出,香港人沸腾起来了,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主权回归的“过渡期”。在这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是香港文学的香港色彩最灿烂的日子,也是香港文学的“香港性”高涨的时刻。
如果说,在“九七”问题提出前,香港的文学是以“移民文学”为主的;如果说,“对香港环境”“缺乏投入感”是“移民文学”的通病,那么,“九七”问题的出现牵动了所有港人的心,过去以不关心政治自诩的港人,现在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 掀起了全民参与的泛政治化的浪潮,在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的驱动下,千家万户的思路都聚焦在“七九”情结这个焦点上。于是,文学的“香港性”凸现,香港文学迅速地完成了从“移民文学”到“当代香港文学”模式的过渡。正像有的论者所说:一九九七年对香港文学来说,是个重要的契机:“一、一九九七问题打破了香港与中国多年来的隔阂。……把香港命运联系到中国命运上,将是香港文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二、一九九七除了促使香港作家关注中国外,也促使他们关注香港的现实。”“三、一九九七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冲击香港人的政治冷感。”(注:引自王仁芸《一九九七与香港文学》,刊于《香港文学》月刊第1期28页。)
主权回归的过渡期的社会政治形式促进了文学从“移民文学”到“当代香港文学模式”的过渡——同时又是从“分流”形态向“整合”的过渡。所以,“过渡期”在香港文学史上就成为一个有多重含义的概念,一、对于回归而言,1984年12月19日起香港地区正式进入“过渡时期”。我们以此为据,称1984年12月19日——1997年7月1日期间的香港文学为过渡期的香港文学。二、若从文学内部运动的规律来看,也正是在上述的同一时空内,香港文学的“香港性”由量变到质变而导之从“移民文学”为主体的文学主潮过渡到以“香港性”为主体的“当代香港文学模式”,(注:关于“当代香港文学模式”的提法,黄维梁在他的《香港文学初探》和《香港文学再探》中有精辟的论述,笔者借用了他的提法。特此说明。)这是香港文学在两个发展阶段之间的过渡时期。
政治历史概念上的“过渡”和文学的“过渡”在同一时空的叠合,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时代的必然。我说两个“过渡”叠合,实际上只是宏观意义的叠合,而不是在完全相同的时空中的分秒不差的绝对叠合。因为,严格的说,从文学内部规律来看,早在《虾球传》和《穷巷》问世之时,香港文学已进入了从“移民文学”向“当代香港文学模式”的演变,但是由于以香港性(香港特色)为主要特征的作品,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寥若晨星,所以,这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演进得十分缓慢,直到“九七”回归问题的提出,1982年撒切尔夫人访华,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主权回归进入了倒计时数的读秒时刻,在“九七”回归指日可待的日子里,不同信仰、观点,不同身份、地位,不同政治态度的港人都被凝聚在“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中,“九七”情结牵动了港人的心,也牵动了文学家的良知。“九七”像一张人人都必须填写的问答卷,不管选择什么答案,限时交卷。“爱港爱国”,这是绝大多数香港人和香港作家的共同选择。不言而喻,“九七”加速了文学内部的矛盾运动的进程,催化了从“移民文学”到“当代香港文学模式”的质变。这也是政治和文学之间良性互动的一个范例。
香港人曾自讥是“经济动物”。不问政治,只知赚钱,这是众多香港人的写照。如今不同了,“一国两制”,与香港的前途,与每一个香港人的前途都休戚相关。今天的香港人,要比国内人更加关心中国大陆的政局变化、关心改革开放的国家大政方针。
进入过渡期后,香港文学涌现出许多“九七”题材的作品,作家每每以一个生活于香港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表达对国家民族和香港社会的看法,流露出对香港及中国前途的强烈关注。这些作品展示了当今香港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及各阶层民众的喜怒哀乐,它们像一面面镜子,折射出过渡期的香港社会的写真,又作为历史的见证留给后人。撰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准确的传达出香港人的心声,这是很多香港作家意识到的责任。什么“香港作家不关心政治”等等观念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即使是一些以风花雪月为题材的流行小说通俗文学,现在也常把个人和时代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倾心于“九七情结中国心”。把个人、香港、中国,三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思考,已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的主要特色。
若把八十年代以来的香港文学作为当代香港文学的一个发展阶段来认定,主要的依据是文学内部的原因,因为,不仅文学创作是这样,文学批评也是如此,正是八十年代以来香港文学批评摆脱了过去在文学批评上大多是大陆母体文学批评话题的延伸或移植,在八、九十年代,建构了以香港意识为框架的香港文学批评的当代模式。建构这个模式的立意就是香港文学对“自我”的关怀。
众所周知,在八十年代以前,无论在大陆、台湾还是香港,作为学术概念上的“香港文学”是不存在的。台湾的应凤凰在参加“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时,曾对采访者说:“几年前,台湾根本不存在‘香港文学’这个概念。”。(注:详见香港《文汇报》1988年12月9日。)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香港不存在文学,而是指学术概念(或者说是学科建设概念)上的“香港文学”,在那时,只是中国母体文学的延伸和移植,文学的“香港性”不够鲜明突出——这不等于说在这一时期不存在有鲜明的香港特色的文学,比如:《虾球传》和《穷巷》等作品就是很有香港特色的小说。
香港文学批评界作为一个成熟的学术群体,对自己文学的历史和特点加以关怀的全面启动,大致也在八十年代,1980年9 月《新晚报》主办的香港三十年座谈会是香港文学“自我”关怀的突出表现。之后,“自我”关怀的潮头接连不断:1983年5 月香港市政局图书馆主办以“香港文学”为主题的“中文文学周”演讲会;1985年4 月中西区文化艺术协会和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等合办的“香港文学讲座”;1985年4 月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的“香港文学研讨会”;1985年,著名的文坛前辈刘以鬯先生主编的《香港文学》月刊创刊,为香港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公开的园地,并先后推出“香港文学丛谈”、“笔谈会·谈香港文学”等专题;1985年11月香港浸会文社主办的“九七与香港文学”讲座;特别是1988年12月召开的“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实际上是给香港文学确定身分的会议。
作为香港文学批评界群体实力的学术标志,是他们八十年代以来陆续推出的有关香港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专著,这些著作充分表现了学术上的“香港性”特色,如黄维梁的《香港文学初探》、《香港文学再探》,卢玮銮的《香港文纵》,罗贵祥的《大众文化与香港》,王一桃的《香港文学评析》,东瑞的《我看香港文学》,黄康显的《香港文学的发展与评价》,洛枫的《世纪末城市:香港流行文化》,也斯的《香港文化空间与文学》,陈炳良编的《香港文学探赏》等等。
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的“香港性”特征的高扬,是八十年代以来香港文坛的标志性景观。同时八十年代以来香港文坛的文学价值观也进入了一个更新转型的过渡时期,关于这些问题应当另撰文论述,故在此不赘。
由此可见,八十年代以来,当代香港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从地域文学与母体文学的关系来看,两者正经历了由“分流”到“整合”的过渡,是香港文学在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和世界华文文学的全球格局的双重格局中重新定位时期;
——从文学生态环境的视角来观察,这段时期的香港文学经历了从二元对立的框架到多元并存的过渡;
——文学观念的更新转型,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的“香港性”的特征的高扬等,都是八十年代以来香港文学自身内部矛盾运动的体现。
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决定香港文学形象的标志性特征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正是文学内部的这一系列的变化,使我们认定八十年代以来当代香港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前辈们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越具有中国特色的,越具有世界意义,我想说的是,对于香港文学来说,香港性是香港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的全球格局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定位的最佳坐标。最后,我想借用当代青年流行的口语来概括自己的意思:对于香港文学来说,只有“很”香港和“很”中国的东西,才会是“很”世界的。
标签:文学论文; 香港文学论文; 香港移民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香港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艺术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移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