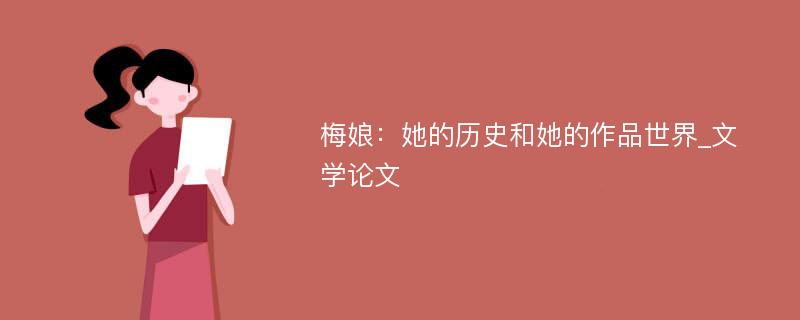
梅娘:她的史境和她的作品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品论文,世界论文,梅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曾一度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作家,梅娘便是其中之一。本文将女作家梅娘置于一定的“史境”之中,阐述并分析了她艺术世界的内在底蕴以及这一底蕴的历史成因。认为其作品中绵延不绝的顽强女性意识和独特叙事风格,正是那个社会环境与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关键词】 梅娘 史境 作品世界
在中外文学史上,一度被忽视的作家得到重新评价并引起广泛的注意,是常有的事情。作家被埋没的原因各种各样:有政治方面的,有宗教方面的,也有艺术趣味和时尚方面的。重新认识历史上的作家并将其汇入主流文学的契机,同样是纷繁复杂、形形色色的,有的时候,在历史的必然中也有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沦陷区文学现象,再一次为文学发展长河中的这一特异景观做了最好的诠释。
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后,中国沦陷区作家中的绝大多数从文坛上销声匿迹,并且被后来的各种文学史所冷落。这样的历史现实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从80年代初期开始,沦陷区作家逐步进入学术界的视野,他们的作品被人们加以重读。以梅娘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她在沦陷时期的部分旧作先后被海内外近十种出版物重新发表。沦陷区文学得以重见天日,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使然,是实事求是的时代精神使然。而沦陷区作家的优秀之作终于在近半个世纪之后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则是由他们作品所特有的构成因素所决定的。梅娘的小说在当时以及现在的接受状况足以证明,她是中国沦陷区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梅娘,原名孙嘉瑞。吉林省长春市人。1920年生于海参崴。作为封建兼资产阶级大户人家的私生子,幼小的梅娘就已经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和世态的炎凉。家庭环境造成了她的孤独、内向和敏感,同时也孕育了她那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汇总了神的、人的、东方的、西方的缤纷色彩”的旧长春,使她亲眼目睹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相;还在小学阶段又逢东北沦丧,又让她过早地体味到民族灾难带来的痛苦。所有这些,对梅娘的情感、思想以及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的作品中出现的最多的人物是战乱中的妇女,往往通过她们那坎坷的经历和悲惨的命运,展示出女人的不幸和人世间的不平。
梅娘在少女时代就显示出了她的文学才华,高中刚毕业便出版了处女作《小姐集》。1938年赴日本神户女子大学读书,1940年梓行短篇小说集《第二代》。在日本期间,她冲破家庭的阻力,与在日本半工半读的北京青年柳龙光结合,并于1942年定居北京,任《妇女杂志》编辑。作品广泛见于华北、东北和日本的报刊,先后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鱼》(1943)和《蟹》(1944)等。
在抗战胜利以后的岁月里,梅娘过着动荡、漂泊的生活。据近年来陆续发表的有关文章,以及梅娘本人的回忆,在完成中共北方局布置的特殊任务的过程中,她的丈夫于1948年意外遇海难,留下了许多“说不清的历史纠葛”。[①]这一段历史还有待于研究者用可信的史料来澄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刻梅娘带着两个幼女及腹中的胎儿从台湾返回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放弃了在台湾和日本担任教席的机会。梅娘在解放后的履历是:任中学语文教员。1949年10月加入北京市文联和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1951年调入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1952年在忠诚老实运动中被认定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而遭批判。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因经历复杂被打成“日本特务嫌疑”。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定为右派,关进劳改农场。服刑期间,13岁的二女儿在救济院中病死。1961年解除劳教,成为无业人员。在没有任何固定收入的情况下,完全靠各种粗活零工维持一家三口的生存。文化大革命期间,23岁的儿子因病夭折。1978年得到彻底平反,重返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
在这几十年中,梅娘基本上与文学创作绝缘。70年代末,她重新拿起了创作之笔。岁月的流逝和浩劫的伤痕并没有使她消沉和退缩。她那只存的女儿早已定居加拿大,她也曾于1994年出国探亲。但一年半以后,她不顾女儿、孙女的百般挽留,毅然只身返回北京。她心头割舍不下的是故土,正如她在1993年所赤诚坦露的那样:“我权衡者再,却怎么也不想离开这片我血泪浸染的沃土;我认定,只有在这片热土上,我才能体现作为中华女性的价值。”[②]这种桑榆未晚的生命观,正与和她同庚的张爱玲形成了耐人寻味的鲜明对照。两人都在沦陷区成名,据说曾被并称为“南玲北梅”,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选择和人生追求。建国初期,张爱玲出席了1950年7月召开的上海第一届文代会,在从容发表了长篇小说《十八春》和中篇小说《小曼》之后不久,去了香港,又移居美国,与美国作家费迪南·赖雅结婚。优裕自由的生活条件并没有促进她的文学创作。她后期的主要工作是改编旧作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丈夫去世之后,特别是在晚年,张爱玲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拒绝会见亲友和来访者。究其原因,推测之一似乎是,这位一生酷爱美的女作家“不想以损颜见人”。[③]结果,1995年9月8日,公寓管理人员会同警察打开几天没有动静的张爱玲的寓所时,她已过世多日,属正常死亡。南玲北梅不同的人生态度和生活道路,是由各不相同的社会环境和教养志趣决定的。这在她们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得到印证。现代主义的唯美追求,与张爱玲晚年选择自我封闭的生活方式并不矛盾。现实主义的人生艺术,必然促使梅娘深深扎根在恩恩怨怨总是情的人世间。在沦陷时期的一代作家中,这正是女作家梅娘的与众不同之处。
梅娘漫长的写作生涯跨越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两个时期。她的主要作品都是在25岁以前完成,在沦陷区发表或出版的。因此,梅娘无疑属于抗日战争那个特定历史时代。
按照常规,处于“低气压时代”的沦陷区似乎最不适宜文艺的生长。然而在上海,出现了被傅雷称之为“太象奇迹了”的张爱玲,[④]在北京,则出现了与之并称的梅娘。这个在当时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使人感到意外和难以理解的文学现象,正是那个社会环境和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随着“七七”事变前后大批文教机构和知名作家学者迁移出走,无论是从作家的人员构成还是从创作的连续性来说,都使得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文学出现了明显的断层。相对封闭隔绝的沦陷区的社会生活运转起来之后,报刊和出版业逐步兴盛,文学也开始复苏。留下来的少数作家重新执笔,更有一大批新作家崛起。过去在国内两大阵营对立和斗争的背景中形成的主流思想和主流文学,不复存在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还要延续下去。在政治立场方面,是坚守民族大义还是投敌附逆——这成了作家们无法规避的行为选择和道德抉择。此外,生存也是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书刊业的发展无疑使编辑、写作行业成了很实际的谋生手段。事实证明,沦陷区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和作家并没有屈从于法西斯的淫威,并没有丧失中国人的立场。尽管不能充分自由地表达思想,尽管不少人借纯碎的文学创作和研究聊以自慰,尽管有人以写作为出名的路径,尽管也有人想通过文学达到卖身求荣的目的,但就沦陷区文学创作的主体而言,纳入伪政权统治轨道的伪文学直至抗战胜利也没有建立起来。抗战时期曾有5年呆在中国的日本作家武田泰淳就说过,日本政府和民间作家没能为中国制定出文学纲领,中国交战地区也没有人注意日本人的毫无意义的荒谬主张。[⑤]这是由诸多因素制约和促成的。
从日本方面看,他们的侧重点主要在军事行动上,对中国沦陷区文坛的控制软弱无力。从活动在沦陷区文学舞台上的作家来看,中国新文学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历史形成的写作动机和模式,促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恪守自己的创作风格。从文学自身的特性来看,说教式的、宣传口号式的作品,在任何时代都是作家和读者两个方面难以接受的,在沦陷时期也不例外。直接贴近现实、反映抗日斗争的内容又很难面世。于是,表现内心体验、讲述身边故事、谈往忆旧的作品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对于身边的战争和战争暴行的疏离,也是对战争和暴行的一种价值判断。在中国沦陷区的战局基本稳定之后,日本的大陆思想战方针,也从战争喧嚣转变成以娱乐消遣为主,妄图使沦陷区人民逐步适应并认可殖民统治现实。但是侵略者软刀子杀人的伎俩未能奏效。张爱玲所叙述的是一件件凡人琐事,却营造出冷峻的基调、丰润的色彩,深刻揭示了欲望世界和人性。在梅娘的笔下,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华大地带来的灾难有所表露。但她主要是通过大千世界中女性生活的纷繁世相,展示女人的不幸和人世间的不平,剖析女人的生存状态及其在身心诸方面所承受的压迫,触及到婚姻、家庭、社会的方方面面。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张爱玲、梅娘的作品看似属“软性文学”之列,却没有起到消闲文学歌舞升平、麻痹斗志的作用,反而常常使人感受到战争以及战争阴霾在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中的投影。这种感受是若隐若现的,然而却是刻骨铭心的。她们在当时的成功以及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勿庸置疑的地位,正是由于她们的作品在自然恣肆地表现日常性的同时,达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共通性(Universal)。从现代文学主潮的流变来看,她们的作品的反英雄趋向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英雄主义也形成相得益彰的鲜明对照,是五四“人的文学”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形态。
可以把梅娘沦陷时期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1939年下半年以前为第一阶段。如果说《小姐集》真实地表现了一个少女内心的爱与憎的话,那么由于作者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生活面的扩展,《第二代》开始步出小姐的闺房,走向社会人生。这些作品刻意探求小说的新形式,“狂野地运用了文士所不敢用的语汇,大胆地采取了文士所不能取的题材,以她那支获有定评的笔,泼辣地描写着一群游户似的男女和一群浮浪的孩子”,使她笔下的人物具有凸出的厚重感。[⑥]而且,在刚劲的笔致中,梅娘并不乏女性的纤巧细腻与悲天怜人,而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正是她后来作品的稳定的风格特征。因此,梅娘一登上文坛就受到时人的注意,并且把她作为“直接间接对于满洲文运有着不可否认的推动的功绩的女性作家”与萧红相提并论。[⑦]可以说,较高的起点使得梅娘的早期作品就在东北沦陷区文学中占有并非无足轻重的一席之地。
从1939年下半年到1941年7月自日本到北京作短期逗留为第二阶段。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水族系列小说《蚌》、《鱼》、《蟹》。三篇作品的情节和人物之间并没有连续性,但相接近的题材和一种朦胧的女权主义思想将它们维系在一起。中篇小说《蚌》作于1939年夏。在自然界中,软体动物蚌的生存能力是十分脆弱的。小说以“蚌”为标题,暗示女主人公梅丽难以规避的厄运。作为赋闲显宦巨贾家庭“庶出”的小姐,她自然成了家庭内部妻妾倾轧争斗的牺牲品。父母把她当成能够使没落大家庭复兴的“摇钱树”。为了攀附天津巨富朱家,他们执意要她与染了一身脏病的朱少爷成亲。而实际上她正在与税务总局同事王琦热恋。祸不单行。此时,局里的一等翻译官也怀着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设下圈套败坏梅丽的名誉,使她横遭心上人出走的沉重打击。当她避开家人的监视追到车站时,王琦已经离去。纵然她有过“与其卖给一个男人去做太太,去做室内的安琪儿,还不如去做野妓,不如去做马路天使”这样的激进呐喊,但终敌不过家庭和社会构筑的樊笼。在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她的人格得不到尊重,她的意愿难以实现。留给她的是心灵和肉体的创伤,以及处于孤立无援境地的弱女子的绝望感叹:“什么地方有给女人留着的路呢?”作品有“蚌”象征沦陷区封建大家庭中的青年妇女的生存状态,为苦苦追寻自由与幸福的女人低吟着哀矜凄婉的命运之歌。
短篇小说《鱼》的主人公则向前迈出了一步。她是一个急于摆脱封建大家庭桎梏的女高中毕业生,在与一位教师的单恋破灭之后,受官宦之家的已婚纨绔子弟林省民的欺骗与引诱,与他在外同居,并生下了一个男孩。林家急于想抱孙子,便同意把她收回家中,作林省民的二姨太,以小孩为筹码宽恕儿子的放荡荒唐。已经获得某种程度自由的鸟儿是不会再飞进另一个令人窒息的鸟笼中去的。她决不就范,准备拼死抗争,正如她自己所说的:“网里的鱼只有自己找窟窿钻出去,等着已经网上来的人再把它放在水里,那是比梦还缥渺的事,幸而能钻出去,管它是落在水里,落在地上都好,第二步是后来的事。若怕起来,那就只好等在网里被提出去杀头,不然就郁死”。然而女主人公把“落在水里”的希望,仍寄托在婚姻之上。她再一次无所顾忌地追求与她感情暧昧的另一个有妻室的男人——林省民的表弟琳,以满足她生理、情感乃至安全感层次上的需求。琳懦弱地退避了。固然,性爱自由的程度,是显示妇女解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如果把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约束的婚姻当作抗争的唯一手段,妇女的解放与妇女的独立人格,是难以实现的。作为水生脊椎动物,鱼的生存能力并不比蚌大多少。标题“鱼”同样意味着,采用这种方式向传统社会挑战的妇女,其境况是岌岌可危的,而且在现实中往往会碰壁。
作者似乎朦胧地觉察到这一点。因此,她有意识地把《蚌》中本不该走投无路的女人,带到《鱼》里,但仍感到后者也“没能表示出我心上的郁结于万一——一种女人的郁结”。于是,她便把她的“女人的郁结”转移到另一部中篇《蟹》里。后者脱稿于1941年4月,写出了作者自称的“一点可憎的爱”。小说中的主人公仍是东北沦陷区一个大家庭里的小姐,但与前两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有了质的差异。实业家孙二爷过去靠与俄国人做买卖发了财。在他死了之后,为了争夺家族财产,兄弟妯娌之间明争暗斗,手段毒辣,甚至不惜寻求日本人的庇护。小女儿孙玲看不起家庭中的那些险诈庸碌的成年人,更痛恨时局的突变使她失掉去北平读书的机会。她不顾家人的恫吓,拒绝焚烧已故父亲留给她的俄文书。最后,这个与趋于崩溃的大家庭和专制腐败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的少女,终于决心离家出走。与蚌和鱼相比,节肢动物螃蟹要强大得多。因此,《蟹》中的女主人公脱开了企图借婚姻达到自由的幻想,更具有政治头脑和实践精神。
这三篇小说与梅娘及其创作的关系非同寻常。在作家传记的层次上,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与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和环境十分相近,特别是第三篇《蟹》,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的社会存在的痕迹。在作品主题的层次上,通过沦陷区传统宦商封建大家庭青年女子的命运,探索了寻求独立与自由的女性的三种境况:在社会和家庭的播弄倾轧中心力交瘁,前景大约只能是束手待毙(《蚌》);在家长制和封建贞操观编织的有形的和无形的“鱼网”面前,带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色彩的反叛女性,往往最终仍在经济拮据和情感苦闷的双重压迫下苦苦挣扎(《鱼》);与破败的旧式大家庭彻底决裂,大胆地走上新的生活道路(《蟹》)。在作品现实寓义的层次上,《蚌》揭露日本的“经济统制”政策使白公馆这样的大户都陷于衰败:“烧锅,粮囤昨天给贴封条了,存粮不许卖,都得归组合”,简直没有了活路;把在大街上撒酒疯调戏中国妇女的人,描绘为“舌头不成形的卷动着,生硬地操着当地的土语”,显然是在暗指日本人;……这些大胆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殖民统治和民族压迫的强烈不满。而在《蟹》中,更出现决定出逃的女主人公看到落日而受到鼓舞的场面。对此,美国学者耿德华曾有过细致的阐释:日方宣传人员“总是把朝阳作为他们国家的象征,而梅娘却选择落日来象征希望。因此,此举如果不是实际上抑制日本人的宣传主题和信条的话,至少是一种明显的冷淡或不敏感。”[⑧]这进一步说明了小说作者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
就题材而言,三篇作品中更值得注意的是《蟹》。描写大家庭的兴衰聚散,是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主题。所谓大家庭(extented family),也称扩大的家庭,系指与祖父母、已婚子女等共居一处的数代同堂的家庭。与其相对应的,是所谓的小家庭(nuclear family),又称核心家庭、基本家庭,即只包括父母和子女的两代人的家庭。而大家族(clan)则不是同一范畴的概念。它与宗族、氏族、亲族的意思相近,是由数个乃至许多有血缘宗亲关系的家庭自然组成的利益集团。因此,文学中描绘大家庭的名作,实际上所写的多是大家族。在古典文学中,《红楼梦》堪称描写大家庭崩溃的杰作。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但在现代文学中,从巴金的《家》到老舍的《四世同堂》,以大家庭为题材的作品仍然延绵不绝,《蟹》也是其中之一。当然,《蟹》的社会包容量不是很大。而且,以一个少女的潜在叙述视角为主的叙事方式,也限制了作品的深度。尽管如此,由于《蟹》很好地表现了沦陷区大家庭的破败,以及新一代与老一代之间在沦陷区这个特定社会背景中的尖锐冲突,它无疑是现代大家庭题材作品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从定居北京到抗日战争结束为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尽管梅娘的个人境况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但她的作品绝少涉及政治时局,而是以其不乏优秀篇什的丰富创作,成为沦陷区颇有文名的女作家,拥有广泛的读者。在梅娘此时的作品中,水族系列小说里的那种激愤和对现实的影射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超然淡远的客观审视和作为叙事者的作者的主观投入,以及渐臻圆熟的短篇小说技巧和创作题材的扩展。两个未完成长篇《夜合花开》和《小妇人》没有离开男女间的故事,属于社会言情小说,但在题材和格调上,又各有不同。前者描写了故都北平上层社会中的情场纠葛。美貌女性的婚姻恋爱依赖大贾,物质生活虽然优裕,但与世隔绝的笼中鸟生活,以及对真正感情生活的渴求,又往往使她们在追求情与爱中一无所获,遭到伤害和被愚弄。作品猛烈抨击了那些在玩弄女性的同时,又践踏她们的感情的卑劣男人。后者的主人公是一对为争取婚姻自主而出走到东北沦陷区的青年。生活的压力,以及新旧情人的介入,不断改变着他们的情感、志趣和生活道路。两部作品的主要特点是细腻地描绘了人物的心理活动。
更为突出的,还是散见于报刊和收入《鱼》、《蟹》两个集子中的短篇。梅娘善于根据作品的题材和内容,采用恰当的形式把平常的事物组织起来。《旅》的篇幅虽然很短,但以情节的安排见长。它以第一人称的“我”为叙事者,恬淡地讲述了叙事主人公在火车上耳闻目睹的一幕活剧。这样的题材和叙述语气是很容易使作品流于散漫的。然而作者却巧妙地设置悬念,使小说具有完整的故事性,通过“我”对两个毫不相干的奸杀和私奔事件的错解、期待,以及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结局,在不知不觉之中揭示出,畸形社会是造成的形形色色的婚姻、家庭悲剧的罪魁祸首,而种种不幸的重压又都无情地落在孤立无援柔弱女子身上。《黄昏之献》类似于速写,很象一幅侧重心理剖析的市井人物画像,没有多么重大的使命,但对于梅娘的小说来说,在题材上是一种扩大。因为梅娘是以描写敏感的女性为主的,而在这篇作品里,她把描写的笔触伸向了一个已婚中年男子,通过他见到一则征婚广告后的心理活动,以及登门应征时,所面对的竟是乞讨村妇的意外遭际,将这位蹩脚诗人想象中的年轻貌美又有钱的小孀妇,同归宁三月即将返回的“味同嚼蜡”的太太,以及导演这场恶作剧的地主小姐“那双星子一样的眼睛”,加以穿插,活脱地描绘出一个想入非非、举止荒唐的伪君子形象,对于他的用情不专、拈花惹草的劣根性,加以无情嘲弄。
《春到人间》构思独特,充分显示出作者驾驭短篇小说的才力。一文不名的无业青年小陈,向玩腻了妓女的两位阔少提议干话剧,以便觅得未染风尘的良家女子。经过巧妙的安排、委婉的周旋,终于在应征者中找出了合适的人选。两位少爷各自满意地带着女人走了,他在飘飘然思忖如何对眼前的猎物王玫下手的当儿,也有几分茫然和心虚,因为他毕竟不是财大气粗的少爷,阔少送给他的活动经费和酬金,剩在他的兜里的只有20元。而作为读者,我们一直在憎恶小陈的心术不正和招摇撞骗,在为太容易上当受骗的纯洁少女感到痛心和惋惜。然而,待到那姑娘一开口便以妈妈有病为由向他“借”80元钱时,读者才和小陈一样如梦初醒:原来这几位少女也是在逢场作戏,而看似不谙世事的申若兰、王玫更为老到,她们不但早已看穿了小陈们的伎俩,而且以自己的出色表演,骗过了机关算尽的小陈,如愿抓到了“几只傻鸟”。形形色色的人物,特别是小陈和王玫,跃然纸上。是褒?是贬?褒谁?贬谁?本来读者是同情少女的,最后受骗的似乎又是小陈。此外,这些少女心灵深处还有闪光和辛酸的另一面:脸上挂着轻惑的微笑的申若兰,是以卖笑为生的,但她心地良善,不惜用自己的血泪钱为女友王玫病危的老母治病;对风情还不甚了了的王玫为了让母亲能够住进医院,正在一步步迈向卖淫的火坑。作品迫使读者回味和思索,的确具备了时人所概括的两个特点:“一,浓厚的感情自然的融流于读者的心坎;二,锐敏的观察和宇宙观念而使笔尖形成一只扑打丑陋的鞭子。”[⑨]
以上几篇作品构思精巧,注重人物的刻画,在略带嘲讽的语气中流露出对于苦难者和不幸者的深切同情,并且把对于婚姻爱情的探讨从家庭扩展至社会。在这个方面,短篇小说《侏儒》是最为成功的一篇。从形式上看,这是一个结构相当完整的短篇。它的情节并不复杂,仍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讲述了“我”在房东家的所见所闻以及灵魂所受到的震颤。开油漆店的房东家有一个畸形的小徒弟,看上去不过十一二岁的光景,可实际上已经十六了,原来是一个侏儒。他神情痴呆,每天的工作只是拎油漆桶,房东太太不把他当人看,让警察在登记户籍时写上“王杂种,要不就是王傻子”。他实际上是房东老爷与一个美丽的贫穷姑娘姘居的产物。他的母亲在怀第二胎的时候,被蛮横的房东太太一顿毒打,小产死了。在荏弱的老爷的哀求下,他这个私生子总算被收留下来,但伴随着他的却是房东太太的毒打和饿饭。原来,侏儒纯系人为的虐待所致。随着“我”意识到“在房东和那孩子之间”,还有“一个美丽的女人怎样悲惨的结束了还在青春期的生命”,作品传达出对于被摧残者的同情与怜悯,对于摧残者的腹诽与嫌恶。然而作者的高明在于她别具只眼,还写了这个小家伙在“我”的窗外探头探脑,仆妇发现后便用茄子敲他的脑袋,讥笑“傻王八蛋也知道女大学生好”。“我”对受欺凌的他有爱抚之举,并在他打翻油漆桶,被房东太太撵出家门的那个晚上,把一盘饺子放在窗台上留给他吃。他看到“我”生病后,居然一反从不搭理人的常态,在没有旁人的时候,径自闯进屋来,拿“我”的手摩擦他的腿部。“我”对这一鲁莽的举动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本能地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一下子就把他吓跑了。回过味来,“我”既觉得好笑又感到内疚。但是,当“我”让丈夫第二次把饭菜送给这个古怪的“我的爱人”时,他却飞起砖头砸“我”的丈夫。在故事的结尾,那个没有归宿的“小侏儒”被疯狗咬死了。对于房东太太来说,这正是求之不得的。其他人也漠然置之。作者却道出发自内心的慨叹:“我仿佛看见一颗亮的星坠下来,坠下来变成一块石头,一块被大家恶意地践踏得成了一个四不像的东西。”在关心和爱抚的人际关系和氛围中,一个被非人的环境造就的痴呆愚拙的畸形人,也能焕发出常人的爱恋与嫉妒这些基于人的“食、色”本性的人类一般情感。于是,私生子那“浪漫”的插曲并非只是娱入耳目的低俗噱头。正是这一笔,在丑中发掘出美,在非人中发现了“人”,以悲愤忧闷的曲调,为被无情践踏的人的尊严与价值,唱出了一曲惨绝人寰的哀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揭露力量,同时也将现实主义的开掘推进到心理的和人性的幽深层面上。
南北沦陷区最流行的女作家当推张爱玲、苏青和梅娘。由于作品自身的内在品格和特殊的历史机缘,张爱玲早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成了一则经久不衰的神话。而梅娘和苏青则在不久前才开始引起海内外研究者的注意。从艺术构成上比较她们的文学文本需要专文深入探讨。但限定在抗战时期的沦陷区这个特定的时空之内,粗略地比较她们作品的题材内容和思想倾向,对于进一步认识梅娘作品的主要特点,还是有助益的。
从总体上看,张爱玲、梅娘、苏青创作的一个共通之处,是强烈的女性意识,但由于自身修养和地域文化环境方面的差异,又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特点。苏青的作品基本上囿于一己的生活和经历,即使“海派”的风情格调和弗洛依德精神分析法,也未能使其打破题材和视野的狭窄,以及写真人真事和单纯暴露的局限(《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在张爱玲那里,她的故事总是与十里洋场和老牌殖民地的光怪陆离融合在一起,在深层上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浸染,因此能够不动声色地展示封建主义的血腥和惨无人道,具有理想幻灭的反浪漫主义倾向。张爱玲认定男女间的真情出现在“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的时候(《倾城之恋》),而梅娘则把“合理的”未来世界寄托在将出世的孩子身上(《蚌》)。这充分显示出两者的差异。梅娘的作品与中国“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关系更为密切。她并不是以“奇”或“洋”制胜,而是注重人与人的现实社会关系,在奋力鞭挞假丑恶的时候,并没有泯灭对于真善美理想的企盼。与此相一致,在写作手法上梅娘的小说侧重心理分析、气氛渲染以及环境烘托,并不过分追求情节的曲折、复杂和完整,却仍给人以故事感。这不能不说是她的作品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她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以散文的抒情笔致入小说,但又不失故事性,行文舒徐,文字清通,字里行间显露出女性纤细敏锐的感受,即使是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也在娓娓道来之中给人以疏离杳渺的感觉,象是在讲述民间传说。故事大多发生在城镇,就是那些依然活动在农村的人物,也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传统色彩较为浓重的城市文明的熏染。梅娘作品中绵延不绝的顽强女性意识和独特的叙事风格,正是积重难返和多灾多难的现代北地都市文明的产物。
物换星移,当作为作家的梅娘这个名字重新在出版物上出现的时候,已经是40年之后。进入新时期以来,小说家梅娘开始发表散文。这些散文主要有以下三类:知识小品;游记文;回忆录。由于长期工作在农业科普战线上,梅娘的散文颇具知识性和趣味性,即使是在抒情游记中,也有对大自然的细致观察和对科学技术的生动描绘。然而,梅娘毕竟又是一位有造诣的作家。因此,就是在科普小品文中,作者也能注入人的情感。至于那些谈往忆旧怀人散文,是梅娘饱经沧桑之后的记忆和反思,既情真意切,又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建国初期与赵树理共处的那一段时光,给梅娘留下了美好的印象。80年代,梅娘曾把日本中国学家釜屋修的《中国的光荣与悲哀——评赵树理》一书译成中文,其中有几个片断先期发表在几家刊物上。原著者看了译文后说,他从“译笔中潜含的情愫”里发现,“梅娘对赵树理怀有很深的友谊之情”。[⑩]在《赵树理与我》和《一段往事》两文中,这种深深的怀念和感佩之情得到了很好的印证。梅娘忆及沦陷区文坛的种种是是非非的文章,目前在许多方面仍是若明若暗的。而且,其还有明显的记忆失误和评判失当之处。这需要用翔实、确凿的原始材料加以辨析和梳理,需要中日双方学者共同进一步考察和探讨。不过,作为亲历者的一家之言,梅娘的回忆文字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认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从这个立场出发,当我们对特定的文学作历史的定位的时候,便有了一个基本的评判标准:作品的“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广阔,人物越是杰出而富有代表性”,它的“历史价值就越大”,“就越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11)如果我们不对“崇高”、“杰出”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就会比较准确地把握梅娘在她的作品中反映现实、构筑历史的独特方式。
梅娘是一位主观追求十分明晰和执著的作家。她的两个看似平凡却不乏深意的笔名直露地表示出这种追求。沦陷时期的笔名“梅娘”是个常见的女人俗名,曾有电影《梅娘曲》和通俗故事《梅娘》在世上流传。而对作家来说,它只是“没娘”——没有亲娘的谐音。新时期的笔名“柳青娘”是众多中国古典词牌中的一个,人们并不陌生。而对作家来说,它仅寓“我”是三个孩子中仅存长女柳青的母亲之意。前者似乎颇具浪漫色彩;后者则显得既遥远又亲切。而在作家那里,两个笔名都流泄出她深藏心底的一腔抹不去、甩不掉的思念生母之情和生为人母之心。《侏儒》所描写的,是人为致残的少年畸形人,但作者仍时时让读者感觉到他未曾出场的母亲的存在,一个懦弱富人的外室,一个年轻美丽的无辜受害者。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人的命运的关怀,对人的命运的关怀,使得梅娘的作品既是那个时代和那个地域的,同时又具备了对超越特定时空的政治历史进行多角度阐释的可能性。
近现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光彩夺目的时期。在这个特定历史阶段,伴随着中外文明的碰撞、交汇和融合,伴随着激进的社会变革的持续展开,伴随着古今文化断裂与承接的对立统一,中国社会类型迅速而艰难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化。风雷激荡的转型期,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其中,也包括文学:不但新文学的话语在转换,叙事模式在转换,而且也生成了与过去有明显差异的文学思潮主潮。新的文学思潮,即现代人文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人的发现。以个性张扬和人性解放为灵魂的对于人的精神自由的追求,是时代在新文学中的历史投影,而新文学作品也以其生动的原生态记录下了这种追求的纷繁性状和坎坷历程。梅娘作品的显著特点是博施济众的泛爱胸襟,积极入世的主观视角,非常规化的女性语言。她关注和爱护的是女人,却流泄出对人的关注和爱护。她呼唤和向往的是女人的地位和权力,却流泄出对人的地位和权力的呼唤和向往。这样的品格,无疑与新文学同步并丰富了新文学的总体画面,是沦陷区文学没有空白的又一个例证。
Mei Niang,the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of Her Time and the World of Her Works
Zhang Quan
Abstract:Large members of outstanding writers emerged in the areaoccupied by the Japanes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Mei Niang was one of them.The author puts the female writer in a certain historical circumstance so as to expound and analyse her artistic experience and value of her works and historical factors shaping her to success.Based on the analysis above,here was brought forward a viewthat indomitable woman awareness reflected in her works with its unique narrative style just inevitable of the social circumstance of thathistorical period.
Key Words:Mei Niang,historical circumstance,the world as reflectedin her works.
注释:
①参见董大中《“南玲北梅”的“梅”》,《文汇读书周报》(上海),1996年6月1日;以及梅娘的《我与日本》,《民主中国月刊》,1955年3月号。
②《远方的思念》,载《吉林日报》1993年3月13日。
③章岩《红楼隔雨相望冷——一代才女张爱玲》,载《团结报》1995年12月20日。
④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1944年5月号。
⑤参见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第30、31页。
⑥山丁《关于梅娘的创作》,《华文大阪每日》(日本)5卷10期,1940年11月15日。
⑦韩护《〈第二代〉试论》,转引自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9辑,1984(6)。
⑧E.Gunn,Unwelcome Muse: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1937-1945,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第42页。
⑨《编后记》,《国民杂志》2卷4期,1942(4)。
⑩釜屋修《中国文学鳞爪——关于梅娘》,《季刊中国》(日本),1994年春季号。
(11)《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引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