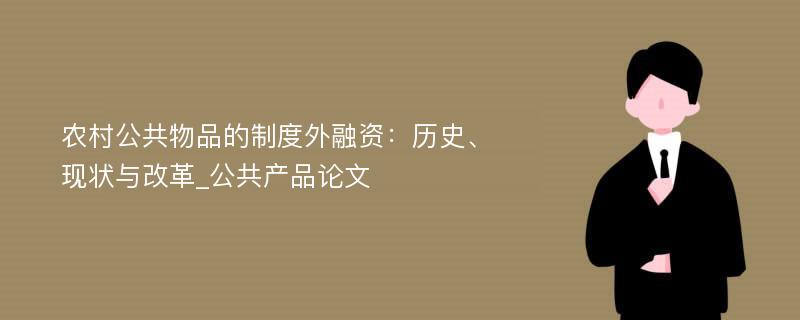
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历史、现状及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状及论文,乡村论文,制度论文,历史论文,产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乡村社区公共产品制度外筹资的含义
本文对乡村社区公共产品(注:在本文中,乡村社区公共产品是指:在乡或村范围内提供的,为乡村社区农民(或其中的一部分)所消费的带有公共产品性质(消费或受益难以完全排它)的产品或服务,包括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技术信息服务和农村基础教育等。这一界定带有“约定俗成”的意味,与公共经济学对公共产品的严格定义不完全相同。)制度外筹资的定义是:政府或集体经济组织采取的,没有纳入到正规财政体制范畴内的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筹资方式。因此,所谓“制度外”,并不是指这种筹资方式不合法,而是指它处于“正规的财政制度之外”。
孙潭镇和朱钢(1993)最先提出了“制度外财政”这一概念。他们将财政定义为“行政当局依靠行政的强制力量,为支撑政府活动而进行的资金筹措和运用”。根据这一定义,可将乡镇财政划分为制度内财政和制度外财政,前者指在现行财政管理体制下的预算内财政和预算外财政,后者指乡镇政府以各种形式筹集的自筹资金以及由此发生的政府支出,虽然也属于财政范畴,但它与制度内财政有明显区别:其收支范围、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由乡镇政府根据本乡镇的实际情况而定,而不像制度内财政那样有全国统一的制度性约束,其资金的使用既缺乏制度规范,也不纳入预算管理(注:需要注意的是,根据199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规定》,从1996年起,用于乡镇政府开支的乡自筹和乡统筹资金,均要归入预算外资金管理范围。)。同样一个概念,樊纲(1995)将之称为“乡镇非规范收入”,以突出其基本特征,即“非规范性”。
根据以上定义,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除了包括政府通过制度外财政进行的公共产品筹资以外,还包括农村各级集体经济组织为供给公共产品而采取的筹资方式。因为在中国农村,除了政府以外,各级集体经济组织也有供给公共产品的职责(注:叶兴庆(1997)将各级集体经济组织供给的公共产品称为“制度外公共产品”。)。它们所供给的公共产品,同样没有纳入到正规财政体制范畴内。
无论是在人民公社时期还是家庭承包制时期,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均是一种普遍现象,在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占有重要地位,值得深入研究。本文的目的是对这两个时期乡村社区公共产品制度外筹资的方式和规模进行对比分析,探讨这一方式在家庭承包制时期的弊端,提出改革方向;并要在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若干关于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有益启示。
二、人民公社时期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使乡(镇)政府被“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所取代,财政体制也随之改变,乡镇财政(注:1953年以后,随着土改的完成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行,一些地方陆续建立了乡镇一级财政。具体内容可参见高英、崔国忠(1998)。)实际上被取消,“公社财政”初具雏形。1962年,人民公社的财政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将“财政包干”改为“统收统支”的管理办法,除农业税附加给公社一定的分成外,公社收入全部上交县财政,公社的支出也全部向县财政领报,这实质上是取消了人民公社作为一级财政的管理体制(邱兴和,1996)。1970年以后,江苏等省的一些地区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先后恢复了人民公社财政,实行不同形式的财政管理体制。在建立了“公社财政”的人民公社,其公社财政的收支内容可归结为表1。
表1 公社财政的收支项目
收入项 支出项
一、国家预算收入
一、国家预算支出
1.商业企业收入 1.支援农业支出
2.公社税收:农业税、工商税、工商 2.公社行政管理费
所得税、屠宰税
3.其他收入:罚没收入等
3.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
二、地方预算外收入 4.抚恤和社会救济费
1.农业税附加5.城镇人口下乡经费
2.工商税及工商所得税附加
二、公社财政社有资金支出
三、公社社有收入1.社办企业支出
1.公社企业利润及折旧基金上交2.农业支出
2.社办事业收入 3.文教科学卫生支出
3.生产大队的部分公积金上交 4.社会救济福利事业费
4.公社其他收入 5.公社行政管理费及其他支出
资料来源:《人民公社财政与财务管理》编写组(1981)提供的资料。
除了财政渠道外,在公社时期,乡村公共产品的另外一个筹资渠道是各级集体经济组织。人民公社既是一个政权实体,又是一个经济组织,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之间有较强的经济联系。表1表明,即使建立了公社财政, 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也仅限于公社一级的部分项目,更没有针对生产队和生产大队两级的支出项目,因而维系整个社区公共产品正常供给除了依赖公社财政外,还有赖于各级集体经济组织(即生产队和生产大队)所筹集的资金。
各级集体经济组织公共产品供给(即乡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的资金筹集,与公社框架下的分配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对于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生产所得,在扣除掉当年生产费用,包括种子、肥料、农药、燃料、机耕费、排灌费、农机具维修费、小型农具购置费、耕畜饲养费及固定资产折旧之后,分配顺序是(农业部课题组,1993):①国家税收和粮食统购任务。②管理费。包括办公用品、差旅费、干部补贴及生产队上交大队的管理费。③集体提留。包括生产队及上交大队的公积金、生产费基金、贮备基金、公益金等。④社员分配。即在总收入中扣除上述支出后的剩余,以工分为权重,分配给社员。因此,在公社时期,集体经济组织公共产品供给的物质成本是以管理费、公积金和公益金的形式来筹集资金的(注:人力成本以增加总工分数从而降工分值的方式加以弥补。)。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公社时期的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有两种模式。
模式一:建立了公社财政的地区,社区公共产品由公社财政(含公社财务)和生产队及生产大队供给。
模式二:未建立公社财政的地区,社区公共产品由县财政(代替公社财务)和生产队及生产大队供给。
无论是何种模式,公共产品的筹资渠道都有两个,即财政渠道和制度外渠道。由于缺乏系统完整的数据,无法对这两个渠道的供给规模进行精确对比。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公社时期,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表2列举了公社时期主要公共产品的筹资渠道,它表明, 社区集体在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表2 公社时期主要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筹资渠道
公共产品项目
筹资渠道
1.社队兴办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凡是社队有能力全部承担的,应自筹解决;对困难社队,
国家给予必要补助
2.所有水利工程 新中国30年兴修的水利工程,国家总投资共763亿元,
而社队自筹及劳动积累,估计达580亿元
3.农村社队集体办学 集体负担为主,国家财政给予必要补助,另由个人负担
少量学杂费
4.公社卫生院实行"社办公助",主要依靠公社集体经济力量
5.农村"合作医疗"由大队统筹全体农民的医疗费用,基本医疗服务费用主
要由社区集体承担;财政补助用于培训医务人员的经费
和支持穷队办合作医疗
6.大队卫生所几乎完全靠集体经济投资和维持
7.公社文化和广播事业公社社有资金为主,国家预算内支出中适当补助
资料来源:程漱兰(1999),第269、292、295页; 《人民公社财政与财务管理》编写组(1981),第56~77页;朱玲(2000)。
另外,还可以从数量上大致估计社区公共产品制度外筹资的重要性。表1显示, 国家和公社从农村中获取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农村的各项税收和社办企业的利润上交(企业折旧基金除外)(注:这是一个粗略的说法,但可以反映大致情况。有资料表明,生产大队上交的公积金仅占公积金的百分之几。具体可见程漱兰(1999)第212页。 国家预算收入中的“商业企业收入”和“其他收入”以及公社社有收入中的“公社事业收入”和“公社其他收入”比重也不会太大。)。根据资料掌握情况,以1978年为例,可以大致估算公社和国家从农村中获取的财政收入以及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集体提留(如表3所示)。
表31978年公社财政收入和集体提留估算
项目大致估计值(亿元)
一、财政收入粗估
1.社办企业利润20.4%①×224.33②=45.8
2.社办企业税收22③×57.5%④=12.7
3.农业税 37.2
4.税收附加(12.7+37.2)×35.5%⑤=17.7
合计 113.4(=45.8+12.7+37.2+17.7)
二、集体提留合计 103.0
注:①指社队企业销售收入利润率,此处大致用来代表社办企业收入利润率;②指社办企业销售收入;③指社队企业总利润;④指社办企业收入占社队企业总收入的比重(此处假定二者利润率相当); ⑤指1976年全国预算外收入占预算内收入比重,大致代替1978年税收附加比。
资料来源:《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78—1987)》,第569页; 《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209页及贾康、阎坤(1999),第83 页数据。
虽然表3对1978年农村财政收入的估算数据并不精确, 但它足以说明这样一个观点:即便是将国家从农村中获取的财政收入(注:可能存在高估。因为:①对税收附加可能大大高估了;②20世纪70年代末起,由于国家的鼓励,社队企业发展很快(谭秋成,1998),1978年社办企业的利税必定要比其他年份高。)全部用于公社财政或县财政的乡村社区公共产品建设上(在当时体制下是不可能的),也不会比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即集体经济组织提取的管理费、公积金和公益金,它尚未包括大量的劳动力投入)高多少。由此可以再次证明:在公社时期,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三、家庭承包制实施后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延续与变化
(一)延续
当人民公社于1983年正式废除时,乡被恢复为一级农村政府。与此相适应,乡镇财政建设也开始了。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随着乡政府的建立,应当建立乡一级财政和相应的预决算制度,明确收入来源和开支范围。”到1997年底,全国已建立乡镇财政所43285个,占建制乡镇的95.6%。公社制度解体、乡镇一级政府的建立和乡镇一级财政的建立三个事件之间并不是独立的,而是有其必然联系:在代替人民公社而建立的乡镇政府不再具有直接的经济管理职能、无法直接获取经济剩余的情况下,建立一级财政以筹集其所需资金及安排资金使用就是必要的制度安排了。
虽然建立了乡镇一级财政,但是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体制也同时以其他形式保留了下来。其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乡镇制度外财政。目前,我国农村乡镇制度外财政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以下四方面:①乡镇企业上交利润和管理费;②乡镇统筹资金,包括五项统筹和乡镇政府按照国家规定征收的其他收入;③各种集资、捐赠收入;④各种罚没收入。
二是农民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所必须承担的村提留、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村提留(又称“三提”)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其中,公积金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兴办村集体经济;公益金用于五保户供养、特别困难户补助、合作医疗保健以及其他集体福利事业;管理费用于村干部报酬和管理开支;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主要用于植树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缮校舍等。
从游离于正规预算财政体系之外这一点看,制度外财政及其他税外负担与公社时期的公共产品制度外筹资的性质是相似的,可以认为:现行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制度是公社时期制度的延续(叶兴庆,1997)。这里要强调的是:这种延续并不是基层政府的创新,而是中央政府做出的制度安排(注:关于为什么中央政府要做如此的制度安排,可以参见林万龙(2000)的分析。)。
分析表明,在家庭承包制实施以后,制度外筹资在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中仍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以乡镇一级筹资为例,孙潭镇和朱钢(1993)、樊纲(1995)和作者本人的个案调研均显示,对乡镇政府来说,制度外财政收入在其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对许多乡镇来说,制度外财政收入已成为其收入的最主要来源。 表4说明,乡镇制度外财政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可能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象。
表4
乡镇一级制度外财政收入占乡镇可支配财力的比重:若干个案
个案地点(乡镇) 制度外财政收入比重(%) 年份
1.北京某乡 77.4
1989
2.浙江某镇 72.5
1989
3.大连某镇 74.6
1991
4.湖南某镇 41.7
1991
5.湖北宜城县某镇59.7
1992
5.广东江门市某镇85.7
1993
7.温州乐清市某镇63.2
1993
8.河北某乡(A)
45.1
1996
9.河北某乡(B)
43.6
1997
10.河北某乡(C) 45.9
1998
11.河北某乡(D) 59.6
1999
注:个案1~4中的比重调研者未说明是占乡镇总收入的比重还是占乡镇财力的比重。
资料来源:个案1~4:孙潭镇、朱钢(1993);个案5~7:樊纲(1995);个案8~11:作者本人调研。
(二)变化
但是,对于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来说,家庭承包制是与人民公社制度完全不同的一种制度环境。事实证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制度外筹资在筹资对象和筹资方式上也因家庭承包制的实施而发生了某些变化。
首先是筹资对象的变化。在公社时期,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其直接承担对象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本身,公共产品所需的物质成本通过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的形式在社员分配之前直接从各个核算单位扣除;公共产品供给的人力成本也是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劳动力资源的损耗。因此,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制度外筹资的直接承担对象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本身。家庭承包制的实施使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制度外筹资的承担对象由集体为主转向以农户为主。由于农户实际支配了农村中的大部分资产,并有了生产经营活动的剩余索取权,因此,对农村基层政府来说,为了维持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其筹资对象就自然地必须由集体转向农户,农户因而成了费用的直接承担者。以农村中的“三提五统”为例,就全国范围而言,农户承担的比例一直占总额的大部分(见表5)。
表5 1987~1997 年农户人均直接承担的提留统筹费及其占总额的比重
项目 1987年1988年1989年1990年1991年1992年
人均提留统筹费(元) 25.7 28.9 33.8 41.2 44.6 47.4
其中:农民人均直接负担(元) 15.3 18.1 20.8 26.1 29.2 31.0
人均直接负担的比重(%) 59.6 62.7 61.5 63.4 65.5 65.3
资料来源:1991年前的人均提留统筹费及农民人均直接负担数据引自农业部课题组(1993);1991年后数据引自《中国农业发展报告》(1996、1998)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9)。
需要注意的是,表5 列示的仅是农民所直接承担的“三提五统”费用的比重,农村中的其他集资和摊派,则几乎全部必须为农户所直接承担。这是家庭承包制实施后农村制度外公共产品筹资对象的一大变化。
其次是筹资方式的变化。在筹资对象发生变化的同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制度外筹资的方式也因家庭承包制的实施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公社时期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方式是与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制度相关的,公共产品所需的物质成本在农户分配之前直接从各个基本核算单位扣除,单个农民并不清楚自己分摊的公共产品物质成本为多少,公共产品所需的人力成本的分摊办法是增加工分总数、降低工分值,单个农民同样不清楚自己的负担份额。在家庭承包制实施之后,这种筹资方式不再适用,这是因为农户已经成为经营主体和剩余索取者,农户成了基本核算单位,农户也获取了其自身的劳动支配权。这样,乡村政府为了完成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就必须直接向农户收取费用,这种费用是对农户生产剩余的一种直接的夺取,而不再是集体收益的一种分配方式了。过去的隐性剥夺被公开化了,它所体现的正是家庭承包制实施后社区公共产品制度外筹资方式的变化。
四、乡村社区公共产品制度外筹资方式的弊端及其改革
尽管中国农村基层所延续的制度外筹资方式,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李富忠、林万龙,2002),但是,它却与农民负担问题直接相关。这是由这一制度的特征以及家庭承包制这一制度环境所决定的。
首先,公共产品制度外筹资制度的最大特征在于它的不规范性和决策机制的自上而下性。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强制性制度安排中的这些特征,使政府供给主体加重农民负担有了可能。这种“一事一费”的制度,不仅为任意开征新的收费项目提供了可能性,而且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当新的公益事项出现时,在“一事一费”的筹资制度下,将诱发新的收费项目的出现;最为主要的是,乡镇制度外筹资属于乡镇各收费部门(包括乡镇财政)的自收自支资金,在家庭承包制下,农村基层政府部门与农户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有各自相对独立利益的两个集团。在缺乏缴费者制约的情况下,各部门有增加收费项目的动机。这是前两点原因背后的本质原因。因此,在家庭承包制下,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制度使政府供给主体增加收费项目、加重农民负担有了机制上的可能性。
其次,在家庭承包制下,公共产品的需求方——农户,对负担的感受非常敏感。在家庭承包制下,农户成为了有独立经济利益的经济活动主体,筹资制度的这种变迁,使农户对负担的敏感程度上升了,特别是在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不符合农户需求时,农户的对抗情绪就明显加强了。事实上,公社时期的农民负担也是很重的,但是农民负担问题却不突出,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在此,本文将公社时期和家庭承包制时期的农民负担做一对比。本文中,农民负担定义为农民所承担的税收、提留统筹和其他摊派。对农户来说,公社时期的负担主要包括国家税收、集体提留和各种杂项负担,为了与家庭承包制实施后的口径一致,农民纯收入相当于分配给社员的份额与集体提留之和(注:家庭承包制实施之后,根据统计指标的定义,农民纯收入=全年总收入-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缴纳税款-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上交集体承包任务-调查补贴。有关内容可见《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9),第490页。)。在公社时期, 农民负担大约占其上年纯收入的比重可以大致估算如表6。
表6 公社时期的农民负担:1958~1979年单位:亿元、%
年份总收入国家集体杂项*
分给农民纯农民负担占上
税收提留负担社员收入 年纯收入比重
1958410.2 39.047.4
214.5261.9
1959384.0 38.448.1
194.7242.8 33.0
1960367.7 35.415.2
208.6224.8 21.7
1961412.3 25.428.0
247.8275.8 24.2
1962423.3 27.527.6
248.6275.2 20.0
1963440.5 28.830.9
255.1287.0 21.6
1964489.6 33.245.7
269.3315.0 27.5
1965531.7 29.847.517.9
304.6352.1 30.2
1970727.3 32.971.219.7
399.0470.2 35.2
1971778.7 34.673.920.7
435.6509.5 27.5
1972795.6 35.268.221.1
437.7505.9 24.4
1973863.8 37.083.222.2
473.4555.6 28.1
1974909.4 37.591.822.5
487.4579.2 27.3
1975924.5 37.1
101.122.3
475.9577.0 27.7
1976944.2 35.795.122.0
479.0574.1 25.7
1977975.9 37.190.9
501.8592.7 22.3
1978
1107.4 37.1
103.0
582.4685.4 23.6
1979
1234.1 39.8
118.4
655.6774.0 23.1
注:*仅有1965~1976年的估计比例。据估计, 这一时期的杂项负担大约为农业税的60%~80%,此处按最低值,即相当于农业税的60%计算。
资料来源:杂项负担比例来自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农民负担史》,第四卷,1994年,第312页; 其余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3)。
从表6看, 公社时期农民间接负担与上年人均纯收入的比例最高年份达到了35.2%(1970年),最低也有20.0%(1962年),一般在25%左右,其平均值为24.8%。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结果尚未把那一时期极为严重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和大量的无偿使用劳力考虑在内。
由于各种集资摊派难以统计,因此对于家庭承包制下的农民负担缺乏系统的资料。在此用有关部门在1993年(42个县)和1997年(5000个农户)的个案调研数据以及1999年和2000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资料》提供的数据进行估计。当然,在公社时期,农户上交集体提留后,还可以享受到一些在家庭承包制下所没有的待遇,这主要是基本免费的合作医疗服务和小孩的基础教育服务。为了使结果更有可比性,应当把这两项支出加入到家庭承包制下的负担中去,本文用全国的人均医疗保健和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数据来代替。由此计算出的这4 年的农民税费支出负担的结果可整理成表7。
表7 我国农民社会负担(当年价)
农业 三提 其他社 总额 人均 人均医疗和文 人均合计占
年份各税 五统 会负担 (亿元) (元) 教娱乐支出上年人均纯
(亿元)(亿元) (亿元) (元)收入的比重(%)
1993125.74379.90 148.19 653.83 76.77 85.50 30.8
1997397.48702.96587.9321688.37194.88220.00 21.5
1999423.50669.53 165.031258.06144.58260.64 18.7
2000465.31620.36 165.511251.19154.19274.29 19.4
资料来源:①1993年的农民其他社会负担来源:1993 年农业部对42个县的蹲点调研提供的个案数据(人均17.4元),参见任全珠(1994);②1997 年的农民社会负担:国家税务总局“农民负担调查”中5000户农户调查资料表明,1997年在农户人均负担195元中,税收负担占46元,税外各种负担为149元。③1999和2000年的其他社会负担:将亩成本外支出作为我国农民按土地播种面积负担的税收外的社会负担,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资料》,我国1999年和2000年6 种粮食平均的每亩成本外支出分别为35.58元和33.52元,亩成本外支出与农作物播种面积相乘就得到我国农民负担的成本外支出总量。④其余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历年)。
表7表明,在所选的4年中,按同口径计算,除了1993年的农民负担水平(30.8%)要比公社时期(24.8%)高以外,其他3 年的负担额均明显低于公社时期的平均水平。4年的平均水平为22.6%。 需要强调的是,据农业部的估计,1993年所调研的42个县的社会负担和劳务负担要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按照农业部的资料(任全珠,1994)计算,高了5个百分点。这也就意味着:就全国来说,1993 年的农民负担水平(25.8%)与公社时期的平均水平相比也并不高。这里要强调的是:对公社时期农民负担的计算还未把严重的“剪刀差”因素考虑在内。
在实际负担相差并不明显的情况下,表现出的农民负担问题的严重性却差异明显:随着矛盾的尖锐,政府现在已经把农民负担问题上升到了“社会稳定”的政治高度(国务院法制办公室,1999)。当然,由于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公社时期的24.8%和家庭承包制时期的22.6%并不具有完全的可比性,负担重与不重,很大程度上是个主观感受,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民对生活水平要求的提高,农民的负担水平理应“与时俱进”而有所降低,因此,并不能仅仅因为农民现在的税费比例比公社时期低,就认为现在的负担不如公社时期重;但是,无论如何,上述比较值得我们深思,同样是制度外筹资、相近的实际负担,由于经营和分配制度的不同,其影响也不同:公社时期农民对负担的感受是不强烈甚至微弱的,而家庭承包制时期则是强烈的、直接的。因此,所谓农民负担过重的提法是笼统的、含糊的,在家庭承包制下,公共产品的供给者(政府部门)及公共产品的需求者(农户)成为了两个具有一定独立利益的主体,不规范的公共产品制度外筹资方式直接与农户的经济利益相对立,公共产品供求不均衡的严重后果因此凸现了出来。这种不均衡突出体现在:许多通过收费而提供的农村公共服务并不是农民所需要的;更有甚者,有许多收费并没有提供任何相应的服务,而是用于了收费部门的私利。在农户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而负担显性化的情况下,矛盾即突出了。这使家庭承包制时期的公共产品制度外筹资方式与严重的农民负担问题联系在了一起。
既然农民负担问题与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体制及其决策规则相联系,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就必须对这种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进行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所试图解决的实际上正是现行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外供给制度的这两个重要方面:前者力图将乡镇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规范化,使之纳入到制度内筹资范畴中去;后者的目的之一,是要解决村级社区公共产品制度外供给的决策规则,即将“自上而下”的决策规则改为“自下而上”,以使公共产品的供求相衔接。
因此,尽管目前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方案均不完善,但是,上述分析表明: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它们所针对的,是公社时期延续下来的、已经与家庭承包制不相适应的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外供给体制。
五、结论性评述
本文对人民公社时期和家庭承包制时期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方式进行了研究。分析表明:家庭承包制实施后,虽然建立了乡镇一级财政,与此同时,公社时期的公共产品制度外筹资体制却也延续了下来;在这两个时期,制度外筹资方式在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均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在家庭承包制的制度环境下,这一制度在筹资对象和筹资方式上都已发生了变化,农户成为了直接的资金供给者,这使得农民的负担由隐性转为了显性。
在农户获得了生产剩余索取权以及政府部门行为缺乏强有力约束的情况下,乡村社区公共产品制度外供给的存在及其筹资对象和筹资方式的变化,引发了严重的农民负担问题。定量的计算说明:所谓的“农民负担”问题,其实质可能是原有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制度外供给体制不再适应新的制度环境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只要公共产品的筹资方式不规范,缺乏预算的硬约束,那么,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基层政府)就可能有扩大筹资规模的动机,并且对需求方的需求考虑不足;如果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求不均衡,那么公共产品的需求者(农户)就可能对筹资制度不满——在负担不重时如此,在负担较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这种不适应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矛盾促使政府必须对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体制进行相应的变革,在筹资制度上,必须争取取消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方式,将之纳入制度内范畴而趋于规范化,在村级公共产品的决策规则上,则必须强调决策的“自下而上”性,以使公共产品的供求相衔接。事实上,这也就是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和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要点。
本文的分析意味着:并不是家庭承包制的实施带来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由于家庭承包制的实施,原有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不再适用了,而现有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也没有完全适应新的制度环境,因此,必须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进行创新。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现象,还体现在农村公共产品的民间供给和公共产品的私人化等诱致性变迁上,这是农村财产权私人化和农村经济市场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林万龙,2001)。因此,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创新,税费制度改革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问题的全部。如果政府能创造条件诱导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诱致性创新,将能充分利用民间资本,拓宽公共产品筹资渠道,形成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多元化格局,从而减轻政府财政的公共产品供给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