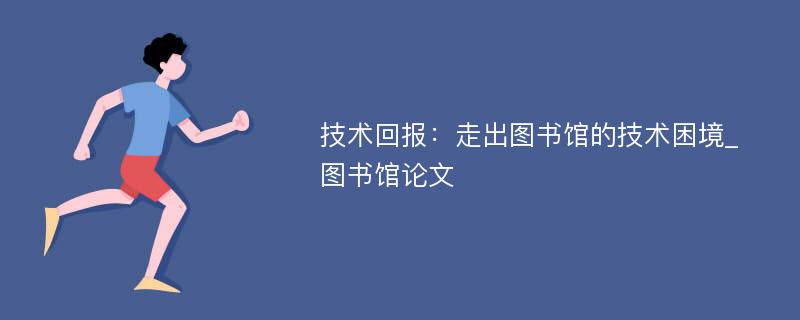
技术回归:走出图书馆的技术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论文,困境论文,图书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技术在图书馆成功的范例随处可见,对图书馆未来发展的潜在影响也广为人知。然而,在国内大多数图书馆的现代化进程中,决策者们对现代技术却采取了相当谨慎和低调的态度,“许多图书馆的管理者或热风吹雨,或冷眼向洋,或不明所以。”他们“有的弄潮逐浪,可方方面面条件又跟不上,只得捉襟见肘,苦苦挣扎;有的乐观其成,但又一时看不清动向,只好坐以待变;有的虽有些思考,不想轻举妄动,但又怕别人说僵化保守,不思进取,也表现得内心矛盾。”[1]这就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为什么面对着如此强大的技术力量,馆长们却心存疑虑?
1 技术能带我们走多远
20世纪末,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为主导的现代信息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它在改变世界面貌的同时,电给图书馆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在技术生产力的催动下,传统图书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计算机管理下规范化的“采、分、编、流”,简便迅捷的全文数据库检索,网络化的文献信息资源共享,Internet资源利用……。我们几代图书馆人的梦想,今天都已成为现实。这一切当然要归功于现代技术的应用。正如戈弗雷(Godfrey)和帕克希尔(Parkhill)所言:“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所有信息,不可能的理想。但是,电脑与现有通讯线路的联姻将使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这个目标。”[2]我国学者也曾撰文,从图书馆计算机网络建没、网络化、数字化信息资源建设、数字图书馆、图书馆软件平台等多个方面,为我们展现了1996-2000年间我国图书馆现代技术的发展及其成就,[3]内容几乎涉及到图书馆工作的全部领域。正是由于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如此广泛而成功的应用,给图书馆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技术生产力无可争议地成为这一时期图书馆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技术在图书馆的成功,激发了图书馆学研究的勃勃生机,也激活了图书馆人丰富的想象力。站在图书馆学研究前沿的学者们,开始沿着技术的道路不断向前探索。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兰卡斯特号召我们要“随着电子资源的日益重要和纸资源的日益减少,随着计算机终端在办公室和家庭日渐普及”,而《走向无纸社会》。L.H.Seiler和T.T.Surprenant则坚信“印本图书馆的终结已经在望,纸本印刷物正在消亡,我们职业的终极目标将是一个虚拟信息中心。”[4]此后,电子图书馆、虚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等未来概念图书馆相继出现,并无一例外地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石之上。在技术魔力的感召下,美国著名的加州州立大学校长B.Munitz明确地声称:“在我们这个时代建立传统式的图书馆根本没有必要。”并率先将他的观点付诸实践。在其Monterey Bay新建的校园中,一应建筑物应有尽有,且十分壮观,惟独没有图书馆大楼。[5]
难道这就是我们追求的未来?难道我们如此信任并寄予厚望的“技术”带给我们的只是我们事业的消亡?技术将带我们走向何方。
2 我们能否跨越技术准入的门槛
“斯坦福-硅谷”模式是现代技术发展的典型模式。“硅谷”的成功为我们揭示了现代高技术发展的两个基本而必要的条件,即资金和人才。这也是图书馆应用现代技术所必须跨越的两道“门槛”。
在资金方面,图书馆启动现代技术项目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如初期购买的硬件设备,开发图书馆应用系统软件,采购数据库和电子出版物等。在运行过程中,又要有稳定的资金来源,用于保障数据的更新、设备的维护以及软硬件的升级。从国外图书馆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看,雄厚的资金投入是主要因素。如美国,早在60年代,政府就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为建立大规模机读书目数据库提供了1000万美元的资助。1994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防高级项目研究机构和美国航空航天局又联合出资2440万美元,用以资助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6个数字图书馆的研究项目,而1996年5月正式开放的美国纽约“科学、工业、商业图书馆”更是耗资1亿美元。而国内的数字图书馆项目,一般由大型图书馆承担,并大多为示范性的,主要靠政府的投资和公司的赞助。对于众多靠正常经费运行的中小图书馆来说,仅是对付前几年的书刊涨价,就已显得捉襟见肘,更不用说启动图书馆现代化建设项目了。
在人才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各图书馆普遍缺乏发展现代技术所必须的人才储备。虽然近年来许多图书馆都认识到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下大力气培养和引进人才,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现代图书馆的人才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按细分程度的不同有十几种甚至几十种之多。而图书馆囿于编制、体制的限制,根本无力去培养和引进这么多人员。二是现代图书馆所需要的多数是热门学科和紧俏专业的人才,以图书馆现实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对他们很难产生吸引力。因此,对大多数图书馆来说,能留住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已属不易,更谈不上大规模的“引进”了。
技术准入的门槛将相当多的图书馆挡在了技术应用的大门之外,只有少数具备有一定“资金”和“人才”实力的图书馆侥幸跨了过去,迈出了图书馆现代化的第一步。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仍是一条永无止境的技术革新之路。在这条道路上,还有无数道“资金”和“技术”的门槛在等待着他们,而且其中的一道可能就在不远处。
3 我们能否跟上技术更新的步伐
曾几何时,计算机还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短短十几年,就成了现代技术社会中所必备的“生存的技能”。现代信息技术一经问世,就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进行着自我繁衍。硬件速度仅是技术更新的开始,接下来是为充分发挥硬件性能而进行的基础软件升级,再接下来是建立在基础软件之上的应用软件的升级,然后还有新技术的开始和扩散,等等,……。正如“人类社会正沿着以技术产品尤其是计算机的革新为里程碑的道路向前发展。以后划分历史时期的依据不再是年份或重大事件,而是软件升级与微处理器的改进。”
我们从不否认技术进步对图书馆事业的整体推动作用,但具体到某个图书馆的某个技术项目而言,过高的技术更新频率意味着技术生命周期的短暂,意味着技术前景的不确定性。它迫使我们应该不停地去追逐新技术,稍有停留,我们的计算机就可能找不到配件,我们的应用软件就会失去操作平台。关于这一点,国内较早进行自动化建设的图书馆大都有过这方面的体会。如硬件设备的换代,操作系统的升级,非关系型数据库向关系型数据库的转换,10M网向100M的过渡等。同时,技术发展的这种不稳定状态,也会对图书馆技术应用产生不同程度的“反动”。这种“反动”可能是两方面的,一是对技术的不信任,决策者在决定采用某种新技术之前会普遍存在担忧,这个项目在建成之日会不会就已经过时了呢?因为他们已经在周围看到或是亲身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例子。第二,他们会进一步对应用新技术的必然性产生怀疑,既然这个项目前途未卜,我们还有必要进行下去吗?。
然而,技术进步的脚步并不会因为图书馆的忧虑而停止。如果我们跟不上技术前进的脚步,就无法在现代社会找到安身之所。
4 技术向图书馆的回归
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在其著名的《图书馆学五定律》中指出,“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在图书馆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许多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技术进步直接关系到图书馆的现实生存和未来发展。我们认为,面对社会技术进步的潮流,图书馆应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么一条原则,那就是:技术向图书馆价值的回归。
4.1 技术客体向图书馆主体的回归
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告诉我们,“技术并未决定社会,而是具体化了社会;社会也并未决定技术发明,而是社会利用技术。”[6]曾号召我们走向无纸社会的兰卡斯特,在1982年时大胆地预言:“作为一个公共机构的图书馆开始走向必然没落的道路。”但10年之后,他在谈到图书馆的未来时却变得谨慎起来,“我们不知道这些不同的见解中哪些将被证明是最‘正确的’”。[7]显然,兰卡斯特已认识到,仅从技术角度来推论和预测图书馆的未来是不够的。在Monterey Bay的那所没有图书馆建筑的加州州立大学,“最近两年购买了成千上万册的图书,因为他们很吃惊地发现,在网上无法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8]而另一所以工程师和计算机专家密集度最高而闻名世界的大学,California Polytechnic State University,花了两年时间来探索建立纯电子的虚拟图书馆的可行性。最终的结果却是耗资4200万美元建立了一所传统图书馆,当然,这所图书馆有着强大的电子功能。难怪Mark.Y.Herring断言,“纯虚拟的图书馆是无法生存的,过去不能,现在不能,甚至在我们这一代都不可能。”[9]Mark.Y.Herring的结论是否过于武断,我们姑且不去评论。至少他给那些技术狂热者们泼了一盆冷水,并提醒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技术是否走得太远?
图书馆的未来不是由技术决定的,决定图书馆未来的只能是图书馆自己的价值实现。1998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到国家图书馆视察,在谈到图书馆未来的发展问题时,曾明确指出“数字图书馆是没有围墙的图书馆,但是,有围墙的图书馆是没有围墙的图书馆的中心。”[10]尽管未来的图书馆可能会使用到更多、更新的技术,甚至可能是构筑在技术基础之上,但任何一个现代化的图书馆,都不是靠几项或十几项现代技术堆积而成的。技术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在讨论技术对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影响时,决不能脱离图书馆的主体。如果我们偏离了这个方向,就很可能会滑入技术决定论的陷阱。
4.2 技术应用向图书馆价值的回归
图书馆从来就不是技术机构。也不是为技术而存在的。图书馆存在的价值在于为社会所提供的信息服务,在于以最少的时间,最快的速度,为最多的读者找到最多的书(信息)。从表面上看,图书馆的现代化进程表现出的是一个图书馆不断技术化的过程。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能明显地看到,技术正以点滴的方式向图书馆渗透,逐渐改变和替代了图书馆传统的工作方法,使图书馆的技术含量和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但在实质上,图书馆的现代化进程,是图书馆不断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改进传统服务,提高自身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过程;是为了满足社会对信息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使图书馆的价值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不断得以再现的过程。
我们投巨资购买了昂贵的现代化设备;花大力气建立了图书编目、流通借阅、数据库检索、网上信息资源收集等一个比一个先进的计算机系统。这一切不是为了减轻馆员的工作量,也不是为了方便馆长们的管理,更不是为了对读者实行严格的控制。我们这么做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图书馆“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的价值。国内著名的图书馆学家黄俊贵指出,“采取先进技术如果不是为服务读者,提高服务水平,不与办馆效益挂钩就毫无实际意义。”[11]
4.3 技术应用向图书馆现实的回归
不同类型的图书馆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实现方式。公共图书馆在普及社会教育、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过程中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大学图书馆也以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提供信息服务的方式实现着自身的价值。因此,我们在考虑技术应用时,要抛弃对技术不切实际的幻想,从各个图书馆现实情况出发,将发展技术的着眼点放在促进和提高图书馆现有的服务水平上。
如果我们能从价值回归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图书馆的技术应用,我们就会发现,技术应用的门槛似乎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技术更新的高频率似乎也没那么可怕。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一批有条件的大型图书馆,可以凭借着雄厚的资金和人才储备,追求技术应用的“高、精、尖”,在技术进步的大潮中勇立潮头。而对于大量中小型的公共图书馆、科研院所图书馆以及大学图书馆来说,也完全可以使用旧一些的设备,老一些的软件,来实现图书馆的技术应用。因为,当我们把技术应用与图书馆的价值实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时,技术本身的分界线就会被现实的价值取向所替代,技术应用或技术更新更多地表现为图书馆现实服务水平的提高和服务能力的改善。
因此,在具体图书馆的技术应用中,我们不必过多地关心那些源自纯技术领域的、关于技术更新的争论,如“传统的”或是“现代的”,“高版本的”或是“低版本的”,这对我们毫无意义。“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我们最宝贵的价值观和技术的设计与应用之间找到一种更好的联结。”[12]以消除我们对现代技术的种种“恐惧”和“忧虑”,增强我们对技术应用的信心和决心。因此,对我们来说,评价技术应用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就在于:技术是否改进了我们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