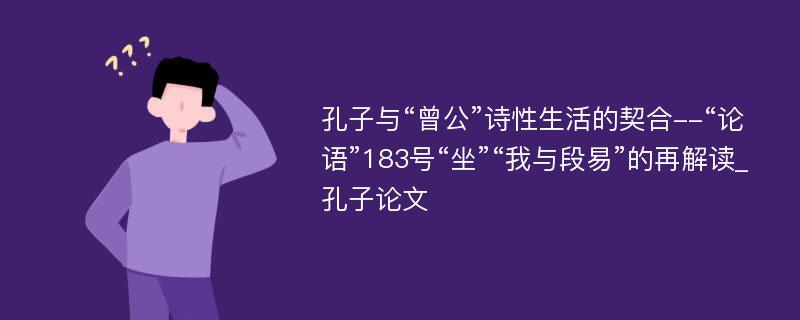
孔子认同曾皙平凡中的诗意生活——对《论语#183;侍坐章》“吾与点也”的重新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孔子论文,诗意论文,平凡论文,侍坐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千古谜题“吾与点也”
儒家经典《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言行的语录体散文集。入选高中教材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又名《沂水春风》)一文中,孔子让四位弟子说说各自的理想。子路的理想是治理一个内忧外患的中等的国家,冉有的志向是治理“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小国家,公西华的志向是在宗庙祭祀或者诸侯会同的时候做一个掌管司仪的官员。第四个弟子曾皙以“异乎三子者之撰”之语说出自己独特的“志向”:“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长叹一声说:“吾与点也!”
孔子一向鼓励弟子入“仕”。子路、冉有、公西华共同的志向都是从政做官,区别是后两个弟子的态度谦让,履行了孔子“治国以礼”中“礼”的思想。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孔子赞同的居然是第四个弟子曾皙的想法。孔子为什么说“吾与点也”,是个千古的谜题。曾皙“莫春者……咏而归”之语说的究竟是什么,历来争议颇多,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①(曾皙所述)不是儒家思想,而是道家的思想;而且这篇文字在《论语》中篇幅亦长,恐怕是战国时期孔门后学所记。[1]
②朱熹《四书集注》引程子曰:“孔子与(曾)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2]
③杨树达《论语疏证》:孔子与曾点者,以点之言为太平社会之缩影也。[3]
④曾皙是主张消极避世,符合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主张,因此孔子“吾与点也”。
观点①认为曾皙所述是道家“出世”理想,而主张积极“入世”的孔子不可能认同“出世”之道,因此怀疑《侍坐》中的文句为孔门后学误记。观点②③的共同点是均认为曾皙的话体现了孔子“礼治”的理想。曾皙的回答表面上虽与治理国家无关,却是“理想社会”的一个缩影,是“礼治”的结果,表示曾皙也有想经“礼治”而实现大同社会的理想,与孔子的“仁政”“礼治”的政治主张相符,因此孔子深表赞同,赞同的是曾皙以隐晦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政治理想,“与点”的实质是孔子之“志在入世”[4]。观点④认为孔子自知济世无望,产生消极退隐的想法,所以他和曾皙产生共鸣,因此“与点”的实质是孔子之“志在出世”。
孔子“吾与点也”,赞同的究竟是“入世”还是“出世”或是其他?
二、追求卓越与享受平凡
宋代理学大家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对“沂水春风”之语曾有一个解读,认为曾皙所说不过是“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5]。这个解读极其重要却被后人忽略了。“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就是接受现状,享受当下已经拥有的一切,简而言之,就是“享受平凡”。联系上下文,曾皙说“异乎三子者之撰”的潜台词是:“子路、冉有、公西华他们三个都是想通过做官的方式追求卓越,我曾皙却回归生活本身,把平凡的生活过好。”“异乎三子者之撰”之“异”处简而言之:三个同学追求卓越,而他享受平凡。
然而,令孔子赞叹的“平凡”,绝对不是那种习以为常、浑浑噩噩的平凡,而是曾皙享受的有些特别的平凡!
“莫春者……咏而归”说的是:暮春三月,草长莺飞,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轻装出发,去沂水中洗去尘土,到舞雩台上临风起舞,兴尽后一路上唱着歌回家。这是何等的悠闲、自在、快乐啊!这是何等的浪漫何等的享受呀!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吟出一句很美的诗:“生命充满劳绩/但仍然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哲学家海德格尔将这句诗的内涵发扬光大:“人生的本质是诗意的,人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沐风而去、高歌而归的沂水春风让曾皙们的心灵诗意地栖居。孔子被曾皙那种虽处平凡却超越平凡的快乐深深地感染了,从内心喷涌出“吾与点也”!他赞同的是曾皙那种精神灿烂之美,那种超拔于平凡现实之上的诗化的人生境界!简而言之,孔子“吾与点也”,认同的是曾皙虽处平凡却超越平凡的诗意生活!
曾皙三个同学的志向都是做官,所述都是政治理想,曾皙以“异乎三子者之撰”之语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不愿从政,而是回归平凡的生活。接着异峰突起,以光芒四射的沂水春风之语描绘出一幅暮春逸游的生活图景,表明自己会将平凡的生活过得蓬勃生姿、诗意盎然。曾皙的三个同学追求卓越,志在云天之上。云天之上是美好的,却高高在上;曾皙的话则是回归,回归大地,回归平凡的生活本身。高远的理想须深深地扎根在生活的大地之上。根深则枝茂,理想之树须充分地汲取生活大地中的养分才能枝繁叶茂,耸入云端。淡泊可以明志,宁静方可致远,安贫乐道、享受平凡正是追求卓越的前提和基础;把平凡的生活过得诗意盎然才能更好地追求“高远的理想”。
人生是由理想和根植理想的生活这两大部分构成。理想是树,生活是土壤。孔子一向鼓励弟子追求远大的政治理想,可他并不因此忽略生活本身的价值。由“吾与点也”可看出,在理想和现实生活两者之间,他深深地认同曾皙对生活的回归。
这种认同源于孔子的人生遭遇。让四名弟子“言志”时,他已经60多岁。他曾周游列国,希望按其“仁”的观点对当时的政治做一些改良,但由于战乱等多种原因,四处碰壁,最后只得回到鲁国讲学授徒,不再求仕。孔子为自己为理想奋斗一生却还是个平凡的小人物而痛苦。郁闷之中,曾皙所描述的那种虽处平凡却超越平凡的快乐和诗化的人生境界令他找到了方向,找到了归属感,令他产生强烈的共鸣,因此他“与点”。其潜台词是:“我奋斗了一辈子到头来还是个普通人,可是‘月圆是画,月缺是诗’,普通人也照样可以有诗化的生活!”
孔子本是让弟子谈谈各自的志向,曾皙回答的暮春逸游是“志向”么?这不是志向,也是“志向”!符合陶渊明式的追求自我心灵自由和精神清洁的隐士式的人生境界和道家的回归大自然,并与自然冥合为一,超然洒脱、逍遥闲适的“出世”之道。所以说,前人四种代表性的观点中,只有“曾皙是主张消极避世,符合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观点大方向是正确的。
三、浪漫的曾皙,人性化的孔子
既然孔子认同的是曾皙平凡中的诗意生活,孔子“与点”的实质是他“志在出世”,那么,为什么一些教学参考资料大多认为曾皙的话体现了孔子“礼治”的理想,是“理想社会”的一个缩影,是“礼治”的结果呢?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孔子一生的主导思想是儒家入世的思想,被后世尊为“圣徒”的曾皙自然应该“与圣人之志同”,同样应该积极入世,于是就将曾皙所说享受沂水春风的话和孔子的“礼治”理解生拉硬扯在一起,将曾皙的话生硬地拔高为“尧舜气象”“太平社会之缩影”“太平盛世之境”,是“礼治”后的结果。也就是说,“圣徒”曾皙居然把孔子奋斗一生却没有成功的那个“幻影”、那个结果说出来了,因此孔子“与点”。
其实,曾皙关注的并不是孔子奋斗一生却没有成功的那个未来,恰恰相反,他关注的是当下!曾皙勾画的暮春逸游图与高官厚禄无关,在当下即得的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实现(孔子四名弟子的志向以其高远指数而言,依次递减;然而以其变为现实的可能性而言,依次递升)。像曾皙这种把当下平凡的生活过得蓬勃生姿、诗意盎然的人,可以称之为“生活艺术家”,而前文写他“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就已经显出他具有浪漫、优雅、洒脱的“生活艺术家”气质了。至此,《侍坐》中四个弟子的“志向”可大致地分类为:军事家(“可使有勇”)→经济家(“可使足民”)→外交家(“会同”“小相”)→生活家(享受“沂水春风”)。
因此,曾皙说出“沂水春风”之语,并非因为他是洞彻“圣人”心中“幻影”的“圣徒”,而是出自他浪漫的“生活艺术家”的气质和隐士式的淡泊、宁静的性格,是出自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会有的对诗意的美好的生活的向往,和“入世”之道中的“礼治”又有什么关系呢?此外,前三个弟子都是谈怎么做官,共同点都是“志在入世”,如果将第四个弟子曾皙的回答生硬地拔高为“志在入世”,是“入世”后的结果,那么,四个弟子回答的都是“入世”之道,曾皙所说“异乎三子者之撰”究竟“异”在何处?岂不相互矛盾?(“异乎三子者之撰”之“异”处不是“治国方法”和“治国结果”的不同,而是“追求政治理想”和“回归诗意生活”这一本质的不同。)
另外,在朱熹等人看来,若认为孔子是赞同曾皙“消极避世”的,这对一生主导思想是“积极入世”并被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而言,是一种亵渎,于是将孔子“吾与点也”生硬地拔高为“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事实是,“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是朱熹从内心喷涌而出的正确的直觉,“盖与圣人之志同”则是刻意的人为的拔高。
在笔者看来,若认为孔子认同的是生活本身的价值,那么,具有和普通知识分子一样的真实性情的孔子,非但没有降低“圣人”的形象,反而更成就了“圣人”之“圣”!
原来,孔子这个貌似古板的人,和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心灵深处也有对美好的诗意的人生的向往,也有超乎残酷现实之上的浪漫情怀。这里的孔子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性化的孔子。向往平凡中的诗意生活的孔子,比那个挂着“大成至圣文宣王”招牌、正襟危坐且严肃古板的“孔圣人”,来得真实可信!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一“喟”一“叹”表现了孔子浓浓的人情味和纯净未染的赤子情怀。细细体会,“喟”“叹”声中其实融合了遗憾和向往这两种情感。
古今中外的所有人都在追求幸福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而“幸福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完美的人生”。孔子一生积极入世,为理想奋斗,他的人生有意义,却因在一个战乱频繁的年代辗转奔波,没有享受过曾皙所描述的那种悠闲、自在、浪漫的诗化的生活。他的人生有遗憾,因此他“喟然叹曰”!
然而“喟”“叹”声中更多的还是向往之情!沐风而去、高歌而归的诗化的生活是孔子所在的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朴素的幸福观。这种朴素的幸福与高官厚禄无关,不需要付出辗转各国、奔波劳碌的代价。事实上,越是精神层面的幸福,就越是简单、纯净、质朴,也就越容易实现。为理想辛劳一生却收获甚微的孔子被曾皙所描述的如此简单、质朴而又强烈的幸福深深地吸引了,情不自禁地以“喟”“叹”之声来表达他的向往之情!《论语·雍也》中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精神世界的灿烂可以消解现实世界的黯淡。无论是推崇“颜回之乐”还是“吾与点也”,都可看出孔子认同超然于物质享受之上的精神愉悦,认同平凡中的诗意生活,推崇于平凡、困苦的现实世界中享受精神层面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