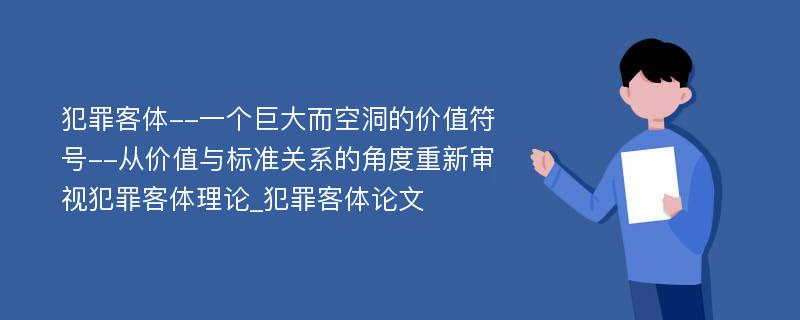
犯罪客体———个巨大而空洞的价值符号——从价值与规范的相互关系中重新审视“犯罪客体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客体论文,价值论文,空洞论文,相互关系论文,符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犯罪客体及其形成的理论观点和理论体系,本人曾专门写过几篇文章,对其历史的起源、形成的过程和现实的作用进行了一些大概的考察分析和理论批评,认为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在其历史的起源上是随着社会主义刑法理论中曾经出现过的政治需要高于一切、政治压倒法律的理论氛围的形成而产生的,其形成的过程,不过是一个为了政治需要而被一些偏离法学应当具有的价值中立的学者人为地吹起来的理论泡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成分的增加,犯罪客体的泡泡逐渐变成了一大堆理论泡沫;而其实际的作用在人治时期是一个无限夸大社会危害性作用的发动机、孵化器和膨胀器,在法治时期犯罪客体实际上是一个巨大而空洞的价值符号,是刑法理论的累赘。犯罪客体理论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必须对犯罪客体理论进行全面和彻底的否定,从而最终结束它在我国曾经无限风光的历史命运。当然本人也很清楚地知道,对犯罪客体理论进行理论性地批判和历史性地终结的这一历史过程,决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
然而近日刑法学者雪千里先生在《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年第六期上发表了《关于犯罪客体的几个问题》的与人商榷的文章,随后在《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三期上再次发表该文的下篇。文章既有历史考证的成分,也有理论讨论的成分。阅读之后,感到又被搅动了一池春水,觉得还有些话可以再说一下,可以再写一些。
一、犯罪客体神秘、神奇、神圣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蕴含的历史吊诡
当我们观察人类的刑法文明所经历的历史发展过程时,能够事先弄清楚一个刑法现象究竟来自于何方,对我们能够获得这一现象的价值所在以便使我们的思维方向不至于一开始就被淹没在扑朔迷离的烟雾之中是大有益处的,甚至以此为途径可以探索其最终又要去向何方。所以当我们再一次将犯罪客体作为理论讨论的对象时,不得不先考察一下犯罪客体的起源以及它如何在社会主义国家经历的从神秘到神奇、从神奇到神圣的发展过程。
客体一词本属于哲学术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相当广的领域内,它和对象一词具有同一性和同义性,以至于两者可以被经常地交替使用。客体一词被引入刑法领域一开始就与犯罪相联系,于是就有犯罪客体一词。但是当沙俄时代的刑法学者季斯甲科夫斯基在1875年第一次(据了解到的资料)将犯罪客体引入刑法领域时,却是清清楚楚地将其视为犯罪对象的同义词加以使用的。① 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俄时代很具影响力的刑法学者塔甘采夫也是把犯罪客体作为犯罪对象的同义词使用的。他认为犯罪构成具有三个要件:a.行为人——犯罪人;b.犯罪人的行为所指向的事物——犯罪客体;c.从内部和外部研究的行为本身。② 尽管据学者考察,塔甘采夫还写下另外一段话,把犯罪行为直接指向的具体事物称之为犯罪对象,把法律规范和生活利益称之为抽象的客体。③ 我们在这里不说塔氏提出的抽象客体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也不准备分析行为指向的“事物”等于犯罪客体后,又把它分解为具体对象和抽象客体的理由是什么。因为凭心而论,创建社会主义犯罪客体理论的前苏联刑法学者们对沙俄时代的刑法学者们的一切观点和理论都是不讲理由、毫不留情地进行彻底批判并加以抛弃的,因此在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血缘关系。但是,如果说沙俄时代的刑法学者已经把犯罪客体视为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的话,我想就已有的文字表述(也许是由于翻译的原因,至少在我看来有些文字的表述有点晦涩甚至是含混不清的)来看还是指犯罪对象的成分更多一些。当然,当我们穿过时光隧道重返刑法领域的“巴别城”,不知道从历史的沙砾和往事的尘埃中通过翻拣老例还可以找到一些新的“什么”?
但是必须指出的问题是,今天为我国许多刑法学者津津乐道的犯罪客体理论事实上来自于前苏联刑法学者的创造,它们与沙俄时代的刑法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已不存在血缘联系的过程表明这是一个另起炉灶的产物。而中国刑法学者所接触到所谓的犯罪客体理论应该是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开始的。从当时的基本状况来看,几乎主要来源于前苏联A·H·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和当时的一些前苏联的刑法教科书,特氏此书的雏形最早成书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而彼时正是全新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一统苏联社会和对资产阶级所有一切精神领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进行彻底批判的年代。以特拉伊宁和皮昂特科夫斯基为代表的新一代苏维埃刑法学者们即使接过了沙俄时代的犯罪客体这一法律术语,却完全赋予了全新的内容,这就是中国刑法学者们再熟悉不过的“社会关系”理论。特拉伊宁曾经写道:“每一个犯罪行为,无论它表现为作为或不作为,永远是侵犯一定的客体的行为”、“任何一种侵害行为的客体,都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义刑法体系中的犯罪客体。”④ 像我们在前苏联的其他一些刑法著作中所看到那样,很多的理论都未经和风细雨般的说理过程,就产生了带有武断性的结论。在理论层面,社会关系怎么变成了犯罪客体?在实践层面,通过什么方法来说明、来论证犯罪行为是怎样指向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关系的?这些问题在前苏联的刑法著作和文章中却是语焉不详,除了一些在今天看来完全是不着边际的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性语言论述外,实在是看不到其坚实的理论基础。于是,犯罪客体就变成了由一支“神来之笔”完成的神秘产物。
由于犯罪客体等于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属于精神的产物,它是基于物质的存在通过人的精神抽象和概括而形成的一种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尽管雪千里先生对社会关系作了一点新的解读,并引用了国外一些学者对社会关系的一些新的理解,认为社会关系与它的构成要素是分不开的。⑤ 但在这里,批评者将社会关系的精神表现与物质内容进行合一的过程时,先承认两者之间可以分解的结论倒是笔者非常赞同的。因为经过分解后,行为可以直接指向物质对象在理论上和生活中就不存在任何矛盾了。由于社会关系属于精神领域的产物,所以它是无形的;因为它是无形的,所以人们之间有无某种社会关系(除了血缘关系以外),主要在于人们内心的确认。人们之间的这种社会关系,既可以人为的“生”,也可以人为的“死”。人“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⑥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神奇性。将社会关系作为犯罪客体进行定义,并以此作为犯罪行为指向的对象,由于它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本质属性使然,所以一种犯罪到底侵犯了什么社会关系,就像社会关系本身一样变得复杂和神奇了,最后就看当事人怎么想和掌握话语权的人喜欢怎么说。于是犯罪客体的理论像“万花筒”一样不断变幻着五颜六色的“光彩”来,真是让人顿生一种过于神奇的感觉。不知道是否有太多的刑法学者曾经掩卷长思或者作过试验,将太多的有关犯罪客体的观点与理论做一下替换表述,它对我们本来想认定的犯罪到底起了一种什么样的规范作用?比如说故意杀人罪当中,毁灭一个有生命的犯罪对象的人和侵犯他人生命权利的客体,两者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区别;人们曾对贪污受贿罪到底侵犯什么样的客体进行过长时间的讨论,可是笔者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弄明白这些不同的客体理论的描述是否可以对案件事实增加一分钱还是可以减少掉一分钱?这种往往多元化的犯罪客体理论的表述和结论有多少能够经得起“证伪”的质疑?
但由于犯罪客体理论的这种神奇作用,由于中国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进程中的受教条主义式的思想僵化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刑法学基础理论基本上处于保守求稳的状态,以至于犯罪客体基本上仍然以一种固定的理论表述和传统内容被拼装在犯罪构成的框架中,坐久日大,尾大不掉,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好像就变得“神圣”起来而不可动摇了。无需多说,只要看看我们直到现在为止的众多刑法教科书和刑法论文就可知道。其实可以想象也已经看到和想到,中国的刑法学是在没有精神准备的状况下接受并移植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的。新中国政权的建立,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我们与前国民党政权下的刑法规范和刑法理论实行了彻底决裂,而我们又没有时间和精力甚至没有意识观念的自我觉醒来进行自己的刑法理论的修养准备,于是在“榜样正确”、“意识形态正确”的指导下的一知半解甚至囫囵吞枣的过程中将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当然包括了犯罪客体的理论)移植到我国来。太多的犯罪客体的理论表述不过是我国刑法学在意识观念深层中顽固保守的体现,在表现形式上依然迷恋于“假、大、空”这一过去旧时代浮夸作风的体现,在内心精神欣赏方面甚至是一种精神“自恋”的体现。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入门于刑法学的,一开始就接受着那种充满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为内容的犯罪客体理论的意识熏陶和技术训练,很多人因此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就好像在森林中被哺育成长的“狼孩”一样定型了,这是一代人的一种历史缺憾。好在时代在前进,世界在变化,观念在更新。国门被打开以后,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参照物甚至有了异质文明可以作为参照、衡量系数,今天完全可以进行比较、分析了,只有经过思辨之后和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结论才更有价值。只要我们同当今世界的多元化的刑法理论进行比较,就会发现犯罪客体理论其实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因为它不过是一种人为吹起来的理论泡沫。现在可以这样说了,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不信这一套,对于各种按照人类文明观念和善良风俗确认的自然性犯罪(这里不想涉及到所谓的法定犯)不是照样一样认定的吗?在我国其犯罪性质并不因为多了一个犯罪客体使犯罪性质变得异样了。既然犯罪客体的理论所拥有的这种神奇实在是不足为人多言,那么我们就有责任消除它的不必要的影响,以至于更应当撼动犯罪客体的“神圣”地位,消除其所拥有的“神奇”光彩。我们每一代刑法学人都有自己反思和进取的任务。经年五十,方知四九之非。对于年长一代的刑法学人来说,需要反思的是自己如何继承和发展犯罪客体理论的?对于年轻一代的刑法学人来说需要思考的是自己为什么还要继承和发展犯罪客体的理论?如果需要,应当怎样继承和发展?如果不需要,那么现在是否可以考虑要不要“冲出”犯罪客体理论的“亚马逊”沼泽以及如何“冲出亚马逊”?
二、犯罪客体到底是属于规范的产物还是属于价值的产物?
随着我国刑法学者开始对犯罪客体进行的不断反思和渐进式的否定,又有一些刑法学者开始对犯罪客体进行技术改造和“器官内脏”的移植,于是有了生产力说、法益说、社会利益说、社会秩序说等等学说取代社会关系说的倾向。但是在对犯罪客体进行技术改造和“器官内脏”的移植之前,笔者认为应当首先解决一个问题,即犯罪客体到底是属于规范的产物还是属于价值的产物?它到底能够起什么作用?
刑法是一定价值的产物,但刑法制定后却是以一种规范形式加以表现的。正因为刑法是一种法律规范,因此只有经过刑法的具体规范性的设定,才可以起到对社会行为的规范作用和对犯罪行为的认定作用。比如说故意杀人罪,只有当刑法明确规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杀人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杀人的行为,其针对的对象必须是有生命的自然人才算有了规格标准。在这里真正决定行为的性质属于杀人的应当是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内容,这里有没有一个所谓的他人的生命权利对于行为性质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因为有生命的人的这一对象属性本身已解释了这一点内容。多说一句无所谓,少说一句也不会影响到行为指向的对象的本质属性。所以在故意杀人罪的条文规范之中并不存在一个犯罪客体的问题。同样在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中,只要行为人明知故犯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心理罪过,客观上采取不为他人所知的秘密方法非法窃取“他人的财物”,其行为指向的是“他人的财物”,就可以认定为盗窃罪。这里的他人财产的所有权,不过是盗窃罪在设立之时的一个价值评价根据。在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中并没有这一规范要件。所以刑法中真正具有“价值”意义的是规范内容,而犯罪客体不是规范的内容。所有“犯罪客体”要涉及到的社会关系、社会利益、社会生产力、社会秩序或者法益,都是刑事立法时的价值评价根据的体现,他们无法直接转化为规范内容。
仔细想来,现有刑法理论言说的犯罪客体理论,放在形而上的高度再去评说一下,无论就其形式说也好还是就其内容说也好,不过都是犯罪概念要讨论的、已经言说过的形式和内容。所有的犯罪客体的内容与“犯罪”概念所要揭示的内容完全一样,是对事物高度抽象和概括的产物,是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因此它可以作为一种意识观念在人们观察客观事物和认识客观事物时起指导作用,但它本身不是衡量事物的规范依据和尺度标准。也正因为如此,许多的犯罪客体理论在刑法总则抽象理论中描述客体时头头是道,一到刑法分则时就王顾左右而言他,大多数都重复着刑法为什么要把某种行为设定为犯罪的原因和理由,或者干脆以犯罪对象搪塞过去。比如说现行刑法规定贪污受贿罪的数额要求一般为5000元人民币,那就意味着4999元就不能构成犯罪。此时把贪污受贿罪的客体理论再怎么发挥得淋漓尽致,达不到5000元的规范要求,行为就是不能构成犯罪。反过来说,数额一到5000元,就“产生”了一个贪污受贿罪的客体了。难道这贪污受贿罪的犯罪客体就存在于1元钱之中吗?也许我们在这里这样设问有点极端,但有谁能解答这样的疑问呢?在贪污受贿中,人们经常讨论到它的客体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很多人却睁眼不看中国的实际国情。因为在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着一个令人非常担忧和十分危险的现象。由于贪污贿赂犯罪的普遍性、大量性和严重性,已经成了中国当代社会腐败的代名词。这不仅造成了“公仆”的话语叙事招致太多的诟病从而背负着重重的骂名,因此也让整个“公仆”阶层在当今的社会公共事务中集体蒙羞,成了中国社会众多民怨民愤指控腐败的“第一被告”。“贪官可恶、贪官该死”已被民间社会视为是贪污贿赂犯罪的天谴魔咒。所以通过价值抽象,我们完全可以说贪污受贿罪的“犯罪客体”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安全和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这样说又有什么错?但即使把话说到这一程度,没有具体数额的这一犯罪对象的支撑又有多大的价值呢?理论上不是有一个犯罪客体的三种类型和三个层次的划分,它们是一种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是一种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但何为具体?何为抽象?不知这里是否蕴藏着一种一直被我们有意忽略不计的诡辩成分?
说到规范与价值的相互关系以及两者存有的区别,我们不得不提到英国哲学家休谟曾经为人类提出了事实——价值二元的命题。刑法根据预设的、虚拟的犯罪事实设置了一定的犯罪构成,这是一种法律规范;行为人实施一定的行为(包括加上直接指向、施加影响或者发生作用的犯罪对象),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这一客观事实一旦符合法律规范,就变成了法律事实。但法律事实就其本身来说,依然是一种客观事实。在这个事实当中,本没有价值的存在,但人们可以给它一个价值。价值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社会的活动主体——人根据自身的需要而对客体设定的一种精神取向。于是乎对同一个客观事实由于人的精神观念和价值取向的不同,产生不同的价值评价和价值判断就不足为奇了。联系到为什么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中有时对某一个犯罪的客体到底是什么会产生如此多的分歧意见和不同的描述,其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此。刑法中的犯罪构成是就犯罪的行为事实作出的一种模型规格的预先设定,所以在这种犯罪构成的规定中并不存在着带有价值性质的“客体内容”,传统的以社会关系(即使被换上其他一些新名词、新名称,也仅仅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技术改造而已)为内容的犯罪客体实际上是存在于犯罪构成之外的价值评价和价值判断。正因为如此,1979年刑法将贪污罪设置于侵犯财产罪之中是贪污罪,1997年刑法将其设置于财产罪之外的独立一类犯罪中依然是贪污罪。1979年刑法将受贿罪设置于渎职罪之中是受贿罪,1997年刑法将其设置于渎职罪之外的独立一类犯罪中还是受贿罪。1979年刑法将私藏枪支弹药罪设置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是私藏枪支弹药罪,1997年刑法将其设置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中不还是私藏枪支弹药罪吗?即使有一天我们设想将贪污受贿罪恢复到原有犯罪类别中或者干脆移至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之中,落实到具体的罪名上,不还是贪污受贿罪吗?同样即使有一天我们取消了所谓的金融诈骗罪,将其全部回归还原到普通的诈骗罪之中,依然改变不了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心理事实和客观上骗取钱财的行为事实。这样的犯罪在1997年修订的刑法中被重新调整移位可以说有太多的例子。这说明价值的趋向我们随时随地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但事实依然如此。以这一事实为基础的刑法规范的具体内容也不过只能如此。
有时想想其实道理很简单。为了干净,必须扫地。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随地吐痰,会污染环境,所以必须严禁随地吐痰。为了严禁随地吐痰,就得进行惩罚。如果有谁随地吐痰,谁就必须接受惩罚。干净和污染,既是一种人们的价值评价和价值判断,也是一种主观的观念认定,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客观的结果状态。但它却不是一个行为过程和一种行为事实。如果我们大讲特讲干净的好处和污染的坏处,而不去告诉人们怎样去扫地,什么叫吐痰,至多让人们明白了一个为什么,仍然没有讲清什么叫扫地,什么是吐痰的道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构成帮助人们搞清楚的是犯罪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价值只有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但价值本身并不是事实。刑法不仅仅给人看的,更主要的是为了用的。所以犯罪构成的设计是基于行为事实为基础、通过规格模型能够加以规范行为、认定犯罪的依据,所以犯罪构成的内容应当是、也只能是事实,而不应该是价值。不管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被演绎得如何豪华,甚至存在过太多太多的多样性理论和选择性意见,实际上都无法进入客观事实内部而改变客观事实的本身存在。有人以曾轰动京城的刘海洋“硫酸泼熊案”最后定为故意毁坏财物罪为例说明财产所有关系这一犯罪客体在犯罪认定的作用,⑦ 我们不说此案在进行价值评价时曾产生过其它不同的一些意见,就故意毁坏财物罪来说,黑熊本来就是动物园里的财物,已属于他人财物的对象范畴,当然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对象要求了。如果说黑熊属于被保护的野生动物,那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就不能定罪,因为刑法中没有这样以野生动物为毁坏对象的犯罪构成。而如果行为人是捕杀野生黑熊,那当然有非法捕杀野生动物罪来进行规范。因为这里有行为和对象的物质现象的存在。只要明确了犯罪对象性质,没有所谓的犯罪客体理论不是一样可以定罪吗?与犯罪客体何干?
三、从价值与规范的相互关系中重新审视犯罪客体理论
刑法是用来做什么的?从狭隘一点的意义上说,当然是用来认定犯罪的。怎么来认定犯罪?就看模型规格怎么设定。那么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中就没有价值的应有地位吗?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只不过在现代刑事法治的司法过程中我们必须坚守住“规范先行,价值随后”这一原则。我们在这里这样说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基础和基本判断,那就是现有的大多数学人讨论到犯罪客体问题的时候,是将自己置身于刑事司法过程中而展开的。其实价值与规范的相互关系,在刑事法治建设过程中具有不同的要求。在刑事立法的过程中,规范必须依据于价值而创立;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价值必须依据于规范而发挥。只要当犯罪客体的形式和内容来源于价值而没有、也无法形成规范,那么注定它在司法过程中不能、也无法起到规范的作用。但是当行为事实已经符合犯罪构成这一模型规格的规范要求后,其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评价和判断在某种意义上倒是价值观念在其中发挥作用,这里有一个执法者可以进行“自由裁量”的问题,但“再自由”也不能突破规范这一底线。
那么价值与规范本身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笔者认为是一种多元与一元的关系。从价值到规范的过程是一个多种利益冲突、多种观念分歧经过利益调节、观念调整走向一元的过程。人们生活在现实社会中,有着太多的自我需要(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难免存在着彼此的爱好有异,各自的目的不同,相互的利益冲突,人生态度相左……,即难免会陷入彼此的竞争、冲突、斗争甚至战争,这在社会利益的分配过程中突出地表现出来。从以往到目前为止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利益的有限性,绝难满足一切人的全部需要,于是社会需要一定的规范来支配有效的分配,以使争执冲突的双方不至于两败俱伤或者同归于尽,从而就产生了一定的社会规范。可以说规范的产生过程是一个价值的遴选过程,充满着价值的冲突。当规范一旦形成,原先所有的价值冲突都让位于取得支配地位的价值标准,这一价值标准就是规范本身。坚守规范形式,其实已经体现了规范背后最高的价值原则。如果撇开已有的规范,又意味着价值标准的混乱。
我们说价值协调、价值评价和价值判断是规范产生的基础,规范形成以后又是进行评价的标准。但规范从来不是评价自己的标准,正像尺从来不会衡量自己的长短一样。所以价值、价值判断一旦转化为规范以后,再对其他客观事物进行评价的时候,规范就成了唯一的(在社会现实中,大概只能属于主要的)标准。同样如此,刑法是价值的产物,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定的。但当刑法根据一定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要求被制定出来以后,其形式是一种规范标准了。“规范是需要理由的,是需要论证的。”⑧ 一种社会行为之所以被规定为犯罪,在于它的社会危害性使然。为什么这种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在于它侵害了既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利益。所以在刑事立法过程中,规范之所以成为规范,必须要给出理由,必须要加以论证。但规范已经成立了,它就已经对评价活动具有了约束的作用和力量。不能因为有人不想承认法律规范的理由及价值而可以逃避法律对他的约束。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都已经在刑事立法的时候和整个刑事立法过程中已经解决了,所以还有什么必要在认定犯罪时再不断地进行回炉烘烤、翻炒蒸热呢?正像贪污受贿罪的数额要求一旦定为5000元,就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讨论为什么不是3000元、4000元,也更没有必要再讨论、探寻它到底侵犯了什么社会关系、社会利益。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机械一点的话)只需要查证和讨论的是行为人贪污受贿(这里不讨论证据效力和行为性质)的数额是4999元还是5001元?
有批评者提出,价值的东西在某种特定的场合依然可以成为某种客体(即对象)的,比如说在价值论的研究中,价值论是把价值当成自己的研究客体的。⑨ 这其实是一种不该有的误解。正像英文中,“I”作为“我”的表示时只能是大写的,因而只能与“am”相对应,但作为字母表中第九个字母排列是可以用作小写的,因而可以与“is”相对应,但此时的“i”已不是彼时的“I”。当价值论把价值看作自己的研究对象时,别忘了此时价值不过是研究的对象,而不是行为指向的对象,这里既谈不上是客观的对象,也谈不上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客体。所以笔者曾在《犯罪构成原论》一书中曾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此,这里的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是研究的对象,说得更直白一点的这只不过是思想的对象,仍然没有偏离物质对物质、精神对精神的哲学范畴所揭示的基本原理。
本人在《犯罪构成原论》一书中还写道:“此次新刑法的修订(指1997年刑法修订),刑事立法者增设了许多的罪名,有的犯罪在现实生活中还未产生,例如危害国防利益罪中许多只有战时才能构成的犯罪。对此我们不能说没有刑法所要保护的某种社会利益。但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却认为,没有犯罪行为,就没有犯罪客体。这不能不说是传统犯罪客体理论一个明显的矛盾和缺陷。”⑩ 有学者批评这里存在着相互矛盾之处。说其中一个明显的错误在于作者把刑法的保护客体与犯罪指向的客体相互调包,因而“在逻辑上违反了同一律。显然,作者在否定同一律的同时,也否定了自己的论述。”(11) 也许对同一段描述,每个人的理解有所不同,这就是价值与事实相差异的原理使然。但我想从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来看,他们所说的犯罪客体就是刑法保护的社会利益(社会关系),所以作者指出了没有犯罪行为就没有犯罪客体的结论的错误所在。而恰恰在批评者眼里将刑法保护的客体与犯罪指向的客体作了区别后(其实在批评者眼里不应该有区别),将它强加在作者头上。这是一个由解读错误引发的误会,这里不想小题大做。倒是批评者又提出一个“侵害客体”的新名词,看得出这个侵害客体,在批评者那里完全可以理解为侵害对象,由此本来不同观点的持有者又回到了客体等于对象的同一起点上了。
由于刑法主要规定的是哪些行为可以构成犯罪,怎样构成犯罪的,构成的什么罪。也正因为刑法是一种行为规范,所以当一种行为要进入刑法被进行评价之时,需要通过一定的行为模型作为依据、作为标准加以衡量。一定的行为事实包括一定的心理事实一旦符合犯罪构成的模型标准,行为就可以被认定为犯罪。一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依据一方面来自于实现已经设定好的刑法规定,另一方面来自于行为人的行为事实。由于刑法是针对行为进行的犯罪模型设定,行为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所以无论是刑法中预设的行为还是社会生活中实际实施的行为,它只能针对物质的客观事物,正所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12) 物质对物质,精神对精神的哲学原理不过表明,精神力对物质,不过是纯粹的空气震荡,精神力量只有转变为物质力量才能具有强大的摧毁力;物质力对精神,就像唐·吉诃德大战风车,实际上是跟幻影作战。无论是传统的犯罪客体被描述为社会关系,还是被替代为社会生产力、社会利益、法益或者社会秩序,都是精神的抽象产物,都属于精神的范畴,它们何以能为物质的行为所直接指向呢?行为人持刀砍向他人,到底要杀人还是要伤人?抑或是为了抢劫或者强奸?其精神的需求存在于行为人的心理活动中、存在于其属于精神范畴的目的之中。犯罪行为受人主观心理活动的支配,由于犯罪故意罪过性质决定了犯罪行为的性质,当这种行为指向了法律已经明文规定的一定犯罪对象时,其犯罪的性质也就定型了。因此,就事物的本质而言只能存在于事物的本身内部,与这一犯罪行为事实(包括心理事实)之外的所谓犯罪客体(社会关系或者社会利益等)没有什么联系。也正因为如此,作为精神层面的所谓“犯罪客体”在刑法中没有一字的规定,所谓的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力、法益、社会利益或者社会秩序在具体的犯罪构成设计中难觅踪影,而只是在对事物的本质抽象的犯罪概念中被描述、被提及,只有在刑法的任务这样一种价值取向中被提及、被规定。它们完全是独立于行为事实和规格模型之外的一种价值评价和价值表现。
注释:
①沙俄时代的刑法学者季斯甲科夫斯基于1875年第一次在其著作《普通刑法初级读本》中提出犯罪构成的四要素:一、犯罪的主体或实施人;二、客体或犯罪加于其上的对象;三、主体的意志对犯罪行为所持的态度或是他所表现的活动;四、行为本身及其结果或是主体的外部活动及其结果。参见[前苏]A·H·特拉伊宁著:《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王作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99页。可见,季氏将犯罪客体引入刑法领域是与犯罪对象作为同义词使用的。
②参见[俄]塔甘采夫著:《俄国刑法》,俄罗斯图拉出版社2001年版,第394页。转引自雪千里:“关于犯罪客体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年第6期。
③转引自雪千里:“关于犯罪客体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年第6期。
④[前苏]A·H·特拉伊宁:《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王作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1-102页。
⑤参见雪千里:“关于犯罪客体的几个问题(续)”,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3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⑦参见雪千里:“关于犯罪客体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年第6期。
⑧孙伟平著:《事实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41页。
⑨参见雪千里:“关于犯罪客体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3期。
⑩杨兴培著:《犯罪构成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11)雪千里:“关于犯罪客体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3期。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