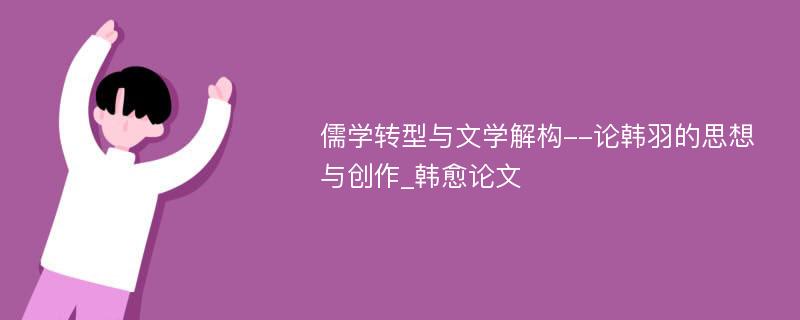
儒学的转型和文学的解构——论韩愈的思想与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韩愈论文,思想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安史之乱”是唐代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此前的天宝初年,整个社会是一片繁华兴旺、歌舞升平的景象,士人的心态也是昂扬和开阔的。而安禄山起兵的“渔阳鼙鼓”,惊破了统治者的盛世酣梦,也送走了士人的和平心境。此后,在无休止的兵戈纷扰、政治动荡之中,整个社会心态从张扬转入内敛。尤其是藩镇割据以后的政治多元化,更促使人们从求同走向求异,从师法转为师心,社会上的公共话语,也越来越变得私人化。同时,与士人们的迷惘和失落的情绪相适应,整个文化界弥漫着一种寻求刺激、求奇尚怪的气氛。人们敏感于超常的事物,社会上的灵怪之风大盛。而文人们亦以奇特风气相高,往往喜欢以不同寻常的风格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方面,以韩愈等人在元和年间提出的尚奇言论最为典型。如韩愈《答刘正夫书》:“家中百物,皆赖而用也,然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文,岂异于是乎!”皇甫湜《答李生论诗书》:“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鸟雀;金石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孙樵《与王霖秀才书》也说:“鸾凤之音必倾听,雷霆之声必骇心。龙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储思必深,饬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以之明道,则显而微;以之扬名,则久而传。”这些人对奇文的极力推崇,正是当时趋奇的社会风尚的反映。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中唐以后的文坛呈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光怪陆离的境界。王谠《唐语林》卷二说:“元和以后,文笔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继,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傥,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这正是对中唐以后文坛巨变的真实写照。而其中所说的浮、荡、涩、浅切、矫激等,从广义上来说都是一种独创的个性化的奇特风格。换句话说,尚奇,是中唐以后文学发展的基本倾向。
而中唐人对于奇特风格的追求与创造,是以一种对既定的传统艺术规则的破坏和“解构”的姿态来进行的。这种“解构”倾向的产生,既有非常深广的社会背景,也是艺术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从社会背景上说,安史之乱以后,唐帝国由极盛转入衰微,政治上的王纲解纽,军阀混战中中央政权的名存实亡,都促成了人们头脑中政治权威的轰毁。而人们对政治权威的藐视,在文化艺术上即表现为对现成秩序的冲击。从艺术发展自身的规律来讲,盛唐的文艺,在很多方面都达到传统的峰极。诗也好,文也好,都在扬弃六朝的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成熟而稳定的审美取向和艺术表现模式。《老子》云:“反者道之动”,艺术要继续发展,必然要求打破现成的秩序、拆解既定的结构。
唐代中后期的“解构”潮流,其先驱是两个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一位是活跃于安史之乱前后的颜真卿,另一位就是安史之乱以后执文坛之牛耳的韩愈。前者是艺术解构的代表,后者是诗文解构的代表。关于颜真卿等人在艺术上对前人的解构,拟另撰文专谈。本文只谈韩愈的解构思想与创作倾向。
不论在中国文学史,还是思想史上,韩愈都是一个重要人物。苏轼曾经以两句话来评价他的贡献:“文起八代之衰,道拯天下之溺”。前句话说的是他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后句话说的则是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韩愈是中唐时期解构旧的文体、创立全新的文章话语和风格,并取得了实绩的关键人物,又是开辟了儒家的汉学向宋学转型的先驱。而这文学的解构和思想的解构,在韩愈那里是密合在一起的。在当时和后世,韩愈有一大批追蹑者,他们对韩愈的评价极高,且都是把韩愈的“道”与“文”亦即思想与文章的成就相提并论的。如皇甫湜说:“抉经之心,执政之权。尚友作者,跂邪抵异。以扶孔子,存皇之极。茹古含今,无有端涯。鲸铿春丽,惊耀天下。栗密窈渺,章妥句适。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来,一人而已”(《韩文公墓志铭》,《全唐文》卷六八七),说韩愈的思想与文章都上追周孔,堪与圣人比肩。宋代的古文家们也这样评价韩愈,比如石介曾专门写过一篇《尊韩》,文中谓天下圣人是从伏羲氏开始,中经尧舜禹汤文武,到孔子,“孔子为圣人之至”。而天下的贤人是从孟子开始,中经杨雄、王通等人一直到韩愈,“吏部为贤人之至”。在他的眼中,韩愈的“文”与“道”,都与圣人经典一样为至高的典范,“吾之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文也”。所有这些评价,虽然不无主观因素在内,但却可见韩愈在思想和文学上对后世影响之巨大和深远。
当然,韩愈虽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却不是一位卓越的理论家,因为他虽能在文学和思想上开一代之风,却不善于从理论上阐述自己的观点,不能直接给我们一个具有严密逻辑的理论体系。相反,他对自己思想的阐述显得驳杂、零碎,不同地方的观点时有矛盾,甚至同一文章的前后观点亦相龃龉,所以苏轼说他:“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迤,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韩愈论》,《苏轼集》卷四三)。而这一点,恐怕也是我国古代多数作家的共同弱点。故我们阐释韩愈,需要剥开芜蔓,取其内核。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到这位文化巨人的思想及其价值。
韩愈的儒学思想和文道合一的理论
韩愈在思想上属于典型的儒家。在当时统治者佞佛的潮流中,他为了捍卫儒家的正统地位,攮斥佛老,几乎丢了身家性命,但仍然“虽灭死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在对古文的倡导中,他曾一再强调自己的本旨并非单纯的倡文,而是“志于道”:“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哀辞后》);“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争臣论》)韩愈所谓的道,指什么呢?他说:“吾所谓道也,非尔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也。”(《原道》)足见韩愈的道指的是儒家之道。他是以儒家思想的复兴者来自命的:“寻堕绪之茫茫,独劳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挽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进学解》)。韩愈是儒家道统说的提倡者,他把自己看作是绍续儒统的人。在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自己宗祧对象的论述:
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杨,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原道》)
这就是说,他认为孟子是他之前最后一位正统儒家的代表,孟子之后的荀子、扬雄之辈,则乖离了正统。故韩愈直宗孟子,并自比孟子,立志承续早已失掉了的圣人之道。他说:“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杨则之墨,杨墨交乱,而圣贤之道不明”;而他所处的时代,是“释老之言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在儒家道统中独许孟子,这是韩愈在许多地方都表达过的意思:“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孟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为孔子之徒殁,尊圣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杨雄书,益尊信孟氏,因雄书而孟氏益尊”;“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杨,大醇而小疵”(《读荀》)。“自孔子殁,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吾少而乐观焉”(《送王秀才序》)。
韩愈之所以独推孟子之学,与孟子的思想体系为精致的心性之学有密切联系。孟子的儒学理论,以先验的心性为本体,以道德修养的自我完满为旨归。在战国时期,他以内向的路线重铸儒学,与荀子的外向路线形成鲜明的对照。而正是孟子的心性之学奠定了中国心学的基础,它不但对后来的儒者,而且对于佛学都有重大影响。可以说,如果没有孟子,也就不会有后来道安的佛性论,更不会有禅宗等大乘佛学的兴起。但两汉以来的儒家内部,只重视经典文本的章句训诂,以对经典的外在阐释为唯一要务,丢掉了孟学这一宝贵资源。魏晋以来,儒学更是在佛老的冲击下走向式微。迨至唐代,在三教争雄的局面中,儒学处于最弱的劣势,其原因,就是因为它一直停留在汉代的经学水平上,颜师古、孔颖达等人所修的《五经义疏》一直被奉为儒家的圭臬,便是明证。事实证明,儒学若不在内容上革故鼎新,则会被威势显赫的佛禅挤出历史舞台,成为绝学。这就是唐代儒者所面临的严重局面。而复兴儒学的关键,必须在原始经典中找到具有现实性和生命力的资源作为号召。这,便是韩愈为什么提出儒家道统、并在道统中独宗孟子的原因。一句话,他要以孟子的心学为起点来重铸儒学,以抗衡在当时士人心中极有市场的佛学心学。再从当时儒者的心态来看,安史之乱以后,国势的急转直下,亦使他们的思想由开放转入内敛,由兼济变为独善,由寻求外在的事功转而追求内部的涵养,这又是中唐以后儒学转型的社会心理背景。而儒学的这种转型,就是首先从韩愈的道统论和宗孟论中透露出来的。孟子在儒学宗统中正式被尊为亚圣,始于宋儒;而宋儒的尊孟思想,则来自韩愈(注:正因为韩愈绍述孟子,也使他本人在后世人宗祧的儒家道统中得以与孟子并列。皮日休咸通中上书,请以《孟子》为学科,并以韩愈配享太学,即已开孟、韩并列之先。宋代石介、欧阳修、苏轼等人皆在道统上以昌黎追配孟子。宋人诗中常把韩愈与孟子相提并论,如王安石“韩公既去岂能追,孟子有来还不拒”(《秋怀》);“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奉酬永叔》)等即是。而欧阳修、曾巩、朱熹、杨万里、陆游等人在文中皆称“孟韩”。)。
当然,韩愈对于儒学转型的贡献,决不止于透露消息,他做了具有实质性和开创性的思想引导,这集中表现在他对孟子的思想核心的阐发上。我们注意到,韩愈于儒学首重“仁义”二字:“平生企仁义,所学唯周孔”(《赴江陵途中作》);“仁义存乎内,彼圣贤者能推而广之”(《答陈生书》);“行乎仁义之途,游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失其源”(《进学解》);“必出入于仁义,其富若生蓄万物,必具海涵地负,放恣纵横,无所统记,然后不烦绳削而自合也”(《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如此等等,都是这类说法。而“仁”与“义”,正是孟子的理论体系中带有本体性的核心范畴。《孟子》七章中曾屡次强调过它,如“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下》);“舜明乎庶物,察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下》),如此等等,说明孟子的哲学正是以“仁义”为核心的。而韩愈在这一点上与孟子完全一致,他在《原道》一文中曾经强调地说:“吾所谓道德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谓道德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己之言也”(《原道》)。清人钱大昕对韩愈在此处的论旨有一段深入的阐发:
老氏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又云:“大道废,有仁义”——所谓“去仁与义言之也”;孟子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所谓“合仁与义言之也”。退之《原道》一篇,与孟子言仁与义同功。(《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原道”条)
这里,钱大昕在阐释韩愈的论旨时特别点出他与孟子的“仁义”说的联系,是对孟韩思想之相通深有会心的。而在孟子看来,“仁”与“义”的本体为心性,它们作为人们的先验的善良本性,原本即存在于人心的内部,是无待于外的。人们学道的目的,不过是“反求诸己”,在自己的内心发现本已有之的仁义之性而已。这用孟子的话说,即“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离娄下》)。在孟子那里,儒学的最高目标并非建立外在的事功,而是内在仁义道德的修养。一个人如果在内心树立了仁义,虽无待外化,而必然外化为仁行义举。故孟子反对把学道的目标定在外部,而主张定在内心道德的自我完成。而这也就是转型之后的宋学所专门致力的“内圣”的基本倾向。韩愈对内在仁义的强调,正反映这一转型的开端。与孟子一样,韩愈特别强调仁义之道德的“无待于外”的特点:“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谓之德”(《原道》)。如果说,这种思想在韩愈那里还稍嫌简略的话,那么它到了韩愈的门人李翱那里,就颇具系统了。李翱的《复性书》,是在韩愈的直接启示下写出来的,它阐扬孟子的先验心性说,又从作为论敌的佛教禅宗那里借用了某些思路,从而明确显示了道学的理论面目。
正是出于这种以内在的道德为本的思想,故韩愈谈作家写作的条件,也就特别强调主观心性的修养。他说:
夫所谓文,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气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淅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成人,辞不足不可以成文。(《答尉迟生书》)
将蔪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答李翊书》)
韩愈把作家的文采看作是他内在德行的必然表现,故提高文学才能必须以修德为基。修什么德呢?当然首先是儒家的“仁义”,“道德之归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这一点,是韩愈与他之前不少提倡古文的儒者一致的地方。入唐以来,先后曾有一批儒者倡导古文,而他们的共同观点就是倡导作文要以道德为根本。如裴行俭说:“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旧唐书·王勃传》引),梁肃谓作家“必先道德而后文学”(《长州刺史独孤及文集后序》);李华亦谓“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如此等等,都是同样的论述。但韩愈毕竟是个文学家,他比这些先驱者进步的地方,在于他所强调的作家之主观修养中,不仅仅只是仁义道德的修养,更重要的是文学素养的长期陶冶。他发挥了孟子的“养气”之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必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答李翊书》)。韩愈所谓的“气”,与“德”有关,但不同于德,它实际上指的是作家经过长期的涵养,从雄厚的内部积累中所产生的卷舒自如的思维能力和表现能力,从“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上看,它主要指的是作家自由驾驭语言的能力。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韩愈讲作家读书,在强调“游于《诗》《书》之源”之外,又特别强调博览百家之言。他介绍自己的读书经验和写作借鉴之范围:“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以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答侯继书》);“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诘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总之,是“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进学解》)。这是一种畅游于广袤浩瀚的文化遗产的海洋中汲取精华,并经过长期的涵泳过程以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的态度。它与前代的古文倡导者所强调的“经术之外,略不婴心”(萧颖士《赠韦司业书》);“非夫子之旨不书”(李华《赵郡李公中集序》)的论调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后来的宋儒往往攻击韩愈的“志于道”只是一个幌子,如王安石《韩子》诗云:“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谁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说他并非识“道”,只是于文章这一末节上主倡“务去陈言”而已。理学家朱熹也说他“只是要做好文章,令人称赏而已”(《沧州精舍谕学者》,《朱文公文集》卷七四);“终生用力深处,终不离语言文字也”(韩愈《与孟尚书书》考异)。这样的评价,对于韩愈来说可能有些冤枉。因为他的“道”决非幌子,而是与他“务去陈言”的文学思想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韩愈的“道”是个内在的标准,对于作家来说,强调其内心修养是根本的修养,也就等于要打破作文要遵从的一切外在窠臼。前人于学问之事,主张“宏中而肆外”,通过内部的修养宏其中,为文必然会表现为肆其外。因此,韩愈对于作家,其内部主“宏”与外部主“肆”密切相联。换句话说,他的力主内修的道论与力主创新的文论是密合在一起的。
韩愈对诗文的解构及其观点
中唐至晚唐,与社会政治和士人的心态的剧烈变动相适应,文坛上出现了一股求奇尚怪、在形式与风格上嘎嘎独造的文学潮流。因为这一潮流所致力的,是对唐以来已臻成熟、稳定的艺术范式的拆解和颠覆,故可称之为“解构”的潮流。这一潮流的中坚,就是韩愈和他的追蹑者,而韩愈是其思想领袖和开风气之先的人。
在不少人看来,韩愈在文章上所革除的只是齐梁以来的骈偶风习,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从唐向前推算,“八代”之衰,是从汉代开始。这就是说,韩愈不只是齐梁骈偶风习的涤荡者,他也是振起汉以来文章衰风的人。苏轼的这种说法,与韩愈自己关于文章革命的对象的说法是一致的:“唯古文章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足见他所努力矫正的,是汉以来就逐渐形成,而且直到他所处的“今”还依然存在的“一律”,亦即传统的、固定的文章风格和范式,而不只是隋人眼中的“编句不只,锤句皆双”的齐梁骈体。韩愈这种改革的矛头所向,从他对自己过去的文章的批判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比如韩愈曾对自己所写的应试之文表示羞愧:“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答崔立之书》)。所谓“类于俳优”,显然并非指四六骈俪的形式,而指的是言不由衷,鹦鹉学舌。又说:“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与冯宿论文书》)。所谓“俗下文字”,当指他出于应酬而作的赠答和墓志一类的东西,而韩愈所写的这些东西也并不是骈体。再从反面来说,倡导古文的韩愈也并非绝对不写骈文,如他被后来的追蹑者孙樵誉之为“拔地倚天,句句欲活”的代表作《进学解》,其中“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以下一大段文字就皆用排骈。而他贞元十一年所写的《感二鸟赋》、十三年所写的《复志赋》、十六年的《悯己赋》、十九年的《别知赋》,也都是骈俪之文。另外,在《与冯宿论文书》中,韩愈说:“辱示《初筮赋》,实有意思。但力为之,古人不难到”。写骈文亦可“有意思”,亦可“到”古人,可见他所推重的古文并不绝对排斥骈偶。
再从唐以来文体的发展情况来看,《新唐书·文艺传》曾把韩愈以前的唐文的轨迹分为两个时期:“高祖太祖,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絺句绘章,揣和低昂,故王、杨为之伯”,这是沿袭六朝余风的时期;“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这是盛唐以来以苏颋、张说和一系列古文家为代表的对六朝风习的矫正时期。我们看《全唐文》,可发现盛唐以后人所写的文章,有不少已打破六朝的四六骈俪,从追求辞采转而追求理致和立意。但在文章的表现方式、行文体格以及美学风格上,却总有一种自古以来就已形成的代代相沿的东西,它作为一种超稳定的深层结构和范式,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之中。一般人著文手惯笔滑,会不自觉地落入这传统的窠臼。这种隐性的窠臼,才是中唐后韩愈等人所努力冲击的对象。
为了实现拆解既定话语结构的目的,韩愈对于文体,并没有像他以前的古文家那样,提出要以儒家的经典作为固定的写作蓝本,而是“破”字当头,不认可任何既定的范式。他对于古代圣贤,是“师其意,不师其辞”的,所谓“意”即精神。什么是古人最可贵的精神呢?在韩愈看来,那就是他们的“能自树立不因循”的创造精神。他说:
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为之最。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浮沉,不自树立,虽不为当世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是也。(《答刘正夫书》)。
这里他指出,圣贤文章之最可贵者,即在于它的独创性。这种文章固然会为世所怪,但唯其如此,才能传于后世。关于为文不摹经典,而只学其创新精神,韩愈的门人李翱也有同样的论述,比如他对经典有这样的赞美:
浩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称咏,津润怪丽,《六经》之词也。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故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如山有恒、华、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不必均也。如渎有淮、济、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浅深、色黄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杂焉,其同者饱于腹也,其味咸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学而知者也,此创意之大归也。(《李文公集》卷六《答朱载言书》)
李翱此论,与其说是一篇对经典的写作技巧的赞歌,不如说是一篇叛经的宣言。因为他在赞美经典的创意造言、独立千古的精神之中,就断然否定了对经典的摹拟。相反,只有超越经典,才真正符合圣贤之精神。这是韩愈等人对于传统的“宗经”口号的一次重要发挥。
在写作实践中,韩愈最充分地表现了他的解构倾向。他直接向千百年来已形成的话语模式进行冲击,用辞有意超出常规,避熟滑而趋陌生,破齐整而求错落,在奇崛的表述之中求得全新的艺术效果。或者“以文为戏”,打破了千百年来儒者所恪守的一本正经的议论方式,尝试用小说的笔法来说理,寓深意于调侃之中。他的文风时而险怪,时而平易,而不论是险怪还是平易,实际上都是对传统文章“雅正”之体格的解构。与险怪平易相应,他对文章风格也有两种相反的提法:一是倡“钩章棘句”、“怪怪奇奇”;二是倡“章妥句适”、“文从字顺”。不过从他的文章创作的主要倾向来看,求奇尚怪的一面更为突出。故柳宗元谈阅读韩愈文章的感受,是“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得暇,信乎韩子之怪于文也”(《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孙樵也说过,读韩愈文章“如赤手捕长蛇,不施鞍控骑生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远人入太兴城,茫然自失”(《与王霖秀才书》),足见在时人眼中的韩文之奇险。在对时人作品的评论中,韩愈对奇文的推重也是不遗余力的。比如对作文“必出于己,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字”的涩体作家樊宗师,韩愈曾给与了极高的评价,说他“富若生蓄,万物毕具,海含地负,放恣横纵,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呜呼,绍述于斯术,其可谓至于斯极者也”(《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这与他本人在创作上的解构倾向是完全一致的。
除了散文,韩愈对诗歌的解构也很值得注意。我国的文人诗发展到盛唐,在体裁、格律和美学崇尚方面都形成了固定的范式,这种范式的典型代表就是律诗。律诗固然给诗人抒情提供了凝炼的形式,但其严格的句法和韵律规则也极大地限制了诗歌的艺术空间。且其发展已达峰顶,如不改弦更张,很难再有余地。韩愈之前的杜甫,身处盛唐到中唐的过渡时期,其后期的诗歌,就已表现出明显的隳废格律的倾向,在对既定的艺术模式的拆解之中追求全新的境界。韩愈正是在这一点上继承了杜甫。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韩昌黎平生所心慕力追者,唯李杜二公。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境。唯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开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韩愈的“以文为诗”在文学史上十分著名,他有意拆解今体诗的严格范式,用写散文的笔法和章法来写诗,行文有意避偶丽而求错落,如“春与猿鸣兮,秋鹤与飞”,“淮之水舒舒,楚山直丛丛”等等皆是。甚至在诗歌中汲取了佛经偈颂的表现手法,以相同的字的大量重复来展开铺陈,如《南山诗》连用数十个“或”字,《杂诗》连用五个“鸣”字,《赠别元十八》连用四个“何”字,《双鸟诗》连用四个相同的句子作排比,皆在句法上有意出奇,别创一格。他在诗中还借用了辞赋的铺陈描写方法,如《南山诗》铺列春夏秋冬四方之景,《月蚀诗仿玉川子作》排写东西南北四方之神,《遣列鬼诗》历数“医师”“灸师”“诅师”“符师”等等都是例子,令人读了,有一种汪洋浩瀚、豪纵恣肆的感受。《答张彻》似乎是一首五律,但它却从头到尾句句对偶,而且在韵律上又全用拗体。其他的诗中,也多用险韵奇字、古句方言,纵横排阖、无法无天,总之是千方百计地“蹂躏”着现成的规则,而从这种破坏之中努力寻求一种新的美质。此外,在诗的意象的选取和塑造上,韩愈也有意打破传统的美学标准。正如刘熙载《艺概》所讲的:“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韩愈写诗,喜欢选取雄奇和怪异的意象,甚至不惜描写血淋淋的场面,以激活人们麻痹的艺术神经,获得一种惊心动魄的感受。在他的作品里,日常生活中那些可怕的、可憎的、野蛮的、混乱的东西,被作者以艺术的强力纳入了诗的世界,使之变成了一种“反美”之美,“不美”之美。韩愈在诗歌的形式和内容方面的解构,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奇崛诡丽的风格,后来司空图说他的诗“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抉于天地之间”(《题柳州集》);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诗“颠倒崛奇,姿态横生,变态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都说的是这种创体的鲜明特色。
伴随着自己的创作实践,韩愈在诗歌评论中也鲜明的表达了他的解构倾向。他特别赞美在诗中“搜奇抉怪,雕馊文字”(《荆潭唱和诗序》);夸孟郊做诗是“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答孟郊》),又说“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醉赠张秘书》)。所谓“背时利”、“惊俗”,亦即对抗时髦,解构传统。他曾以“险语破鬼胆,高辞妣皇坟”自许(《醉赠张秘书》),在诗评中亦给奇险的作品以特别的青睐,如《荐士》中赞许孟郊的“冥观动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夰”;《贞曜先生墓志铭》中又激赏他“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所有这些,都是和他本人的创作倾向完全一致的。
总之,从韩愈的创作倾向和主张来看,他决非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复兴”古文的人,而是借复古为口号而凌轹千古,自成一家,解构旧体,力创新言的巨匠。《新唐书》本传评韩文:“尽刊陈言,横骛别驱”,“卓然树立,成一家言”,“造端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文艺传》谓其“排逐百家,抵轹晋魏,上轧汉周”等等,皆指他横扫一切现成窠臼的解构倾向而言。韩愈对传统诗文法则的解构,对当时和以后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文风格和创作路径,不但直接影响了中晚唐的一大批作家,诸如孟郊、贾岛、皇甫湜、孙樵、来无择、卢仝、马异、李贺、李商隐、韦楚老、庄南杰……甚至也拉开了唐诗向宋诗转变的序幕,所以叶燮《原诗》中说:“唐时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发起端,可谓极盛。”他看到了韩愈之力变旧体对于宋诗的发端作用,是很有见地的。
标签:韩愈论文; 国学论文; 儒家论文; 孟子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读书论文; 原道论文; 孔子论文; 答李翊书论文; 进学解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古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