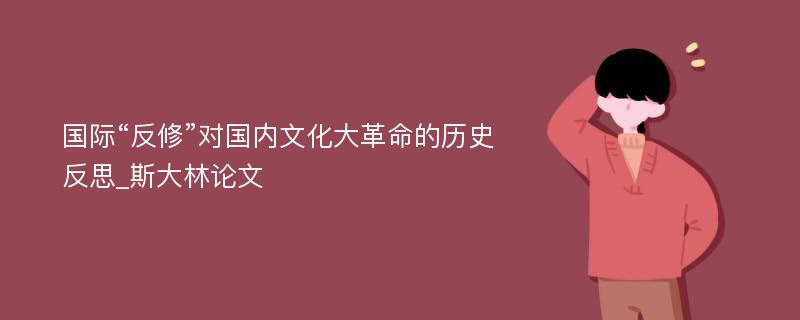
从国际“反修”到国内文革的历史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革论文,国内论文,历史论文,国际论文,反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发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国内关于十年文革的研究、特别是对文革以前的中苏论战及反修斗争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实际上,反修斗争和文革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的阶段。若没有对文革前十年间反修斗争的深入研究,就无法说明后十年文革为什么会出现,也就无法说明为什么批判刘少奇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会成为文革中的重要内容。认真研究这段历史,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从1953年我国实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逐步抬头,批判胡适,声讨胡风,发动“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加快“城市社会主义改造”等等,极左思想指导下的社会运动一个接着一个。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公开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左倾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后,中国共产党迫于苏共二十大的反左思潮,开始加入了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和左倾教条主义的行列,并且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但当时我们只承认若干年来我国学术界在某些方面接受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影响,在党的领导方面似乎还没有意识到有什么教训可以总结。如果总结苏联共产党的教训的话,那就是作为领导者今后“应该使错误限制在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范围内”,而不应让它“变成全国性的或长时期的错误”[1] (P11)。这表明当时的领导者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在实际生活中已经产生了的1950年代那种从上到下的左倾错误,甚至还在主观上坚信自己走在一贯正确的道路上。
1956年底到1957年初,由于斯大林的去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教条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政策“解冻”,匈牙利、波兰等苏联的“卫星国”出现了批判斯大林的群众运动,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而且很快波及到中国。中国当时刚刚接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反左”口号,这时国内外政策又迅速由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转回到批判右倾修正主义,由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转向批判南拉夫和铁托,并为斯大林的“伟大功绩”辩护,同时开始大讲阶级斗争,强调知识分子的改造,重新解释双百方针。
1957年7月,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认为“左倾教条主义”只是一部分人“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但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革命者,而另外一种“修正主义或叫右倾机会主义”,则是“比较危险”[2] (P423)的。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中,既肯定了苏共二十大不仅“对苏联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同时又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调子强调“在目前的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3] (P11)。在当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4] (P6)。自此以后,反对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成为中国内外政策的基点,一切政治斗争都是为了反修防修,直到文革结束。
1958年中国共产党的左倾路线极度膨胀,在国内又掀起了全民“大跃进”运动,开始向共产主义进军,而且把一切对这种“大跃进”的批评都视为不怀好意的攻击。为此而在国内外进行了捍卫“三面红旗”和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1960年开始,又借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机,在全国各报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反修文章,批判的对象表面上是一贯不听斯大林指挥的南斯拉夫及其领导人铁托,实际上批的是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赫鲁晓夫。批判的基本方法是大量引用马克思和列宁针对他们那个时代的言论,去论证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许多问题。凡是不符合几十年以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言论,统统被批判为“现代修正主义”,而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许多重大变化,却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1960年,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大张旗鼓刊登的《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等文章都是不顾事实而言过其实的典型代表。以这种夸张失实的舆论向导为背景,1960年代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国际反修斗争。实际上,在列宁去世之后的近半个世纪内,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当时的一些以反修为主题的文章还是高喊着“保卫列宁主义”的口号,把凡是不符合几十年前列宁主义的言论,统统称为“现代修正主义”加以无情批判。这些反修文章用不同的形式重复着列宁关于“现代修正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相关论述,对1950-1960年代的所谓“现代修正主义”进行讨伐。在文艺领域,1958年,姚文元出版了《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批判胡风、冯雪峰等人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1960年初,为了开展国际范围的反修斗争,《文艺报》第1期首先发表了反修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为争取文艺的更大丰收而奋斗》,同时发表了重要的署名文章《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两篇文章发表后随即由《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与林彪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相呼应,在全国掀起了“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批判国际“修正主义”的浪潮。当时的国家领导者认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及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领导权,马克思主义学说也被他们篡改为“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所以,中国共产党要在全世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传播中国革命思想,以便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前发展,使“井冈山道路通天下”。同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几年来“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和“反右倾”等运动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入开展“反修斗争”。形成了1960年代初反修斗争的第一个高潮。
二
第三次全国文代会的精神尚未认真贯彻,就出现了“大跃进”、“反右倾”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在被迫进行各项政策的调整中,反修斗争也无法按原计划进行,左的教条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受到了遏制,到1963年初,国内经济情况刚有所好转,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反修斗争。于是《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同志》、《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和《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文章相继发表。可是这时的苏共中央并没有反击,竞以和缓的、同志式的态度在1963年2月21日给中共中央发来书信中主张通过彼此交换意见、消除分歧、加强团结。这时连毛泽东本人也认为苏共在这里所表现出的态度是友好的、诚恳的,因此理应得到中共中央的积极友好的回应。于是中共中央在1963年3月9日的回信中,也诚恳地表示:应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同志式的讨论和互相批评,弄清是非,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同年3月30日,苏共中央再次致信中共中央,表示欢迎中共中央提出的举行中苏两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并就两党会谈的内容,特别是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从这些意见可以看出,两党空谈团结是可以的,一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问题,就产生了明显的、严重的分歧,而且各自都非常自信的坚持自己的意见。针对苏共中央3月来信,经过近3个月的准备,中共中央于6月14日正式发表了长期引以为自豪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可以说是我们当时及以后很长时间进行大规模“反修斗争”的理论纲领。
上述《建议》共计25条,针对苏共中央的来信及批判斯大林以后的一贯表现,对其“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而且还郑重声明: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中国共产党人将继续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站在一起,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当然也包括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1965年6月14日,《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在纪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两周年的文章中再一次明确指出:当时中苏两党争论与斗争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同苏共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与“全民国家”、“全民党”等“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矛盾斗争。
苏共中央原以为他们提出的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是绝对正确的,不料却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无情批驳,于是发出了一封《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在反批评中对自己的理论作了系统的阐述。中共中央正好找到了批判的靶子,便于1963年9月至次年7月先后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直到当年11月赫鲁晓夫下台为止,在这场历史性的中苏论战中,双方都“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以“绝对正确”的姿态批判对方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立场,只是中国一方要保卫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苏联一方则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当代性”和“创造性”,批判“左倾教条主义”。“九评”中共中央公开信,是1960年代在国际上进行的反修斗争中的重要战役,通过这次论战,苏共中央及其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名正言顺地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者,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再拉出南斯拉夫和铁托来作为修正主义的代理人了。
1964年10月,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3个月之后,赫鲁晓夫被解除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红旗》杂志在《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一文中说:这个“窃取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地位的大阴谋家,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终于被赶下台了,这是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胜利”,它充分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5] (P1)。可是,当时的领导者很快就发现,赫鲁晓夫虽然下台了,却仍然存在着“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于是又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发出了“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呼吁。这次“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伟大胜利”,因为在方针上坚持传统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斯大林模式不变,而把稍稍离开这一模式的变革统统批判为大逆不道的“现代修正主义”,从而把西欧、北美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说成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一统天下”,结果是使中国在世界上限于孤立地位,成了革命的“孤家寡人”。所谓世界“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其实是自己四面出击所造成的孤立处境的自我解嘲式的描述。不必讳言,当时正是这种极左的“反修斗争”与“世界革命”的理论与政策,使中国陷入于封闭与半封闭状态之中。
《一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明确提出:苏共提出“反个人迷信”和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二十大以后批判斯大林的做法格外反感。在理论上虽然不得不承认斯大林后期犯有严重的错误,但同时又千方百计地为其错误进行辩护,强调斯大林对于苏联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伟大功绩”。当强调“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重要性之后,就把批判的矛头转向了南斯拉夫的铁托和苏联的赫鲁晓夫。到了后来,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以及“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更是几乎处处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辩护,谁要批判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就是犯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尤其是在以《关于斯大林问题》为标题的“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更是根本否定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谁要批判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那就是“别有用心”,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要“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正是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不久就出现了以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借口的中国的个人崇拜狂,终于导致了历时十年的文革悲剧。
三
“三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提出了如何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上台和“资本主义复辟”中接受教训的问题,“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则专门论述了由南斯拉夫到苏联的共产党人“变修”而引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其中说:先是铁托“修正主义”使南斯拉夫由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随后又是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与国家的领导”那样的事。这些“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共产党,当然也包括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敲起了警钟”:我们不仅在国际上,同时也要在中国国内进行大规模的反修斗争。从这里,毛泽东还总结出一整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如何在继续革命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理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新的“里程牌”。“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在结尾部分说: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中增添了新的武器,这种新的武器对于我们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并且还十分肯定地说:“只要按照这些原则办事,就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援助世界各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运动,并且保证在将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6] (P58)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值得骄傲的并应该向世界推广的“理论”。
从国际“反修”到国内“文革”的过渡是通过文艺领域内的斗争进行的。1963年到1964年间,毛泽东就国内文艺问题发出了两次重要“批示”。特别在第二个“批示”中,明确指出:最近几年,我国文艺界“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当时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是被当作社会主义国家中典型的“修正主义”文艺团体看待的,正是在这个“批示”的贯彻执行中,文艺界的许多重要人物都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批评、被打倒。而在毛泽东身边执掌文化大权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有“反修战士”康生、“理论家”陈伯达等,都成为反修斗争的中坚力量。他们利用毛泽东的极左思想和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知识分子、特别是对赫鲁晓夫的恐惧心理,在文化艺术界兴风作浪。1965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全国范围内将反对修正主义的文艺批判升级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政治斗争,并由此引发出国内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这个由毛泽东亲自签发的指导“文化革命”的文件,几乎完全是按照毛泽东个人对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修正主义”的理解去认识中国的。其中说:在中国“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几年来从国际到国内的“反修斗争”,竞然越批判越斗争,“修正主义”越严重,赫鲁晓夫这个名子越批判越可怕。所以在我们连续发表的反修文章中,几乎每一篇都少不了批判赫鲁晓夫的内容。一开始,赫鲁晓夫还是苏联有,外国有,随后中国有,在我们党的领导层也有,甚至他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再后来上自刘少奇,下至各级党政领导,几乎都有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这时,在各级党政部门的文件中,都要明白无误地写上“反对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是“反对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等等。甚至连党中央副主席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的公开讲话中,也一再强调:“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是我们的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7] (P203)这时,赫鲁晓夫虽然已经下台了,但是他的影子却在中国上空飘荡,而且直接威胁着党的最高领导权。所以当时的中国,“文化革命”是势在必然的了。由此可见,长达十年之久的中国“文化革命”所要达到的目的,无非是要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拥护者斗倒斗臭,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而这一目标,正是在批判从苏联到中国的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过程中逐渐明确的。十年“文化革命”所要“大树特树”的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也正是这一大批判的必然结果。可以肯定地说,正是赫鲁晓夫的幽灵,使毛泽东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去通过“文化革命”清除国内外的赫鲁晓夫及其拥护者。可以这样说:假若没有愈演愈烈的国际范围的“反修斗争”,特别是从《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到“九评”苏共公开信所展开的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也就不可能有持续十年之久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81年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1957至1966年,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这就导致了文化革命的发动”[8] (P21-22)。同时,还有一个与此相联系的导致了“文化革命”的原因,那就是在同一个十年当中调子越来越高的中苏论战与反修斗争,而上述“决议”由于历史原因却有意回避了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国际上日趋激烈的中苏论战与反修斗争,使毛泽东越来越感到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以及开展“文化革命”的重要性。
研究十年文革的专家金春明先生告诉我们,目前国内关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起因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1、阶级斗争必然说;2、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3、封建余毒说;4、毛泽东帝王思想说;5、奸臣祸国说;6、乌托帮碰壁说;7、群众反官僚主义说;8、东西文化冲突说;9、人性兽化说;10、“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他在分析了上述这些观点之后,又进一步提出了对十年“文化革命”的爆发具有决定意义的原因,即以对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认识为主要特征的左倾思潮的“恶性发展”,并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随后,他又把这种“恶性发展”具体化为三个“恶性循环”,即左倾理论与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集权体制与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国内反修与国际反修的恶性循环[9]。这里他只是在第三个“恶性循环”中提到了“国内反修与国际反修”问题。笔者认为,要认真研究中国的十年“文化革命”,就必须深入地研究出现于文革之前国内外的“反修斗争”及其恶性发展。因为正是1950-1960年代越来越激进的“反修斗争”,才直接导致了文革的发动。所谓“左倾理论与左倾实践”,在文革以前主要是国际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同时也开始了国内的“反修斗争”。十年文革当中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则是十年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在国内的进一步发展。若没有十年批判赫鲁晓夫的国际“反修斗争”,也就不会有十年的国内“文化革命”,不会有文革中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大批判、大清算。有了前者,后者的出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说,要搞清楚十年文革中的是是非非,就离不开对文革以前中苏论战及国际反修斗争的认真研究。
标签:斯大林论文; 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 修正主义论文;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个人崇拜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