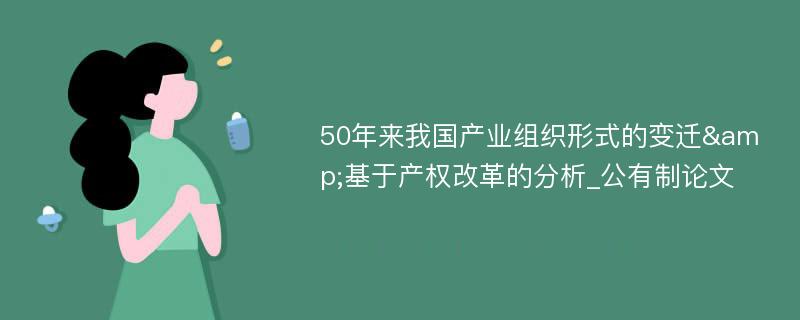
近50年来我国产业组织形态的变迁——基于产权变革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态论文,产权论文,年来论文,组织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理论渊源
产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是指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组织或市场关系,包括交易关系、行为关系、资源利用关系和利益关系等。产业组织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的名著《经济学原理》,书中马歇尔首次把组织解释为企业内部、同一产业间和不同产业间的组织形态和政府组织等,并将之视为与劳动、土地、资本相并列的生产要素。从此,对产业组织的研究逐步发展成为产业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日益集中,垄断、寡头垄断成为支配市场的主要产业组织形态,产业组织理论也围绕垄断与竞争的成因与形态展开。1933年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与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均认为产品差异使市场成为垄断竞争市场。在此之后的产业经济学家(注:例如:梅森(1939年出版《大企业的生产价格政策》)、贝恩(1959年出版《产业组织》)、凯森与特纳(1959年合作出版《反托拉斯政策》)、凯维斯、谢勒、谢菲尔德、科曼诺等。)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了产业组织理论,形成产业组织的哈佛学派。1968年斯蒂格勒出版的《产业组织》则从信息的不完全性、进入壁垒、政府规制等方面论述垄断、寡占等产业组织形态的形成和特征,标志着产业组织理论的芝加哥学派的成熟。至此,对产业组织形态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技术的角度围绕垄断、竞争展开,其框架是建立在西方主流学派的微观分析基础之上的数学、效用主义的边际分析,未涉及制度分析。然而,垄断、竞争过程中产生的市场失灵,除了源于有限理性、信息不完备等传统因素以外,还在于产权构造上的缺陷而造成的交易摩擦。因此,作为企业间的动态均衡模式,产业组织形态的形成不可能不涉及产权的界定方式。
科斯于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和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开创了产权与交易费用理论。产权(Property rights)是经济行为主体对所拥有的财产(资源)的一组权利束,包括所有权以及由所有权派生出来的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等与财产(资源)相关的一切权利。科斯定理指出,在存在市场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产权的不同界定方式将影响经济绩效。(注:科斯定理I: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是不受法律状况影响的;科斯定理Ⅱ:一旦考虑到市场交易成本,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转引自何维达、杨仕辉:《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71页。)资源产权的初始界定决定了企业初始的资源禀赋,在社会资源一定的情况下,资源在市场主体之间的界定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决定了产业组织形态的特征。根据哈佛学派的SCP分析框架,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和市场绩效(Performance)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政府为了提高市场绩效而进行的改革以及市场主体为寻求更高的经济绩效而发生的交易行为均可从产权关系变革的角度理解,因此,产权和产业组织形态的内在关系便体现在产权关系的变革历程当中。
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无法套用西方的理论对产业组织进行研究,而基本上是从社会分工、专业化生产与协作、规模经济的角度研究分析。1978年以后,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使得中国产业组织现象和问题趋同于西方,为产业组织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进入20世纪90年代,对产业组织问题研究日益蓬勃,(注:如王慧炯的《产业组织及有效竞争——中国产业组织的初步研究》、马建堂的《结构与行为——中国产业组织研究》、夏大蔚的《产业经济学》、金碚编著的《产业组织学》等。)他们的研究基本上从我国的产业管理制度、劳动人事制度、流通体制、金融体制、外贸体制等角度运用SCP分析框架、新制度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等进行分析,却少见有文献从产权的角度对产业组织形态的形成展开讨论。实际上,自1956年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以来,产权制度一直处在变革当中。1978年以前,是在不触动经济体制的前提下的行政放权与收权,而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则是将产权改革以法定的形式落实到实践当中,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间之间进行资源产权再界定。产业组织形态随着产权关系的变革从国有企业“一家独大”到今天的“百花争鸣”。本文试沿着1956年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以来的历史进程,以城镇经济为主,试图在产权与产业组织形态之间找出这种联系。
二、历史变迁
从产权的角度考虑,经济体制变革的过程包含着社会资源的各项产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民间之间多次界定的过程。按经济体制的变革历程,本文将近50年以来我国产业组织形态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1979年改革以前为公有制企业行政性垄断;1979年改革以来,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垄断竞争;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竞争性行业企业之间的自发整合——企业簇群。
(一)公有制企业行政性垄断(1979年以前)
经过1949年到1952年对官僚资本的没收和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作为全民代表,获取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的产权,因而可以按照重工业化赶超战略的要求制定产业组织政策,大办公有制企业。由于资源的产权并没有界定给民间,所以在随后的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产业组织形态保持着公有制企业(包括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类型)垄断。从1957年到1979年,国家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分别从4.96万个和11.99万个增加到8.38万个和27.12万个,工业总产值从378.5亿元和134.0亿元分别增长到3673.6亿元和1007.7亿元。(注:数据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垄断并非达尔文式的竞争结果,而是行政性垄断。由于国家是资源产权的法定主体,因此国家意志体现在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中,作为国家的代表,政府支配着企业的资金调拨、生产计划、要素流通及人事安排等,而企业只不过是行政命令的执行者,不享有合法的经营权,即缺乏资源的使用权、支配权、处置权等产权,因而市场行为例如兼并、联合、进入、退出等不可能是企业的自主行为,而是行政安排,这就是行政性垄断的含义。例如在“大跃进”时期,各地的“小土群”、“小洋群”、“五小”企业(注:指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工业。)之所以得到发展,就是因为在地方性垄断的情况下,企业不享有资源的大部分产权,无法采取自主的市场行为,在绝对服从行政命令的前提下为配合中央钢产量指标的完成而开展的运动。而在之后的调整时期(1961-1965年),中央保留了骨干企业,重点裁并中小企业,并试办具有托拉斯性质的大型工业公司,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对企业进行统一管理。所有的这些行政性安排都是在公有制企业垄断的前提下对企业规模的一些调整,企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传统经济体制缺乏效率的弊端,在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不久就已经暴露出来,因此,中国针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就展开。而在1979年以前,这种变革是在不触动传统经济体制的前提下的行政放权与收权,即在资源所有权属国家的前提下,中央和地方之间对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权利进行再界定。从表1中可以看出中央直接控制企业的规模随着产权界定给中央的不同程度(即分权与收权的程度)而变化的趋势。然而,这只是在公有制内部国家所有企业和集体所有企业之间在规模对比上的改变而已,并没有改变公有制企业行政性垄断的产业组织形态。
表1 中国改革以前分权、收权周期
1953年 1957年 1958年底 1963年 1971-1973年
中央直接控制的企业 2800
9300
1200
10000
2000
中央部委分配的物资
227
532
132500217
资料来源:Yu Guangyuan(ed.),China' 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84,p·76.(转载自: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9页)。
(二)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垄断竞争(1979年以来)
经过近30年的实践,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已经完全暴露出来,“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经济几近崩溃。在不触动经济体制的框架下进行措施性安排的变革显然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1979年经济改革开始,中国进入经济转轨时期。随着资源产权的再界定,公有制企业行政性垄断的产业组织形态被打破。
从产权变革的角度看待经济体制改革,可以理出两条线索:
第一,在国家所控制的资源内,产权的大部分逐步界定给微观经营主体,换句话说,除了资源的最终所有权以外,大部分产权的产权主体由国家转向具体公有制企业,适当减弱集权程度。这个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4年),“放权让利”。即给予企业以新增收益的部分所有权,激励企业经营者提高生产效率;第二阶段(1984-1986年),围绕着增强企业活力展开,主要手段有简政放权,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实际上是给予企业代理人以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第三阶段,1987年以来,围绕着重建企业经营机制而实行各种经营责任制。因此,从1979年以来,作为一组权利束的资源的产权,其各项权利是渐进地、逐步地界定给企业,最终形成的事实是除资源所有权以及部分收益权属国家以外,其余产权属于企业。
第二,资源产权在中央、地方和民间之间进行再界定,包括中央向地方行政分权以及允许民间拥有资源的部分或全部产权。这个过程催生了不同于传统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一方面,由于地方获得了具有实际控制价值的资源产权,使地方可以大规模兴办乡镇企业。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到2001年末,全国共有乡镇企业2156万家,为1990年的115%;从业人员13086人,为1990年的141%;该年实现增加值29356亿元,占全国GDP的30.6%。(注:数据来源:《中国企业管理年鉴2001-2002》、《中国乡镇企业年鉴2002》。)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央所控制资源逐渐向民间开放,私营企业逐渐发展起来。1987年以前,国家对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个体工商户名义存在的企业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不禁止也不宣传。然而,这些民营企业大部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二权合一,产权关系明晰,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市场作用不断得到认识,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则明确指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中共十六大的召开更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到2001年底,个体私营企业达2048万家,占全部企业的96.8%,该年实现增加值20238亿元,净利润4337亿元,实交税金1335亿元,占全部企业比重分别为68.9%、72.3%和57.8%。(注:数据来源:《中国企业管理年鉴2001-2002》。)
通过以上所述的产权改革,公有制企业在其生存的空间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除传统的公有制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是在一定的市场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并经过市场竞争而体现出一定生命力的企业——私营企业大多采用两权合一的古典形式,乡镇企业虽然所有权属集体,但由于集体所容纳的行为主体较少,企业负责人实际上获得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因此,这些企业的产权关系在经济转轨中是合理性的安排,具有相当的竞争力。所以,公有制企业行政性垄断的产业组织形态被国有企业、乡镇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等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相互竞争所替代。
随着产权改革的深入,公有制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逐渐退出,让位于这些非公有制经济。1999年9月22日通过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领域应仅限于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行业、提供重要公共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因此经过产业调整,在大部分竞争性领域,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企业间的竞争通过兼并、收购、联合、退出等市场行为而不断整合,形成垄断竞争的组织形态。例如,我国的彩电行业,其厂商数目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为120多家,CR[,4]=13.7%,经过不到十年的市场洗礼,竞争力不足的企业退出该行业,而脱颖而出的名牌企业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到1996年彩电生产厂商数目减少为95家,CR[,4]=57.8%,超过贝恩的产业集中度指标的40%,属于寡占型产业组织形态,其中长虹、康佳的市场占有率在20%左右。(注:参见夏大蔚、陈代云、李太勇:《我国彩电工业的产业组织分析》,《财经研究》1999年第8期。)
(三)竞争性行业企业之间的自发整合——企业簇群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
改革初期,产权的重新界定重建了微观经营主体的激励机制,激发了相当大的生产率。在卖方市场中,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均在竞争中得到发展。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国经济转轨进程加速,市场机制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买方市场出现,游离的企业个体已经在严峻的市场竞争压力下显得力量不足,必须寻求新的竞争优势。由于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已经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明晰,企业拥有资源的实际控制权,因此可以以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的身份面对市场竞争,采取相应的市场行为。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企业主动探索资源产权的新的界定方式以寻求新的发展,产业组织形态也因此进一步演变。
在市场上从事交易活动必须花费一定的交易成本,包括各种信息搜寻、获取、处理的成本,而相当一部分信息具有很强的公共财产的性质,例如创新、声誉、企业文化等资源,它们很容易引起“搭便车”行为。产权的有效界定影响企业的交易成本,如果将这些资源界定为私有财产,则企业之间将在非合作性博弈过程中为垄断这些资源而花费相当大的成本,所以游离的企业个体为了防止外在性而造成收益偏低,不得不花费相当大的成本保护信息所有权,这便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削弱竞争力。相反,如果将这些资源产权放置入公共领域,由社区各方共同承担交易成本,则可减少界定这些资源产权的费用,而更重要的是,长期的合作性博弈减少消费公共财产而引起的租金消散的程度,提高了信息的利用效率,无形中增强了企业竞争力。
为了达到共赢的局面,在某个地理区域内,围绕某个主导产业衍生出的一系列相关产业及其支持或中介机构聚集在一起,形成企业簇群。在簇群内部,各主体之间重新界定社区资源的相关产权,在长期合作性博弈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的社区规范所形成的信任机制、约束机制等进一步减少产权界定的成本,使得企业簇群的运行收敛于某种均衡的稳态,从而又进一步节约交易费用,二者互动推进,形成良性循环,提高整体竞争水平。
企业簇群最初出现于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如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以珠江三角洲为例,南海大沥的铝材厂有200多家,年产值160亿元,产量占全国40%,占全省60%,形成铝材产业的企业簇群;南海南庄陶瓷业企业簇群则包括140多家企业,年产值100多亿元,产量占全国35%;中山古镇被誉为“中国灯都”,有近千家灯饰厂,产品销售量占全国一半以上;还有东莞虎门制衣产业企业簇群、东莞大朗毛织企业簇群、江门蓬江区摩托车企业簇群等等,(注:资料来源:南方网。)企业簇群提升了社区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成为珠江三角洲区域竞争优势的重要体现,这是对企业簇群这种产业组织形态的客观合理性的一力证。
通过以上对历史的回顾而得出的结论是,我国产业组织形态的演变是随着社会资源产权的再界定而进行的。当政府代表全民掌握社会资源的几乎全部产权时,产业组织形态只能是公有制企业这一单一的所有制形式行政性垄断市场。随着资源产权由中央向地方和民间分散,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均得到发展并在垄断竞争中达到均衡。随着竞争的加剧,他们以市场主体的身份进行自发整合,在资源产权的进一步界定中寻求整体竞争优势,产生了企业簇群这一种产业组织形态。因此,产权和产业组织形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三、未来展望
随着世界范围内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为适应新的挑战,各地政府纷纷将建立新型产业体系提上日程。所谓新型产业,就是强调信息技术的作用,促进传统产业和信息产业之间的融合,使之成为科技含量高、技术水平高、聚集性高、辐射能力强的新的产业形式。展望新型产业的组织形态,同样将是产权关系变革下的产物。
新型产业具有信息化、聚集性和强调知识支持等特点。一方面,当社会进入消费个性化、多样化和现代技术日新月异时代,市场竞争更讲究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处理的高效性,并强调产品的高附加值。有效信息除了市场的供需信息外,还囊括产品的品牌、声誉、技术、创新、文化等内容,正如上面已经阐述,这些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外在性,企业簇群的交易模式是解决这种外在性的有效的产权安排。由于新型产业对信息的规模、准确度、及时性等要求提高,因而更需要强化对信息资源的产权安排的有效性,因此,新型产业组织形态应该基于企业簇群而又满足信息化和聚集性的更高要求。另一方面,新型产业强调高新技术、前沿知识的研发作为持续发展的支撑,这便要求产业组织主体不但包括消费品、中间产品的生产企业,而且要求有大量的研发机构、中介机构、智力型企业参与的知识生产,因而公共资源产权应该在包括这些知识型产业主体之间进行界定。所以,新型产业组织形态是在信息网络平台、知识型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下的企业簇群的高级模式。
美国微电子、半导体及IT产业的聚集地硅谷以及以汽车制造业为主导产业并形成相关产业的聚集地底特律等便是高级企业簇群模式之一。目前我国的企业簇群尚处于初级阶段,要发展成为与新型产业相适合的高级企业簇群还有相当的距离。上海提出在优先发展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高技术先导产业的同时,将通过信息化改造和提升汽车、精品钢材、石油化工、现代装备等优势制造业,并加速发展以研发设计和轻加工为主的都市型工业,与此同时,将加速这些产业的空间集聚,形成若干生态产业集群;武汉提出的中国光谷则由研发创新体系、产业支撑体系、辐射带动体系和空间布局体系四大体系构成,依托武昌东湖地区的高校,将高新技术企业、大学、科研机构聚集起来,形成跨电子、信息、软件等领域的产业集群;山东蓬莱确立了以休闲度假型旅游产业、“名酒城”、生物医药产业三大朝阳主导产业构成的新型产业群。可见,高级企业簇群这一新型产业组织形态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共识。我国的产业规制具有政府主导的传统,各地提出的建立新型产业体系均在政府牵头下进行,那么,在面对新型产业的发展中,应该如何确定政府角色呢?
诺思强调制度安排先于经济发展,从工业革命、第二次经济革命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史上的绩效在于产权制度的有效确立节省了交易费用。这使得产业组织有利于进一步的分工和创新。本文已经论证产权与产业组织形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在未来的产业结构变革当中,产权制度的安排同样将通过产业组织形态的合理化演进影响经济绩效。第一,高级企业簇群在更高程度上强调公共资源消费的有效性和低成本运行,为了促进簇群内部行为更迅速地收敛于均衡状态,除了簇群内部主体的相互博弈之外,政府可以以诱导性方式促进其社区规范的形成,明确资源产权的交易方式和公共资源的消费方式,包括建立诚信机制、落实社区行为规范等,防止簇群内部出现过度竞争或垄断;第二,对大量的科研、技术研究的扶持十分重要,日本就是在新技术产业成长期对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实施大型的研究助成计划,促进技术的共同开发、创新和成果分享,加快了经济的腾飞。由于我国的研发机构多为事业或具有国有背景,其市场化导向并不明确。因此,政府角色便在于进行有效的产权安排,特别是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制度,促进科研成果转换成市场供给,以市场需求作为知识生产的动力。再者,中小型企业仍然是我国创新的主导力量,因此,必须大力促进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进入簇群。这要求降低民营企业进入门槛,将资源产权充分开放给民营企业,包括提供畅通的融资渠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建立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等。
产业组织形态的演进固然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强调产权变革与产业组织形态演进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因为资源产权的安排决定企业在交易过程中的市场行为,从而形成一定的产业组织形态,进而影响经济运行效率。因此,科学的产权制度将有利于促进经济绩效,而扭曲的产权制度将阻碍经济发展,我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制度变迁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政府在制定产业组织政策时,必须以史为鉴,关注产权关系安排的有效性。
标签:公有制论文; 产权理论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产权论文; 产权保护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垄断竞争论文; 市场垄断论文; 组织发展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