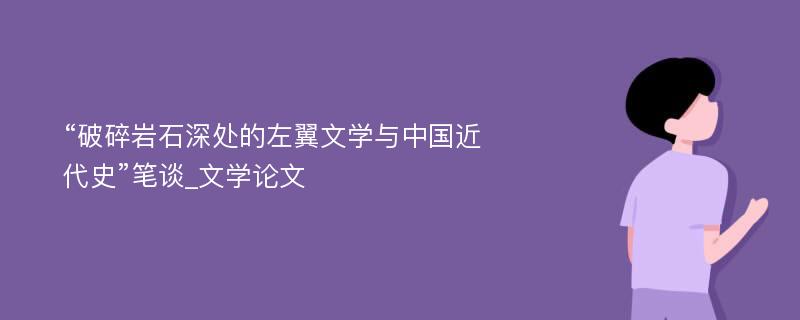
“左翼文学与现代中国”笔谈——断岩深处的历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左翼论文,中国论文,深处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似乎真的带来了“历史的终结”,所谓“历史的终结”,不过一面是资本主义 全球化的有力扩张,一面是作为历史抵抗力的左翼的悄悄湮灭。在中国,随着80年代以 来“重写文学史”实践的不断积累,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仅重新被建构,而且现代文学史 的评价已经被颠倒过来,“翻烙饼”的说法不幸成为预言。与此同时,曾经在中国现代 文学史叙述结构中被置于主流地位的左翼文学已经淡出视野之外,左翼文学的研究几乎 成为空白。然而,对于左翼文学的历史压抑并不新鲜,“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这不过是历史的故伎重演。然而,左翼文学的淡出并非等于死亡,即使是一些已经 破碎的字词也会像历史的碎片一样具有记忆和言说的力量。同时,左翼文学的退却或者 放逐也并非没有留下任何隐身而去的痕迹。只有对于随波逐流的人来说,仅仅沧海横流 才具有意义;然而,也许重要的不是沧海横流,而是某个词的崩溃、扭转。
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说:“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 已。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 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如上文所说,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 之输入,即新言语之输入之意味也。”晚清、五四、20年代末,都是中国思想界崩溃与 重建之际,这时,我们也可以发现明显的语言的除旧布新的现象。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人 对“新名词”大摇其头,然而,“新名词”总是意外地、不断地带来“新时代”。梁启 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论及晚清诗界革命时,就谈到当时所谓“新诗”与“新名词”的 某种连带的现象。从晚清开始,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对立,实际上往往就是新名词与旧名 词的对立,而反过来新名词与旧名词的对立实际上又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与“世界观 ”的对立。通常,一个时代取代了另一个时代,是一批名词驱逐了另一批名词,一些概 念覆盖了另一些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说法战胜了另一种说法,是一种话语压倒 了另一种话语。80年代以来,“新时期”、“现代化”、“后现代”、“全球化”、“ 与国际接轨”和“发展”这样一些概念不知摧毁了多少东西,埋葬了多少问题。
1840年西方入侵,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的结果是,中国的“天下”破裂,从而 义无反顾地“走向世界”。在晚清,“国家”、“议会”、“学校”、“民主”、“科 学”这些新名词开始出现。我们仍然可以想象鲁迅那种“‘物竞’也出现了,‘天择’ 也出现了”的兴奋。晚清所谓的启蒙运动,当时流布全国的各种各样的白话报刊强聒不 舍地向“愚众”灌输的就是各种西洋的新思想和新知识,也就是各种新名词和新概念。 在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中,《文化批判》杂志上引人注目地开辟了“新辞源”的栏目 。后来,在《思想》月刊上也开辟了“新术语”的栏目。在激剧变化的“思想革命”和 “理论斗争”的时代,这样系统地、大规模地输入新名词的现象毫不足怪。在《文化批 判》创刊号上就介绍了唯物辩证法、奥伏赫变、布尔乔亚、普罗列塔利亚、意德沃罗基 等新名词。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与五四的知识产生了深刻的断裂。在五四时期,我们 通过现代/传统、个人/国家、民主/专制、科学/迷信、白话/文言、贵族/平民的坐标来 建立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在个人自由和社会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我们的意义世界。 国民性、人性和个性构成了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维度和方式。在文学上,白话文和写实 主义成为了我们表现这个世界的基本技术和工具。然而,经过1928年的“文化批判”, 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组完全不同的概念: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意识形态。在文学上,同时需要语言和技术的更新:阶级性、大众语、现实主义。五四 时期抽象的“人的文学”在30年代变成了具体的“文学的阶级性”。正是这些名词和概 念有力地重新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它摧毁了旧的既成的知识,建立了新的对于世界的 认识。如果我们不是严格地借用库恩的“范式”和福柯的“知识型”的概念的话,那么 ,从晚清到五四,从五四到30年代,我们用来描述我们所处身的世界和社会的名词和概 念的不断变化,实际上我们经历了不同的范式和知识型的变化。从晚清以来,我们不断 地与旧的名词、概念进行决裂,实际上我们也是在与不同的知识、不同的思维甚至不同 的世界观进行决裂。同时,我们也是在与不同的世界进行决裂。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 是“换了人间”。
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是一场自觉的“理论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浪漫 主义诗人曾经自命为宇宙的“立法者”,而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以及中国30年代左翼文 学奉行的一个基本的观念是文学“组织生活”。这一现代的文学观念我们有重新进行反 思和批判的必要。这一观念渗透了所谓“现代性”的重量。“文学组织生活”的思想在 中国其实最早是由梁启超提出的。由梁启超之提倡政治小说,以及他的《小说与群治之 关系》中的有关论述,将文学作为社会改造的工具这种文学观念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 文学。他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 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 ;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是社会重构的一种非常重 要的手段。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的生活是由文学“组织”起来的。实际上 ,我们在根据《谁是最可爱的人》、《千万不要忘记》、《爱,是不能忘记的》、《我 爱美元》在不断地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与此同时,我们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 有重新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必要。我们把文学与政治的密切联系视为左翼文学的一个区别 性特征。然而,实际上,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最早是由资产阶级理论家梁启超建立起来的 。同时,不论是在晚清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那里,文学和政治的密 切联系,都是不容否定的。文学与政治的联系不仅是30年代左翼文学的特点,也不仅是 “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特点,而且同时也是“新时期文学”的特点,甚至也 是所谓“后新时期文学”的特点(如果我们不否认反政治的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的话) 。
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是无产阶级的五四,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是对于表达 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五四的“文化批判”。左翼文学既是对于五四文学的批判,同时 又是五四文学的自然发展和历史延伸。左翼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充满了历史的断裂与延 续,正如成仿吾“奥伏赫变”这个词所说明的那样。之所以说左翼文学是五四文学自然 发展的结果,是因为五四文学已经为30年代左翼文学的出现和胜利做好了准备和铺垫。 30年代左翼文学实际上是利用了五四的话语资源。一方面,30年代左翼文学是对于五四 文学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仍然采取了五四文学“新的”和“进步的”时间神话和叙述 方式。五四时期,“新文学”取代了“旧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作为“第四阶级文 学”和“新兴文学”取代了“第三阶级的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的发展是对于五四文 学的一种逻辑推进,有着逻辑同一的关系。左翼文学是五四文学的自然发展,正如鲁迅 在五四落潮以后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一样。同时,30年代左翼文学又是在新 的历史层次上展开五四的矛盾关系。五四的“平民文学”到30年代进一步为“大众文学 ”所替代,五四的“白话文”转变为30年代的“大众语”。
左翼文学的流行和左翼文化的胜利首先是一种知识的胜利。在《文化批判》杂志上发 表的李初梨的《科学与人生观——近几年来中国思想界底总结算》和朱镜我的《德模克 拉西论》对五四“科学”和“民主”这两个基本概念完成了批判和解构。创造社的《文 化批判》杂志尽管一共只出版了五期,但是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却产生了巨大和深 远的影响。它的历史作用决不亚于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杂志。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 现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而《文化批判》则相反通过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批判,造成了一场无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正如郭 沫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中所描写的那样:“新锐的斗士朱,李,彭,冯由日本回国 ,以清醒的唯物辩证论的意识,划出了一个‘文化批判’的时期。”在晚清梁启超等人 那里是“国家”、“政治小说”;在五四陈独秀和胡适等人那里是“科学”、“民主” ,“个人”、“人的文学”,30年代则是“经济基础”、“阶级斗争”、“党的文学” 。30年代左翼文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新的知识,运用阶级、经济基础、上层建 筑等透视社会的结构和矛盾。左翼文学的生长有着深厚的土壤,它的下面是社会主义的 历史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对于高度复杂化和结构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如果不 揭示它的深层结构和基本矛盾,那么我们对于它的认识就是瞎子摸象,我们对于它的谈 论就是痴人说梦。
尽管资产阶级一直想从艺术上来彻底否定左翼文学,然而还没有任何一种文学观念能 够自夸跨越了所有的时代,所以对于左翼文学的“文学性”判决实际上恐怕略显武断或 者为时过早。所有的文学观念都是排斥性的,所有的审美观念都是时代性的,即就市民 文学而言,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它都有漫长的遭受压抑和贬低的历史。而“白话 ”从“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登上“国语”的地位,则是由于现代资产阶级建立民族 国家的需要。左翼文学的历史意义并不能够及时地充分地被认识,然而,即使在直观上 ,左翼文学在其所表现的主题、题材和人物等方面所造成的变化就是有目共睹的。古代 的神话、史诗、传奇,其人物还带着神的光环,只有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文学才真正成 为人性的,也就是说成为人间性的,但是文艺复兴时代仅仅是帝王贵族的戏剧。只有到 了启蒙时代的市民喜剧中,资产阶级才开始正面进入舞台。五四时期提出“人的文学” 和“平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和宫廷文学,但是所谓“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实 际上是指资产阶级市民的文学。五四文学革命中,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指出 旧的文学的描写仅仅局限于“官场妓院与龌龊社会三个领域”,“今日的贫民社会,如 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 在文学上占一位置。”历史上不同的文学主题和题材的浮现是由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所 规定的,即使像胡适的《人力车夫》这样的在今天看来毫不足道的人道主义的“问题诗 ”,却也只有在五四这种背景之下才能产生出来。而只有在左翼文学中,工农大众才能 以新的历史姿态进入文学的叙述之中。
在形式主义的眼光看来,文学发展的历史可能是“形式”的历史。然而,如果用社会 学的眼光来看,文学发展的历史就可能成为了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通过阶级斗争 ,封建帝王与贵族、资立阶级、无产阶级依次登上文学的舞台。毛泽东在《给杨绍萱、 齐燕铭的信》中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 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 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面目。”这种历史的变化,这种新的文艺形态,有 的人把它叫做“人民文艺”,有的把它更鲜明地称为“工农兵文艺”。30年代,鲁迅在 《文艺的大众化》中正确地指出,文艺的大众化“必需政治之力的帮助”。“工农兵文 艺”的出现只有在延安解放区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新的历史 条件下才成为可能。艾青在《论秧歌歌剧的形式》中指出:“我们已临到了一个群众的 喜剧时代。过去的戏剧把群众当做小丑,悲剧的角色,牺牲品;群众是奴顺的,不会反 抗的,没有语言的存在。现在不同了。现在群众在舞台上大笑,大叫大嚷,大声歌唱, 扬眉吐气,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洋溢着愉快,群众成了一切剧本的主人公。这真叫‘ 翻了身’!”这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这是“新秧歌”伟大的文化史意义。周扬在《 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中说:“在新社会条件下,小丑的身份已经完全改变了。边区及 各根据地,是处在工农兵和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人民是主人公,是皇帝,不再是小丑 了。”
“内容大于形式”一直被认为是左翼文学令人遗憾的明显缺陷,最极端的责难就是“ 概念化”。今天我们应当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左翼文学的概念化,因为这种概念化 的现象不仅存在于蒋光慈这样的左翼文学的先驱那里,而且同时也存在于梁启超和胡适 这些资产阶级文学的先驱那里。更重要的是,曾经我们的文学为了反抗(某种特定的)政 治,因此而把文学理解为必须规避政治,为了某种具有挑战性的“纯文学”从而走向引 刀自宫的“纯文学”。“为文艺正名”、“文学回到自身”的结果,是文学的“净身” 。左翼文学有着严重的失误和教训,但是左翼文学的失误不在于它对于“政治”和“内 容”的关心。恰恰相反,文学的进步就是在于不断地要求内容,不断地扩张文学表现的 可能性。葛兰西在《内容与形式》中指出:“不妨说,谁坚持‘内容’,事实上他就是 为争取特定的文化、特定的世界观,反对另外的文化、另外的世界观而斗争;还可进一 步说,从历史的角度看,迄今为止,所谓的‘内容至上主义者’,远比他们的对手例如 高蹈派诗人‘更富于民主精神’,因为他们希望文学的使命不仅仅是为了‘知识分子’ 。”
30年代左翼文学、40年代延安文学和新中国文学并非健全、成熟和社会主义形态的文 学,它仅仅是社会主义文学的萌芽,而且它是粗糙的。甚至还必然地受着旧时代的束缚 。葛兰西在《给丹吉亚娜的信》中指出:“克罗齐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我觉得同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待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的立场相似:‘路德所到之处,文明销声匿 迹’,埃拉斯慕斯这样说。然而,历史学家们和克罗齐本人今天也承认,路德和宗教改 革运动,是包括克罗齐哲学在内的全部近代哲学和文明在内的开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 不曾理解,一场伟大的精神、道德的革新运动,即要被广泛的人民群众所接受,正像路 德所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一样,自然会采取粗俗的、以至迷信的形式。”他在《马利蒂 涅是革命者吗?》中曾经这样说:“将要诞生的无产阶级文化(文明)跟资产阶级文化(文 明)泾渭分明……那需要做些什么呢?摧毁文明的现存形式,别无选择……它意味着摧毁 精神上等级森严的统治秩序、偏见、偶像和僵化的传统,意味着毫不畏惧新生事物的勇 敢精神,毫不畏惧奇异的怪物;它意味着,当一个犯了语法错误,或者一首诗歌像瘸子 一颠一跛地行走,不那么尽善尽美的,或者一幅油画同一纸宣传画何其相似,或者青年 一代的举止行动使科学院的天真无邪的遗老们陷入尴尬的困境的时候,不相信世界会因 此而沉沦。”在未来广阔的历史视野中,人们将会正确地评价左翼文学。这也正如鲁迅 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所评论的那样:“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 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 切所谓的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需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标签: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文化批判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读书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