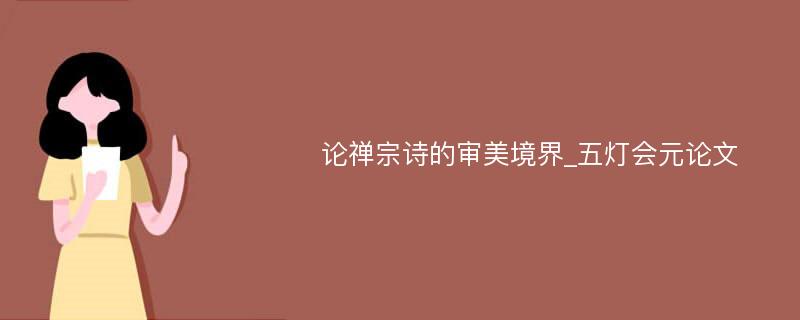
禅诗审美境界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境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00(2000)01-0061-07
禅宗以彻见本来面目为终极关怀。禅宗认为,由于迷已逐物,逐物迷己,导致了“本来面目”的失落。为了重现“本来面目”,禅宗运用般若智观粉碎迷情妄念,以回归于纤尘不染的生命源头。[1]般若智观表现为电光石火、棒喝截流的公案机锋,迸射出壁立万仞、不可凑泊的禅悟思维,形成了禅宗诗歌的审美现量境、如如境、圆融境、日用境,以及与之相应的澄明高远、色相俱泯、圆融谐美、质朴自然的美学风格。
一、一切现成的现量境
佛教禅宗把山水自然看作是佛性的显现,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在禅宗看来,无情有佛性,山水悉真如,百草树木作大狮子吼,演说摩诃大般若,自然界的一切莫不呈显着活泼的自性。苏东坡游庐山东林寺作偈:“溪声即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潺潺溪水,如同佛陀的广长舌,彻夜不停地宣说着微妙佛法;葱郁青山,明明白白地呈露着清净法身。溪水流珠溅玉,彻夜不停宣说着千千万万首禅偈,它们是如此的丰盈富瞻,凡夫之舌又怎能将它的妙义传达给别人?黄山谷的开悟,也得益于对山水真如的感悟。山谷参晦堂,多次请求禅师指示佛法的径捷入门。一日侍行之际,岩桂盛放,清香飘拂,晦堂遂借用“吾无隐乎尔”开示山谷,山谷豁地大悟。禅道明明白白地呈露在眼前,如果舍近求远,就不会闻到岩桂幽香,从香悟入。晦堂将仲尼之“吾”,置换成自然之“吾”,正表征了山水真如的禅悟体验。禅僧吟颂山谷开悟公案云:
渠侬家住白云乡,南北东西路渺茫。几度欲归归未得,忽闻岩桂送幽香。[2](《颂古联珠通集》卷39)白云乡是白云万里之外的乡关,是精神的故里。游子思归,多少次努力都没有成功,因为歧路太多,找不到回归之路。忽然间岩桂送幽香,嗅闻之际,灵光作现,方悟大道就在目前,故乡就在脚下。诗人心有灵犀,于岩桂飘香之际顿见本来。由于万物皆是佛性的显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乃是一切现成的圆满自足境,“火不待日而热,风不待月而凉。鹤胫自长,凫胫自短。松直棘曲,鹄白乌玄,头头显现。”[3](《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1)“月白风恬,山青水绿。法法现前,头头具足。”[4](《五灯会元》卷15)对圆满自足的现量境,只有泯然忘我,脱落情尘,作即物即真的鉴赏,才能得其三昧,所谓“处处逢归路,头头达故乡。本来现成事,何必待思量。”[4](《五灯会元》卷6)
现量境一切现成,不假推理,它是原真的、即时呈显的、未经逻辑理性干预的境界,不可用比量来推知揣度,是现量境的根本特点。仅凭知性逻辑并不能达成禅悟,不落二边的禅不可以计量解会。禅既不能思量,也不能不思量。落入思量,禅就会蜕化成空洞的概念、抽象的名词;坠入不思量,反理性的弊病就会产生。禅建立在非思量的基础之上,是超越了思量和不思量的现量。现量指感觉器官对于事物原真态的直接反映,纯以直觉去量知色等外境诸法的自相,如眼见色、耳闻声,未加入思维分别,毫无计度推求等作用。与现量相对的是比量,比量是以分别之心,比类已知之事,量知未知之事,如见烟比知彼处有火。禅的“现量”,指不容情尘计较直契本来面目的禅悟观照。所谓情尘计较,即是指人生种种实用利害的心念。根据审美距离说,在审美中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使客体无从与现实的自我发生钩搭,才能使之充分显示其本色。透过距离看事物的方式是特殊的观物方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事物才单纯地为我们所观赏。禅者能够不起利害不起意欲,而以纯粹无杂的审美眼光来观赏对象。此时人“自失”于对象之中,“人们忘记了他的个体,忘记了他的意志;他仅仅只是作为纯粹的主体,作为客体的镜子而存在,好像仅仅只有对象的存在而没有知觉这对象的人了……这同时即是整个意识完全为一个单一的直观景象所占据,……置身于这一直观中的同时也不再是个体的人了,因为个体的人自失于这种直观之中了。他已经是认识的主体,纯粹的、无意志的、无痛苦的、无时间的主体。”[5]
现量地观照审美对象,也是西方现代哲学的灵魂。西方哲学的主流历来是把逻辑思维方式当作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和研究,随着卡西尔“神话思维”、胡塞尔“直面于事情本身”等观念、口号的提出,20世纪西方尤其是欧陆哲学的重要特征在于哲学研究已经日益转向“先于逻辑”的东西。著名的现象学的“悬搁”、“加括号”,即是要求把人们习以为常以至根深蒂固的逻辑思维暂先悬搁起来,暂时中止逻辑判断,把逻辑思维所构成的一切认识对象也暂先“放进括号里”,以使人们可以不为逻辑思维所累,从而穿透到逻辑的背后,达到对事情的“本质直观”。现象学方法的基本精神——把逻辑思维“悬搁”起来——构成了欧陆人文哲学的灵魂。德里达的“涂掉”仍是“悬搁法”的更具体运用。被公认为英美分析哲学开山祖师的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竟也喊出了一句足以与胡塞尔的名言相比美的口号:"Don't think but look!"[6]现量的观照,正是不要想,而要看!在“看”、“直面于事物本身”的刹那,人“自失”于对象之中,空诸一切,心无挂碍,“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这自得的、自由的各个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7]“自失”于对象之中,乃是从宇宙图象未受理念歪曲时用直观方式去接受、感应、呈示宇宙图象,尽量消除由“我”造成的类分和解说,肯定事物原样的自足,此时观照主体仿佛已经化作事物的本身,与山河大地宇宙万象圆融一体。
二、水月相忘的如如境
中华民族的传统观物方式,是以我观物、以物观物。以我观物,故万物皆著我之色彩;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而禅宗的观物方式,则是迥异于这两者的第三种观物方式,它不是观物论,而是“如物论”:对“物”(真如)作直觉的“观照”,以体证遍布宇宙的真实本体如如,这就形成了“如如境”。它的关键是保持主体心灵的空灵自由,即无住生心。无住生心是金刚般若的精髓,对禅思禅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8]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中,即提出“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体现无住生心的范型是水月相忘。[9]禅者不为境转,保持心灵的空明与自由,生发水月相忘的审美观照:“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留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4](《五灯会元》卷16)“宝月流辉,澄潭布影。水无醮月之意,月无分照之心。水月两忘,方可称断。”[4](《五灯会元》卷14)无住并不是对外物毫无感知、反应,在无所住的同时,还必须生其心,让明镜止水般的心涵容万事万物。事情来了,以完全自然的态度来顺应;事情过去了,心境便恢复到原来的空明。无所住是生其心的基础,生其心的同时必须无所住。吕温《戏赠灵澈上人》:“僧家自有芳春兴,自是禅心无滞境。君看池水湛然时,何曾不受花枝影?”禅者既有芳春兴又不滞于芳春兴,禅心一似清池水,映现着世上万事万物的影子,但是受影的同时,仍然保持澄明平静,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认得性,无喜亦无忧。心若停止流动即成腐水,心必须流动,感受外境。但在流动时要保持它的幽玄微妙,在无心中映现万境的本来面目,而不注入任何东西,这便是幽。这样,才既能心随境转,又超于其境,随流之时仍保持心的虚明本性,而获得超越忧喜的安祥与宁谧。存在而超越,充实而空灵,竹影扫阶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度寒潭,雁过而潭不留影。事来心始现,事去心随空。
对水月相忘的如如之境,禅宗以“井窥驴”来象征。据《曹山录》,曹山问德上座:“‘佛真法身,犹如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作么生说‘应’底道理?”德说“如驴窥井”,曹山说只道得八成。德问曹山怎样看,曹山说:“如井窥驴。”驴窥井还有主观的成分在内,而井窥驴,则完全消泯了主观意念的中介性,主客俱泯能所双亡,超越了情识分别,是不思议的直觉境界。对此,禅诗中有极其生动的吟咏:
银碗里盛雪,冰壶含宝月。纵具四韦驮,到此虚摇舌。[2](《颂古联珠通集》卷35)
牵驴饮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踏蹄,水中嘴连嘴。[2](《颂古联珠通集》卷27)
“银碗里盛雪”是巴陵答僧“如何是提婆宗”语,表达“冰壶含宝月”的通体澄明所能双亡之境:冰壶含宝月,宝月含冰壶,身心一如,不复分别,纵使熟吟了古印度的圣经四韦陀,对此境界也无容置喙。“牵驴饮江水”系咏九峰无心合道公案。僧问十二时中如何合道,九峰答:“无心合道。”无心合道,犹如牵驴饮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踏水中蹄,水中嘴对岸上嘴,踏而非踏,对而非对,驴饮江,江饮驴,一片天机,不容凑泊。从驴窥井到井窥驴,犹如从月在水到水在月。牛头未见四祖时“如月在水”,既见之后则“如水在月。”[4](《五灯会元》卷6)水在月时的月在水,较之月在水时的水在月,能所双亡,圆融互摄,是高华澄澈的审美境界。
三、珠光交映的圆融境
禅诗的圆融境深深地烙上了华严思想的印痕。华严禅思的根本特征是圆融,表达圆融妙喻的是《华严经》中奇妙的帝释天之网。它取材于印度神话,说天神帝释天宫殿装饰的珠网上,缀联着无数宝珠,每颗宝珠都映现出其他珠影,并能映现出其他宝珠内所含摄的无数珠影。珠珠相含,影影相摄,映现出无穷无尽的法界,呈显出博大圆融的绚丽景观。圆融是华严的至境,也是禅的至境。表达圆融境的禅诗,彰显出帝网交光、重重无尽、圆融谐和的美感特质。[10]
在所有现象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时间与空间。禅诗的空间圆融境,表现为过现未三际的回互交融:“过去一切劫,安置未来今。未来现在劫,回置过去世。”在多维的涵容互摄中,过现未的对峙得到了消除:“如何是禅师?”“今年旱去年!”现在被回置到了过去,时间的单向流向变成了双向互摄:“三冬阳气盛,六月降霜时。”[4](《五灯会元》卷7)“焰里寒冰结,杨华九月飞。”[4](《五灯会元》卷13)“三冬华木秀,九夏雪霜飞。”[4](《五灯会元》卷13)“半夜日头明,日午打三更”[4](《五灯会元》卷11)是禅宗时间观念的经典表述。同时,无量劫一念,一念无量劫。对时间长短的互摄,禅宗也有超妙之悟:“宗非延促,一念万年”,[4](《五灯会元》卷1)“道本无为,法非延促。一念万年、千古在目。月白风恬,山青水绿。法法现前,头头具足。”[4](《五灯会元》卷15)祖秀的禅诗兼括了时间圆融的三际回互与一念万年两重意蕴:
枯木岩前夜放华,铁牛依旧卧烟沙。侬家鞭影重拈出,一念回心便到家。[4](《五灯会元》卷18)枯木绽花,是枯萎与新生的互摄;夜晚开花,是夜晚与白昼的互摄;铁牛卧烟沙,是无情与有情的互摄;一念到家,是一念与旷劫的互摄……在剿绝思量的禅境中,蕴含着圆融的至妙境。
《维摩经·不思议品》说“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而大海本相如故。《华严经》将此妙谛发挥到了极致,呈现出毛端纳世界、大小相如故的超悟境界:“一一毛孔中,亿刹不思议。种种相庄严,未曾有迫隘。”在一微尘、一毛孔中,有无数大海、亿万佛刹,以及须弥铁围所组成的莲花藏世界。不论是大海、佛刹、须弥、众生,容于一微尘、一毛孔时,都不失其本来相,丝毫没有压迫狭隘之感,这种观念对禅宗影响尤巨,禅宗宣称:“人得我门者,自然转变天地,幽察鬼神,使须弥、铁围、大地、大海入一毛孔中,一切众生,不觉不知。”[4](《五灯会元》卷6)并以“万柳千华暖日开,一华端有一如来。妙谈不二虚空藏,动著微言遍九垓。”[4](《五灯会元》卷18)的超悟诗境作为象征。
禅宗不但体证到时间长短的圆融、空间大小的圆融,而且体证到“无边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终不移于当念”的时空一如境。把宇宙当作一个由时间度加上三维空间的四度时空连续区,是现代相对论宇宙观的基础。要客观地了解宇宙,时空二者便不可分开。一切时间的量度,其实是空间的量度。禅者对时空的认识是“因物故有时,离物何有时”:时间因事物之存变而引起,离开某物之存在来想像时间不合于真相。唯有时空一体时,一切法的真相才显现出来,正如《宗镜录》卷28所云:“如见花开,知是芳春;茂盛结果,知是朱夏。凋落为秋,收藏为冬,皆因于物知四时也。”通过对时间现境化的充分体证,小我融入“大我”,融入宇宙生命本身,个体生命和宇宙生命成为一体,一朝风月涵摄了万古长空,电光石火包容着亘古旷劫,对时间的焦虑遂得以克服:“寿山年多少?”“与虚空齐年。”“虚空年多少?”“与寿山齐年。”[4](《五灯会元》卷4)“和尚年多少?”“秋来黄叶落,春到便开花。”[4](《五灯会元》卷13)令人焦虑的时间之流被截断,时间被空间化,对时间的恐惧最终消融于自然、消落于空间的纯粹经验世界中,这形成了禅宗的特殊的生命观,使禅宗在表达生命“向何处去”时,充满了生机圆趣:生命如青山泻翠,似皓月流辉,是杨柳扶风,是聚沫拥浪,是归海的水,是回山的云……微小与博大,黯淡与光明,浮沤与江水,短暂与永恒,个体与族类,自然与人生,都涵容互摄,织成了珠光交映重重无尽的华严帝网。在这里,有的只是生命大圆满,境界的大圆融。
理事圆融也是禅宗审美的一个重要内容。禅宗五家七宗对理事关系都十分注重。禅宗诗歌中运用了大量鲜明可感的艺术形象表达理事圆融的审美感悟。玄觉大师《证道歌》云:“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是禅宗表达理事无碍的名句。在五家七宗中,曹洞宗对理事关系尤为注重,并将理事无碍作为宗风,其偏正回互、君臣五位理论,远绍华严,近承《参同契》,以“正”指本体、平等、绝对、真如等,“偏”指事相、差别、相对、生灭等。正偏回互,组成五种不同的阶位,是为正偏五位。“正”相当于理法界,是本体界;“偏”相当于事法界,属现象界。只有理应众缘(事),众缘应事,达到理事圆融(兼带)的认识,才合乎真宗大道。由此出发,曹洞宗的禅诗象喻系统,由相应的两大意象序列组成,一是皓月、寒岩、青山、流水、岩谷、孤峰顶上之类的本体意象序列,一是轻烟、薄雾、白云、波浪、市廛、十字街头之类的事相意象序列。曹洞宗的各种五位,都是两大意象的不同回互关系。理事回互构成了曹洞宗禅诗象喻系统的核心,形成了曹洞宗禅诗触目菩提能所双遣的美感特质。[11]
最能表征禅宗圆融观念的,是现象圆融境。按照华严宗旨,本体由现象呈现,现象与现象之间均为本体之呈现而可相互呈现,不必于现象界之外寻求超现象的世界,不必离现象求本体,不必离个别求一般。这就打通了众生界与佛界、现象与本体、个别与一般的隔绝,而达到圆融无碍。克文《法界三观六首》其三:“事事无碍,如意自在。手把猪头,口诵净戒。趁出淫坊,未还酒债。十字街头,解开布袋。”将事事无碍表达得淋漓尽致,表达了现象的当体就是本体的悟境。智通禅师《法界观》云:“物我元无异,森罗镜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彻真空。一体含多法,交参帝网中。重重无尽处,动静悉圆通。”[4](《五灯会元》卷18)红法滚滚万象森罗的大千世界里,有情与无情、个体与族类、高峻与深幽、光明与黑暗,都是同时具足相应的缘起大法,共同织成了帝网宝珠,纵横交错,珠珠相含,影影相摄。它们都在光华溢目的毗卢遮那佛照耀之下,清纯澄澈,显现出一真法界的庄严绚丽图景。宇宙万象,互为缘起,又各住自位,呈显出千奇百状的生命样态,自在自为地嬗演着大化的迁变纷纭、起灭不缀、看朱成碧。在这重重无尽的法界中,情与非情,飞潜动植,静云止水,鸢飞鱼跃,都彰显着圆通法门。圆融之境脱超越了一切对立。在世俗之眼看来对峙、矛盾的意象,在禅诗中形成了不可凑泊的的禅定直觉意象:“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4](《五灯会元》卷2)这些意象在世俗之眼看来之所有矛盾、对峙,是由于经过了逻辑二分法的筛子的过滤。逻辑经验不是纯粹的经验,因为它经由了二分法这层筛子的过滤。当我们看见一座桥而称它为桥时,以为这个认识是最后的,但是事实上只有当它被概念化之后,这个认识才有可能。真正的“桥”存在于“桥”的概念之前。当概念干预现量后,桥只有依赖于非桥才得以成为桥。而圆融存在于概念化作用之前。要充分体其三昧,就必须跃出逻辑的囚室。般若智观将矛盾、对峙、枯寂的世俗意象,转化为圆融、和谐的直觉意象。这是超越了一切对立、消解了一切焦虑、脱落了一切粘著的澄明之境。它是一段论的观物方法,如果用二元的相对的眼光来看待,则如蚊子叮铁壁,永远也不可能透过。
四、任运随缘的日用境
禅诗的事事圆融境消解了一切对立,汇百川河海为一味,熔瓶盘钗钏为一金,是撞破乾坤共一家的超悟境界。但禅之所以为禅,在于它能够不断地否定、不断地超越。禅宗不但对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进行超越,甚至对禅的本身也进行着超越,且超越而没有超越之念:“文殊普贤谈理事,临济德山行棒喝。东禅一觉到天明,偏爱风从凉处发。”[4](《五灯会元》卷20)不论理事圆融、事事圆融,还是临济喝、德山棒,在饥餐困眠、秋到风凉的自在自为中,都脱落无痕。由此生发了禅诗审美感悟的另一个重要境界,这就是任运随缘的日用境。本净《无修无作》偈:“见道方亲道,不见复何修。道性如虚空,虚空何所修。遍观修道者,拨火觅浮沤。”[4](《五灯会元》卷2)本来面目如同虚空,不可修作。一旦起了修道之心,就将道作为修的对象,将无为法当作有为法,这样修成的道仍然容易堕坏。为了扫除学人向外寻求的意念,禅宗将修行与生活一体化,反对外向而修道,而主张内照式的修道,能所双泯,当下现成。源律师问慧海修习禅道是否用功,慧海说用功,“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源律师认为这与别人并无两样,慧海说并不一样,因为“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4](《五灯会元》卷3)饥吃困眠,是禅宗任运随缘、率性适意生活方式的形象表述。禅宗对随缘任运式的生活境界尤为注重。九顶惠泉甚至“饥来吃饭句、寒即向火句、困来打眠句”作为“九顶三句”,与云门三句相提并论,[4](《五灯会元》卷8)守端则以“饥来要吃饭,寒到即添衣。困时伸脚睡,热处爱风吹”作为“四弘誓愿”,[4](《五灯会元》卷19)临济也指出,“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眠。”离开饥吃困眠而追求禅道,不异南辕北辙。但任运随缘、饥餐困眠并不是把道庸俗化,而是使日常生活呈现出高情远韵。要“离家舍不在途中”,保持“土面灰头不染尘,华待柳巷乐天真。金鸡唱晓琼楼梦,一树华开浩劫春”[2](《颂古联珠通集》卷3)的存在而超越的心境。
中华民族所追求的真理,表现在民生日用之中,它与外来佛教思想相化合,成了后来隋唐时代佛教标志“触事而真”的起源。僧肇的《不真空论》说如来并不离弃真理的世界,而承受一切现实的存在,“非离真而立处,立处皆真”,这形成了僧肇以来最具中国特色的思维。真理存在于声色言语之中、日常生活之中。宗教行为,从发心、修行、证悟到涅槃,构成一个无限的圆圈,其中每一点既是开端也是终点。大道既然在声色语言之中,求道之人就不必回避声色语言,与世隔绝,而要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真理的搏动。马祖提出“平常心是道”,指出禅的体验离不开日常生活,要在日常生活中如吃饭、洗钵中都感悟到真实才是修行,所谓“鹤立松梢月,鱼行水底天。风光都占断,不费一文钱。”[2](《颂古联珠通集》卷19)《大慧宗杲禅师语录》卷26谓:“佛法在日用处,行住坐卧处,吃茶吃饭处,语言相问处,所作所为处。”禅宗对离开日用别求玄妙的倾向予以批评,主张任运随缘,将禅道落实于日常生活,化为亲切平易的人生境界,否认离开生活去求玄中玄。因此当学人问什么是玄中玄、玄妙之说时,禅师往往以“玄杀你”、“莫道我解佛法”蓦头一锥,指出离开生活别求玄妙,则与禅道日远。庞蕴偈云:
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偕。头头非取舍,处处勿张乖。朱紫谁为号,丘山绝点埃。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
禅的神通妙用,就是运水搬柴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只要运水时运水,搬柴时搬柴,就是莫大的神通妙用。日用无非道,安心即是禅。佛法在日用中,是“吃茶吃饭随时过,看水看山实畅情”式的“平常心合道”,能在日用中体现出高情远韵就是禅,无门慧开颂平常心是道,生动地描绘了禅的日用境: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闲事”指妨碍平常心的事,亦即浪费心智的事。心灵的明镜若蒙上了闲事的尘垢,则反映出来的万事万物亦将失去本来面目。一旦抛开世俗的名利欲望,那么无论在哪里,楼台上的月亮都清丽明亮,此时,饥吃困眠便有占断风光的意义,“了取平常心是道,饭来吃饭困来眠。”[3](《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5)奇特还原于平常,至味回归于淡泊,形成了禅宗极为“独特”又极为“平常”的感悟:“春来草自青”、“柳绿花红真面目”、“菊花开日重阳至,一叶落时天下秋”。
禅诗审美境界的内涵极为丰厚,为了说明的方便,本文从四个层面进行探讨。实际上这四个层面既有独立性,更有关联性。现量境剿绝情识,不容凑泊,要求审美主体以空灵之心原真地直观审美对象,能所俱泯,这就是水月相忘的如如境;禅宗认为,宇宙人生的如如境,是万物互融互摄,处于重重无尽的缘起中,这便是禅的圆融境;圆融得脱落了圆融念,便是禅的平常心、日用境。再者,禅不可说,本文提出的禅诗审美现量境、如如境、圆融境、日用境,只是于不可言说中权立的言说化域而已。禅宗禀持金刚般若,随说随扫,不论何种境界,言筌既立,立予扫除:“华严现量境界,理事全真……卷舒自在,无碍圆融。此虽极则,终是无风匝匝之波!”[4](《五灯会元》卷19)(扫除现量境、圆融境)“道个如如,早是变了也!”[4](《五灯会元》卷3)(招除如如境)“或又执个一切平常心是道,以为极则,……此依草附木,不知不觉一向迷将去!”[13](《五灯会元》卷44)(扫除日用境)真正的禅诗审美境界,不容凑泊,心行处灭,正如盘山所云:“心月孤圆,光吞万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复是何物?”[4](《五灯会元》卷3)只有到了这里,才是禅宗千圣不传的向上一路。
收稿日期:1999-0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