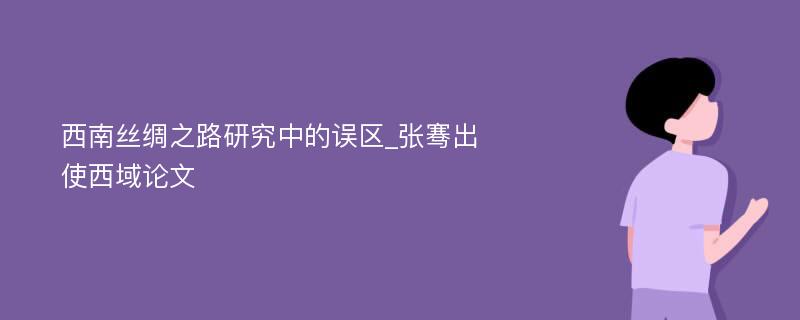
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认识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丝绸之路论文,误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学术界积极开展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发表论文近百数,并有多部专著和论文集编辑出版。这当然是一桩盛事。其实该项研究并不自近年始,早在本世纪初,西方的汉学家以及我国的一些学者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抗战期间由于修筑滇湎、中印公路,更兴起一时热潮。算来已有半个多世纪,今后恐怕还要继续下去。
对它的最初研究,好像不是专门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912年发表的《支那名称之起源》,在谈到中国与印度交往时,顺便提到张骞在大夏见到四川的竹杖和布,“而运输的路线,不是交广的海道,乃是缅甸高原的陆道”(注:伯希和著、冯承钧译:《支那名称之起源》,《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42页。)。类似的话也在他的另一部专著《交广印度两道考》中出现。由于他主要不是论述这个问题,因而着墨不多,有一种传达学术信息的意味。20年代,梁启超撰《中国与印度之交通》一文,提出“滇湎路”,以为此“即张骞所欲开通而卒归失败”的道路(注:《中国与印度之交通》,《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版。),论述亦过简略,实际只是说出一个观点。此后,有关学者在各自的论著里多把这条交通路线与张骞联系起来,进一步肯定了川滇缅印古道的存在。
但是,这些论著在方法论上似乎都有一种偏差:问题是由张骞从大夏回国后向武帝建议开通身毒国道而提出来的,但却很少从这个建议的始末缘由,或者说从记述这件事情的《史记》之《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的原始材料本身进行研究。也许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及深入,特别是滇缅和中印公路的建成通车,已经在事实上给古代川滇缅印道做了证明,再从张骞的原始材料来讨论就显得无此必要了。
殊不知这样一来,给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后的研究,带来了先入为主的障碍。由于以往研究的历史较长,又出自名家之笔,因而因循旧说,以讹传讹的现象时或有之,某种程度上将研究引入一个误区。今举其中几个要点,祈望时贤予以指正。
一
张骞当年向武帝建议开通的,或者说他所指求的“身毒国道”应该是哪条路线,在以往的研究中始终没有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好像这不是个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在张骞向武帝汇报的时候早已明确了。比如上引梁启超《中国与印度之交通》即云:“滇缅路,即张骞所欲开通而卒归失败者也。”虽未便明言此即张骞本人早已经认定的路线,但这种倾向是有的。西方的一些学者亦著文说:“张骞事实上已清楚地知道,在四川和印度之间,通过云南和缅甸或阿萨密有一条商路。”(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中译本,第376页。)“阿萨姆—缅甸路线的最早资料出处,见于公元前126年汉代张骞出使月氏国归来向武帝提交的报告中。”(注:S.L.Baruah《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印度历史证据:阿豪马人迁居阿萨姆的路线》,江玉祥译,《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二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这就确确实实将滇缅道的专利权归之于张骞。
事情果然是这样吗?
为便于分析,先将《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的原始材料照录如下: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
从以上两传的记述可以肯定,无论是张骞抑或汉武帝,都不知蜀身毒道的具体走法,所以才“四道并出”,以今成都(蜀)和宜宾(犍为)为始发点,从不同的方位探索。结果出máng②、出冉,即从成都西北经今阿坝地区的一路,为氐族所阻;出徙,即由成都西南经今天全县的一路,为筰族所阻;出邛、僰,即由成都和宜宾分别向南和西南进入云南境内的二路,又在今大理一带为昆明族所阻,皆半途而废。这本没有什么疑问。唯一容易引起误解的,似乎只有《西南夷列传》“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这一句话。但这不过是张骞因在大夏见到邛竹杖,而相应做出的揣度之词,他头脑中并无肯定意向,更无具体的路径。或此句为太史公的夹叙亦未可知。西方学者可能不谙古汉语句式结构,出此讹误,而中国学者何以不察?尤其80年代中发表的一篇论文,在引证了上述两段记述之后,写道:“司马迁不嫌重复,写出的两篇文字,把它参合审核,文义非常清楚。即是说:蜀西南经滇缅是与印度有一条原始的商道相通的。蜀物曾从这条路输入印度,更远销阿富汗(大夏)和伊朗、伊拉克等半沙漠亚热带气候地区。这位精细的侦察者张骞,推断得没错。”(注:任乃强:《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古代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这就更令人费解了。思之再三,或作者出于这种考虑:司马迁初时虽有“四道并出”的记载,但两传最后都落在开通西南夷以指求身毒国这一点上,因而客观上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这是张骞谋划的结果。实则不然。
首先,开发西南夷最早并非由张骞提出。早在张骞回国之前,武帝即“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略定西夷”(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为使这件工作有效进行,并发巴蜀之民数万人,以期开通西南夷的道路。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朝廷上有不同意见,道既未开通,经略西南夷亦就此搁置。在这个时候,张骞从西域回来,陈述经身毒以通大夏的利害,武帝乃旧事重论。开发西南夷始终是武帝“怀远”的既定方针,张骞的提议促使武帝将指求身毒国与经略西南夷这两件事合并执行。“四道并出”,最后落实在西南夷路线上,与其说是张骞的主张,勿宁说是武帝早有的成算。在武帝的心里,指求身毒国道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更现实的恐怕还是借此开发西南夷。
另外,在四方探道的过程中,又有些新的线索加重了西南夷道的筹码。如派往南方的一路,虽闭于昆明,但打听到了一个消息,即由此往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而其国人“乘象”,又正好与张骞在大夏听到的关于身毒的情况相符。还有一种情况也值得重视。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及《武帝纪》等章节,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秋,司马迁曾随驰义侯往征西南夷,直到次年十月方归,在那里总共住了有一年的时间。毫无疑问,他对当地的交通是熟悉的。《大宛列传》所记昆明以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以及蜀商在那里货贸的情况,既可能来自武帝派出探道的“间使”,亦有可能是太史公本人实地考察所得到的第一手材料。著史者的个人导向不可轻估。在这之后,武帝下更大决心,派遣将军郭昌和卫广率数万士兵“往击昆明之遮杀汉使者,斩虏数万人”(注:《史记·大宛列传》。),西南夷道仍不能通。纵观武帝之经略西南,前后凡30年,始终是将探索交通路线置于大的政治框架之内,探道最后落实在西南,是客观政治形势发展的结果,并不能说明此即张骞所指求的路线。
二
研究西南丝绸之路的学者,为要证明中国西南与印度早有交通往来,经常使用的论据即《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中一节文字:“(永昌)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永昌,一般认为即今云南保山一带,其地既有“身毒之民”,当然与印度关系密切,或以为这些人即是来永昌通商的印度侨民。
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先要弄清这里所说的“身毒之民”到底指什么?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总叙》:“武帝使张骞至大夏国,见邛竹、蜀布,问所从来,曰:‘吾贾人从身毒国得之。’身毒国,蜀之西界,今永昌是也。”看来,他对身毒国的概念不清楚,而且对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知识所知甚少,这对于一个专门史学著述家是难以理解的。因而现代学者或以为“永昌”后脱“徼外”二字(注: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15页;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0页。),补加后即成:“身毒国,蜀之西界,今永昌徼外是也。”句子既能读通,也合乎情理。这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常璩当日未必如此疏忽,本意恐亦非如此,应另有说。按《慧琳音义》卷八十一注释“牂柯”一词,有云:“若从蜀川南出,经余姚、越巂、不喜、永昌等邑,古号哀牢玉(按即哀牢夷,“玉”与“夷”通假),汉朝始慕化,后改身毒国,隋王之称也。”原来,“身毒国”是哀牢夷后来改称的国号,其居地即在永昌,此或即常璩将张骞所说之身毒与永昌混为一谈的原因。“隋王之称”一句中,“隋”当为“随”字之误,是哀牢夷某代国王名“身毒”,故国亦随王改称身毒。此种做法在哀牢并非首创。《后汉书·西南夷传》注引杨终《哀牢传》:“(哀牢始祖)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知。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耦代。桑耦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栗代。”扈栗,《后汉书》作贤栗,光武帝刘秀建武二十三年(47年)前后在位,如果以二十年为一代,上溯四代至哀牢,当公元前一世纪后期,“哀牢夷”之得名显然系因其酋长取名“哀牢”的缘故(注:《后汉书·西南夷传》:“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沙壹,居于牢山。”《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以“牢山”为“哀牢山”,曰:“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其先有妇人,名曰沙壹,依哀牢山下居。”则哀牢之得名似因哀牢先民居于哀牢山的缘故。今人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以杨终《哀牢传》中所说的禁高以下第四代王“哀牢”系因其父祀哀牢山而得子,故以哀牢为名。今甚可疑者,倘若哀牢夷之得名确如常璩所言,系因该山为哀牢夷之民族发祥地,那么《史记》及《汉书》“西南夷传”中应该有所反映,可惜没有。说明那个时代还没有“哀牢夷”之名。东汉明帝时杨终的《哀牢传》始见其名。今据哀牢王世系,
以“哀牢”命名的酋长当公元前一世纪后期,已近西汉末年,大概从这时起,它才与中原联系,而对外打出的国号即以酋长的名字“哀牢”应之,则哀牢之得名以“随王之称”的说法最为近是。这种传统影响后世,哀牢之再改名“身毒”,或即其延续。)。至于它何时改称身毒,史无明载,但以《慧琳音义》的行文逻辑(古号哀牢玉,汉朝始慕化,后改身毒国)来分析,总在“汉朝”之后。《唐会要》曾引《南中八郡志》:“永昌,古哀牢国。传闻永昌西南三千里有骠国,君臣父子,长幼有序,然无见史传者。”按南中原为七郡,西晋太安二年(303年)置晋宁郡,与前七郡合为八郡。顾《南中八郡志》之书名,当写于晋太安二年之后(注:参阅方国瑜上引书第31-32页。),是西晋中后期哀牢夷并未改名;而《华阳国志》成书于东晋永和年间(345-356年),常璩此时已称哀牢夷所在的永昌为身毒,则改名亦必在这之前。前后限定,哀牢夷之称身毒国或在两晋之交。
诚如是,则《华阳国志》所谓永昌郡有身毒之民,该句中的“身毒”不过是哀牢夷的代称,绝非指印度;而常璩将“身毒”与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这些西南夷中的族名并列,显然是把“身毒”(亦即哀牢)作为西南夷中的一支来提的。按永昌之设郡在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分益州置(注:《后汉书·地理志》。),地域十发辽阔,汉时西南夷的各民族,相当一部分在永昌境内,哀牢不过其中之一,因而才与闽濮、鸠僚等并列之;而哀牢在常璩撰书时既已改称身毒,那么言哀牢夷便以“身毒之民”当之,不过变通一下写法而已。此顺理成章之事,应无疑惑。而且,哀牢改称身毒的时候,已是两晋之交,去汉遥远,以此印证汉时,甚至是西汉初年的中印交通,也失去了应有的针对性,作为论据是不能成立的。
三
西南丝绸之路,按照通常的解释,系由四川西南经云南、缅甸而入印度阿萨姆邦,不少学者在论述这条路线的走向的时候,引用《高僧传·慧叡传》以说明之:
释慧叡,冀州人,少出家,执节清峻,常游方而学,经行蜀之西界,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见而异之,疑是沙门,请问经义,无不综达,商人即以金赎之。既还袭染衣,笃学弥至。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
引用者将文中“经行蜀之西界”与“乃至南天竺界”联系起来,以为慧叡西行求法必循滇湎道。袁嘉谷在《卧雪堂集》卷二二《滇南释教论》中说:“由蜀通竺,非滇即藏,可断言也。晋慧叡从蜀之西界至南天竺,法献以元徽二年游巴蜀,道经芮芮……唐玄照取道吐蕃,在印十一年……皆由蜀川牂柯道西游者。夫牂柯为蜀、滇、黔交界之处,由此入竺,非滇莫属。”梁启超亦云:“《求法传》言五百年前有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柯道而出,注云‘蜀川至此五百余驿’,计当时由云南经缅甸入印也。《慧叡传》称‘叡由蜀西界至南天竺’,所遵当即此路。果尔,则此为东晋时一孔道矣。”(注:梁启超:《中国与印度之交通》,《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2-133页。)
此说非是。袁嘉谷和任公先生均将《慧叡传》中“蜀之西界”概念理解错了。
东晋以至南朝之世,“蜀之西界”而又据交通要道者,应从益州(成都)西出郫县的方位去寻求。同一部《高僧传》,其卷八《玄畅传》谓刘宋末叶,玄畅由荆州至成都,“至昇明三年,又游西界,观嘱岷岭,乃于岷山郡北部广阳县界见齐后山,遂有终焉之志。”按广阳县治在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西北,此处既云“西界”,当可借以明确《慧叡传》中“蜀之西界”的概念及其地理范围。《玄畅传》并有“河南吐谷浑主遥心敬慕,乃驰骑数百”迎玄畅于齐山之语,尤证“蜀之西界”应与青海的吐谷浑为邻。吐谷浑迎请玄畅以及慧叡“经行蜀之西界”被掠,走得均为同一路线,即由成都西出郫县,经广阳(茂汶)、龙涸(松潘)而至吐谷浑。至于慧叡被赎后再去印度,当从被掠的地方——蜀之西界直入吐谷浑,经西域而至,绝不会走滇、缅。固不待言。
今人看待“蜀之西界”,往往失之宽泛,有时还用来指连接云南的地段。但古籍所载,均有定位。“蜀之西界”在晋、宋之时是一个严格的地理用词。且不言上举《玄畅传》实证,即从慧叡在蜀之西界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的情节,也难以将它比附为与云南交界之处。因为晋、宋之际,蜀中能够用作牧场的只有茂汶及其邻近的吐谷浑地,“牧羊”是此地独有的人文景观。将“经行蜀之西界”理解成走滇缅道,袁、梁二氏之误甚矣!
袁氏,滇史专家;任公先生,学界泰斗。二氏治学不可谓不精,然亦有疏漏者。后人不辨,附和者多,又不肯从史料本身字斟句酌,辗转抄缀,妄用此则文字,致生偏误,是极其可惜的。
四
还有一则被经常引证的材料,似也应审慎对待。见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慧轮传》:
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寻弶伽河而下,至密栗伽悉他钵娜寺。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柯道而出,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年矣。
室利笈多大王即印度笈多王朝的建国者旃陀罗笈多(Gandragupta I)的祖父,梵文'Srīgupta,公元3世纪晚期在位,则此20余僧赴印时间亦当在3世纪末。由于文中指明唐僧系由“蜀川牂柯道而出”,不少学者便推测系走滇缅一路,并以此极证川滇缅印古道开发利用之早。上引梁启超等文在谈慧叡的同时,亦谈到《慧轮传》的内容,并将“蜀川牂柯道”与由滇缅入印的交通路线联系起来,在两者之间画了一个等号。凡此,笔者认为均有可商榷之处。
首先,蜀川牂柯道是否即为川滇缅印道?《汉书·西南夷传》记载:
建元六年(前135年),大行王恢击东粤,东粤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晓南粤。南粤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可行船。南粤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粤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为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上许之。乃拜蒙以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符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
引文中的“牂柯江”即盘江,自贵州东南流经广西、广东入海。广西一段又称红水河,广东一段称西江。番禺,南粤首府,今广东广州市。僰道,今四川宜宾西南安边场。由僰道至番禺,系从宜宾南下,穿越贵州,即古夜郎国境,浮舟北盘江、红水河、西江而至。牂柯道的开发是针对南粤的,“自僰道指牂柯江”,目的是通过牂柯江抵南粤境,由西北而东南,此道的大方向至为明确,不能随意解释。
张骞向武帝建议通身毒国,其事要晚于唐蒙开牂柯道。当时曾“四道并出”,从不同的地理方位进行探索,其中出邛、僰二道,被如今研究西南丝绸之路的学者认定为由四川经云南、缅甸进入印度的路线。特别是出僰,由于它和牂柯道的始发点相同,最初的地段又有重合,故连带以为牂柯道亦是由陆路通身毒的路线之一。实误。
按“出僰”一路,不过因袭唐蒙旧道,或者时间再往前,因袭秦五尺道,试由此重新探索一条新路,最终并非走牂柯,而是由川南的僰人居住区分道向滇西走去,遂闭于巂、昆明。所行与牂柯道的方向刚好相反。一个西南,一个东南,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因此,可以肯定,蜀川牂柯道绝非川滇缅印道。
牂柯道最早的或者说原始的出处,皆见于汉代的史学著作,作为历史地理学上的严格概念,它的起点为今四川宜宾,终点为广东广州。如果义净明了这一点,而所说“从蜀川牂柯道出”也确实遵从这个原则,那么“唐僧二十许人”的赴印路线必定循陆路(包括北盘江、红水河和西江的水路)由宜宾至广州,复由广州循海路穿越马六甲海峡或克拉地峡,沿中南半岛的西海岸从恒河入海口进入南亚次大陆。支那寺的地点在恒河下游,亦给人一种由海路而至的印象。
然而,事情多有枝节。《慧琳音义》卷八一曾注释该《传》中“牂柯”一词:
案牂柯者,南楚之西南夷人种类,亦地名也。……今因《传》中说往昔有二十余人从蜀川出牂柯往天竺得达,因有此说。遂检寻《括地志》及诸地理书、《南方记》等,说此往五天路径:若从蜀川南出,经余姚、越巂、不喜、永昌等邑,古号哀牢玉,汉朝始慕化,后改身毒国,隋王之称也。此国本先祖龙之种胤也。今并属南蛮,北接互羌,杂居之。西过此蛮界,即入土蕃国之南界。西越数重高山峻岭,涉历川谷,凡经三数千里。过土蕃界,更度雪山南脚即入东天竺东南界迦摩缕波国,其次近南三摩怛吒国、呵利鸡罗国及耽摩立底国等。
看来注者把概念完全弄颠倒了。他所公布的路线,即“从蜀川南出,经余姚、越巂、不喜、永昌等邑”,根本不是牂柯道,而是零关道向南,复向西的延续。文、题不符。不知是何缘故?或以为此二十余僧必循陆路,而义净又明言“从蜀川牂柯道出”,遂强作解人,硬把东边的牂柯道拉到西边,与零关道及其延续的路线重合,最终指向天竺,以圆其说。
义净的自注亦颇令人费解。传文“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僧所造”句后,义净注云:“支那即广州也,莫诃支那即京师也。”应有一定含义。或指明此唐僧二十余人来自广州。但“从蜀川牂柯道而出”句后复注:“蜀川去此寺有五百余驿。”又生疑惑。按义净作注,大抵有闻必录,但注释与原文的对应以及逻辑关系,往往失之严谨,时或有误。即以此句“蜀川去此寺五百余驿”来说,当本义净本人的另一部著作《南海寄归内法传》。该书卷一在论及佛教的部派时曾提到“东裔诸国”,自注云:“从那烂陀寺东行五百驿,皆名东裔,乃至穷尽有大黑山,计当土蕃南畔。传云是蜀川西南行可一月余,便达斯岭。”审其路径,显系前引《慧琳音义》卷八一的走法,此是唐人在往昔零关道的基础上,通过实践重新确认的一条经吐蕃南界至东天竺的“陆路捷径”。但义净截取此注“五百驿”之说,转用在“支那寺”上,却忽略了牂柯道的基本走向,顾此而失彼。
其实,义净与慧琳一样,可能都错把从四川东南行的牂柯道当做西南行的川滇缅印道了,因而作注时才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既云支那指广州,那么以“支那”命名的寺院里的唐僧自然来自广州,从广州至印理应循海路;但又注“蜀川去此寺五百驿”,驿站只有陆路交通才有,似又喻示唐僧由陆路入印。令读者无所适从。
当然,笔者不能妄断古人文义,不拟就此具体讨论当年唐僧二十余人的入印途径,但也不能跟着古人犯错误。汉唐史籍所载各交通路线均应有一定指向,不能串用,如果在字面上写明“出牂柯道”,而实际上根本不经过牂柯,那么这个牂柯道就要画一个问号。对义净此文连同慧琳注释,我们目前还没有太多的材料可以做出圆满的解释,窃以为应慎用为是。
五
西南丝绸之路既由川滇缅而通印度,理所当然会想到印度的佛教是否也早由此道传入四川,并进而传入中原。有些学者习惯于简单地运用这个推理公式,但实际情况却未必如此。在这里,我只是想说明,这个逻辑推理的前提是否存在,亦即川滇缅印道是否开发得这么早?其次,它开发之后是否便即具备了佛教传播的条件?
关于第一个问题,发表的论文很多,多数意见认为在张骞向武帝提出建议前已经民间开发,只有少数持否定意见。本文不准备在这方面多谈。综合史籍有关西南夷的论述,武帝在益州建郡之后数年,曾“并昆明地”(注:《后汉书·西南夷传》。),因而可以认为昆明夷的道路开通了一部分,但不是完全畅通,昆明夷时有反复,武帝以后未再见大的举动,终西汉之世,仍未再向昆明以西发展。
东汉初期,“昆明”以西的哀牢夷同汉朝对立,建武二十三年(47年),哀牢王贤栗率军进逼益州西部边境,与归附汉朝的夷人部落鹿茤交战,遭到惨败,乃率种人2770户,17659口,诣越巂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帝封贤栗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时在建武二十七年(51年)。至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柳貌(抑狼)又“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比上次户口人数多几十倍(注:《后汉书·西南夷传》。)。这两批大规模“内属”已尽哀牢其国。东汉政府将这一大片领土分置哀牢、博南二县,并将原滇西的巂唐、不韦、比苏、邪龙、云南、茤榆六县由益州郡划出,与新置哀牢、博南合并而为永昌郡。至此,西南夷居地全部纳入汉朝版图。也就是说,直到公元一世纪后半叶,川滇湎印道的川滇一段(包括今缅甸的一部分)才得正式开发。
东汉中期,和帝永元六年(94年),永昌郡“徼外敦忍乙王慕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九年(97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永初元年(107年),徼外僬侥仲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永宁元年(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注:《后汉书·西南夷传》。)敦忍乙、掸国、僬侥种夷皆在今缅甸境内,是公元一世纪末,此道的缅甸一段亦得开通。奇怪的是《后汉书·西南夷传》并无一字提及印度,遍索这一时期的汉文文献未有印度经西南夷交通中国之事,而中国的史官对此时的中印关系并非一无所知。《梁书·诸夷传·总叙》:“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来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是桓帝时印度与中国通过日南海路联系;桓帝之前则通过陆路,即西域联系,与川滇缅印道无涉。证据见于同传中天竺国条:“汉和帝时(89-105年),天竺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遂绝。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四年(161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引文中的“西域反叛”系指班超离开西域后,继任的都护任尚任事峻刻,对西域诸国不加抚恤,引起反感,纷纷起兵攻尚;朝廷征河西羌兵驰援西域,又引起羌人起义,陇道因此断绝,檄书不通。东汉政府感到西域险远,难相应赴,乃于安帝永初元年(107年)罢西域都护,并撤回西域的戍卒,“自此遂弃西域”(注:《后汉书·西域传》。)。由于道路不通,天竺自难再由西域入贡,这才探索别的途径,一直到桓帝延熹二年始由海路再至中国。这段记载清楚表明,和帝、安帝间,当缅甸境内诸君长通过西南夷交通中国的时候,印度仅取西域西北一线贡献,尚未经缅甸进入中国;至汉末桓帝世,又改由日南海路,仍未利用缅甸陆路。一句话,川滇缅印道作为中西交通线,迄于汉末,仅完成了前三段,最后一段通印度的道路并未凿通。
要之,此线的开发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早,印度佛教早由东汉甚至更早从此线传入的说法并无交通路线方面的真实凭据。顺便提一下,本文第二、三、四部分谈到研究西南丝路的学者误用或者应慎用的几则史料,也同时被这些学者用于论证佛教早由川滇缅印道传入的证据,自然也不能说明问题。不再赘述。
那么,汉代之后,假设在一个不算长的历史时期已经全线开通,印度佛教是否具备由此线传入的条件?
我们知道,在佛教产生的时代,印度恒河流域分布着许多著名的城市,如瞻波、舍卫、吠舍厘、王舍、波罗奈、迦毗罗卫等等。由于佛教与商人的特殊关系,最初佛教活动的场所均在这些大城市,释迦牟尼每年“夏坐”以及平时停留的地方,所谓“精舍”之类,亦在这些大城市之中(注:季羡林:《商人与佛》,《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8页。)。这在早期的阿含部经典中有所反映。这个特点贯穿早期佛教传播的整个过程。释迦牟尼在世时,他“游行”的路线基本上都是经济繁荣的商路,此后佛教对外传播也都是循着一些著名的国际商路进行,这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
应该指出的是,佛教自在恒河流域发展起来以后,几个世纪,它的传播方向一直指向西北印度,后来扩展到南印度。这有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文地理方面的原因,暂不讨论。向东,则没有确凿的资料可以显示出它的传播迹象(注:佛教史有个说法,在阿育王时代曾派遣高僧大德向孔雀帝国的九个周边地区传布佛教。其中末示摩(Maj-jhima)被派往雪山(Himavanta),亦即喜马拉雅山地区,须那(Soma)和郁多罗(Uttara)被派往金地(Suvarnabhumi),亦即孟加拉和下缅甸,似乎喻示了佛教向东早期传播的可能。但学者们对阿育王向九方布教之事,历来有不同意见,特别对上述两地,尚未有更多的材料(文献及出土物)能够证实。)。迦摩缕波国所在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在印度古代历史发展阶段上比较落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称此地为“蛮国”。好象在公元7世纪之前,佛教还没有传到这个地方。《大唐西域记》卷十“迦摩缕波国”条:
迦摩缕波国周万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土地泉湿,稼穑时播。般核娑果、那罗鸡罗果,其树虽多,弥复珍贵。河流湖陂,交带城邑。气序和畅,风俗淳质。人形卑小,容貌釐黑,语言少异中印度。性甚犷暴,志存强学,宗事天神,不信佛法,故自佛兴以迄于今,尚未建立伽蓝,招集僧侣。其有净信之徒,但窃念而已。天祠数百,异道数万。
玄奘抵达该国的时候,尚“不信佛法”,甚至到了宋代,这种情况亦未有多大改变(注:宋沙门志磐所撰《佛祖统记》卷三二亦称“此国(按指迦摩缕波)已历千世,至今不信佛法。”),在此之前,佛教怎么可能通过这些真空地带再传中国呢?当然,有的学者会提出,迦摩缕波是否在佛教传播中起一个中间“过路”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东汉及其以后一个时期,尚属佛教的初传阶段。如上所述,当时的传播方向指向西北,并按国际商道进行。这个商道的某个中间地带可能仅起过路作用,比如明帝佛教初传中国之时,西域即为“过路”(注:参阅拙文《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但西域毕竟是在著名国际商道上,早在佛教传播之前即已沟通西北印度,成为丝路的中枢,而迦摩缕波国以及由此想像出来的川滇缅印道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其一,佛教当时并未向东传播;其二,前已说明,该道迄于汉末,其开凿止于中国西南边境及其连接缅甸的一部分,所谓“蜀贾奸出物者”有可能穿越北道到达印度(如果“滇越”真的是印度阿萨姆邦,亦即玄奘所记迦摩缕波国),不过为牟取暴利,以生命作赌注,行险侥幸而已,不能认为它就是流通有序的正式商道,佛教的传播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进行。
认为印度佛教应早由此道传入,或系不甚了解佛教传播的自身规律与特点以及它的早期传播的历史使然。
六
一些学者曾就考古发现,比如四川茂汶早期石棺葬中出土的不含钡的琉璃珠、云南江川李家山战国墓出土的蚀花肉红髓珠等域外工艺品,以证西南丝绸之路,亦即川滇缅印道的早期存在。并引用文献资料,如鱼豢《魏略·西戎传》:“大秦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以补充说明之。1990年以来开展的关于“佛教初传南方之路”的学术讨论中,又有学者将云南大理东汉墓出土的吹萧胡俑认作佛教由滇缅道传入的证据之一。
可是,怎么证明它们必然是由滇缅道,而不是别的路线输入的呢?
诚然,不含钡玻璃珠也好,蚀花肉红髓珠也好,都不是中国本土的东西,戴尖帽的胡俑也可以认为与中西的文化交流有关。但四川和云南通域外的交通路线并不只滇缅路一条,而这些域外工艺品和陶俑又并不具备经滇缅的独有的文化特征;茂汶不含钡琉璃珠被认为来自中亚和西亚(注:高至喜:《论我国春秋战国的玻璃器及有关问题》,《文物》1985年第12期。),蚀花肉红髓珠亦来自西亚和大秦(注:张增祺:《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思想战线》1982年第2期。),这些地方的物品进入中国,固然可由滇缅道,但也可由西域道、牂柯道和蜀交趾道。至于《魏略·西戎传》,行文逻辑已将永昌与通过永昌与交趾七郡的关系摆放得十分明确,恰恰不能证实其地所出之“异物”来源于滇缅道交通。
汉墓所出胡人俑,非仅云南大理一处,更多的是在广西和广东发现。如广西贵县、广东广州以及广东顺德等汉墓中均出土了大量胡人俑,迥非偶然。如果云南大理所出胡人俑体现了中外来往的历史事实,与其说是通过滇缅道,毋宁说通过牂柯道或交趾道更有说服力。
本文第四部分曾简单论述了牂柯道,实际上这条道路的开发是很早的。《史记》和《汉书》的《西南夷传》均言南粤“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按同(桐)师在今云南保山一带,在大理以西,地属西南夷。是西南夷在西汉初年已通过牂柯江交通南海诸郡。
大约在这前后(具体时间不能确定),由蜀经僰道、滇池东南交通交趾的蜀交趾道也已开通。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偏于中国西南的益州以及南隅的交趾相对来说比较安定,大批士人进入这两个地区,并在这个范围内移动。诸葛亮治蜀,积极发展周边关系,故交趾与蜀来往密切,我们完全可以从《三国志》的某些记载说明此道在东汉朝的一些情况。蜀汉建国之初即为太傅的东汉名士许靖,于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避乱交州,与交趾太守士燮交厚,后应刘璋之招,由交趾入蜀(注:《三国志·蜀书·许靖传》。)。具体入蜀的路线未做交待,但据《三国志·蜀书·刘巴传》可推其大略。该传称:“刘巴,字子初,零陵烝阳人也。……先主奔江南,荆、楚群士从之如云,而巴北诣曹公。曹公辟为掾,使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会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远适交趾。先主深以为恨。巴复从交趾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辞谢罪负,先主不责。而诸葛孔明数称荐之,先主辟为左将军西曹掾。”注引《零陵先贤志》:“巴入交趾,更姓为张。与交趾太守士燮计议不合,乃由牂柯道去,为益州郡所拘留。”汉末的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县东北,刘巴由交趾入蜀,或溯红河,或溯明江和盘龙江而上,西北入益州郡界,经滇池北上蜀郡。又据《晋书·陶璜传》,晋灭蜀汉后,南中监军霍弋遣将“自蜀出交趾,破吴军于古城,斩大都督修则、交州刺史刘俊。”按此时之“南中”当指以滇池为中心的地区,是晋军自滇池起兵无疑;同传并载晋灭吴后,吴交州刺史陶璜留任,在其上朝廷的奏文中称:“宁州、兴古接据上流,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陆并通,互相维卫。”晋时宁州即汉末益州郡治所,兴古在今云南弥勒县以南,则由交趾入蜀路线应溯明江和盘龙江直上;陆路傍河岸而行,二路互相维卫,皆西北经滇池,道里甚明。
蜀交趾道如果不溯明江和盘龙江,而是溯红河,并且不北上滇池,而是一直向西,溯元江可直达今云南大理,所以汉时由永昌郡通交趾的路线也是十分便捷的。《魏略·西戎传》所称之永昌“异物”很可能便是由此水道输入。
牂柯道和蜀交趾道皆由四川东南出,它们最初的某些地段可能重合,自曲靖和晋宁以下即分股,一由牂柯江(盘江)、红水河和西江去广州,一由红河或盘龙江、明江去交趾。它们在汉代为四川通往南海和交趾的两条根本交通线。
实际上,汉代在中国西南开凿的真正能够使用的中外交通路线也就是这么两条。以往开展的“西南丝绸之路”或称“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在概念上有一个限定,专指川滇缅印道(注:参阅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和1995年出版的《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上的有关论文。)。我以为这个框框应该打破。大西南古代早期的中西交通,以今日论之,将其比之牂柯道和蜀交趾道或较川滇缅印道更为切合历史实际,也更为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