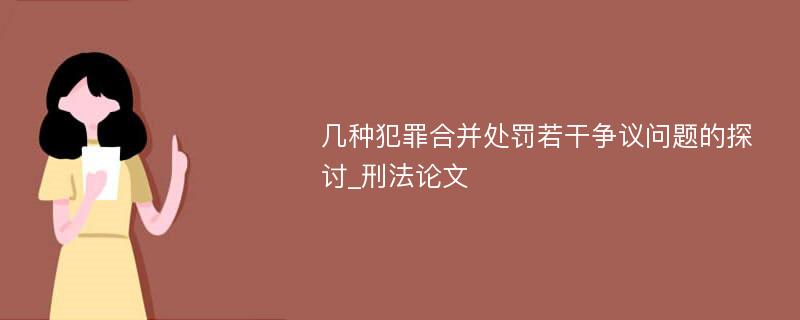
数罪并罚若干争议问题研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于同种数罪应否并罚
《刑法》第69条中所谓的“一人犯数罪”是仅指数个性质不同的犯罪即异种数罪,还是也包括数个性质相同的犯罪即同种数罪?也即对于同种数罪是否应实行并罚的问题。对此,理论界有不同的意见分歧:有的认为,对一人所犯同种数罪无须并罚,只按一罪酌情从重处罚即可;①有的认为,刑法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并未限定只适用于异种数罪,因此,对于同种数罪当然应实行并罚②;有的认为,对于同种数罪是否实行并罚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当以能否达到罪刑相适应为标准,决定对具体的同种数罪是否实行并罚,即:当能够达到罪刑相适应时,对于同种数罪无须并罚,相反,则应实行并罚。③
笔者认为,虽然对同种数罪不并罚而按一罪处理,是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的通行做法,但从司法与立法的关系上看,司法应当受制于立法,而不能超出立法的规定进行司法。根据《刑法》第69条规定,只要是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就应当实行数罪并罚。这意味着只要承认同种数罪也属于数罪的范畴,就应当对同种数罪实行并罚。因此,不对同种数罪实行并罚,没有法律根据。而且,上述观点之所以主张对同种数罪一概不实行并罚或者原则上不实行并罚,其主要根据就是要贯彻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认为现行刑法对各种犯罪规定的法定刑也能够满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但是,笔者认为,刑法之所以规定对数罪实行并罚,主要也是为了使对数罪的处罚能够贯彻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事实上数罪并罚制度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因此,对同种数罪不实行并罚也不具有必要性。当然,对同种数罪实行并罚与否,有时在法律效果上也会有所差异,但这一问题只能通过立法修改来解决,而不是为了单纯追求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法律效果而超越立法的规定进行司法。
二、犯数罪被判处的数个无期徒刑并罚时能否升格执行死刑
对于一人犯数罪被判处数个无期徒刑的,在并罚时能否升格执行死刑的问题,理论上有不同的见解:肯定说认为,这种情况中,尽管各个犯罪都未达到判处死刑的条件,但一个人犯数罪并被判处两个以上的无期徒刑本身就说明其社会危害性很大,因此,只有将被分别判处的数个无期徒刑合并执行一个死刑,才能体现罪刑均衡的原则;④否定说认为,死刑与无期徒刑虽然相差一格,但存在死与生的本质区别,而且肯定说的主张不适当地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与我国坚持少杀的死刑政策相违背,因而不能将数个无期徒刑升格执行一个死刑;⑤折中说认为,一般说来,不能将数个无期徒刑升格执行一个死刑,但如果一人所犯的两罪中,其中之一的法定最高刑是死刑,倘若他只犯这个罪,属于可杀可不杀的情况,而事实上他又犯了另一罪,并且分别看来都应当判处无期徒刑,那么,审判人员就可以根据整个案件的情况,对其中一个挂死刑的罪判处死刑,然后采用吸收原则,决定执行死刑。⑥
笔者认为,对于一人犯数罪并被判处数个无期徒刑的情况,尽管从总体上看,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及其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客观危害都相当大,只执行一个无期徒刑确实会存在处罚偏轻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只可能通过修改刑法加强对无期徒刑的执行(如推迟无期徒刑的减刑时间、严格无期徒刑的假释条件)来解决,在目前的条件下,不能单纯为了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将数个无期徒刑升格执行死刑。因为,虽然《刑法》第69条对于犯数罪被判处数个无期徒刑的情况如何并罚没有明确规定,但从该条规定的逻辑关系和无期徒刑自身的特性看,既然对这种情况不能实行限制加重原则、并科原则,那么自然应该采用吸收原则。而在数个无期徒刑之间不能吸收的情况下,只执行一个无期徒刑是当然的结果。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刑法》第69条对于犯数罪被判处数个无期徒刑的情况如何并罚没有明确规定,那么就不见得就非采取吸收原则不可,将数个无期徒刑升格执行一个死刑也不能说是违背了刑法。但笔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包括罪的法定和刑的法定。在一人犯数罪被判处数个无期徒刑且最终必须执行刑罚的情况下,在客观上刑法对并罚的原则没有明确规定而存在着数个可能的解释时,选择一个最不利于行为人的解释应当说是违背使公民对其行为的后果具有可预测性的罪刑法定原则。因此,肯定说不值得赞同。至于折中说,虽然较肯定说作了一定的限制,但将行为人所犯的另一个犯罪作为将可杀可不杀之罪的刑罚升格为死刑的条件,也不足取。因为,若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否认另一个罪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是不客观的。即便不考虑这个问题,那么在对一个罪判处无期徒刑的同时,又将其作为把另一个可杀可不杀之罪的刑罚升格为死刑的条件,也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而且,行为人所犯的数罪之所以能够单独判处无期徒刑,就意味着数罪之间根本不存在像牵连数罪之间那样的关系,而不可能将一罪作为另一罪的从重处罚情节。
三、所犯数罪被分别判处不同的有期自由刑时的并罚
对于一人犯数罪被分别判处不同的有期自由刑时如何进行并罚的问题,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折算说认为,首先将不同种有期自由刑折算为同一种较重的刑种,即将管制、拘役折算为有期徒刑或者将管制折算为拘役,然后按限制加重原则决定应执行的刑期。具体的折算方法是管制二日折算有期徒刑或拘役一日,拘役一日折算有期徒刑一日。⑦吸收说认为,应采取重刑吸收轻刑的规则决定应执行的刑期。⑧分别执行说认为,应先执行较重的刑种,再执行较轻的刑种。⑨折中说认为,对判决宣告的不同种有期自由刑,不应绝对地采用某一种方法进行并罚,而应依具体情况或者根据一定的标准加以区分,分别适用不同的方法予以并罚。其中,有的主张,以能否达到罪刑相适应为标准,对不同种有期自由刑,可以分别采用吸收说和分别执行说的方法进行并罚;有的主张,对于不同种有期自由刑,应依具体宣告刑的结构,分别适用折算说和分别执行说予以并罚;有的主张,对不同种有期自由刑,宜分别采取折算说和吸收说的方法实行并罚。⑩有限制的酌情分别执行说认为,对不同种有期自由刑,仍应采用体现限制加重原则的方法予以并罚,即在不同种有期自由刑的总和刑以下,最高刑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罚,其结果或仅执行其中一种最高刑的刑期,或酌情分别执行不同种的自由刑。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并于1981年7月27日起施行的《关于管制犯在管制期间又犯新罪被判处拘役或有期徒刑应如何执行的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管制犯在管制期间又犯新罪被判处拘役或有期徒刑的,应在对漏罪所判处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执行完毕后,再执行前罪所没有执行完毕的管制;对于管制犯在管制期间因发现判决时没有发现的罪行而被判处拘役或有期徒刑的,也应如此办理。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和司法解释的规定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不过,在现行的立法条件下,应当采取折算说的主张。因为,从《刑法》第69条的规定看,不管一人犯数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或者管制,还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显然均应采取限制加重原则实行并罚。既然如此,对于一人犯数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的,客观上就必须根据一定的标准将不同的有期自由刑折算成同种的有期自由刑,否则不能适用限制加重的原则。对于是将较重的刑种折算为较轻的刑种,还是将较轻的刑种折算为较重的刑种的问题,《刑法》第69条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考虑到在第69条将并罚后管制的最高刑限定为3年、拘役的最高刑限定为1年的情况下,若采用将较重的刑种折算为较轻的刑种的规则进行折算,则在有期徒刑的刑期较长时将其折算为较轻的刑种然后进行并罚,会因刑期不能超过并罚后管制、拘役的最高刑的限制而出现处罚过轻的问题;若为了避免这个问题而对这种情形采取将较轻的刑种折算为较重的刑种的规则,而对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情形采取将较重的刑种折算为较轻的刑种,则又会出现同样采取限制加重原则而折算的规则不一致的不妥。因此,比较而言,一律采取将较轻的刑种折算为较重的刑种的规则相对合理。
四、并罚时如何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
《刑法》第69条第1款规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对于决定执行的刑期时应当如何酌情,或者说应当考虑哪些情况,理论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具体酌定的内容应包括量刑情节、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最高刑以外的其他罪的处刑情况等因素。对于从宽或从严的量刑情节,应在对数罪的定罪量刑中分别体现,在对数罪并罚而决定执行的刑罚时不能在数刑的总和刑之上加重或在数刑中最高刑之下减轻,但在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时应予以考虑。因为,限制加重原则允许法官在决定执行的刑期时在一定的范围内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情决定,而案件的具体情况中理所当然应当包括案件中的从宽或从严情节。否则,酌情决定便无所依据,成为擅断的借口。(11)另一种观点认为,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时,不应再考虑各罪之法定或酌定的量刑情节。因为这些量刑情节已经在各罪的量刑中考虑过了,在决定执行的刑期时再予以考虑,有违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同时该观点主张决定执行的刑期时的酌情,应当是指考虑总和刑与数刑中最高刑之间的数量关系。如果各罪之刑接近,其总和刑期高,应在总和刑期以下适当下降以决定执行的刑期。如一人犯两罪均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为14年,酌情在7年至14年之间决定执行的刑罚,其执行的刑罚以11年左右为妥。如果各罪之刑悬殊,其总和刑期低,应接近总和刑期决定执行的刑期。如一人犯两罪分别被判处2年和7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为9年,其执行的刑期以8年为妥。(12)
由于各种法定的或者酌定的量刑情节在决定各罪的刑罚时已经予以考虑,在并罚时决定应执行的刑期时再予以考虑,确实有重复评价的不妥。因此,第二种观点考虑问题的思路是正确的。但能否像第二种观点主张的那样,在酌情决定应执行的刑期时只考虑总和刑期与数刑中最高刑之间的数量关系?笔者认为,如果这样的话,就似乎没有强调“酌情决定”的必要,因为这实际上把决定执行的刑期的标准变成了一个近似固定的数学计算模式,法官也没有什么自由裁量的余地。但刑法强调由法官“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既然客观上数刑中最高刑期与数刑的总和刑期之间存在一个幅度,刑法又规定须“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就意味着法官获得了在这个幅度内决定执行的刑期的自由裁量权,而不是按照一个近似固定的数学计算模式来决定执行的刑期。那么法官根据什么来自由裁量执行的刑期呢?当然要遵循裁量刑罚的原则,即依法根据犯罪分子罪行的严重程度包括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和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大小,来酌情决定应执行的刑期。但是,为了避免刑法的重复评价,这里应酌情考虑的不是各个犯罪自身的性质、情节、危害社会的程度以及各个犯罪中体现出的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小,而只能是因为数罪的存在才具有的那些反映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和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大小的因素和情节,如犯罪的数量、数罪中罪过的类型及其数量比较情况、根据各个犯罪的严重程度所宣告刑罚的轻重比较情况,等等。
五、在数罪并罚后刑罚执行完毕前发现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前有一罪没有判决的并罚
在数罪并罚后刑罚执行完毕前发现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前有一罪没有判决的,如何并罚?理论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原判决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如果对漏罪所判的刑罚不与原判决决定执行的刑罚实行并罚,而与原判决对数罪分别所决定的刑罚实行并罚,就意味着推翻前一判决或者否定前一判决已发生的法律效力,从而势必影响刑事判决的严肃性,因此,应当将对漏罪所判处的刑罚与原判决对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的刑罚,依照相应原则决定执行的刑罚。(13)另一种观点认为,判决宣告以前发现数罪的并罚与刑罚执行过程中发现漏罪的并罚,只是并罚的时间不同,所采用的原则和结果都应当是相同的,所实际执行的刑罚也应当相同,因此,只有把原判数罪的刑罚与漏罪的刑罚实行并罚,才更符合立法精神;(14)同时,若将对漏罪所判处的刑罚与原判决对数罪决定执行的刑罚实行并罚,则不仅会出现对有漏罪事实者实施的数罪两次适用限制加重原则进行并罚,进而可能造成轻纵罪犯之弊,而且,将原判数罪的刑罚与漏罪的刑罚实行并罚,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前一判决的法律效力,而是弥补其不足,增强其准确程度、强化其稳定性的合理做法。(15)
笔者认为,虽然对《刑法》第70条所规定的“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中“前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前个判决对数个犯罪分别判处的刑罚,另一个是前个判决对数罪判处的并罚后应执行的刑罚,但是应当正视的是,前个判决毕竟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如果不将对漏罪判处的刑罚与前个判决对数罪实行并罚后决定执行的刑罚实行并罚,无疑就是对前个已生效判决的否定,这当然是不妥当的。那么,能否因为第二种观点提出的理由而存在否定前个判决效力的必要性呢?笔者认为,将判决对漏罪确定的刑罚与前个判决对数罪分别判处的刑罚并罚,和与前个判决对数罪并罚后决定应执行的刑罚并罚,绝不仅仅是并罚时间的不同,由于两种并罚情况下,数刑中的最重刑与总和刑期均会不同,相应地,并罚后决定执行的刑罚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主张第二种观点的学者所谓的只有把原判数罪的刑罚与漏罪的刑罚实行并罚,才更符合立法精神的说法值得推敲。如果说采用第一种观点可能会造成轻纵犯罪之弊的话,那么由于采用第二种观点可能在比较多的情况下使数罪中的最重刑期降低和总和刑期升高,进而也可能出现重罪轻处或者轻罪重处的现象,因此,以仅仅存在这种极少数甚至个别的情况就要否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是不妥当的。再者,虽然采用第二种观点确实不是完全否定前一判决的法律效力,但也决不能认为是弥补其不足,增强其准确程度、强化其稳定性的合理做法。因为,如果前一判决确实存在问题,那也是需要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解决的问题,并非能够在对漏罪的判决中解决;如果前一判决不存在问题,仅仅从与漏罪并罚的角度认为其存在问题,那是不客观的。总之,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不宜采纳。
六、在犯一罪被判处刑罚后刑罚执行完毕前发现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前有数罪没有判决的并罚
在犯一罪被判处刑罚后刑罚执行完毕前,发现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前有数罪没有判决的,如何并罚?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观点:(16)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在对数个漏罪分别定罪量刑的基础上,首先对漏判的数罪合并处罚,然后将所决定执行的刑罚即执行刑与原判之罪的刑罚再实行合并处罚,并决定执行的刑罚;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首先对数个漏判之罪分别定罪量刑,然后将判决所宣告的数个刑罚即宣告刑与原判之罪的刑罚进行合并处罚,并决定执行的刑罚。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应当得到赞同。虽然《刑法》第70条规定没有直接明确“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是否应按照第69条规定先行并罚,但从“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的规定来看,由于第69条所谓的数刑均是指宣告刑,因此,应当认定第70条所规定的“后个判决的刑罚”,就是对新发现的数罪分别作出的宣告刑。
七、前罪被判刑后在刑罚执行完毕以前既发现有漏罪又犯新罪的并罚
对于前罪被判刑后在刑罚执行完毕以前既发现有漏罪又犯新罪的应如何并罚的问题,理论上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先按照漏罪的刑罚与原判的刑罚并罚,决定应执行的刑罚,然后再将新罪的刑罚与前一判决决定执行的刑罚中未执行的刑罚并罚,决定应执行的刑罚。(17)有赞同这种观点的学者进一步提出,即使在新罪被先发现并已并罚后才发现漏罪的,在实行并罚时也应先把漏罪与前罪并罚,然后再将该并罚后确定的刑罚中未执行的刑罚与对新罪判处的刑罚并罚。(18)第二种观点认为,对在刑罚执行期间再犯新罪并发现漏罪,采取分别判决、顺序并罚的并罚方法,只能适用于漏判之罪和再犯之罪被同时发现,或者漏判之罪先于再犯之罪被发现的条件下;至于再犯之罪被先行发现并已并罚后,才发现漏罪的条件下,只能在承认已有判决及并罚结果的基础上,将漏罪的刑罚与已有判决决定执行的刑罚并罚,决定最后应予执行的刑罚。(19)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先将漏罪的刑罚与新罪的刑罚,决定执行的刑罚,然后按“先并后减”的方法决定执行的刑罚。第四种观点认为,将原判之罪的刑罚与漏罪的刑罚和新罪的刑罚并罚,决定应执行的刑罚,再从中减去原判决中已执行的刑罚。第五种观点认为,应先将新罪的刑罚与原判之罪的刑罚并罚,决定执行的刑罚,然后将前一判决决定执行的刑罚与漏罪的刑罚并罚,决定执行的刑罚。(20)第六种观点认为,对漏罪和新罪分别定罪量刑后,将漏罪的刑罚和新罪的刑罚与原判之罪未执行的刑罚并罚。(21)
笔者认为,对于解决在刑罚执行完毕以前既发现漏罪又有新罪如何并罚这一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在实行并罚时既要体现对漏罪的并罚,也要体现对新罪的并罚,同时能够使并罚效果在总体上体现刑法对于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再犯新罪须从重处罚的精神,但不能以否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为代价。这是解决在刑罚执行完毕以前既发现漏罪又有新罪时并罚问题应遵循的基本思路。以此衡量上述观点,除第二种观点外,其他几种观点都值得商榷。例如,第一种观点的总体思路虽与第二种观点相似,但其主张对于刑罚执行期间再犯的新罪已经并罚之后才发现的漏罪、在实行并罚时也应先把漏罪与前罪并罚、然后再将该并罚后确定的刑罚中未执行的刑罚与对新罪判处的刑罚并罚,否定了先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这种以单纯追求实践中极少发生的个案的公正而牺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的严肃性、权威性的做法并不可取。第三、四、六种观点完全混淆了漏罪与新罪在并罚时的区别,违背了刑法规定对漏罪与新罪分别采取不同并罚方法所追求的对新罪处罚从重的价值取向。第五种观点完全颠倒了漏罪与新罪并罚的先后顺序,从而会使犯罪分子执行的刑期不当地缩短,甚至出现并罚后还应执行的刑期短于并罚前还应执行的刑期的问题,这显然违背刑法规定数罪并罚的宗旨。因此,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的主张。具体来说,对于在刑罚执行完毕以前既发现漏罪又有新罪的情况,应区分如下三种情形处理:(1)漏罪和新罪同时发现,并案处理的,应当先把对漏罪判处的刑罚与前罪判处的刑罚,按照《刑法》第70条的规定实行并罚,然后把对新罪判处的刑罚和对漏罪与前罪并罚后确定的应执行的刑罚中还没有执行的刑罚,按照第71条的规定实行并罚。(2)先发现漏罪,在对漏罪依法并罚后才发现新罪的,直接依照第71条的规定,把对新罪判处的刑罚和漏罪与前罪并罚后确定的应执行的刑罚中没有执行完毕的刑罚,实行并罚。(3)先发现新罪,在对新罪依法并罚后才发现漏罪的,应直接把对漏罪判处的刑罚和新罪与前罪并罚后确定的应执行的刑罚中没有执行完毕的刑罚,按照第70条的规定实行并罚。
注释:
①参见林准主编:《中国刑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13-215页。
②转引自高铭暄主编:《新中国刑法科学简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③参见樊凤林主编:《刑罚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5-456页;杨敦先:《关于先后奸淫幼女罪犯能否适用数罪并罚问题》,载《民主与法制》1983年第3期。
④参见高铭暄主编:《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1949-1985)》,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5页。
⑤转引自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07页。
⑥参见周振想:《刑罚适用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325页。
⑦参见周振想:《刑罚适用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332-337页。
⑧参见林准主编:《中国刑罚教程》(修订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97-198页。
⑨参见顾肖荣:《刑法中的一罪与数罪问题》,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137-139页。
⑩转引自赵秉志主编:《刑罚总论问题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73页。
(11)参见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08页。
(12)参见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下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35页。
(13)参见姜伟:《犯罪形态通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498页。
(14)参见唐大森主编:《现代刑法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
(15)参见赵秉志主编:《刑罚总论问题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91-492页。
(16)转引自高铭暄主编:《刑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17)参见姜伟:《犯罪形态通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504页。
(18)参见赵秉志主编:《刑罚总论问题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00-501页。
(19)参见顾肖荣:《刑法中的一罪与数罪问题》,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周振想:《刑罚适用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344-355页。
(20)第三、四、五种观点均转引自高铭暄主编:《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1949-1985)》,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8-499页。
(21)参见高铭暄、王作富主编:《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