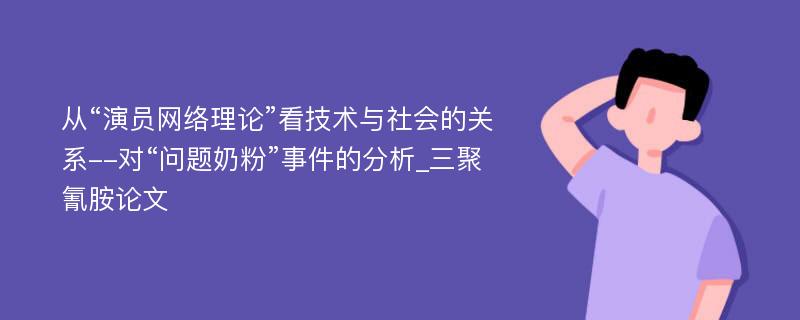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谈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奶粉”事件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奶粉论文,理论论文,事件论文,关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934(2009)01-0037-05
2008年9月,三聚氰胺奶粉事件震惊全国,世界注目。其实,早在数月前,某些地区就已经发生较多婴幼儿出现不明原因并集中罹患肾结石的现象。当时,在分析病因时,有人曾联想到奶粉问题(因为婴幼儿的主要食物是奶粉),并对可疑奶粉进行了检测。遗憾的是,当时得到的结果是:“被检奶粉合格”。这就把人们的视线引入歧途,放松了对奶粉的进一步追查,最终导致数月后问题在十几个省范围内的大爆发。问题爆发后,由于在患儿尿液中发现三聚氰胺的代谢物,然后倒推检测,才算查明事情的真相——在奶粉中混入了三聚氰胺!于是人们责问检测部门:原来“合格”的奶粉合的是什么“格”?为什么没有发现其中的三聚氰胺?这必将涉及到现行的质检技术以及“标准化”制度等深层次的问题,也正是在一种突发事件出现的情况下,人们开始从社会的角度重新审视科技的问题。
和其他西方现代学科相似,食品科学以及营养学的基础正是相信客观能够完全脱离于主观,“科学”地存在。在此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科技工作者致力于追寻纯净的客观物质,统一的客观理论,而人们往往忽视了正是在此过程中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实验室的工作正是理想状态下的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中介所在。笔者接触的许多中国、美国实验室工作人员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也在积极地参与创作这个世界,而并不是纯粹的客观性研究。“问题奶粉”事件,再一次证明现实生活中,任何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个体,包括人、动物、植物,甚至是实验室中的仪器,都以各自的存在和活动参与社会现实的建构。这也正是法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ANT(Actor-Network-Theory)理论的精髓所在。本文试图通过他的理论,以网络为背景再现“问题奶粉”事件,并对其反映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思。为给读者一个清晰的理论背景,本文在第一部分将简要地介绍一下布鲁诺·拉图尔和他的ANT理论。
布鲁诺·拉图尔是法国著名的科学社会学、科学人类学学家,在科技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1979年,布鲁诺·拉图尔和史蒂夫·伍尔格(SteveWoolgar)出版了《实验室的生活(Laboratory Life)》一书[1],第一次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引进了科技学的研究领域,它展现了实验室的研究是如何通过科学家们的常规惯例性质的工作展开的,其中包括做实验,发表论文,寻找课题及研究经费,以及其他一切微小琐碎不被人们关注的事件。该书的出版奠定了布鲁诺·拉图尔在科技学领域的第一人类学者的地位,改变了科技学学科一直以来的哲学研究倾向。学者开始关注科学家们鲜活的实际科研生活,以及与外界的社会人际互动。之后,布鲁诺·拉图尔又相继出版了《我们从来不是现代的》(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2],和《行动中的科学》(Science in Action)[3],借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尽管有人将他对科学事件的研究列为社会建构论的方法论,美国当代科学人类学界普遍认为:布鲁诺·拉图尔和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约翰·劳(John Law),师承一派,是actor-network-theory的奠基人和推动者。
Actor-Network-Theory,简称ANT,它挑战了认识论中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命题。该理论并不认为主体与客体、文化与自然、社会与科技之间有根本的划分和不同。首先,无论是人还是技术,各自的孤立存在是不具意义的。他们的意义体现在与其他个体的联系之中,正如约翰·劳所说,“If differences exist it is because they are generated in the relations that produce them.Not because the exist,as it were,in the order of things”,即“不同存在于制造不同的社会关系中,而不是存在于不同的秩序中”[4]。个体行动者不是停滞的、固定的,而是根据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同其他个体的关系而不断变化的。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个体包括人和技术都不是清晰的、稳定的,而是模糊的、多变的。以“问题奶粉”事件中的三聚氰胺为例,化工词典给予的解释是:一种三嗪类含氮杂环有机化合物[5]。这种精髓式的解释与存在本身并不能带来任何现有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它真正存在的意义却是当它与其他物质发生关系的时候,改变了现有的秩序。比如,当它用于制造业,可与甲醛发生反应,形成三聚氰胺—甲醛树脂;当它被不法分子用于食品工业,可以提高食品的含氮量,作为“伪蛋白”,以达到“凯氏定氮法”所测蛋白质含量的技术指标的目的;当它进入人体肾细胞中,和氰尿酸相遇,形成结晶体,沉积形成肾结石。在上述三种不同的关系中,三聚氰胺展现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要了解什么是三聚氰胺,必须把它放置在动态的关系网络之中,而不能孤立地谈论所谓的“特质”或“毒性”。
其次,为了批判性地对待科学技术,ANT将人和非人的科技、机构、市场主体等在认知论的层次上都称为“Actor”(行动者),他们都具有同样的行动能力。人的能动性很容易理解,而ANT提出的物的能动性就不那么显而易见。约翰·劳和米歇尔·卡隆给出了目前被学术界广泛引用的“电话”的例子来说明物的能动性。电话表面上是普通的被动的装置,但当它响铃的时候,它的被动形象就改变了,即使人们决定不接听,电话仍然激起了人进行决策的过程和反应。在这个例子中,电话就脱离了人而具有能动性[6]。从ANT出发,看待在“问题奶粉”事件中的“凯氏测氮法”,它就不仅仅是检测食品中蛋白质含量的一种被动状态下的技术手段,它本身也具有能动性(agency),因为它直接引起了很多其他社会成员的决策行动:如何增加奶产品中的含氮量?把技术和其他传统意义上的客体赋予主体性,有利于我们用动态的观点来审视网络中的每一种关系及整个网络的复杂性。
应用ANT理论思考蛋白质含量的检测技术,即把该技术看作是整个网络的一个行动者,可以有效地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从而最大限度避免科学简化主义带来的弊病。在“问题奶粉”事件中,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乳制品网络”:奶源(奶牛、奶农、养牛场)、乳制品加工企业、奶制品供应商、国家质量检测机构、销售商、消费者、医院等。这个网络建立的基础是“高蛋白乳制品可以提高婴儿的身体素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网络中那些被认为是“自然”的而非“社会”的因素,比如科技活动、实验室工作等,人们往往并不细究其复杂的过程,而是将之作为一个不需解析的整体拿来讨论。这被布鲁诺·拉图尔称为“黑箱”化(blackboxing),即如布鲁诺·拉图尔指出的:“科技的成功掩盖了它工作的过程。当一部机器有效地运转,当一个事实稳定地存在,人们只注意到它的输入数据和产出结果,而不追究其内部的复杂性工作。因此,科技越成功,它们就越不透明,越晦暗”[7]。譬如,该乳制品网络中的质量检验的实验室中的技术问题——“凯氏定氮法”。人们很少在意从事检测的科技人员在实验室中是如何进行“凯氏定氮法”的研究工作的,而只讨论其所出具的结果。从ANT出发,这一系列的研究、实验过程都是我们科学学者所应关注的,其中还要包括它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它的创始人的实验室活动的研究。
1883年,丹麦化学家约翰·基耶达(Johan Kjeldahl)提出将蛋白质经过一系列化学处理,把蛋白质中的代表性元素——氮剥离出来,转化为结构简单的小分子铵盐。然后通过检测铵盐的含量,再乘以系数,最后折算出原样品中蛋白质的含量。这显然是采用一种间接的方法。由于它解决了当时检测蛋白质的重大技术难题,而得到认可与肯定。由于这个方法符合“标准”应具备的“科学性、准确性、可操作性、可重现性,兼顾简便性和普及性”,而被确定为检测蛋白质的国际通行的“标准方法”,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当谈论“凯氏定氮法”与“问题奶粉”事件的联系时,无论是从事分析检测的科技工作者还是普通的消费者,都会认为它只是一个游离于主观世界之外的科技问题。显然,“凯氏定氮法”并不能鉴别最终形成铵盐的氮到底是来自蛋白质或是其他含氮的物质,是“不法”分子、“无良”企业利用“标准”上的漏洞,在奶粉生产的可能环节中加入了含氮量很高的三聚氰胺,将掺假奶粉变成“优质奶粉”而引起了悲剧的发生。这种评论反映了人们在潜意识中是将技术作为无能动性的客体对待的,也即“经是好经,只是让歪嘴和尚念歪了”,“技术是好技术,只是让坏人利用了”。可是这种看法恰恰忽视了这个世界是由“和尚念经”、“人利用技术”等一系列行动构成的,而不是“经”和“和尚”,“人”和“技术”,“主体”和“客体”两个独立可分的世界构成的。
ANT认为在网络中,由于每一个演员都具有行动的能力与各自的利益。因此网络的稳定性就取决于各个行动者利益的不断协调(translation)。而人与人之间的协调类似于共同利益的协商,人与物之间的协调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ANT认为,一项科技创新和发展本身就是同网络中的行动者的协调过程。研究的资助者、研究的目的及过程、研究的社会背景等因素的不同可直接影响到技术的选定。以“凯氏定氮法”为例,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基耶达当年承担的科研项目是检测用于酿造啤酒的不同谷物的蛋白质含量——“蛋白质含量越少,酿造的啤酒越多”。在有限的资料中,我们得知,当时基耶达受啤酒酿造商之托,从事啤酒生产的工业分析。他的“主要任务是测定啤酒及麦芽汁中提纯的酒精含量,……并需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系列的氮测定”[8]。因此,笔者推断,当时基耶达研究的目的可能不是把蛋白质含量作为一种营养成分,而是将其作为影响啤酒的酿制工艺和出酒率的因素之一来考虑的。然而,在检测奶粉及其他奶制品时,蛋白质的含量则是作为一种主要营养成分指标的——“蛋白质含量越高,质量越好”。这与基耶达的研究出发点“酿酒原料中的蛋白质含量越高,酿造啤酒越少”,正好相反。“凯氏定氮法”产生的详细研究过程资料的欠缺,尤其是研究过程中的“琐碎的不为人注意的小事”,比如当时的技术条件、设备的局限、人员的常规工作情况等等,从另一侧面反映出ANT理论的重要性。因为物的局限性恰恰是其行动能力的体现,它使得其他行动者的意图受阻,而必须与之协商进一步的行动计划。
“问题奶粉”突发事件将原有的乳制品网络的稳定性打破了,作为行动者的“凯氏定氮法”的检测能力自然受到了质疑。人们突然意识到了“凯氏定氮法”作为“检测食品中蛋白质含量”的“标准方法”,是以“样品中不含蛋白质以外的其他含氮化合物”为前提,而这种前提产生的时代背景并没有被明确地指出来。更为重要的是在紧接下来的一系列技术改进的提议中,大家始终是把检测方法作为一种被动的研究对象。可是我们忘记了,正是在“凯氏定氮法”与其他行动者的联系过程中,人们才会想到添加三聚氰胺,而这一点正是科技的能动性的体现。科技工作者开始研究该技术的缺陷,认为它在100多年前被提出,完全适应当时的科技水平,为蛋白质的检测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可作为乳制品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形成相对稳定的网络。随着科技和社会因素的发展与变异,原来稳定的网络被打破,人们必须通过改变网络某一节点元素的结构,通过协调,产生新的相对稳定。
在“问题奶粉”事件之后,国家标准和质检管理部门正在组织修订乳制品的有关“标准”,将“三聚氰胺”列为必检项目,并公布三聚氰胺的检测方法。然而,任何“正常”的产品中所含的固有成分和允许添加的成分都是有限的,而不允许存在或添加的成分却几乎是无限的。他们认为将三聚氰胺列成为奶粉的必检项目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将三聚氰胺作为“蛋白精”加入食品,这一行业性的秘密被揭穿以后,三聚氰胺成了过街老鼠,注目的焦点。可以预测,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再敢向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但谁又能保证不会出现“四聚、五聚”之类的新玩意呢?随着科技发展,新的物质正在源源不断地被发现、被合成,总不能把几乎无限多的不允许添加物质的名单都列入“标准”,都一一检测吧?
笔者在与分析测试方面的专家讨论的过程中,了解到他们的建议。根据目前科技水平的发展,可以采用两种新的方法检测食品中的蛋白质:第一种方法:鉴于可以直接检测蛋白质的仪器——高效液相色谱—高分辨率质谱联用仪(HPLC-IT-TOF)目前已有商品化问世,可用该设备直接检测食品中的蛋白质。但是该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①样品前处理复杂,要求尽可能除去样品中蛋白质以外的其他杂质;②仪器价格高昂(数百万元);③运行成本极高。目前只在少数研究机构配备这种仪器,短时间内难以普及,以此建立标准的时机尚不够成熟。第二种方法:需要将蛋白质中的氮一直转化到铵盐,将样品在近似于人胃酸度的条件下进行处理,使蛋白质水解成为18种氨基酸,然后用高效液相色谱仪分析各种氨基酸的相对含量,最后再以氨基酸的相对含量推算蛋白质含量。由于在这种条件下,其他含氮物质不可能生成氨基酸。在此基础上再用“凯氏定氮法”检测一下总氮,如果根据总氮含量折算的蛋白质的含量大大高于由氨基酸折算的蛋白质含量,真相即刻一目了然——样品中肯定添加了“伪蛋白”。这样设计出的“标准”就更加科学,漏洞要小得多。高效液相色谱仪的价格不算很高(10万元以下),一般企业完全可以买得起,具备普及条件。
笔者深信,由于“问题奶粉”事件对人们健康的影响,不久一定会有新的技术来弥补“凯氏定氮法”的不足。假设某一项提议得到了支持,并付诸实践,展现在大众面前的就又是一项科技创新或发展,乳制产品网络就会重新稳定。但是如果缺乏科学学、科学人类学,尤其是ANT对此项技术的研究,多年后,我们可能又忘记了这项技术产生的过程,忘记了技术是——行为者,是具有行动能力的,而把它作为一项被动的客体对待,从而将社会与科技、人与物分离起来,好像科技是存在于没有文化的真空状态中。这样的弊端在于,没有把社会问题与科技问题放置在同一平台上综合讨论,因而难以有效避免各个环节的脱钩。
在乳制品网络中,奶粉和“凯氏定氮法”这两个行动者是通过相关“标准”设立而彼此发生互动关系的。在这个过程中,就牵扯到了另外的行动者,即国家。国家标准GB/T 5009.1—2003[9]规定检测食品中的蛋白质采用“凯氏定氮法”。在这一与国家标准制定者互动中,“凯氏定氮法”被赋予了法律意义,这不同于它在实验室中和其他行动者的动态关系。就如同一个人穿上了法官的制服,他的角色和行动就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就成为国家公权力的行为者。作为标准方法,“凯氏定氮法”在于乳制品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的互动中,就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控制权力,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它同时也体现了现代权力对标准化、科学化、统一化的逻辑理念的追求。比如,国家标准GB/T3935.1—1996对“标准化”做出这样的定义:“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实际的或潜在的问题制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的活动”[10]。因此,作为标准方法的“凯氏定氮法”,必然要掩盖其产生的具体而特殊的社会历史政治条件,而展现其客观性、广泛性和通用性。
在“问题奶粉”事件引起的一系列有关食品安全、信任危机的反思中,在指责“无良”企业的违法和个别官僚机构的渎职行为时,人们认为添加“伪蛋白”和防止添加“伪蛋白”本身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因此,人们提议:在设计“标准”时,既要考虑冷冰冰、硬邦邦的易于量化的自然科学技术因素,又要考虑鲜活多变的难以量化的人文社会因素。人们要求在发展中不断完善“标准”,政府主管“标准化”和“标准”管理工作的部门要及时淘汰过时的“老标准”,组织设计制定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新标准”。笔者认为,这一系列的良好愿望仍然是建立在将自然与人文、客体与主体分离的现代二元论基础之上。这种二元论哲学体系是现代权力制度运行的基础。标准化制度正是现代管理模式的典型代表。它的局限性在于掩盖了世界的多样性、多变性、特殊性和具体性。布鲁诺·拉图尔认为[2],现代社会正是不断地创造一个纯粹的客观世界。然而,它试图掩盖的却是客观世界被分离的一系列动态过程,包括人的活动也包括物的活动。可是恰恰是在这一过程净化(purification)中,产生出许许多多的自然与社会、科技与文化的混合体(hybrid)来。现代社会的问题更多展现的是复杂的网络,比如环境问题,早已超越了科技领域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这种复杂性也从“问题奶粉”事件中得以体现。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行为者的活动都会引起整个网络的不安与躁动。当一个社会越来越现代的时候,人们会发现人和物、科技与社会越来越融合。如果我们还固守西方二元论的哲学思想去观察认知世界,我们就会感到疑惑和迷茫。
表面上,ANT赋予我们一个社会学的视角去观察认识科学技术,但是它更为深层的意义却在于:它打破了社会(society)和自然(nature)的绝对意义上的区分。正如布鲁诺·拉图尔在他的《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一书[2]中指出的:“任何世界上事情都是两者的杂交体(hybrid)”。布鲁诺·拉图尔进一步挑战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严格意义上的所谓“社会”抑或“社会性”的,因为这种提法本身就建立在社会和自然的区分的假设基础之上,似乎是存在人和物两个有本质区别的世界。其区别在于人是主体,物是客体;人有主观性,物只有客观性;人可主动地改变物,物只是被动地接受改变。ANT的发展赋予物和人同等的能动性,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二元论的哲学思想,从而避免了“sociologism”和“technologism”两种极端的出现。布鲁诺·拉图尔认为社会是科技的社会,科技是社会的科技。正如他所言,“我们从未面临客体(objects)或者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我们面对的是人和物组成的链(chain which are associations of humans……and non-humans)……没有人见过纯粹的单一的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 by itself)……也没有纯粹的单一的科技关系(technical relation)”[11]。从“问题奶粉”事件中凸现出的“乳制品网络”恰恰展示出了这个复杂的科技—社会的现实世界。将科技仅仅作为受动的客体,不去深究其产生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甚至是文化条件;同样,将社会分离于科技之外,不把科技作为重要的社会行动者,而照搬挪用具体的技术与社会制度,都必将引起一系列的无法预知的科技—社会问题。
标签:三聚氰胺论文; 行动者网络理论论文; 中国奶粉论文; 蛋白质结构论文; 凯氏定氮法论文; 蛋白质论文; 奶制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