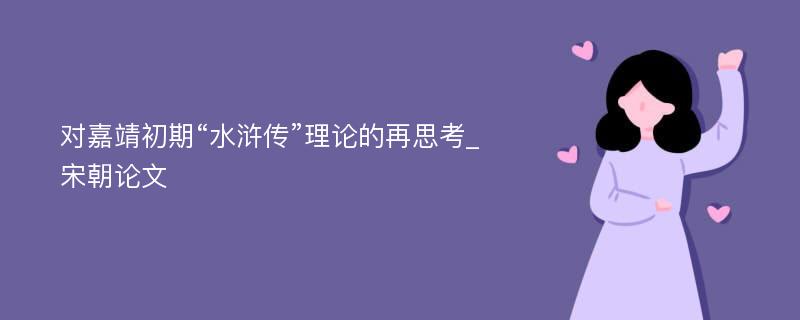
《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说再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浒传论文,嘉靖论文,初年论文,成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5)04—0109—03
我的《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几个“内证”考辨》一文发表后,在读书时陆续又发现了一些证据,但只是记入了我的读书札记,并没有写成文章;我那篇文章也确实是偶然得之,无论是书证,还是分析,都很不充分,但自信是言之成理的。最近又读到石先生的答复文章《〈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续考》(《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对我上文的商榷一一做了答复,继续坚持“嘉靖初年说”, 同时对我的商榷意见提出反驳。读后觉得有必要再写一小文,谈谈近一年来对这一问题的一些新发现和新想法,也算是对石昌渝先生“答复”的答复吧。
首先要感谢石先生的是,他指责我上篇文章引证多“只引片断之文”,因此他在大作中将我“略去”一些内容“恢复”,从而使我引证的背景和内涵更加清楚了。说实话,我那样做并非想偷懒省事,更非只看那个“词”而不管其内涵。那样做的唯一原因是遵照刊物的要求,文章不能写得太长,因此引证和分析只能选择最重要的部分,点到即止,无法像石先生这样长篇大论地展开和发挥。好在石先生的文章已经补足了这一点,相信读者将两文对照着看,会很清楚的。
第二是要弄清楚我们讨论土兵、用银、腰刀等问题的出发点。对这些问题本身的研究,坦率地说我属于“外行”,但如果把握住考证《水浒传》成书年代这个目的,那么对有关历史材料的分析就会有的放矢,不至于离题万里。以“土兵”为例,我是要证明宋、元、明三代皆有土兵,而且其形态、职能一向是多方面的,所谓“政府编制中的土兵”和“地方豪族组建的自卫武装”两种情况也是三个朝代都有的,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由宋代的“战斗部队”向明中期以后“衙役”转化的过程,因此,土兵这个问题是不能作为《水浒传》创作年代的证明的。
特别要说明的是,南宋时期土兵和官兵被“私役”的现象非常严重,有关文献很多,这里再举一例。宋代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七十四载绍兴年间“军制之弊”谓:“夫习击刺攻骑、射履行阵,固兵矣;擎肩舆、供伎巧,服厕役,又兵乎?今自一州守贰,下至宫观里居之士,皆破兵为白直,冗占私役,诡名重垒,其弊百出,……”还可以参看《宋史》卷三百七十五《李邴》、卷四百六十五《外戚下》等等。这说明,南宋时期,相当一部分土兵在各种名目下被“民化”了,所谓“擎肩舆、供伎巧,服厕役”,已完全丧失了土兵的职能,导致南宋军队战斗力的严重下降,这种状况便是叶适在《水心集》卷五《终论二》中疾呼的:“古者民为兵,今者兵为民,宜其消惰犀弱而不可制也。”这里所谓“为民”,就包括如《水浒传》中描写的那种几乎成为长官家丁的那种情形。官兵尚如此,土兵被私役就更是司空见惯的事,可以说这是南宋的一种普遍风气,而且集中在江浙一带。这些史料就为那个时期诸多文献中关于禁止私役土兵的诏告、文告等提供了背景。《水浒传》所描写的土兵不是与此更相像吗?何以一定要来自明代中期以后的“生活经验”呢?认真考察有关史料,《水浒传》的作者为元末明初施耐庵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在没有找到更直接、更确切的证据前,不可轻易怀疑古人的说法。
明代嘉靖以后的土兵情形也并非只如石文引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说的那种情况,因此我称为单文孤证。明人叶春及《石洞集》卷八《兵食议》第一条即为“议土兵”,谓:“夫今之所以重客兵者,岂未睹其害耶!”文中列举了客兵之“五害”,如客兵远离父母妻子、无乡党之亲、不习地里、养兵费用过高等等,然后论证“知其害,则土兵之利可推也。”该文的核心观点是阐述土兵之利,主张大力发展土兵。这里,“土兵”与“客兵”相对,很清楚地表明了土兵地方军队的性质。文中丝毫看不出当时土兵已经“形同衙役”的情形。而叶春及正是嘉靖年间举人,其所记也是嘉靖以后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二谓:春及字化甫,归善人,嘉靖壬子(1552年)举人,官至户部郎中,事迹附见《明史·艾穆传》。……艾穆官四川巡抚时,春及为宾州知州,尝举以自代。所著政书,井然有条)。这表明,无论是宋代还是元、明,土兵的多种形态是并存的,并且三朝情况很相似。陆容、沈德符的记载是实情,叶春及的记录也是实情,而且是更直接的实情,而非如陆、沈两书的小说家言。当然,它们同时并在,并不矛盾,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因此我认为,仅根据土兵这一点,是很难判断出某种情况必是宋代或明初的,某种情况必是明中期以后的,以此来推导《水浒传》的创作年代证据不足。至于石先生所谓“土兵”和“土兵制度”的区别,我以为是不必争论的,因为什么叫“制度”是可以有多种解释的。
第三,关于元朝民间已使用白银进行日常交易以及腰刀产生的年代问题,我可以再提出几条证据供石先生参考。石先生承认我引用的那几部元杂剧及其时代都没有问题,但批评我引用的是新编的《全元曲》,而《全元曲》依靠的主要底本为明代臧懋循所编《元曲选》,臧又以改动元剧文本著名。似乎我对此毫不了解,因而犯了不究版本的“考据学大忌”。石先生暗示,我引用的文字可能是经过臧懋循修改过的,算不得真正的元代文献,故不足为据。
说实话,元杂剧戏文中出现用银子交易的描写不止那几处,石先生若有兴趣,也不妨“用电脑检索”一番。我引用时,是充分考虑到代表性和版本问题的,只是在最后表述时,为了简明统一,同时根据“后出转精”原则,只使用了《全元曲》的文本。最重要的是,我使用的那几段引文,用现存的各种元曲版本校勘,都是如此,不存在任何异文,换句话说,所谓“版本问题”根本就是不存在的!石先生信不过《全元曲》,我不妨再举几部当代元曲学者的著作,分别是王学奇等校注《关汉卿全集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王学奇主编《元曲选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这几部元曲集并非只用《元曲选》,而是参考了当今所能看到的包括《元刊杂剧三十种》、《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等在内的几乎所有元杂剧、戏文的各种版本,精心校勘而成的,凡有异文,必定出校。我核对过这几部书,可以证明,至今我们所能看到的元曲版本,那几处引文是没有问题的。略将几部著作引文的有关页码列出,以供查对:《杜蕊娘智赏金线池》楔子引文见《关汉卿全集校注》第288页;《杜蕊娘智赏金线池》第三折引文见《关汉卿全集校注》第310页;《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楔子引文见《关汉卿全集校注》第545页; 《郑孔目风雪酷寒亭》楔子引文见《元曲选校注》第2543页;《须贾大夫谇范叔》第二折引文见《全元戏曲》第661页;《冯玉兰夜月泣江舟》第三折关于“腰刀”的引文见《元曲选校注》第4390页。
当然,即使如此,只要经过明人之手的,仍然免不了“被明人妄改”的嫌疑,毕竟,传世的元刊本杂剧是太少了!石先生要我“证明引文为元刊本原有而不是臧懋循后加的”,仿佛向我索要所谓“宋版《康熙字典》”,我只能徒唤奈何了!还好,我想起《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来,这应该是学术界公认的没有经过明人“妄改”的元代戏文了吧,即使它也不能算作元代文献,但总是明初的吧。于是找来翻检,没想到一查就得,《小孙屠》第三出《李琼梅卖酒》中,便有这样一段对白:
(生白)酒钱多少?(旦)这个不妨,看官人与多少。(生)略有些小银子,权当酒钱。(旦梅)谢得官人!(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7页)
谢天谢地!真该感谢洋鬼子们手下留情或一时疏忽,给我们留下些《永乐大典》的残卷。那么这些说明了什么呢?臧懋循固然改动过元杂剧的文字,这是事实。但究竟他是以怎样的动机修改的?修改的具体情况又如何?这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我们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他要修改诸如用什么东西买酒、用什么东西杀人这些情节的动机。据我看,他改动最多的是在增加文采、更适宜阅读方面。
再谈谈腰刀的年代问题。我新发现的两条证据,其一是宋代梅应发、刘锡同撰《宝庆四明志·四明续志》卷六的记载:“宝祐六年八月,……丞相吴公开藩以来,抚御阅习,纪律素严,淬砺缮修,器甲素备。”其后记其军队装备有:“……长枪一百二十八条、腰刀一百七十柄、弩二百枝……”其二是宋代周应合撰的《景定建康志》卷三十八《武卫志》的记述:“给军器衣甲付各屯椿管以备使用”,其下列“……弩箭六万二千八百只、腰刀二千五百一十二把……”。
这里,腰刀是和其他许多兵器并列在一起叙述的,应该不会是别的什么东西。这表明,至晚在南宋时期,腰刀就已经是一种常见的兵器,在军队中使用量很大,相当普及;可能由于形制相似,到元代更与蒙古人所谓“环刀”混为一谈,笔者上篇文章谈到的《蒙古帝国史》中记载“环刀”的发音与“腰刀”相似,可能是来自汉族人的称呼。但无论如何,这两条宋代的材料总可以证明腰刀绝非什么“明代中期才有的新式兵器”吧。当然,石先生可能还会拿“版本”来质问,我先交待,这里用的版本是四库全书本,至于这些枯燥的史料是否也经过了四库馆臣的“毒手”,笔者真是无能为力,不敢判断了。
石文还说:“梁山好汉们挎着腰刀跨乡走县,在大街上游来荡去,这种情形断不可能发生在宋朝,更不可能发生在元朝,也不可能发生在明代前期。”说得相当肯定。对此,我只想举出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一首诗,题为《十山歌呈太守胡平一》,诗有小序谓:“螺冈市上恶少为群,剽掠行旅,民甚病之。太守寺正胡公命贼曹禽其魁,杖而屏之远方”云云。其第六首写道:“王黄二盗久驰声,手棒腰刀白昼行。逢著村人持一物,喝令放下敢谁争。”(《全宋诗》第4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51页)这是说有王姓黄姓两个大盗,手持棒,腰挎刀,白昼出行,抢劫行凶。此诗属于典型的“白描”手法,其真实性当没有问题。朝廷有禁令,固然是事实,但就是有人“手棒腰刀白昼行”,是否“合法”与是否存在完全是两回事,恐怕哪个时代也都会有这类事吧。再说,《水浒传》中的那些好汉们可不是什么普通“百姓”,而是地道的“山贼”啊。按石文的说法,明代正德以后,刀、枪等兵器似乎已不在禁止之列,老百姓都可以“大摇大摆”地挎刀出行了,这才给了《水浒传》作者以“生活经验”,这又有什么根据呢?《明会要》所记也只能证明当时在准许“私家制造”方面部分开禁啊!
关于《水浒传》中的子母炮是否就是明人所说的“佛郎机铳”,我认为不仅是一个单纯资料考证的问题,更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即:我们是否允许和承认一个小说家可以超越他的“生活经验”和时代环境,虚构出一些东西来?如果石先生对此持完全否定的态度,那么再争论下去就完全没有必要。我的上篇文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里不再赘述。
最后我想说的是,向来考据学有所谓“说有易,说无难”的说法,盖说“无”必须穷尽文献,哪怕只遗漏了一条重要例证,都不能证成其说;说“有”则只用枚举法即可,哪怕举出的只是一个“例外”,也总能说明些问题,相对来说就容易多了。客观地说,石先生面对的问题比我面对的要复杂和困难得多,假如他的研究真的有所突破,当然也更有意义、有价值得多。我倒真心希望石先生能够充分利用一下现代化的文献检索手段,穷尽有关研究文献,或许会得出些更切实的结论来的。与石先生文章同期发表的李铎、王毅两先生的文章已经作出最好的说明。
收稿日期:2005—04—28
